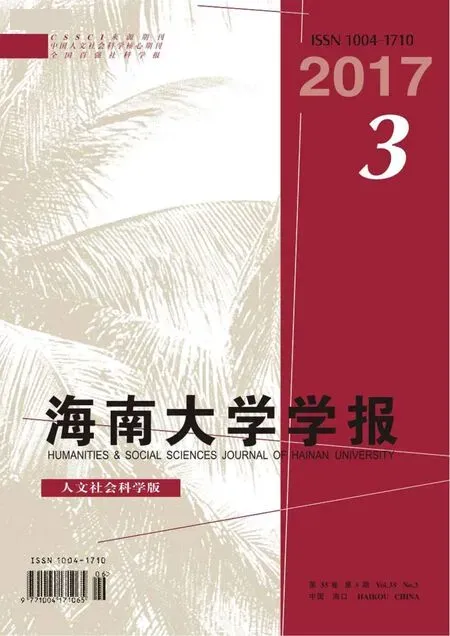科学与德性相容吗?
——卢梭《论科学与文艺》中的修辞策略
龙卓婷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科学与德性相容吗?
——卢梭《论科学与文艺》中的修辞策略
龙卓婷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卢梭既反对启蒙又支持启蒙的立场来自于他身份的双重性及与此相应的双重修辞。他宣称科学与德性不相容,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奉劝常人远离科学或哲学,以保护常人的德性免受科学知识或知识的虚假形态之侵害,而其最根本的理由乃是为了防止启蒙对哲学本身的败坏。科学与德性实则并非不相容,而是少数极具智识的人才具有将之结合起来的能力,只有他们才能用真正的知识去启迪人民的德性。《论科学与文艺》已经包含了卢梭思想的关键要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即是卢梭政治与哲学的双重立场,这种双重立场是理解卢梭整体学说的基础和门径。
卢梭;《论科学与文艺》;科学或哲学;德性;双重修辞
卢梭文字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及其学说的复杂性给理解他的真实意图带来了诸多困难。这种自相矛盾首先体现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文艺》中。在这部令卢梭毁誉参半的作品中,最显著且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卢梭通篇都在强调,科学与文艺的进步会导致德性的堕落,即科学与德性不相容;然而,在第二部分结尾,卢梭声称像佛鲁冷、笛卡尔、牛顿这些具有巨大天赋的哲人,他们能把科学与德性结合起来,“把智慧传授给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一论》,第59段)[1]*《论科学与文艺》(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arts or First Discourse,以下简称《一论》)的中译文皆引自卢梭:《论科学与文艺》,刘小枫译,未刊。此译本未刊,因此仅在文中括号内标出段落数。其他中译有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英译本请参阅Rousseau,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 Uni. Of Cambridge, 1986/199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03年。。作为一位颇为深刻的现代思想家,卢梭真的自相矛盾吗?《一论》是卢梭的首篇论文,其中的自相矛盾是否可能是卢梭思想不成熟的结果?还是因为卢梭对科学和文艺的态度持有双重立场?卢梭要传达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的真理*卢梭并未区分科学与哲学。在古典时代,科学指的即是哲学,哲人对宇宙、对自然以及对整全的探讨,正是科学或哲学探讨的范围,科学与哲学的分野是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后。文艺则与科学不同,古典时代的文艺形塑城邦的习俗礼法,可以说,与科学或哲学相比,文艺与城邦和民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现代社会,文艺比科学或哲学更为通行,因此更具启蒙性。?
《一论》的确遭遇了诸多争议和批评。除了对《一论》中卢梭的惊世骇言的批评,也不乏对《一论》文章结构本身的批评:虽然文笔优美,博闻强识,却缺乏明晰的逻辑和秩序,前后矛盾,令人费解。卢梭在《忏悔录》中声称,在他所有作品中,《一论》是“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的作品[2]。但这并不影响卢梭对这篇作品的重视,他很快回应了那些他认为值得回应的批评,而回应文的篇幅加起来竟然是《一论》的三倍。在回应文中,卢梭再次捍卫了《一论》的立场:痛斥启蒙、抨击科学与文艺,而且他宣称他是在捍卫德性和真理。在1762年卢梭的自编文集中,他为《一论》增加了一个短小的“致读者”,他说,“如果这篇处女作以其值得的方式被接受,作者该会避免何等的悲惨深渊”(《一论》,“致读者”)。 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卢梭之所以受到批评和毁谤,是因为这篇文章从未获得公正的对待和正确的理解。卢梭把《一论》视为他的“主要作品”,蕴含了他“全部学说的萌芽”,是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基石[3]276。《一论》的确已经包含了卢梭政治思想的关键要素,在卢梭后来的学说体系中,这些关键要素得到清晰的表达和延续。我们可以设想,卢梭在《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或许是他刻意为之。换言之,卢梭对科学与文艺之不同态度的矛盾或许仅仅是表面上的,来自他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修辞。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卢梭“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赞扬科学与反对科学——赋予了不同的品格,或者他在《论科学与文艺》中说着两种品格不同的话”[4]282。本文试图通过细读卢梭有关科学与文艺的主张,厘清卢梭的自相矛盾之处及其真正的思想意图。
一、《论科学与文艺》的双重修辞
要理解卢梭的政治写作意图,首先得揭开他双重修辞的真正意涵。在《一论》一开篇,卢梭就声称,他打定主意,即便遭受普遍的非难,也要“忤逆人们在今天所热衷的一切”;而且,他从未指望获取公众的赏识,这里的公众指的是启蒙时代的“美妙才智”“风头人物”和“狂热分子”(《一论》,第2段)。因为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缺乏接触科学的机会并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的认知是由“公众”启发和塑造的,在本性上他们只是一群“在任何事情上都受自己感情奴役”的“人民”[4]81。公众则不同。由于天性的限制,他们不善沉思,“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的支配”(《一论》,第2段)。他们对科学与文艺抱有炽烈的热情,却缺乏审慎德性,会把自以为掌握的真理或知识传播给人民。真理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将会成为“孩子手中的危险武器”(《一论》,第34段)。卢梭在《一论》中所要传达的教诲首先针对的即是这些受自己炽烈热情蛊惑的公众,痛斥他们所宣扬的流俗意见和启蒙理念。卢梭断言,“他绝非是在攻击科学”,而是“在有德性的人们面前捍卫德性”(《一论》,第5段)。言下之意即是,正是这些启蒙心智搞大众启蒙,败坏了人们的德性。科学与德性不相容的真正意涵在于,科学与人们的德性不相容。为了捍卫人们的德性,卢梭才抨击科学与文艺,颂扬无知。人们的德性必须以无知为基础,因为只有无知,才能让他们避免遭受自吹自擂的启蒙的败坏。宣称“科学与德性不相容”是卢梭在《一论》中对公众采用的显白修辞。
因此,卢梭在《一论》中批判科学与文艺,是为了保护常人的德性免受科学知识或知识的虚假形态的侵害。在《一论》的结尾,卢梭自称常人,他说,“对于我们,平平常常的人们啊,上天绝没分配如此伟大的天资,也没命定[给我们]如此多的光荣,待在我们的蒙昧中吧”(《一论》,第60段)。卢梭写作《论科学与文艺》时,署名为“一位日内瓦公民”,这意味着,他以常人的身份奉劝常人远离科学或哲学、保持无知和蒙昧,是出于公民的义务为人民谋求根本福祉。但是卢梭声明,在科学与文艺是敦化还是败坏风俗这个问题上,他选择的立场是苏格拉底的立场。卢梭宣称“科学与德性不相容”实际上来自那一古典政治哲学的原理——科学或哲学与社会不相容。出于保护大众德性免受哲学侵害,卢梭必须向公众宣扬对整个政治共同体有益的显白教诲,即科学与德性不相容,或者说卢梭“科学与社会不相容”这一政治哲学原理得到了“科学与德性不相容”的支撑。因此,卢梭抨击大众启蒙或科学与文艺的普及,显得是在抨击科学与文艺本身。然而,卢梭抨击科学与文艺,最根本而且最首要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启蒙对哲学本身的侵害。无论什么时代,科学或哲学都只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卢梭反对启蒙,首先是因为他要保护科学或哲学本身免受民主社会的启蒙精神败坏。科学或哲学的流播不仅危害社会,也会危害到哲学自身。科学或者哲学一经普及,便堕落成一种时尚或蜕化成一种意见。卢梭既是从公民的角度也是从哲人的角度宣称“科学与德性不相容”,而如此宣称既是出于对德性的捍卫,也是对科学或哲学本身的捍卫。
卢梭的确真诚地信奉古典哲人的教诲,即天性命定研究哲学的少数人与不善沉思的多数人之间的差异无法摈除。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传统,区分了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宣扬与共同体不相抵牾的显白教诲,而隐微教诲则是出于哲学根本利益的考虑,向潜在的哲人揭示隐蔽的真理。卢梭声明,采用显白修辞或隐微修辞的衡量标准是真理是否有用。在1762年的《致博蒙书》中,卢梭坦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在一切有用的事情上说出[真理]”,在有用的真理上,他会“坦率、坚定地向公众说话”[4]114。所以,在《一论》的前言中,他就陈言他“不会去探究种种形而上学的微妙”,而是要讨论“与人类幸福攸关的诸多真理之一”(《一论》,第1段),即是因为,形而上学的真理对于人类幸福而言毫无益处,它们无法成为人民德性的基础。既然如此,卢梭为何还要隐蔽地宣称“科学与德性相容”?难道“科学与德性相容”就是卢梭要向少数真正的哲人揭示的隐微真理吗?
在《一论》中,卢梭一开始就拒绝为“受自己时代、国家和社会意见支配”的公众写作,他说,“为了超逾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而写作”(《一论》,第2段)。他只希望获得某些个贤哲之士的赏识,这几个贤哲之士显然指的是那些真正具有哲学天赋而且天性命定研究哲学的人。在随后为《一论》所作的辩护中,卢梭再次区分了两类读者:
我论述自己的观点,仅是也总是为了少数几位读者。我所珍视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真理,为的是让真理更能让人接受,使得它更有用。通常,我试图把长久的冥思,注入到看似随意抛出的一段话、一行文字、一个语词中,这往往徒劳。我的大多数读者时常发现我的论文结构混乱、几乎完全没有条理,他们无法看到树干,我仅仅向他们展示了树枝。但对那些懂得如何理解的人来说,这已足够,我也从未想过向其他人说话。*参见“致博德斯第二书前言”,笔者根据古热维奇的英译本译出,见Rousseau,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 Uni. Of Cambridge, 1986/199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03年。[5]110
采用字里行间的修辞策略是古代政治哲人进行双重教诲的方式之一。卢梭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一论》中采用混乱的逻辑秩序、晦涩难懂的风格、含糊等修辞手段,是因为他要让少数几位具有哲学天性的读者仅仅从一些看似随意写下的段落、文字和语词中领会他“长久冥思得出的结果”[5]110。 因为卢梭天性上是哲人,恐怕对他而言,向少数命定研究哲学之人揭示他长久而深入的沉思才是更为迫切的事。对真正的哲人而言,“种种形而上学的微妙”才是最值得探究的真理。正如卢梭后来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中所表达的那样,“普遍而抽象的真理是一切好东西当中最珍贵的”[6]。在《一论》的最后,卢梭花了不到600字的篇幅揭示“科学与德性相容”,实际上是在教育引导那些真正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使之明白,哲学生活高于社会生活。卢梭把这一隐微的真理隐藏在了其显白的教诲——“科学与德性不相容”——之下。然而,卢梭说,即便是为少数几位读者揭示的真理,也要让它更有用。卢梭断言,纯粹的哲学生活对社会而言是无益的,也就是有害的。少数极具智识的人也应该尽到公民的社会义务,“把智慧传授给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一论》,第59段)。在卢梭看来,并非科学与德性不相容,而是只有少数极具智识的人才具有把科学与德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因此,只有极少数人才被赋予了启蒙和教育人民的特权,他们具有理性和洞察力,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看到“高贵的好胜心所激发出来的德性、科学和权威以及为了人类的幸福而通力合作能够取得何等成就”(《一论》,第59段)。他们能让科学与德性相容,让科学或哲学为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服务于德性。如此看来,卢梭的自相矛盾的确是表面性的,他所要传达的是双重真理:对于启蒙智识人或公众,他告诫他们“科学与德性或社会不相容”,而对另一类具有巨大天赋的极少数人,他启迪他们用真正的知识去启蒙人民的德性。不过,要理解卢梭的真实意图,就得认清卢梭所说的德性到底是怎样一种德性?
二、卢梭对科学与文艺的政治批判
卢梭在《一论》中宣称“科学与德性不相容”,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科学与文艺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科学与文艺滋生“纤巧而又精制的趣味”“温软性情以及城市化道德”(《一论》,第9段)。人们的种种原则和道德风尚因科学与文艺的盛行而变得趋同,永远是“卑鄙而又具有欺骗性的同一副面孔”;得心应手的社交、文雅得体的举止、造作的语言,掩饰了灵魂的琐碎、渺小和毫无德性。伪善披上了仁慈的面纱,让人们“显得具有根本就没有的任何德性”(《一论》,第9段)。科学与文艺的精微细腻为虚假的公共意见提供土壤,更严重的是,这种不合理的偏见变成人们行事的规矩和原则。处在这样一种虚假的意见之中,人们不可能形成健康合理的德性。伴随着科学和文艺兴起的,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冷漠,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真正的友爱、敬重和信任,社会的纽带变得松散了。爱国的热情、民族的仇恨也随之消失*可以对观“纳喀索斯序言”中相似的表述:“正是对于哲学的爱好,使得尊重与仁慈的纽带关系变得松弛,而正是这些纽带将人同社会联系起来……”哲学破坏了人的情感,也就破坏了社会的德性基础。转引自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胡兴建、黄涛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13年, 第291页,注释2。。文艺与科学培养的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和一种谨小慎微的趋利避害心理。总之,科学与文艺根本无法为各种具体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品性类型进而为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德性基础。
卢梭从历史上去寻找证据:“虚妄的好奇心惹来的这些坏的起因与这世界一样古老。”(《一论》,第16段)他证明,越崇尚科学与文艺的民族,恰恰是最受累于科学与文艺的民族,他们往往会受到那些尚武民族的羁轭。科学和文艺的确带来博学,但也让人沉湎于感官享受,奢侈之风盛行,削弱人身体的活力和生气;科学与文艺无法激发勇敢德性,削弱我们爱国的热情以及保卫祖国免受羁轭的牺牲精神;因此,随着文艺的进步和道德风尚的解体,异族人的轭便接踵而至。作为“全球第一所学校”“哲学和美术之母”的埃及很快就被冈比斯以及其他民族征服;两度战胜亚洲的希腊,文艺进步的后果就是“被奴役”以及“频繁地更换主人”;“昔日的德性殿堂罗马”因奥维德等下流作家而最终沦落;君士坦丁堡的启蒙带来了荒淫、败坏和邪恶;科学也并未让中国人民变得“智慧、自由和不可战胜”,启蒙和“法律所宣称的睿智”“也无法让他们免于无知而粗野的鞑靼人的轭”(《一论》,第17~21段)。最坚韧强健的民族是那些从未被空虚的知识所累而崇尚德性的民族:波斯人、斯基忒人、日耳曼人、贫困和无知时代的罗马以及卢梭的日内瓦共和国,正是他们的“质朴、单纯和种种德性”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保有勇气和忠贞,并成就了他们的伟大*马斯特注意到,卢梭所驳斥的五个民族全都建立了帝国,而他所称颂的五个民族是“独立而自由的国家”。他认为,卢梭对启蒙的道德批判的背后是对征服与帝国的政治批判。参见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第293页。笔者认为,卢梭分别驳斥和称颂的五个民族并非是对征服与帝国的批判,而是出于建立卢梭心目中理想的共和国的想象(参见卢梭:《献给日内瓦共和国》,见李常山著、东林校:《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1、53页)。卢梭认为,公民社会必须是封闭的,健康的公民品格基于一种“民族性的哲学”,因此,即便卢梭批判征服和帝国,也是对一种普世化的哲学价值的批判。。
最显著的例子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卢梭在此把斯巴达作为有德性的共和国的典范,而雅典则成为信奉虚妄学说、施行僭政的例证。但在有关《一论》的回应文中他谈到,将两个民族进行比较“在某些方面总是缺少精确性”,应该“追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将其中知识的发展与其道德风尚的变革相比较”[3]297。卢梭的确倾向于比较各个民族历史的不同时期:两度战胜亚洲和最后被马其顿人征服的希腊、君主制和共和制下的罗马;在《二论》的献词中,卢梭显然把雅典当作民主制的模型,(《二论》,献词),在此,他大肆驳斥了雅典的僭政。卢梭实际上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野蛮状态(即《论不平等》中所称的自然状态)、尚未败坏的德性时期、已经走向堕落和不幸的状态。与之对应的德性状况是:自然人纯朴无知的德性、尚未败坏的社会中的“质朴、单纯和种种德性”、腐败的社会状态下败坏的德性。通过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进行历史考察,卢梭试图表明,无知与德性、科学和文艺与堕落总是相伴相生的,科学与文艺的盛行会让公民失去德性,一失去德性就会走向衰落,并且遭受奴役*接下来我们看到卢梭援引苏格拉底,通过审查学问人和艺人们的自负和肆心,提醒雅典人远离这些虚妄的科学,并赞颂无知和德性的价值。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同,卢梭的苏格拉底似乎不仅对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无知,而且一无所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自知无知,指向的是知识,他知道自己对高贵与好的无知,所以要去探求高贵与好;而卢梭的苏格拉底自知无知,指向的却是无知。“他一无所知,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就不怎么样”(《一论》,第4段)。卢梭的苏格拉底是反哲学的苏格拉底。有关卢梭对苏格拉底的持守和背离,参见Clifford Orwin:《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Rousseau’s Socratism),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8(60):174-187。。
卢梭似乎同时也在论述“科学与共同体或社会不相容”——这是否偏离了主题?实际上,“科学与社会不相容”和“科学与德性不相容”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论题是相关的。换言之,卢梭抨击启蒙,凭靠的是古典哲人的立场:科学或哲学与社会之间的不相容。他援引苏格拉底、赞颂罗马政治家,所捍卫的却是这样一种德性:它是“淳朴灵魂的崇高科学”(《一论》,第61段)。这些“淳朴灵魂”,本来是一群正直之人,正是科学与文艺的流播亦即普遍启蒙让他们变成了一群追逐个人利益的松散的个体!尽管他抨击科学与文艺凭借的是自然德性之名,却时不时将德性置换成政治德性。卢梭的政治哲学难题即在于此:如何将这群松散的个体变成承担社会义务的公民——政治上的好人,而非一群伪善的、没有爱欲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者?因此,必须抵制启蒙,抵制科学与文艺的流播,保护人们的德性——“淳朴灵魂的崇高科学”。而卢梭对于德性的解释,却来自他的启蒙前辈孟德斯鸠,即德性是一种情感或一种“良知”,一种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它需要灵魂的力量和生气来获得。淳朴灵魂的德性只可能来自无知,来自灵魂的力量和生气。科学与文艺的盛行,消耗了灵魂的力量和生气,也就是侵蚀了政治共同体的德性基础,因此不利于形成一个健康、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卢梭似乎超越了他的时代,思考科学和文艺与德性以及社会的关系问题,其着眼点在于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稳固、公正的政治秩序及其基础。
三、启蒙对科学与文艺的败坏
难道卢梭注定要以德性之名,与科学和文艺为敌?科学和文艺与德性真的不相容吗?在第一部分的最后,卢梭否认了这一点,他声明,或许并非科学与文艺本身导致德性的堕落,因此,应该“进一步审查那些名分的虚妄和无聊”(《一论》,第35段)。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卢梭批判的并非科学与文艺本身,而是针对普遍启蒙,防止科学与文艺的流播。科学与文艺一旦流播,就会堕落成一种意见或偏见,堕落成一种虚假知识。卢梭意在提醒启蒙智识人,普遍启蒙只会对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受自身炽烈情感蛊惑的启蒙智识人,卢梭必须宣称,科学与文艺会损害社会和德性,或者必须显得是在驳斥科学与文艺本身。他旨在用有益的意见取代有害的意见。因此在第二部分,卢梭对普遍启蒙的批判显得更具修辞效果。他在注释中讲述了普罗米修斯发明科学的故事,提醒像萨图尔一样不适合科学与文艺的普通人要远离科学与文艺*这个故事来自普罗塔克。在后来的“致格里姆书”中,卢梭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故事:“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就是科学之火,目的是唤醒伟大的天才;萨图尔第一次看到火,向它跑去并且想要拥抱它,代表普通人受文学的绚烂光华所诱,轻率地投身到这项研究中;而朝他们喊叫并提醒他们的普罗米修斯,就是这位日内瓦公民……”转引自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300-1页。。
卢梭驳斥的是这样一种启蒙的现代意见,即认为对民众的启蒙可以为人类带来根本福祉。他继承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对“知识”与“意见”作截然区分,社会的基础是信仰和意见,但意见也可分为真实的意见和虚假的意见。卢梭试图将社会意见从同时代启蒙的虚假意见中解脱出来,因此,他必须告诫公众,科学与文艺本身诞生于虚荣和自负:“天文学诞生于迷信;雄辩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的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的自负”(《一论》,第36段)。卢梭对科学与文艺的起源的论述,就是某种程度的显白修辞。对普通人而言,关心的应该是“人的义务和自然的需要”,而非“毫无结果的沉思”(《一论》,第37段)。闲暇和虚荣滋生了科学与文艺,科学与文艺又反过来滋养闲暇和虚荣。对科学与文艺以及随之产生的愉悦的关注和关切,会损害对有用的社会活动的关注和关切。“对炫耀的趣味和对正直的趣味很难结合”(《一论》,第43段)。创作文艺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博得同时代人的赞誉,彼此取悦,这会让那些懒散、虚荣、不入流的流俗作家们降低自己的天资而屈从于大众的意见和品味。文艺与科学变成了精巧、矫揉造作和谄媚的筹码。科学与文艺让人们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关切上,这对政治社会而言是无可弥补的时间损失。这些不具有真正哲学天赋的人接触到哲学或科学,又导致了科学探究中成百上千的错误,这些错误或虚假知识一旦流行起来,就会损害政治社会的意见和道德。
闲暇和虚荣诞生了文艺,而文艺又带来奢侈。接着卢梭话锋一转,开始大肆批驳奢侈以及奢侈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他认为,奢侈只会导致道德风尚的解体,进而败坏整个共同体的品味。良好的道德风尚而非奢侈才是统治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此,有必要颁布禁止奢侈的法律。“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呢?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一论》,第41段)。他驳斥现代政治家从经济和商业的角度来估价人的价值,且断言,金钱无法获得“道德风尚和公民”(《一论》,第42段)。他再次从历史上去寻找证据,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富庶、显赫的民族往往被那些勇武而贫穷的民族所征服。卢梭对奢侈的批判实则是对现代商业共和国的批判,他试图证明,奢侈和财富不仅会损害德性,而且会损害一个共同体之稳定的基础*在《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中,卢梭提出,科西嘉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他们发展农业、从事农业。他认为,商业只能创造财富,农业才能保证自由。有关这一点的具体论述,参见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卢梭为何会转而批判奢侈和财富,以致看起来像是财富与科学和文艺合谋,共同破坏了政治秩序之稳定的基础呢?的确,卢梭声称,科学和文艺总是与奢侈和财富相伴相生。更确切地说,在一个崇尚财富、崇尚奢侈的社会里,科学和文艺就会盛行起来,而且,它们会堕落成一种“迎合我们矫揉造作的精巧”的精细文艺(《一论》,第44段)。因此,他批判奢侈首先是因为,奢侈所带来的是科学与文艺的堕落形式——看似精巧细腻的精细文艺。启蒙最大的佯谬就在于,它促使人民去关注这样一种对社会毫无价值的文艺。这种文艺会让人们把精力从有用的社会事务中转移开,忘记自己的社会义务;它们会拖垮身体,软化、削弱武德和勇敢,损害战士的品质;它们对人们的道德品质也有害,“大度、节制、仁慈、勇敢”以及敬畏,一旦科学与文艺盛行,这些德性就会消失不见;最后,这种精巧的文艺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卢梭反问:“如果不是天资的差异和德性的堕落在人们中间引出灾难性的不平等的话,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又是哪里来的呢?”(《一论》,第53段)“不平等”是科学与文艺或奢侈带来的所有后果中最显著且最危险的后果。一个文艺作品获得赞赏,并非因为它所具有的德性而是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天资,而人们又“更偏爱迎合人心的天资而非有益的天资”(《一论》,第54段)。卢梭大肆批判这些企图获得赞誉的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天资、财富与权力的结盟。
在这种结盟的过程中,印刷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印刷术的兴起为普遍启蒙提供了契机。正是印刷术,让那些不具哲人天性的普通人接触到哲学,这对他们而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倘若没有印刷术,这些灾难性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启蒙者们“写下的不敬神明的东西随着他们一起灰飞烟灭”,印刷术让那些危险的著作传世,“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危险梦想永久留了下来”(《一论》,第58段)。可以说,启蒙时代的环境比以往更加恶劣和危险。因此,卢梭在《一论》中采用双重修辞,就是要把所有不配接近科学的人从启蒙中解救出来,“设下种种障碍来守护缪斯女神的神殿”(《一论》,第59段)。更进一步说,他宣扬“科学与德性不相容”,是为科学设置可接近的障碍,把公民们从学问中拽出来,让他们投身到对社会有益的技艺中去。
四、卢梭的政治哲学意图
卢梭对科学与文艺的批判,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对普遍启蒙的批判。社会的基础是信仰和意见,知识的启蒙却让社会的信仰和意见受到极大冲击。卢梭之所以反对知识的传播,是因为他认为,“从知识到无知,只有一步之遥;各民族经常从一边走向另一边;然而从未有一个民族一经败坏,还能再恢复德性。”[5]50然而,倘若把无知和德性完全等同起来,那绝对是一种错误偏见。尽管在《一论》中,卢梭一再赞扬自然人的德性或自然之善,然而,却把自然人看作愚蠢的动物,在注释中,他援引蒙田嘲笑美洲野人“连裤子都不穿”(《一论》,原注三)。在卢梭的理论体系中,“自然人或好人”或者自然之善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指前社会的原始人或自然人,另一种则是真正自足、爱好沉思的哲人。既然卢梭认为原始人实际上是“愚蠢的、受到限制的动物”[4]147,那么,他赞美的自然德性则指的是真正哲人的德性,哲人德性才是真正的自然之善。卢梭批判启蒙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于,要保护哲人的德性不受启蒙时代的偏见所污染。
卢梭区分了两种知识:一种是真正的科学,另一种是僭越无妄的虚假知识。这种真正的科学是“形而上学的种种微妙”,是对整全的真正发现;而僭越无妄的虚假知识则是“那些个发散着我们世纪的道德风尚腐气”的作品,诸如“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危险梦想”(《一论》,第59段,第58段)。在此,卢梭似乎是在批判某种道德哲学。这两种知识无论哪一种的流播对社会和知识本身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但归根结底,后者的错误更危险。卢梭看到,“错误有无穷的结合方式,而真理只有一种形式”(《一论》,第38段)。即便发现了真理,也只有极少数具有巨大天赋的人才懂得好好应用。在《一论》的最后,他谈到:
如果一定得允许某些人献身科学和文艺研究,就只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感觉到有力量循着自己的足迹独步,而且超越自己的足迹;只有这些少数人才配去为人的才智的光荣竖起纪念碑。(《一论》,第59段)
为了防止“不义与暴力堂而皇之地获取正当与公平之名”[3] 330,哲学或科学必须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只有那些具有巨大天赋,并且能够用自己巨大的天赋去探寻宇宙的无垠空间之人,才能够进行科学与文艺的研究。他们可以充当“人类的导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识别哪一种知识或意见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德性之路。在《一论》的最后,卢梭表明,这些人类的导师可以进入君王的宫廷,“把智慧传授给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一论》,第59段)。在卢梭研究者欧文看来,这不仅像启蒙,甚至像是“启蒙的暴政”[7]。 而看看这些人类导师的名单——佛鲁冷、笛卡尔和牛顿,足以看出他对现代理论科学的忠诚。在《论不平等》中,他再次谈到,布丰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才是“哲学家们最尊敬的权威”,因为他们的论著建立在“坚实的崇高的推理”之上[8]。作为现代启蒙的典范,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是对宇宙和自然现象的一种科学认识,它们如何为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在马斯特看来,卢梭对牛顿、布丰等现代科学家的推崇,以及在《论不平等》中对现代科学视野的接受,这“在诸多方面对卢梭的思想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3]16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梭试图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回到古典思想对于人的理解中去。尽管卢梭在《一论》中驳斥了他的启蒙前辈,但他却接受了他的启蒙前辈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理论前提,即自然状态说。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卢梭彻底地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立场,他认为,人并不天生是政治动物。他对现代理论的忠诚决定了他必然遭遇的政治哲学难题:根据“公民社会要求的一致性”——即要求“契约的平等”和“约定的自由”[4]139,如何将像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自然人形塑成公民。卢梭在《一论》中对科学或哲学的普遍启蒙大加鞭笞,所凭靠的正是人的理智自然不平等这一古典政治哲学观念。然而,自然的不平等对于政治秩序而言毫无助益,或者说,自然的不平等无法有效地推出政治的不平等。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应该以所有人的自然平等为前提。卢梭致力于设计一个自由共和政体,这个政体能“培育出最富德性、最为开明、最为智慧、最好——就这个词最广的含义而言——的人民”[4]7他真正的自相矛盾即在于此,“他一方面主张立法权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人人参加立法活动”[9]。更进一步说,只有“一种能洞察人类的全部需要而又不受任何需要所支配的最高智慧”才能为这个自由共和政体立法[10]49。
把迥然相异的个体整合起来,变成致力于共同利益和福祉的公民共同体,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行动,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完成这项行动。身为自由共和政体的设计师,科学与德性是否相容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科学与民主政制或自由政体是否相容的问题。在卢梭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4]273。在《一论》中,卢梭之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扬“科学与德性不相容”,是因为启蒙的虚假意见破坏了公民社会具有德性与义务的生活,更进一步说,科学或哲学的普及抑或普遍启蒙让卢梭后来所宣扬的公民德性丧失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他必须诉诸公民德性,为民主政制或自由政体奠定神圣化基础。形塑公民德性的任务必须由少数极具智识的人来执行,或者说只有像卢梭这种具有德性的智慧人才能教导人们明白“他的种种义务和自己的归宿”(《一论》,第7段)。科学与德性实则并非不相容,而是需要极高的人为技艺才能使之相容。卢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只有理解了卢梭的思想意图,才能理解后来被称之为卢梭思想大逆转的那部著作——《社会契约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为之立法的社会,正是他此前称为人类所有堕落和不幸之来源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卢梭自己后来会积极地推行启蒙。卢梭的确是一个悖论式的政治思想家,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如何凭靠古典政治哲学的原理又凭靠现代科学的视野,来抨击或赞扬科学与文艺。
[1] 卢梭.论科学与文艺[M]∥刘小枫,编. 卢梭与我们.刘小枫,等,译.未刊.
[2] 卢梭. 忏悔录[M]. 范希衡,译.徐继增,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4.
[3] 马斯特. 卢梭的政治哲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4] 刘小枫. 设计共和[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5]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M].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03.
[6] 戴维斯. 哲学的自传——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思》[M]. 曹聪,刘振,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83.
[7] Clifford Orwin. Rousseau’s Socratism[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8(60):174-187.
[8]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 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2.
[9] 王辉. 略论卢梭的立法权思想[J].江淮论坛,1987(5):103-105.
[10]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孙绍先]
Are Science and Virtue Compatible? Rhetorical Strategy inDiscourseontheSciencesandArtsby Rousseau
LONG Zhuo-t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Rousseau’s standpoints of anti-and pro-Enlightenment originate from the duality of his ident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dual rhetoric. He claims that science and virtue are mutually incompatible and urge on common people from their own stands to stay away from science or philosoph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virtues against the infringement of science knowledge or its false forms. His fundamental excuse is to prevent Enlightenment from corrupting philosophy itself. Science and virtue are in fact not incompatible, and only few with high intelligence have the ability to combine them together, who can use genuine knowledge to enlighten the virtues of people.DiscourseontheSciencesandArtsencompasses the key elements of Rousseau’s thought, of which the most critical is dual stances of Rousseau’s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hat serve as a foundation and an access to understanding Rousseau’s general theories.
Rousseau;DiscourseontheSciencesandArts; science or philosophy; virtue; dual rhetoric
2016-12-29
龙卓婷(1987-),女,湖南隆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典诗学与世界文学。
B 565.26
A
1004-1710(2017)03-00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