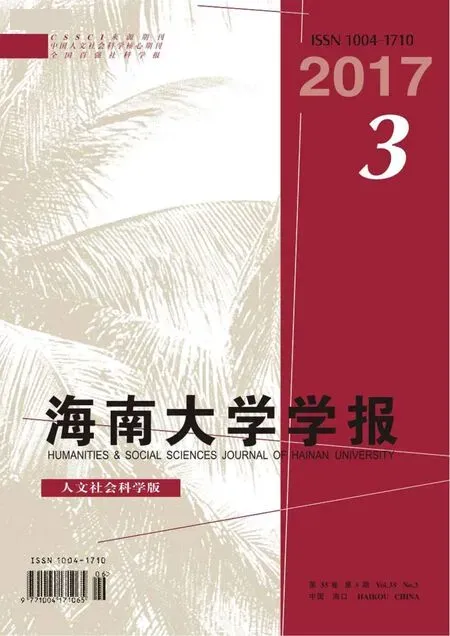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
——美国文化传统的人文性考察
李安斌,卢俊霖
(1.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2.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
——美国文化传统的人文性考察
李安斌1,卢俊霖2
(1.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2.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从变异理论的角度出发讨论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美国精神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美地区清教文化的接受过程。美国清教文化反映出“现实主义”“个体本位”“禁欲主义”特质,是美国在拓荒时期、独立革命时期具体语境所选择的结果。在人文性的角度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一脉相承。在变异观的基础上,建立了“变异—接受”的文化演变模型。
清教主义;美国文化;变异理论;“两希”传统
一、同源而异质的欧美文化
对美国文化根性的追问与思考,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观点——
以史学家赫伯特·奥斯古德为代表的“帝国学派”和以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认为,美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于对欧洲宗教传统的剥离。他们一方面否定“清教历史”,批判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统治是一种“伪民主”。另一方面,他们坚持美国精神产生于北美这一特殊地域,尤其是“西进运动”这一特殊时期。特纳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从普利茅斯“五月花”号船上运来的,而是“来自美国的森林”[1],“这种永恒的重生、流动式的生活、西进扩张中的新机遇以及和朴质的原始族群不断接触,为塑造美国性格提供重要动力。”[2]
相对地,以哈佛大学英语系美国文学教授肯尼思·默多克、佩里·米勒和历史学教授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则肯定了清教主义在早期美国历史传统乃至美国文明中的地位。认为要理解“新英格兰生活方式”对美国民族文化生成的重要性,就必须对17世纪以来的清教主义进行所谓的“心智”(mind)考察,即使在北美这一特殊地域发生变异,但考察美国文化的基点仍然在于清教主义本身。米勒宣称,清教是西方智性(intellect)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创造了美国文化所必需的一整套系统的概念,因此,需要严肃地加以考察[3]。在米勒看来,17世纪以来新英格兰的历史,就是研究清教主义这种“舶来的、高度阐释的智性体系适应北美环境的个案历史”[4]。
从本质上说,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欧洲文化传统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美国清教文化”这一核心“历史”问题。然而,在深层结构中,争论双方却并非截然对立。从研究视角上说,“帝国学派”等则注意到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美国文化异于欧洲传统的个性,而“哈佛学派”注意到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联系性。从研究方向上说,“帝国学派”“边疆学派”则从世俗文化层面入手,构建新的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基础,而“哈佛学派”是从宗教文化层面切入,以确立美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显然,论辩双方都不否认“清教运动”这一美国历史事实,也不否认清教主义在宗教精神层面对美国文化的建构作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清教文化对美国文化、尤其是对美国世俗观念的影响。正因如此,把清教文化从美国文化整体中割裂出去,绕开清教主义(及其诞生的西方文化根源)去把握美国文化传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机械地说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移植也是不可取的。理论上说,“一种事物从一个国土传播到了另一个国土,它必然会生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变异。”[5]因此,美国清教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包括英国清教文化)的基础上变异而来,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同源而异质。用变异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美国文化或文学传统,既是对英国清教传统、欧洲文化的回应,又是对美国个性的肯定。
因此,本文即从变异的角度出发讨论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解构“哈佛学派”与“帝国学派”、“边疆学派”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同时建构一种变异观的美国文化传统。具体来说讨论涉及三方面的问题:(1)变异问题,即讨论清教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清教文化如何发展出异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文化特质;(2)接受问题,即讨论既有西方传统又有地域特质的清教文化如何在美国历史长河中被扬弃;(3)源流问题,即追溯欧洲文化的历史传统如何为美国清教主义的诞生提供土壤。
二、变异过程中的清教主义
与西方传统宗教文化相比,清教文化变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首先对所谓的文化“变异”演进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阐发。笔者认为,基于“变异观”的文化演进过程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渐进性。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文化的变异与演化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变化不是在一瞬间完成,而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变化的过程也是可以洞察的。历时地看,清教主义的德行标准并非是对中世纪天主教教义的直接继承与反驳,而是承袭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加尔文教,这即是宗教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渐进性。二是过渡性。在文化变异演进过程中,旧有的文化特性不会马上消失,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和新的文化特质共存,并且展开竞争。共时地看,在清教诞生之初的一段时间内,清教文化中还保留着天主教文化的一些原有观念,只不过这些旧有观念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渐消蚀。文化演进依赖于变异逐步进行,渐变性和过渡性是文化演进过程的两大重要特征,这一演进过程可以表述为:A>A~B>B,由文化A发展为B的过程,必然经历A至B共存的阶段。
回过头来看基督教文化到清教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宗教的核心内容在于指导人们如何寻求幸福,用宗教话语来说就是建构一个完善的救赎体系,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即大多数宗教救赎论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这三个基本特征遵循如下的发生逻辑:(1)由于幸福不是可以立刻实现的“现世报”,人类要想寻求幸福只能寄托于“来世”或者“彼岸”,所以宗教往往将“幸福”置于彼岸世界,如佛教话语体系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话语体系中的“天堂”,即重来世。(2)来世、彼岸和现世、此岸是割裂的,来世、彼岸是不可在现世、此岸得见的,宗教面临着回答另一个问题,即“现世的我为何且何以享受来世的幸福”。于是,宗教设计了一套“灵魂不死”的话语体系,通过“灵魂”来架构现世与来生的联系,即重灵魂。(3)在方法论上,要让灵魂在来世得到幸福,这就需要升华灵魂,到达德行上的“至善”,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禁欲主义,用人的理性意志对抗自然欲望,走向极端则表现为苦行主义,如基督教、印度教中的苦行僧,他们将“苦行”作为自己修道的方式,如长期断食、断水、忍受酷热严寒等,以寻求灵魂的提升。一是利他主义,如尸毗王割肉救鸽,耶稣为人类受刑赎罪的故事,都在倡导利他主义、宣扬博爱精神,即群体本位。
总的来说,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是大多数宗教普遍具有的特征,也是基督教的文化特质。如蒋承勇先生所指:“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一种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的理性型文化,……它对以破坏力和‘恶’的形式出现的人的原始欲望,是有制约作用的,这种制约让人从善、求善,追求灵魂与精神的充实与富裕,调和本能欲求与现实可能、个人需要与社会制约、个性张扬与道德规范、肉体与灵魂等的矛盾冲突,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正效应。”[6]“清教文化的价值观准则可以概括为现世主义、禁欲主义、功利主义”[7]202,由中世纪天主教到清教的发展过程,可以在我们的变异演进模型A>A至B>B中得到观察。
先说演进过程的渐进性。清教与路德教、加尔文教,乃至中世纪天主教本身是一脉相承的。中世纪天主教认为,人虽有原罪,但未完全失去自由意志,因而人类在救赎中可以避恶从善、有所作为,即“行为称义”。在此基础上,中世纪天主教会建立起“善功救赎”论,人要称义只能依靠善功,购买赎罪券。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教提出,上帝因基督已经原谅了人的罪,在上帝眼中,所有的信仰者都是义人。因此,称义的原因不在于善功而在于上帝,人类甚至无法抗拒这一“恩典”。人若有了“信仰”,就可和上帝发生联系,即“因信称义”。“信仰—恩典”的救赎方式虽然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在内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人更多的个体自由。加尔文教也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的命运由上帝的绝对意志所“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消极地接受上帝的安排,人可以通过“蒙召”(Calling)来探知上帝的意志,以验证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包括信仰、道德在内都是选民身份的标志。加尔文教通过建立“蒙召—预定”的救赎方式,使得人可以借助现实世界联接彼岸世界。而后,“预定论”在清教教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拣选”“召唤”“称义”“成圣”“荣耀”构成了清教救赎论的全部。在救赎链的最后一环,选民不仅享有上帝的荣耀,同时也“荣耀上帝”,这就使选民从一个受动者转换为施动者,使得与之相连的整个清教信仰带有强烈的进取性与入世倾向[7]210。从人文性的角度看,由天主教的“善功赎罪”到清教的“荣耀上帝”,这个演进过程就是世俗个体不断凸显的过程,人从依靠外物救赎变为依靠自身,从关注来世转为关注现世,从接受者变为主动者,这个过程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
再看变异演进过程中的过渡性。现世主义、禁欲主义、功利主义是清教价值观的三大特征,但并不是说清教文化轻视来世,否定肉体,只追求世俗功利。相反,至始至终,清教的终极关怀是彼世而非现世,它在根本上对现世持否定态度,宗教的首要目标就是把“人从现世的精神和徒劳的交际中拯救出来”。其次,清教重视灵魂,但不否认世俗中的人,清教的禁欲主义被韦伯称为“合理的禁欲主义”。当肉欲用于繁衍后代时可以得到保护,只要娱乐不导致道德的堕落,并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受到肯定。最后,从目的上看,清教徒并不关心德行的伦理意义,而是关心这些德行所能带给他们的宗教利益,以验证自己是否入选,进而荣耀上帝,这确实是一个个体本位。但从结果上看,清教诚实、勤勉、节俭的德行要求,在为个人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积累财富,具有社会意义。只不过相比之下,清教徒选择“从个体到社会”的财富积累路径,而非群体本位所倡导的“舍己为人”价值观[7]220-223。米勒也认为,尽管“清教学说中确实存在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但与此同时,清教哲学要求社会中的所有人,至少是获得了‘再生’之人紧密团结在一起。”[8]所以,早期清教文化并非是绝对的现实主义、禁欲主义、功利主义,相反,现世与来世,灵魂与肉体,个人本位与群体本位在清教文化中兼而有之,即变异演进过程中的过渡性。
所有这些所谓的来世的、现世的,灵魂的、肉体的,个体的、群体的文化观念,都伴随五月花号来到了北美“新英格兰”。
三、清教文化在北美的接受与发展
由于“过渡性”特征的影响,在清教文化中,旧有的基督教文化的“重来世”“群体本位”的文化特质不会马上消失,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和新教“重现世”“个体本位”的文化特质共存。从“重来世”到“重现世”,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文化变异如何得以实现,或者说清教文化中“重来世”“群体本位”等观念何以淡化,“重现世”“重灵魂”“个体本位”等观念何以凸显为清教文化特质,这涉及到清教文化在北美地区的接受与发展问题。
(一)世俗精神的确立:拓荒与清教徒的现世经营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远涉重洋清教徒初登北美荒野,开始了其宗教实践和世俗扩张的双重历程。马瑟对他们的使命描述道:“船队载着几千名宗教改革者,它将把他们运往……美洲荒原,目的是……吾主能首先显示给他们大量善行的样本,然后吾主将同他们一道,在其他地方施行这些善行……地理学家现在有了新的工作……他应当记载新英格兰以色列历史中的基督教地理志,和其他新耶路撒冷国的诞生。”[9]27对清教徒来说,北美大陆既是此岸的荒原又是彼岸的“迦南福地”,面对上帝的恩典,新英格兰清教徒肩负着“荣耀上帝”的伟大责任,践行上帝的意志,用世俗话语来说,就是拓荒。特殊的环境决定了特殊的信仰,他们将拓荒北美视为营建上帝之城,建立“属于未来的国家”,通过现世的共同道路达到千福年。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现世与来世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或者说在拓荒语境下,清教徒们开始积极的现世经营,“现实主义”思想也因而得到了凸显。
拓荒北美的历史语境同时也决定了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走向。是时的文学主要以史志、自传、日记等叙事类文体为主,较为著名的如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摩群岛通史》,威廉·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以及科顿·马瑟、塞缪尔·休厄尔、约翰·伍尔曼等人的日志。马库斯·坎利夫认为,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既不能称其为美国的,又不能称其为文学。不能称其为美国的是因为作者大都是英国移民,不能称其为文学是由于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而它呢?只是一些见闻录和宗教记事。”[10]然而,从接受的角度讲,清教移民者对书写形式的选择,正是出自其拓荒北美的宗教实践的需求。北美殖民时期,早期清教殖民者通过传记、日志类叙事文学,详实地记录自我是如何在上帝的指引下,克服漫长而艰辛的越洋航行,以及如何在新大陆实践上帝的旨意,营造着上帝之城。在温斯罗普的《日志》中,甚至记录了一些十分琐屑的世俗生活,以及与土著人的冲突。清教徒以虔诚的态度忠实地记录着他们获得通往救赎的“天路历程”,这就开启了清教文化“现实主义”转型的实现。
此外,布道文也是当时广受欢迎的文学形式。标准的布道文包括四个部分,解说《圣经》、宣读教义、论证、用途。和宗教冥思不一样,布道文属于应用文体范畴,这就决定了布道文学更加关注于文学的现实功能,同时,为了布道讲经,布道文必然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这就意味着,世俗需求开始引导宗教表达,换句话说,宗教向世俗倾斜,这也就推动了清教文化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二)“自我书写”:从宗教群体到世俗个体
拓荒只是形式,而目的是清教徒的自我证明——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没有辜负上帝的期许。在清教徒未登美洲荒原之前,美洲荒原就已成了“迦南美地”的代名词,被他们纳入到了圣经隐喻之中。清教徒援引《圣经》中的先例和预言来解识个体的现世实践,世俗日常的桩桩件件,也都被他们赋予了伟大的宗教意义。这种认识“激发人们的利益感与忠诚感,将人们带入共同的事业中,使人们相信上帝赋予北美人民以特殊使命。”[11]在布拉福德《普利茅斯种植园史》中,上帝指引清教徒们接近新的应许之地、建设人类新的耶路撒冷城,把自己那种被放逐、流浪荒野的状态神圣化。温斯罗普的《日志》中,温斯罗普将自己及其追随者视为怀有神圣使命的选民,将他们在殖民地上的所作所为,视为对上圣神圣意志的实践。另一方面,这批清教徒面对迫不得已的出走,波涛汹涌的航程,荒凉贫瘠的原野,也需要来自上帝的精神安慰,在《圣经》中理解灾难的意义。清教徒根据《圣经》发明了群体的自我,他们不断地肯定这个群体自我,并通过一系列的界定自我的语言手段来扩展和修改这种群体自我的形象[12]。于是,对“选民”的自我证明成了他们在北美荒原的世俗成就推动力。
早期清教徒的这种自我审视,强化了清教文化中的“个体本位”思想——当然,是时的“个体本位”还是一个“选民”身份的集合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力图寻找能与他们的新大陆使命相匹配的自我本质特性。当他们把联邦契约作为他们‘特有’的社会契约时,上帝特选的民族这一观念就成了清教对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大贡献。”[9]32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些心怀对母国忠诚的拓荒者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而基于对上帝绝对虔诚的宗教实践,最终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国家意识的出现,导致了北美族群从“选民”到扬基佬的认同转变的发生。在18世纪前后的文学中则表现为对“美国新人”形象的塑造、对“美国信念”的歌颂、对美国梦的寻求。富兰克林的《自传》就是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富兰克林及其《自传》是北美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产物,《自传》的主人公不仅代表了现实个体,也代表了一个正在崛起的“美国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反映的远不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伦理道德,还确立了一系列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个人道德行为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传》等作品首先凸显的是一个“人”的形象。在北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鉴定,从世俗的角度出发,他们看到一个宗教之外的个体——世俗的个体。
在脱离宗主国统治后,摆在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面前的是这样两个问题:我是谁,以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谁。而且,脱离了宗主国统治等于和过去的历史告别,这时的美国也急需对“自我”做一个新的认识与陈述,不然,政治层面的独立不代表在文化意义上摆脱殖民。无论是超验作家群抑或是清教文学家,他们对“我是谁”的问题诸派口径一致——“新亚当”,要书写新的自我——独立自由的美利坚民族[13]。所谓“新亚当”,首先是从历史中解脱出来的个体(由于摆脱了祖先,而免受家族和种族影响),同时也是独行于世的个体(依靠自己的智慧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14]。在此意义上,爱默生笔下的“超灵”、惠特曼诗歌中的“自我”,霍桑笔下的海丝特、麦尔维尔的比利·巴德,都是人类历史上“新的亚当”。
17世纪到19世纪,美国心中的“自我形象”发生改变,从宗教群体 “选民”到世俗群体“美国人”,再到世俗个体“新亚当”,个体本位成为清教文化、乃至美国文化的典型特质。正是在这个世俗精神层面的“个体本位”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平等、自由精神。
(三)灵魂:驾驭世俗欲望的缰绳
经历了早期艰辛的拓荒实践,18世纪的新英格兰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发生论的角度讲,清教所包含的一系列精神品质,即由预定论、天职观等推导而来的勤奋等成功动力以及由禁欲衍变而来的节俭等道德品质的结合体,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客观前提以及道德保障,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接受论的角度讲,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原始积累,而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的情况下,无论是宗教意义的“禁欲”,或者是世俗意义“节俭”,对原始积累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种禁欲主义是有选择性的,在“荣耀上帝”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语境下,禁欲并不阻止世俗个体的追求成功、追求财富的欲望。它只是在道德层面规范人的世俗成功,同时节制人的享乐欲望。
进入到19世纪,在欧洲浪漫主义的驱使下,超验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当时主流思想潮流,宣扬者认为人则可以通过直觉来认识上帝,或者通过置个人心灵于超灵之中来寻求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世俗的“人”极端膨胀。在《自然沉思录》中,爱默生称颂道:“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头脑沐浴在清爽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那无限的空间中,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是一个‘无’,我看见了一切,普遍的存在进入到我的血脉,在我周身流动。我成了上帝的部分或分子。”[15]当世俗个体无限扩大时,人体内的恶也被无限放大。面对整个时代“神性”的缺位,清教作家群对“灵魂”发出歇斯底里地呼唤,以灵魂约束人类自由意志的泛滥,为人性立法。霍桑借助《红字》忏悔世俗欲望,麦尔维尔《白鲸》中的命运悲剧则预言着缺失信仰的恶果。这说明,任何时代,人都不能缺失“灵魂”的约束,这也是宗教徒之所以坚守“灵魂”的现实意义。
综上,笔者认为,在特殊的时期,基督—天主教孕育出新的文化样式,这些新的、旧的文化样式在具体的历史地域语境中被拣选而形成新的文化特质,文化的变异发展即环境选择的结果。就如美国式清教文化,选择了以“现实主义”(重现世)、“禁欲主义”(重灵魂)、“功利主义”(个体本位)作为其核心价值。
四、“灵”“肉”交错的欧美文学
在北美地区对清教文化接受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美国精神”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清教文化的选择与接受过程。因此,无论早期清教文化“新英格兰”的地域性特征如何的明显,也不论后来形成的基于清教主义的“美国精神”如何地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其本质上并未改变其作为欧洲文化传统子系统的地位,尤其是从人文主义传统角度出发,这一联系就更为紧密。我们把美国文化拉入到西方文化的脉络中讲述,以期对美国文学的源流做一个通盘考察和完整表述。
如同蒋承勇先生所指,欧洲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从文化本质上说就是“两希传统”。具体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化内质体现的是人的“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结构,在文学中体现为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罗马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理性型的,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16]。从古希腊神话对世俗人性的张扬,到基督教以宗教理性对过度张扬的世俗人性的反拨,从中世纪文学对人性的过度遮蔽,到文艺复兴文学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和定位,直到启蒙文学中人的理性精神的真正确立,这是欧洲文学人文主义发展的主线。从根源上说,清教主义极而言之的源头仍然在于欧洲异质互补的“两希”文明,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是欧洲“两希”文化交替演进的产物。因而清教主义在新英格兰所表现的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特质,可以看作是欧洲“两希”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地域的一种翻版。正因如此,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所反映出的“灵”“肉”思辨,也在整个美国文化发展中交替演进。
在17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宗教人本意识无疑是一个显赫范畴。对于出走北美荒原的清教徒来说,“五月花”号离开大不列颠岛的那一刻就是苦难的开端,等待他们的是大西洋的黑风孽海以及北美洲的风沙环伺。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作为世俗个体的人显得异常的渺小与卑微,现世人生意义得不到肯定,他们只能求助于宗教隐喻,期待灵魂的升华与超越,以抗衡生存窘境。于是,现世的苦难成了宗教意义上的“灾难”,流浪者成了上帝的“选民”,现世的困苦只是人类“原罪”的延续,宗教人本意识就是以这种方式介入对世俗个体的“治疗”。相对来说,本时期的世俗人本意识作为一种文化潜流,被宗教人本意识的强大光芒所掩盖。个体的自然欲望因外界环境而被压抑,而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则由宗教话语来表达。
到了18世纪,剧情发生反转。当世俗个体战胜了自然环境所设置的层层阻碍之后,当资本主义已经在北美荒原破土而出之后,禁锢在世俗个体之上的枷锁就不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为自我救赎而设置的、外在的“神”对个体“原欲”的约束。至此,世俗个体开始寻求新一轮的“治疗”,将世俗个体从宗教人本意识的约束中解救出来。恰好,“两希”传统中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人类的自然原欲提供了一个表述框架。对“神”的矛头首先指向了“社会神”——宗主国,表达在社会——政治层面则是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表达在精神—文学层面则是对“美国梦”“美国精神”“个人英雄主义”等主题的书写。然而,世俗人本意识向宗教人本意识的冲击刚刚开始,人尚未对“神”发起进攻,因而,这一时期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新人形象,并不是单一的世俗新人,“神”仍然以道德戒律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智当中,这也不啻为宗教理性精神与世俗理性精神的一种接合。
世俗人本意识在真正意义上对“自然神”发动全面进攻的时间是在19世纪。在西方启蒙运动与自然神论的助推下,世俗个体被提到不可一世的高度。在这一语境下,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群开始对清教文化中的“神”发动最后一击。他们摒弃了“原罪说”,强调人自身的神性,以“性善论”填补“性恶论”对世俗个体所预设的道德缺陷,以寻求在精神上的永恒的治愈。显然,当上帝的精神等同于人的精神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的神性的缺失。个体欲望的张扬,对于上升时期的美国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自私的基因蔓延而带来的新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以霍桑、麦尔维尔为代表的清教主义作家,一直坚守着宗教人本意识的大旗,呼唤宗教理性对世俗人性的挽救。19世纪的美国文学,宗教人本意识与世俗人本意识一直针锋相对,互为文化的他者,以不同的方式和向度对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不完满展开“治疗”。进入到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文学逐渐回归世界文学,其对“人性”的探讨也日益走出了北美特定的地域,但美国文学中宗教人本意识与世俗人本意识的冲突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更深和更大的层面上得以展开。
从上述来说,“两希”传统在美国文化中的交替演进与冲突,也是一个接受—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这个过程并未完结,始终停留在“A至B”的过渡阶段。无论是宗教人本意识还是世俗人本意识,它们关注的焦点都是人本身,从根本上说,文学即人学,文学在精神意识层面上对人类自身缺陷展开“治疗”,人在想象的空间实现自身的完满性。
五、结语
本文基于变异理论的思想,重新检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观察同时,我们建立了“变异-接受”的文化变异模型,认为,由文化A到文化B的演变过程,是具体语境选择的结果,即A>A至B>B。
首先,“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路德教、加尔文教、清教等新教逐渐滋生出“重现世”“重个体”等新特点。而旧有的文化特征不会立马被新的文化特征所取代,文化变异的过程要经历一个过渡性阶段,这个阶段中,新、旧文化特征会长期共存,在早期清教文化中,现世与来世,灵魂与肉体,个人本位与群体本位等观念,兼而有之。这就是A>A至B的阶段。
其次,变异演化最终得以实现,取决于具体历史的、地域的语境的要求。在对美洲荒野的拓荒实践的历史语境下,清教徒们开始积极的现世经营,推动了“现实主义”在清教文化中的凸显;从缔造“上帝之城”到独立运动再到超验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清教徒的自我阐释与自我认同,确立“个体本位”在北美清教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俗欲望的上升,则呼唤着“禁欲主义”的助推与制约。这就是A至B>B的演变过程。
所谓“美国精神”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清教文化的选择与接受过程。正是由于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人文性上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异质互补的“两希传统”及其宗教人本意识与世俗人本意识的织关系,是识解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我们可以拒绝将其作为考察美国文化发展的尺度,但无法拒绝将其作为考察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维度。
[1]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0:293.
[2]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5.
[3] Miller Perry.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9:8.
[4] Miller Perry.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M].Mass: Belknap Press, 1983:10.
[5] 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38.
[6] 蒋承勇.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人本意识新解[J].外国文学研究, 2002(3):22.
[7] 柴惠庭.英国清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 1994.
[8] Miller Perry.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M].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4: 143.
[9] 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通伯,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10] 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 [M]. 第3版.方杰,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15.
[11] Hudson Winthrop S. Religion in Amer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 M]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5:76-77.
[12] 李安斌,王梅.清教话语与美国文学中的神话象征[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8(7):100.
[13] 李安斌,卢俊霖.于“灵”、“肉”思辨中建构另一个自我——美国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清教传统[J].广西社会科学,2016(7):175.
[14] Lewis R W B.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5.
[15]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 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6.
[16] 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39.
[责任编辑:吴晓珉]
From England to New England:A Humanistic Investigation into Cultural Tradition of United States
LI An-bin1, LU Jun-lin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cul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tion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merican spirit is, in a sense, the reception of Puritan culture in North America. “Realism”, “individualism” and “asceticism” are thre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Puritanism, which result from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situ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frontier and War of Independence. In terms of humanistic perspective, America culture is the direct successor of European culture. A “variation-reception” model of cultural evolution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Variation Theory.
Puritanism; American culture; Variation Theory; Greek and Hebrew Tradition
201-7-02-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W042)
李安斌(1971-),男,四川广元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比较文学。
G112
A
1004-1710(2017)03-015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