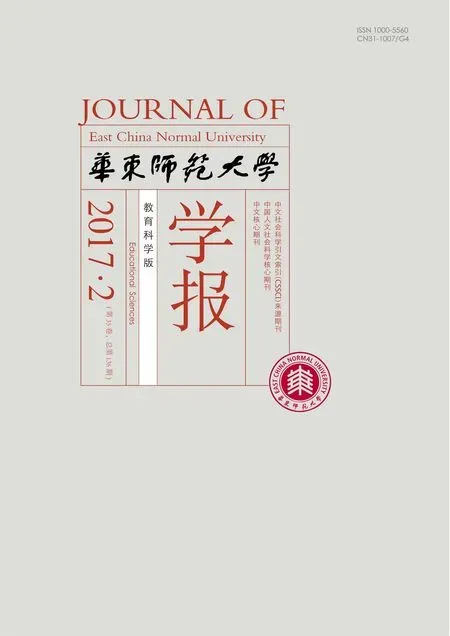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
孙时进 施泽艺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
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
孙时进 施泽艺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
校园欺凌事件因其恶性影响在近年来受到人们普遍关注。校园欺凌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发生率。欺凌行为的发生,有欺凌者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性的原因,治理欺凌行为需要对不同原因有充分理解。被欺凌者往往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被欺凌,他们是被同情的对象,但是也正因为它们不自主地展现出心理弱势而“吸引”冲突的另一方欺凌自己。增强被欺凌者的自尊与自强,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欺凌现象的发生。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着欺凌事件。当三者都倡导自由、平等、支持、亲密等价值时,校园欺凌数量便会大大减少。治理校园欺凌,应当以问题为中心,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入手,实施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
校园欺凌;欺凌者;被欺凌者;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国有关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新闻日益获得人们的关注。一段某市一群初中女学生殴打同学的视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时隔几日,类似的校园欺凌现象的图文又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毫无疑问,校园欺凌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都会造成一定的身心伤害。有研究发现,8岁到12岁之间有过欺凌行为的学生在以后的犯罪率会显著提高,而那些有过被欺凌经历的学生则会有学业上的问题和心理上的问题,如焦虑、抑郁、回避、孤独、低自尊等(Bender&Lsel,2011;Chan&Wong,2015)。
校园欺凌事件并不是个别现象,在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也都有一定的发生率,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事件(Wang,Iannotti,&Nansel,2009)。Chan和Wong在2015年的报告中总结了我国校园欺凌的现状,结果发现,在我国大陆的不同学校中,有从2%到66%不等的学生曾被欺凌过,而实施欺凌的则从2%到34%不等(Chan&Wong,2015)。而美国的一项研究对全美范围内6到10年级的在两个月内参与过校园欺凌的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有20%的学生报告曾在身体上施行欺凌行为,有53.6%的学生报告参与过言语方面的校园欺凌,报告参与过社交性欺凌的学生占比是51.4%,而在网络上参与校园欺凌的有13.6%(Wang,Iannotti,&Nansel,2009)。
在上文提到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有关部门在事件发生后进行了积极的处理。但他们的调查处理并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引发人们关注并努力治理校园欺凌与暴力的另一个起点。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就是希望从法律、教育、社会、心理等多个角度共同治理这一现象。回顾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如何治理校园欺凌也已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综合前人的一些研究,评述校园欺凌者、被欺凌者的心理特点,以及社会环境的作用,并最终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校园欺凌的定义
“校园欺凌”指的是以校园为背景发生的欺凌事件。欺凌事件包含身体、言语、关系、网络各个层面的攻击,如身体上的击打、推搡、踢打行为,言语上的辱骂、嘲笑,关系上的社交排挤、散播谣言,网络上的各种攻击,等等。有研究者认为,欺凌是一种“强势者对弱势者的重复攻击行为”(魏重政,刘文利,2015),并且这一行为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有研究者认为,校园欺凌是青少年之间的一种问题行为,它经常被定义为一种蓄意的、重复的特殊的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影响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学业成绩、亲社会技能和心理健康(Wang,Iannotti,&Nansel,2009)。此外,国内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概念也有所区分。“校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校园为背景实施的暴力攻击行为,而校园欺凌是一种较低水平的暴力行为(吴桂翎,辛涛,2009)。
综合前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在校园欺凌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存在权力之间的强弱差异,欺凌者往往会对被欺凌者加以身体、言语、社交等不同方面的攻击,当这种攻击性行为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欺凌行为则上升为暴力行为。也就是说,校园欺凌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在校园背景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蓄意的、重复的攻击(包含身体、言语、关系、网络各个层面的攻击),这些攻击行为往往会影响行为参与者的身心健康。在校园欺凌事件中,主要参与者就是欺凌者与被欺凌者。
二、校园欺凌的参与者
(一)欺凌者
欺凌者因其攻击性行为,往往被冠以“恶”的名号。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与生理状况、年龄、控制力或对高社会地位的渴望等因素有关(Juvonen,&Graham,2014;吴桂翎,辛涛,2009)。有些学者试图从生理的角度来对校园欺凌的攻击行为进行解释,如解剖学家加尔的颅相学,精神病学家克雷奇欧尔的体型论,犯罪人类学鼻祖龙勃罗所阐述的人种退化与隔代遗传的返祖现象,20世纪60年代欧美科学家用染色体畸变或基因缺陷来解释攻击本身产生的原因,等等。这些解释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批评。也有学者认为,暴力与攻击性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于大脑中枢回路有异常,致使情绪调控产生障碍,从而失去自我驾驭能力(郑开诚,张芳德,2002)。此外,不同性别在欺凌形式上也有差异。虽然男孩也会和女孩一样使用间接欺凌的方式搞臭被欺凌者的名声,但是男孩会比女孩更多参与直接欺凌;而女孩相比直接欺凌,会更多参与间接欺凌(Bjrkqvist,1994;Juvonen&Graham,2014)。年龄在欺凌行为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利时学者凯特勒认为,随着欺凌者年龄的增长,校园欺凌行为会从直接攻击行为(如踢、打、骂等)慢慢演变为间接攻击行为(如敲诈勒索等)(吴桂翎,辛涛,2009)。但是也有元分析发现,年龄在校园欺凌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Card,Stucky,Sawalani,&Little,2008;Juvonen&Graham,2014)。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一些欺凌行为的发生也受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如一部分欺凌者本身就处于较高的地位,他们企图通过欺凌来巩固这一地位。一些研究发现,在青春期早期,敌意行为与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Parkhurst&Hopmeyer,1998)。这或许可以用动物行为学解释,因为攻击性行为是一种在团体中确立统治地位的方式(Juvonen&Graham,2014)。在个人特质上,这些通过欺凌来获取高社会地位的个体是十分冷血和精于算计的,因为他们知道欺凌他人可以达到某些目的。这些人缺乏同情心,并且知道如何操控权术来掌控同伴的行为。这些特质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个体特质十分相似(Berger,Batanova,&Cance,2015;Sutton&Keogh,2000)。
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欺凌者自身可能也是“受害者”。欺凌者“施恶”的来源可能正是家庭或者社会环境的“施害”。班杜拉的经典实验(Bandura,1974)表明,攻击性行为是可以模仿而来的。不难想象,一部分校园欺凌者正是在家庭或社会的环境下模仿了父母等成年人的一些行为才掌握了这种用拳头解决和沟通问题的方法。有些学生则是由于幼儿期间与社会群体隔离,从而缺乏与同伴交往的能力,他们会通过不恰当的行为(如攻击行为)与人建立人际联结(Olweus,1978)。这些欺凌者也需要心理援助来扭转他们扭曲的人际链条。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去理解欺凌者攻击性行为的本原,思考其行为背后的历史源头与存在意义,那么我们的治理也将“治标不治本”。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欺凌者或者施加暴力行为的人并不总是被鄙夷和遏制的。一些暴力行为被人们欣赏甚至崇拜,如角斗场在罗马的盛况、人们对横行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喜爱、对梁山好汉的敬畏、“暴力美学”的流行等。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在古老的丛林中,人们一部分行为的意义往往与生存有关(Pinker et al.,2007)。强势者作为部族的领导,需要一定的攻击性才能保证群体内的人不被其他群体所侵害,也需要展现一定的攻击性以保证自己在族群内的社会地位,甚至需要遗弃群体内的一部分弱者来保证群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历史发展,人类的道德也随之发展,但是进化却也在人身上遗留下一部分攻击性特质。确实,他们的欺凌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是,当我们拨开欺凌行为的表象来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时,会发现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单纯地消除欺凌行为,而是接纳其攻击性,并将其转化和整合为被社会与道德接受的行为。换句话说,对这些欺凌者的改造不应当只通过惩罚这一方式,如何将那些欺凌者的“魔性”转变为“佛性”才是更需要我们考虑的。
(二)被欺凌者
大多数被欺凌者在冲突中遭受了身心伤害,是值得同情和被保护的对象。被欺凌者是更为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往往不只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受害者往往是与众不同的、没有朋友的、不被社会接纳的和被孤立的对象(Juvonen,&Graham,2014;Pellegrini,Bartini,&Brooks,1999;Veenstra,et al.,2005)。有研究者发现,那些超重的、晚发育的、残疾的学生更加容易被欺凌(Juvonen&Graham,2014;魏重政,刘文利,2015)。
但是换个角度思考,人际冲突在人的生命中永远不可能消失,为什么有的冲突自然地消失了,有的冲突却演变成了两方不均等的攻击行为呢?美国微观社会学学者柯林斯(2016)认为,如果有一方在冲突中一味地回避,就会打破人际间的冲突-紧张平衡,并最终导致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一部分被欺凌者自身往往存在一些弱势的特质“吸引”欺凌者实施攻击。Olweus(1994)将这些人描述为被动的、消极的、服从的,并认为这些人在社交时会焦虑、敏感、缺乏自信(Salmivalli&Isaacs 2005)。
有童年专制经历的孩子也更容易卷入欺凌事件中。比如那些被家长严厉对待的男孩也更容易在学校被欺凌(Whelan&Barker,2014)。而在温暖、充满感情和有良好家庭氛围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则更少被欺凌(Lereya,Samara,&Wolke,2013)。
由上文可以看到,被欺凌者虽然应当被保护,但其表现出的弱势会不自觉地“吸引”冲突的对立方采用攻击手段。如果不能通过心理训练让这些被欺凌者内心强大起来,只是单方面遏制欺凌者的攻击性行为,欺凌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
三、社会环境的作用
(一)家庭环境
家庭是一个人社会支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负面的家庭环境或者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孩子在校的“自毁行为”。如果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温暖较少、对孩子有负面情绪、纵容孩子的攻击性与敌对行为,或者使用专制型教养方式(如对孩子进行虐待、忽视、体罚等),孩子也会更多参与欺凌事件(Whelan&Barker,2014)。但是,过高的家庭亲密度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一个妈妈非常“焦虑”地投入与孩子的关系,那些孩子就会过多地依赖和自己父母的关系,而不和其他的孩子玩,从而成为被孤立与被欺凌的对象(Olweus,1980)。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缓冲欺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能避免孩子成为欺凌参与者中的一员。研究发现,家长支持可以有效地保护青少年不受欺凌(Wang,Iannotti,&Nansel,2009)。那些不参与校园欺凌的孩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更为适中,父母双方更为平等(Berdondini&Smith,1996),也有更加良好的沟通、更加温暖和充满感情的家庭氛围(Smith,Bowers,Binney,&Cowie,1992)。
(二)学校环境
学校是大多数学生生活、学习与社会交往的场所,也是大多数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场所。大量研究表明,学校层面的校园欺凌干预是十分有效的(Richard,Schneider,&Mallet,2011;Smith,Cousins,&Stewart,2005)。有研究者评估了44个校园层面反校园欺凌的项目,结果发现,项目执行后欺凌者的比例下降了20%到23%,而被欺凌者的比例下降了17%到20%。由此可见,学校环境对于缓解校园欺凌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学校系统的支持(如同伴支持、成人支持、甚至学习上的支持),就如同家庭支持一样,对缓解校园欺凌十分重要(Turner,Reynolds,Lee,Subasic,&Bromhead,2014;Gage,Prykanowski,&Larson,2014)。除支持感以外,帮助学生建立对学校的认同感(即联结感与归属感),也是减少校园欺凌的一大方法(Turner et al.,2014)。
(三)社会环境
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看,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都影响着校园欺凌事件的形成(Cross et al.,2015)。一些在社会环境中导致暴力的因素(比如种族歧视、吸毒、使用武器、虐待儿童等)也会引起校园欺凌与暴力。可以说,“学校通常是周边邻里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映”(吴桂翎,辛涛,2009)。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具有同构性。具体而言,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包含自由、平等、支持、亲密、安全、认同感等元素,这些都能减少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家庭、学校、社会的同构性正如一面面镜子,相互映照。学校周围的环境会映射出社会的大环境。社会的专制会导致家庭的专制。家庭中人际关系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孩子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尊重他人的态度,都有平等、民主、自由、和谐的价值观,那么学校和家庭中的个体也会相互报以同样的态度。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倘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散发出这样的气质,那么欺凌者不会认为自己比少数群体更高一筹,被欺凌者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唯唯诺诺,校园欺凌事件就能大大减少。
三、治理方法
首先,就积极方面来看,对校园欺凌关注的增加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我国各大领域的学者与媒体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在近五年有显著的增长。在“中国知网”中以“校园欺凌”为关键词搜索后发现,近五年与校园欺凌相关的文献环比增长350%,而媒体发表的文章增长了600%。但是另一方面,对校园欺凌关注的增加并不完全意味着校园欺凌事件数量的显著增加。Rigby和Smith(2011)研究了1990年到2009年多个国家的校园欺凌数据后发现,欺凌事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在这期间并没有明显增长。可以说,我们在担忧校园欺凌恶性影响的同时,更应当承认并感激我国社会的进步,这些进步为我们关注校园欺凌并进一步治理校园欺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二,校园欺凌治理应当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以问题为中心指的是研究者和治理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应该紧贴当下主题与社会现状,从目前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制定相应的对策。综合治理指的则是从法律、教育、心理等多个学科视角入手综合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譬如,法律学者应当对校园欺凌中涉及的攻击性行为设定一条底线。当校园中学生的欺凌行为触犯了这一法律底线时,就需要加以处罚。这一法律底线不仅能够遏制部分极端事件的发生,也能对还未发生的事件起到警示作用。教育者则应参考国内外的一些校园防欺凌策略(Ttofi&Farrington,2011;李锋,史东芳,2015;许明,2008),从道德教育、校园风气建设、家校互通联动、校园内外的监管等方面综合治理。在心理建设上,应针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两个人群,结合团体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方式,转化他们扭曲的人际关系。
其三,校园欺凌应当综合调动家庭、学校、社会的力量以实现标本兼治。欺凌参与者所处的社会、学校、家庭环境都影响着他们,并且这些环境也会相互映照。治理路线应当从个人到家庭,从学校到社会风气,自下而上进行。正如《礼记·大学》所云“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即使用诸如内观、团体心理辅导等方式,构建一种自由、平等的团体氛围,以缓解扭曲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构建更为积极、平等、和谐的家庭氛围,此谓“齐家”。学校教育应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在教学活动中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观。从个人特质、家庭环境、学校氛围到社会风气多个方面入手,综合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对校园欺凌的根本治理。
所谓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就是在操作层面让欺凌者不能、不敢、不想欺凌他人。“不能”指的是在法律层面设定绝对的底线,让欺凌者的一些极端行为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恶性欺凌事件的发生。“不敢”是指通过道德教育、行为监管等手段及时记录并制止一些欺凌行为的发生。“不想”就是指通过心理教育,从个人、家庭、学校到社会多个层面入手打造个体的心理强度,提升他们的冲突处理能力,构建平等的人际氛围。我们应当多注意欺凌参与者的心理状态,让他们向善,这样才能从源头着手,实现真正的“治本”。
但是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校园欺凌的外延不能被无限地扩大,对矛盾冲突也不能无限度地干预。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条文和进行校园监管时,不能将任何矛盾冲突都认定为校园欺凌。如果代表底线的一座警钟太过灵敏,那么这座警钟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此外,校园和社会虽然应当对学生之间的冲突有一定了解和监管,但是并不能无限度的干预。因为,学会处理矛盾冲突是人社会化的必要步骤。如果一直扶着学步的孩子走路而不放开,那么未来这个孩子就会过度依赖帮助者,从而失去自理能力。由于校园与社会的同构性,当未来在社会中同样出现欺凌事件时,那些被欺凌者可能会因为过度依靠监管方而没有自我处理能力,最终酿成悲惨的后果。
综上所述,人们对校园欺凌现象日益关注,这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也为治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治理校园欺凌,应当以问题为中心,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入手,实施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
柯林斯.(2016).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锋,&史东芳.(2015).挪威反校园欺凌“零容忍方案”研究述评.教育导刊,(2),91-95.
魏重政,&刘文利.(2015).性少数学生心理健康与遭受校园欺凌之间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4),701-705.
吴桂翎,&辛涛.(2009).校园暴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特殊教育,(6),75-79.
许明.(2008).英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其解决对策.青年研究,(1),44-48.
郑开诚,&张芳德.(2002).校园暴力溯源及其防治对策.成都师范学院学报,18(2),2-4.
Bandura,A.(1974).Aggression: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6(1),1101-1109.
Bender,D.,&L sel,F.(2011).Bullying at school as a predictor of delinquency,violence and other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adulthood.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21(2),99-106.
Berdondini,L.,&Smith,P.K.(1996).Cohesion and power in the families of children involved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an Italian replication.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15(1),99-102.
Berger,C.,Batanova,M.,&Cance,J.D.(2015).Aggressive and prosocial?examining latent profiles of behavior,social status,machiavellianism,and empathy.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44(12),2230-2244.
Bjrkqvist,K.(1994).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verbal,and indirect aggression: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Sex Roles,30(3),177-188.Card,N.A.,Stucky,B.D.,Sawalani,G.M.,&Little,T.D.(2008).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ender differences,intercorrelations,and relations to maladjustment.Child Development,79(5),1185-1229.
Chan,H.C.O.,&Wong,D.S.W.(2015).The overla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assessing the psychological,familial,and school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4(11),3224-3234.
Chan,H.C.,&Wong,D.S.W.(2015).Traditional school bullying and cyber bullying in Chinese societies:prevalence and a review of thewhole-school intervention approach.Aggression&Violent Behavior,23,98-108.
Cross,D.,Barnes,A.,Papageorgiou,A.,Hadwen,K.,Hearn,L.,...Lester,L.(2015).A social-ec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duc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urs.Aggression&Violent Behavior,23,109-117.
Gage,N.A.,Prykanowski,D.A.,&Larson,A.(2014).School climat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a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 analysis.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29(3),256-271.
Juvonen,J.,&Graham,S.(2014).Bullying in schools:the power of bullies and the plight of victims.Psychology,65(65),159-185.
Lereya,S.T.,Samara,M.,&Wolke,D.(2013).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 risk of becoming a victim and a bully/victim:A meta-analysis study.Child Abuse&Neglect,37(12),1091-1108.
Olweus,D.(1978).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20(1),205-206.
Olweus,D.(1980).Familial and temperamental determinant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boys:a causal analysi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6(6),644-660.
Olweus,D.(1994).Bullying at school: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42(4),12-17.
Parkhurst,J.T.,&Hopmeyer,A.(1998).Sociometric popularity and peer-perceived popularity:two distinct dimensions of peer status.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18(2),125-144.
Pellegrini,A.D.,Bartini,M.,&Brooks,F.(1999).School bullies,victims,and aggressive victims:factors relating to group affiliat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91,216-224.
Pinker,S.,Buss,D.M.,Tooby,J.,Cosmides,L.,Kaplan,H.S.,Gangestad,S.W.,Campbell,L.(2007).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J.F.,Schneider,B.H.,&Mallet,P.(2012).Revisiting the whole-school approach to bullying:really looking at the whole school.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33(3),263-284.
Rigby,K.,&Smith,P.K.(2011).Is school bullying really on the rise?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14(4),441-455.
Salmivalli,C.,&Isaacs,J.(2005).Prospective relations among victimization,rejection,friendlessness,and children’s self-and peer-perceptions.Child Development,76(6),1161-1171.
Smith,J.D.,&Stewart,R.(2005).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s in schools:ingredients of effective programs.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28(4),739-762.
Smith,P.K.,Bowers,L.,Binney,V.,&Cowie,H.(1992).Cohesion and power in the families of children involved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an Italian replication.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14(4),371-387.
Sutton,J.,&Keogh,E.(2000).Social competition in school:relationships with bullying,Machiavellianism and personality.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70(Pt 3)(3),443-456.
Ttofi,M.M.,&Farrington,D.P.(2011).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programs to reduce bullying:a systematic and meta-analytic review.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7(1),27-56.
Turner,I.,Reynolds,K.J.,Lee,E.,Subasic,E.,&Bromhead,D.(2014).Well-being,school climate,and the social identity process: a latent growth model study of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29(3),320-335.
Veenstra,R.,Lindenberg,S.,Oldehinkel,A.J.,De Winter,A.F.,Verhulst,F.C.,Ormel,J.(2005).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a comparison of bullies,victims,bully/victims,and uninvolved preadolescent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41(4),672-682.
Wang,J.,Iannotti,R.J.,&Nansel,T.R.(2009).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physical,verbal,relational,and cyber.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dolescent Medicine,45(4),368-375.
Whelan,Y.M.,&Barker,E.D.(2014).MAOA,Early experiences of harsh parenting,irritable opposition,and bullying-victimization:A Moderated Indirect-Effects Analysis.Merrill-Palmer Quarterly,60(2),217-237.
(责任编辑 胡 岩)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2.0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同成长个体的心理贫困感与生命史策略、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16BSH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