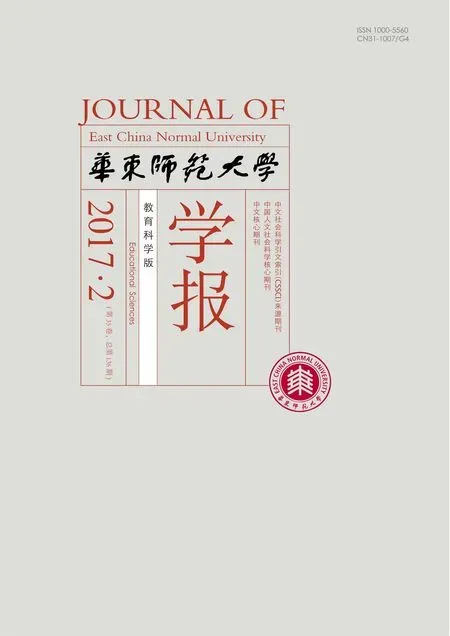在“延传变体链”上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
胡金木 栗洪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710062)
在“延传变体链”上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
胡金木 栗洪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710062)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往往被视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过去的教育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是需要抛弃的东西,也成为启蒙者所批判的对象。其实,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处于一种“延传变体链”之上的。教育发展的过程是教育传统不断重构的过程。教育现代化不是完全背叛传统,而是不断优化传统,是承续与革新的统一。然而,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逐渐被自卑情绪所代替,他们开始怀疑自身的教育传统。自身的教育传统从“无所不能”到“一无是处”。只有尊重自己的教育传统,才可能实现教育的启蒙。中国教育现代化既不能固守传统,亦不能抛弃传统,而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延传变体链”上重构教育传统,实现教育的启蒙。
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传统;延传变体链;启蒙
“传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词语,好像大家都明白,却又都说不清楚。传统一般来说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从范围分,有家族、团体、地区、民族、国家等区别。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某些积极的传统因素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辞海,1989,第561页)传统连接着人们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生活,它是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们世代相传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文化遗产,如价值系统、社会习俗以及日常行为方式等。美国学者希尔斯(1981/1991)认为,“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而这种世代相传的东西就是“文化遗传的总和”。既定的文化传统在时间的维度上从上一代延续至下一代,“在延传与承袭的相继阶段或历程中基本保持着同一性”;同时,这种传统的延传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是处于延传变体链之中的(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
一、“延传变体链”中的教育传统
任何“现在”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都包含着“过去”人们的某种想法,“现在”的想法也会影响着“未来”的人们;每一代人都是在前几代人的基础上“重构”着自己的传统,“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人们所生活其间的传统也是绝对不一样的。“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黑格尔,1928/1959,第8页)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教育观念,是活跃于教育发展中的动态的流变体。教育传统是一种时间性存在,表现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教育观念,意味着过去教育向未来教育的延伸。
(一)启蒙与批判:传统常常被误当作启蒙的敌人
传统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历史遗产,它深刻影响着特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启蒙运动以来,传统遭受到猛烈批判,“传统性成为每个旧秩序批评者无所不在的敌人”。生活在“传统”中的人,却把“传统”视为一个负担,一个累赘,一种需要根除的罪恶。“当传统性让位于理性和科学知识时,它所维持的所有邪恶也都将消失。”(希尔斯,1981/1991,第8页)
启蒙运动批判迷信、无知、偏见、权威,倡导自主、理性的生活,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理性思想与以理性为基础的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基本法则。民主与科学所要摈除的则是无知与偏见、权威与迷信,而这些东西则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若要向无知与偏见、权威与迷信宣战就必须向传统宣战,向传统的旧观念、旧秩序宣战。“人们一直赞誉科学和理性,视其为统治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法则之源。每当这时,传统就要遭到批判。”(希尔斯,1981/1991,第5-6页)所以,启蒙思想家在借助理性思想批判教会统治与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将“无知与传统联系在一起,两者似乎都是可恶的欧洲旧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性却在进步主义者中间背上了迷信所享有的那种坏名声”(希尔斯,1981/1991,第7页),与陈旧迂腐成为了同义词。好像,我们脱离了传统,就进步了,就是现代人了。
启蒙的否定性指向了传统秩序、制度、文化、观念、行为等方面,若是不批判负载在传统上的无知与偏见、权威与迷信,那么启蒙就不可能成功;同样,若是不加分析地把传统当作敌人,抛弃传统,启蒙也会变成空中楼阁。其实,传统并不是人们可以肆意抛弃的无用物,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文化前提,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启蒙不能离开传统,传统是我们理解历史,创造未来的根据。“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反思理解我们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伽达默尔,1960/1999,第355页)因此,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固守教育传统或抛弃教育传统,人们对教育传统的批判与反思是优化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在教育传统中理解、发现与创造新的教育传统;并且,教育“‘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传统’即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朱德生,1996,第51-57页)。我们生活在教育传统之中,指的是人们的教育观念和行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教育传统的影响。教育传统不仅影响着我们思考教育的方式,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传统是不变的、外在于我们的,它是内在于我们的,并随着现在乃至将来教育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教育传统在时间链上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希尔斯,1981/1991,第59-60页)。
(二)启蒙与承续:启蒙应该是一种传统的“重构”
把传统当作启蒙的敌人,仅仅是一种变革的策略: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传统所存在的问题,唤起人们变革的决心。传统之所以能够延传,是由于其具有同一性、持续性与变革性,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传统不是固化的整体,而是一种混合物,由长期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与各种创新构成。“任何叫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要经过接受、修改或抵制这样一个过程。对传统的反应带有选择性。即使那些自认为正在接受或抵制‘全部内容’的人,也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进行抵制的;即使当他们看来在进行抵制时,他们仍然保留相当一部分传统。显然,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希尔斯,1981/1991,第286页)
启蒙是一个新旧更替的过程,并不是以完全不同的“全新”来取代传统,而实际上只能是部分地变革传统。教育现代化是教育传统不断“重构”的过程。这种“重构”不是“背叛”教育传统而是“优化”教育传统,是承续与革新的统一。处于“延传变体链”之中的教育传统在稳定、延续中体现其历史性与可塑性。教育传统具有一种选择性机制,它会随着时空格局的变化而发生一种适应性的变化,从而进行一种“重构”。过去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念与社会教育习俗有可能成为现今人们的传统,也有可能被将来的人们所扬弃,进行一种传统“重构”,形成一种新的教育传统。教育传统正是在这种时间维度上的选择与重构中展现其延续性与可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传统是流动的文化积累。“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稳定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稳定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楼宇烈,1989,第9页)
传统作为族群共同的记忆,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延传变体链”之中。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不会觉得传统是一个问题,教育传统也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在社会出现激烈动荡之时,教育传统与现实生活就会出现摩擦,这时人们才会意识到传统是一个问题。这时,人们往往会以“危机心态”来认识教育传统,而这种心态往往会导致两种极端地认识倾向:一部分人认为,教育传统已经陈旧,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激烈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育传统已经失落,很多优秀的教育传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需要恢复传统以维护社会的发展。前者是一种抛开传统向前看的激进主义,它面对教育传统,主张“推倒重来”;后者则是一种固守传统向后看的保守主义,它面对教育传统,主张“复古守旧”。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以来这两种对待教育传统的价值倾向都是有问题的。残酷的历史表明人们往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而没有正确看待传统的连续性特征。近代以来,国人对待自己的教育传统就表现为一种钟摆式地现象,忽而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忽而激进主义夺回阵地,来回拉锯,争争吵吵百余年。从拒斥变革的“药方只贩古时丹”到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倒重来”式的“告别传统”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传统伦理、教义、偶像、权威等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几近荡然无存”(周策纵,1989,第27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下,教育传统呈现出了一种坍塌之势。
二、中国教育传统的逐渐坍塌
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启蒙是从反思与批判传统开始的,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没有对传统文化与教育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就不会有启蒙的发生。面对浑浑噩噩的人生,面对危机重重的国家,先知先觉者通过批判传统开启了中国教育的启蒙历程,教育传统与教育变革问题也开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一)从自负到自卑:教育在坚守中进行调适
晚清时期,“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以假定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费正清,1978/1985,第35页)。中国不属于世界,世界属于中国。世界各国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世界秩序,中国是内部的,既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中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渗透到文化教育上,则是认为中国的教育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模板,只有学习中国教育,世界各国才能摆脱“蛮夷”的身份。在看待教育传统方面,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有自信的。他们眼中的西方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西学仅仅是“奇技淫巧”而已,西学只能存于“器”,中学才是治世之“道”,中学也是人之“立身之本”。教育要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样,“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背叛之弊”,如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就明确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朱有瓛,1987,第78页)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也初步认识到“中学”亦有不足,“西学”亦有先进之处。面对国内危局,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学”、复兴“中学”以强国富民。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们认为“西学”仅仅限于技艺层面,而“中学”才是修身齐家治国之本源。“对于西方文化,只可接收其科学,接收其技术,接收其法度;对于己国文化,仍当保守其礼教,保守其伦常,保守其风俗。”(陈青之,2009,第608页)
面对西方的强势入侵,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盲目固守教育传统,而是企图通过“中体西用”来复兴教育传统,实现强国富民。洋务运动中新式学堂的建立与留学生的派遣,维新变法以及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兴学校”,都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教育传统进行了持续地改造。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之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慢慢地对于自己的教育传统有些不自信了,甚至有些自卑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对教育传统的依恋走向了对教育传统的批判。这两种对立情绪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话语中更是演变为一种“古今中西”之争。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实现全面的“新旧更替”,对“不合理”的“旧”传统、“旧”习俗进行批判,以“合理”的“新”制度、“新”观念代替之,还实现了一种“中西变换”,以“西”为“新”,以“西”代“中”。对于“西学”,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历了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吸纳过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态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已经完全地展现出来了。五四知识分子开始猛烈地抨击以伦理为导向的教育传统。陈独秀认为:“既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者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993,第179 页)他们在批判专制主义的同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教育传统及其代表人物孔子,要“打向孔子,破坏偶像”,认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在批判“吃人的礼教”的同时,把基于礼教的“家庭制度看作是万恶之源”,认为一切与儒家相关的制度、礼仪、规范、教育都应统统丢弃。“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丧失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葛兆光,2001,第545页)
(二)从部分到整体:强烈地否定教育传统
从认为“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有“舍己从人的必要”,到认为“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教育传统的批判逐渐强烈。中国教育从对传统的局部批判转向全面化的否定,从建立一批新式学堂,到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再到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观念都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晚清以来的教育变革之所以没能实现自救,国家依旧一副破败而混乱的景象,国民依然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五四知识分子把关注投向了国民性上,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问题,归结于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传统,归罪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传统已萎缩为附丽于皇权政治和家族社会的一套礼俗规范。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张灏,1989,第54页)他们认为国家的富强、国民的改造与教育的变革需要着眼于全方位、深层次的文化思想批判,需要“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儒家的文化教育传统,而不能是修修补补式的局部批判。
正是在外力的冲击下,儒家传统从“无所不能”到“一无是处”,教育的优越意识逐渐地被自卑情绪所代替。一个导致传承人屡次三番遭受痛苦的传统,自然就会受到排斥。正是在这种自卑意识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嫌弃自身的教育传统。正如希尔斯所言,“如果传统给继承它的人带来明显的和普遍的不幸后果,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了;一个传统要延续下去的话,就必须‘发挥作用’。一个传统反复带来灾难,或反复被证明明显不灵,那就行将灭亡了”(希尔斯,1981/1991,第286页)。
基于儒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规范制度、行为方式、教育观念等是一体化的,是近代中国处处落后、时时挨打的思想根源。“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转变,如要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林毓生,1989,第3 页)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秉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传统的道德教化系统给予了一种否定性的评价。“最可憾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撮激烈的人士,他们只看到中国文化之黑暗面,把精力悉数用到破坏文化传统上去,他们反对社会既存的结构与价值,带着一种狂热的性格,寻求新事物,如中风狂走,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都被一一肢解,而他们所展开的‘批判运动’,便变成了‘否定运动’或‘打倒运动’。”(金耀基,1999,第27页)
在以“西”为“新”、以“西”代“中”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思想历程。“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林毓生,1989,第2页)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成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人们认为,教育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从批判孔子开始。“儒学和祖国遗产(包括其合理内核、精深大义)遭到全盘否定。”(周策纵,1989,第29页)教育把传统视为一种负担,要极力摆脱它。“在近数十年来的中国,‘传统’却被多数人看作一个贬义词。更不幸地,人们对于‘传统’所涵摄的确切意义并无适当了解,对于‘传统’的憎恶径达于极点。”(余英时,2006,第121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中,一切儒家传统都被当作批判的标靶,一切与儒家传统有关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实物器具、行为方式等统统被视为糟粕。在这种情况下,“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东西,礼仪规范是束缚人的东西,儒家经典是腐朽的东西,历史文物是封建的遗存。一句话,全面反传统,不管优与劣,精华与糟粕,“旧”的就是要抛弃的。
近代中国的教育传统重构并不是文化系统内的知识分子自觉、自发推进的,而是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为应对外来压力而被迫进行的。正是在这种危机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并未能“心平气和”地理性地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古今中西等问题。五四知识分子激烈地反传统,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旧”观念,迎接“西方”“新”教育,造成了教育传统的割裂。甚至直至今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未能扭转教育研究中的“重西方、轻传统”的思想断裂状况。
三、“延传变体链”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开始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也强烈地冲击到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全面的挑战。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教育传统受到的挑战与冲击更为明显,以至于先觉者要“冲决伦常之网罗”。中国知识分子从固守教育传统到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现代学制、拟定教育宗旨等,向教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批判儒家教育传统,吸纳新学的同时,并未给予儒家教育传统应有的尊重,而是抛弃了这些传统,甚至在五四时期还出现了强烈的“全盘西化”与“反传统”倾向。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需要以此为戒,不再重蹈百年前的覆辙,在教育传统的“延传变体链”上“重构”传统,实现新的教育启蒙。正如杜威在百余年前所说的那样:“一国的教育绝不可胡乱模仿别国。……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学说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如此做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杜威,2008,第407页)
(一)动态生成中的教育传统
虽然传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某些经验参照系统,但每一代人的具体生活情景都是不同的,所以,“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去改变它们”(希尔斯,1981/1991,第2页)。教育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吉登斯,1990/2000,第33页)抛弃自己的教育传统是没有出路的,固守教育传统当然也是一条死路,这就需要在“反叛传统”与“返回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批判与反思旧的教育价值观念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批判与反思不能建立在“自卑情绪”之上,不能不考虑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境遇,不能完全抛弃自身的教育传统而盲目吸收西方的教育价值观念。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批判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让人们认清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教育传统的局限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执着于教育传统的批判与西学的崇拜,而未能心平气和地审视西方教育的局限性与自身教育的优越性,以“虚无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态度建设我们的教育,这直接导致教育传统的重构一直没有完成。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中国教育传统出现了断裂,教育传统价值观念或被击碎,或被丢进了历史的仓库而束之高阁。“中国的现代化工作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根本无一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是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的。”(金耀基,1999)将教育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传统是现代的模板,现代是未来的模板。现代教育是传统的“重构”,现代教育也是未来“重构”的基础。“所谓的‘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余英时,2004a,第8页)
(二)建设性地反思与批判
在近代中国,教育传统被视为现代的对立面,“过去的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是亟需抛弃的东西。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要摆脱国内黑暗的政治,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不能仅仅立足于器物、制度,而要着眼于文化的改造。他们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灰烬上,才能重建中国文化”(张灏,1989,第54 页)。
譬如,在道德教育传统方面,被批判最多的当属“孝道”教育。“孝道”是基于自然血缘而形成的一种情感关系,强调后辈对长辈的敬爱忠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特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道”观念在近代以来遭受到前所未有地批判。从“百善孝为先”到“万恶孝为首”,“孝道”成为现代生活的最大障碍,被认为是戕害人性的罪魁。那么,“孝道”能否简单的抛弃呢?能否因为“孝道”而抛弃道德传统呢?
关于父子关系,孔子期望实现“父慈子孝”这一父子双方相对称的义务体系,既主张子对父的“孝”,又强调父对子的“慈”。而到了董仲舒那里,父子关系就演变为单向度的“子孝”,这片面地强调了孝道。这一片面强调“孝道”的伦理关系成为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到了近代,“孝道”就演变为教人顺从长上,这不利于个性的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也无从生发。毫无疑问,这种片面强调子女义务、不尊重子女的人格、单向度的“孝道”需要摒弃,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抛弃中国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教育,抛弃“父慈子孝”的教育传统。
在父母与子女关系疏离的当今社会,“父慈子孝”的教育传统犹为重要,是维持家庭和谐的重要情感支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固守“孝道”传统,回到那种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孝道”之中。对于“孝道”教育,我们需要结合现代生活,引入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构”。“孝道”教育传统需要实现一种转化,从单向绝对的道德义务到双方对等的道德义务,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不能成为父母支配子女的理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也不能成为子女忤逆父母的理由。
传统代表着过去,批判意味着革新,对“孝道”这一教育传统的批判有着积极的意义。若是不批判片面强调“子孝”的伦理关系,自由平等的个体就难以诞生,现代民主政治也无从建立。但是这种对道德教育传统的批判不应该是单纯否定性的,“破而不立”就会使传统失落,亲子关系疏离,这同样难以实现双向平等的“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对道德教育传统缺少尊重,就会使我们的教育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对待传统,我们要建设性地批判,而不要摧毁性地批判,要对教育传统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三)在“延传变体链”上思考中国教育
在中国社会教育启蒙的过程中,要自觉地调整并扩大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现代教育模式的同时,应批判地看待它们。中国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教育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对中国旧的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对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金耀基,1996)。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2008)就已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中国,而不是不顾中国国情的模仿。“吾人试观夫中国之教育,实胚胎于日本,直接模仿日本之教育,而间接模仿德国之教育。不知欲定一国教育之宗旨和制度,必须审国家之情势,察国民之需要,而精心定之。绝不可不审国情,不察需要,而漫然效颦。”(第200页)抛弃教育传统、不顾国情地胡乱模仿,到头来也只能演绎“东施效颦”的教育笑话了。
“传统不仅仅是沿袭物,而且是新行为的出发点,是这些新行为的组成部分。”(希尔斯,1981/1991,第62页)当代中国教育既不能固守传统,亦不能抛弃传统,而要立足本土教育境遇与教育传统脉络,关注到教育传统与现代的连续统,在教育传统的“延传变体链”上重构教育传统。虚无之上没有现代教育,灰烬之上无从建设现代教育,教育启蒙只有立足于传统这一基石之上才有可能。离开了教育传统,现代教育什么都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也不例外。无论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进和反社会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希尔斯,1981/ 1991,第50页)
若是我们把自身教育传统摈弃,现代的我们将无所依凭,摧毁教育传统就是毁灭自我。现代人需要传统。教育传统需要尊重,不需要固守。“在现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把传统当作社会进步发展之累赘的学说,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错误。”(希尔斯,1981/1991,第440页)今日的教育变革要注意到教育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传变体链”。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传统是何种意义上的传统,现代教育又是怎样的现代。每一种教育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我们在借鉴西方的教育现代化理念与方案的同时,也要关注到自己的现实境遇与教育传统。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能遗忘自己的教育传统而盲目移植。固守教育传统、拒斥现代不行,遗忘教育传统、盲目移植,也是不行的。所以,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张力,中国教育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反”与“返”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才有可能实现教育传统的“重构”。
“如果中国人能够不受约束地消化他们所需要的西方文化,同时排斥他们视之为是糟粕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传统之上获得健全的发展,通过把我们的优点同他们的精华结合起来,而产生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转变期间,需要避免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被全盘西化,使得他们的不同凡响之处荡然无存。……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被逼迫成为极端排外的保守主义分子。”(罗素,2006,第162-163页)先哲的告诫言犹在耳。教育传统永远在变动之中,但没有一个民族的教育能够放弃其传统重新开始。“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文化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post-modern)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余英时,2004b,第38页)
陈独秀.(1993).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青之.(2009).中国教育史(下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辞海编辑委员会.(1989).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杜威.(2008).杜威教育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费正清.(1978/1985).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葛兆光.(2001).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黑格尔.(1928/1959).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吉登斯.(1990/2000).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伽达默尔.(1960/1999).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金耀基.(1996).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7.
金耀基.(1999).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林毓生.(1989).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楼宇烈.(1989).论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9.
罗素.(2006).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希尔斯.(1981/1991).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2004a).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总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余英时.(2004b).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2006).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灏.(1989).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周策纵.(1989).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朱德生.(1996).传统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1-57.
朱有瓛.(198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 岩)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2.011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小学生正义品质的培育机制研究”(CAA15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