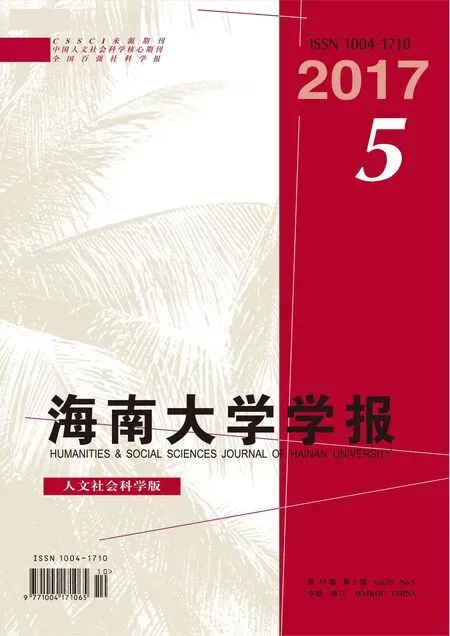论康德从道德到宗教的推理
刘 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论康德从道德到宗教的推理
刘 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在康德那里,理性追求无条件者的本性,导致在理论领域中出现二律背反,然而它不足以产生在实践领域中的至善的二律背反。人的有限性是理性在实践领域中产生至善的二律背反的根源。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理性扩展道德学的范围,把至善作为道德法则的结果引入道德学之中;另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至善只有在宗教中才具有可能性,同时上帝得到相应的规定。人的有限性这一视角清晰地呈现康德从道德推导向宗教的思路,并且能够澄清学界的一些误解。
理性;至善;道德;宗教;人的有限性
很多人仅仅从义务论的角度研究康德的伦理学,忽视康德伦理学中的宗教维度,或者对康德的宗教学说有误解*罗伯特·约翰逊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现代道德哲学理论》编写的“康德的道德哲学”词条中详细地展现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学说,然而没有涉及康德的宗教。这代表西方学界的一种研究思路。参见罗伯特·约翰逊:《康德的道德哲学》,阮航译,陈燕校,《德国哲学》2014年,第129-158页。对康德的宗教学说的误解本文后面会涉及。需要说明的是,在康德那里,道德学是伦理学的理性部分,本文的主题不涉及实践人类学,所以没有严格区分二者。。在康德那里,道德的基础是纯粹意志的自律,意志不考虑行为的结果,只应当遵守纯粹理性的法则。道德是自足的,不需要在理性之外寻求其他根据。然而,康德有一个著名的命题“Die Moral führt unausbleiblich zur Religion”,译为“道德不可避免地引向宗教”。unausbleiblich 有无法避免的意思。康德一再强调道德与宗教的关联,比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里,康德在说明思辨理性无法达到对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的知识之后,得出结论:“因此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我们要放弃把这些超验的理念当作我们知识之对象的企图,而应该把它们当作信仰的对象,放在自由的领域。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提到上帝作为至善的公设时,提到:“以这种方式,道德律就通过至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和终极目的的概念而引向了宗教,亦即引向对一切义务作为上帝的命令的知识”*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可见,康德的立场很清楚,即道德导致宗教。更进一步来说,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问题是:为什么道德不可避免地引向宗教?如果没有宗教,道德会怎么样?
一、理性与无条件者
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的“理性的纯粹运用”这一小节中,具体地描述了理性能力。理性在逻辑的运用上是以推论的形式,针对的是概念和判断,力图将杂多的知性的知识归结为更高的乃至最高的原则。所以理性的逻辑准则就是“如果有条件者被给予,则整个相互从属的本身是无条件的条件序列也被给予(即包含在对象及其连结之中)”*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第233页。。有条件者与其条件是分析地相关,都属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但是整个条件序列是无条件的,超越可能经验,在经验中不可能有相应的对象,无法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追寻无条件者是理性的自然倾向,由于这种无条件者既不能在经验中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所以以它们为对象的形而上学总是处于“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的状态。
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更好地说明了形而上学所处的状态,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指出:“纯粹理性在其超验应用上的这一产品是纯粹理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一切现象中也是最有力地作用于把哲学从其独断论的安睡中唤醒,并推动它去从事理性自己的批判的艰难工作”*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这一产品”指宇宙论的理念,是理性超出可能经验范围推论得到的无条件者。独断论和经验论的不同思维方式使理性的这种推论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在条件的系列中推出一个无条件的存在者,它处于系列的顶端,使得整个序列具有完备性;一个是把整个序列看作无条件的。因为这两种思维方式所得到的结论是相反的,虽然都无法在经验中得到证实,但都可以得到证明,所以二者相持不下。这种状况比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些先验理念更好地展示形而上学所处的混乱状况,说明理性批判的迫切性。毕竟后面两个理念虽然也是超验的,但是关于它们的结论都是确定的,表面上具有科学的确定性。二律背反的出现直接显示出理性在追求原则的统一性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无法保持自身的一致性。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区分现象和物自身,把这些理念放入物自身的领域,不再是我们知识的对象,即使它们在知识领域依然具有调节性的作用。
理性在实践上的运用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追求无条件者是理性的本性,在理论的运用中,理性只具有调节性的(regulativ)运用,但是在其实践的运用中,理性具有构成性的(konstitutiv)运用。理性在自由的领域是立法性的,给人的意志颁布道德法则。理性抽掉所有感性质料性的东西,在它给意志立法时,所颁布的法则只能是一条形式的法则。这条法则并没有告诉我们作某种具体的行动,而是要求我们的准则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法则。从感性的质料上来看,道德法则是空洞的,没有把任何质料性的东西放入其中。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道德法则又是有内容的,它表达了理性以自身为目的的要求。如果意志服从理性的法则,那么意志的准则就是法则,此时理性在实践运用中能够保持自身的一致性。
实践理性所产生的辩证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种法则本身,一个是法则的对象。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一章中,康德提出“自然辩证法”,认为普通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一样,也会产生辩证法,这种辩证法“除了在对我们的理性的一个彻底的批判中,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安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这种辩证法具体体现在,人们即使知道应当做什么,由于感性爱好的强烈要求,他们仍然会怀疑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严格性,从而把爱好的满足放在第一位。道德法则与爱好的准则之间的对立,要求普通的实践理性走出其朴素性的状态,上升到实践哲学,对纯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指出,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严格性的基础在何处,即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是可能的?康德在这部著作的第三章,通过对定言命令的演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邓晓芒教授把这里的“自然辩证论”等同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关于至善的二律背反,他认为:“但这里的意思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意思是一致的,就是指实践理性中的二律背反”(邓晓芒:《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对道德法则的有效性的怀疑所产生的辩证法,后者是在道德法则已经确立起来之后,由道德法则的对象所产生的辩证法。前者是在《奠基》第三章所要解决的问题,后者才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本文没有严格区分道德法则和定言命令,准确地说,前者适合于一切的理性存在者,后者适合于有限的存在者,比如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理性的事实”这一概念,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都有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这说明道德法则对我们是有约束力的。不管这两个文本的解决思路有何关联,可以确定的是,康德在理性的范围内解决了这一“自然辩证法”。
理性不借助于任何感性的爱好直接规定意志,道德是自足的。然而,道德行动在自然中发生,受到在先的事件的影响,同时也产生相应的后果。康德批判幸福主义伦理学,把伦理学建立在纯粹理性上,这并不意味着行动的结果不属于道德学关注的范围。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认为:“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第530页。。道德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实践的,依然是道德学所关注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对结果的关注,道德学是不完备的,即使结果不能作为行动的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规定为“作为自由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的表象”*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71页。。一个对象是善的,意味着如果人有合适的能力,他愿意采取行动把这一对象产生出来,使得这一对象的观念变为现实。对恶的规定与之相反。善恶的评判由道德法则规定。我们将一个对象评判为善的,它必须在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都是被欲求的对象;我们将一个对象评判为恶的,它必须在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都是被厌恶的对象。
理性的本性要求它不满足于个别的对象,而是不断地追求无条件者。理性需要为道德法则的对象寻求无条件者,即最高的善。“最高的”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作为不是其他条件的条件,一种是完善的整体。如前所述,这两种无条件者体现了理性追寻无条件者的不同方式,在理论领域,分别表现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的推论方式。在实践领域中,道德法则是我们意志的直接规定根据,是无条件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最高的善。第二种意义上的善就是德福一致,其中道德法则是分享幸福的条件,康德称之为至善。理性的本性需要无条件者,只有在无条件者那里,它才可以得到满足。无条件者超越经验,理性在提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求时,会导致冲突,二律背反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那么,在确定了无条件的道德法则的有效性之后,康德为什么要把至善放入其道德学之中?
二、至善与人的有限性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提到,我们理性的一切兴趣集中下面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在1793年他写给司徒林的信中,康德加上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人类学,2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道德学的问题,即我应当做什么,因而我能够做什么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的问题,即我可以希望得到什么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的问题,即我能够做什么和现实地做什么的问题。康德的思路是,人是一个自由的存在者,因而我能够做道德法则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也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当我做了道德的事情之后,我希望得到幸福,而这种幸福只能在宗教中获得满足。
理性在实践领域具有构成性的使用,它直接规定意志,给我们颁布道德法则,同时规定我们意志的对象,即善与恶。然而,理性对无条件追求的本性,使得它不满足于对特殊的善与恶的规定,而要求对全部的善做出规定。“它作为纯粹实践的理性,同样要为实践上的有条件者(基于爱好和自然需求之上的东西)寻求无条件者,而且不是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是即使在这个规定根据(在道德律中)已被给予时,以至善的名义去寻求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121页。一个遵守道德法则的意志为自己设定目的,其行动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这些目的形成等级序列,有的目的是有条件的,以其他目的为条件。处于这个序列最高的是德行,幸福也在这个序列之中,但是它以德行为条件。这样就构成一个称之为至善的完善的总体,寻求至善体现它无法摆脱的自然倾向。然而如前所说,道德是自足的,理性不考虑行动的结果就直接规定意志,那么理性为什么还要把至善作为道德行动的完善的对象放入伦理学之中呢?
把至善放入伦理学中,康德有进一步区分意志的规定根据与其对象的考虑。在《奠基》中,康德没有提到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他批判最多的是同时代的幸福主义伦理学,后者把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至善的问题此时不是他所关注的问题。然而,他发现,古代人把至善作为道德研究的主题,使之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明显地透露出错误,近代人虽然没有把至善问题作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把上述错误(如同在许多别的情况下那样)隐藏在一些不确定的词句后面,然而人们仍然从他们的体系中看出这种错误在透露出来”*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78页。,这种错误在于,他们把某个对象当作意志的规定根据,显示出意志的他律。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在德性原则中实践的质料规定根据表”中,他把沃尔夫和斯多亚学派放在一起。二者都把完善当作意志的规定根据。不管是古代人还是近代人,都可能会混淆意志的规定根据和意志的对象。通过对至善问题的探讨,康德进一步区分二者,维护道德法则的纯粹性。然而,康德在具体探讨至善概念的二律背反时,并没有着重批判近代哲学混淆二者的误解。因而笔者认为,康德把至善放入伦理学中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
人的有限性是至善概念进入康德伦理学中的根本因素。在1784—1785年冬季的《人类学-蒙格荣维斯》(“Anthropology-Mrongrovius”)中,康德认为,道德学如果没有人类学,那么就只是学院式的,不能运用于这个世界,“人类学与道德学的关系类似于空间几何学与大地测地学”*Kant,“Lectures on Anthropology”,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eds.,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45.。虽然在与这个讲义几乎同时出现的《奠基》中,康德经常批判把道德学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学不需要考察人的本性。人的有限性体现在,在理论领域中,人需要感性直观,他对对象的认识是分析的普遍,而不是综合的普遍;在实践领域中,人有感性的爱好,对爱好的追求甚至比道德法则更能让人感到兴趣,以至于它会诱使人做违背道德法则的事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论证敬重是唯一的道德动机时,提到人有“自爱”和“自大”的倾向,这些概念都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
幸福是人必然追求的一个目的,“获得幸福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者的要求,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37页。。纯粹理性不会不考虑人的这一需求,只不过它将幸福不是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是把幸福看作意志的有条件的对象,所以道德学是配享幸福的学说,而不是如何追求幸福的学说。人重视幸福,重视从行动产生的结果,这是人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把目的的概念引入道德学,而由此使道德学进入宗教。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第一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道德是自足性,不需要先于意志规定的目的概念,但是目的概念和意志仍然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即使目的不是充当意志的规定根据,也可以成为意志的必然结果。这种关系表现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即“要使尘世上的可能的至善成为你的终极目的”*康德:《单纯理性界限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这个命题是由道德法则所引入的,道德法则命令我们追求尘世的至善。至善不是道德法则的根据,而是道德法则要求我们追求至善,在这个世界上产生至善的效果。问题是,道德法则是纯粹形式的,不考虑行动的任何后果就给我们颁布无条件的命令,它为什么把行为可能的效果作为义务呢?在康德看来,在作用因的秩序中,目的是最后的,它通过实际的行动产生出来,但在观念的秩序中,目的是最先的,它先于行动。人具有在法则之外为一切行动设想一个目的之自然属性,在行动之前,人都会考虑此行动会导致何种目的,试图从目的中寻找自己喜爱、而非敬重的东西。道德法则为了照顾人的这一属性,扩展自己,把目的考虑进来。所以这个命题的综合性在于人的有限性的本性,其概念的可能性在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一个遵守道德法则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把至善当作自己的义务,力图在这个世界中产生至善的后果。正如菲力茨塔斯·慕策指出:“考虑我们任性和行动的目的首先导致人作为行动者履行目的的问题,它超出了道德法则……道德责任的问题不仅与从形式上来说与人们的义务相关,而且与人们的行动(由道德法则命令的目的之实现)相关。”*Felicitas Munzel,“What does his Religion contribute to Kant’s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reason?”Gordon E. Michalson ed.,“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 Critical Gu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15.康德把目的作为行动的后果引入道德学,扩展了道德学,使得道德法则具有质料性的内容。
三、宗教的必然性与人的有限性
人的有限性也使得从道德推向宗教成为必要。康德批判斯多亚学派未能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从而丧失解决至善的可能性问题的契机。在他看来,在解决至善问题时,古希腊诸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在规定至善时,都错误地把道德和幸福看作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把幸福原则误作道德的法则。斯多亚学派把德行当作幸福的原因,正确地选择了至上的原则,可惜他们依然无法解决至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上帝,仅仅凭借德行就可以解决至善的问题。康德批判斯多亚学派把人提到智者的地位,忽视人的有限性,以为人可以在今世达到自己的德行的完善性。殊不知,人对幸福的追求使得他总有违背道德法则的倾向。人需要与这种倾向做斗争,这种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的道德完善总是逐步进行的,所以人在此生无法达到道德的完善,纯粹实践理性才需要悬设灵魂不朽。斯多亚学派认为,智者能够完全不顾及感性爱好的影响,即使处于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所以人在此生能够达到德行的完善。“但在其中,他们通过他们自己本性的声音本来就已经能够被充分驳倒了”*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139页。,实际上智者也难以摆脱感性爱好的需要,斯多亚学派的道德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英雄主义,没有现实性。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也从这个角度批判此学派。智者自以为有一种崇高的方式,把帮助患难的朋友、而不期待得到朋友的帮助看作自己的原则。然而,在朋友真的需要帮助时,这位智者却推脱:“这关我什么事?”*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正视人的有限性,重视人的感性需求,这是康德伦理学和斯多亚学派的最大区别。
从道德如何推理到宗教的问题就变为从至善的可能性如何推理到上帝之存在的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认为,道德法则具有效力需要预设上帝的存在。这是何种效力?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那么道德法则要求我们实现至善就是不可能的,道德法则就是一种幻相。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上帝存在,至善就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摆脱道德法则的约束呢?一个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是否也能够不承认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呢?康德以不可置疑的口气回答:“不!只不过谁要是那样,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遵守道德律在世上实现终极目的的这种意图。”*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第483页。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在任何时候都得承认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受到道德法则的约束,因为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只是如果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他就无法希望获得与遵守道德法则相应的幸福。康德此时非常明确地回答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上帝与道德法则的关系问题,上帝本身不是道德法则有效性的根据,而只是使得道德法则有效的结果,即尘世中的至善具有可能性之根据。
我们从至善的概念中,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他之前的形而上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认为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都犯了从概念跳跃到存在的错误。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本体论证明的结论“上帝存在”(Gott ist),并没有进一步规定上帝具有何种属性。康德给予自然神学的证明方式一些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把意图的概念引入对自然的观察,鼓舞了对自然的研究,但是它只能推论出整个自然有某种原因性的根据,无法进一步得到这一根据具有何种属性的结论。依至善的概念,人的德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至善的可能性需要悬设灵魂不死。人有幸福的需求,幸福需要人认识和掌控自然规律,人无法掌控这些因素,所以从道德无法直接产生幸福,理性需要悬设一个全能的存在者,即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全知的,知道每个人是否是道德的;上帝是全能的,能够为每个人的行动分配相应的后果。
如果《实践理性批判》着重从人对获得幸福的希望来推导上帝的属性,那么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侧重以人的从恶转变为善的希望来推导上帝的属性。人具有根本恶的倾向,倾向于颠倒道德法则与幸福原则之间的应当的秩序。这种倾向植根于人的意志的自由运用之中,人到底有没有可能根除这种倾向,一棵坏树如何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康德提出上帝具有三种属性,即圣洁的立法者、慈善的统治者和道德上的照料者以及公正的法官。对于第二种属性,康德给出如下说明:我们不能把上帝的慈善设定在对人无条件的宠爱中,而是必须设定在“他首先关注这些造物借以能够使他喜悦的那些道德品性,只是在此之后才来弥补他们在由自己满足这一条件方面的无能。”*康德:《单纯理性界限限度内的宗教》,第146页。人应该努力摆脱自己的恶的倾向,履行自己的义务,以之为基础,人才有可能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善人。
可以看出,康德对上帝的规定与传统的宗教不同,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于康德从上帝到宗教的推导,学者们有一些异议。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推导以神义论为隐形前提,在一个“义”的世界里,“人应当都是有德之人,而世界也应当保证有德之人都享幸福”*李秋零:《道德并不必然导致宗教——康德宗教哲学辩难》,《宗教与哲学》2013年第二辑,第150页。,这样的世界只有在一个“义”的上帝那里才可以得到保证。在笔者看来,康德强调人应当是道德的,这是从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的角度来说的。人具有理性,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前者并不使得他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他此时依然服从机械的自然律,只有后者才使得他具有独特的价值,能够摆脱外在的规定而自行开启一个现象的序列。这是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无法则的,而是受到理性的规定。自由的存在者所遵循的是理性的法则,即道德的法则*韩志伟教授指出:“历史导向、逻辑导向和问题导向构成了把握现代自由问题的复杂性的三种方式,他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揭示了现代自由问题的复杂面向。”(韩志伟,吴鹏:《如何切中现代自由问题的复杂性》,《理论探讨》2016年第6期,第50页)康德的自由概念为现代自由奠基,本文暂时不做详细论证。。不过,由于人的有限性,自由这种能力并没有在现实中完全实现出来,而是一种应当不断完善的能力。也由于人的有限性,人希望德福一致,由此种希望,他会赋予上帝以相应的属性,悬设上帝的存在。可见康德的推导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理性要求我们做一个道德的人,人的有限性使得他希望获得幸福,从而由道德推导到宗教。由此神义论不是这种推导的前提,而是它的结果。
在《逻辑学》解释信念的一个很长的脚注中,康德指出,信念是契约中的忠诚,因为一个人要对他人信守自己的承诺。“按照类比,实践理性仿佛是承诺者,人是受诺者,而预期由这个行为而来的善则是承诺。”*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实践理性意识到人的有限性,给人做出在他做了应当做的事情之后,能够获得幸福的承诺。人接受这个承诺,它给人带来对未来的希望,虽然它本身不是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由此,实践理性就必须履行承诺,否则它就失信于人,无法与自身保持一致性。这个承诺只有在宗教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实践理性把自己从道德的领域扩展到宗教。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这是实践理性自身的要求。
四、结论
理性具有追求无条件者的自然倾向,使得它在理论领域中产生二律背反。然而这种自然倾向只是实践理性产生至善概念的二律背反的必要条件。只有考虑到人的有限性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为何把至善概念放入他的伦理学中,以及对至善概念的二律背反的解决为何诉诸宗教。因而从人的有限性这一视角能够更好地说明道德何以必然导致宗教。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宗教概念不同,康德把宗教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虽然没有宗教,道德是自足的,可以自成体系,但是它忽略了人的有限性这一个重要的方面。考虑到人的有限性,至善是必须的。至善只有在宗教中才有可能性,宗教赋予理性以一个新的维度,即人有获得幸福的希望。现代人不一定认同康德的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的观点*克劳斯-迪阿特·奥斯特欧维尼指出,康德的宗教概念虽然在他那个时代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现代影响却小得多。这与人们对宗教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关。因而,康德的命题,即一个过着没有宗教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快乐的,在现代获得认同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但是康德的另外一个命题,即‘宗教是每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28:1323)有可能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同。”(Claus-Dieter Osthōvener,“Religion”,Marcus Willaschek and Jürgen Stolzenberg eds.,“Kant-Lexikon”,Berlin: De Gruyter,2015,p.1960.)王天成教授指出:“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在宗教诠释的范围内提出‘爱’‘生命’的本性是对立统一。”(王天成,田伟松:《绝对精神在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演进过程》,《理论探讨》2015年第3期,第60页)黑格尔把宗教与道德联系起来,体现康德对他的影响。。在现实中,一方面,有道德的人不一定有宗教信仰;另外一个方面,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一定有道德。然而,康德的这一观点体现每个人所关注的问题: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在理性的指导下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引起人们超越经验的世界,思考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宗教的问题。
OnKant’sReasoningThatMoralityLeadstoReligion
LIU Zuo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In Kant’s Philosophy, nature that reason pursues the unconditional produces antinomy in the field of theory, which, however, is not enough to produce the antinomy of the highest good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 is the root of the antinomy of the highest good that reason produces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 enables reason to extend the scope of ethics, and the highest good, as the object of the moral law, is put into eth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makes the highest good only possible in religion, and God obtains the corresponding attribut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 clearly shows how Kant deduces from morality to religion, and clarifies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academic field as well.
reason; the highest good; morality; religion;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
B516.31
A
1004-1710(2017)05-0101-06
2017-04-0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X04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MLC005)
刘作(1983-),男,湖北仙桃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