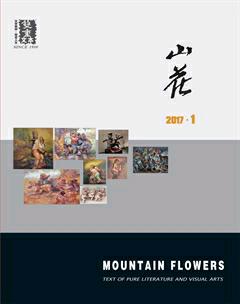邂逅
姜东霞
一
只有在雨天,这座南方城市,才会让人感觉出冬天的清冷。潮湿的街道,潮湿街道上的开紫花的树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紫花,从树上坠下来,满街都是。
那会儿,雨突然就停了。雨一停,阳光就出来了。那是下午近黄昏之时的阳光,既柔和又刺目。冬天的文林街道路正在施工,两边车道堵得水泄不通。
Z带着儿子坐在公交车上,她心烦意乱。跟他之间的事让Z整夜失眠,这会儿,患有轻微自闭症的儿子在学校里不断受到委屈,于Z也无异于雪上加霜。走投无路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情感处境。Z这样想的时候,后面的司机焦躁地按喇叭,刺耳的喇叭声穿破了街道,车流已经停止移动,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街道上人群的密度增加了混乱。
Z也是刚从学校将儿子接出来,跟老师对话的情形,让Z无法释怀。儿子刚上初一,Z费尽周折给儿子选择了K城的这所重点中学。孩子住校每周接送一次,算是一种心理上觉得亏欠儿子的弥补。
老师一早就打电话让Z到学校一趟,这是请家长。正好县委有个重要的会,Z无法请假,这让老师很恼火。
老师把儿子叫到Z的面前时,搡了他一把说:“这样的学生我们教不了。”
儿子歪了一下,抻了抻衣服低着头站在那里。这个动作像针扎在Z的心上,敢怒不敢言的Z低声下气地说:“老师,能不能鼓励一下孩子,给他一点信心。”
老师坐到椅子上,她的脸不经意间露出了嘲讽:“他要有值得我鼓励的地方呀。”
Z欲言又止,她不知道老师怎么会这样说话。
司机不再按响喇叭,整个情形出现了暂时的混乱和持久的焦躁。
儿子的小手在Z的手里,他们相互握得很紧。Z完全能感觉到儿子的紧张。Z转头看儿子,儿子正眯缝着眼看窗玻璃上射过来的阳光。窗外一对夫妇牵着背书包的孩子走过来,一家人其乐融融,Z为他们看上去的那种幸福,为没有给儿子足够的关心感到自责。如果没遇到他,自己是不是就不会用那么多时间来忽略儿子,儿子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患上自闭症?这个残酷的事实,是Z不断逃避的,她不相信医生,在老师面前极尽所能地掩盖,她更不能够面对的是现在这个结局。这个世界的后悔永远都是在无法挽回的时候,现如今鸡飞蛋打,Z除了悔恨别无他法。
Z转过头,心里有点不安,她向窗外望过去。太阳的一缕光芒映照在路边上那家咖啡馆的玻璃上。透过咖啡馆的玻璃,Z看到了她。Z的心在猛然的惊诧间狂乱地跳起来。Z的身体朝前倾了一下,将整个头抵到了车窗上。
这不可能。Z这样想的时候,她感觉到心在猛烈的跳动中隐隐地抽搐。她的出现毁了Z关于爱的全部想象或向往。
是她。Z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她长得非常清秀。她的样子让Z感到刺痛。
Z的身体像是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撞击,整个地开始晃动起来,眼睛也因为太阳光的照射有点迷乱。
就是她。她不在这个城市。她一定是因为他而来的。Z想到这里,就有芒刺样的尖锐之物顺着窗外耀眼的光芒扎进了心里,这样的感觉让人有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半年前他出外学习,遇见了这个女人,一切就都变了。他开始回避自己,东拉西扯地拖延见面的时间,或根本就不说见面。
Z不是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而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痛感。被人抛弃是女人倍感羞耻的事。或许Z最想掩盖的就是这种感觉,Z更愿意将一切想成是爱。把一切羞辱和疼痛都想成是爱,也许会好过一些或更尊严一些。在政府部门习惯了一切把戏的Z,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尽管Z仍然行有夫之事,但是她对他的每一次表达,都充满着期待。当Z明白自己真的失去他之后,凭着自己做秘书工作的机敏,便从众多的与他一起学习的人群里找到了她。那几乎也是一种不可能,可是Z就是找到了她。她比他大了那么多。Z还是能确定无疑地找到了她。
不久前,接连的几个夜晚,Z跟她通了電话,Z只想拼死一战,跟所有的女人一样,Z使出了自己认为会置对方于死地的解数,那就是将真相告诉她,从而击败她。Z相信她一定不会知道他之前的行为,Z曾经将她的博客翻了个底朝天,凭着一种对她文字的直觉,Z知道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Z在电话里滔滔不止,连Z自己也感到意外,或许自己更像一个言情作家,一个梦游者的呓语,Z甚至都怀疑那些细节和情景,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想象,四十岁以后的女人已经缺乏基本的想象了,她们被现实磨得粗砺无聊无趣,或者更坚实,对一切已经不再需要想象了,如果一定要有想象,那么也只可能是对世俗生活的想象。
Z坚信她会把每一句话都听到心里去,所有的话都会变成毒液流淌不止,正如自己每一个夜晚对着夜空时那样。
Z将头贴在窗玻璃上,仿佛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垮掉,才不会当众让该死的心脏从口腔里跳出来。
她坐在靠窗的地方,正好对着Z坐的车窗。实际上只要她一抬头,将目光投向窗外,就能看到Z。那么她们之间,就不仅仅只是声音相遇过了,她们的目光也俩俩相遇了,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原来是如此地近,如此地不堪一击。她们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辆车那么远。
她端坐在咖啡馆窗前,肩上披着一块桃红色的围巾,看上去并没有她的实际年龄那么老。她一点也不老。这让Z感觉到,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突地扎了一下。Z原以为她的老,可以让自己有一丝鄙夷来聊以自慰。可是她一点也不老,不仅不老还如此优雅。
Z下意识地捏紧了儿子的手,儿子转过头来看Z,摇摇手,叫了妈妈一声。Z什么也没有听见。儿子将身体向外挪了挪,将手指放在嘴里,又开始咬起来,Z转过头来看了一眼。
二
一缕阳光通过窗玻璃,照在她的身上。她优雅地喝着咖啡,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书。她坐在那里,显得旁若无人。窗外的三角梅透过阳光,将影子投射在咖啡屋的门窗上。
她比照片还要漂亮,在这样一个雨后天晴的时间里,显示出的是一种透彻的漂亮。
她显然是在等他。否则她没有理由来到这里,如此悠闲地坐着。Z心慌意乱。Z没有见过她,一次也没有。可是Z确信无疑就是她了。Z在网上见过她的所有照片,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
她是如此的优雅。
Z的身体开始抖动起来,手心出了汗。儿子从Z的手里抽出手来,将汗手在裤子上来回地擦了几下。然后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转过头来看着Z。
儿子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Z没有理会儿子说的话,这不是儿子第一次说这样的话,Z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儿子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一下Z。
“安静点。”Z说。
Z从包里拿出手机,她的手抖得厉害。Z拨打了他的号码。电话通了,他不接。车窗外是一片混乱的喇叭声,尖利得要将人的心脏刺穿。Z在杂乱的声音里,捕捉到了一种划开血肉的声音,那就是他的电话长长的没有人接的声音。他不会接电话,很久以来他就用这种方式告诉Z,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结。
Z拨打他办公室的电话,一个女人接的,Z知道她是单位的美编,怕她听出自己的声音,就换成普通话憋着声音说:请找明克老师。
那边将通话筒放在桌面上,高声烂气地喊明老师,电话。
接下来是杂沓的脚步声和电流哧哧嚓嚓的声音,Z感觉心脏已经贴到嗓子眼了,只要自己稍一用劲,就会立即从喉咙里冲出来。Z想象着他走过来的样子,他的手会先在空中甩那么一下。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他的手因为弹琴腱鞘肌肉萎缩,他总会下意识地在空中甩一下。自从Z认识他以来,每次接电话他都会如此。他会说:“嗨,不用想我就知道是你。”
Z会在电话另一头,屏住呼吸,静静地感知他的气息通过话机流过来,一直流到她的心里。Z总是握住话筒,她喜欢听他说话,喜欢他喊她的名字。他喊她的名字,是通过舌尖弹跳出来的,因而她的名字在他的发音里,变得弯曲而有意味。Z喜欢那样的感觉。
无数的日子,那样的夜晚,他开着车到Z所在的县城找她。从他家开车到Z所在的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总是风尘未定地站在她家房屋的入口处,那是县政府的住宅区。他是从后门跨过一条窄窄的门,拐进大院的,这样就会避开很多的人和眼睛。他虽然会显得敢做敢当,却也会机警聪明,保持着一种高度的不被女人反感的警觉。
那儿有一蓬蔷薇花,顺着石墙爬到了旁边的葡萄架子上。他选择这样的位置等待,是因为更便于躲闪。Z曾经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的身后是一个水泥搭出来的架子,上面爬满了紫藤,他只要一闪身就可以轻易地隐蔽。Z这样想他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不够光彩的感觉。
Z每次猝不及防地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在楼下时,总是狼狈不堪。面对丈夫和儿子,Z得想方设法编谎。Z的丈夫总是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偶尔回过头来看她一眼,她的谎言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可是他总是显得漫不经心,视若无睹不管也不问。丈夫在乡政府工作,每天下班不是喝了酒回来,一步三摇摆地倒在沙发上,就是一头扎在电脑上,玩一种最不需要智力的游戏。他时常会玩得颠三倒四,当屋子里充斥着他奇怪的笑声时,Z就会觉得那简直是一种愚蠢至极的笑。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无聊的人才会发出那样的笑。自从Z遇上他以后,觉得丈夫越来越不可理喻,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自暴自弃地活着呢?一个女人心里有了爱情,就会把日子想得敞亮。
儿子坐在餐桌上写作业,但他不是抠指甲,就是每隔几分钟跑进洗手间哗啦啦冲水。老师已经为他上课抠指甲请过多次家长。每当Z想要告诉老师,儿子这是病时,Z都会心惊肉跳,也许这是连自己也不愿面对和接受的。很多次Z想跟老师好好地谈一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理解和帮助。可是每次见到老师,Z都会突然打消这个可怜的念头。
晚上躺到床上,Z会因为没有告诉老师儿子的事而庆幸。至少儿子还有一个秘密。Z觉得自己对儿子的关心太少了,现在儿子已经在缺失中长大,Z虽然自责,却还是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工作、男女之事上。男女之事或许是最能让人丧失一切能力的,这种事会讓人很少顾及到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儿子从洗手间出来,将一双小手悬空垂着,嘴不停地向外呲气。看见Z从房间换衣服出来,就将笔含在嘴上,眼巴巴地看着Z,有哀求有怨气。而Z总故意不去看儿子,Z甚至觉得儿子的眼神几近一种折磨和阻止,阻止自己逃离这沉闷的毫无希望可言的生活。Z将身体倒着退到门边,然后一边穿鞋一边往房门外退。Z这样跟儿子之间的身体对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简直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难以继续和承受的战役。Z为此常常会既沮丧又愧疚。关门时Z的动作很轻,然后踮起脚尖,飞跑时尽量让脚尖落地,这样楼道里的声音就会小一些。
春天的时候,他站在那儿,月光照射在那些刚刚开放的花上。他看着Z从楼群的阴暗处闪出来。Z总是会警觉地朝后面张望,风吹过那些花丛,就有一股植物的味道夹杂着雨水的湿气,让他觉得神清气爽。
他说:“我想你了。”
Z就又朝家的方向看一眼,Z总是要比他显得稳重,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跟Z从事的职业有关,秘书工作需要的就是谨小慎为。
Z带着他穿过紫藤花架,他们会闻到紫藤花特有的香味,很淡像是被风吹散后,不经意间留在空气中的香味,有阳光的时候,这种香味还带着嗡嗡营营蜜蜂飞舞的缠绕声。
他们很快来到大街上,Z便释然了许多。然后再走一段路,走过街面上的杂铺店,通过一家写有“亮丽发廊”招牌电线杆,拐进更偏狭的巷子,就可以出城了。Z会兴奋地拉住他的手,两个人快速朝城外走。
那个时候,Z觉得他们之间,一定会有天长地久的时间。无论自己是否离婚,他都会这样不离不弃地来找她。。Z问他,有一天他们都老了,他们还会不会这样走下去。他说两个默默相伴的人不会老去。Z就将头靠在他的胸上,他一路拥着Z。Z知道他的所有的温情,都来源于他太缺乏爱。Z比他的年龄大了好几岁,Z一直试图掩藏这个事实,模糊掉与自己年龄有关的全部数据。他甚至从来没有问过Z的年龄。在他的心里似乎没有年龄这样的界线和概念。而他通常又是难以把握的,他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生活里,这个世界在他眼睛里的图景,是被他构思出来的。
他们一直那样亲热地走,走到县城最南面的一家小客棧,远处是一片蛙声。他每次来,都去这家客栈,他们和店家都成为了熟人,他们可以从店家只有十四岁的女孩眼睛里,看到他们关系的异样。女孩长得很漂亮,是那种精灵古怪的漂亮。她的眼神落在他们身上,总是那样黯淡,使得她的漂亮里多了一种神秘的东西。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楼的房子。站在窗前可以眺望远处的小河,河边的垂柳,以及夕阳映射下的田野。晚风吹过来,能够闻到河水的气味夹杂着沙土的干裂。
每次Z都把楼板踩出很响的声音来,他会转过脸来看她,然后两个人相视而笑。
Z曾经试探性地对他说她要离婚,Z总是想如果他说离吧,Z就真的会离吗?而他不说话只看着窗外。月光从窗外照进屋子,影子映射在墙上,Z的心里就有一种渺茫感。这种感觉会让Z陷入一种淡淡的忧伤之中,而自己会受到这种情绪的牵引,越走越远,甚至想入非非。也许一切关于爱的想象,都是女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之于饮食男女不过尔尔。但是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炽热。第一次在水边的月光地上,月亮也是如此地明亮。两个人望着天空,远处有夜鸟的鸣叫。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时断时续地飞迸而来。Z将头埋进他的腋下,河水一浪一浪地涌上来,然后又静静地退去。Z就想人的生命里,涌来涌去的激情,是不是也终会如这河水一般,悄然退去。那个夜晚留在Z记忆里的,既是美好的,又是伤感的。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给Z打过电话。而Z打过去刚听到他喂,就插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似乎是从另一个屋子冲过来的,有点怒不可遏地对着他大声地吼:“这么晚了,是哪个不要脸的打电话。”
电话挂断了。Z以为是串线,过了几分钟又拨过去。他接了,这次他没有出声,可是那个女人这次的声音离话机更近了,Z吓得挂掉了电话。Z知道一定是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怎么会发出那样的声音?Z记得自己对他说起过这种感觉。他还是不说话。他的沉默总是让人无法或者不忍继续深入交谈。Z本来想说女人发出那样的声音,也是因为没有爱。Z看着他欲言又止。Z是一个懂得分寸的女人,不该说的话绝对不会说。那些说出来对自己毫无好处的话,最好一句也不要说。
Z想到他对自己的依恋,知道他是一个渴望爱,一直在寻找爱,却又缺乏爱的情感纤细的男人。Z对他怀有一种格外的怜惜,这并不是自己比他大了很多的原因,Z始终认为这是一种爱,或许夹杂着母性之爱,也总能让自己心驰神往。
Z也许更加迷恋他说:“我爱你,很爱。”
那简直是一种难以自拔的情绪。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Z认为这句话是干净的,不着纤尘。
事情就出在九月。Z的心暗沉下来,那是一个怎样的九月。雨下了整整二十天,在另一座城市。Z每次从网上看到的都是雨天,那个该死的城市,使得人整个地陷入,那种阴湿的晾不开的天气里,或者更是因他在那座城市学习的原因,给Z造成的莫名的危机感,加重了自己对另外一个城市天气的反应。
那些日子虽然自己所在的城市阳光明媚,在Z的心里映现的仍然是,那座遥远的陌生城市的阴霾。Z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不管在家或是在办公室,总会拿出电话,拨打他的号码。
Z从九月的某个早晨开始跑步,为的是能更紧密地跟他建立,某种时间或者空间上的联系。他是个喜欢晨跑的人,他多次建议过Z晨跑。他说他会从晨跑中获取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感。Z不能够心领神会他说的话。Z朝着县城外跑,顺着那条他们曾经走过的小河,穿过小树林就看到了那片荷塘。七月的时候,他们坐在荷塘的夜色下,那时塘里的花开得正艳,还能听到青蛙跳水的声音。
Z停下来,看着已经萎顿的荷塘,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感。Z拨打了他的电话,告诉他每天陪着他晨跑,告诉他自己站在荷塘边,而荷花已经没有了。电话响了很久,他才接说他刚结束跑步洗完澡出来,走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信号不好,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断断续续,Z仍然感觉到了,他已心不在焉。
一切Z都预感到了,从他走之前来看她,就有一种即将失去的感觉笼罩于心。Z不知道怎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他不过是出外半个月,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Z就是感觉到了。
三
车身似乎晃动了一下,司机将油门熄了火。人心也随之一下子沉陷下去,那些乱七八糟的说话声,突然停了片刻。这样片刻的停顿,让时间变得虚弱无力。Z努力镇定着自己,儿子不安地动了一下,转过头来说:妈妈,老师下周会不会还不让我上课。
Z又是一阵心痛。她有点后悔将儿子送到K城,这所让家长们趋之若鹜的重点中学。Z以为这些年因为工作,那个讨厌的县政府秘书工作,让自己丧失的东西太多,其中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日日地加班赶写文件,陪同吃饭喝酒至深夜难回的生活,让儿子的成长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儿子回到家中,常常一个人待到深更半夜,独自趴在床上睡去。儿子轻微的自闭症,与Z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那些时候自己年轻,不懂得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以为只要他回到家中就安全了。一个孩子的孤单,会给心灵造成怎样的忧惧?!Z很后悔明白得晚了点。
秘书处的办公室在县办的二楼,后窗紧靠着那条人工湖。每天透过窗口,Z可以看到水面上飞过的各种鸟。水中夹杂着一种腥臊的味道,那是一股淤泥的味道。处长海中每天清晨都会站在Z的身后,很多年Z一直混杂在这样的味道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却也没有觉得什么好。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无聊无奈无趣。海中的嘴巴里也经常透出那种咸湿的气味,也许是他们家喜欢吃死海鲜的原因。
海中喜欢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掐Z的胳膊。没有人的时候凑近Z的耳朵,蹭得她耳鬓发红。有时候他会给Z说,昨晚红来找我了,是她自己找来的,我们都喝醉了,她喜欢用酒浇湿自己的身体。
Z不说话。海中说的红是Z的好友。红不知道,海中每一次都会将自己的事告诉Z,红给Z打电话,Z总是不接。那个放浪轻薄的女人。Z这样想就忘记了心中的不快。
电脑的QQ上闪出头像,是他的。Z没有去点击。挤在Z凳子上的海中说:“你还喜欢搞网恋?”
海中就将手伸到Z的腰上,撩开衣服搓揉着。Z心里生起一股厭恶,从未有过的厌恶。Z想这么多年自己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够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人辱没地生活下去了。
自从他走进Z的生活,一切都在改变。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已经在想办法帮Z调离县政府办秘书处。
Z用手肘向外拐了海中一把。海中就势抱住Z,将头埋进Z的胸上说:“你变了,你变得让我感觉刺激了。”
Z想到电影上的镜头,应该就势给海中一嘴巴,然后抽身走人。Z抬起手来,Z的手突然就僵住了,它缓缓地落下来,落在海中的头上。这个刚进中年的男人,就已经谢顶了。Z轻轻地抚过海中头顶那绺稀疏的头发,食指划过那片光秃秃头皮,Z闻到一股带着油腻、还有腥澡之味的腐败气。Z的心里涌上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多年来的秘书工作将自身的隐忍度训练到了极致。Z早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海中曾经在工作中给了自己很多的帮助,在这样一个盘龙卧虎、甚至张牙舞爪的县政府大楼里,Z在举步艰难里学会了凡事不露声色。
只有在他那里,Z感觉到了一种存在,那似乎是远离尘世的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存在感,给了Z许多的想象空间以及不切实际。或者这许多年来自己都是不存在的。Z想。Z曾经怀揣的理想,早已随着时间褪尽。生活已经让自己变得麻木,即使没有光彩也得过下去,所有的人都这么过着。他给了Z光芒,那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光芒,让她陡然间有了许多幻想和奢望。她甚至觉得那缕光芒会一直照耀着他们。
他从外地学习回来之后,Z感觉他变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主动找Z,或者不管不顾地跑到Z家的住区楼下去等Z。Z想尽快寻找到关于这一切的蛛丝马迹。以Z秘书职业特有的细致和敏感,Z很快通过博客找到了她。也许这便加速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死亡。
那是她和他在分别之时,两个人都写了关于分别的博文。他在离开时,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和心情,他没有掩盖他对她,以及对那个他只停留了十多天的城市的依恋,他甚至动了留下来的念头。而她却很隐晦地写下送别,写下进入深秋时季满地的落叶和雨水。她开着车将他送到机场,她说返回时她将车停在路边很久。这样的描述非常隐秘,只有他看得懂。她在写下博文时,也许那个时候在她的心里,他之于她也只是一次偶然的际遇,是不需要把握的。谁会将一次远隔千里的际遇当真?
可是他却写得如此刻骨铭心,尽管这样的深重的情感,完全隐现在别的文字里,Z或者她却都能明白无误地读出来。他完全没有顾及到Z的感受,也许那篇博文,只是写给两个都看得明白的人看的,那就是Z和她。Z从两篇可以对应的文章里,准确地找到了她。Z给她留言,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了回复。看来她是一个毫不设防的女人,她丝毫没有觉察出Z的良苦用心。
Z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了与他交往的全部过程,意在让她明白。她去过Z的博客,并在Z的博文后面留言说,是什么样的男人让你如此痛。那时她没有丝毫的猜测,她不会意识到千里之外的这个女人,正经历着与己有关的折磨。为此Z有点轻视她。女人凭直觉能够感知的东西,到了她那里为什么就不起作用了呢。她为什么不想一想,跟他同处一个地方的女人,怎么就会跟自己有了联系,这一点也不会偶然。Z甚至有点愤恨她的迟钝。这样一个女人,他怎么会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呢,况且她比他年长了那么多。
后来她居然来到了K城,居然告诉Z她来了。那是十月,到处都充满着阳光,通往他家道路两旁的薰衣草开得正灿烂。Z发了一条短信给她。Z很想见她一面,让她知道真相。她说好要先到古城去,之后返回。
之后的几天,Z一直等待着,她没有一点消息。Z是个极有耐心的女人,在这件事情上Z不想显出太主动。Z以为她一定是明白其中一切的,所以Z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等待。
她走了,上火车之前,给Z发了告别的短信。Z接到短信刚刚晨跑完,头发被汗水濡湿了。Z给她回短信,告诉她自己刚跑完步,其意在于暗示她,他也跑步,他们都跑步。她没有回复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还算是能够了然心计的Z,至今没有想明白,自己是不是上了她的套。她的那篇关于薰衣草的博文。她在博文里轻描淡写地流露出一种深重的爱和伤感。她说和他坐在咖啡吧里看书,喝咖啡,整整一个下午,两个人浸泡在一种温馨的情景之中,外面下着雨。她在博文中特别地写到了,去往他家的路途中的那些艳灿的薰衣草。
Z没有沉得住气,到博客上给她留言。在这个问题上Z显然过余地心急了。Z千方百计想要让她知道,自己与他的一切。Z给她写了一封邮件。她看了。她给Z回复时,特地提了他的名字,还有薰衣草。Z没有把控好自己。或许是Z处心积虑已久,一定要将真相告知她,让她受到伤害后自动退出。
后来她们通了电话。电话是她打给Z的。Z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说出了全部。Z在电话里完全能感知她受到伤害的气息。她一直沉默,她说话的语速缓慢的程度,呈现出她受伤害的程度。她先前对一切竟然一无所知。让Z同时也受到伤害的是,Z能感觉到她是那样地爱他。
Z甚至不知道自己添油加醋得寸进尺的描述,同时更多地毁灭了自己。那个夜晚她们通了两个小时的长途电话。她不说话。Z知道她一直在听。Z说还有一个细节,元旦节前我们在一起开完会,他送我回家,车开到我们的住宅,他拉住我,然后我们在车上……
电话挂断了。
Z将话机从耳边移到眼前,话机上粘满了汗水。Z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久以来郁积在心里的怨愤屈辱渐渐散开,Z感觉到心情舒展开来。Z想这下好了,她会退出去的。只要她退出去了,他又会一如既往地来找自己。可是Z没有想到自己错了。人们通常用“一根筋 ”这样的话来形容,一个人的愚笨和执着,那么他仅仅是只有半根筋的人。
四
她将身体向前倾斜了一下,然后朝着服务生招招手。服务生走到她身边,弯下腰去给她续咖啡。她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杯子,说了句谢谢。
那一刻,她抬起头朝窗外的车流看了一眼,她的目光在一瞬间竟然与Z相遇了。Z确信她一定看到了自己。
那个梦魇样让Z不安的女人,她的眼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Z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Z继续拨打他的电话,她显得有些筋疲力尽。Z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接电话,却不屈不挠地打着。很久以来,Z一直在经历着这样的煎熬,似乎这样便能卸掉那些附着在心里的赘物,那些搅扰着让自己难以喘息的赘物。
为什么不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这样想的时候,心里的痛感加深了。Z想起那天下午,是他给自己打了电话,而Z正在开会,手机在办公室。散会时已近八点,Z站在楼梯间给他回了电话。而就在那个夜晚,他告诉Z他们的事不能继续了。Z问为什么。他说有些话还是留着不说吧。
Z透过水泥镂空的楼道缝隙,看到了远处的湖水,以及湖面上的波光。想起那些跟他在这样的月光下说过的话,一切都随烟云消散在风中。而留下来的全是刺痛。
他说他的老婆知道了一切。他还说他跟他的老婆正闹着离婚。Z说不可能。他说他老婆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Z沉默下来。他说对不起就挂断了电话。
Z从单位走回家的路上,拨打了她的电话。她不接。然后Z又换了她的另一个号码,她没有将这个号码存入手机,所以她接了电话。当她听出是Z的声音时,她说:“我们不用通电话了。”Z不甘心,拖住她说:“我只想问一句,你们到了什么程度。”她沉默了一阵,说:“生死相依。”
这几个字极像是咬破了时间,附着着沉重和不可替代,从那儿钻出来,有了一种字字珠玑的光亮和质感。Z和她都在这种质感中沉默下来。她挂断了电话。
那天深夜,Z又拨打了她的电话,她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中接了电话,当她明白过来是Z时,她就又沉默不语。Z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她一句也记不得。她只想赶快结束这种无端的纠缠和折磨。她在Z不断的诉说间隙里告诉Z,不要再打扰了。Z还是不依不饶地发短信给她。她将两个手机都关掉了。
之后,他也就像这块大地上,突然隐没的一块石头,兀地落在荒野中然后无声无息,任凭风吹草动,飞沙走石,都无法惊扰他。他的电话号码如同虚设的一般。
Z去小镇找过他。将他拦截在石门小巷外。那是他回家时必经的路,也是他们从那儿到水边去的地方,无数次他带着Z从这儿来到小镇,穿过石拱门柱,沿着小巷回家。是他告诉Z回家,再没有第二条路。道路两边开满了薰衣草。紫色是他最爱的一种颜色。Z在那儿等了他整个下午。
他从远处走来。Z一直看着他从远处走来,一如先前他们一同踩踏着碎石子发出的声音时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扬起的尘土,掩过了脚踝。
这是进入小镇最古远的一条路,一条几乎废弃的路,只有牛群和他才喜欢走的一条路。道路两边杂草丛生,被风吹得错乱不堪。他说他喜欢走这条路,因为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他和奶奶走过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到达他家最近的路。那个隐蔽在青石街巷的小屋,在年深日久中损毁陈旧的屋子,是他和奶奶生活了一辈子的屋子,直到死去,奶奶都一直住在那里。
他曾经带着Z从这条路到达奶奶的墓地,那是清明节上坟。后来Z独自来过,为了能使他回心转意,Z一个人跑到山上,用手机拍下了通往坟地的那条盖满松针的小路。Z把照片发在微信里,Z相信他一定能看得见。
Z站在石柱门的背阴处,他突突踏踏地走来了。当他来到Z的面前,当他看清了Z时,他的身体朝后倒退了一步,然而他很快镇定下来。他显然没有想到Z会来找他。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地僵持了一阵,他将脸转向通往河边的那条路上,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姿式,两头牛悠闲地在树影下移动,河面上闪着波光,从这面看过去,有点无边无际的感觉。
Z说:“告诉我真话。”
他仍然看着河的方向说:“我说的全是真话。”
Z说:“你发誓。”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要发誓 。”
Z说:“因为你说了假话,你不敢发誓。”
他将脸调过来,他们的目光就在那一瞬间遇上了。Z的眼睛里全是泪水。他脸上僵硬的表情软和下来。
Z说:“为什么要欺骗我。”
他说:“没有。”
Z说:“我都知道了,我和她通过电话。”
他又将脸转向河的方向说:“正因为你们通过电话,事情才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滑去。”
Z说:“你不可能爱她。”
他说:“你错了,非常爱。”
Z说:“你曾经也这样对我说过。”
他不看Z,只看着远处。牛已经缓缓地走到土路上来。
Z说:“那我们算什么?”
他不说话站在那里。Z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他朝前挪动了一步说:“原谅我,我们已经结束了。
五
Z有点按捺不住,几次都想起身下车。Z想走进那家店里,然后坐下来。Z想让她跟自己面对着面地说话,而不是通过电话。Z在电话里跟她说的有关他的所有的事,Z都想重新给她说一遍。可是Z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在往下坠,那是一种悬空的无法把握的感觉。几个月来,自己所经历和忍受的一切,在一起随着身体往下坠。Z感觉身体在时间里,形成一个黑暗的沉重之物,只有破釜沉舟之后才能完成的贅物。
Z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车启动了,整个道路开始畅通。Z张开嘴喊司机开门,然而她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Z重又将身体坐稳,道路上所有的车开始动起来。
Z从车窗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的憔悴焦虑,看到了即将被妒火烧尽的脸。这个时候,Z偏偏又看到了他。他从远处走来,一歪一拐的,前脚着地时用劲很大,总给人一种不稳当的感觉。看到他Z心乱如麻,眼睛一片模糊。汽车渐渐地挨近他了,经过他身边时,他一抬眼便看到了Z。那一刻,Z看到了他脸上的惊愕,他的脸僵在被树影遮挡住的那抹光亮里。
Z的心脏加速运转的程度超过了身体的承担力,她突然就发出了声音:停车,停车!司机转过脸来看了一眼,所有的人都转过脸来看Z。Z有点无地自容,儿子也看着她。汽车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看到了Z。他脸上的惊愕,随着车速一闪而过。他的脸僵在被树影遮挡住的那抹光亮里。
Z转过头看着他。他没有调转头来,他连迟疑的举动都没有。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Z心里发着恨,又拨他的电话。Z看见他将手机从包里拿出来,埋下头,他看清了电话号码,他迟疑了一下,头侧了侧,最终没有回过头来,将手机握在手里, 然后他走进那家咖啡店。
Z觉得身体一块一块地被拆散开了。
六
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下雪了。铺天盖地的雪,有一种强烈的压迫自天而来。这是K城罕见的鹅毛大雪,天空昏暗,能见度很低,街上的车辆一律缓行。即便开着车灯,仍然处在昏暗之中,道路很滑。
Z冒着大雪转了几次车,来到儿子上学的学校那条街上。Z已经下定决心将儿子转回县中学。接近中午放学的时间了,孩子们踩着地上的雪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声音通过校门敞开的电子门传出来。Z站在对面的街上,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控制的酸涩。眼泪竟然在她毫无觉察的情形下流了一脸。Z有些迟疑起来,她不知道将儿子转走,这样的决定对不对。Z担心毁了儿子。
Z走进那家吃石锅鱼的小店,找到他们曾经最爱坐的角落,那个靠近厨房的窗下,依然放着一把琴,那是店老板儿子的琴,被他无数次弹奏过。
老板娘的儿子,那个皮肤微黑的青年小伙子拿着菜单走过来。他认真地看了一眼琴,然后冷静地将菜单放在Z的面前。他还记得Z。Z能凭借直觉知道这一切。Z已经有半年没有来这里了,他还认得自己,并且记得发生过的一切。
Z跟往常一样点了鱼,然后要了两个凉菜,还要了酒,两个杯子。小伙子收起菜单时,谨慎地问了句:“两个人吗?”
Z没有回答。
Z的脑子里全是儿子站在老师面前的样子。因此Z每吃一口饭,给儿子转学的决心就坚定一分。人不必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儿子本不属于这座城市,自然不会被它接纳,正如自己和他。儿子和自己都只是瞬间的,某时或某物的显现,何必强求。
Z办完儿子的转学手续从学校走出来,地上的雪已经在融化。Z一下子释然了许多。从今往后,自己将和儿子共同面对现在或往后的一切。
那天夜里所有的微信上都出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K城火车站发生暴徒砍杀无辜事件。死了很多人,伤了很多人。
Z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她。如果她也正好回去,她会不会也在火车站。Z的心骤然间跳动起来,难以平复。Z又开始拨打他的电话。手机关机。Z只想证明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出事时,她是不是也在火车站。
Z一连几天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一直关着机。Z打他办公室的电话,那边说不在。去哪了,不知道。单位也在找他。
Z走到窗前关了窗帘。儿子坐在餐桌前写作业,一边咬手指一边看着,在家里走来走去的Z。
那一夜,Z辗转难眠。
窗外又开始下雪,越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