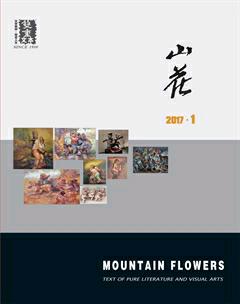走阴
老屋大门的门框有两米来高,我站在门槛上,伸手便可摸到门楣。门前光线暗淡,挂着蛛网,飞着蜻蜓,时而也有少许的野蜂在墙壁上筑巢,嗡嗡地低吟。
大门老旧了,头上盖着的瓦越发黑了,松木的门板和门墩、门槛都成了棕黑的颜色。两旁的土坯墙也斑斑驳驳。门头上的瓦沟里长了一些石帘花。
每到有人开门,“吱呀”声庸懒沉重。门里的巷道只有二三米宽,比较深,都铺了瓦砖。开门声在深深的巷子里缓慢地流淌。
巷道里有一口老井,井槛上写着“龙泉清”三个字。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门槛上,听野蜜蜂轻声吟唱,望着井槛和“龙泉清”几个字发呆。井水清澈,井槛上长满了青苔。井里有一条红鱼,听说是奶奶爷爷打井时就养下的了。常常会看到奶奶蹒跚走过老井,她会情不自禁地朝井口张望一会。她似乎是在照自己的脸。我觉得奶奶往井里一照,脸色似乎红润了一些,走路也精神了许多。
奶奶穿青布长衫,个子显得矮小,脸上皱纹很多,眼睛小却明亮,时不时会透出神秘的光亮。
有人敲门,奶奶来到门前,俯身到门缝前,望是谁来了。看清门外人,才作出最后的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
这天,我坐在门里的石墩上,远远看见奶奶来了。深深的小巷里,太阳光很亮,天空蓝得深邃虚幻。我坐在暗处,看到奶奶手搭凉棚四下里看。也没有人敲门,我不知奶奶到门口做什么。奶奶看四下里没人,便往墙上掰了块土坯。这时,我看到了奶奶手上的玉手镯和纤细的手指。那只玉手镯晶莹透亮,映衬着奶奶枯瘦的手腕和手指。奶奶的玉手镯仿佛在空中摇曳。
这时,奶奶的手指显得十分灵活,一块坚硬的土坯瞬间掰下来。掰下就急忙往嘴里塞,然后不停地咀嚼。
我曾多次在大门口看见奶奶悄悄地在门口吃墙上的土坯块。
后来,我在《百年孤独》里读到雷贝卡吃泥土的情节,惊奇地发现和我在老屋门口看到的情形相似。
我很少看到奶奶这样慌张,她从来都是一脸淡定。看到奶奶神神秘秘,我坐在暗处不敢做声。
土坯咀嚼碎了,咽下去了,奶奶用绣花手帕把嘴抹干净。奶奶的手帕上绣着一朵鲜艳的山茶花,用一只别针别在胸口。抹干净了,奶奶自言自语念叨。
我听不清奶奶在念叨些什么。奶奶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讲她的纳西母语。
奶奶走了,我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门后的那根门杠。门杠光滑,有小碗口粗,棕色,圆润,冷冷的横在大门中间。
走到老井边上,奶奶又往井口张望了一下,我想她是在望那条红鱼。我多次想往井里扔点东西喂那条红鱼,奶奶都严厉地禁止。她说:这条鱼是不能吃东西的,它只能喝干净的泉水——吃其他的东西它就死了。
奶奶还用毛巾把“龙泉清”三個字认真的擦拭了一下。这三个字是我爷爷写的,写得不好,但很认真,我清楚地记得,龙泉清的龙写的是繁体字“龍”。
这口老井是奶奶嫁到我们村子的时候打下的。奶奶的娘家在丽江一个叫风流沟的茶马古道上,她家世世代代经营着一所马店。马店地处交通要道,生意很好,每天都住满来往的马帮。生意很好的原因,听说与奶奶的漂亮有关。年轻的马帮们,来往丽江都喜欢住风流沟。
所以,奶奶家的马店随时都人欢马叫,马铃“叮叮当当”在响,年轻的赶马人打着口哨,那尖锐的口哨声伴随着马粪味、牲口的汗水味在院子里弥漫。马帮来了,奶奶婀娜的身姿在院子里十分引人注目。奶奶娇小玲珑,细腰,圆臀,脸蛋像秋天里的苹果,眼里常常像有一泓清泉荡漾。当奶奶扭动着的身体走过马店,马帮们的眼睛都亮了,说话声音特别响亮。他们都忘记一天长途跋涉的劳累。
然而,那些想入非非的马帮们,都不敢轻易招惹奶奶。奶奶的爷爷是个非常有名的老东巴。
奶奶小的时候,常常摇着爷爷的东巴铃走过马店的大杂院。那铃声清脆,细腻,传递出难于言说的魅力。东巴爷爷曾经预测,奶奶将来接替他的位置。东巴爷爷准备将我的奶奶许配给风流沟另一个东巴世家。
爷爷和奶奶的婚姻具有传奇色彩。奶奶是跟爷爷逃婚来到我们村子的。那个夜晚,奶奶跟爷爷手牵手逃到了我们村子。奶奶和爷爷逃到我们村子的时候,在村北头“妃子寺”旁的牌坊前放了一挂鞭炮。那时候,寺院里刚刚响起夜半钟声,清冷的石牌坊上照着淡淡的月光。
鞭炮是奶奶准备好的,一直装在裹着一件七星披肩的包袱里。奶奶说这是她们风流沟的习惯,说放了这挂鞭炮她就是爷爷的人了。
鞭炮惊动了整个妃子村的人。夜色朦胧中许多人都猜测说:不知是哪个马帮又拐着女人回来了。当人们看到爷爷领着奶奶进村的时候,谁都有些想不通。他们没想到爷爷会“拐”到如花似玉的奶奶。爷爷是个马帮,常年赶马跑丽江和鹤庆。但爷爷是个不太称职的马帮。在妃子村子里,不是好马帮说不到好媳妇。
爷爷胆小,赶马的时候,一个牲口的笼头,拴在另一个牲口的马鞍上,生怕牲口跑掉。爷爷是村子里唯一读过私塾的马帮,生得秀气,说话文质彬彬,完全不像一个赶马人。但爷爷的手很灵巧,会弹优美的弦子,他总是要带上弦子赶着马上路。村子里会弹弦子的马帮不少,但爷爷的弦子与众不同。别人的弦子是三根琴弦,爷爷的弦子是四根琴弦,被称为“月琴”。爷爷的“月琴”中间有一面小镜子,像个小月亮,弦轴上雕了精致的龙头。爷爷的手指修长,每当他抱起“月琴”的时候,修长的手指上流出优美的声音。爷爷的嗓音也好,会唱十分动听的民间小调。就是这种原因,一些年轻女子暗暗喜欢爷爷……
爷爷娶了奶奶就不赶马出门了,这让奶奶非常失望生气。奶奶不喜欢守在家里的男人。奶奶说:我宁愿嫁一碗米的赶马汉,也不嫁一斗米的守家奴。
爷爷不对奶奶做任何解释,和奶奶在门口的巷子里挖了一口井,养上了一条鱼。说也奇怪,井挖好以后,又养下了鱼,奶奶就安分得多了。她喜欢在井口照自己了。
那条鱼原来是黑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就变成红色的了……
奶奶面色红润,步履蹒跚离开老井的时候,爷爷望着她的背影嗫嚅着说:你奶奶脸红了,是“回光返照”了——可能要去了。
爷爷说话不太清晰,原因是他中风了。爷爷的嘴巴有些歪了,说话不清楚不说,还会流口水出来。爷爷奶奶都不知道是血压高导致中风了,他们把中风的原因归咎于垫了糯谷草草垫。太阳好的时候,奶奶把爷爷的糯谷草垫拿到院子里来照太阳,轻轻地拍打着草垫上的灰尘。草垫上还会拍下红色的臭虫或黑色的蚂蚁。所以,只要奶奶拍打草垫,院子里的鸡就会围了过来。那些鸡的嘴上瞬间沾满了鲜血。
拍打着草垫,奶奶对我说:你爷爷那样子,越来越难看了,再歪就更难看了。我把从娘家带来的狗皮褥子拿给他垫上了。
爷爷不管奶奶说他嘴歪了,依然说自己的。他依然重复地说道:你奶奶脸红了,是“回光返照”了——可能要去了。
奶奶耳朵早就不好了,但爷爷的话她却又听得清。听到爷爷说她“可能要去了”的时候,她停住了拍打,掉头骂道:老鬼!你才要去了呢!
爷爷就不敢说话了。
奶奶就把一套“老衣”让爷爷穿上。奶奶说:“老衣”要在世的时候穿一穿,不然到阴间便不贴身。爷爷的“老衣”是一件天蓝的缎子长衫,一顶黑锦绒布的瓜皮帽。瓜皮帽上,奶奶特意做上了一个红色的顶子。
爷爷偶尔穿着这身“老衣”在村子里走一遭。妃子村人说爷爷真像个秀才。
奶奶关心爷爷,爷爷从来就怕奶奶。奶奶随时骂爷爷,说自己是嫁错人了,说自己是前世欠了爷爷的账。奶奶还骂爷爷后来不赶马不出门是被一个叫“风摆柳”的女人绊住了。
所以我对“风摆柳”这个词印象极深。
村子里真的有“风摆柳”这么个女人。直到现在,老人们对“风摆柳”的描述还在妃子村流传。他们说“风摆柳”瓜子脸,脸色白皙细嫩,四肢柔软飘逸,如柳絮飘摇,从巷子里走过,速度比常人快,甩着手,扭着腰,感觉十分妖冶。
可惜“风摆柳”红颜薄命,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
奶奶好像有一种预感,预感爷爷会好上“风摆柳”。爷爷不去赶马了,奶奶也不让爷爷出门。奶奶在老屋旁买下了一片田地,闭门种下了一片罂粟。大片罂粟花开的时候,奶奶站在田边,脸也映红了。奶奶赶快让爷爷上好了门杠,不让任何人进屋……
父亲对我说,奶奶对爷爷产生戒备心理是一个春天的上午。那天,奶奶在屋旁地里欣赏罂粟花的时候,村西的小河边隐隐约约传来琴声和山歌。奶奶立刻辨出这琴声来自爷爷的月琴,那山歌又仿佛出自“风摆柳”之口。奶奶到院子里去找爷爷,发现大门敞开着,马厩里的那匹枣骝马也不见了。爷爷没事的时候喜欢赶着枣骝马到小河边放风饮水。
奶奶决定去河边寻找爷爷。奶奶出门的时候,特别地打扮了一下自己。那天,她特别穿上了天蓝色的“佳水布”衣裳,戴上了黑色的首巾,腰间系了条百褶围裙。天气晴朗,太阳金光闪闪,初夏的田野里,秧苗碧綠,麦子金黄,河边的柳絮飘飘摇摇,浮到了水面。
奶奶匆匆忙走到田野里,果然看到了爷爷正在与“风摆柳”对歌。
奶奶的预感千真万确。然而,奶奶不知道这种对歌只是妃子村里的一种习俗。每到栽秧季节,村子里的男女青年就会在田野里边干活边对歌。所以,春夏之交,妃子村的田野都会飞出了清脆的调子。大片的栽秧田里,水的亮色围绕着所有的女子,她们迷人的气息在农田里弥漫。
奶奶却认定是“风摆柳”缠上了爷爷。田埂上长满了青草,奶奶脚步开始踉跄,像踩着海绵一样的,视野也开始模糊。奶奶依稀看到爷爷和“风摆柳”相隔比较远,一个在柳絮轻飘的河岸,一个在水光晶亮的秧田。远远的,奶奶看到“风摆柳”手不停地栽下了秧苗,嘴上却唱出了优美的山歌。
然而,就在奶奶快要到达小河边的时候,“风摆柳”的调子偃旗息鼓。“风摆柳”的调子停了,爷爷的月琴也戛然而止。
自从听了“风摆柳”的山歌,奶奶的耳朵不太好了,除了爷爷说话,任何人说话她都说听不见。奶奶停止了罂粟的种植。奶奶喜欢上了巫术。
奶奶的东巴爷爷的话得到了验证,逃婚离开风流沟十多年后,奶奶开始了她的东巴活动。同时,奶奶的巫术是无师自通。她在我家的老楼上设了祭台,挂起了经幡,每天点起了香火,摇起了磬铃。除了祭祀需要,奶奶不准任何人自行上楼。
自从信奉上了东巴后,奶奶行踪诡异,说话神秘。只要走到神台,她就闭上了眼睛,耳朵也有了听觉。她唱经、算命打卦,无一不精。每到初一十五,我家的老楼上,便响起了清脆的磬铃声和奶奶的唱经声。奶奶的唱经是我们听不懂的她的纳西母语。奶奶的磬铃声和唱经声让整个妃子村蒙上了神秘色彩。
时间不长,便有人到我家找奶奶测风水、合婚、测八字……哪家的牛马丢了,人走失了,都会来找奶奶卜卦。奶奶在祭台前点燃了香烟,祈祷一会,然后拿起了她的两片羊角卦。奶奶做东巴时间不长,两片羊角卦光滑,颜色漆黑,显得很旧了,显然是用过不少年代。爷爷说,这羊角卦是她的爷爷早就藏在她的羊皮披肩里的了。
奶奶卜的卦,总是十不离八九。
奶奶最灵验的是“走阴”。奶奶说她经过做法事后便能看到阴间的人,与地狱里的人对话,把阴间人的话传回来,又把阳间人的话传到阴间。奶奶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候才做这种法事。后来,奶奶在“风摆柳”家做的那场“走阴”法事让我终生难忘。
奶奶的另一项特殊功能就是“喊猫”。村子里哪家的人病得不行了(主要是年轻人),就请奶奶去“喊猫”。奶奶要夜半的时候才去病人家。黑夜里奶奶不要人去接她,伸手不见五指,奶奶跟着一只大黑猫,步履轻盈,两脚如风,不用指点就找到了病人家。
到了病人家里,奶奶烧香、点灯、卜卦、做法事。那只大黑猫静静地呆在奶奶身边,眼睛里扑闪着蓝色的光。奶奶慢慢地便进入了昏迷状态,脸色瞬间由红变黑,人也抖抖索索,嘴里学着猫叫并不停地叫着病人的名字,那声音缠绵悠长,在夜空里飘荡。奶奶说,她是在帮病人叫一个替死鬼。
村子里人说,如果梦中听到有人叫自己,一定不能答应,如果答应了,就要替那个病人去死。奶奶成了妃子村里十分神秘的人物。妃子村的人,都十分怕奶奶,也有人称奶奶是“蛊婆婆”,说那只黑猫就是奶奶养的蛊。
走下祭台,奶奶是个正常人。在我眼里,她与妃子村的老人没有两样。同时,随着年龄增大,爷爷奶奶常常像小孩子一样辩嘴。没有人的时候,爷爷奶奶都陷入沉默,只要有人,他们就嘀嘀咕咕,互相指责和猜忌。有时候,我觉得爷爷奶奶的辩嘴好像只是辩给我听的。我觉得他们要我在面前的时候才辩嘴。
有一天,奶奶看到爷爷离开了,小声对我说:你要对你爷爷好,他至今可能还藏着一块很值钱的烟土。
奶奶说,有一年,家里一块最值钱的烟土突然失踪了。奶奶说爷爷去卖烟土回来,卖了烟土却交不出钱来。爷爷也说不出烟土的去向。奶奶一直认为,烟土不是给了“风摆柳”就是他自己藏起来了。爷爷那么小心的人,烟土肯定不会丢失。
奶奶要我对爷爷好,就是要我每天给爷爷端茶端饭。
一天,奶奶突然对我说:你爷爷整天说我回光返照,要去了,如果我真的去了,你端茶给你爷爷喝吗?
看到我不作声,又问:你端饭给你爷爷吃吗?
说完,也不期望我回答,却是摇头叹息着进老屋去了。
奶奶爷爷住的屋子在楼房堂屋的最里面。
楼房是爷爷奶奶靠种罂粟修下的,是妃子村典型的楼厦房,高矮错落有致,阳台、走廊、书房、香台、堂屋布局得当。门窗都是请有名的剑川木匠雕刻的,龙凤兰草,幽竹游鱼,蓑笠渔翁,都是古朴风雅,熠熠生辉的。堂屋里有灵台,有香炉,挂着经幡,点着油灯。时间久了,整个堂屋的墙壁,门窗和彩画,还有精心描绘的房梁都被香烟薰黑了。奶奶爷爷结婚的对联,从来没有换过,大红纸变成了枣红,对联上的字依稀可辩:芝兰茂千载,琴瑟乐百年。
奶奶回到了她自己的屋子里,便把门关上了,她也好像永远地消失了。
奶奶不见了,我会情不自禁地盯着那屋子门看一会。里面什么动静也听不到。我不知道奶奶会在里面做些什么。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奶奶才走出小屋子。这时候,奶奶已经洗了脸,穿戴整齐。她的双手捧着一杯油茶,站在院子里祭献,态度十分虔诚,闭着眼,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先是从东南西北祭献,然后她对着太阳念叨好些时辰。
爷爷的中风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终于睡下起不来了。奶奶开始服侍爷爷了。一天,奶奶走到院子里来叫我说,让我去为爷爷捶背。爷爷总说背上疼得不行。
我从来没有进过爷爷奶奶的房间,一直对奶奶爷爷的屋子充满神秘感,同时也感到恐惧。听到奶奶的召唤,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奶奶看到我畏畏缩缩的样子,便拉住了我的手,把我往屋子里拉。奶奶的手指纤细,仿佛尽是骨头。她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茫然地跟着她进进了屋子。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温暖而怪异的味道扑面而来。中成药的味道、陈艾叶的味道、老年味道……应有尽有。进了屋,奶奶放开我,点亮了豆油灯。我看到屋子只有十来平米,但铺了两张窄床。爷爷躺在靠北的那张床上,盖着老土布的印花被子。豆油灯下,我看到爷爷瘦骨嶙峋,半闭着眼睛。眼睛里放出微弱的光亮。
奶奶说:你孙子来帮你捶背了。
爷爷喃喃地说:要你捶。从来都是你捶,你捶才舒服。
奶奶对我说:你爷爷老糊涂了,我的手也没劲了!
奶奶不由分说地掀开了爷爷的被子。爷爷的身上尽是骨头,肋骨都清晰可见。
我赶忙往后退。
奶奶对我说:你不要怕,他是你爷爷呢!
我忐忑着走上前,握紧拳头,使劲捶打着爷爷的背部。
爷爷的背上啪啪直响,我的手上也产生了疼痛感。但是我不敢停下来。
爷爷呻吟着说:木祥的手不得力,没有劲,我的背还是疼。
奶奶无可奈何地说:我的手也没有劲了。
爷爷只好说:你去叫木祥找根棒子来,那样就有力了。
我赶快走出屋子,去找一根柴棒。我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找不到合适的木棒。最后,我在厨房门口找到了一根吹火筒。这根吹火筒是楸木树枝做的,用了好多年了,光滑,油腻,发着淡青色的光亮。
我拿着吹火筒进了屋子,奶奶高兴起来,眼睛里发出了光亮,说:木祥真聪明,这吹火筒就是捶背的材料。
我得到了奶奶的鼓励,便用吹火筒在爷爷背上使劲捶着,吹火筒在爷爷的背上发出“啪啪啪”的有节奏的响声。捶着捶着,爷爷就睡着了。
看到爷爷迷糊着,奶奶悄悄对我说:你问你爷爷,烟土到哪里去了。
我还没说话,爷爷喃喃地说:丢失了,烟土丢失了。
奶奶叹了口气,说道:真还是给了“风摆柳”了!
然后转过头又对我说:你爷爷是想喝油茶了。
听到喝油茶,爷爷翻了一下身,咂了一下嘴。
奶奶于是说:我说对了吧,俗话说,“三天不吃油茶饭,十二栏杆打偏偏”。你爷爷是赶马的时候惯下的喝油茶的毛病了。
奶奶就在老屋里烧起了炭火。一个拳头大的陶罐从床底下拿出来了,一砣豬板油雪一样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雪白的板油。奶奶就用猪油在炭火上用陶罐里烤米。奶奶枯瘦的手灵巧地抖动着陶罐,慢慢的,屋子里弥漫着糊米的味道。
我却不停地用吹火筒为爷爷捶背,捶着捶着,爷爷感到舒服了,发出哼哼声。爷爷说:只有你奶奶才能烤出这种味道。
奶奶说:怎么不喝“风摆柳”的茶,到头来还是要我服侍。
听到奶奶说起“风摆柳”,爷爷就不说话了,静静的任奶奶数落。
奶奶说:我说到“风摆柳”的时候,你爷爷就不叫疼了,他可能心里顺畅了……
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奶奶的思维异常地活跃。她知道死去一位老人,在妃子村是件大事,丧事的办理,关系到一个家庭在村子里的声望。
奶奶更想表现一下自己,让父亲率领我们去村子里磕头报丧,请乡亲们参加爷爷的葬礼。
我家院子里从来没有那样热闹过,昔日清静的老屋里人声鼎沸,烟雾弥漫,香气袭人。奶奶坐在堂屋,接受人们的慰问,她还要指挥宴席及装柩事宜。此时的奶奶,淡定自若,运筹帷幄,一副大家风范。
自己的家人,奶奶不能自己做主持,她根据主持看好的时辰,首先拿出备好的老衣给爷爷穿上,然后入柩。红色的棺木里睡着爷爷,他穿上了奶奶准备好的天蓝色的缎布长衫,戴上了锦绒布的黑色瓜皮帽。瓜皮帽上红色的顶子十分抢眼。
然而,棺木里的爷爷,始终是半睁着眼睛。妃子村的习俗是死人入柩不能睁着眼睛。主持入柩的法师让父亲去抹爷爷的脸,爷爷的眼睛依然不闭。
父亲无可奈何地离开。
主持人便让父亲去叫奶奶。奶奶站在棺木前端详了一会爷爷,一滴清泪清晰地出现在奶奶布满皱纹的脸上。奶奶缓缓俯下身,她枯瘦的手掌在爷爷的脸上轻轻一抹,爷爷的眼睛就闭上了。然后,棺木的盖子才打上了木质的铆钉。
爷爷出殡的时候,奶奶让我们跪在老屋在大门口“背棺”。昔日紧闭的大门,打开了厚厚的门扇,门前的墙壁上,插上了青色的香烛,那根圆润的门杠上,绑上了白色的孝布。奶奶思维十分敏捷,她指挥着抬棺的八个大汉,要他们把爷爷的棺木绕过老井。
老井上,父亲做了一个木质的井盖,井盖上挂着一把老铜锁。
这时候我匍伏在地,看着奶奶的的脸,我突然想起她吃土坯块的情景。
爷爷去世后,奶奶与“风摆柳”尽释前嫌。
“风摆柳”的病痛也多了起来,变得多愁善感,比从前沉默寡言。一天,她们在一个庙会上相遇。“风摆柳”也老了,但衣服还是穿得整洁,眼睛明亮有神,头发梳得光亮,身材纤瘦,走路飘飘如仙。见到我奶奶,拉住她的手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姊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要请奶奶走一回阴。
晚上,奶奶早早地就到“风摆柳”家。“风摆柳”也率领着子孙们,早就等候在堂屋里。奶奶一脸虔诚,先在堂屋的神台前烧纸火请神。先烧黄纸,再烧白纸,青香烛也插在了香炉里。堂屋里香烟弥漫,奶奶的磬铃响起,“风摆柳”便率子孙全部跪在了堂前。手摇磬铃,奶奶开始念咒语,完全是只有她听得懂的咒语。念着念着,奶奶慢慢失去了知觉,好似完全不在人世了。奶奶说她是到了阴间。奶奶整个人都发起抖来,声音也变调了,完全不像真实的奶奶。
堂屋里的人都吓住了。“风摆柳”起身,眼神神秘,摆手对大家说:不要慌!堂屋里安静下来。堂屋里安静了,奶奶脸都绿了,绿着脸开始发话了。但声音嘶哑。奶奶一呼喊,说主人家阴间人的灵魂也回来了。
奶奶还说她看到“风摆柳”家死去的人在阴间的事了。
“风摆柳”赶快带领子孙们磕头。
奶奶闭着眼,抖动着身体,嘶哑着声音说:你家的亡灵热闹得很呢,整个院子熙熙攘攘。
“风摆柳”家的人跪在神案前,情不自禁地往院子里看,院子里空空荡荡。但他们还是相信奶奶的话,认为自己家的亡灵真的回来了,都忙着磕头。
于是,奶奶问“风摆柳”家的人:个头不高,身穿青布上衣,黑色大裤裆的是你家的什么人,已经进屋了。
“风摆柳”听了,与儿孙们窃窃私语,商量了一下,说这人是侯光斗。
侯光斗是“风摆柳”的丈夫。侯光斗死得早,那时候奶奶还没有嫁到我们村子里来,怎么会知道他入柩的时候是穿青布上衣,黑色大裤裆的呢?
还没来得及让“风摆柳”家的人惊叹,奶奶说:对了,这个操四川口音的是你家的什么人?哭哭啼啼嚷着要什么债。
“风摆柳”家的人面面相觑,都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
奶奶说:想不起来?但人家不走呢!再想一想。
“风摆柳”的婆婆老迈了,别人想不起,她却知道呢,瘪着嘴说:还不是那个过去帮我家赶马的肖马帮,赶马路上被猴子扳石头下来打死了,一年的长工钱没有付……
“风摆柳”听了,连忙烧纸,说道:肖马帮,这世界都说是人死账烂!你在世的时候,主人家对你也不薄,领些钱回去吧,早去投生呢……
“风摆柳”边说边烧了些纸钱。
然后,奶奶又绘声绘色地传回死去的人想对活人说的话,又说是能把“风摆柳”家想对死人说的话传到阴间。这个晚上,奶奶成了死者与活人的传声筒……
纸錢烧得差不多了,奶奶的脸色好像回转了一些。然而,时间不长,奶奶马上又抖动起来,嘶哑着声音问道:怎么了,这个时辰了,又进来了个瘦高个的,穿蓝色缎长衫的,头戴瓜皮帽的?
“风摆柳”家的人都吃惊,想站起来的又跪下了。然而,都猜不出这个人,想不起自家有这么个人。
奶奶说:想不起来啊,真没有啊?但真是进来了啊,瓜皮帽上,还有个红顶子的——有点像个秀才呢。
“风摆柳”眼里却是噙着泪花了。他知道是我爷爷的灵魂去她家了。
“风摆柳”只是什么也不说。
奶奶说:是不是我家那老鬼走火入魔走错了门,我把他赶出去!
然后摇了一会磬铃,说道:出去出去,回家去,我给你烧油茶。
说着说着奶奶就醒了。奶奶醒了,用枯瘦的手指揉了揉眼睛,然后对“风摆柳”家的人说,这个人回去了,可能是走错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