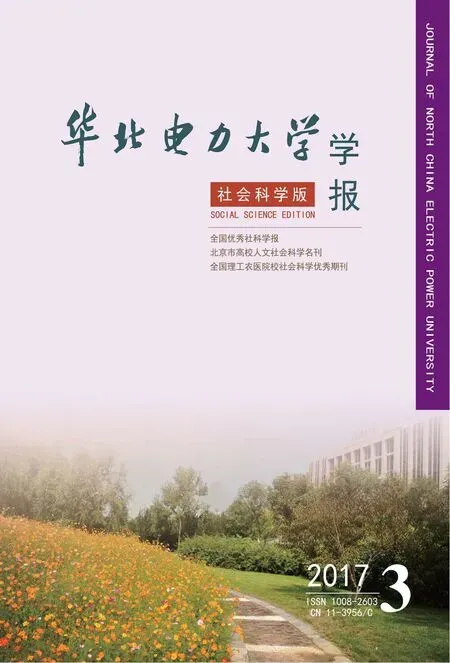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
——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倪培根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
——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倪培根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分歧。由于鉴定义务分配属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故而解决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现行法上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尽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但《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将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
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 环境侵权诉讼; 功能; 因果关系; 鉴定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认定向来是困扰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其认定多涉及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法官在审判中往往对鉴定意见比较依赖。当并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因果关系的真伪状态时,这种依赖性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即法官完全根据鉴定意见的结论来认定因果关系要件的真伪。然而,现实世界的状况要远远复杂得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经常会出现应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应缴纳鉴定费用的当事人没有缴纳费用,抑或即使进行了鉴定也无法得出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结论等情形。一般而言,这些情况下的不利后果均由负有鉴定义务的当事人承担,这一点在实务界已达成共识;但不能达成共识的是,究竟应由哪一方当事人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负担鉴定义务。对此,通过分析四则案例就能够很好地说明。
(一)原告对于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承担鉴定义务
案例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苗木死亡与三被告排酸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被侵权人应对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应举证证明其苗木的死亡与三被告的排酸行为存在关联性。因排放含酸污水的干渠并非直接流经原告的承包地,亦未直接污染原告的苗圃,故原告要求排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应首先证明其苗圃内苗木的死亡原因。原告虽申请了对苗木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但因未缴纳鉴定费而被退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原告无法证明苗木死亡的具体原因,亦无法证明三被告的排酸行为与其苗木死亡之间具有关联性,故本院认定,三被告排酸行为与原告的苗木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引自《王言高诉青岛恒胜石墨有限公司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3550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二:“本院认为……第三,关于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问题。首先应当确定蜜蜂的死亡原因,死因确定后,才能判断蜜蜂采上浜河的污水与其死亡之间的关联性。而原告在本院通知其申请对蜜蜂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后,未能在要求的期限内申请鉴定,其提供证人黄某到庭作证证明现场查某时间晚于蜜蜂死亡时间近一年,该证言不足于证明之前蜜蜂死亡的真实原因及与采污水之间的关联性。综上,原告虽然存在蜜蜂死亡的事实,但其主张蜜蜂的死亡原因及造成的损失缺乏证据支撑,不能确定,故其诉讼请求不能被支持。”*引自《陈林保与常熟市尚湖镇翁家庄村村民委员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5)熟环民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书。
在案例一中,受诉法院认为,原告应对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联承担举证责任,而若要完成这一举证责任,其必须首先证明禾苗死亡的具体原因,但原告只提出了鉴定申请却未缴纳鉴定费用,以致对苗木死亡原因的鉴定无法真正展开,因此原告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在案例二中,法官也认为,应由原告承担污水排放与蜜蜂死亡之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在通知原告应对蜜蜂死亡原因申请鉴定无果后,法院直接认定因果关系事实不存在。总而言之,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申请、费用缴纳以及鉴定不能的后果,均是由原告也即被侵权人承担的。
(二)被告对于因果关系要件事实负有鉴定义务
案例三:“……因此原告张贵琼应对损害的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通过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张贵琼所出示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显示,被告兴华公司在占用张贵琼的承包地进行便道施工并回填后,现场留有大量的建筑垃圾以及明显不同于周边未开挖部分土质的石块、土块,张贵琼就土壤种植条件遭受破坏与承包地上存在建筑垃圾之间存在关联性,已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兴华公司应对其施工行为与张贵琼承包地土壤种植条件受到破坏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庭审中,各被告均未就兴华公司的施工行为与土壤种植条件受破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故被告兴华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对张贵琼的承包地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引自《兴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与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4民终1501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四:“本院认为,本案系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根据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辽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茨榆坨镇偏堡子村受污染农作物的生产鉴定意见》已经证明系非农业因素造成原告农作物受害。被告生产场所与原告耕种地块邻近,且当时存在生产排污行为,在2014年5、6月份,被告与原告等24户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时,在辽中县环境保护局处理过程中,被告没能及时就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致使本案现因错过季节、现场情况无法还原,无法进行因果关系鉴定,对此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本案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引自《高松诉辽中县茨榆坨镇益春釉彩加工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辽宁省辽中县人民法院 (2015)辽中民三初字第1188号民事判决书。
由此可见,与之前两个案例恰恰相反,这两个案例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鉴定义务,分配给了被告也即侵权人。
以上表明:对于因果关系要件鉴定义务的分配,实务中存有明显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会导致当事人在攻防策略安排上的无所适从,以及受诉法院在相关法律适用上的捉摸不定。事实上,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鉴定意见属于法定证据的一种,因而当事人对因果关系申请鉴定自然是证据提出行为。在学理上,这种证据提出行为归于主观证明责任的调整范畴。[1]848因此,若要终结实务中的混乱做法以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搞清楚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活动中的功能及分配标准,便具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性意义。
二、理论工具: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活动中的功能及分配标准
按照我国学界的通说,证明责任分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又称为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又称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即指当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时,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的责任。[2]166而主观证明责任又存在抽象和具体之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一般由法律预先予以明确规定,故断然不会在具体诉讼进程中产生变更;而后者可能因证明活动的展开和法官的临时心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流转。[1]9-20由于鉴定义务的分配属于静态意义上的责任分配,也即其仅涉及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故而,本文只详细论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活动中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分配标准。
(一)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活动中的功能
在德国,有学者曾质疑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独立性,将其仅理解为客观证明责任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德国著名学者普维庭却认为,虽然客观证明责任一直在证明责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只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当然反射,也不仅仅是克服真伪不明的抽象意义上的利益。[3]39言下之意是,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还具有独立于客观证明责任的价值和意义。
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最早创设于德国,目的在于克服真伪不明所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4]这也就预示着,只有在诉讼结束之后争议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时,客观证明责任才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5]221而在此之前的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过程中,法官则主要依赖于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来裁判案件。具体而言,在诉讼的辩论环节,当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未提出本证时,即便对方当事人就前者所主张的事实提出了反据,法院也不会就该事实的真伪状态展开证据调查,而是直接依据主观证明责任认定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对于此种做法,若仅依据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加以说明,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释力和充分的说服力。原因在于,此际法院通过调查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或许同样能够发现争议事实的真伪状况,而不是非得将该事实认定为真伪不明不可。[6]由此看来,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之概念便有了独立创设的必要。
主观证明责任独立于客观证明责任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其一,对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采取的攻击防御策略,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譬如,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提出同一证人或鉴定人时,其预付报酬由负有主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3]39-40再如,在证据保全程序中,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法官是否批准申请的标准。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是为了实现其将来的利益,而主观证明责任则是这种利益的前提,即当事人知道其在诉讼中对某需要确定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在此情形,若仍旧认为主观证明责任只是客观证明责任的依附则不免失之妥当,因为,客观证明责任的功能发挥系以真伪不明为前提,而证据保全程序却是为了避免真伪不明的发生。[3]41
其二,在当事人没有或者不能就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时,抽象的主观证明则可以为法官提供裁判的依据。具体而言,如果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没有对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那么法官应对此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向其释明,并催促该方当事人尽快提供相关证据。此时,倘若这种释明与指示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法官则应依据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直接认定该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无需让对方当事人承担任何举证义务。[7]
在此,必须要予以补充说明的是,只有在奉行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中,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才存在发挥功能的空间与可能。[8]按照大陆法系理论的经典表述,辩论主义的基本要求有三:一是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由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提供的,而法官不得变更或补充其事实主张;二是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必须予以确认;三是法院只能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9]循此要求,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需要积极地提出事实主张,并在必要时提供证据对其事实主张加以证明。否则,当事人应就其不当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这正是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得以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前提。就我国而言,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同样奉行的是辩论主义原则,因此,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在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功能,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完全可以得到应用。
(二)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
从本质上讲,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即是诉讼主体的客观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其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待客观证明责任的。[3]36所以,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在分配标准及结果上均与客观证明责任保持一致。基于此种认识,我们不妨先对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进行考察,而这种考察一旦完成,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也就不证自明了。
围绕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这一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存有争论,并产生了待证事实分类说、法规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包括规范说)、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等理论。[2]16在这之中,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最具代表性。该学说以法规范的要件事实分类为逻辑起点,主张通过法律规范的语义表达和条文结构,分析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分配证明责任。[10]具体而言,规范说主要涉及四个命题:一是只有当事人对既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达到了应有标准,法官才能适用与此要件事实对应的实体法规范,但是,若该要件事实陷入了真伪不明的状态,法官则只能拟制该要件事实未实现,从而适用证明责任规范裁判案件;二是,每一方当事人要对有利于自己的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此为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三是,至于何种事实规范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则需要根据规范之间的支持、排斥和补充等性质与关系来确定,即权利主张者对权利形成规范承担证明责任,权利相对人则需要对权利妨碍规范(譬如合同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权利消灭规范(例如债务清偿、履行等)和权利限制规范(譬如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承担证明责任;四是,在区分以上四种规范时,需要依据法律条文的形式结构和用语表达。[4]125由此可知,“规范说”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思路是,先依据既定法律规范的文义和结构,识别出其属于基本规范还是属于反对规范,再根据每一方当事人要对于己有利的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这一基本原则,发现原就蕴含在实体法规范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
在以上四个命题中,基本规范与对立规范的识别是准确分配证明责任的关键,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理论问题。由于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同,权利生产规范与权利消灭规范、权利限制规范,尚且能够通过条文的语义表达进行轻松地辨别;[4]124但是,权利生成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却很难依据此种标准予以区分,因为二者其实就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恰恰也是反对者批评规范说的主要论据。[11]对此批判,罗氏并不认同,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透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来区分这两种规范。其理由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对于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经常以基本规范的形式予以规定,而对于权利妨碍规范则会以例外规范的形式加以规制。[10]187这也就意味着,罗氏观点若想成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立法者在制定实体法规范时必须具有分配证明责任的真实意图。换言之,能否直接依据实体法规范分配客观证明责任,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否充分考虑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必要性。[5]227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在制定或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时,显然对环境侵权构成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了充分的考量。*至于说立法者对于环境侵权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考量,文章第三部分会详细交代,故而,此处不再赘述。因此,反对者在方法论上对规范说所表示出的担忧,在我们国家其实并不存在。
而如此分配证明责任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以将深奥、复杂的证明责任分配原理变得极为清晰、简单,从而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把握。正是基于此,该学说在德国学术界占据通说地位竟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且得到了德国实务界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5] 185不仅如此,规范说还被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界和实务界所采纳,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12]尽管,规范说也曾遭受不少来自其他观点的尖锐批判,但是,其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标准及大致思路却依然被主流观点肯认,所谓的批判也仅仅是对其理论细节的具体修补而已。[12]此外,学理上认为,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应尽量追求稳固性,因为只有如此,当事人在从事民事诉讼行为时才能明了需要对哪些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并以此为指引来安排证据的收集、保存等策略,以及预估诉讼可能产生的最终结果。[13]由于规范说在创设之初就以寻求统一而固定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为目标,且主张根据稳固而抽象的法律规范来分配证明责任,因此该理论具有极高的法律安定性和可预见性。[1]103-104而这则是其能够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之通说的另一重要原因。
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与制度多传习大陆法系的传统,并且,规范说又具有以上的理论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本文也将采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分析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即实务界对于规范说已经作出了认可与接受的官方声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1条进行解读时曾明确表示,司法解释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就是依照规范说而制定的。[14]316
总而言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具有分配鉴定义务、并在鉴定不能时提供裁判的功能,且其分配标准始终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保持一致,即均遵循规范说划分证明责任的基本思路与标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形成的一个初步结论是: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申请、费用预缴以及鉴定不能的后果,均应由对该要件事实负有抽象主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至于说具体应由哪一方当事人对该要件承担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只有在考察我国现行法上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后,才能作出准确而肯定的回答。
三、我国现行法上环境侵权之因果关系要件的主观证明责任分配
在我国,涉及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条文,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65条和第6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下面本文就针对这些法条逐一地展开分析。
(一)基本规范与反对规范:《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第66条的关系解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此法条中,“污染环境”是指加害人从事的污染行为,包括排放废气、废水、废渣以及制造噪音等行为;“损害”是指受害人遭遇的具体损失,包括身体伤害、健康损伤以及财产损失等;而“因…造成…”的句式构造则表明,污染者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损害结果是由污染行为引发的,也即是二者必须存在因果关联。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污染行为、损害后果,还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均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意味着,只有以上三个要件事实都得到了证实,被侵权人才能要求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由此看来,因果关系之要件事实似乎应属于权利生成规范。而作为侵权之债的权利人,被侵权人应对此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但是,本法第66条却又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依据该条文的内容,污染者需要对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在我国,一般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一组可以进行代替性使用的概念。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但是主流观点对两者依旧不作过多的区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在术语翻译和法律移植过程中在所难免,且不会对我们理解和把握一些概念造成实质性困扰,故而在此持通说观点。。按照规范说对法律规范的类型划分,“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无疑属于权利障碍规范,理由是,一旦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环境侵权行为就不能成立,而侵权人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很明显,“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侵权人而言是极为有利的。从这一角度看,将该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侵权人承担,完全符合规范说的基本思路与逻辑。但问题在于,对于同一个要件事实,立法者先从正面将其证明责任分配给被侵权人,随后又从反面将其证明责任分配给侵权人,这种做法似乎会造成法律上的矛盾与冲突。
其实,本法第66条之于第65条,就如同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于一种特殊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关系。按照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15]但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并未对当事人主观过错进行规制,学界普遍认为环境侵权行为应奉行无过错的归责原则,也就是说,侵权人即便对环境污染行为的产生没有任何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也应就其污染排放行为对被侵权人的损害结果承担民事侵权责任。[16]因此,虽然本法第65条在逻辑上与侵权行为的基本归责原则相冲突,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前者属于特殊规则,并具有优于一般规则的法律效力。同样,本法第66条与第65条也构成了一种规则与例外的关系。而罗氏在论述权利形成规范与权力妨碍规范的关系时,恰恰也是援引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加以阐释的。其认为,权利形成规范所具备的前提条件一旦证成,既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便会产生;但是权利妨碍规范又告诉我们,如果加上某一个或几个特定要素,则该权利或法律关系便例外地不发生。[1]129综上所述,在我国的环境侵权领域,权利生成规范只包括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两个要件事实,且两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均应由权利人即被侵权人承担;而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属于权利妨碍规范,应由权利相对人即侵权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当然,以上只不过是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为了确保这一结论的周延性,还应利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其进行检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至第31条,分别规定了过失相抵、受害人故意、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六种情形,此六种情形皆属于侵权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因此学理上称之为“免责事由”和“减责事由”,也叫做抗辩事实。[17]按照学界通说,由于这些抗辩事实具有对抗损害请求权实现的法律效果,因而应由侵权人承担其证明责任。[15]而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之要件事实在《侵权责任法》第66条所处的位置来看,立法者很明显是将其作为“免责事由”及“减责事由”的同位语加以表述的。因此,该要件事实也属于抗辩事实的一种,而其证明责任也应由侵权人承担。
最后,该结论还能够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立法者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由于污染行为本身具有长期性、潜伏性、持续性、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如果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企业的排污数据作支撑,人们就很难判断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于此情形,若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侵权人承担,被侵权人经常会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收集能力,而遭受举证不能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更加不利于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预防。所以,《侵权责任法》第66条才从反面对环境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规制,即由侵权人就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18]
如前所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因此,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事实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也应该由权利相对人也即侵权人承担。
(二)“拨乱反正”:《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的兼容性解释
按照《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受害人应对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加以举证证明。对此,有文章指出,结合本解释第7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经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关于侵权人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规定,可以将这里的关联性理解为初步的因果关系。[19]虽然这种初步的因果关系具体指代何种含义,其文并未作出进一步交代。但是,通过字面含义我们依然可以揣测,所谓初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因果关系要件的正面形态即因果关系的存在。这种揣测在另一篇文章的论述中得到了印证。该文认为,这里的关联性,指代的是原告对因果关系提出的初步证据。这种初步证据的提出,便意味着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成立因果关系的可能性。[20]而无论是初步的因果关系还是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在核心观点上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即均主张受害人应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甚至最高法院也认为,《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是在坚持《侵权责任法》第66条有关因果关系之证明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又要求被侵权人对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承担证明责任,而这一规定对细化被侵权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最高法院公布的九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然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不当地忽略了。如上所述,侵权法66条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已经作出了安排,即由侵权人对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倘若将该解释第6条中的“关联性”,理解为初步的因果关系或者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则会出现一个要件事实却由两方当事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的怪异现象。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当因果关系出现真伪不明时,法官既可以“因果关系存在事实”难以证成为由,将败诉风险裁判给受害人承担;也可以“因果关系不存在”事实无法证实为由,将败诉风险分配给加害人承担。[21]如此一来,不仅法律制度的安定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且立法者借助证明责任规范分配诉讼风险的原本目的更是难以实现。此外,如果接受这种解释方案,《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66条就会形成一种冲突或紧张的关系,进而给法官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虽然,从法律位阶上看,基本法的法律效力无疑要高于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但既有的司法实践已充分说明,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司法解释的依赖丝毫不亚于基本法,有时甚至更“钟情”于司法解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官们可以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随意变换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例如,在《杨尚领诉周安排除妨害纠纷案》*“本院认为,因坏境污染引起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周安在屠宰生猪过程中,将污水排入原告杨尚领承包的鱼塘,被告周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排放污水与原告杨尚领鱼塘鱼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杨尚领的鱼塘中鱼的死亡与被告周安排放污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周安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引自《叶县人民法院(2015)叶民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6条,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承担,在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时,判定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在《黄满兴诉龙门县恒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等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本案中,原告自称其果树受污染减产,但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果树受污染减产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达到盖然性的程度,故原告未能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所以本案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引自《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2015)惠龙法汉民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审理法院适用《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告承担,在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时,判定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在学界,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具有法定性。具体而言,既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是预先由实体法加以规制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只能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去发现已然蕴含在实体法规范中的分配方案,而绝不能自行变更抑或创设既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结果。[14]317这一理论观点在我国实务界也得到了肯认。[14]317因此,为了协调这种冲突并改变实践中的混乱现象,有必要对《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进行兼容性的解释。在这里,对于“关联性”含义的准确界定至为关键。按照本解释第6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65条请求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应对污染物质及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这一事实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从语义上看,该条文明显是在根据《侵权责任法》65条的规定分配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前文已经言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结果完全取决于客观证明责任;而《侵权责任法》65条又仅仅是涉及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两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因此,污染物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就只能解读为污染行为要件或损害后果要件的具体性事实主张。鉴于损害事实是发生在被侵权人的身体健康或财物上,被侵权人对其固定和收集证据资料又比较容易;并且权利人在请求司法救济时应该明确具体的被告是谁,以便于随后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22]故而不妨将“关联性”理解为损害结果之要件事实的扩展性内容。其具体包括,污染物质到达了被侵权人的住所或财产所在地,被侵权人的人身损害与财物损失是在污染物质到达以后才发生的等内容,简言之,“关联性”所指代的,仅是污染物质与损害结果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已,并不包括损害事实发生的具体原因为何。这样一来,便可以有效地避免同一要件事实、却有两方当事人对其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当后果。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或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提供证据证明,但是《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经将因果关系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因此,为使既有法律规范能够彼此兼容,解释条款中的“关联性”只能被理解为污染物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绝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还应由侵权人对环境侵权之因果关系要件承担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
四、案例回应:抽象主观证明责任之功能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具体应用
由上可知,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并在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未对事实主张提供证据时发挥裁判依据的功能。而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对因果关系事实申请司法鉴定又属证据提出行为,因此,这种行为自当受到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的节制。由于我国现行法将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承担,故而,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申请之提出、鉴定费用之预缴、以及鉴定不能的后果均应由侵权人承担。具体而言,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当双方当事人就因果关系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争议而存在鉴定必要时,负有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侵权人,应积极地向受诉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并及时地交纳鉴定所需的费用。倘若侵权人没有提出鉴定申请或者没有缴纳鉴定费用,而致使相关鉴定无法进行,则法官应将由此产生的不当后果分配给侵权人承担;如果侵权人提出了鉴定申请且缴纳了费用,但鉴定机关却不能就因果关系事实是否存在得出结论,法官也应将此不利后果分配给侵权人承担。当然,以上两种情形下的不利后果并不一定就会导致侵权人败诉,因为,侵权人完全有可能向法院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因果关系不成立的证据材料,譬如,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排放的污染物质并未到达被侵权人的居所或者财产所在地,或者有证据证明其污染排放行为是发生在被侵权人遭受相关损害以后,亦或者其污染物并不存在诱发侵权人相关损害的物质成分,等等。但是,如果侵权人不能提供这些能够排除因果关系事实存在的证据资料,那么,法官只能依据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直接认定因果关系事实存在,进而判决侵权人承当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因果关系要件鉴定义务之分配发挥功能的具体轨迹。沿着这一轨迹出发,笔者将对文章开头部分所列举的四则案例在因果关系鉴定义务分配上的做法进行一一回应。
(一)案例一、二中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错误
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被侵权人应就侵权人的排酸行为与其禾苗死亡的“关联性”承担举证义务,而若想完成这种举证义务,被侵权人需对自身禾苗死亡的具体原因申请鉴定;由于被侵权人没有缴纳鉴定费用导致侵权人退出鉴定,因此被侵权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法院最终认定,侵权人的排酸行为与被侵权人的禾苗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由此可见,该案的审判法官将“关联性”与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等同,从而误认为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负有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最终导致被侵权人承担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败诉后果。
案例二的审判思路与案例一的审判思路并没有任何差异。在该案中,受诉法院认为,只有在被侵权人首先证明了其蜜蜂死亡的具体原因为何,才能进一步判定侵权人排入河道的污水与蜜蜂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因此,法院告知被侵权人应就蜜蜂死亡的具体原因申请司法鉴定,在其没有于指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且提供的证人又不足以证明蜜蜂死亡与污水排放之关联性的情形下,法院认定因果关系要件事实不存在,进而驳回了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上,这里的“关联性”依然被不当地理解为污染物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种错误认识,又促使法官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给被侵权人,其结果同样是,被侵权人不当地承担了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败诉后果。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两则案例之所以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审判法官对于法律规范的解读能力欠缺,没有准确把握司法解释中“关联性”的应有内含;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实务工作者对于主、客观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了解不够。
(二)案例三、四中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正确
在案例三中,虽然,受诉法院同样认为被侵权人应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被侵权人证明所承包土地存在大量建筑垃圾以后,法官便认定其土壤种植条件遭受破坏与建筑垃圾的不当回填之间具有“关联性”,也就是说,这里的“关联性”仅仅涉及侵权人存放的污染物与被侵权人损害在空间上的牵连性,并不包括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实质上的因果关联。在被侵权人完成对“关联性”的举证责任以后,受诉法院认为,接下来侵权人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建筑施工行为与土壤种植条件破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然而,侵权人并没有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故受诉法院认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而判定侵权人对承包地的土壤损害负有修复与赔偿责任。
在案例四中,被侵权人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该证据能够证明其农作物的损害是由非农业因素造成的,在此情形下,法院结合侵权人生产场所与被侵权人耕种的土地邻近,以及侵权人当时确实存在生产排污行为等事实,认为被侵权人已经举证证明排污行为与农作物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人应对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诉讼之前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侵权人却未能及时就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致使案件因错过季节和无法还原现场情况而不能对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故法院认为此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侵权人承担。在本案中,受诉法院对于“关联性”的理解和把握也是非常妥当的,即仅仅指代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时间与空间的联系,并不涉及损害发生的具体原因为何。
总体而言,案例一与案例二对于司法解释中的“关联性”理解有误,以致于错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被侵权人,在被侵权人没有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提出鉴定申请或缴纳鉴定费用的情况下,法官便直接认定因果关系不存在,进而导致被侵权人承受不当的裁判结果,系法律适用错误;而案例三和案例四则准确把握了司法解释中的“关联性”的含义,将其与环境侵权之因果关系要件事实区别开来,在被侵权人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完成举证义务后,由于侵权人未对因果关系要件提出鉴定申请或未及时申请鉴定,法官认定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真实成立,进而判定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故其法律适用正确。
五、结语
行文至此,围绕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这一问题,笔者可以形成的结论有以下四点:
1.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们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由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承担鉴定义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要件事实承担鉴定义务。
2.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的证据提出行为具有指引功能,且在当事人没有对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时能够为法官提供裁判依据。由于鉴定意见属于法定证据的一种,因此,鉴定义务的分配属于抽象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也就是说,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需要依据该事实之抽象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结果作出判断。
3.学理上一般认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始终与客观证明责任保持一致,因此,一旦明确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之分配结果,该要件事实的抽象主观证明责任也就不证自明了。
4.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规定,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由侵权人承担,虽然《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又规定,被侵权人需对污染物与损害的关联性进行举证证明,但是,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关系,而并不涉及实质上的因果关系之内容。也就是说,侵权人应就因果关系要件承担抽象主观证明责任以及鉴定义务。
[1]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848.
[2] 赵钢,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3] 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9.
[4]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2.
[5]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 胡学军.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德、日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家,2012(2):167.
[7] 奥特马·尧厄尼希.德国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8.
[8] 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值新开展[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216.
[9]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
[10] 陈刚.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
[11] 吴泽勇.规范说与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适用——兼与袁中华博士商榷[J].中国法学,2016(5):55.
[12] 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J].中国法学,2012(4):151.
[13] 姜世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真实义务[J].东吴法律学报,2005(3):71-72.
[14] 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15]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8-90.
[16]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30.
[17]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
[18]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33-335.
[19] 袁中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及其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之述评[J].法律适用,2015(8):50.
[20] 薄晓波.论环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18-119.
[21]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制度的深层分析[J].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24.
[22] 贾小龙.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成立证明问题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5):121.
(责任编辑:李潇雨)
On th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in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Elements
NI Pei-gen
(Law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there are serious differen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fication obligation. Because the function of category identification obligation distribution belongs to the abstract subjective proof responsibility, the ke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is to clear the existing law of causality to the abstract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of allocation.The sixth articl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problems on environmental tort" provises, the Victim shall be proof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lution and the damage proof, but sixty-sixth of "tort liability law" has assigned the o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of causality elements to the Offend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stribution and customer subjective proof Abstract responsibility. The concept of burden of proof has always been consistent, and to maintai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legal norms, the "relevance"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pollution and damage in space and time on the implications, not involving causal relationship.
abstract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function; causal relationship; causality identification obligation
2017-03-29
倪培根,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
D922.68
A
1008-2603(2017)03-0053-10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