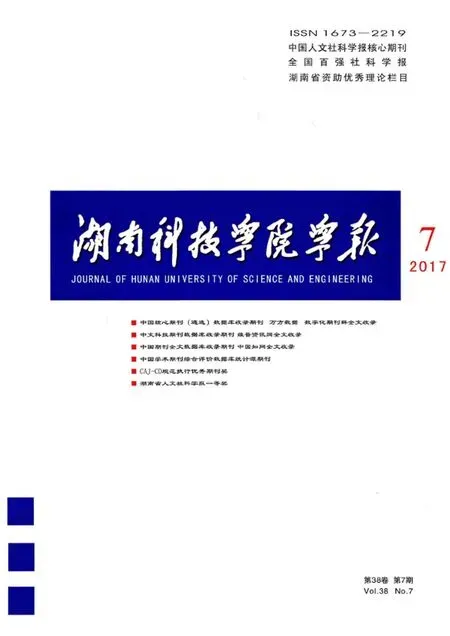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视觉透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意蕴
李新美
从女性主义视觉透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意蕴
李新美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除了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还特别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透过不同女性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揭示关于“轻”与“重”的主题,作者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哲学思辨,跳出故事情节去哲理思考,表达了对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关心和关注,给现代女性以启示和反思。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女性主义;主题意蕴
一 特蕾莎——关于“生命之重”的阐释
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女主人公特蕾莎堪称为“生命之重”的的代表。小说主题讨论“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其实就是探寻“存在”的“轻”与“重”。生命中,许多人都追求自由自在,希望在生活中能够心灵放纵、随心所欲,以获得更高层次的身心愉悦,追求“生命之轻”;在生命中,理想、欲望、责任,使人体痛苦、深重与压抑,这种束缚无休无止,就算是某一欲望暂时获得了满足,在生命中,又会产生新一轮的欲望。[1]人们想摆脱存在之“重”,却又难以摆脱。特蕾莎的成长环境,是给她带来“生命之重”的首要因素。特蕾莎自幼家庭生活比较不幸,在这个家庭中,不仅物质环境贫苦,精神环境更加贫瘠。特蕾莎的母亲曾经是一位圣母一样的漂亮女人,曾经有九个男子向她求婚,在这九个男人中,都有着各自的优势,或英俊、或富有、或机智、或才学等等,然而,最后由于最具男子气概的男人霸王硬上弓,使得她怀上特蕾莎,不得不违心的嫁给这个男人,在婚后的日子里,她越来越觉得其他八个男人都比第九个强,她心里产生不满,并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生命。特蕾莎从小渴望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渴望一个具有灵魂的自己,在与母亲生活的那段日子里,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所以,她选择逃离,却不想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那一刻,又走向了另一种“生命之重”[2]。
小说中,特蕾莎起初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弱者,她也很想试图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现实生活却总是不尽人意,给她带来无比的沉重感,在与这个世界的抗争中,她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特蕾莎追求灵与肉和谐统一,然而,在面对生活的种种经历的时候,她体会到了灵与肉的冲突,每一次现实社会的体验,都让她觉得非常沉重。特蕾莎将性与爱看作一体,然而,托马斯却将二者分离。特蕾莎始终追求着灵魂与肉体的和谐统一,然而她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她想要改变,却又始终无力改变这种“生命之重”。软弱性格和依附意识是特蕾莎承受着生命之“重”主要因素之一。母亲肆意践踏肉体,摧毁着特蕾莎的灵魂,践踏着特蕾莎的尊严。在“自我毁灭”的母亲那里,她始终处于自我缺失的状态,所以,她要逃离母亲的世界,去寻求依靠和庇佑,寻找真正的自己。在遇到托马斯后,托马斯强大的力量吸引着她,特蕾莎幻想着在那里能够寻求到依靠和庇佑,然而,在这个“花花公子”身上,她很难获得灵魂与肉体的和谐统一。特蕾莎只想听命于他和服从于他,虽然特蕾莎也知道托马斯的背叛和生活方式,也知道这个男人不能信任,然而,软弱性格和依附意识又使她没有办法不去依附这个男人,软弱的性格促使她不断地要逃离生命之“重”,然而,她又很难摆脱生命之“重”,命运始终让她承受着生命之“重”[3]。
二 萨比娜——对“存在之轻”主题意蕴解读
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女主人公萨比娜堪称为“存在之轻”的代表。这个女性形象顺从自我感觉,她的生命体验与特蕾莎完全不同。在萨比娜的人生中,一直在追求心灵放纵的生命体验。她反抗媚俗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身心愉悦,通过不断的背叛去追求自由。因此,女主人公萨比娜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对萨比娜来说,整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自由,不断背叛的过程,对萨比娜来说,背叛有着致命的诱惑。在她十四岁时,由于其父亲反对她恋爱,为了报复父亲,她处处与父亲作对,并学父亲瞧不起的立体派美术,她的背叛之路从此开始。后来,她还选择嫁给一个平庸丈夫,这个男人离经叛道,父亲被她的所作所为活活气死。在背叛的道路上,萨比娜感到一丝的宽慰,并越陷越深。[4]美术学院要求她在绘画的时候,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派画法,然而,她偏要像毕加索那样地去画画,不喜欢因循守旧。随后,她又觉得丈夫变成一个讨人厌的酒鬼,不再是一个乖张的浪子,又选择离开了丈夫。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使她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自此,她开始不停地背叛,她要摆脱一切沉重与束缚,在成长的道路上,承受生命之轻。
萨比娜的背叛,归根结底,她背叛的是媚俗。萨比娜反抗媚俗,背叛一切盛行的东西,在反抗媚俗的过程中,萨比娜成为了“轻”的代表,她一直在追求心灵放纵的生命体验。媚俗一词源于德语的Kitsch,那么媚俗是什么?米兰·昆德拉认为,媚俗是一种泯灭个性来取悦大众,以撒谎作态取宠社会的行为,可以说,媚俗是人类的一种通病,萨比娜反抗的媚俗,是极权文化、男权特征的政治制度下所推崇的善与恶、美与丑标准。萨比娜不仅在生活中反抗媚俗,在与男人性爱的过程中,也与媚俗思想抗争。在与弗兰茨性爱过程中,萨比娜颠覆了传统思维,颠覆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思想。她一改性爱中男性凝视女性,女性被看模式,做爱时,她一直凝视着弗兰茨,在萨比娜面前,弗兰茨是弱小的,萨比娜目光高高在上,而弗兰茨做爱时总是闭着眼睛,在性爱的过程中,萨比娜也表现出一种反抗媚俗的行为,表现出对传统男权思想的背叛。萨比娜用这种反抗媚俗的态度,来宣泄男权社会女性失去自我的愤恨,她用背叛的方式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世界。背叛是萨比娜一生的行为准则。[5]她要背叛一切可以背叛的东西,压倒她的不是生命之重,而是导致她最后走向空虚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三 从女性主义视觉透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意蕴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残酷地、又难以摆脱的人生命题:生命,是轻还是重?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恒而又难解的命题。“是沉重还是轻松”,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昆德拉运用了大量议论,多次重复暗示这一富有哲理意味的主题。主人公托马斯始终徘徊于生命的“轻与重”的追问,性与爱的轻与重、灵与肉的轻与重、良知的轻与重,最终回归到生命的轻与重的追问中。[6]托马斯将肉体之爱看作是“轻松的”、“简单的”爱情,并且以这种与多个异性发生性关系,随意的自由单身生活看作是“生命之轻”的标志之一,托马斯认为,人伦之爱、夫妻之爱让人生活受压抑,那种“爱”是责任,是负担,为此,他甚至放弃了被世人普遍认可的人伦之爱。托马斯认为,人伦之爱、夫妻之爱是生命被扭曲的“重”。然而,当托马斯遇上特蕾莎之后,单身的托马斯却意外的发生了思想变化,他背叛了自己的“轻松”,出于“奇怪的同情”,托马斯接受了小酒馆女招待特蕾莎。托马斯接受萍水相逢的特蕾莎是近乎无意识的。在与特蕾莎交往中,托马斯还发现同情居然是最高档次的爱情,虽然许多人一直将同情看作是“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但是,托马斯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种出于生命本质的感情,是最真诚的、至高无上的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生命随之变得沉重。[7]
昆德拉笔下所描绘的“轻”与“重”,是以男权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在男权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居于被支配的地位,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就充分体现出特蕾莎被置于“他者”的地位。就社会地位而言,二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托马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物,作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不仅受人敬仰,而且待遇丰厚。而特蕾莎只是一名乡间女招待,为了逃脱母亲的世界投奔托马斯而来的。所以,二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两人的爱情也是极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小说中托马斯一再强调:“特蕾莎就像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8]二人对于彼此之间的忠诚度是不一致的,特蕾莎幻想追求灵与肉和谐统一,而托马斯是个花花公子,他很容易赢得女性的青睐,并对女性有着无力控制的占有欲。他要在不同的女人身上猎奇,在性爱中去寻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托马斯觉得自己的风流与对特蕾莎之间的爱情毫不矛盾。然而,爱情又是自私的。当特蕾莎与其他男人跳舞,别的男人紧紧的抱着特蕾莎的身体时,“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之情”。特蕾莎与托马斯的爱情,并不是一种相互的给予和赠送,真正赠送的只有特蕾莎,在这个爱情里,特蕾莎的忠贞是维系情感的唯一一根柱子,如果失去了这根柱子,他们的爱情大厦会彻底坍塌。因此,作为一个弱者,特蕾莎的现实生活总是不尽人意,给她带来无比的沉重感,所以,她要逃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萨比娜一直在追求自由的生活。出于艺术家的敏感,她意识到社会氛围里一种浓浓的“媚俗”意识。因此,背叛就成为了她自我存在的方式。萨比娜一生不停地在背叛。背叛父亲背叛自己的丈夫,最后背叛祖国、背叛情人,萨比娜在背叛的路上摆脱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背叛一切可以背叛的东西,使她一身轻松,没有任何使命,获得生命的轻盈,走向无限自由的极大解脱。然而,萨比娜美好的幸福却是建立在无线的孤独基础上的,由此可见,萨比娜的悲剧不是因为“生命之重”,压倒她的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9]看到暮色苍茫中幸福人家的闪亮窗户时,她不止一次地感到双眼被泪水打湿。在背井离乡,倍感虚空的时刻,她不免被媚俗中的温情所打动。萨比娜背叛的极点不免虚空,其潇洒背叛世界的背后,也隐含中对世俗温情的向往,这似乎是她终身背叛的尴尬。然而与别人不同,短暂停留后她,又走上寻求自我生命存在的征途。短暂停留并不能抹杀她的高傲与决绝,她走向极端同时又质问极端,一如既往的探索人生存在可能性的意义。萨比娜虽然选择了背叛,但其背后仍是为寻求个体生命而存在。
四 结 语
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将两个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女性展示给读者,让读者从女性的视角,去解读“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的主题意蕴,目的是告诉读者,每个人都在为寻求个体生命而存在,有时候,我们很难逃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也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1]黄璐.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究——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J].戏剧之家,2014,(9):381-382.
[2]乔婷婷.牧歌式宁静与背叛式逃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女性主体意识[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4):52-54.
[3]陈江.生命之轻之重——对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赏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8):131-132.
[4]郭向宇.沉沦或本真——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昆德拉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J].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10):167-169.
[5]谢永鑫.感性牧歌对两性冲突的消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阴山学刊,2012,(3):47-50.
[6]梅启波.昆德拉哲思概念中的女性独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的形象分析[J].语文知识,2009,(1):30-32.
[7]周洪松,郝加齐.女性主义视角下《围城》的主题意义探究[J].科教导刊,2016,(2):142-143.
[8]唐艺嘉.期待视野下的“轻”之意蕴——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10,(12):90-91.
[9]邓平平.“灵与肉”的叩问——试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1,(3):4-6.
(责任编校:呙艳妮)
I106
A
1673-2219(2017)07-0035-02
2017-03-26
李新美(1981-),女,云南凤庆人,硕士,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