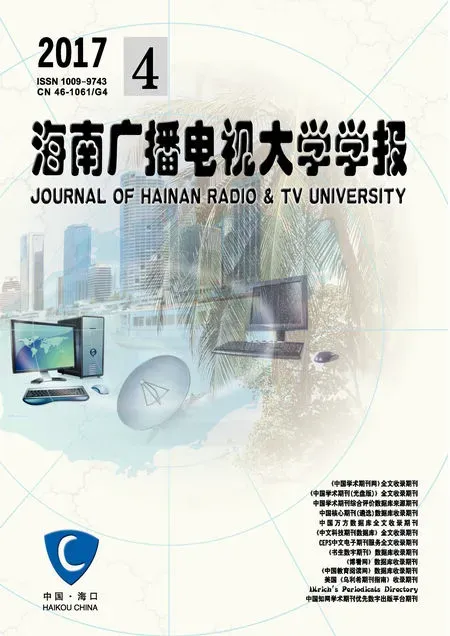也论南海之英译
李双梅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也论南海之英译
李双梅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领海,南海一词的命名是中国人民认识客观世界、根据地理特征所赋予的文字代号,它富含中国元素,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因此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当下的通用语研究,建议在南海英译时直接采用汉语拼音。采用汉语拼音意义重大,它不仅彰显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提升我国的话语权,而且还为英语提供了丰富词源。
南海英译;通用语;汉语拼音;英语词源
一、引 言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情系乡土的称谓,而决非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或者一个单纯的地域名称。它是人们长期以来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赋予共同约定的文字代号。从语言学角度而言,作为代表特定地域色彩的、专用汉字的地名,是人类语言词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指称符号,蕴育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也是该国主权的具体象征。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而言,地名不仅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它还具有象征意义,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的浓缩,风情画卷的再现;它蕴含逸闻趣事,承载着人文底蕴,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法律层面而言,地名的属性犹如一件商品有其专利权一样,不容假冒,更不容纂改,其尊严不容肆意践踏。
二、南海的由来
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 Duyvendak)在其《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一书中论述道:“《前汉书》记载极有价值,因为它表明了中国自古就与印度洋诸国有贸易关系。[1]”16世纪,葡萄牙水手驶入南海,首次将它称为中国海(Mar da China)。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公元前1046-771)最早将南海命名为南方海,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的《诗经》《左传》《国语》也称之为南方海。战国时期的楚国把它称为南海。东汉(公元23-220)将它喻为涨海,南北朝将它称为沸海。南海这一称谓到清朝年间得到进一步确立并一直延续至今。据记载,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在《使西记程》中,他描述道:“船人名曰齐纳西,犹言中国海也。”“齐纳西”为China Sea的音译,但绝非是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的音译。1707年英国船舶“密克勒斯费”号到达南沙群岛,因而称南沙群岛为“密克勒斯费滩”。二战期间,南海及其周边海域被日寇侵占,日寇将其命名为南支那海(南シナ海),这一蔑称一直持续到2004。出于一己私利,越南将南海称为“Biên Dng”(东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纷纷摇旗呐喊,称我南海为“南中国海”[2]。菲律宾甚至煞有介事把南海称为“西菲律宾海”,其野心昭然若揭。
从上述各种称谓中人们不难发现,自古以来我国对南海的称谓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今天之所以有人将南海称为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 ) 并对其大做文章其实别有用心。他们用心叵测,将南海冠以south一词,想以此偷梁换柱,证明所谓的南海位于中国“以南”、位于越南和柬埔寨“以东”、位于菲律宾“以西”、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以东”等[3]。按照这一荒诞逻辑,上述这些国家对南海理应享有主权,似乎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达到分割我国领海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见,在南海前加上前缀south 和不加south 一词关系重大,意义深远。它绝非仅仅是一字之差,而是包藏祸心、用心险恶,为瓜分我领海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
三、中国地名英译变迁
陈剑(2014)研究发现,我国地名英译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宋元至清早期)、近代(清中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现代(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4]。由于外商与传教士之故,古代命名注重音译,这一点从国外绘制的地图以及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鉴于古代我国地方割据势力盛行导致各自为政局面,因此译名时难免夹杂一些方言土语。Travels of Marco Polo的英译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明朝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605年所著的《西字奇迹》(Wonders of Western Writing)首次将罗马字母用于汉语注音,也是最早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26年所著的《西儒而目资》(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被誉为“汉字字汇”经典,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采用罗马字母标音的字典。清朝早期的译法与宋元明时期相比更趋合理,拉丁字母使用的拼写和方法也日趋完善[4]。此时的英译名对清朝后期的“威妥玛式”拼法奠定了基础。
外商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名英译的发展,此时一切翻译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在汉字拼写拼读的译法上采用了罗马字母,较具代表性的有“危妥玛式”和“邮政式(旧邮电式)”拼法。“危妥玛式”拼法典型的有易经(I Ching),道教(Taosim),功夫(Kungfu)等;邮电式拼法有Peking,Nanking,Tingtao等。现代译法日趋科学,它遵循“名从主人”和“专名音译,通名意译”原则。如直接启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按民族语言拼写的有Lhasa(藏语),Urumqi(古蒙语),Hohhot(蒙语),Habin (满语)等。民族文化特色词汇的英译有fengshui,gongfu等。而地名更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不允许有随意性,更不容篡改。地名属于特定的、富含民族文化的特色词汇。特色词或文化负载词是指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代表该民族文化内涵特定的词语和表达习惯。它反映了该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大自然抗争的历程。它具有独一无二、约定俗成的特点。它和功夫(gongfu)一词一样,只要人们一提到功夫二字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成了中华武术的代名词,在西方青少年心目中,gongfu成为了中国人的象征,也是西方青少年崇拜的对像。它富含中国元素,寓技击于体育之中,但又将技击寓于搏斗运动与套路运动之中。它内外合一,具有形神兼备的民族风格;既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有人曾一度将功夫译为martial arts,其实两者南辕北辙。因为后者重技,而前者技神兼备,所以将它译成martial arts不足以体现前者那种特有的刚正不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精神,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这一原因,现如今很少有人将功夫或武术与martial arts 相提并论。
四、归化、异化与地名的英译
如前所述,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文化负载词范畴。人们在面对诸如文化负载词这类翻译时,会情不自禁地从归化或者异化寻求解释。诚然,归化与异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能对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提供理论依据。所谓归化是以目的语为宗旨,把目的语视为最终目标。异化则与之相反,它将源语文化视为其最终归宿。德国翻译理论家Schleiermacher最先提出来归化与异化这一概念。他称,译者要么使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使作者向读者靠拢,两者必居其一[5]。Venuti (1998)是归化的鼓吹者,他认为,译出语必须直白、流畅、无翻译痕迹,无生硬感;要与读原作“别无二致[6]。”看来,采用归化或异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Wiersema 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独到见解[7]。他认为特色词的翻译之所以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因为人们对目的语文化缺乏认识和了解所致。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熟悉环境,环境有助于加深对文化的了解。他同时指出,人们不必过分担心外来词汇影响,因为外来词汇不仅使译文丰富多彩、纯正地道,它还丰富和发展了作为通用语的英语词汇。这些词汇有异域色彩,能激发人们对异域文化进一步了解的热情。Wiersema把吸纳外来语词汇视为翻译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缩小文化差异的必要手段[7]。Seidlhofer曾这样形容英语,“英语之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表现了强大的包容性”[8]。所以,不可否认通用语具备灵活多样、适应性强 、富有创意、易于发挥等优势,也因此具备了交际策略所需的合作功能特点。的确,随着全球化进程,英语作为通用语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这便是英语通用语的特点。译者在面对文化特色词的翻译时,不必畏首畏尾,相反应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这正是今天通用语发展的一大趋势。
Crystal的研究显示,当下英语为母语者与英语为非母语者之比为1比4,即每5个非母语英语者当中只有一个英语为母语者[9]。虽然难以准确统计英语使用者的确切人数,但说英语的人数仍在呈上升态势,而且人们一致公认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时代已经到来。通用语的到来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以往人们对其所持的态度和传统的翻译模式。人们已经逐渐接受英语为通用语,过去那种非标准英语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观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无益发展,因为谁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Seidlhofer曾精辟地论述道:通用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10]。可见,英语已经超越了它的国界,它已不再属于某一国或几国的专利,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吸纳着各国英语的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如果通用语是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庞大的说英语群体以及中国英语变体催生出的中国英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中国英语彰显独特文化内涵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学英语人口比例位居世界之首,在长期的英语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推广和普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发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践行英语的学习与普及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英语。中国英语一开始便以弘扬民族文化为使命,以其特有的民族身份屹立于世界英语之林。可以说,中国英语已经成了在中国被中国人使用的、源自标准但又带中国特色的英语。现在,中国英语已经被越来越多英语国家所接受、所欣赏。中国英语的特点不是别的正是它的文化特色词,这些词之所以有特色是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耳濡目染、深深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中一种不灭的情怀。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战天斗地、与封建势力、与外国列强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特殊性难以复制、不可模仿。这就是为什么一大批汉字以拼音形式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英语的原因。如pinyin (拼音)、Putonghua (普通话)、yamen(衙门)、dazibao(大字报)、tai chi(太极)、fengshui(风水)。可见,汉语在传扬中国元素、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以海纳百川、大道致远的博大胸襟吸收外来词汇。
近年来,中国特色词以它特有的魅力闪亮登场,呈现出一大批新的合成词,如‘xiaokang society’(小康社会)、‘hongbao’(红包)、 ‘hukou’ (户口)、 ‘gaokao’(高考)等。有些则是直接从汉语译成英语,语序不变,如 ‘four modernisation’ (四个现代化),‘one country,two systems’(一国两制),‘running dog’(走狗),‘to get rich quick is glorious’(发家致富光荣),‘iron rice bowl’(铁饭碗),‘open-door policy’(开放政策),‘paper tiger’(纸老虎),‘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the three represents theory’(三个代表),‘Project 211’(211工程),‘three stricts,three steadies’(三严三实)等等。这些特色词文化浓郁,特色鲜明,具有典型的中国英语特色。它进入英语的同时不仅丰富了英语的内涵,同时又传扬了中国文化,不愧为我国文化推广与普及的外交使者。毫不夸张地说,今后主宰全球的两大语言非英语与汉语莫属。前者将发挥其独有的外壳优势,后者将在这一外壳下提供丰富的精神内涵。两者可谓强强联合,相得益彰,这无疑在语言的发展史上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 翻译的文化问题
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现象,作为传递文化的媒介——翻译,无不如此,所以人们在翻译时不应过分注重字面含义,而要注重文化所承载的内涵和精髓。严格地讲,翻译时难免碰到语言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说穿了,这些问题与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文化转借可以化解文化涉及的难题。Seidlhofer对文化转借也情有独钟。他指出,同传译员在面临诸如文化涉及的表达时应借助文化转借这一杀手锏解燃眉之急。如同踢皮球一样,译员可将源语直接向与会者和盘托出,“让他们品味原汁原味”[8]。
所谓文化转借是将源语完整地移植到目的语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源语词句逐渐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久而久之便成了规范标准且不可替代的用语。汉语中的马达、卡宾枪、可口可乐等便是有力的说明。文化转借在史料、法律、政治文本中十分普遍,如语言学中的“La langue”“La parole”源自法语,如今它成了语言学界家喻户晓的词语。文化转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彰显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它不仅能自觉抵制霸权文化的渗透,而且还能积极消除殖民主义流毒的影响,比如南海一词的英译。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澳大利亚国会在最近通过议案宣布废除旧国旗,启用新国旗。因为旧国旗体现了殖民者余毒,是大英帝国与殖民者的象征。此举是后殖民主义倡导的多元文化典范。
(二)后殖民主义与多元文化
Spivak(1993)首次提出了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11]。后殖民主义以其独特视角审视文化与翻译之间关系。按照后殖民主义学派观点,翻译长期以来被殖民者所绑架,被他们用作武器奴役被殖民者。不仅如此,殖民者借助翻译宣扬其意识形态,兜售其价值观。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历史事实。他们对被殖民者强加其语言,从精神上进行奴役,鼓吹白人至上,企图达到巩固其殖民统治目的。
可见,译者在面对文化特色词翻译时,应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借助翻译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弘扬民族文化。译者不应把在翻译研究中被忽略、但对翻译活动又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即权力忽略不计,因为权力揭示了翻译活动中两种文化不平等的关系[12]。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滥用权力或阴谋篡权对被奴役国家造成的灾难至今阴魂未散。最典型的莫过于南海一词的英译。南海诸岛这个我国人民有着特殊“原始性权利”的岛屿如今却陷入激烈的国际争端,南海周边国家纷纷提出地名更易,提出主权要求并肆意侵占,这不得不令人反思。众所周知,南海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19世纪,英国踏入南海海域,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殖民意识,他们按照自己的殖民意图,不是任意命名,就是肆意更易地名,使得南海命名远远偏离名从主人的国际命名适用原则,成为国际法所不容的殖民地名[13]。今天,一些国家无视国际法,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政治化,以南海问题挑起国际事端,以达成其从中渔利、遏制中国、称霸全球的野心。可见,南海一词的英译直接关系着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意义已超出了翻译层面。如若要消除歧义,采取汉语拼音是上策。
(三)汉语拼音
译者有义务纠正南海一词的英译,还其本来命名,真正捍卫名从主人的国际原则。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南海可以被肆意更易为the South China Sea(南中国海),那么同属中国五大海的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湾又当如何翻译?有人将南海译成China Sea,看似有一定道理,但仔细品味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模棱两可之嫌。它是专指南海还是指所有的中国海域?这使人感到概念模糊,指称不具体。如此看来,将南海译成the South China Sea的人用心叵测、居心不良。要揭穿殖民者歪曲历史事实、对被奴役者强加其语言,从而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狼子野心,必须要从源头上拨乱反正。作者认为,若要消除殖民意识的影响,捍卫国家主权,最好将我国五海分别命名为其对应的汉语拼音:Nanhai,Bohai,Huanghai,Donghai,Beibuwan。至于海和湾的英译问题,建议初次使用时在其旁用英语加以注释。常言道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人们便习以为常。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彻底消除歧义,避免争议。
其实,早在1977年8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已经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的决议。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ISO 7098—1982),确定了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文(包括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地位。1999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国家标准《地名标牌城乡》(GB 17733.1—1999),规定街牌、巷牌、楼牌必须标示汉字名称和汉语拼音,并作为强制性条款给出标准制作图样,要求街、巷名称的专名和通名都必须使用汉语拼音标注,如:长安街,应在汉字下标注汉语拼音CHANG'ANJIE。
因此,根据名从主人原则,南海理所应当地命名为汉语拼音Nanhai。
(四)汉语拼音与英语发展的关系
严格地讲,英语当下之所以成为通用语或国际语,是因为在其发展演变过程彰显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今天的英语通用语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1.拉丁语、如street (Lat. Strata via); cheese(Lat. caseum);2.日耳曼班北支,如skin,skill,ill,get,leg,Thursday;3.法语,如生活词汇:master,servant,dinner,banquet;法律:court,assize,prison,custom,vent,price;官衔:duke,marquis,viscount,baron;军事:battle,siege,standard,fortress;亲属:uncle,aunt,nephew,niece,cousin;4.希腊语,如telegraph,philology,geology,gramophone,cybernetics。英语还从其他语言中吸收养分,极大丰富了英语内涵。有学者研究发现,英语的同义词数量异常丰富,居所有其他语言之首,如almighty-omnipotent; blessing-benediction; bloom-flower; calling-vocation; manly-virile; womanly-feminine,在此仅举几例。
美式英语是当今最大的变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英语夹杂了大量美国黑人英语。美国黑人英语拥有一套既复杂又系统的语法,与美国标准英语相距甚远,但与其他英语变体又有某些共性。同时,它也有其独特的词汇和韵律特色,例如:单词gumbo 的意思是spicy stew辣汤,它来自班图语Bantu;bogus 意思是fake假的,来自豪萨语Hausa (boko);dig表示 like,appreciate喜爱的意思,来自沃洛夫语Wolof (deg)。可见,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更是与时俱进的。汉语进入英语不仅彰显了自己特色,丰富了英语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或许正是英语作为通用语之所以通行的原因所在。
六、结 语
我国先人对南海一词命名由来已久,南海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还是一个富含中国情结的文化特色词。因此人们在翻译时不可断章取义,更不可望文生义,相反,人们要充分考虑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鉴于英语难以找到其对应的表达,建议在英译时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早在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就已得到确立。采用汉语拼音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我国的话语权,而且它还为英语提供了丰富词源。它同时还表明,作为英语通用语的中国英语正在亚洲英语变体中异军突起,昂首走向世界。
[1] 连益.论南海诸岛的发现、命名及英译[J].译苑新谭,2013(5):139-146.
[2] Pacpaco,Ryan Ponce. Rename South China Sea—solon | Nationa. [EB/OL]. http:∥www.journal.com.ph/index.php/news/national/6669-rename-south-china-sea-solon journal.com.ph.
[3] Kratoska,Paul et al. Locating Southeast Asia: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M]TØnnesson,S. Loca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5:203-233.
[4] 陈剑.古代时期中国地名的英译研究[J].昆明学院学报,2014(2):128-132.
[5] 公斐.对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翻译策略的思考[J].青年作家,2015(6):36-36.
[6] Venuti,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the Differenc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210.
[7] Wiersema,N. Globalization and translation:A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oday’s translation[J].Translation Journal,vol. 8,2004:333.
[8] Seidlhofer B. Key concepts in ELT: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ELT Journal,2005(4):339-341.
[9] Crystal,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2nd edi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3.
[10] Seidlhofer,B.Accommodation and the Idiom Principl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09(2):195-215.
[11] Nelson Cary & Lawrence Gossber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Spivak,G.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London:MacMillan,1988:271-313.
[12] 弋睿仙.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44-147.
[13] 黄碧蓉. 从南海地名演化看我国的海洋认知——及英国的海洋殖民意识[J].求索,2011(11):65-67.
OntheEnglishTranslationofNanhai
LI Shuang-m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Nanhai has been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since ancient time. Its naming is the result of how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world based on its geographical entity. Its naming is rich in and full of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ntiments. Hence,account should be taken into when it comes to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in combination with lingua franca,it is concluded that given that there is no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it is suggested that Pinyin should be employed in translation. Pinyin is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at it not only highlights our traditional culture,promotes discourse rights,but also provides English with rich source of etymology.
Nanhai English translation; lingua franca; pinyin; English etymology
H315.9
A
1009-9743(2017)04-0001-06
2017-06-16
李双梅,女,汉族,河南南阳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笔译。
201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生态翻译三维原则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编号:YB15-117)成果之一;2017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海南渔民《更路簿》地名命名与南海维权研究”(编号:17AZS017)成果之一。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7.04.001
张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