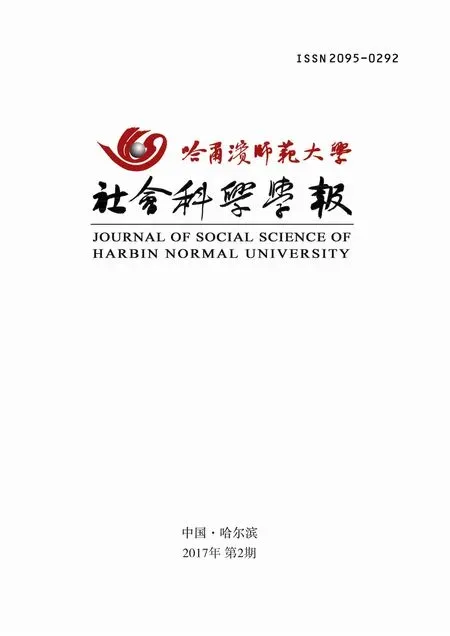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概念界定、时代内涵与体系构建
李敦东
(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概念界定、时代内涵与体系构建
李敦东
(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从跨文化交际转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相结合的高度,提出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概念,即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时代素养之一,其培养是我国外语教育的时代使命,对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本体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学有关理论,对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进行概念界定、内涵分析与体系构建,提出基于当代混合式教学理念的“知行合一”培养模式。
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传播能力
一、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出
教育之目的当为个体修养与国家利益之统一。就大学外语教育来讲,“其目标就要服从国家利益,从国家利益去考虑外语教学方针”[1](P6-15)。在全球化语境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出色的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已是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外语专业大学生必备的时代素养。他们的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状况如何?令人提忧。虽然学界二十多年前就已意识到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目的语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问题[2][3],顶层设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课程要求》(2004)指出要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重视英美及其他外国文化输入的同时也要适当融入中国文化的教学内容”。《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也明确要求“英语专业学生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提高对外介绍能力”。亦做出迅速调整,但实践层面严重滞后导致我国各层次各专业大学生都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症”[4][5],更谈不上中国文化传播能力。虽然目前少数高校已在本土文化导入共识上行动起来,但教学实践仍处于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初级阶段,或许在较大程度上是针对大规模外语测试而做出的调整,远谈不上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系统培养。究其原因在于外语教育界尚未对该素养及其培养问题进行系统思考。有鉴于此,笔者从跨文化交际教学和国家战略相结合的高度提出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这一时代性概念,结合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学有关理论,对与之有关的概念界定、内涵分析及体系建构等基础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外语教育时代使命之推进添薪鼓风。
二、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概念界定与时代内涵
心理学家将能力定义为“个体为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或任务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或素质”[6](P1)。传播学界将传播看作“个体/群体之间或相互之间通过使用相互理解的、有意义的符号传达预定意义的信息共享行为”[7](P54)。据此,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可初步界定为大学生为顺利完成通过使用相互理解的、有意义的符号向其他个体或群体传播中国文化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
然而,跨文化交际观念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以及信息化语境等既赋予它独特的域限,也是定位其时代内涵的坐标系。
第一,新的跨文化交际观念认为,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既包括异域文化输入吸收,也包括本土文化输出传播;其教学应在本土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平衡对比中,发展学习者健康的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8](P253)[9](P67-70)。因此,传播中国文化是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应有内涵,跨文化交际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第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党和政府在21世纪初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提出的国家战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做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大学生,尤其是外语专业大学生,既是目前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也是今后跨文化交际的最大潜在群体。他们毕业后可能会在国内外企业从事直接或间接的涉外工作,甚至出国留学、工作、旅游或定居,必然会与异域文化者发生种种联系。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必定是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多渠道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极。
第三,传播是基于通用符号系统的信息交流。语言,作为最方便高效的交流工具,必然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首选符号。其中,已获得国际通用语地位的英语自然是最佳选择。当然,以交际对象的母语或汉语作为信息通道在语境许可时亦无不可。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只是符号系统的一种,中国文化传播也应适时适当地综合运用图形、影像、声音等其他意义通道进行。
第四,信息化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时代际遇。信息化互联网带来的环境改变为跨文化交际及信息传播提供全球化社交平台,丰富它的步态、模态与形式,使其跨越面对面同步语言交流和书信异步交流的传统方式。中国文化传播活动在空间上可发生本土、异域或是基于互联网的跨国交流;在步态上既可同步也可异步;在模态上既可语言单模也可富媒体多模;在形式上既可以是个体或群体之间也可以是个体对群体。信息化语境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更丰富的载体和更多样化的方式。
第五,中国文化传播目标的实现与跨文化交际和传播的社会性、交互性特征密切相关。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有意施加影响的控制性行为[10](P57-66),必须以顺利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为前提,以得体适当的传播方式确保传播的恰当性和有效性。
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定义更新为: 大学生为顺利完成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以外语(尤其英语)为主其他符号为辅,多方式、多步态、多模态地向跨文化交际对象传播中国文化这一任务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或素质。
三、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体系构建
能力不是个体的某种单一特性,而是一系列心理品质或素质的有机综合[6](P1)。结合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学有关理论,本文认为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主要由以下六大系统构成:
(一)环境认知系统
中国文化传播的环境认知主要涉及:一是对物理环境的认知,如交际场所、时间、天气、声音环境等;二是对参与者性格特征的认知与判断,如自己喜欢交朋友、对方喜欢接受新事物等;三是对参与者社会身份的认知与判断,如教育背景、社交网络、经济条件等;四是对参与者实时情感、情绪、意愿状态及其动态变化的认知与判断。环境认知与判断是个体运用感知与理性、基于实时获取的信息、结合已有百科知识基础上做出的,它为传播主体做出与传播平台(跨文化交际)的构建与维持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过程的控制有关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二)心理行为调控系统
信息传播过程需要主体适时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做出动态调整,它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动机、情感/情绪调整、移情、心理调适等是该系统的关键要素。动机是一种为目标或对象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动力,它激发并引导个体调整并维持自我行为过程直至目标达成。中国文化传播动机,既是跨文化交际动机与民族文化传播动机的结合,也是外在动机(国家战略)与内在动机(个人意愿)的结合。
情绪和情感是个体基于愿望和需要的满足程度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在外部表现为表情、身体姿态、手势、语调等。积极乐观的情感和情绪促进交流,悲观消极的情感和情绪具有瓦解破坏作用。中国文化传播主体,一是在发展健康的跨文化意识基础上调整对异域文化的消极情感;二是根据环境认知对自己的内在情绪有效地动态调整。同时,使用语言或非语手段引导传播对象的情感和情绪朝着促进交际与传播的方向发展。在情感和情绪调整中,移情极其重要。作为“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以及分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11](P180),移情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它通过传播主体对传播对象感受与反应的关注、理解、求同和自我约束行为,促进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与亲密度发展,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良好的交际平台和情感语境。
心理调适能力既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12](P13-21),也是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要素。在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需要面对处于目标语文化语境时可能产生的疏离感、陌生感和言行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中国文化外语表达和传播出现失误甚至失败时的焦虑、难堪、挫败感等负面压力。此时,传播主体必须适时寻求其他系统的支持,及时调整交际与传播策略,尽快减轻或消除此类压力,保证交际与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技能策略系统
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技能策略系统包括跨文化交际与信息传播两个子系统,前者为后者的平台构建服务,后者支撑中国文化传播活动。跨文化交际技能需要交际主体:基于异域文化交际系统知识,顺利启动、维持与结束跨文化交际;有效遵守目标文化交际系统对交际的方式、途径、环境、话题内容、符号媒介、交际语用等规则方面的要求;同时,在目标文化交际规范系统内对交际各维度进行合理调整、控制和引导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向发展。跨文化交际策略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失误、障碍或目标无法达成时的补救措施和方法”[13](P1-47),它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相对的,达到完美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和交际能力缺陷等原因造成的交际失误和障碍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恰当的策略消除它,例如,语义关系、描述性表达等转述方法和语码转换、语言迁移等方法。
信息传播技能与策略是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核心,它要求传播主体在其他系统支持下,主动发现、引导交际对象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内容、恰当的传播方式、有效的符号组合和信息表征方式等及时满足对方需求或主动进行传播。另外,信息传播是一种具有控制性的社会活动,传播主体须特别注意信息传播的适当性,并能根据环境认知系统的实时信息对传播内容、方式、媒介、信息量等做出恰当调整。同样,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难免会因为种种原因(如文化冲突、外语表达不畅、知识缺乏等)遇到障碍或失误等情况。此时,传播主体应采用恰当策略及时解决问题。例如,内容失当可采用幽默化解、停止传播、转换话题等方法来解决;表达问题可寻求转述策略、符号转换等。
(四)信息表征系统
信息表征能力是传播主体使用能为传播对象所理解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进行意义表征的能力。信息表征既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首要环节,主要包括:
1.一般外语表达能力指使用外语进行普通信息表达的能力,主要包括与目标语有关的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语用能力(目标语文化的语用规则、语用理解等)和语篇能力(语篇衔接与连贯手段、组织风格等)等[12](P13-21)[13](P1-47)[14](P66-70)。
2.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是指传播主体使用交际对象的母语或交际共同语(如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要素的能力。单独罗列出来,一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不同于一般外语表达,而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曾有专家用“中国英语”指称此类表达;二是因为流畅的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绝非中国文化知识与外语能力简单相加,而是系统学习的结果。
然而,语言只是跨文化交际和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符号,人们还用许多其他符号和手段表征情感、传递信息。就交际活动来讲,眼神、手势、身势、微笑、面部表情、交际、距离、音量、空间使用等都是有效的信息表达方式[14](P66-70)。就中国文化来讲,图像、视频、音频,甚至身边实物等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五)跨文化意识系统
跨文化意识是个体基于对本土与异域文化充分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待双方文化的客观公正之态度,它是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国文化传播的思想准备。
文化知识,在类别上既包括本土文化,也包括异域文化;在时间上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代文化;在内容上既涉及政治、经济、科技、风俗、艺术、文学、宗教等一般维度,也涉及与交际/传播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则、准则、价值观、思维行为模式等内容。从联系角度看,既要了解二者的共性、相似性,也要理解二者的差异和冲突,还要了解两个国家之间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在认知层面确认世界文化的多样化性,进而在情感上认同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偏执,既不要唯异域文化优越论,也不要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要以开放的心态理解、接受与包容本土、异域文化及其差异[15](P128)。健康的跨文化意识,一方面,为传播主体提供交际行为上的启发,减少交际压力与不确定性,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良好平台;另一方面,引导主体灵活处理文化差异,在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方式及策略等方面做出恰当选择,有效防止跨文化冲突、降低传播对象的情感抵触。
(六)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信息化及网络技术既提供海量信息,也为跨文化交际和信息传播提供多样化的社交平台和技术手段。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应当具备以下能力:一是网络检索:通过各大网络搜索引擎及时获取中国文化知识及其地道的外语表达、各种模态的中国文化符号,可解决个体记忆与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社交平台与即时通信软件应用:熟练使用国际上流行的社交平台和即时通信软件,例如,Twitter、Skype、Wechat等。如此可超越传统面对面同步和文本书信异步交流的跨文化交际与信息传播方式,实现网络平台上多步态、多方式、多模态的跨文化交际与中国文化传播,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果。
上述系统构成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系统框架。环境认知系统提供信息支持,信息技术支持系统提供技术平台,跨文化意识系统提供思想引导,心理行为调控系统负责灵活应变,信息表征系统提供符号手段,技能策略系统保障行为合规运行。各系统相互作用构建出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
四、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转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双重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时代素养。它既是国家战略在个体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个体发展在国家民族层面上的内在要求。该能力需要大学生在顺畅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平台,以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和适宜的行为方式,积极主动地采用有效地传播策略,使用外语向跨文化交际对象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培养服务国家需要的外语人才是外语界义不容辞的使命”[16],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既是外语教育社会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它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基于目前跨文化交际教学已有成效,建议开设以中国文化外语表达与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课程。考虑到课时的有限性与文化知识的极大丰富性,基于当代混合式教学理念的、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知行合一”教学模式是极佳选择。首先,将以外语表达的中国文化知识和信息传播知识进行线上教学,为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奠定认知基础。其次,在线下课堂通过模拟训练和课外真实活动将线上所学与跨文化交际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让学习者在知识与技能的互动中不断提高中国文化传播能力。
[1]许国璋. 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78(2).
[2]王宗炎. 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J]. 外国语,1993(1).
[3]高一虹. 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
[4]从丛. “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 光明日报,2000-10-19(C01).
[5]宋伊雯,肖龙福. 大学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现状调查[J]. 中国外语,2009(6).
[6]David Matsumoto.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M]. CUP,2009.
[7]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2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Samovar A. Larry 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9]袁芳. 试析外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地位与作用[J]. 外语教学,2006(5).
[10]王怡红. 西方传播能力研究初探[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
[11]David Matsumoto.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2]杨盈,庄恩平. 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J].外语界,2007(4).
[13]Canale, M.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1980 (1).
[14]毕继万. 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中国外语,2005(1).
[15]Risager K. Language and culture pedagogy: from a national to a transnational paradigm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2007.
[16]戴曼纯. 培养国家需要的外语人才[N]. 光明日报,2016-10-16.
[责任编辑 孙 葳]
Undergraduates’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Ability: Definition, Contextual Connotation and System Structure
LI Dun-dong
(Zhou Youguang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The concept of Undergraduates’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Ability (UCCA) is put forward against the current context of a new concep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ational project of “Communic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his papers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UCCA, then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 and system structure,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a Blended-learning-based instruction model of “Combining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UCCA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contemporary undergraduates, and that its cul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at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f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CCA; communic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2017-01-06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大学生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研究——以江苏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为例”(D/2015/01/31)
李敦东,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二语教学。
G20
A
2095-0292(2017)02-01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