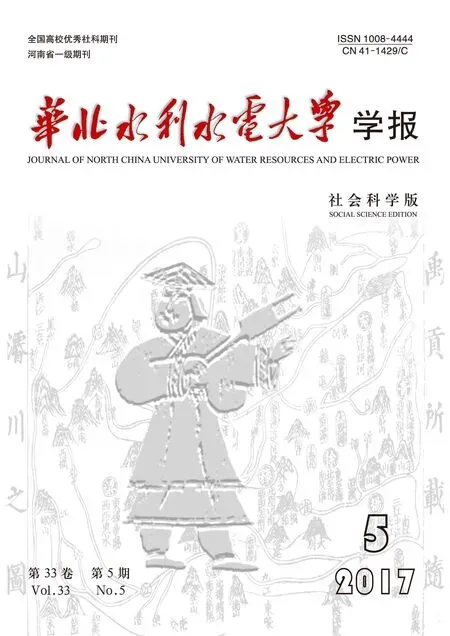清末养民思想文献研究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末养民思想文献研究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目前,学术界对清末养民思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兴农养民作为古代养民思想的沿承,在清末仍然存在,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清末养民重在救贫而非富民,从这个层面上则反映出清末社会的凋敝、民生的艰辛。设厂养民是清末养民思想的亮点,民间与政府对设厂养民主张,达成了共识,这都与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及西方科技的影响有关。
养民思想;清末;经济视角
养民思想的概念在我国古代十分丰富,到了近代,又衍生出了新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对近代养民思想研究中,最集中体现的就是雷晓彤之文《富国养民为第一义——略论〈万国公报〉对西方经济的介绍》[1],其它则多为有限的触及,总体上显得颇为欠缺,需要强化和深入。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为视域,以经济为视角,以养民思想为视点,梳理脉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兴农养民——古代养民思想的沿承
我国古代注重养民,如《政在养民》所道:“《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字最妙。”[2]32到了晚清,养民依然是重中之重。如上谕称:“从来求治之道,养民为先。”[3]地方告示亦曰:“安民之道,首重养民。”[4]在民间,也有相同的认识。如时论指出:“救荒无及也,而在备荒;戡乱无及也,而在弭乱。备荒、弭乱无长策也,而在养民。”[5]需要强调的是,从古代到近代,朝廷与社会沿承下来的不仅是普通的养民思想,还有其兴农养民思想。
兴农养民思想与实践,在古代早已有之,且有相当发展。如黄六鸿所著《养民四政》提出四点主张:“一曰兴水利,二曰垦荒田,三曰植果木,四曰种桑榆”[6]704-706,全是围绕着兴农而言。到了清末,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沿承。
1897年,《知新报》登载了文廷式的奏折[7]。在折中文廷式认为:“窃维国家之设官,以为民也,然数千年来,于理财之道,但谋所以取民,而不谋所以养民,使各尽其一手一足之烈(力),而国家从而征之税之,于是乎大利不兴,众力不集,民几不能自养,而国家亦因而患贫。”[8]698-700解决之道就是兴农:“中国从古重农,自应以农事为急,而农政之要,则以开渠种树为先。应请旨明谕天下,各就本省可开之水道,固有之利源,董劝民间,妥筹兴办,民力不足,官助其成,不得故事奉行,亦不得藉端苛扰。唐人讲水利,元代重农政,史书具在,成效昭然,至中国现有四大利,可以致富强者。一曰蚕桑之利,二曰棉花纺织之利,三曰葡萄酿酒之利,四曰畜牧之利。以上四事,本皆中国旧法,虽参用机器,兼资人工,可养无数贫民,即可销无穷隐患,既为闾阎广生计,更为国家增税厘。”[8]698-700文廷式所举的养民方法的几个例子,不外经济作物种植及畜牧等内容。
1905年,《江西官报》载文《讲种树之利》,提出种树是养民之法。“树之用大矣!造屋造舟车,造桥梁及一切器具,惟木是赖。以天地自然发生之理,而可以人力种之,种之占地甚少,费时甚暂,施力甚薄,耗资甚微,而获利甚大。近可为及身之谋,远可为子孙之计,且可以养身体,可以豁胸襟,可以蔽雨日,可以祛水旱,失此不图,愚亦甚矣!”[9]该文作者胡维贤竭力倡导的种树主张,类同于文廷式。
胡维贤另著文《讲养畜之利》。他说:“养畜之利,吾民尽知之矣!马牛以服役,羊豕以供餐,鸡骛以佐馔,亦何待我之多言哉?虽然知其利而未尽其利也。生殖不蕃,配合未得其道也,瘟疫时闻,饲养未得其法也。无专家以考其业,无广畜以溥其利,则虽无人无日不目击之,口啖之,而其孳乳习性若何,知者实鲜,坐使有生活力之动物,未能发达。上既无官地发种之令,下未有私家试验之场,此牧业之所以衰,吾民之所以贫也。不然,陶朱之富,讵外是哉?况乐邑山场之多,五谷之贱,游人之众,苟精其一,亦可于旧业之外,辟一新机,各业之中,树一专利也。”[10]胡维贤列出了发展畜牧业的十类动物:牛、马、绵羊、山羊、猪、兔、鸡、鸭、蜂、鱼,这也涵盖了文廷式兴农的主张。
1910年,《尚贤堂晨鸡录》所载文《养民篇》,提出养民之道“宜劝垦牧”。“垦牧之利,曰地产,曰物产。地产则桑麻谷果之类,随处可以种植;物产则牛羊鸡彘之类,随时可以蕃息。”[5]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这些都属于农业。
总体来看,兴农养民作为古代养民思想的沿承,在清末时期仍然存在,并得到了朝廷与社会一致的重视。
二、救助贫民——清末养民思想的重中之重
自古以来,直到清末,朝廷的经济主体主要是“维生经济”的形态[11]。这种形态的经济更多时候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所以,养民主要是救助饥民,而非富民。虽然其间也不时有富民的声音,如前清余廷灿撰《富民》[12]979-980一文,1898年《万国公报》上刊登《富民策》[13]等;但前者只是强调重“常平社仓”,重谷不重金钱,后者仅翻译国外文章而已。
救助贫民确实是清末养民思想的重中之重。1898年,《万国公报》载《政在养民》一文,报导的上谕主题就是“办仓谷”。“上谕,御史韩培森奏请筹办仓谷一折。积谷为民食攸关,遇有偏灾,藉资补救,乃各地方官,往往不以民事为重,以致所设仓廩,半属有名无实,如逢前后任接代,恒以银钱抵交,期于简便,一遇荒歉,辄请开放赈款,留截漕粮,复图中饱,毫无实惠。此风亟应禁革,著各督抚,严饬各府州县,凡有仓谷,务当认真筹办,实储在仓,其有以银钱列抵交代者,勒限一律买补,以备缓急,不得阳奉阴违,虚应故事,钦此。”[14]上谕要求认真筹办仓谷,不许以钱抵充,这一养民方式目的在于荒歉救饥,决非富民。
1899年,《申报》载文《中国宜留意养民之政说》,指出了水旱灾害发生后开设粥厂难以为继的窘状。“谓天生民而立之君,建以百官有司,所以为民也,衣服、饮食之琐屑,凡愚民所不能谋者,必得在上者为之代谋。庶藉日康而民日阜,倘平日不能为之广生财之路,但煦煦焉,孑孑焉从事于施赈,是犹为父母者不使子孙各习一业,致其筋骸手足日就怠惰,无复能自树立,然后日啖以糠籸,谓如此已足尽慈爱之道,恐为子者未必得果腹之乐,而为父母已不免左支右绌矣!由此言之,施赈之说即能持久,犹不足恃,而况未必能持久耶?”[15]接着文章提出了解决之道:“然则为今之道奈何?曰以工代赈之法,本为前代之美政,今中国芦汉、粤汉等处铁路,次第肇兴,用人必广,彼数十万哀鸿,大半皆在壮年,有力可用,倘得驯之作工。既可免夫饥寒,又可有所管束,其无铁路之处或筑石路,或筑木路,苟能次第成之,往来既便,商务必有裨益。至若垦荒之说,亦可推广,中国地狭人稠,可耕之处虽属寥寥,而南洋各岛地脉肥厚,颇便树艺,倘得中国政府与各国钦使明订约章,凡华民之往彼耕地作工者,当一律相待,不可偏苛,如此则中国之人往者必多,不啻于中国之外又开一中国,是亦安置闲民之一术也。”[15]无论是以工代赈,还是移民海外,这都是救济贫民。
为救助贫民,清政府还设立有专门的机构——留养局。如《抚教留养局章程》规定:“此举专为无家幼孩流离道路,或遭迷拐出境起见,特设留养局,暂为安顿,以便招属认领,凡有家可归及年逾十四已有知识、业经受赈可以自赡者,一概不收。”[16]并规定:“凡无着幼孩,准由邻右地保开明姓名、年纪、父名母氏、向依何处等由,于八月以前送留养局核实收养,其或父殁母存、孤贫乏食,亦准送局抚养,共以千名为额,就中选择可造之才,随时拨入抚教局。”[16]1906年,“皖省各属被水为灾,贫家童孩往往售于富户,母子离散,情实可怜,现经散赈人员报由安徽官义赈抚局,饬被灾各州县设立留养幼孩局,暂将饥民子女收养,一俟麦熟即行赴局认领,已报明抚宪查核矣”[17]。
留养局之外,清末还设有庇寒所,留养难民[18]。
政府之外,民间社会力量所倡导的养民主旨也是救助贫民。如1910年《北洋官报》报导,“奉天锦西庙朝阳府交界之地,僻处边门,居民生计素拙,壮者、少者多羼入匪类,老者、弱者则填于沟壑。附近该处绅士近议立一慈安院收养贫独,拟定章程,不动官款……”[19]同年,上海还有士绅呈文两江总督:“拟仿东西各国成规,在上海集资建设贫儿院,并附设孤童感化所,专收贫寒子女及流落乞儿,教授粗浅小学兼各种工艺,免致失所成为废物。”[20]社会力量介入贫民救助,反映了救助贫民作为养民思想的核心已经深入民间。
总而言之,清末养民重在救贫而非富民,从这一个层面上可看出清末社会有多么凋敝、民生的艰辛有多么深重!这也看出了不同社会养民侧重点的差异,成为一个社会发展走向的晴雨表与风向标。
三、设厂养民——清末养民思想的亮点
清末养民思想中,以设厂养民主张最为引人注目。有论者所称之“机器养民”[21]129-137,不如设厂养民主张涵盖的更为全面。
较早提出设厂养民主张的是薛福成、康有为、陈炽等。1892年薛福成著文《用机器殖财养民说》指出:“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22]681-682“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22]681-682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提出:“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23]89-94同时期陈炽也认为:“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24]239其中既有机器养民主张,亦有对设厂养民的倡导。设厂养民思想,包含有机器养民的内容。
早期改良思想家的首倡,起到了引领作用。
1898年,《无锡白话报》载文《养民新法》,提出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的主张。“从前西洋造各样物件,都是用人工做的,现在都用了机器,不用人工了。因为人工做得慢,不及机器做得快,这机器比人工快几倍呢!”[25]
同年,《知新报》上刊载刘桢麟之文,力主“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26]。作者指出,“凡一国之盛衰强弱,必视其人生利与分利者之多寡以为比例差”[26],而善堂传统的济民方式“有补于一时,而无补于将来”[26]。因此,“以吾粤一省善堂之多几于百数,其大者储款十数万,小亦数万或数千,诚移其款以作工厂,或以一堂之力而开之,或合数堂之力而开之,于省会繁盛之区设大厂,于乡邑僻远之地设分厂,因其近地之工宜,顺其人事之所习,分类建立,凡近厂所有无业之民,分别男女,区划长幼,皆使报名投厂,择技以授,吾尝总计其利,盖有十二”[26]。
1910年,《尚贤堂晨鸡录》“论著门”专栏刊登《养民篇》一文,认为养民应兴工艺。“今策养民,一宜兴工艺,品不必贵重,适于造作者是;物不必精美,切于日用者是。此为始基而言,适造作则易学习,切日用则易销售。”[5]
设厂养民不仅在民间反响连连,政界亦不乏认同的声音。
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济南府南门外,创设养育学堂一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手技,俾资糊口,甚得欧西养民之法云”[27]。
1904年,广西巡抚柯逢时奏请试办工厂以养游民而兴实业。他认为:“夫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商之所资以转运,其源实出于工。广西河流险阻,铁道未通,如仿东南各省之制造厂,购置机器,动费百十万两,其势有所不能,惟有就本地所出,为民间所必需者,专恃人工造作,而必求其精则器以售,而维新事以轻而易举。”[28]“总期本地多一制造,即开一利源,民间添一工师,即少一游手于乐事,劝功之中,即实化暴为良之意。”[28]
1905年,陕西省藩司樊增祥在批文中针对留养局强调:“留养贫民,名为作好事,实吾中国之秕政也。有民而不令其各自谋生,长此设局以养之,是教民惰也。”[29]并且认为:“拟就该局现有之款,稍为扩充,将省城贫民、罪犯分别鸠集,俾习粗浅手艺,仰西安府尹守督同两县妥定简易章程,克期兴办,俟省城办好再行推及外府州县一律办理,以符部章而开民智。定章以后,即将留养局改为习艺所,局中委员绅士酌量撤换,从前不实不尽之处,姑免深究,倘因失此利薮,造作浮言,阻挠新政,则二罪俱发,定予重惩不贷。”[29]
1910年御史萧丙炎上奏指出:“治民之要,端在养民,请饬通设习艺工厂,以裕生计。”[30]
由上可见,民间与政府对设厂养民主张,达成了共识。之所以如此,与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及西方影响有关。学术界在论述近代工厂发展历程时,往往习惯于从工业化角度立意,从而忽略了养民思想。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兴农养民是对古代养民思想的沿承,救助贫民是清末养民思想的重中之重,设厂养民是清末养民思想的亮点。
[1] 雷晓彤.富国养民为第一义:略论《万国公报》对西方经济的介绍[J].湘潮,2008(9):79-80.
[2] 袁栋.书隐丛说:卷3[M].清乾隆刻本.
[3] 上谕[J].大同报,1907,7(24):25-27.
[4] 保定工巡总局告示[J].北洋官报,1907(1476):9.
[5] 养民篇[J].尚贤堂晨鸡录,1910(3):8-9.
[6]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第28卷[M].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7] 文廷式.养民要折[J].知新报,1897(3):4-5;1987(4):4-5.
[8] 文廷式.条陈养民事宜疏[M]//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第35卷.清光绪石印本.
[9] 胡维贤.劝民说九:讲种树之利(附树种植期养法禁约)[J].江西官报,1905(30):36-39.
[10] 胡维贤.劝民说十二:讲养畜之利[J].江西官报,1905(33):40-49.
[11] 苏全有.共生机制与我国宗族制度的长期延续[J].焦作大学学报,2010(4):17-19.
[12] 余廷灿.富民[M]//贺长龄.清经世文编:第39卷.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13] 富民策[J].万国公报,1898(114):21-25.
[14] 中朝新政:政在养民[J].万国公报,1898(116):39-40.
[15] 中国宜留意养民之政说[N].申报,1899-01-8(1).
[16] 抚教留养局章程[N].申报,1877-11-27(3-4).
[17] 设立留养局[N].申报,1907-03-25(10).
[18] 又批德惠县申覆县属难民于庇寒所暂时留养各情形文[J].吉林官报,1911(9):66.
[19] 恤养边民之善举:录东三省日报[J].北洋官报,1910(2402):11.
[20] 呈两江总督禀[J].上海贫儿院月报,1910(1):3.
[21] 徐培华.市场经济的义利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2] 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M]//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第34卷.清光绪石印本.
[2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M]//姜义华,吴根梁.康有为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4] 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5] 养民新法[J].无锡白话报,1898(2):2-3.
[26] 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J].知新报,1898(57):1-3.
[27] 工艺养民[J].湖北商务报,1901(67):7.
[28] 柯逢时.桂抚柯奏试办工厂以养游民而兴实业折[J].秦中官报,1904(39):17-18.
[29] 樊增祥.藩司樊批咸长两县造报留养局三十年全年分贫民数目淸册[J].秦中官报,1905(5):5-6.
[30] 萧丙炎.交旨(三月十三日)[J].政治官报,1910(890):2.
LiteratureResearchontheThoughtofSupportingthePeopleintheLateQingDynasty
SU Quanyo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The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supporting the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not enough. Supporting the people by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s the ancient culture, still exis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get some atten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supporting the people focused on saving the poor rather than enriching the people. Setting up factories to support the people is the highlight, and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rise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pporting the peopl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2017-06-09
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K257
A
1008—4444(2017)05—0154—04
(责任编辑: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