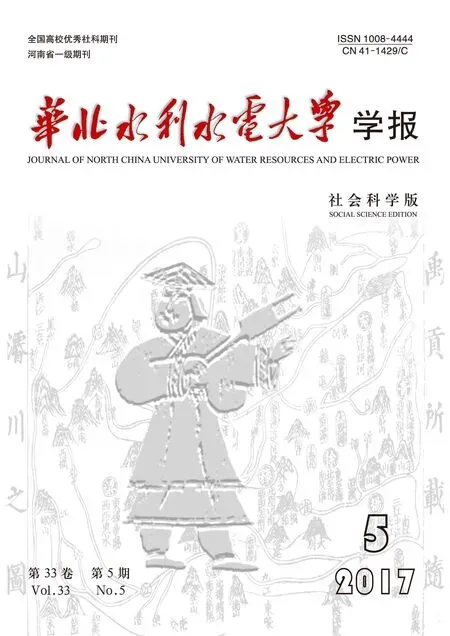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和适用
臧蒙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 纪检监察处,湖北 武汉 430081)
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和适用
臧蒙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 纪检监察处,湖北 武汉 430081)
携带具有可以随时使用的特点,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形来理解携带行为;对凶器的理解应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凶器的范围进行限定性解释;正确处理携带凶器盗窃和其他盗窃方式的关系。
携带行为;凶器的范围;其他盗窃方式
一、携带凶器盗窃独立入罪的立法背景
携带凶器盗窃之所以独立入罪,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有直接危及被害人人身安全的现实可能性,由此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更大[1]266。与一般的盗窃行为相比,携带凶器盗窃体现了行为人更大的主观恶性。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被发现后,为逃避抓捕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入室盗窃时由于行为场所具有隐蔽性,携带凶器盗窃对被害人的人身威胁更为严重,携带凶器盗窃演变成为暴力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大。
其次,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不包括对被害人人身安全的侵犯,对被害人有较大威胁的盗窃行为是盗窃罪所不允许的。所以,刑法应该加大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依据我国修订前的刑法规定,携带凶器盗窃要构成犯罪也必须符合盗窃罪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要求,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携带凶器盗窃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对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明显不足。
最后,同为携带凶器类型犯罪,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对于携带凶器抢夺的,直接转化为抢劫罪。刑法这一条文的规定,充分考虑到携带凶器型犯罪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和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体现了刑法加大对携带凶器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于携带凶器盗窃,有学者指出,携带凶器行窃之所以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条件,是因为其潜藏的危险性较高。赤手空拳行窃,遇追捕,对事主与他人的伤害有限;持械行窃则不同,危害扩大的可能性提高了[2]295。把携带凶器盗窃独立入罪能够更客观地体现其社会危害性,有利于对此种犯罪行为的打击。同时,有鉴于携带凶器的盗窃随时可能转化成抢劫或者伤害甚至杀人行为,对其加重处罚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人身安全的特殊保护,其立法理由也是充足的[3]1758。
二、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
(一)携带行为的理解
从携带的具体形式上看,可以将携带行为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凶器外露型携带,即行为人直接将凶器显露于外;二是暗示凶器型携带,即指行为人虽没有将凶器外露,但却向受害人或其他人暗示凶器的存在;三是隐匿凶器型携带,即行为人隐匿凶器,将凶器置于受害人或其他人无法发觉的身体位置或随身行李之中[4]175。携带凶器盗窃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示或者暗示凶器的存在,隐匿凶器型携带属于典型的携带行为。对于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明示、暗示凶器是否属于携带凶器盗窃,应该结合案件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形,行为人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盗窃,且主观上没有借助凶器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的意图,其明示凶器的行为也未被被害人察觉。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明示凶器只表明一种客观危险状态,在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过程中,所携带的凶器并未发挥作用。这种明示凶器行为与隐匿凶器型携带所起到的作用一致,应当属于携带凶器盗窃。与此同时,如果行为人携带凶器并且凶器处于外露状态,且受害人已有所认识,但是行为人认为受害人并未认识到而实施的盗窃行为,该情形的判断实际上是认识错误的问题,对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可以阻却行为人的抢劫故意[4]175-176。
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盗窃,主观上有借助凶器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意图,即在被害人发现盗窃行为时,行为人希望通过明示或者暗示其所携带的凶器,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以完成盗窃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被害人一直没有发现盗窃行为,那么行为人携带的凶器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应该属于携带凶器盗窃。但是,如果行为人发现盗窃行为后,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明示或者暗示其携带凶器,使得被害人产生精神强制而不敢反抗的,主客观上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构成抢劫罪。
第三种情形,盗窃行为虽然通常具有秘密性,但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现象,所以,国外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不要求秘密窃取,事实上完全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况[5]727。在公开盗窃的场合,行为人如果在盗窃的过程中向被害人明示或者暗示其携带凶器,并且对被害人产生了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而窃取财物的,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抢劫罪定罪处罚。
从携带的定义上来看,携带是指在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5]720。例如手里拿的物品、放在随身衣物或包中的物品,都属于携带行为。携带要求将物品带在身边,具有可以随时使用的特点。携带的基本特点是随身性。而持有的定义是指,持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行为人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持有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对特定物品的占有、收藏、控制、保管等方式,但是并不要求行为人将特定物品随身携带[6]。可见,持有强调的是对物品的可支配性,并且不要求随身携带。
(二)对凶器的理解
在司法实践中对凶器的理解应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凶器的范围进行限定性解释。在主观方面,无论任何器具或工具只要被人用于行凶伤人、杀人就成为作案的凶器[7]1039。在客观方面,要求该器械对人身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具体而言,可以将凶器分为两类。
第一类凶器是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禁止私人违法携带上述器械,这类器械不属于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范畴,且具有较大的杀伤力,使用不慎会对公共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法律禁止个人携带这种类型器械,凶器认定过程中主客观因素都较为明显,在司法实践中易于作出判断。
第二类凶器是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器械,例如菜刀、锤子、铁管等,这类器械被称为用法上的凶器。由于这类器械不属于国家法律禁止私人携带的器械,并且其与人们的生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于如何认定这类器械,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判断。
对于第一种情况,当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实际使用了所携带的器械,且携带的器械本身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无疑属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但此时也应该注意区分凶器和杀伤力较小的作案工具。由于盗窃行为有时需要携带一定的作案工具,有的作案工具杀伤力较小,从一般社会的观念上来看这些物品就是专供作案所使用的,所以一般带有镊子、刀片等物品进行扒窃的,该物品不应该被认定为凶器。
对于第二种情况,即只随身携带但实际没有显示、使用该器械的,主客观判断较为复杂。在主观方面,要结合案件情况、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进行判断。在客观方面,判断器械是否具有杀伤力应该采用社会一般人的观念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的判断。在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使用携带器械的主观意图时,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以携带凶器盗窃进行认定。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携带凶器盗窃并不要求行为人实际使用凶器,处罚携带凶器盗窃的目的是惩处其潜在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在携带凶器盗窃时,行为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凶器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转化为抢劫罪。
(三)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比较
我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携带凶器抢夺直接转化为抢劫罪。但是同为携带凶器型犯罪,携带凶器盗窃的依然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之间的区别,是值得进行探讨的。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携带凶器型犯罪,都成为了刑罚加重处罚的根据,表明携带凶器类型的犯罪行为较一般的犯罪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两者的不同点是,携带凶器盗窃仍然在盗窃罪的范围内进行定罪处罚,而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法律拟制,直接按照抢劫罪进行处理,显然携带凶器抢夺的处罚要重于携带凶器盗窃。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抢夺行为是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夺行为与被害人的人身直接接触,在抢夺的过程中往往会遭到被害人的反抗,同时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往往具有抢夺不成就直接进行抢劫的主观故意,故行为人使用凶器的盖然性很大,对被害人的人身威胁也很大,携带凶器抢夺具有很多与抢劫行为相类似的因素,同时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罪的行为,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8]。所以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是合理的。相对于携带凶器抢夺而言,携带凶器盗窃一般是秘密进行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小,行为人在盗窃的过程中使用凶器的盖然性要远远低于抢夺罪,对被害人的人身威胁也要明显小于携带凶器抢夺。对携带凶器盗窃规定构成盗窃罪已经扩大了其处罚范围,是对其社会危害性的正确考量。
三、携带凶器盗窃和其他盗窃方式的关系
从法条规定上看,“携带凶器盗窃”和“数额较大”“入户盗窃”“扒窃”是并列的关系,因此,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只要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用考虑其获取财物数额或者盗窃次数,一律都按盗窃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理由如下:我国刑法在对犯罪的认定上总体采取的是“定性 + 定量” 的模式,并且根据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对分则具体罪名的认定上应该坚持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原则的指导。对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来说,由于在刑法中并没有规定该行为构成盗窃罪具体量的要求,按照刑法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入户盗窃构成盗窃罪应该受到刑法第13条的限制。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不符合数额或者次数要求的携带凶器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应该结合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具体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分析判断。对于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规定,应该认为不构成盗窃罪 。例如,对于携带凶器准备进行盗窃,但在实施盗窃行为之前就被抓获的,不属于携带凶器盗窃的情形,不能按照盗窃罪进行处罚。
同时,在携带凶器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扒窃的情况下,可以将携带凶器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进行考虑,分别比照入户盗窃和扒窃行为进行加重处罚,并且,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考量,携带凶器入户盗窃比携带凶器扒窃的危害性更大,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携带凶器入户盗窃在处罚上应该重于携带凶器扒窃。
[1] 张军.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2] 林东茂.刑法综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朱孝清,莫洪宪,黄京平.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4] 高巍.盗窃罪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5]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 陈正云,李泽龙.持有行为: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样态[J].法学,1993(5):17-19.
[7]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8] 张明楷.盗窃罪的新课题[J].政治与法律,2011 (8):2-13.
UnderstandingandApplicationofTheftwithLethalWeapon
ZANG Meng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y Bureau South Bureau, Wuhan 430035, China)
Carry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it can be used any time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o understand portability. Giving a limited explan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lethal weap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thal weapon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sisten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ft with lethal weapon and other forms of theft should be correctly handled.
carrying; the scope of lethal weapon; other forms of theft
2017-04-09
臧蒙(1985—),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纪检监察处经济师,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D914
A
1008—4444(2017)05—0104—03
(责任编辑:袁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