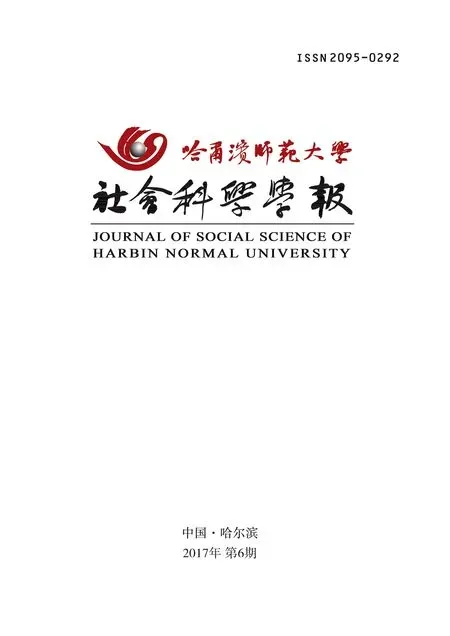清代东北流人文化的传播意义研究
蒋 爽
(沈阳音乐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辽宁 沈阳 110004)
清代流人是清代文化史上一支特殊的队伍,这一群体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以戴罪之身远离家乡和故土,来到东北这片当时被称为蛮荒苦寒之地的塞外,开始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流放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即便他们面对秋风冷雨、寒霜刀剑,却依然书写出大量有意义的诗文、地方志,与此同时,他们在当地办学结社,开启了清代东北文化的新篇章。
一、研究背景
“流”作为中国历史上五刑之一,萌芽于先秦,历经多个朝代,发展到清,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即波及人数更多,流放时间更长,流人生活条件更为艰苦。以往朝代的流放地遍布全国,多集中在南方,到了清代,流放区域开始由南向北移动,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新疆两地。东北因其为满族文化的发源地,长白山脉更被誉为满族龙脉所在,因此清政府更倾向于将流放之人置于此地,据李兴盛先生《东北流人史》考证,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被流放至东北者便不下十余万众,史称“东北流人”。这些流人的身份比较复杂,其中虽然不乏危害社会治安的罪徒,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名士,有反抗清朝统治的普通百姓,更有政绩卓著却蒙冤受屈的官绅。一些人在流放前就已经声名显赫,因此他们被流放之后的这段历史往往备受关注。就当时来说,东北地区常常被称为“蛮荒苦寒”之地,因此流人的流放之行也就成为令人恐怖的“畏途”。不少“衣絮单薄,无以御寒”的贫苦流人“冻毙于路”,不得生还。而能侥幸到达戍所者,更因“既无屋栖身,又无资力耕种,复重困于差徭”,而在“苦寒之地,风气凛冽”之中颠沛流离。
当时东北地区的流放地主要有盛京(今沈阳)、尚阳堡(旧址在今辽宁开原县东清河水库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南爱辉乡),被流放的人群中,有案可查的文人名士官绅,多达数百位,包括陈梦雷、张光藻、刘凤诰、函可、吴兆骞、方拱乾、方孝标、方式济、张缙彦、徐灿、董国祥、郝浴、李呈祥、顾永年等。值得欣慰的是,他们被流放后,在困厄的环境中,依然不忘治学,不废吟咏,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康熙时期著名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充分说明了清代东北流人数量之多,身份之特殊。众多名士从江南来到塞北,开始了他们这段辛酸的人生之旅。
尽管流人流放的背景各不相同,原来的思想志趣互异,但壮志难酬,万里流徙,历尽坎坷的遭遇却是共同的,因此表现出相似的文化认知和体悟,因而形成东北流人独特的文化品格,这些品格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又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流人的生活遭遇,反映了东北地区的山川物象、风土人情、历史沿革,以及清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抗俄斗争等方面情况,关于全国性的大事件在清代东北流人诗文中多有记载,比如诗人吴兆骞有多处赠诗涉及的是17世纪的中国抗俄斗争,函可的诗歌则多处涉及当时辽北地区的宗教文化活动,这些诗文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流人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活动,构成了光波滟漾的清初历史画卷,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具有以诗存史、以文证史之用。与此同时,一些流人到达当地后,对所处地区的文化教育起到开蒙作用,如流人郝浴在铁岭建书院,周恩来少年时曾于此地读书,银冈书院的威名至今依然在北国熠熠生辉。
流人或赋诗、或撰志、或授徒、或结社,与当地人的文化交往非常频繁。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到这里,遣返后的流人又将北国文化带入江南,这种南北互动交流,加强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特殊意义。
二、东北流人文化活动构成
第一,创作诗文。据张玉兴先生《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和严志雄先生点校的《千山诗集》中记载,东北流人共创作了近万首诗,仅函可一人便创作诗歌1500多首,在流人吴兆骞的《秋笳集》中,共存录诗歌700余首,其中,500余首都是他遣戍宁古塔期间创作的。流人方拱乾乃桐城望族方氏之后,家学渊源,方拱乾7岁“能属诗文”,20岁时诗文已为世人所称许,被流放宁古塔后“无一日辍吟咏”,创作了大量异地史诗。其他诗人如钱威、方孝标、方膏茂、杨越、祁班孙、张贲、陈志纪等也都有诗歌留存。在张玉兴先生的著作当中,共收录了48位作家。这48位作家在东北地区的经历都有据可考,他们创作的诗歌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歌颂了东北大好河山,记载了当时流人真实生活史。如流人函可在诗歌中直言不讳地揭露清廷对人民的榨取:“画阁已空搜白屋,小民欲尽索穷儒。”抨击清朝的文字狱是“四海皆秦坑,诗书同一炬”。谴责清兵的大屠杀:“叹息人间劫尽灰,惠州天上亦荒莱。”面对黑暗的现实他悲愤地慨叹:“举世令人闷。”揭露、抨击可谓淋漓尽致。在流人诗家中敢于接触实际的并非只有函可一人,蔡础云:“饥饿霜爪摧雀丛,翡翠凋零金蝉空”,这是控诉官府的残民以逞。郝浴更直接讽咏了清廷在近畿一带推行“圈地令”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近闻如柴骨,高挂枯林间”[1](P13)。函可《老僧》一诗则描写了一位近九十岁的老僧的遭遇。他远为躲避后金的残酷压榨而遁入空门,二十年后,他返归故里探视,却只见“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家乡已面目全非。虽然他性命犹存,可是“凄凄恨孤独”,无限伤心的凄凉寂寞之感袭击着他。这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清初东北经过明清之际战乱之后,社会凋敝的残败景象[1](P13)。而“一度边关即鬼门”一句更是真实再现了东北流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东北流人诗文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包括一些台湾学者,如严志雄教授先后发表了《函可流放诗中的鸟兽》《流放、帝国与他者——方拱乾、方孝标父子诗中的高丽》等论文,他在《吴兆骞流放初期的创伤记忆与文学、宗教的追求》一文中指出:“流放是时间、空间、身份、文化的多重断裂,而记忆是流人赖以维持自我完整、统一感的重要心理、精神机制。”该论断道破了文学创作是流人维系其流放生命的依托,是其流放生涯中重要的生存方式。2013年,该论文被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收录于《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中,该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只收录包括葛晓音、蒋寅、陈尚君、赵昌平、张宏生在内的国内一流学者的论文,严志雄教授从流人诗的角度谈文学被入选其中,足见东北流人诗文的学术价值之高。
第二,编撰地方志。其中,《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笔陈梦雷流奉期间,先后编撰了《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著名流人董国祥在流放期间编撰了《铁岭县志》、方拱乾编撰了《宁古塔志》、张缙彦编撰了《宁古塔山水记》、吴兆骞之子吴桭臣编撰了《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编撰了《龙沙纪略》、杨宾编撰了《柳边纪略》,这些地方志及一些纪略的撰写,形成流人文化独有的特色,即以志补史,以纪记史。吴桭臣《宁古塔纪略》中记载,宁古塔东门外“摈林玫瑰,一望无际。五月问玫瑰始开,香闻数里。予家来为玫瑰榴,土人奇而珍之”[2]。显然这里记录了当时东北地区玫瑰摄制法的传播过程,真实地再现了当地人勤劳朴实、展示了东北人们豁达智慧的人生态度。此外,这部纪略还从多个侧面详细地叙述了宁古塔地区的山川风物、物产贸易、住宅服饰、风俗习惯等,是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宁古塔地区历史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东北文化史、东北风俗发展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兴办教育。流人郝浴被流放到铁岭后,在当地创建了银冈书院,当年的银冈书院有关东第一书院之美称,是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周恩来少年时曾在此就读。而今,银冈书院已经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基地,成为我们研究东北教育发展史的重要依据,目前该书院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后人瞻仰,郝浴兴办教育的壮举也被当地人历代传颂。流人吴兆骞被流放到宁古塔后,先是教授宁古塔将军巴海之子,后又于此地建学堂,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生。东北流人被流放后,并没有怨天尤人,无所作为,而是力所能及地将自己所知所学带入东北,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到北国,开启了东北封禁文化教育的序幕,这些历史会永远为东北人民所铭记,他们对当地文化繁荣做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被载入史册。
第四,结社集会。流人函可与左懋泰等人在沈阳组织“冰天诗社”,参加者达三十三人。流人张缙彦、吴兆骞等在宁古塔组织“七子之会”,当时吴兆骞评价另一位流放诗人钱威和杨越时说:“钱德维议论雄肆,诗格苍老;杨友声诗甚清丽”,可见,流人当时的结社非常频繁,他们的这种文学团体性活动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与当地人集会,并将写作的诗文赠给当地人,沟通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传播宗教文化。流人函可被誉为“千山诗僧”,正是因为他被流放到盛京后,将佛教理念带入这里,此后,他又来到海城金塔寺作为住持,继续创作和文化传播活动,后因其身体多病,被移锡千山双峰寺。函可生前广收门徒,当地很多人都在他的带领下加入佛教组织,辽北地区一时间成为清代东三省佛教文化中心。而今,沈阳、海城、鞍山等地依然保留了函可当年的遗迹,函可为东北宗教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东北流人文化的传播意义
东北流人文化作为东北地域文化的分支,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东北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数万东北流人由南到北的拓疆,对近代东北文化的启蒙和开化做出特殊贡献,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广泛地传播东北流人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不忘历史,还可让我们立足历史,展望未来,挖掘流人文化之魂,对于当下弘扬北疆文明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有利于弘扬东北地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是一定区域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地方精神面貌、人文风俗习惯、社会风气秩序、地理环境品格等,这种面貌和品格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恒久的当地传统。形成这种地域文化的原因固然离不开长期居住在此的当地人在认知领域形成的地域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离不开曾经流寓、客居、放逐在此的异地人对当地文化的拓荒与改良。东北地域文化土壤深厚,长白山是满人的祖居地,今日的沈阳被满人称为“盛京”,足见满人对这片沃土的情有独钟。流人不远万里来到东北,接触到的是众多阶层、众多民族的人民,他们通过与当地人民的往来,既了解到当时东北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充分领略到塞外边疆的独特魅力。清代东北各民族人民的勤劳、各地区山川的壮美在流人的笔下都有很好的诠释,研究东北流人的文化活动,立足于东北流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而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的命脉所在,对于未来我们根植本土文化、创新生态文明、把握时代脉搏、弘扬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广泛的意义。东北流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有价值的财富,我们可以立足于此深入挖掘东北文化发展历程,进而向世界展示东北的雄浑。
第二,有利于开发东北旅游文化资源。2000年,研究东北流人史的开拓者李兴盛先生就曾经发表过题为《关于流寓文化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的论文,他明确指出,深入研究流寓文化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事业发展[3](P128-133)。东北地区地处白山黑水,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未来的旅游文化应该走一条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道路。打造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的深度开发,是目前东北地区发展东北亚经济优势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发了相关的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相关产业,但在文化旅游方面还需要加大深度和力度,相比较江南地区,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薄弱,可开发的项目极其有限,将流人文化纳入旅游产业的视野,作为提高旅游文化品位的核心,这本身既是对流人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又是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
第三,有利于充实清代文学史、东北文化史。迄今为止,清代文学、东北文化是目前学术研究领域相对薄弱的环节,清代诗歌流派数量众多,地域文化特征明显,但以往成果涉及东北流人的少之又少,更少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究。事实上,无论从流人数量和作品数量上看,无论从流人的文化活动和传播意义来看,清代东北流人都应该被纳入学术视野,清代流人文化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贬谪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增添了比以往朝代更为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意识恰恰是东北文化的脊梁所在,是在逆境中求新求生的精神内核,这种文化本源的追溯,对于充实东北文化史,启迪后人意义重大。
四、结语
据李兴盛先生《东北流人史》考证,东北流人始于西汉时期,清代流放人数约为150万,在数量上达到历史顶峰[4]。东北流人的流放区域、范围和人数来看,可谓史无前例。当我们回首那些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蛮荒苦寒之地”的流人,当我们枕读他们的诗文与志略,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深邃与强大的生命力浑然一体,那些沧桑的史实告诉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曾经为清代东北边疆开拓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是他们把中原文化带到这里,把热情带到这里,把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忠义之情、赤子之感带到这里,这一切值得后人铭记。
[1]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M].沈阳:辽沈书社,1988.
[2]吴桭臣.宁古塔纪略[M].
[3]李兴盛.关于流寓文化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0(8).
[4]李兴盛.东北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