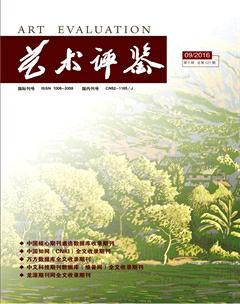从中国画角度看当代士夫精神
陈贲
摘要:书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成教化,助人伦”的宣教方式,也是“代去杂欲”的个人内心表征。既有“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的论断,也有“画者,文之极也”的评述。凡此二论,都讲出了从事绘画之人的身份及个人修为的层次。这两点也是支撑传统绘画演变流传的重要因素,绘画体现出来的士夫阶层的心境气象,更是我们追崇的一个高点。时至今日,绘画的形式丰富多变,画者也成为一种职业的选择,当从事绘画的人的身份转变,带来的必然是创作理念的转变。从而使得传统绘画中的士夫精神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关键词:士夫;文人;中国画;当代
中图分类号:J2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8-0058-04
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命途多舛。文化的变革随着政治经济变革的推进而难逃悲命,中国画作为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素,在这样的局势中也波折重重,被革命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在这种沉痛而又紧急的“衰败落后”、“生死危亡”的特殊社会环境之下,肩负着救国存亡的历史使命,对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农业文化提出了否定。在“救国存亡”的时候,这种固有的农业文化、农业文明与当今的工业文明相比起来显得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文化审思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反思和否定相应的也转变到了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上面,也提出许多对中国画的改革和批判的建议和意见。如康有为较早地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判断,认为“此事亦当变法”。再如陈独秀所倡导的“美术革命”,其矛头也指向了中国画,并主张通过西洋绘画的写实主义精神,变革中国画。正是这样的一种呼声,拉开了中国画新的演进历程。它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念及文化体系,也随之崩塌。图形、图真的观念逐渐代替了绘心表意的传统中国画理念。这样一种转变,所导致的不单单是绘画形式的改变,创作者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至今天,在中国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人们出门坐个飞机、挤个汽车,哪怕吃个饭人们都显得比较浮躁。今天的这种“浮躁”正是由于多年的文化精神、民族传统的缺失,造成的“心”无所依和精神支柱的丧失,进而导致迷乱浮躁。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式微,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的批判和打击日趋严重,好的与不好的一并当成不好的,在批判与舍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恰当的价值判断,以偏概全。再到后来的十年动乱,对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是何等的痛心。在此之后,为发展经济而开始的改革開放,逐渐确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策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远大于对复兴文化的夙求。
从文化艺术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迷失了许多,同时又急切的想“成功”,包括名利的成功。因此就出现了形式丰富多样的绘画样式,形式上的探索远大于对绘画本源意义的探讨,更多的情况下,笔墨只是一种工具,一味地追求新形式的绘画面貌,使得人们很少有精力去研究传统笔墨和笔墨所包含的道德层面上的内容。可以说一些画家因为缺失了思想力和精神境界,所以只能从这些图式符号题材上追求奇迹。其实这些都是在寻找一些不同的表现符号和方式,如此肤浅,为什么呢?近百年落后的社会状态,所导致的人们心理上的不自信,长期生活在信息单一的社会中而产生的猎奇心理,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瞬间爆发。因此很多国人都趋之若鹜的向往外国生活,都渴望通过移民到国外生活,成为精神和物质生活合体的“贵族”,而这种“贵族”精神其实我们也有,传统的“贵族精神”表现为一种优秀人文精神——士夫精神。那么何为士夫精神呢?我们需要先了解在历史上是如何定义区分士夫和文人的,从中国画的角度士夫和文人所画的画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一、士夫和文人
要区分文人和士夫在绘画上的区别,就应该先分清楚士夫和文人的区别。士是最第一级的贵族,在周代的周室班爵制度中分为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其中下士掌管各部门最基层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对权利的渴望导致对一些贵族阶层的打压,士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春秋时期,这种阶级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斗争导致的贵族身份沦落,另外,随着人们思想的觉醒,尤其是诸子百家争鸣,使得庶人也能够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的修为而迈入士的阶层中。“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①。这是孔子对士一阶层的期望,抑或说是要求。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既有从贵族下降为士一层的人,如颜回、曾参等人,也有出身贫贱而通过学于孔子,进而转换身份成为“天下名士显人”,免遭屠戮的,如子张。这么看来,本为贵族的士一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了新的变化。“至少下逮春秋、战国之交,庶人以学术仕进者已多其列”②。
而“文人”又作何解呢?《文心雕龙·知音》记载:“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故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思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淡也”③。这里也指“文人”即为有学问之人,能够识文断字的读书的人。
在概念定义上,可见文人和士人就有本质的区别。士人注重内外双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传统儒家观念中,对士一阶层的道德要求,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此之士所一贯坚持的一种标准。而文人在没有进入士的阶层之前,那只能说是能够读书识字之人,能够诗词歌赋之人,他们的才识在主观上并没有作为治国之用,这种才识其实只是表现为生活上的一种“技能”而已。文人先天不足,后天学力、用心也不深,往往浅尝辄止,浮浅、骄矜,因此他们也多是为每个朝代粉饰太平作锦上添花之用,汉代杨雄称此为“雕虫小技”。但是我们并不能从概念上去给士夫和文人一个明确的区别,毕竟古代能够入仕为官的人,都曾经是一个文人。历史时代的转换,往往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志于仕途的文人来讲,时代鼎革所导致的政治局面的混乱,经常使得一些文人失去精神寄托,或苟活于世,或沉溺于私情,卖弄才华,在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里喜怒哀乐,有才、无志、德薄。与士人志于德,德才兼备,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差距所在。哪怕不能做到完美,但是也严格按照规律去要求自己。由于士人和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所处的位置高度不同,对待问题的方式必然也不同,对待绘画上的态度及创作法则也就迥然不同了。
二、文人画与士夫画的异同
那么何为文人画呢?文人画的概念由明代董其昌首先提出,他还推崇唐代的王维为文人画的开创者。王维不但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他精通儒家文化,又参悟禅学意理,因此在绘画上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诗性的绘画风貌。如果把王维的画放在唐代整个大时代中去看的话,并不属于主流绘画,唐画尚法,阎立本、李思训等就职于朝中之人的绘画,莫不是严谨工致,焕烂求备。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士夫阶层中的不同个人,绘画风格也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后来文人画更为人熟知,而很少提及士夫画呢?这与宋代选官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宋代之前,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十分严重,虽然隋唐科举制度,使得一部分人能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但毕竟还是极少数的。到了宋代,这一局面被打破,取士不问世家,平民阶层能够通过学习考试进入政界,服务国家。这样看来,士人、文人的区分并不是特别明显,文人考得个一官半职,也就成了士人。士人受到贬谪疏离,自己也自然成了一个文人了。但是士人和文人心态上的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可以对比文同和苏轼二人的绘画,便可明显的看出处境不同而导致的绘画气象的差别。
文同为官,且一生都处于仕途之中,苏轼与文同有亲戚关系,但是仕途却没有他这么顺利。文同代表作品《墨竹图》所绘竹之姿态劲挺隽秀,严谨而又不失竹子的自然之态。这和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念显然是不相称的。苏轼本为朝廷官员,称得上是个士人了,但是几经贬谪,仕途之坎坷使其心智大变,只得于书画中求得内心安慰,但终究还是保持自己的一种恣意洒脱的人生立场,这一点也是能够从其《枯木怪石图》得到印证,一块怪石,一棵没有叶子的枯树,虽有萧素之感,却也耿直不屈,有自己特有的姿态。
古人所讲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④,从艺是要有一个道德标准的,需要有一种道义上的约束,这也是张彦远所讲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朝代更迭带来的士人心理上的变化,催生了另外一种绘画理念。因此,文人画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如士夫之绘画。宋以后的政权颠覆,蒙古族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使得文人气度渐弱,倪瓒所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虽是一种绘画观念,但更深刻地反应了其内心对时局的无奈和退避。与之相比,赵孟頫入朝为官,贰臣之身份虽为人所诟病,但是他在绘画上所主张的“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意”,这里所讲之“古意”,是晋唐之气象。对比倪瓒与赵孟頫,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身份之不同,所带来的认知上的差别。明代以降,绘画沦入到对前人的仿摹境地,虽有一些文人画家能够夐然独立,有一定风格,但終还是跳不出宋元画意,更不用说晋唐绘画气象了。
到了清代,绘画面貌变化更大。宾虹先生提到“画事品格,人不全知……不知中国有士夫画为唐宋元明贤哲精神所系,非清代文人画之比”⑥。清代文人画的陈陈相因所导致的形式上的雷同和程式化,是文人绘画应该警惕的。他特地指出唐宋及元明时期的士夫画,要知道这些绘画所依赖的思想体系,如宋明理学、心学等,是支撑起绘画气象的重要因素。而有清一代,不过是在考据学等方面对中国的文化做了一个系统的汇编,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又怎能在绘画上另辟蹊径,开创新面貌呢?当然,清代石涛为代表的“四僧”绘画是个特例。
等到了近代,革命的概念介入到绘画中来,况且提出这一思想的人也曾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姑且算作是士人阶层。这种认识的激进和偏颇,使得绘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演变,而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虽然形式丰富,但终究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内涵的绘画作品。这个过程中间,有坚持绘画之道的人,但毕竟大的时代趋势还是不能够使其成为主流。士夫画也好,文人画也好,在近现代早已成为了时代的附庸,而失去了中国绘画的本初精神。自我意识的主导,也使得绘画在这个时代,缺少了传统绘画应有的气量和韵致,虽然也有像蒋兆和《流民图》这样的关注民生状态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绘画出现,但毕竟这样的作品还是少之又少。人们对绘画的理解,已经逐渐偏离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而转向对西方画学思想及创作理念的依赖。这种态度使得文人画逐渐离弃“德”而“游于艺”,这种“艺”也成为了文人画家沽名钓誉的手段,成为文人墨戏或文人余事,因此也就谈不上“依于仁”,更谈不上追求艺术形而上的“风神气象”。
三、当今社会绘画状态与“士夫精神”的缺失
前文已提及当前中国画发展之心态。形式感大于一切,过分追求绘画技法而导致的制作感过强。传统中国画所倡导的书画同源之主导,及其所依附的价值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被认可,被嗤之以鼻的,甚至还出现了中国画穷途末路之论说。这些状况,凸显了中国画当下的尴尬境遇,一方面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有着不同时代的丰富特点;另一发面,也面对着当前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含义,却似乎有了与过去割裂的趋势。士夫精神,也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中渐行渐远,似有遁迹于世的态势。
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奈,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社会职业的划分越来越细,经济利益的夙求也变得更加迫切。画家逐渐成为一种职业,绘画成为一种于经济社会谋得生存的一种技能。这样的情况,如何能够让他们有所谓的固守和坚持呢?但稍有成就的画家,还是愿意用文化人的身份去武装自己,毕竟绘画还是文化的一个支脉。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有“文绉绉”一词,通常情况下,用来赞扬那些有学识及道德修养较高的人。但在今天的社会中,由于文化力量的缺失,文人群体的弱化,“文绉绉”一词的意思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解读开来便可理解为太过文气、小家子气,不够自然大方,扭捏作态。士人为君子,君子成人之美、自强不息,而文人不一定为君子,也有可能是小人,读书识字便是有“文化”有“知识”,或者叫知识分子,但不等于有“素质”,士人是有“文化素质”的人,在天赋才气之上能够致力于学问的客观研究,比起文人不仅宏识,更具有恒心。同时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在内心上对自己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所以士人往往看起来不显得张扬也不显得花哨。士人因为主要用到很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学问研究,而相对起士人,“文人”就更致力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的活动这些“文人画家”获得相应的名气、名声以及社会地位等,在社会上显得是获利者,例如在今天,一些画家进入专业单位之后画价暴涨,主动去迎合市场,批量复制自己的作品出售,而后买豪车置豪宅,出门都是前呼后拥,参加各种商业活动等,在画家在世的年代中收获许多身外的名利,显得十分“光鲜”,而这个“光鲜”和“士人”的埋头做学问、孜孜不倦的深入研究、勤奋练习的内心内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人们眼中士人更显得默默无闻。
据说陈洪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年年中的时候,邀请一些同仁到家中参观自己的作品,但凡有一个人称赞其画好的人,他便会拂袖而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陈洪绶会有如此的举动呢?人皆之好,就非真好,实际上这反应出陈洪绶对社会的普遍认识是比较高的,他认为如果对自己界定的比较低的普通世人认识表示赞同,那么自己作品必然不够超拔、不够脱俗,所以他会选择撕毁自己的作品。从现实价值角度来分析有人围观称好,这件作品就已经具有现实价值,但还是被他否定了,这些都反应出陈洪绶在内心上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反应出了社会对士夫画的普遍认识,社会往往无法接受士夫画,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例如印象派、野兽派等,因为他们的精神思想超拔,对现实社会有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比较高,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缺乏认识高度,生活在“常态化”的生活中,没有充分的“文化储备”就自然不能理解“在普通之上”的更深层用心。因此普通人难以读懂、看懂,也因此才会有徐渭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陈老莲的“人之见好即裂去”的状况。这也就是社会对士夫画的认识。因为社会不容易认识士夫画、接受士夫畫,所以士夫自己得有担当,因为世人不认识不接收也应该做,世人认识接收也应该做,这也体现了士夫需要具备文化使命感,还应该具备能够沉淀下来的静穆精神。
四、呼唤“士夫精神”
时代的发展决定了绘画在每个时段内不同的演变方式,它紧随着时代,也反映着时代,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当前绘画形态的多种多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势,是时代的一种实时的反应。在经历了近代国画改革,绘画创新,思维转换的几个阶段以后,从艺者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地审视一下绘画的发展正脉。张彦远所言及的善于绘画之人,莫不是衣冠贵胄,有地位之贵族;逸士高人,有着极好的文化夙求及个人修为的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绘画有其特有的文化属性,从艺者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它并不是一种恣意而为的行为,需要一种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下很快就会变成历史,后人在回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绘画时,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判断?是浮于表面的绚烂多彩,还是内敛包容的厚重敦实,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和斟酌。
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是形而上的,思想成分占的比较多,因此往往类似“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富有诗意”、“构图完整”这些“外修”都只能用来形容和评价“文人画”,相对于形而上的士夫画则更注重于“纯全内美”。黄宾虹在《国画非无益》文中指出:“士夫之画,华滋浑厚,秀润天成,是为正宗。得胸中千卷之书,又能泛览古今名迹,炉锤在手,矩矱从心,展观之余,自有一种静穆之致,扑人眉宇,能令睹者矜平躁释,意气全消”⑦。这里的“静穆”即是指士夫画应该具备的静穆精神:安静、沉稳、深刻、矜平燥释、让人低头沉思的,反观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却是喧嚣的、浮华的、艳丽的、漂亮的、使人赏心悦目的普通“文人画”,然而这种静穆、这种不喧嚣也就注定了士夫画必将默默无闻,不容易被世人发现与认识,这种“曲高和寡”、“知稀为贵”更体现出了它的难能可贵。其实这也体现出了文人与士夫最大的差距——内心的自我要求与社会的担当。在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人们都进过学堂,都懂得识文断字,都可称之为文人了,那么为什么还称士夫呢?其实士夫在当今社会指的是一种心态而并非阶级了。士夫精神指的是有当下意义的,是沉静、专注、深刻、主动去有担当的,这种士夫心态、士夫精神并非是这个社会给予的定位,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求的,这种主动要求是可以学习和使用的,因为它对这个社会有更深刻的帮助。而对社会的这种担当,未必是社会赋予,而是士夫自己应该有主动的文化使命担当,不需要任何人聘用,而努力争取为中国的文化添砖加瓦,例如近代著名画家潘天寿,陈师曾等人,他们都有沉痛的文化忧患意识,都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履行着自己的文化使命。
时至今日,国家对文化的强调和重视已成为一个重大政策,文化兴国的方针也催促着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能够重拾文化自信,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面貌也当顺势而上,在关注时代变换的同时,及时地回望传统,以一份静谧的心境,审看中国画的发展脉络,然后选择其之后的演变方向。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时候,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要求的士夫精神更应该得到宣扬和推广,人人学习这种士夫精神更显得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王盛元 注解《孔子家语通解》,译林出版社,2014年.
②余英时 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梁·刘勰 著《文心雕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③钱宁 编《新论语》,三联书店,2012年.
⑤张彦远 著《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⑥黄宾虹 著《黄宾虹谈议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⑦黄宾虹 著《黄宾虹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