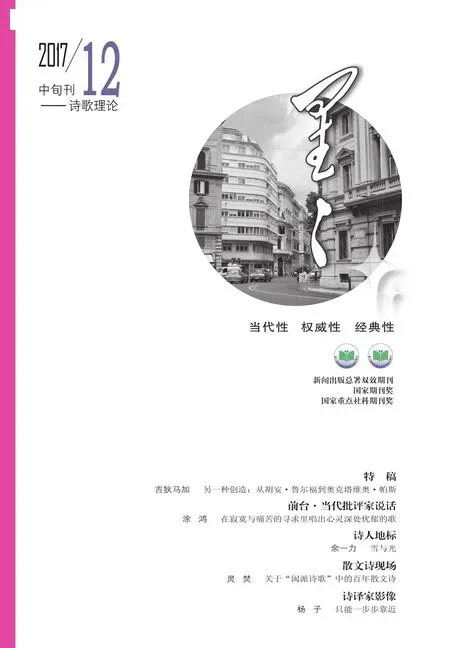在寂寞与痛苦的寻求里唱出心灵深处忧郁的歌
——论重庆当代女诗人冉冉、红线女诗作的意象空间
涂 鸿
我所学到的所有语言,
我所写出的所有语言,
必然要展翅,不倦地飞行,
绝不会在飞行中停一停,
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
在夜色中向着你歌唱,
远方,河水正在流淌,
乌云密布,或是灿烂星光。
——叶芝[1]《我的书本去的地方》
2000年以后新世纪的重庆当代诗坛,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嬗变的纷繁多彩的时代,一批年轻的女诗人,以其忧郁、浪漫的情绪传达,细腻、敏感的诗歌抒写,恬美而酸楚的情感体验,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引人关注,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这个群体的诗人主要有:冉冉、红线女(何小燕)、金玲子(蒋信琳)、梅依然(唐梅)、白月(宋桂兰)、沈利、梦桐疏影(张鉴)、余真、周冬梅、简(滕芳)、海烟(罗晓玲)、吴维(吴洪华)、隆玲琼、弗贝贝(费丽)、阿雅(单宇飞)、雨馨(余馨)、重庆子衣(何春仙)、周鸿鹄、宇舒(赵域舒)等。情感传递与抒发是诗歌最本质的特征。诗歌作为心灵与情感的载体,必然表达主体对客体的体验与感受。长期以来,重庆的女诗人们沿着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她们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情感的倾诉,一种对艺术的机敏,一种个性的展现,一种对生活的真挚和深情,他们在诗中营建的情感天地是狭小的,然而透视的人生体验却又是独特的丰富和深邃。我们在此选择有代表性的两位女诗人冉冉、红线女分析其诗作构建的意象空间。
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场阈,其艺术触角可能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也可扩展到未知而神秘的情感世界,作为心灵对象化的诗歌,必然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坦露和复杂情绪的聚合。诗人的创作在其作品里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并以一种充满个性的艺术言说传递情感。如何在诗歌中营造主观的意象空间,表达自己对时代与社会、精神与灵魂的理解;如何分享和记录一个现代人的孤独、痛苦与欢乐,如何聆听自我心灵的歌声。这在冉冉、红线女与梅依然的诗作里,完全融入一个他人很难介入的神秘幽深,敏感而多情的意象空间,她们在作品里灌注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根据自我情绪的流动和瞬间的情感体验开拓主题、设置意象以及创造语言。
她们不仅根植于巴渝文化的土壤,而且站在了更高的艺术观照层面上,审视自我的世界,从而使言说个体传递了对自然、社会、时代和生活的敏锐感受,创造了属于她们的深情而忧郁的主观世界。我们从冉冉、红线女两位女诗人在诗作中诗歌意象空间的构建这一角度,来说明她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剖析她们所构建的诗歌艺术世界,阐释她们的诗学观。
2000年以后新世纪的中国处于一种遽烈变革和躁动不安之中,这种影响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当地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且对当地整个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重庆的女诗人。冉冉(1965— )、红线女(何小燕,1972—)也在纷乱、斑驳的时代巨变中构筑着自己的诗歌世界。冉冉先后出版了《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出版1996)、《从秋天到冬天》(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空隙之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朱雀听》(作家出版社2013)、《和谁说话》(作家出版社2015)等,其中重要诗作有:《树与河流》、《湿房子》、《再次梦见杨》、《暗处的梨花》、《在鸟儿的眼里》、《草原上的水洼》、《公交车上的几十个人》、《手心的镜子》、《赶在天亮之前》、《夜幕合围之前》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艾青诗歌奖、重庆文学奖。红线女先后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红岩》、《大家》、《绿风》、《中国作家》、《延河》、《天津文学》、《绿洲文学》、《山东文学》以及美国文学刊物《常青藤》、《新大陆》等发表诗作一千余首,其重要诗作有:《儿子的码头》、《我们》、《重庆,我是你一根受伤的小指头》、《儿子》、《痛》、《遭遇解放碑》、《我们自己取火》、《殇》、《乐乐》、《桂》、《他》、《小弟》、《大哥》、《月半节》、《心神难宁》、《海的声音》、《我不会削苹果》、《白月亮》等。出版了诗集《频来入梦》(中国文艺出版社2005)、《风中的眼睛》(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手指上的月亮》(珠海出版社2009)、《大千大足》(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说吧,荷花》(青海出版社2011)、《我的岁月之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纸码头》(团结出版社2017)等。作为底层诗人的红线女虽未获诗歌的奖,但苦难的生活砥砺了她,对理想的执着追寻与对生活的热爱成就了她,在以灵魂抒写生命的诗意历程里,她以自己孤独、浪漫与真诚的歌咏,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可,曾被很多文友称为当下诗坛的“红线侠女”,有诗人梁小斌、舒洁,评论家叶橹、谭延桐、吴昕孺等为其诗集作序或撰文评论其诗作[2]。从这些可看出底层诗人红线女的诗作受到人们的关注,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两位女诗人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对现实的忧虑,对人生的惆怅以及对理想的期盼,使得她们将太多的憧憬置于自己所构建的主观理想主义的情感世界之中。她们离现实生活的激流很远,而离自己生活的世界很近,她们多以无比细腻和敏感的心凝视着生活的内部世界,成为寂寞人生旅程上的吟唱者;她们的诗从意象、语言、意境乃至氛围和格调都在铸造着寂寞又独立的灵魂,她们将创作的凝聚点更多地集中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倾述、自审与开掘,“诗本是最富于个性的艺术,离开诗人个体对世界独到的观察和感觉,离开诗人面对生活的心灵的颤动,离开诗人特有的艺术地掌握和表现生活的方式……诗就失去了真诚的魅力。”[3]因此,她们总试图将自己在诗歌中所构筑的情感世界作为透视外部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小窗口。
一、诗歌抒写存在于主体与客体间并最大化地构建这个空间
当下重庆或中国女诗人的诗作里,不少人没有停留在以往多数老一代女诗人创作那种独立于创作者主体意识之外,多以“旁观者”的态度,对生活的表层意象空间所作的简单营造和拓展上,她们是将情绪传达的角度完全转向了话语言说的主体——诗人的心灵世界,并由此来观照客体世界,抒写心灵深处的歌,在主体与客体间拓展诗歌意象的空间。正如红线女所谈及的“在纷繁复杂的俗世生活里,我终于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并且用诗歌的方式,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一种热烈而持久的,关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关于大足石刻,关于菩萨,关于荷花,关于一切美丽的生命的呼吸的声音!”[4]诗人在痛苦而孤寂的灵魂追寻里,在内心深处痛苦与孤独的体验中,抒写自己对生命与世界的感悟:
……
整个夜晚开始循环往复
火鼓穿越了一切。摆脱了一切
我们开始摇晃
我们似乎在忘记
我们似乎又记起
我们跪在生命本身之上
死亡和黑暗,都在溃散
并逐渐远离
——红线女《火鼓》(《绿风》2012年第2期)
诗人在对诗歌所描绘的客体世界湘西的地方节庆,在汉、苗、侗的欢舞中努力重现景观,不仅描绘了客体的外象,还穿透自己的心灵。艺术创作应该超越其所依赖的物的表象而进入非具象所能涵盖的世界。所以红线女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一种既适合表现客体世界,又能以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艺术传达,复原出了有生命的诗歌意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不少传统的女诗人停留在对外在客体的表现上。
红线女在《心神难宁》里这样写道:“凌晨三点/他来到我的梦里/把我喊醒了就走了/凌晨四点/他又来我梦里走了一圈/最后一次是早上六点//他居然在我梦里/死了三次又活过来三次/每次都很清晰/要么在吃饭,要么在喝酒/要么嘟囔着想告诉我什么//想说什么呢/旧事千疮百孔/新的,更如活鬼缠身/我不能安静地描述一切/更不能以期待的宁静活在世间//给我一点启示/要么让梦快点死去/要不等到明年的月半节/咱们一起再醒来”(《诗刊》2014年4月)。诗人在带着寻梦之中的无比惊悚、寂寞和惶惑之外,还有一层忧郁与苦涩。她在孤独中饱含了寂寞,在寂寞之中渗透执着的追寻与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在《她》中这样表述:“她一直坐在轮椅上/坐在四川达州/庙坝下街26号/在很黑很黑的夜晚/看星星和月光坠落/看黑暗掩埋人世流长//她总想躲在世人的目光外/用死亡把自己救赎/用影子走路/用梦说话/用诗歌中的姓名与自己作伴//然而,她总是打开半扇窗/把一只手伸出窗外/像一只被放生的鸽子/悄悄回到人间”(《大家》2008年3期)。美国艺术史家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n,1895-1982)指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无限的一种渴望。它从来不无保留地接受现在,它永远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而且永远在发现有某种更好的迹象。”[5]作为底层诗人的红线女,她诗歌的视野就在身边,她始终以一种敏感而深情的目光、一种执着真诚的精神关注着重庆的普通百姓的情感与生活,关注着巴渝山乡的时代与社会。她在诗中忧郁而痛苦地寻找着凝聚在人情与人性中永恒的价值,一种信念,一种生命支柱,从而来完成她对无限与永恒的渴求。
冉冉在《我和杨》、《再次梦见杨》、《香蕉林》、《无端地想起某个词》、《星子一颗颗向窗口走拢》、《静夜》、《绿翅膀的夜莺》、《爱人》以及《湿房子(外二章)》等等诗篇中,美丽的、温馨的梦的寻求和爱的怀想往往交织在一起,爱是梦的实体,同时又是诗人美好理想的象征。冉冉在构织这些带着温馨和充满依恋温情的梦境时,其作品所传达的最深刻与最本质的情绪,仍然是她对人生寂寞、惆怅和忧伤的感知。冉冉总是将爱涂上一层神秘理想的色彩,它像梦一样的虚幻和飘逸,又像梦一样的温馨和难以捉摸。女性心灵的细腻使得她在狭小对象的世界里体味到微妙的真实与忧伤。但无论她将爱的角触伸向现实生活的土壤,还是伸向遥远的历史的记忆,她的痛苦仍映现了当代人的痛苦,她的寂寞仍是当代人体验到的寂寞。诗人放逐在自我情感天地的时空里,也赋予了这种情感普遍的时代意义。
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反映”的模式,正如黑格尔所说:“它(诗)所处理的不是展现为外在事迹的那种具有实体性的世界,而是某一个反躬自省的主体的一些零星的观感、情绪和见解。”[6]冉冉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这种“反躬自省”的情绪表现,完全真实地再现了诗人隐秘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世界。
笔者与冉冉曾是长达九年的邻居,比较了解她那种独特的细腻和敏感所蕴含的内在情绪,她常常独坐窗前,默不作声,在自己主观世界里孤独而艰辛地寻求。作为生活的探索和思考者,作为清高而敏感的人生跋涉者,她远离了浮华而躁动的时代潮流,寂寞与苦闷几乎成了她主要的心理特征。诗人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创造的艺术世界,与喧嚣的时代生活是隔膜的。她独自步入了另一个委婉、寂寞的世界,她倾力营造温婉而美妙的梦幻,但过多透示的却是失落和感伤。她的诗从意象的选择、语言的锤炼以及意境氛围的营造都在表述着寂寞而孤独的灵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的重荷在这位忧郁而敏感的诗人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她在梦的吟诵中,跃动着一颗率真而无奈的心。她深情地叹息着爱的迷失:
左手掌心里 有一小片镜子
被右手捂着
为掠过的鹰难过
“它映照的不是死亡 只是鹰”
“死亡没那么高 那么小
死是薄薄的摊晒的羊皮”
“死亡也没那么孤单 那么黑
死不过是并拢双膝 好比两座雪山
相视而眠”
……
——冉冉《手心的镜子》
(冉冉《和谁说话》,作家出版社2016)
在冉冉的《草》、《有星子的夜晚》、《面对灯火》等作品中,还暗示了人生旅程中的忧郁以及逃离寂寞的强烈情感。从她的《追忆战火(组诗)》、《在鸟儿的眼里》、《坐在火边幻想飞去》、《今晚 我三次被照亮》等诗篇里,我们可窥见她强烈的渴求与无限的期盼,同时也可深切地感受到她那颗伤感、疲惫和寂寞的心。
冉冉是敏感的、细腻的,同时也是忧郁和寂寞的,她在诗中对生活体味的幽深,使得她的诗作在当代女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视阈空间,诗人以寂寞忧郁的情绪诉说着她的向往与感悟,她带给读者的,既有无限的朦胧和忧伤,又有轻柔的浪漫。她与红线女诗歌中坚忍、率真、豁达、刻骨铭心的倾述中所形成的明晰而破碎、清新而灵动的意象空间所不同的是,冉冉努力编织温馨的梦境总是寂寞,在寂寞和忧郁的情绪传达中,渗透了迷茫与幽深的情怀。
二、在诗歌意象符号与语言符号的设置里拓展抒情的空间
冉冉与红线女诗歌的空间维度有对生命、存在、梦幻、和自然的透彻认定以及对自我世界的穿透,她们的作品呈现出的清新、忧伤、敏感而浪漫的歌吟,她们在诗作中没有刻意地表现,诗人的体验不仅仅是来自内心,也来自她们的生活境遇以及她们对世界的体认。她们诗歌话语的言说符号更多地表现在对内心情感的传递,生活苦难的承载,生命存在状态的探寻以及巴渝自然物象的展示中。她们往往以一种充满了强烈暗示色彩的方式,构织了一种神奇、幽远和充满梦幻般的艺术世界。
对于冉冉而言,她更多的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纤巧,以冬天、雪、炭火、农舍、青岗林、鸟儿、田野的草垛、乌江等意像,编织她诗歌的意象空间,创造了一个远离现实,充满着美丽忧伤而又深执幽远的诗歌世界。这在诗人的《青林回首》、《有星子的夜晚》、《烤火》、《乡村旅店》、《除夕夜》以及《踏雪》等不少诗篇中都有所体现。两位诗人的作品几乎都染上了哀愁,她们的诗行里都被寂寞和忧郁浸透,她们的感觉是真切而又深沉的,这只有无比深情执着的情感和充满无限渴望与希冀的灵魂,才会有如此的忧郁和深沉。
作为女诗人,冉冉与红线女那颗孤寂、飘零和忧郁的心,注定了她灵魂的沉重与悲凉,她永远都在孤苦地寻求前方那个新鲜而神秘的世界,那是诗人所构置的童话般的理想空间:“我是蓝色的吗?当睡眠/像另一棵树罩在头顶/我是红色的吗?当太阳/像另一只鸟儿将我张望/我是白色的吗?当雪/像另一种遗忘四下扩散/哦鸟儿/当我向你回眸之时/我是棵光秃秃的鸣响的枫香/……”(《在鸟儿的眼里》,见冉冉《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1996)这是以心去体悟世界并将其充分情感化的抒写,诗人在一种主观色彩极浓的表述里,努力拓展她情感的意象空间。“……/我看见雪中的姐姐/纯洁的额让人爱怜/她跟玻璃交谈/宽大的房屋悬空轮转/我看见我在冒气/我在飘扬姐姐/我们是邻居/雪花之外我整天叹息/飞扬飞扬/离开火焰/我们这些幻想的物质/成群结队的雪落在瓦上/今年与往年不同”(《坐在火边幻想飞去》,见冉冉《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1996),红线女也几乎是以同样敏感深情的体验在抒写:“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捡不完你心上的石头/和石头下不定性的阴影/童年的小马车/从一个山坡奔向另一个山坡/蒲公英没有种子/向日葵不知去向/一些噩梦总在小马车之后//没能给你美玉和火焰/没能给你富足和完整/在阴影和疼痛之间/我只能扮演秘密父亲和爱你的妈妈/我们甚至遗失了小马车/没有人看见我们总在捡石头/当黑色的夜落在世上/儿子,我们自己碎石,取火”(《我们自己取火》,载《红岩》2009年3期)诗人以无比清丽、率真和委婉的笔调,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美丽忧伤而又深挚委婉的意象空间。
冉冉与红线女是当今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对人生社会十分敏锐的女诗人,她们逃避喧嚣浮华的世界,但同时又无比细腻和真切地心关注、体察着鲜活的生命和世界的真象。注意追求把握世界和传达内心情绪方式的内敛与率真,诗人虽将生活、社会与感情直接入诗,但她们都努力把生活和感情升华提炼为诗人独自拥有的经验,即把生活的真融化为艺术的真,“把感觉的真同艺术的真统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7]。我们在她们的诗里看到的不再是生活和感觉的因子,而是由这些因子凝聚、融化与升华而成的独特感受经验铸就的意象世界,于是她们那无限的渴求与无尽的忧郁之情便总是潜流于她诗歌中那片独特的情感天地里。委婉细腻、依恋忧郁、清丽温柔,再加上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创造出了一个深情的主观艺术世界的意象。
诗歌创作可以看作一个由语言符号和象态符号有序化了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大体上看又有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表层的语言符号系统,词是语言最小的独立的表意单位,因而诗歌的表层便是以词语为基本构成元素的语言符号系统。又因汉语中汉字与意义、音节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的诗人就把握这一特点,运用语言符号时分析到单个汉字,以创造诗歌某些特有的审美特征。透过语言符号层我们可以看到深层的象态符号系统,即所谓“意境”。
意象是载“意”(情感和思想)的“象”(表象,客观外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映象),因此,一首诗就可以解剖出“意象”、“事态”、“词语”等基本元素。诗人的工作就是运用这些元素进行有序化,即编码过程。当代诗歌理论家孙绍振认为,“诗歌形象是生活特征、自我感情特征和艺术形式特征的三位一体”[8]。概括的生活特征和特殊的自我感情特征组合成意绪结构之后,就要寻找表达艺术形式的特殊符号特征传达出来。正如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所认为的“艺术形式里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9]。在诗歌中这种“客观对应物”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意象”的“象”和“事态”的“动作”,找到恰当的象态符号便成为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开端。把握象态符号的特征是正确运用象态符号的前提,对象态符号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在冉冉与红线女诗歌意象空间的构置里,来自巴渝元素性质的意象,如青山、冬天、雪、炭火、青岗林、农舍、菜地、石刻、儿子、水码头、田野的草垛、乌江与长江、重庆的城乡等在诗歌中比比皆是。她们在那些种种具有隐喻、具有象征意味和寓意色彩的地域物象以及古老文化的历史积淀中,以灵魂与生命的自由,舒展着个性生命,从整体上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情感、伦理、情欲等基本主题的表现。
选择某一象态符号是将意绪结构转化为象态符号系统的第一次编码,即意境营造。第一次编码是将象态符号系统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即语言表述的过程。在诗歌中,美感等意绪信息是以意象和事态为载体,编组成“意境”这有机的象态系统,象态系统再通过语言的表述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完成诗歌创作。意境的营造,也就是将意绪信息编译成象态符号,组构象态符号系统的过程。
象态系统不仅有机地组织了各象态符号,而且其整体的意绪指向超越了单个象态符号之和,这是象态系统功能的表现,而且,其有序化程度越高,功能便越强。[10]冉冉与红线女这两位忧郁、浪漫而真诚的歌者,带我们—起走进了那灵动而感伤的情感世界。在诗人的笔下,那里正为我们开启着充满孤独、痛苦的生命之旅,那是一个率真、忧伤而迷茫的世界。
三、在诗歌外在与内在世界的和谐统一里寻找深邃与丰采
从诗歌的审美选择上看,冉冉与红线女诗歌情绪的委婉、内蕴与细腻是诗人审美意识的核心,她们在寂寞寻求的痛苦里,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忧郁的歌,在这一点上,她们与当时诗坛上不少具有先锋色彩的青年诗人的情感传达是一致的,她们更重视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揭示,通过对“自我”的情感心理内容的表现,传达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在两位女诗人作品的意象,所传达的情感世界是细腻、朦胧而又狭小的。但就诗人整个人生经验和情感潜流的容量看,它又是特有的广阔与丰采。
冉冉与红线女的诗作在委婉、含蓄、率真的情感表述中,浸透了诗人对社会生活、人生理想深沉执着的追求和独特的体验,时代、社会、人生的投影,透过她们诗篇里那些狭小的情感窗口,得到较为充分和多彩的展示。
为了服从表现内心世界的需要,她们都十分注意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即努力在被人们忽略了的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情,在细微琐碎的事物中发掘诗思。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受,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这种“穿透力”表现出诗人在生活领域里发现诗的敏感度。在冉冉与红线女的作品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敏感:土家山寨青林里的回首,山林里穿梭的挑水女人,课余吹着土造笛子的山村教师,三月里放风筝的男孩;大足的石刻与荷花,儿子的痛苦与忧伤,林中的飞鸟,山坡上金黄色的油菜花,孤独漫长的黑夜等等意象都传递了这种情感体验。
从冉冉的诗集《暗处的梨花》、《朱雀听》、《和谁说话》,到红线女的诗集《风中的眼睛》、《手指上的月亮》、《我的岁月之书》、《纸码头》等营造的诗歌意象,可以发现她们努力凝聚自己的审美眼光,在微屑琐细的事物中发掘富于诗意的对象,来构建他们所爱和所恶的世界,即使是无“诗”的事物也成了她们诗情的象征性载体。
然而,在微细平淡的事物里发掘诗思,并不是将诗人的情绪降格到卑微的境地,而是诗人的敏感对生活深层蕴藏的诗美的宣泄与升华。在她们饱浸寂寞忧郁的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现实深挚的关注,感受到她们对美好理想和温馨情愫的深情呼唤,感受到她们那一首首精美的诗篇中的深邃与丰采。
朱自清认为:“判别诗人还是写诗者,要看他是否真诚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情绪;判别诗还是非诗,要看它是否独特地传达出诗人独具个性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经验。(所谓生活感受,指的是诗人对时代生活脉搏的感应;所谓内心经验,是指溶化和积淀在诗人的情感气质等生理机制中的种种历史的、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事物)。这个标准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内涵,其一是必须真诚地呼应生活的真实,其二是必须具有艺术表现和语言表达的独创性以及心灵感受和思想发现的独特性。不能满足这两者的或只满足一部分的,就是非诗,或劣诗。”[11]从这个角度考察,冉冉与红线女的诗,都以特殊的情感传达方式,清新、朴质的语言,细致入微的情感投入,个人化的情绪体验,从平凡细微的客体中传达出对生活的丰富而深刻的感悟。她们对诗歌意象的开拓,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而冉冉与红线女的诗属于时代,也是属于未来。
诗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久远、最崇高、最本真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与人的生命流程、精神意识同一的语言生存,是人对自己生存的历史一种象征化的超越,是人对自我的透视与逼近,是一种对存在的歌唱。作为最古老的艺术样式的诗歌,一个即使再小的民族,时至今日,只要该民族内部仍在释放着能量,便能够毫不逊色地向外部世界展示出它生命的光辉。
从上述这些意义来看,我们对重庆当代女诗人的创作进行研究,将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对她们诗作的意象空间进行审视与把握时,试图在另一种艺术世界里寻找一种情感历程与艺术呈现。
注 释
[1][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亦译“叶慈”、“耶茨”,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诗集《古堡》(1928)、《回梯》(1929)、《新诗集》(1938),另有散文剧《窗棂上的世界》(1934)、诗剧《炼狱》(1938)等。
[2]梁小斌(1954—)《苦难之尊》,见红线女《大千大足·序》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舒洁(1958— )《竹的品质——读红线女诗集〈我的岁月之书〉》,鲁十四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23a99a0101eyoh.html;叶橹(1936— )《红线女诗歌简评》,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谭延桐(1962— )《把光披在自己的身上》,见红线女《风中的眼睛·序》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吴昕孺(1967—)《冰火融铸诗人心》,见红线女《风中的眼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第152—155页。
[3]吴欢章(1935—)《回首朦胧诗》,载上海:《文学报》,1998年12月3日。
[4]北京,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诗歌研讨会”(2011年11月15日)红线女发言稿。
[5][美]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n,1895-1982)《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张洪岛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第86页。
[6][德]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76页。
[7]辛笛(1912—2004)《手掌集·序》,上海:上海书店1988。
[8]孙绍振(1936—)《文学创作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502页。
[9][英]T·S·艾略特(1888—1965)《批评的功能》,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65-66页。
[10]涂鸿(1963—)《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24页。
[11]朱自清(1898—1948)《新诗杂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