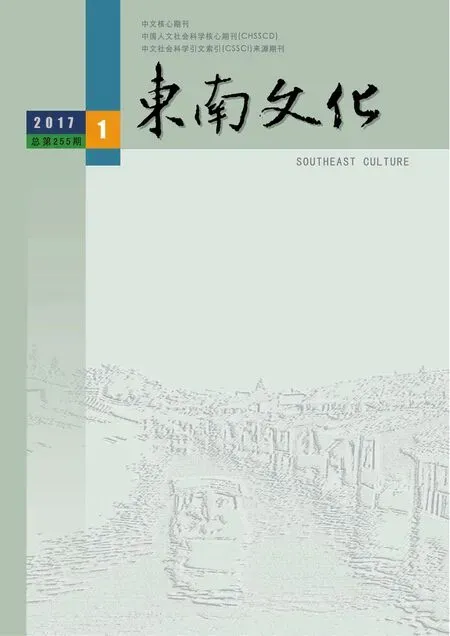论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出土的小铜鼓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论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出土的小铜鼓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浙江安吉上马山墓地曾出土一面小铜鼓,为国内首见。经比较可知,该小铜鼓属东山文化器物,由越南北部输入。随葬小铜鼓的M 10约为西汉中期墓,墓主生前可能到过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和九真郡一带,在当地获得小铜鼓并带回家乡。这一发现与百越内部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无关,反映的是汉帝国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岭南地区与内地间的密切联系及相关的人员往来情况。
上马山墓地 小铜鼓 东山文化 西汉
1989~1990年间,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清理过程中出土一面小铜鼓,其体量之小为国内铜鼓材料中所仅见。越南学者郑生认为,此面小铜鼓属于东山文化的器物,来自于越南北部[1]。从上马山小铜鼓的特征、风格以及同类器物的考古发现和分布看,此判断显然是正确的。不过,对于上马山小铜鼓到达当地的途径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笔者认为还可结合具体考古材料及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既有助于加深对小铜鼓及墓葬本身的认识,还能为考察汉代中国南方各地间的联系及人员流动等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一、上马山墓地及小铜鼓的出土
上马山墓地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安吉县良朋镇,与分布其北侧的五福墓地实际可连为一体,是太湖南侧苕溪流域一处重要的古墓葬遗存。自发现以来,上马山墓地经多次发掘,已清理墓葬500余座,年代大多在两汉时期。这些汉墓均埋葬于土墩之内。土墩以圆形居多,直径一般10~20、高2米左右,其内所埋墓葬少则1座,多则数座,最多者达20余座。大型土墩内常见布局有序且年代和等级均相近的多座墓葬,应为经周密规划的家族墓地。墓葬多为竖穴土圹墓,部分尚存棺椁葬具,有的还带边箱、头箱等设施。墓内一般都出随葬品,多者可达数十件,以陶器居多,另外还有铜器、铁器、玉石器、漆器等[2]。陶器有泥质陶、硬陶和釉陶等质地,常见成组合出现的鼎、盒、壶、钫、瓿、罍、豆等礼器,另外还有罐、釜、洗、盆、瓮、杯、勺、匕、熏炉、印章等器类以及井、灶、猪、狗、鸡等模型器。铜器主要有鼎、鍪、洗、豆、镦、鐎壶、勺、镜、环、泡钉、鼓以及半两和五铢等钱币。铁器主要有釜、剑、削刀、三足架等。玉石器有璧、琀、鼻塞、耳塞、研石、研子、玛瑙珠等。根据对地层关系以及出土器物的分析,上马山汉墓的年代主要在西汉早期至东汉中期[3]。类似上马山墓地的汉代土墩墓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还有不少分布,地点包括湖州市杨家埠、长兴县和平镇、杭州市余杭区、海盐县南抬头等[4]。这些汉代土墩墓在文化面貌上既有汉墓的时代特点,又与江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土墩墓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此外,部分西汉墓还具有楚式墓的一些特征。
在上马山墓地东南约3.5公里处,为安吉古城遗址。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600、南北宽约550米,四周尚存城墙和护城河。据调查和发掘,城内文化堆积较厚,出土大量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初步判断古城始建于战国,沿用至汉晋,是汉代鄣郡郡治所在[5]。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鄣郡改丹阳郡[6],治宛陵(今安徽宣城),此城作为故鄣县治继续使用。上马山墓地规模大,沿用时间长,从年代和空间位置看,所葬人群应主要为当时鄣城内的居民。
小铜鼓出土于上马山M10。该墓规模较大,南北长6.1、东西宽5.2米。墓内椁长5.6、宽4.7米。椁内居中置棺,棺长约2.5、宽约0.9米。棺东侧有一边箱,西侧有两边箱,南侧已遭破坏,推测为头箱,简报称之前曾有钱币出于其内。人骨不存,从铁剑等随葬器物看,墓主头南足北。出土随葬品30余件,除小铜鼓(M 10∶32)外,主要有鼎、盒、壶、瓿、钫、罐、瓮、灶等陶器,以及铜镜、铁剑、玉璧、研石、研子和泥质印章等器物。泥印1枚,方形中空,两面分别阴刻篆文“司马息”和“司马中孺”,可能属明器。铁剑、玉璧和印章位于棺内,铜镜、研石和研子位于头箱,其余器物基本都摆放在两侧边箱内。小铜鼓发现于西侧外边箱近西南角处,出土时距墓底约35厘米,鼓面向下,鼓内保存有油脂类残渣(图一)。根据出土随葬品的组合及特征,发掘简报推定上马山M 10的年代在西汉武帝时期的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后,墓主可能为当时居住于故鄣城内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阶层[7]。

图一// 上马山M10平面图

图二// 上马山M10出土小铜鼓
二、上马山小铜鼓的特征和来源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地区一种常见铜器,使用者主要为当地少数民族。但浙江地区古代不属于铜鼓分布区,此前也从未出土过铜鼓。因此,推测上马山这面小铜鼓应非当地所产,而是由其他地方输入的器物。发掘简报根据这一发现认为该地区古代也有使用铜鼓的习俗,是不成立的。
上马山M 10出土的小铜鼓身分三段,胴部突出,腰部内收,足部外张。鼓面中央有钮的残痕。胴腰间有辫绳状扁耳4个,两两相对。鼓面饰十二芒太阳纹,芒间饰斜线纹,芒外饰锯齿纹晕圈一周,胴部及腰足交接处饰弦纹和锯齿纹,腰部饰七组竖叶脉纹。鼓高5、鼓面直径7、足径9厘米(图二;图三:1)。从整体器形看,此面小铜鼓与李伟卿先生所划分的Ⅰb式铜鼓非常相近[8]。后者也有称“石寨山型”铜鼓的,集中出土于云南滇池地区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此外在云南曲靖、文山以及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广西西部也有发现[9]。不过,目前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均为大型乐器和礼仪重器,直径和高度一般都在数十厘米以上,像上马山铜鼓这么小,且鼓面原先还有钮的,迄今未见。所以,上马山小铜鼓不大可能来自上述石寨山型铜鼓的分布区域。
除中国南方外,东南亚也是古代铜鼓的重要分布区域,特别是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和马江流域一带,出土有大量的东山文化铜鼓。东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10],与滇文化大致同时期,是当时生活在越南北部的骆越等族群所创造的一支颇具影响的青铜文化,铜鼓是其代表性铜器之一。东山文化的铜鼓形制多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石寨山型。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化中还存在不少小型化的铜鼓或铜鼓模型,它们直径和高一般仅几厘米,过去多被认为是随葬用的明器[11],甚或作为钱币使用[12]。这种小铜鼓很早即有发现,迄今已出土逾百面[13],地点遍布越南北部的很多地方,其中有些便同上马山所出小铜鼓非常相似,如河北省(今越南北宁省)嘉良县浪吟(Lãng Ngâm)遗址和河内嘉林县中妙(Trong Mầu)遗址出土的两面小铜鼓,大小、形制、纹饰与上马山小铜鼓基本一致,且鼓面都带钮[14](图三:2、3)。因此,从器物类型、风格和分布等各方面看,判断上马山小铜鼓来自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是有依据的,也是可信的。

图三// 上马山和越南北部出土的东山文化小铜鼓
三、上马山小铜鼓的传播途径及背景
上马山与东山文化区相距遥远,后者器物是如何到达当地的,值得进一步关注。有学者研究指出,上马山小铜鼓可能是骆越人作为贵重礼物馈赠给墓主人的,也可能是墓主人曾到达骆越地区而从当地直接获取的,这反映了百越内部各地间的文化交流,也说明两地越人及其后裔曾有过相同的文化习俗和潜在的文化认同关系。另外,该小铜鼓从东山文化区流落到浙江一带,是海上交通的结果[15]。这些看法无疑都很有启发性,但如果结合墓葬年代、墓主身份以及当时的历史形势等来分析,笔者认为这方面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按发掘简报,出土小铜鼓的上马山M10约属西汉武帝后期的墓葬。从随葬品的组合及特征看,该断代大体不误,特别是陶灶模型以及“昭明”和“日光”重圈铭文铜镜等器物的出土,表明墓葬年代不会早于西汉中期。这一时期,原先属越地的浙江西北部地区经战国晚期以来楚、秦、汉的先后统治,尤其是秦汉帝国大一统下民族与文化的不断融合,汉化程度已经很深。这从上马山及其附近地区的西汉墓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在埋葬方式上延续了先秦越人土墩墓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其墓葬结构、棺椁制度以及大部分随葬品却都体现了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包括一些楚文化因素)。就上马山M10来说,其汉式风格亦十分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该墓出土刻有“司马息”和“司马中孺”的印章,基本可确定墓主就是汉人。所以,如果说东山文化小铜鼓进入浙江地区与上马山M 10的墓主有直接关系的话,其所反映的已非百越内部的文化交流,而属汉帝国大一统下内地汉人与边远地区土著文化的一次接触和互动。当然,不排除该小铜鼓于较早时候传入的可能,但这种概率很小,且即便如此,也不会早很多。原因在于,东山文化中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最早可到战国末[16],甚或秦汉之际[17],而按照一般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小铜鼓的出现显然要晚于普通铜鼓,推测应当不早于西汉时期。
东山文化的小铜鼓不是普通的日用品,且目前国内仅发现一面,因此其作为贸易品流通至浙江地区的可能性极小。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这种个别物品的远距离传播,主要和人员往来有关。西汉时期,是否有骆越人到达浙江西北部,文献无考,此前亦未见这方面的考古线索。不过,当时由北方南下的汉人却很多,特别是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于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等郡,进入骆越地区的汉人也应有不少。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可能曾有故鄣一带的人到过骆越地区,后将小铜鼓带回到家乡。当然,这个人也许就是上马山M 10墓主本人。如上所述,上马山M 10规模较大,随葬品亦很丰富,发掘简报推测其墓主属故鄣城内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阶层。而按此人生活的时代,其以军人或官吏的身份到达骆越地区并在当地居留过一段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铜鼓作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特有之物,其为南下汉人收藏并被带回内地,在历史上也并不鲜见,直至清代还时有发生。如浙江温州博物馆收藏的一面灵山型铜鼓和一面北流型铜鼓,即是道光、咸丰年间当地人在广西等地做官时带回的[18]。又如山东临沂博物馆和苍山图书馆各藏有一面北流型铜鼓与麻江型铜鼓,分别为道光和乾隆年间由在广西、云南等地做官的当地人带回[19]。这里要指出的是,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下诏征南越国,“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其中一路大军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经豫章郡南下。豫章郡与丹阳郡毗邻,上马山M10的墓主是否就是此次随军进入岭南,后又前往骆越地区,亦未可知。
浙江和越南北部都属沿海地区,两地之间自然可以通过海路交通往来。据文献记载,西汉时岭南与北方地区的海上交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承担着岭南诸郡常年的“贡献转运”任务[20]。不过要说明的是,限于航海技术,当时的海上交通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经常是“风波艰阻,沉溺相系”[21]。因此,除战争、贸易以及政府大规模的物资运输外,一般的人员往来估计不会选择海路。况且,秦汉时期沟通岭南和岭北的南岭交通得到了大力开发,特别是汉武帝统一岭南以后,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壁垒被打破,南方地区的陆上交通条件较以往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南岭以及岭南地方交通网络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22]。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上马山小铜鼓经由陆路或内陆水道到达浙江地区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在某些路段,如交趾到合浦或番禺,因海上交通发达,走海路倒也不足为奇。

图四// 越南北部出土的东山文化小铜鼓
四、上马山小铜鼓反映的文化传播问题
按照一般的看法,东山文化的小铜鼓多属丧葬用的明器,但部分小铜鼓因鼓面带钮,个别鼓身内还挂舌,被一些越南学者认为是钟或铃一类的乐器[23]。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以及参观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清化省博物馆时,亦对东山文化的小铜鼓进行了观察。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制作粗糙,无纹饰或纹饰简单,有的仅有手指头般大小,应多属明器(图四:1、2)。在东山文化中,类似的小型铜质明器还有筩、盅、钺、矛等,因非实用器,大多制作粗劣。另一类制作较精致,外表多施纹饰,且鼓面一般附半环形提钮(图四:3),有的还见立体的伏蛙装饰(图四:4),应为实用的乐器。从结构看,这类小铜鼓可从顶部悬挂并通过敲击或摇晃发出声音,与钟或铃非常相似,故严格讲可视作一种鼓形的钟或铃。上马山小铜鼓显然属于后一类。不过应注意的是,在上马山墓地,这面小铜鼓出土时鼓面向下,鼓内还发现有油脂类残渣,可见其并没有被当做乐器来使用,且鼓面的钮可能在当时就已经不存。另外,从位置看,该小铜鼓发现于M 10外边箱内,与各种陶器摆放在一起,也暗示其未受到墓主及其亲属的特别重视。发掘简报认为小铜鼓在这里或用于祭祀,或属于以鼓代灯的情形,均不无可能。总之,不论被视作或用作何物,东山文化小铜鼓被带到浙江地区以后,其最初的功能、用途及文化意义没有为当地人所真正了解或接受,是可以肯定的。
越南学者郑生认为,东山文化小铜鼓在浙江地区的出现,反映了东山文化极其强大的扩散力;还有学者提出,上马山M10墓主的思想里已接触和接受了铜鼓文化[24]。而由以上分析可知,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笔者认为,作为目前发现的向北移动最远的一件东山文化器物,上马山小铜鼓对讨论东山文化的扩散或传播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由人员往来造成的个别物品的远距离移动,毕竟带有偶然性,很难对其产生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价。与其说上马山出土的小铜鼓反映了东山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及扩散力,不如说这一发现折射了当时岭南地区与内地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史实以及汉王朝统一、经略南疆过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归的历史图景。要指出的是,在南岭以北,除上马山小铜鼓外,还曾发现过一些可能属东山文化的遗物,如湖南长沙出土的人形柄铜短剑[25]以及浙江鄞县出土的羽人划船纹铜钺[26]。但这方面的发现数量很少,且均为单个小件器物,因此不难看出,它们在当地的出现与上马山小铜鼓一样,应当都和一些偶然因素有关,同时也未形成实际的文化上的影响。
由于人类交往和交通的存在,文化遗物离开其原产地而传播至其他地方或其他人群中,是考古学上一种常见的现象。正因如此,透过文化遗物的空间移动来考察当时的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在考古学研究中历来颇受重视。不过,文化遗物的空间移动有多种不同的情形,所反映的文化传播也不宜一概而论。对于安吉上马山小铜鼓这类情况,笔者认为其属于个别器物的远距离传播,且是秦汉大一统历史环境下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物品向内地的输入,应审慎评价其在文化传播或文化扩散上的意义及影响。实际上,汉武帝平南越国和开西南夷之后,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强势扩展,中国南方很多土著民族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都迅速走向衰落和消亡,它们对内地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很有限的。此外,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文化传播是有选择性的,并非所有传播出去的文化因素都能被其他社会接受或借用[27],个别物品特别是弱势文化的物品发生的流通或传播,应更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此类考古发现不重要,相反有时很值得关注,因为即便是一件蕞尔小物,也往往与某些重要的历史背景甚至历史事件有关,有必要从年代、动因、线路、途径等方面探究其背后的诸多历史信息。
(本文部分线图由李常洪重新描绘。)
[1]〔越〕郑生著、农立夫译、蒋廷瑜校:《中国浙江新发现的东山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八期,2002年。
[2]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田正标、游晓蕾:《安吉古城及上马山汉墓群的调查与发掘》,《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第49号墩汉墓》,《考古》2014年第1期。
[3]胡继根:《试论汉代土墩墓》,《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4]胡继根:《试论汉代土墩墓》,《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陈超:《汉代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5]田正标、游晓蕾:《安吉古城及上马山汉墓群的调查与发掘》,《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7]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
[8]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年第1期。
[9]童恩正:《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1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11]〔法〕V·戈鹭波著,刘雪红、杨保筠译:《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年。
[12]Olov R.T.Janse,Archea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VolumeⅢ),Bruges,1958,pp.63。
[13]〔越〕阮文好:《论东山文化青铜器的风格和特征》,《声震神州——文山铜鼓暨民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15]蒋廷瑜:《对浙江上马山小铜鼓的认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按:书中所说的东山文化A型和B型铜鼓即石寨山型铜鼓,参见同书第20页。
[17]童恩正:《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按:关于越南早期铜鼓(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该文认为,如果根据实物资料的类比,可定在秦汉之际至东汉初年;如果根据越溪船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或可早至春秋末或战国初。不过,最近有学者对越溪船棺墓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通过分析碳十四测年数据以及出土器物等,推测出土铜鼓的M2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50年之间(见雷安迪《越溪墓葬的再思考——越南发现的汉代船棺葬》,《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
[18]伍显军:《温州博物馆馆藏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九期,2004年。
[19]史红卫:《山东临沂市、苍山县馆藏铜鼓》,《考古》1986年第10期。
[20]邢丙彦:《秦汉时期北方与岭南交通的发展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21]《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6页。
[22]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4辑,2008年。
[23]Nguyễn Giang Hải and NguyễnĐình Hiển,Vềnhững chiếc trốngđồng nhỏ,Những pháthiệnmớivềkhảo cổhọc năm 1981,pp.171-173,1982;Nguyễn Việt,HàNội Thời Tiền Thăng Long,NhàXuất Bản HàNội,pp.538. 2010.
[24]蒋廷瑜:《对浙江上马山小铜鼓的认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按:人形柄铜短剑出自M1647,发掘报告称之为铜匕首;另据墓葬登记表(附表六),墓葬年代被定为战国。
[26]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按:铜钺等出土器物为开挖河道时所获,年代是否为春秋,难于判定。
[27]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295-298页。
(责任编辑:刘兴林;校对:张平凤)
The SmallBronze Drum Unearthed from theW estern Han Tomb in Shangmashan, Anji,Zhejiang Province
YANGYong
(Instituteof Archaeology,Chinese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10)
The small bronze drum unearthed from the Shangmashan cemetery in Anji,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its kind in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drum belonged to the Dongshan Culture and was brought into China from northern Vietnam.The M 10,from which the drum was unearthed,was identified as dating to themiddleWestern Han.Itwas believed that the tomb owner ob⁃tained this drum from his trip in northern Vietnam’s Jiaozhi and Jiuzhen and brought it back to China.The drum is not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within the Baiyue territory, buta reflection of the close contact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between the Lingnan and the inland regions un⁃d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Han empire.
Shangmashan cemetery;smallbronze drum;Dongshan Culture;Western Han
K871.41;K876.41
:A
2016-06-10
杨勇(197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考古、西南考古、手工业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