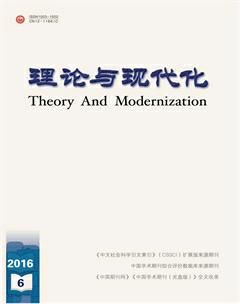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策略探讨
杨龙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不能完全沿用以往的区域战略推进方式。其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任务艰巨,涉及面广,需要更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在社会中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需要新的思路,即区分首都功能和北京定位,分别维持中央政府行政区和发展适合北京的城市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还需要在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专门的派出机构,以提高执行力,确定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政治合法性;首都功能;协调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14-07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通过一年多了,三地分别推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规划纲要》属于区域政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进。由于协同发展涉及大量跨行政区的活动和事务,在其启动的初期,还需要借助政治合法性的“势能”来推动,并且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三地的协调性发展仅靠政府的推动无法实现,还需要动员起各种社会力量,需要民众广泛地参与。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既是重中之重,也是难啃的“骨头” ,不妨从区分首都功能和北京的城市定位入手,中央行政区和北京市分别发展。
一、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创造软环境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一年多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已经在若干领域铺开,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限制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发展,搬迁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通过政策鼓励和刺激非首都功能下的企业离开北京市区。由于搬迁涉及到机构或企业的整体搬出、人员的再就业、家庭的重新安置等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政府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企业或个人,是一项艰难的选择。为了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顺利进行,需要充分的动员,以便形成搬迁的政治合法性和广泛的共识。
1.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提供政治合法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战略,涉及国家的核心区域——京畿地区,跨二个直辖市和一个省,跨行政区协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是瞄准建成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增长极、世界级城市群等重大战略目标。要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实现这种高规格的区域化,沿用原有的地方间自发合作的方式难以完成,而是需要借助中央政府较深的介入和直接推进。尽管中央政府可以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三地的合作,但是毕竟中央地方有职能分工,如果直接介入地方行政过程,还是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区域战略时候,中央政府的介入以项目为导向,根据项目的需要协调不同的地方政府,协调的内容主要是项目带来的利益如何在相关的地方之间分配,所以区域合作基本上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京津冀协同发展以问题为导向,把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作为首要任务,需要津冀两地配合北京。首先,为了承接北京疏解出来的企业、机构、人员,天津和河北的相关地方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生活设施的建设等等,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使用宝贵的土地资源。其次,天津和河北必须修改原有的规划,而修改规划是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牵扯面大,是艰巨的任务。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需要津冀的付出,而不是直接从中受益,这两个与北京平级的省级政府服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仅靠行政命令和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而是要提高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因此,需要为北京的城市功能疏解建立政治合法性。
北京城市功能的疏解必须通过搬迁,要把众多企业、机构、人员搬出目前国内福利最高,文化教育和医疗条件最好的大城市之一,其动员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初期的搬迁以行政方式为主,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文化团体,行政性和事业性机构、企业总部等的迁出,都需要以政治动员开路。一般性产业的迁出、区域性专业市场的搬出涉及大量人员的生计,动员和组织势必面临困难。完成如此规模大、涉及面广的搬迁工作,市场机制难以奏效,也需要各方树立大局意识,以政治合法性作为搬迁动员的依据。
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政治合法性还可以来自国家安全的考虑。从国家的安全出发,首都的城市功能应该尽量简单,人口不宜过多,市内交通应该随时保持通畅,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中枢能够反应及时,运转正常。一旦明确了首都的这些安全需要,不但天津和河北可以无条件配合,其他地方政府也必须配合,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将会较为顺利。
实现公平也是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由于河北与北京的发展差距悬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河北迫切盼望的事情。北京的搬迁工作如果从缩小北京与天津,特别是与河北的发展差距出发,可以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的选点以帮助京外地方的发展为目的,比如,把北京的产业搬迁与消除河北的“环首都贫困带”结合起来,缩小北京与天津及河北公共福利供给上的差距等,既可以疏解北京的过重城市负担,又可以帮助周边地区的发展。这种双赢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搬出北京人员的迁移,而且能够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并且可以进一步塑造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治合法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的前期以行政手段为主,主要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强力推进协调发展,只能通过中央的安排,借助来自中央的政治“势能”。确立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政治合法性以后,可以大大节省三地合作的协商成本,也可以节省推动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说服成本。
2.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立共识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是从经济发达、各类优质资源集中的首都向外搬迁,除了提出搬迁的政治理由,还需要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形成关于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共识。尽管京津冀三地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但目前也暴露出过于强调政府推动和‘从上到下的执行,‘从下到上的问题反映和解决渠道较弱、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等问题。”[1]
搬迁共识的形成需要公开的讨论和耐心的说服,例如韩国首都圈城市功能的疏解从1970年代就开始了,直到2015年才完成世宗市的搬迁工作,历时近45年,从朴正熙到李明博,经历了多届总统和政党轮替。从部分中央政府部门分流到果川市到最终国务院向世宗市搬迁,期间多种方案提出,经过反复论证,多次修改,面对各种反对意见,甚至经历了违宪审查[2]。在这个漫长的争论和修订过程,韩国朝野以及地方与中央在首都城市功能疏解和城市搬迁工作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为向行政中心复合中心城市的搬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动员。
京津冀三地行政平级,互不隶属,企业、事业单位、居民也处于不同的政策辖制和引导下。这三个省级政府的规模大,下辖的部门多,下级政府也多,三地间任何一项共同行动都远比在本省或本部门范围内的单独行动困难。这三个省级政府,以及下属的市、区、县,都有自己的利益,各自的权限也在自己的行政辖区之内,合作或利他的行动无法自发形成。此次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力度空前,但也没有直接介入地方合作的具体事项。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但具体执行需要各个地方政府、各地的企业和民间的自发行动。京津冀范围内的地方合作除了中央或上级的安排之外,还要依靠三地的企业和民间形成关于合作的共识。北京城市功能疏解涉及搬迁,下级政府和地方的社会及民众形成此项“大工程”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各地各界在疏解北京城市功能上达成共识,会减少搬迁的阻力,降低执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成本。
目前三地合作的依据是《规划纲要》,而《规划纲要》2015年4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但是一直没有全文公布,只是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2015年8月25日《人民日报》上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介绍了《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总体目标和要点。相比之下,目前已经出台的其他国家级的区域发展规划都已经全文公布了。《规划纲要》没有全文公布给坊间的各种猜测留下了空间,其中有可能出现负面的猜测。猜测者往往依据个体了解的信息,依据自己的知识,出于自己的利益,所以猜测非常不利于共识的形成。另外,政务公开与政府公信度是正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猜测还可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深化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对问题的充分认识。
为了对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形成共识,本文建议适时公开《规划纲要》全部的内容,或至少在比目前更大范围内公开,配以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三地民众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规划纲要》的了解越多,越有利于共识的达成。建议加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宣传力度,并且允许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展开争论。争论是形成共识的重要途径,通过争论,可以让各方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对于搬迁涉及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有足够的信任,该知情的应该并让其知情,这样便于就搬迁达成共识。
二、区分首都功能和北京城市功能
在确定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基本思路以后,在疏解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非首都功能,学界不同的理解[3]23。对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解也有分歧,比如是不是所有行业的科技创新中心都在北京,是不是所有的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就有不同的看法。据此,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北京的城市定位和首都功能,对北京的四个定位里只有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属于首都功能,其他两个属于北京的城市定位[3]24-25。对北京城市功能的界定是以北京得自首都的集聚效应而多年累积下来的城市形态和产业格局,比如,文化中心是千百年来作为帝都的文化积累的结果。科技创新中心是由于北京集中了大部分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大部分最好的高等院校,结果北京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集散地,北京技术交易成交额2014年占全国的36.6%[4]。根据以上的分析,目前北京的城市定位并非纯粹的首都功能,因此在如何维持其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时候,会遇到定位不清或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而且由于此两项功能存有争议,也有可能导致对其他非首都功能的认识不清,从而影响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1.设立“中央特区”或“国家行政中心区”
沿着区分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功能的思路,应该把北京城市定位中的纯首都功能与北京的功能分开,划定区域范围,设立中央特区或国家行政中心区,只承担首都的城市功能,作为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由中央财政供养。中央特区直属中央政府,其城市功能有别于一般城市,没有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其运行由中央财政负担,即有别于普通地方财政的“首都财政”。“首都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需要通过设立唯一性的特殊行政区方式,由国家最高政府来直接管辖,重点履行和发挥政治行政管理职能。”[5]实际上在北京属于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机构和部门在区位上也相对集中,因此具备了划定中央行政中心区的空间基础。
中央特区之外的部分作为北京市,其仍作为地方政府,保留适合京畿地区的产业结构,比如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等。由于历史的积淀,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过多削减城市功能会导致基础设施等城市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把中央政府与北京市在区划上分开更合理。目前北京的四项功能里除了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之外的两项非首都功能由北京市承担,科技创新中心并非首都的核心功能,而是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功能,“北京的‘四个定位中的文化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并非必然是首都功能,因而这两个方面的部分功能也可能被列为非首都功能之列。”[3]24实际上北京市政府的迁出已经在进行了,按照《规划纲要》,已经开始在通州建立行政副中心城市,北京市政府很快会搬出。北京的发展重心外移,反过来可以为中央政府保留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
2.大力发展适合北京的城市功能
剥离了首都功能以后,北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适合于自身的产业。北京不能因为城市功能的疏解而衰落,作为特大型城市,北京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好,服务业尤其发达,这个基础必须利用好。按照《规划纲要》的安排,北京要努力维持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但是面临其他地方的竞争和挑战。在政府不断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市场和社会得到更多的自主性,地方政府也得到中央的进一步授权,科技的发展在空间上走向多极化是天然趋势,所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并非高枕无忧。随着非首都功能的转移,支撑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势必有所削弱,将直接威胁到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随着制造业撤出北京,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总部也会搬离北京,也会削弱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条件。再加上北京城市的生存空间严重饱和,严重的大城市病使得北京的生存环境恶化,生活成本畸高。那些对生存质量要求较高,同时又是工薪阶层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外地有适当的鼓励措施,他们很可能选择离开北京。
为此,北京在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时候不能“一刀切”,不能把服务业和制造业都迁出北京,而是要保留必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保持居民的生活质量[3]25与此同时,北京应该大力发展与高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高端服务业,以及与科研相关的制造业,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服务。
北京集中精力强化适合自己的城市功能以后,也便于与天津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真正发挥“双城”在京津冀区域的带动作用。比如,科技创新活动需要金融服务业,但是北京没有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城市定位,而天津的定位只有“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尽管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设在北京,国内和国际大金融机构的总部也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城市定位没有金融管理功能,天津又不可能形成金融管理中心,所以在京津冀没有形成运营和监管一体的金融中心[6]。这种分散的产业分布不利于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也不利于实现把京津冀建成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增长极、世界级城市群这样重大的任务。可见,通过区分首都和北京,给北京发展自身城市功能的空间,不仅有利于维持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也可以促进津冀与北京在产业方面的合作,并且实现合理的功能分工。
剥离了非首都功能以后,还可以为北京减负。多年来北京作为首都,负有“四个服务任务”,即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服务。仅第一类中央机关的数量,截止2010年有中共中央机关57个,国家机构1940个,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33个,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2067个。仅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31.8万,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7]。为了完成这四项服务任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金方面,除了从中央政府得到财政转移支付,主要靠北京自身的财政收入。北京城市经济的效率一直不高,与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第一的上海相比,上海仅用了北京的1/3左右的城区面积①。如果首都功能交给“中央特区”或“国家行政中心区”,中央部门和相关人口的公共服务等由中央财政支付,北京不再担负直接服务中央的任务,北京可以“轻装前进”,可以像其他地方政府一样,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产业,与上海等城市竞争。所以区分首都功能与北京的城市定位,是一件对中央和北京“双赢”的安排。
三、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常设机构
为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实现协同发展,中央为京津冀分别规定了新的发展定位,三地各自的四个新定位与自身以前的发展定位差别较大,三地都已经重新制定了发展规划②。规划只是规定了地方发展的总体格局和方向,至于如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相协调,如何执行《规划纲要》还需要各地的各部门制订具体方案,其中涉及大量的相互沟通和协调等工作,目前有了领导机制,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但是还需要建立专门的执行机构。
1.充分利用既有的行政系统
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了现有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程序。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规划纲要》以后,当年年底之前三地专门召开地方党委全会,制订了本地落实《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按照《规划纲要》的任务和时间表,把任务分解到省级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下属各级地方政府,各级下属政府再把任务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成为各部门自身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使用通常的行政方式,利用现有的行政程序,在国内是最为有效的执行方式。
从三地的情况看,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转移升级三个重点领域都已经取得进展。这些进展得益于在既有行政层级和部门的坚决贯彻,例如,北京市根据《规划纲要》在2020年总人口不超过2300万的要求,把人口总量控制的指标逐年分解,下到16个区。起初各单位的压力“山大”,感觉任务的难度很大,由于把任务执行情况落实在干部年度考核中,2015年各区都完成了年度人口调控指标[8]。
2.设置专门的执行机构
三地的协同发展还有大量的协调事务,需要三地与其他行政区的政府部门就某项共同的任务或某项事务进行衔接和协商。这些任务不在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能之内,也不是必须的行政程序,通常是经由专门的机构或固定的机制,定期或不定期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工作衔接或事务协商。因此需要执行过程中设立固定的对接机制,“有关中央部门、三地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共同参与的日常沟通、议事决策和执行协调机制,及时传达中央精神、反映地方诉求、共同研究决策、协调解决难题……。”[9]
目前京津冀间的领导和协调机制是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议事协调与决策机构,该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的一些部委也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如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分别成立了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领导小组、京津冀协同发展税务工作领导小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由京、津、冀、晋、蒙、鲁和国家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住建部、气象局和能源局共七省八部委组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第一个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战略,其领导小组应该比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等区域发展战略领导机制具有更多的行政权力,能够对共同事宜进行统一调度和规划,有足够的政策能量引导三地的合作。但是作为一种议事协调机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不是常设机构,其成员均为兼职,其精力不可能集中于京津冀事务,而且政策执行还要依赖于三地政府,领导小组体制难以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期解决方案[10]。通常领导小组会议不定期开,其工作有间歇性,只有到了有相应工作需要的时候,才“动”起来。“领导小组”是“特殊类型的组织,以专门负责较为重要、但已有的工作部门不适合或无力承担的新型和交叉型事务。这些对常设性的组织部门起着备用性作用。”[11]而实际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日常性事务,其工作性质是协调国务院部委,协调省级政府,所以适合于设立专门机构。再有,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属于归口管理,行政级别低于三省市,难以有效协调三地的共同行动③。
因此,需要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常设性机构,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负责执行协同发展的规划,处理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跨行政区问题。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执行某项特定的任务,从中央政府得到授权。派出机构可以在不改变派出它的机关规定原则的条件下,灵活处理有关事宜[12]。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下设的常设机构可以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从国务院得到授权,执行京津冀合作或一体化事务,这类区域管理机构是“一个具有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协调机构,但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政府机构,只为解决跨行政区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区域问题而设立。”[13]
此外,还需要设立专门的推进机构,负责协同发展具体项目或领域的推进工作。这里可以参考的经验是韩国,韩国在中央行政机关向新行政首都世宗市搬迁过程中设立的专门的组织,主要有三个:世宗特别自治市支援委员会、世宗特别自治市支援团和世宗特别自治市启动准备团。这三个组织都是新设组织,负责协调和处理搬迁事宜。由于搬迁没有依托已有的政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扯皮可能,特别是韩国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政府间并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如果搬迁工作依托于已有政府组织,将产生诸多的冲突,从而降低搬迁的效率。其中的支援委员会设在总理室下,总理兼任委员长,具有权威性,其在协调和处理相关问题时能超脱于一般的政府间利益 ④。
我国可以考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分支部门,负责协同发展项目的推进、评估、监督,负责协调三地之间的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等事宜。由于此类机构及其部门的职能定位于实现协同发展,任务明确,权力边界清晰,有利于协同发展具体事项的落实。三地既有的政府部门也可以集中精力于分解到本部门的协同发展任务,它们的执行情况通过本行政系统来考核,也有利于协同发展任务的落实。
由于京津冀多年来分立,各自封闭,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所以《规划纲要》启动期的协同发展主要靠政府推动,企业和民间自发的参与还不够。“目前一些措施的落实,还是靠行政的办法,不管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相对收紧,还是我们现在一些产业协同发展的安排,还是交通方面,都还是以行政的方式,而在真正创造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差距还是很大。”[14]经过进一步的动员,协同发展的精神深入三地的民心,民间的力量得以调动以后,加上北京的城市定位进一步明确,为特有的产业发展留有充分的空间,均可以使得协同发展的潜力得以进一步的发挥。
注释:
①北京的面积1.7万平方公里,上海的面积6430平方公里,上海下辖16区1县,北京下辖14区2县1个经济开发区。(以上数据截止2014年10月)。
② 三地的定位为:北京,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③国家发改委有协调区域问题的职能,设有几个专门的司负责,如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
④见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建设厅网站(www.macc.go.kr)
参考文献:
[1]宣晓伟.区域协调:京津冀一体化的意义与困难[J].改革内参,2016(2):21.
[2]〔韩〕李志京.国土均衡发展和地方分权的战略:以世宗市原案和修正案的争论点位中心”[J].法政评论,第27卷(1).
[3] 张可云.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本质与疏解方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3):23.
[4] 童曙泉.北京技术合同年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J].北京日报,2015-03-11.
[5]陶希东.我国首都圈跨行政区治理模式构想[J].改革内参,2016(2):37.
[6] 邢元敏,薛进文,龚克.新时期京津“双城记”——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334-336.
[7] 天津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借重首都资源[M].天津:天津人民政府研究室,2013.
[8]人民日报[N].2016-02-18(5)
[9] 崔向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J].改革内参,2016(2):30.
[10] 孙兵,等.京津冀区域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J].改革内参,2016(2):7.
[11] 周望.“领导小组”如何领导[J].理论与改革,2015(1):98.
[1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282.
[13] 肖金成,等.优化国土空间开放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360.
[14]张军扩.权威专家谈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与建议[J].改革内参,2016(2):22.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s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and it cannot continue to use the old way of regional promotion strategy completely. The relief of the capital city function of Beijing is a difficult task. It is widely involved and needs stronger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needs to get a more broad consensus in society. Relieving the capital city function of Beijing needs new ideas, such a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and the position of Beijing ,to mainta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o develop the suitable urban function of Beijing respectively. The promo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lso needs a leading group to set up special local agency to improve the execution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the committee of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