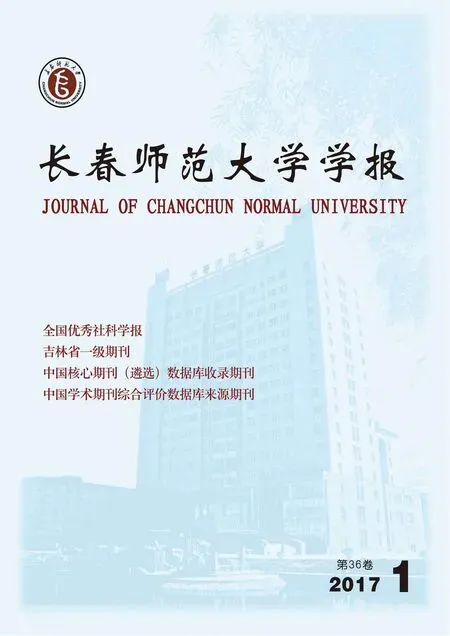《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
刘思诚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
刘思诚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我国民间文艺搜集工作能够延续延安文艺注重搜集和学习民间文艺的传统,抢救了一批宝贵的民族民间文艺遗产;在新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推广了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推广方面积累了蒙汉合作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新文艺的建设。
《东蒙民歌选》;民间文学;搜集史;蒙汉合作
《东蒙民歌选》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新中国初期我国民歌搜集工作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使用文献法和田野作业法,搜集了《东蒙民歌选》的四个完整版本,并以此为基础,从延安文艺搜集传统与新文艺搜集政策、推广难题与工作方法两方面,介绍和讨论了《东蒙民歌选》搜集与推广工作的意义和经验。
一、版本关联与文艺地位
(一)四个版本的先后关联
新中国初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各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和出版工作,成果丰硕[1]111。《东蒙民歌选》是这一时期我国民歌搜集工作的代表作之一。笔者先后于2014年2月14日、2015年1月2日和2015年2月2日,在北京对搜集者许直先生进行了三次田野访谈;又于2015年2月5日,在呼和浩特对翻译者胡尔查先生进行了田野访谈。结合文献法和田野作业法,笔者搜集的《东蒙民歌选》的四个版本如表1。

表1 《东蒙民歌选》的四个版本信息及来源一览表
《内蒙民歌》(油印本)这一珍贵版本,是笔者在对重要当事人——《东蒙民歌选》的记录者、编者许直先生的田野访谈时搜集到的。其余三种版本来自于文献搜集。
《内蒙民歌》收录了105首民歌,是手写体油印本。它记录了民歌的曲谱、蒙语歌词的汉字谐音、传统蒙文歌词和汉文译文。许直指出,它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但它是《蒙古民歌集》的雏形。
《蒙古民歌集》收录了156首民歌,是正式的印刷本[2]。它记录了民歌的曲谱、新蒙文歌词、传统蒙文歌词和汉文译文。《蒙古民歌集》还补充了大量的注释,使其带有研究性质。许直指出,勇夫和安波都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出版《蒙古民歌集》就是第一次文代会的决定,安波安排许直和胡尔查去内蒙古日报社落实出版工作[2]。胡尔查指出,安波写了一封介绍信,许直和胡尔查来到乌兰浩特,把介绍信交给内蒙古共产党东部区工作委员会王铎书记,他们被安排在内蒙古文工团住宿,在内蒙古日报社编排《蒙古民歌集》。曲子、新旧蒙文歌词和汉文四种样式的文字排版在一起有难度。
《东蒙民歌选》收录了85首民歌,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丛书之一[3]。《东蒙民歌选》分为歌词和歌曲两个部分,两部分都拿掉了蒙文。歌词部分由汉语歌词和注释构成,突出了民歌的文学、文化价值;歌曲部分由曲谱和汉语歌词对应构成,使蒙古民歌转化成了能够用汉语传唱的蒙古民歌。关于《东蒙民歌选》收录的民歌来源,安波在《东蒙民歌选》的《编后记》中指出:“现在本集中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选自东北文协文工团出的本子,有一些是未发表过的,有一些是选自内蒙文工团油印出版的‘蒙古民歌集’。”[3]333可见,《东蒙民歌选》是在《内蒙民歌》(油印本)和《蒙古民歌集》搜集民歌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未发表的作品,还吸收了内蒙古文工团搜集的部分成果。
《内蒙东部区民歌选》收录了84首民歌,是1952年版《东蒙民歌选》的第三次印刷本[4]。《内蒙东部区民歌选》与《东蒙民歌选》基本上是一致的,《内蒙东部区民歌选》删掉了在《东蒙民歌选》中作为附加内容的《内蒙古解放歌》;而最大的改变是作品选名称的改变,即由“东蒙”变成了“内蒙古东部区”。
(二)两个版本的文艺地位
这四个版本,尤其是《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具有较高的文艺地位。1950年初,文艺家严辰在《文艺报》上发表《读<蒙古民歌集>》,高度评价了《蒙古民歌集》[5]。1950年,音乐家安波在《民间文艺集刊》发表了《谈蒙古民歌》,热情地介绍了接触和搜集蒙古民歌的历程,阐释了蒙古民歌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和民俗文化等内容[6]。1950年,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钟敬文在《一年来的新民间文艺学活动》中特别指出:“在这种出版物中比较优秀的,要算去年11月出版的、安波编辑的《蒙古民歌集》。这不但是介绍我们兄弟民族(蒙古族)民歌的第一个集子,而且就它的数量或质量看,也都是值得我们称许的。”[7]《蒙古民歌集》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了一套民间文学丛书,以期在全国推广。出版的第一本是何其芳、张松如(公木)编的《陕北民歌选》[8],第二本就是安波、许直合编的《东蒙民歌选》。可见,《东蒙民歌选》这一版本当时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
二、延安文艺搜集传统与新文艺搜集政策
(一)延安文艺搜集传统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描述了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工作的情况:
在解放区,各文化单位搜集、油印了许多流传于人民中的抗日歌谣和其他革命歌谣,并进行了推广,使这些作品在动员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大规模地开展了起来。[1]4
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深远,形成了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搜集和学习民间文艺作品,改编和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工作传统。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鲁艺是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汇聚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家,培养了大批的抗战文艺人才,发挥了打击敌人和凝聚革命力量的宣传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需要,部分延安文艺干部来到东北。1947年,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联大鲁艺”)成立。它按照延安鲁艺的模式进行建设,承担着培养革命文艺干部和培训文艺宣传队的职责。它具有战时性质,抢救了一部分珍贵的文艺遗产,培养了包括少数民族文艺干部在内的三期学员,为新文艺的建设储备了人才。《东蒙民歌选》中的多数民歌是这一时期在联大鲁艺院长安波的号召下,由许直记录、胡尔查翻译而保留下来的。安波、许直和胡尔查这三位当事人都深受延安文艺思想的影响,搜集工作延续了延安文艺的搜集传统。
安波是延安文艺干部。据其回忆,在延安时期,吕骥和刘炽先后采集过蒙古民歌,使安波有机会接触蒙古民歌资料,萌生了采集蒙古民歌的兴趣,1945年日本投降后,安波在下乡时期搜集过七八十首蒙古民歌[2]3。1946年,安波到热河喀喇沁右旗这一蒙汉杂居区帮助群众做翻身工作,搜集了四十几首,其他同志也记了一些。在联大鲁艺,七八十位能唱民歌的蒙古族同学的到来,成为安波等人搜集蒙古民歌的契机[3]331。吕骥认为,安波在冀察热辽时期从事内蒙古民歌的收集研究工作,体现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重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向民间音乐遗产学习的重要意义[9]。许直也高度评价安波的音乐创作,认为其音乐语言具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和简单易学的特点,创作的歌曲在士兵和群众中广为流传;安波还引入了延安的音乐创造,如上滑音、下滑音,自己还有散板等音乐体裁的创造。
许直和胡尔查在革命工作中,在联大鲁艺充分濡染了延安文艺精神,能够认识到搜集和学习民间文艺的意义。
许直是北平艺专音乐系的第一期学生,曾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秘密奔赴冀察热辽解放区参加革命,在解放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土改,体验群众生活,后来被分到了联大鲁艺,成为戏音系教员。许直深切地回忆,1948年6月30日是自己见到安波的日子,记住这个日子比记住自己的生日还重要。安波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对自己的影响特别大。1950年,许直在《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中指出:
我开始记录民歌是很偶然的。那是四八年的十月间,在热河名“那拉必鲁”的一个村子里,——冀察热辽联大鲁艺的短训班所在地——在短训班里有五六十个蒙古同学,他们来自东蒙各处,一直到最北的达古尔蒙古。先是有位同志用四胡拉蒙古小曲,我觉得很动听,便随意的记录了一些,那知随着记录其他的同志便纵情的唱起来,这时我才了解到这些同志虽是文艺工作者,但却与汉人中生长在城市里的文艺工作者不同,他们是熟知自己的民歌、民间故事,以及民间习俗的,不但会唱很多民歌而且能源源本本的把有关于民歌的故事,产生的地点,以及最初的创作者,加以详细的说明。[3]324-325
许直采集蒙古民歌的缘起是被蒙古族同学演奏的音乐吸引。许直具有较好的音乐素养,偶然的记录过程中却认识到了蒙古民歌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认识到这些蒙古同学是宝贵民歌遗产的真正传承人。
胡尔查在参加联大鲁艺之前,接受过东北抗日军政大学的短期培训,客观上已经是民族干部的储备人才。毕业后,17岁的胡尔查就被任命为土改工作团组长之一,后来成为联大鲁艺的第二期学员。胡尔查近距离接触了延安文艺干部,如赵毅敏、安波和罗文,受到延安文艺精神的熏陶。
(二)新文艺搜集政策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具备大规模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条件。勇夫将内蒙民歌得以搜集的原因归为两点:一是内蒙地区流传着丰富的民歌,具有深远的民族音乐传统,二是中共领导下的新内蒙的文化政策重视和扶植人民的文化。[2]1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周恩来在《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文艺的“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全局观念问题”和“组织问题”,并指出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大团结、大会师”[10]。这六个问题明确了新文艺的方针和政策,即要有全局观念,统筹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文艺工作;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深入群众生活;团结广大旧艺人,改造旧文艺等。
许直指出,出版《蒙古民歌集》是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决定。安波、勇夫参加完文代会,就安排许直、胡尔查出版《蒙古民歌集》。1949年11月,《蒙古民歌集》出版,很仓促,但体现了国家对这批蒙古民歌的重视和扶持。安波写信给内蒙古东部区党委联系出版工作,党委书记王铎、内蒙古日报社社长勇夫、编辑额尔敦陶克陶及那森巧克图、内蒙古画报社社长尹瘦石等人,都为《蒙古民歌集》的出版做出了贡献。总之,《蒙古民歌集》的出版体现了新文艺方针、政策对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视。
许直强调,《蒙古民歌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忠实地记录和保护了这批蒙古民歌的原始资料。《东蒙民歌选》收入的民歌是精华,是优秀的,以推广为目的。《蒙古民歌集》中的《秃子》版本,最后两段涉及“睡觉”的部分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2]153-156;但在《东蒙民歌选》中的《秃子》版本中,这两段就被删掉了。[3]153-156许直认为作为搜集资料,这部分内容也不是糟粕,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不能绝对地评判它。在新文艺搜集政策的观点里,这部分内容是应该接受改造的旧文艺。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全国的民间文艺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会上,周扬指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11]2郭沫若指出成立民研会的研究目的是“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民间文艺”[11]5-6。
安波在《东蒙民歌选》的《编后记》中指出:“今年六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给我以任务,要我重新加以编选,并编成汉文歌词,配上曲调。”[3]332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织下,《东蒙民歌选》经过部分改编,成为反映蒙古人民生活、保存珍贵民歌遗产、符合新文艺政策的全国性民歌范本。
三、推广难题与工作方法
(一)翻译难题与蒙汉合作
少数民族民歌的推广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翻译。这种难题是语言上的,是艺术形式上的,也是民俗文化上的。
对于语言翻译的困难,安波在《东蒙民歌选》的《编后记》中指出蒙文和汉文在语系上的差异,其语词结构和表达翻译起来非常艰难。汉文译文与蒙文原文不能完全对应。[3]332许直、胡尔查在《蒙古民歌集》的《关于采译本集民歌的几说点明》中介绍了翻译蒙古民歌的困难和方法。
关于本集民歌的翻译方法,为了使汉人研究民歌的同志能比较直接的理解蒙古民歌的内容,除遇有特殊困难时,一般都以直译为主,但有时在汉人生活里找不出适当的语句,(比如蒙古话形容马的走法就有十几种,在汉词中只有几种)也只得用近似的词句代替。[2]7
以上文字指出《蒙古民歌集》的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但在蒙汉词语对译的过程中有时出现难以找到对应表达的不平衡现象。
关于搜集少数民族民歌的方法,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指出:
1949年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亲密合作,大规模地搜集整理了大量优秀的民歌、故事,打开了少数民族灿烂夺目的民间文学宝库,极大地推动了各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1]74
以上文字介绍的开展少数民族民歌搜集工作的方法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合作搜集。
安波在《<蒙古民歌集>出版感言》中指出:
就在这一时期,许直同志与胡尔查同志亲密合作,记录了二百余首民歌,他们整理、抄写、翻译,前后经过了半年之久,到现在总算完成了初步的工作。[2]4
搜集蒙古民歌需要汉族和蒙古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许直精通音乐和汉文,胡尔查兼通汉文和蒙文,二人的通力合作使得记录、整理和翻译蒙古民歌的词曲,进而编纂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民歌集《蒙古民歌集》成为可能。除此,还有汉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安波的指导,蒙古族文艺工作者勇夫、那森巧克图、额尔敦·陶克陶,[3]331-332奇木德道尔基、奥德斯尔、叶贺、奇哈拉哥等人的翻译意见。[2]8
谈到《东蒙民歌选》的翻译工作时,安波将《东蒙民歌选》的出版首先归功于许直“热情而专心的劳动(包括选材、编词、配歌、抄写等工作)”[3]332,其次归功于胡尔查提供的材料和翻译工作,还有鲁艺同学扎木苏的口译和民歌背景的介绍。[3]333这种蒙汉合作搜集和翻译的工作模式,对少数民族文艺的搜集与推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涉及蒙古民歌艺术形式和民俗文化的翻译是更大的难题,更需要采取蒙汉合作的方式。安波在《谈蒙古民歌》(代序)指出:
由于语言的要求,构成蒙古诗歌最显著的特征是用韵的不同。它不同于汉文只要脚韵,而是除了脚韵之外,还用“头韵”与“半谐音”。……所以蒙古民歌歌唱起来立即会感到词的音韵之美,这是译成汉文后所不能弥补的损失。[3]8
这是安波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出的经验。蒙古民歌语言与韵律密切联系,翻译成汉文后,蒙语的一些艺术表达则很难传达。
安波曾谈到自己在翻译蒙古民歌中的一些做法。他指出,当提到蒙古族的民间歌手、说唱艺人等名称时,采用保留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在后面用括号注明汉语对应称谓的方法,如“道亲”(即民间歌手)、“郝什切”(即说唱艺人)、“脱利齐”(歌手名)。在蒙古族的民俗观念中,民间歌手等称号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在东蒙现今,‘道亲’(即民间歌手)与‘郝什切’(即说唱艺人)仍是最受尊敬的人。据说,在西北蒙古奥伊拉特族中的职业歌手多系世袭的贵族出身,‘脱利齐’(歌手名)是最辉煌的称号……”。[3]1在提到蒙古民歌体裁时,采用保留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并加以解释的方法,如“图林道”“育林道”。“前者是在庄重严肃的场合唱的,后者则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唱的”[3]2。歌手的称谓在汉语中没有类似情感的用语,民歌的名称在汉语中也没有对应类型的用语。蒙古族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民歌、说唱在蒙古族的日常、节日和仪式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文化注释,能够弥补蒙汉对译过程中民族特殊民俗情感的缺失。
(二)传唱难题与改编配歌
少数民族民歌的推广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传唱,这对汉语歌词和配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许直在《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中,谈到蒙古族民歌语言的翻译问题,是从理解和学唱蒙古族民歌的角度提出的。他主张“把蒙古歌词变成汉文歌词”,这样虽然削弱了蒙古民歌的美,但在思想情感和艺术体验上带给人更深入的理解。[3]328-329这是许直在搜集和学习蒙古民歌过程中的经验之谈。某种程度上讲,将蒙文译为汉文是很必要的,这有利于蒙古民歌思想情感的传达,有利于各民族民歌的交流。同时,我们要深入理解蒙古民歌,学习语言学、音韵学,力求更好地展现出蒙古民歌的魅力。
把蒙语歌词变成汉语歌词,并与蒙古民歌的曲子融为一体是困难的。但不解决这一难题,就不能实现蒙古民歌的汉语传唱问题,就不能在全国推广。
贾芝在《记民间文学萌芽时代的浇灌者》中指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安波、许直合编《东蒙民歌选》就是选题之一[12]72。安波指出,在《东蒙民歌选》的编辑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除了我日常工作的繁杂之外,还因为,(一)我是不懂蒙文的,对于内蒙民歌的认识亦只是一知半解。(二)翻译可唱的歌词本来就是很难的,又配上原来的曲调更是难而又难。因为蒙文与汉文根本隶属的语系就不同,有许多句子由蒙文口译而加以意会觉到甚美,但一经译成汉文,就觉得十分蹩脚了。而且句子的长短与汉文同一意义的句子就相差甚远,一般是两段蒙词才能译成一段汉词,但有时既不够一句,比半句又多,真是麻烦得很。[3]332
安波指出蒙文和汉文在语系上的差异,其语词结构和表达翻译起来非常艰难。汉文译文与蒙文原文不能完全对应,使之与原有曲调相配更增添了歌词的翻译难度。贾芝是积极整合延安时期培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他指出安波曾到民研会与他一起商定《东蒙民歌选》中几首民歌的译文问题,反复推敲,以便入乐。[12]74
《东蒙民歌选》是用汉文歌词传唱的蒙古民歌,通过改编配歌,突破了《蒙古民歌集》不能用汉语演唱的局限,有利于蒙古族民歌在全国的推广。推广《东蒙民歌选》,可以使更多人在思想上了解蒙古人民在旧社会经受的苦难,在艺术上领略蒙古族“天籁”的音乐魅力,在民俗文化上增进对蒙古族民俗观念和民俗活动的理解。
总之,《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我国民间文艺搜集工作能够延续延安文艺注重搜集和学习民间文艺的传统,抢救了一批宝贵的民族民间文艺遗产;在新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推广了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推广方面,积累了蒙汉合作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新文艺的建设。
[注 释]
①被访谈人:许直,男,1927年生,指挥家、音乐家,《蒙古民歌集》搜集者,《东蒙民歌选》编者。访谈人:刘思诚。访谈时间:2014年2月14日。访谈地点:北京许直家中。录音样本整理:刘思诚。
被访谈人:许直。主访人:董晓萍。访谈助手:刘思诚、徐令缘、高磊、鄢丽娜、黄美玲。访谈时间:2015年1月2日。访谈地点:北京许直家中。录音样本整理:刘思诚。
被访谈人:许直。主访人:董晓萍。访谈助手:刘思诚、王文超。访谈时间:2015年2月2日。访谈地点:北京许直家中。录音样本整理:刘思诚。
被访谈人:胡尔查,男,1930年生,蒙古族,民间文学家、翻译家,《蒙古民歌集》汉译者。主访人:董晓萍。访谈助手:刘思诚、王文超。访谈时间:2015年2月5日。访谈地点:呼和浩特胡尔查家中。录音样本整理:刘思诚。
②“《东蒙民歌选》的四个版本信息及来源一览表”,制表人:刘思诚,制表时间:2015年4月10日。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东北文协文工团.蒙古民歌集(蒙汉文双语)[M].乌兰浩特:内蒙古日报出版发行部,1949.
[3]安波,许直.东蒙民歌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4]安波,许直.内蒙东部区民歌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5]严辰.读《蒙古民歌集》[N].文艺报,1950-01-25.
[6]安波.谈蒙古民歌[J].民间文艺集刊,1950(1):23-30.
[7]钟敬文.一年来的新民间文艺学活动[M]∥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95-496.
[8]何其芳,张松如.陕北民歌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
[9]吕骥.纪念安波同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M]∥纪念著名革命音乐家安波诞辰七十周年活动委员会.安波纪念文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29.
[10]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7月6日)[J].人民文学,1950(1):13-20.
[11]贾芝.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12]贾芝.记民间文学萌芽时代的浇灌者[M]∥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EastMongolianFolkSongs
LIU Si-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81,China)
The colle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work ofEastMongolianFolkSongsreflected that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our literary collection work on the one hand had inherited the Yan’an literature tradition in focusing on collecting and learning from folk literature, which had saved some precious national folk literature legacy; on the other hand were guided by new literary policy, which had popularized a number of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of high quality. These efforts had helped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unity among all ethnic people, and accumulat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popularizing folk litera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were a contribution to build our new literature and art.
EastMongolianFolkSongs; folk literature; collection history; cooperation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2016-06-12
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2016-2017年度重点课题“大连民间文学与城市文化建设研究”(dlskzd066)。
刘思诚(1990- ),女,助教,硕士,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
J642.21
A
2095-7602(2017)01-01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