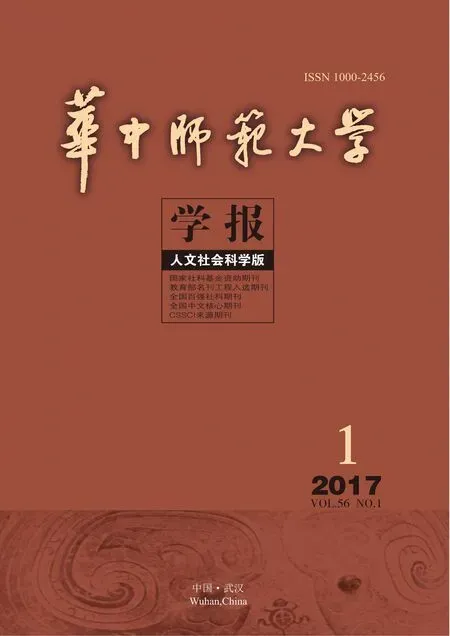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姜晓萍 代珊珊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姜晓萍 代珊珊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阐释范式,覆盖了政治学界针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本文在重新剖析、审视这种阐释范式的基础上,认为“官治绅理”的分析逻辑虽然能够通过对治理主体进行本质性解构来说明传统乡村治理的权力逻辑与组织行为,但却忽略了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张力与作用,无法清晰揭示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权力—权利内在逻辑。虽然学界已有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的努力,但本文认为仍需在前人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主体分析维度,转向国家—民众—士绅(以民众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分析维度。并且还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仅仅从静态治理主体解构乡村治理结构的局限,从动态的治理机制视角解码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实现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的研究视角转换。
基层治理; “国家—社会”二元结构; 全景关照; 范式转换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以及治理形态的研究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设,掌握着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阐释权。一种认为传统中国疆域辽阔,国家政权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国家权力难以向下实现有效渗透,故而依靠基层社会中的乡绅、宗族进行辅助,实现行政强控制;另一种假设则强调基层社会的地方精英与宗族等社会组织是民意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国家旨在宏观上加以督导。但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研究实际出自同一路径。若用本土化的话语资源进行表达,即是费孝通归纳表述的“双轨政治”。即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分割的二元结构,其中一元由皇权及其官僚进行治理,另一元则由士绅或“地方精英”治理。①然而这种“官治绅理”的分析框架虽然能够由解构治理主体来说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权力逻辑与组织行为,但却极大地忽略了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张力与作用,无法清晰揭示在传统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权力——权利内在逻辑,且仅仅从静态的治理主体视角解构乡村治理结构未免失之偏颇,也需要从动态的治理机制视角解码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
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分析范式的思问
有关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且论著颇丰,但必须说明,传统乡村治理研究首先涉及到的领域是历史学,其次才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旨趣所在。因此历史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理路必然深刻嵌入到传统乡村治理的探索中,影响甚至指挥着其研究路径。而历史学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便备受西方范式影响,其写作集矢于叙事建构,取代了帝制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编年史。通过讲述一个线索清晰的故事,并将与其历史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统括一切的主题强加给叙事化的过去,史学家可以把貌似凌乱破碎的过去整理为前后一致且具备政治意义的“事实”。
而“国家—社会”这种分析范式的导入直接与西方中国学界对传统命题的反思与修正有关。在肯定了国家政权的首席代表——官僚制度,与地方乡村社会的区域划分是建立于权力分化与平衡关系的基础之上,该种切入方式假定了此二者分别为独立的权力实体,组成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双方之间通过互动、谈判、对峙,设定、变换着权力边界,由此造成相关社会秩序、法则的变化。与先前注重宏观分析的整体论研究视角相比,“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相当关注对微观的社会权利边界的审视,以及各种社会势力在争夺权力资源时表现出来的具体社会形态,也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士绅”这一传统社会至为重要的权力主体上并直接开启了至今仍在盛行的地方史研究。于是自40年代起,便陆续兴起了关于中国士绅的研究,试图延续之前对治理主体的探讨,回答“在皇权无法深入农村基层时,究竟是谁在治理基层”的问题。在数十年的演进历程中经历了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拓展,形成了“士绅”模式和“地方精英”模式。与之相对立的,还有华南学派的“宗族”模式。这几种模式关注的治理主体不尽相同,内部也因此存在诸多抵牾,但都共享同一种研究视角,都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笼罩下对权力实体(治理主体)进行本质性的定义进而再展开对其具体治理活动的探索。但是,这种研究路径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严重的问题,下文笔者将概述这一研究视角下乡村治理研究的演变过程并进行反思审视。
提到乡村治理研究,绕不开费孝通为代表的原创型学者,他们最先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前提下展开研究,敏锐地觉察到广大乡村与国家权力的梳离关系,发明了“上下分治”、“皇权无为”、“绅权缓冲”、“长老统治”②诸多极富解释力的概念。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多集中于社会学、历史学,但其研究成果早已外溢到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基本奠定了日后研究的主旋律。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针对乡村权力来源,提出的反映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双轨制”假说。费氏认为在上的中央集权有效性仅到县一级为止,在下的地方自治由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负责,国家政权很少加以干涉。而牵制皇权专制统治有两道防线,一是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另一个就是行政机构范围上的限制,使得皇权并不直接针对每个家庭。③而对地方权威的权力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权威主要来自于国家体制的承认(“功名”);另一种则主张地方权威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才是其获取权力资源的主要方式,从而其权威来自地方社会授予。不同的权力来源导向各异的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方式,也因此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或者地方权威同国家合作,充当国家利益在乡村的代言人;或者地方权威和民意站在一边,形成庇护关系,与国家机器分庭抗礼。于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
研究假设中的第一种,便是强调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将基层社会里的半正式或非正式行政人员收买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给予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令其严密控制监督广大乡村,遏止任何自治自主性质的活动的发展。此类学说典型代表如萧公权,就认为清代皇帝为了巩固统治,不断集中权力,制定严刑峻法监控臣民,实行暴政。反映在基层统治方式上,就是利用乡民辅佐官治,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监督、控制乡民言行,时时向官府回报乡村治理的动向。靠着这样一套“准行政”制度,帝国专制统治得以在基层无孔不入。④瞿同祖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同样认为通过种种监督手段,乡民皆落于国家股掌之中。⑤孔飞力则通过研究晚清“乡村自治运动”,发现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奏本文献中,“自治”建议的出发点在于密切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之联系,促进二者目标一致契合,使地方政权成为助长国家政权的左膀右臂。⑥
从他们的看法中可以发现,其一,操纵村事的基本都是乡绅、族长一类的精英人物,在治理乡村的具体实践中看不到不同村民的身影,他们被当作愚昧无知的群氓,湮没在茫茫史料当中,也因此传统中国乡村未能发展出由基层民众共同参与的自治共同体。其二,即使是那些在村社内握有实权的地方权威,在跟官府打交道时也毫无优势可言,不论是士绅阶层的利益还是村民的利益都得不到法令上的和事实上的保障。其三,地方权威充当两面角色,对内主宰乡村日常生活,对外遵循官方意志协助官府。
另一种假设中士绅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则积极得多。“庇护”是该种研究假设的核心词,盖因地方权威的权力来源是地方社会,因此士绅们对内作为有声望的民众利益的代言人,按照地方习俗调解主持村级内部事务,对外抵制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行政人员讨价还价,努力使村庄治理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这一方向的研究者,当以韦伯为先声。他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始终停留在中央政权的“有限治理”,着重强调地方相当程度的自主性。韦伯认为中国村庄的自主和凝聚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宗族势力抵制了世袭君主行政体系,支配着乡村社会生活,一个必然的结果,便是“自上而下的世袭君主统治与自下而上的宗族强大反制力的冲突⑦”。其次是村庄中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组织,多以村庙为聚集点行使类似于当今公共服务的职能。韦伯相信,正是由于乡村有组织的自治和强大的宗族势力使得国家政权建设无法深入乡间。他认定中国的村庄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的居民点⑧”。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它包括不断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系。身处其中的乡村精英出于维护自身威望、实践保护乡民的道德义务对村民提供庇护。也据此地方社会精英建立起了他们的权威,被称为“保护型经纪人”。⑨

截至目前,有关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大都共享“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相应的,其研究视角也多着眼在国家和社会,或国家—士绅/地方精英—社会之间的权力拉锯战上,围绕着“国家支配—社会反抗”展开论述,较少质疑“国家—社会”这一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得出的研究成果虽丰富,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弊病,不可小觑。

作为读者,我们往往忽略了“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之所以引入中国,实际上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经历了由天下主义分娩出来的阵痛,建构民族国家的需求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对其时的学者和政治精英而言,他们对现实的洞察及其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政治社会实践,会激励或束缚他们描绘过去,他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出发点是为国家现实决策的合法化寻找历史依据,而不是在追求真理,或是如实地再现历史。所以,这些研究者用来架构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事实的意识形态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都富含了政治目的,并最终致力于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


第四,“国家—社会”的分析取向直接拓展出了地方史研究的新境界,为乡村治理研究增添了材料来源和诸种研究之可能性。但是这一取向引发了很多问题。一是地方史关注的地方态势自成一体,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脱离了与其他地区和国家政权的联系。这容易导致对跨区域现象的漠视,比如天灾、叛乱、贸易活动等会对乡村治理状况产生较大影响的自然与社会事件。二是由此导致的碎片化、空洞化的研究特点,体现为通过研究传达乡村治理基本态势以及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困难,学术研究由此失去了实际意义,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实践的表达形式。我们不能无视地方乡村研究本身呈现的魅力,但此种路径仍旧不能表现跨地区的整合意义。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
二、“第三场域”与乡规治理的视角发现






从晚近的中国乡村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突破原有框架的努力,新一代的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望日后逐渐突破陈旧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型。但是新的研究视角的建立并非易事,尽管很多学者努力通过个别地方乡村治理的研究提炼出整体性的框架和视野,但大多数作品仍停留在普通乡民与国家制度的正式系统相对抗的行为言论层面。如何有别于传统框架支配下的解释,重新裁剪并拼贴出一幅完整真实的乡村治理图象,仍是亟待完成的议题。
三、跨域对话与全景关照的视角转换
乡村治理当中,我们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能以一个真实的、不歪曲历史的表述方式还原传统乡村治理境况。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已有的研究涉及人口流动、权威秩序、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或是关注国家专制权力而忽略了地方权威与村民,或是聚焦地方权威却省略了农民的在场,所设计的分析框架似乎逻辑性很强能自圆其说,但实际上却是对西方语境的盲目效仿,对理解传统乡村治理的真实状况有弊无利。乡村治理应是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共同参与,缺少任何一方的能动参与去研究乡村治理的真实情况都无从谈起。因此,国家权力在乡村的配置及运作方式、地方权威的倾向品性以及普通乡民的行动逻辑都应被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角当中。
如此看来,我们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理解,当不宜仅仅囿于国家与士绅、地方精英之间或依附顺从、或充满紧张的简单关系,而应当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超越这一主导研究框架,在研究视角上实现转换:
首先,从学科角度,传统乡村治理的模式建构建基于不只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实际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牵涉到多种社会学科的理论范式应用。而且,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和政治学研究者一样,关注乡村治理问题,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外溢出自身领域,政治学、行政学也大量借用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相同的研究假设前提下开展研究工作。但是目前面临的研究悖论是,学科专门化的趋势下,对研究方法严格性的专注加剧了各个学科自我孤立的趋势,将不同学科的学者彼此隔开、拒绝分享,制造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样的研究发现往往脱离具体情境,引用其他研究学者的成果时也经常是蜻蜓点水,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乡村治理的总体把握。换句话说,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乡村治理的研究发展似乎表明学科之间的藩篱已越来越少,但从乡村治理研究内部角度看,这其实反映了研究本身碎片化的态势。如何促进各学科之间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对话交流,是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研究者必须不断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的对话中寻求灵感,避免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乡村治理分析框架,自觉超越地方乡村治理的教条而赋予乡村治理研究以新意,重新培养起整体解释的意识。

第三,研究主体要突破“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形成国家——民众——士绅(以民众为核心)的全景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要突破静态的主体结构视角形成动态的治理视角。

注释
①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60-63页。
②参见费孝通:《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袁方:《论天高皇帝远》;胡庆钧:《论绅权》;史靖:《绅权的本质》;均载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费孝通:《乡土重建·基层行政的僵化》,《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
④Hsiao, Kung-chuan.RuralChina:ImperialControlintheNineteenth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⑤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⑥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97页。
⑦⑧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第91页。
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责任编辑 王敬尧
From Binary Structure to Panoramic Atten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Perspective
Jiang Xiaoping Dai Shans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in academic circles is influenced by the paradigm of “national-gentry” du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re-analyzing and examining this paradigm,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analytic logic of “official gentry” can explain the power logic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essential de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The tension and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can not clearly reveal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power-right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fiel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hif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gentry” dualistic analysis to the national-public-gentry(people-centered) multiple dimension. And it believes that,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which is only from the static governance subject to deconstruct the limitations of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the introduction of “process-event” analysis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decode the operation law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is needed, and 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binary structure to a panoramic view can be achiev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ate-gentry” dual structure; panoramic consideration; paradigm shift
2016-11-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机制与监测体系研究”(14ZDA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