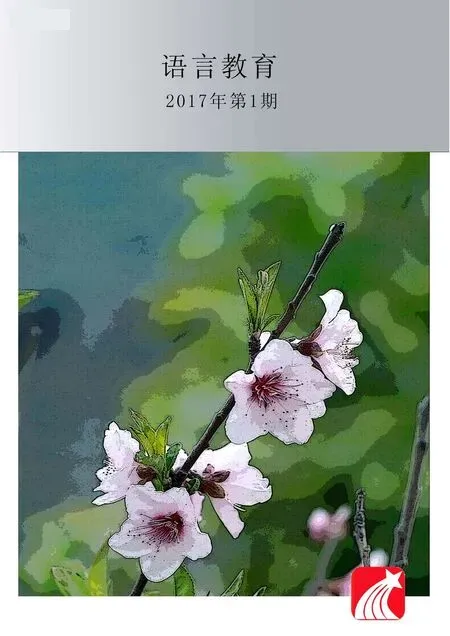“走出去”的新视角:《为西方读者翻译中国
——反思、批评与实践》述评
刁 洪 朱 斌
(1.重庆工商大学,重庆;2.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书评
“走出去”的新视角:《为西方读者翻译中国
——反思、批评与实践》述评
刁 洪1朱 斌2
(1.重庆工商大学,重庆;2.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外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声音的必由之路。目前,“翻译中国”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2015年出版的《为西方读者翻译中国——反思、批评与实践》是“翻译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在典籍翻译和古诗外译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论文集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顾明栋教授和Rainer Schulte教授主编,汇集了中国、美国、德国、瑞典等十几位知名学者、译者在“翻译中国”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该论文集既有聚焦翻译美学、翻译诗学的理论探讨,又有侧重隐喻、俗语翻译的案例分析;其将当代翻译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相结合的努力值得称赞,以西方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相信本研究将为国内翻译界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参考。
翻译中国;典籍翻译;古诗翻译;读者中心
1.引言
文学“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并非新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就开始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张南峰,2015)。20世纪80年代至今,“熊猫丛书”、“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陆续推出,彰显了政府推动“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的决心。近年来,文学“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内译学界的研究热点,大量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议,如胡安江(2010)、高方、许钧(2010)、鲍晓英(2013)、马会娟(2014)、谢天振(2014)、朱振武、杨世祥(2015)等。然而,国外译学界在此课题上的关注焦点和研究模式有何不同?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在一些问题上共鸣大于分歧抑或相反?
《为西方读者翻译中国——反思、批评与实践》(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Reflectiv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Essays)(以下简称《翻译中国》)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该论文集的第一主编是美国华人学者、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顾明栋,第二主编是国际翻译学期刊Translation Review编辑Rainer Schulte。该书于2015年1月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 Press)出版,集结了中国、美国、德国、瑞典等海内外十余名翻译学者、译者对“翻译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西学者、译者在此课题上的深入探讨和广泛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2.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录12篇论文,按照主题分为三大部分,即“翻译概念问题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nceptual Issues of Translation)(前四篇)、“翻译的‘艺’与‘技’”(The Art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中间四篇)和“翻译实践的批判性评价”(Critical Assessment of Translation Practice)(最后四篇)。文集以“翻译中国”为主线,以“西方读者”为立足点,理论实践结合,批评反思并重,其整体性、多元化、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颇具示范意义。正如编者指出,本书旨在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著作外译实践的译者和外译研究学者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一部分的4篇论文集合了对翻译本质、功能、历史价值和翻译元理论的深入思考。第一篇为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Chung-ying Cheng)撰写的《解释学理解原则:翻译的逻辑基础》(Hermeneutic Principles of Understanding as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基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本体论解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和作者自创的易学本体论(Ontology of Yijing),作者提出了阐释文本(特指古典文学、哲学著作)可译性逻辑基础和评价翻译有效性的七大理解原则。在其《隐喻可译否?》(Does the Metaphor Translate?)一文中,瑞典学者Martin Svensson Ekstrm开篇指出西中诗歌蕴含的哲学基础大相径庭,前者为形而上学,后者为关联宇宙论。因此,“西方诗歌源于诗人的深思熟虑、精心打磨,而中国诗歌则来自灵感、浑然天成”(p.51)。依循这一逻辑,隐喻似乎不可译。然而,作者随即推翻了这一假设,继而指出尽管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概念,但是隐喻的迁移性、共通性决定了隐喻的可译性。第三篇文章是清华大学王宁教授的《翻译中国文学——经典的消解与重构》(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Decanonization and Recanonization)。作者以布鲁姆(Harold Bloom)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学批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翻译文学史上的几个案例,阐明了翻译在不同目的语中重构文学经典的重要角色。他认为,经典翻译文学的重构有赖于中文原作者、西方汉学家、国外出版商之间的密切合作。收尾之作是顾明栋教授的《读者型翻译与作者型翻译——追本溯源的翻译理论》(Readerly Translation and Writerly Translation: For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at Returns to Its Roots)。文章创立了“读者型翻译”与“作者型翻译”两个概念以重新审视翻译评估的本质和标准。在分析美国现代诗人洛威尔(Amy Lowell)与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中文诗歌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理想的译者应当是熟谙译出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学者,嗅觉灵敏、独具慧眼的文学评论家,从阅读、思考和批判中汲取营养并润泽实践的思想家,堪称一流、富有创意的作家”(p.114)。
第二部分的4篇论文聚焦于翻译的艺术与技巧,旨在为翻译出可读性强、受西方读者喜爱的文本提供建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撰写的《翻译中国历史哲学著作》(Translating Text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以诸子百家典籍英译为例,剖析了经典著作翻译中的常见错误与缺陷,如作者认为“鬼神”被译为“ghosts and spirits”实属牵强,因为古汉语偏爱形式对称、音律调和的两字、四字和六字词语,“鬼神”亦属其类,应被视为单义词,因此译为“collective spirits”更为妥帖。美国犹他大学教授吴伏生(Fusheng Wu)的《翻译古代中国应诏诗》(Translating Medieval Chinese Panegyric Poetry)阐述了译者在翻译应诏诗时如何根据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调整翻译策略。为了使对古代中国感兴趣的普通西方读者也能接近译文,体会另类古诗的独特韵味,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添加尾注、附加分析等方法。如在翻译《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其一》中的“五德更运”时,译者在提供译文“Five virtues replace each other in turn”的基础上又辅之以尾注:“五德指金、木、水、火、土……”。第三篇文章是大陆学者刘华文的《化境与事件化——诗歌翻译的现象学视角》(Real-m-ization and Eventualizatio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Poetic Translation)。作者认为,“境界”传递是评判中文古诗英译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而其中的最大难点在于中文和英文的语法差异,即前者名词(境界多依赖名词传递)占优、倾向静态,后者动词占优、偏于动态。多伦多大学教授Richard John Lynn撰写的末篇《古文经典英译的网络与电子资源》(Internet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Translation of Premodern Chinese Texts and Howto Use Them)稍显“另类”。作者对翻译理论着墨不多,而是以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为基础,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有效利用《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网络电子资源协助翻译实践。
第三部分的主题为“翻译实践的批判性评价”,4篇论文以诗歌翻译与小说翻译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角度论及了翻译策略、翻译美学、协作翻译、读者与译者关系等课题。波恩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撰写的《括号中的译者与翻译散论》(Translators in Brackets,or,Rambling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Work)阐述了如何在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在顾彬教授看来,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美国大受欢迎而在德国颇受冷落,原因是美国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的优秀译者,而德国的中文小说翻译多为“未接受翻译训练、德语水平低劣的汉学家”(p.224)。可见,拙劣的译者足以“杀死”原作。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美国诗人Frederick Turner。在《翻译唐代诗人:基于西方诗人与读者视角》(Translating the Tang Poets: A Personal Viewby a Western Poet and Reader)一文中,他指出西方人了解中国诗歌、美术、音乐和戏剧必须以西方人固有的、习惯的方式进行。而中西译者的合作既能保证译文精确,又能确保译文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这是翻译唐代诗歌的首选模式。第三篇为Tony Barnstone撰写的《文学翻译的三个矛盾—中文诗歌形式之翻译》(The Three Paradox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 for Form)。作者将中文诗歌翻译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了诗歌翻译中的主要矛盾、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全书的收尾之作是大陆学者陈月红博士的《审美忠实与语言忠实——庞德与洛威尔译诗的再思考》(Aesthetic Fidelity versus Linguistic Fide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zra Pound and Amy Lowell)。作者以“意境”、“意象”的传递为诗歌翻译的评判标准。在分析庞德与洛威尔的中文古诗英译后,作者指出庞德的译本更成功地传递了“意境”,达到了审美忠实,因此更为英美国家读者接受。
3.评价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间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与文化正努力“走出去”。那么,翻译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的翻译策略比较合适?谁来翻译更好?西方读者更偏爱何种翻译作品?为什么葛浩文和庞德的翻译取得了成功?本论文集就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建议。概括而言,其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研究主题突出,各篇文章关联性强。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大多着力于典籍、古诗的外译。典籍与古诗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和思想宝库,到目前为止,对它们的翻译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正如谢天振(2014)指出,许多旨在“中学西传”的翻译作品尚未真正“传出去”,例如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中华文库”并未在海外获得多少粉丝。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颇为热门,但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多论者难以跳出传统藩篱,甚至充斥着一些只顾喊口号的空论,不落窠臼、视野广阔之论甚少。《翻译中国》汇集多方言论、凝聚广泛共识、具有开创意义。其次,尽管论文集的三大部分各有侧重,但是它们之间是高度关联的。理论研究(第一部分)可为微观(第二部分)与宏观(第三部分)层面提供研究路径与核心概念;宏观层面可为微观层面与理论层面指明方向、深化理解;微观层面的翻译实践则为另外两部分研究提供实证案例。
第二、研究视角独特,读者接受度备受关注。读者中心论从书名、篇名中可见一斑。典籍、古诗的外译是一项难度巨大的文化工程,其成功有赖于恰当的翻译策略与传播手段。就翻译策略而言,多数作者主张归化翻译,即以目标读者的需求为导向,“按照目标文化的状况来制定翻译策略”(张南峰,2015)。然而,这种策略还未被国内发起与从事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外译的组织者和译者理解和接受。就传播手段而言,多篇文章(如第三篇、第九篇、第十篇等)提及的顺向翻译(即由外语译入母语)、中外译者联手、国内外出版社合作、举办文学推介会、译者进行文化考察等都是可取之道,体现了目标读者与市场的中心地位。
第三、研究思路强调学界与译界打通,体现中西对话、多元并存。书中既有理论性、系统性的学院式思辨,又有描述性、启发性的译者式剖析,还有不拘一格、灵感迸发的诗人、哲人式漫谈,然而每一篇都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文章的作者们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和瑞典四个国家,他们当中多数是一流大学的知名学者,也不乏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例如成中英教授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代表人物”,他既熟谙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精神内核,又对中国哲学与文学传统有着深切关怀与忧思。他以易学本体论和现代解释学为基础构建的七大原则为我们评价翻译质量提供了新途径。而TonyBarnstone教授不仅研究翻译,还投入大量精力翻译出版了Laughing Lost in the Mountains: Selected Poems of Wang Wei(1992),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 (2005),Chinese Erotic Poems(2007)等作品。他周旋于诗歌翻译的三个矛盾中,游刃有余,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唐诗”。总之,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对话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探寻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正确途径。
第四、研究成果表现出深刻而系统的批判性。《翻译中国》在论述“走出去”各类问题的过程中,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典籍和古诗翻译的错误认识。当前,外译中的“文化优胜论”和“强势输出论”颇有市场,一些学者(徐珺 霍跃红,2008)鼓吹以异化翻译为途径提升“中国英语”(Sino-English) 地位,她们认为要大胆使用“中国英语”,从而填补由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表达真空,增进外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而《翻译中国》中多篇论文(第三篇、第四篇、第九篇)指出,中国文学目前仍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地位,因此,翻译古典文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主动适应目标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译文的接受度和流行度。
4.结语
总之,该论文集主题突出、视角新颖、层次清晰、内容丰富、批判性强。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某些理论构想未能深入展开,翻译案例重叠较多等。瑕不掩瑜,总体而言,此论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值得中国翻译界学习借鉴。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步子已经迈出,以海外译者为主体,作者译者、中外出版商合作的翻译模式和以目标读者、目标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翻译策略必将推动我们走得更远、更好。Sino-English的主张虽然体现了文化自豪感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勇气,但其本质无疑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无助于外译工作。
[1] 鲍晓英.2013.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5): 62-65.
[2] 高方 许钧.2010.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6):5-9.
[3] 胡安江.2010.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6):10-16.
[4] 马会娟.2014.解读《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兼谈中国文学走出去[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112-115.
[5] 王治东.2015.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关系范畴[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4-49.
[6] 徐珺 霍跃红.2008.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7):45-48.
[7] 谢天振.2014.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1):1-10.
[8] 张南峰.2015.文化输出与文化自省——从中国文学外推工作说起[J].中国翻译,(4):88-93.
[9] 朱振武 杨世祥.2015.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误读与重构——以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1):77-80.
A NewPerspective of “Going-out”: A Reviewof 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Reflective,Critical,and Practical Essays
Outbound translation is the only way of promoting Chinese stories and cultures in foreign countries.In this background,“translating China”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Reflective,Critical,and Practical Essays,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5,is a milestone contribution to this research field.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written by prominent scholars fromseveral countries such as China,USA,Germany and Sweden and compiled by Pro.Mingdong Gu and Pro.Rainer Schulte,has focused on topics such as translation aesthetics,translation poetics,metaphor translation,proverb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Featuring a Western readers-centered perspective,this work will be inspi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or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China.
translating China;classics translation;classical poetry translation;reader-center
H059
A
2095-4891(2017)01-0081-04
本文系2016年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典诗歌‘走进英语世界’研究”(项目编号:16SKGH109)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古典诗歌英译译者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isu2016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刁洪,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翻译史;朱斌,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地址:1.400067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2.4000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33号四川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