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纹理、文化焦虑与重建可能
——评李俊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文 金春平
乡土纹理、文化焦虑与重建可能——评李俊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文 金春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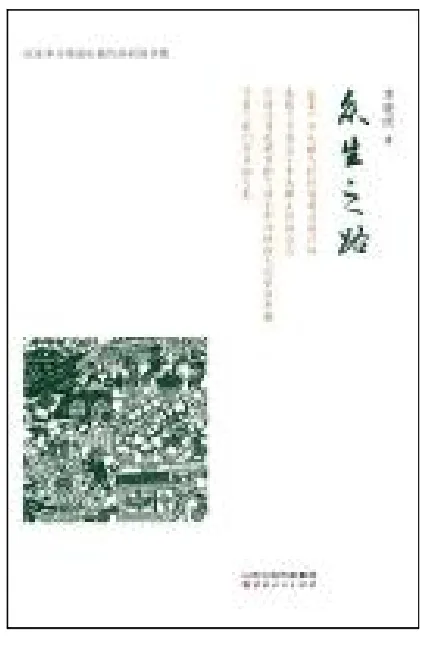
编者的话 李俊虎是山西青年作家里的代表人物,创作成就显著,受到文坛广泛赞誉,其代表作《母系世家》《众生之路》反响热烈。新近出版的《众生之路》,把乡村写得丰满而沉重,这期我们选发三篇关于《众生之路》的评论与读者一起分享。
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叙事,总是充满着个体化的美学偏颇,在时代文化语境的顺应或反叛的制掣下,乡土成为展开中国陈述的修饰词汇和话语前提,它所具有的巨大而深邃的黑洞能量,成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攫取源动力,演变为与“西方现代性”相并列的“中国乡土精神”。现代与乡土,构成了国人生存的两极——现代性以外发性的方式,让人的主体性得以独立和飞扬,实现了物质生存的巨大进步和精神桎梏的解脱,但也让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着理性、资本、权力、法制等“硬性文化法则”而运行,它是人的世俗生存需要;而“乡土”则是人的精神心灵需求,乡土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人关系维系的民间伦理,乡村日常运行的道德、舆论、约定、限度、民间等“软性文化法则”,因为能依托于集体话语,摆脱个体状态可能具有的精神孤独和存在区隔,在人与大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活网络与文化凝聚中,获得心灵的归属与静默,而这些正是人的诗意浪漫精神的生成前提。新世纪之交崛起的乡土叙事,其叙事理路、真实效度、典型样本乃至情感基调,面临着来自文学自身、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大众传媒等领域的多重质疑,虽然“乡土”和“乡村”在被构建起的启蒙寓言化、民间诗意化、革命政治化、宗教神秘化、城乡对立化等叙事模式的纠葛中,成为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洞悉国人精神的一幅有效而微缩的社会场域,但是乡土的本体也在阐释的无边界、无限性中,被削弱、被遮蔽或被扭曲,乡土空间叙事走向了异质性的多元和破碎,失去了能用单一视阈观照的可能。因此,当前的乡土叙事需要纳入立体的时空维度,即静态的历史远观、动态的现实审视、存在的未来走向的多维坐标体系,寻觅乡土文化在历史行进语境中的价值输出,而这个崭新的叙事使命,意味着当前作家要有意识的突破传统叙事范式的固有经验,进行先锋式的艺术超验建构。李俊虎的小说《众生之路》,正是对沉默的乡土文化机体的主体代言,对乡土生命本体的美学呈现,也是对乡村命运基体的痛感展望。小说以“南无村”的封闭地理空间为文化载体,在漫洇着浓郁的文学地域性的同时,对中国整体性的乡土社会的安稳、剧变、撕裂和“损蚀冲洗”的“变”与“不变”的横亘,进行了艺术性的高度浓缩和抽象化的典型勾勒。在后现代语境当中回望前现代文明,其文学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思想和艺术的价值立场问题,而李俊虎先锋性的对乡土叙事的“时间”线性模式进行超越,更倾心于对叙事学领域当中“空间”维度叙事的偏好与探索,即他精心于对一个个彼此联系又彼此隔绝的空间场景进行细微的刻摹,在叙事空间的共存叠加中,通过叙事视角的多维棱镜,消解了小说寓意指向的单一化,在特定空间场景所隐喻的格局当中,让文本呈现出意义的复调性、发散性、可逆性、包容性,散点式的空间化叙事转向将历史、现在和未来并置,实现了对小说文体的虚构场景与非虚构现实的功能交融,由此反思和发掘现代化语境中传统乡土文明的“建设性”功能对现代人生存的补葺,这种叙事范式的暗示,是重新激发乡土文学内在精神活力,释放乡村、乡土、乡愁所包蕴的艺术能量和价值先锋的有效方式。
风物记忆:乡村空间的质地面向
《众生之路》以“众”为主角的场景式、截面式、意识流式的叙事铺陈,展示出南无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立体景观,小说跨时间、跨领域、跨意识的内在体验话语,深藏于多重空间的隐喻当中,它颠覆了乡土小说在社会现代性观念的制掣下作为思想演绎或艺术操练的工具角色,而让乡村在审美现代性的场域中从喑哑的存在走向丰富的面向。李俊虎在这部小说中,让乡土成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展示着自身的生命活力和质感纹理,他将乡土上升为一种与人齐等的生命体,抒写这位从青年走向垂年的幸福和宁静、痛楚与扭曲、命运与困惑,由此建构乡村的文明史、族群史,谱写一种生活史、一段生命史。“空间并置”源自于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的批评概念,“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众生之路》当中乡村风物包含了实指性的叙事空间,也包含了依托于空间环境的稳定性所隐喻的虚拟心理场景和精神画面,正是在对乡村的实体环境和虚拟场景的主体言说中,开启了对“众生”之“众”的内涵释放,人与景、情与心、生与死等的主题共存,避免了将乡村风物作为先行化工具演绎的窠臼,而进行着“日常生活”内里的演绎,在彼此连续的“众”空间的“并置”中,寄寓着对乡村思考的多维理念与美学趣味。
首先,小说在童年记忆的情感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的诗意安守与身份逃离的生存悖反。“无土时代”的乡村回望,是一代人走出乡土走向城市、经受着现代理性和社会规约束缚的精神梦游,乡村的器物符号、生活体验、情感反刍,已经化为经历过乡土洗礼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渴望、屈辱、荒诞、狂野,都蕴藏着自然心灵悸动的生命活力,是对工业现代化时代人类精神平庸的救赎,是对人类平面化处境的信仰重建。《寻常巷陌》当中,学书可感知的生活风物是他幼年情绪化的艳羡,谜语式的陈述是对乡土尊卑秩序稳定结构的眷恋。学书眼中的“村景”,其潜在参照是学书成长之后的知识者身份、城市化背景——这些乡村风物是身居城市者遥望乡村的寻根载体,是失根者对原初身份的自觉追溯,在以空间之点来呈现南无村乃至乡村整体抽象化环境的塑造中,是文本主体和创作主体对已逝心灵静谧的场景象征。学书对乡村“野性”和“越轨”的参与和体验,其中的惊奇、担忧、激动等情绪,是一位恪守“知识者”社会准则的自觉童年认知和脱离现世身份限制的回忆飞翔,也是在“彼此中断的不同质的空间”和“彼此不能沟通的不同质空间”的心灵漫游,隐喻着对乡村岁月超脱现实的精神化诗意想象。执着的羡慕和想象拥有戒指(《团结学校》),歇斯底里的发怒、对庆有不信守承诺的失望、体力劳动后的痛苦感受(《百年孤独》),激起了他身份蜕变的强烈意志,浪漫和纯真开始褪色,目睹了乡村无望的残酷面目之后,也隐喻着他与乡土大地的最终分离。
其次,小说在精神猎奇的群体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生活的精神沉珂与生命卑微。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同一团体的人事‘兼善’的,就是‘相同’的。”这样的差序格局,决定了“私人的道德”是人际交往的内在原则,也由于道德的“私人化”的标准游移,导致了乡村生活的人性“非爱”与生活“非仁”。《众生之路》当中的“表演性”场景,隐喻着对乡土现代性改造的文化诉求。婆媳的“争吵”,是乡村的蛮、野、狠的表演舞台,村民的远观与参与,是乡村整体虚空伪善的练习场,在看者与被看者的互动中,完成了一场平庸生活精神宣泄和情绪发泄的大戏,并在走向悲伤的表面获得皆大欢喜。祭拜亡灵的仪式上,祭祀者的悲痛需要戏子的表演来完成,这种情感代替的虚伪表演,是人们在特殊时刻的一种集体情绪发泄——“人们期待着看到的她的哀荣,听到她的哭声,以满足某种隐秘的对这伤心事最大化的窥伺和感受”,于是在表演者和欣赏者的共同入戏当中,大家陶醉和享受着个人情感发泄的虚幻情境,从而获得卑微生活的压抑释放。乡村一个个生命的逝去,并未勾起集体的悲悯,却是一件自然的日常生活,生与死牵引出的是乡野社会冷漠而卑微的集体心理和生存呈现,乡村“表演性”的悲痛,寄寓着集体的狂欢、个体恩怨的发泄和复仇的乖戾,这是乡村的日常生活法则,它的存在超越了法律和制度,更多的具有了生命的通透。乡村精神的沉珂还体现在对神性领域的隐性敬畏,展示着乡村人在生活未知中的精神幽冥和心理郁结。民间神性领域的存在,是一种除却民间舆论之外的内化型的软性道德约束,在敬畏和恐惧的心理暗示下,那些打通神性领域和人类领域的中介物,就被视为神性的替代物而备受忌讳或尊崇,对这些中介的亵渎、拥有或放逐,也就成为私德与功利调和的实践行为。红生因砍伐亡者“寄居”的大柳树而意外摔伤(《团结学校》),铁头砍倒勾走父亲魂魄的大柳树,大柳树被砍之后卧病的巧儿突然痊愈等(《百年孤独》),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在神秘氛围的逻辑中,被赋予了因果报应的涵义。这是乡村对待命运多舛和灾难偶然的略带“阿Q精神”的仇恨转移法,是生存压抑的无奈,也是宿命捉弄的反抗,这种民间的宗教性伦理所具有神性玄学的逻辑合法,让民间的生死轮回、德守的践行长久持续的运行。
再次,小说在性别等级的两性之相中,展示着生命本能的野性激扬和伦理失范。传统乡土社会的男女关系将性别尊严视为身份权利确立的表征,比如兴儿的性无能因有违男女性别关系的专制模式成为示众的谈资(《普天同庆》),但在长期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文化定向中,这样的男女关系模式,却维持着乡村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甚至社会关系的稳定。《众生之路》对乡村两性恣肆的描摹,显然具有道德化批判和狂野性焦虑的双重色彩,一方面寄托着性别觉醒和人格独立的期冀,但也对乡土性别角色关系的觉醒和颠覆所附带的秩序混乱和稳定破坏怀有深刻的忧虑。《团结学校》当中,郭老师对庆有妈、铁头妈的婚外情歧视和辱骂,代表着乡村传统民间伦理的道德判断;庆有妈和铁头妈对自己与林校长婚外情状态的心甘情愿,是乡村女性对知识阶层越界向往的实践诉求(越界的途径就是身体资本的牺牲),同时也包含着反叛性别伦理秩序的个人情感的释放追求;她们二人之间的敌视,源于乡村本原的生殖意识敌视,而事实上,她们都是违背乡土专制性别关系秩序的彼此镜像。如果说她们颠覆性别秩序的诉求是“知识身份”,而云良与小巧(《百年孤独》)、艳艳与喜喜(《五福临门》)、海云与众多弱势女子的两性关系(《普天同庆》),已经置换为“经济身份”的诉求,在道德与物语的角逐中,道德彻底败退。南无村的性别景观,再无集体伦理的重负和自责,亦无道德的歧视和批判,相反脱离伦理之后的世俗回报,让道德约束彻底让位于物质渴望成为乡村的价值认同。
第四,小说在荒蛮自然的政治之相中,展示着乡村自治的伦理蒙昧与欲望残酷。基层权力高度集中之后所具有的财富资源的占有特权,使乡村的政治权力成为乡民实现物质越级和身份越界的捷径,对权力的争夺也就成为展示弱肉强食的人性场域。权力制度的不完善,使权力欲望者不得不屈从于民众的意愿而示弱,但是权力获得之后制度监督的缺失,又使权力基层区分于民众的专制格局得以可能。而民众现代公民意识的匮乏,又使得公民选举权的行使受制于物质诱惑、民间人伦、私德私仇的支配,最终权力的生产处于法律约束、物质诱惑、人伦恪守的多重夹缝当中,而这个权力网络场域也成为文化、心理、人性的决斗、厮杀和妥协的情境。于是,乡村的自治可以用野蛮来维续(《寻常巷陌》),村民的纠纷可以被乡村当权者敷衍推诿(《团结学校》),犯罪行为可以在人情的斡旋下肆意决定(《五福临门》)。《普天同庆》当中,乡村基层权力的争夺,是权力欲望者与乡民话语权的一种当前个体利益和未来集体利益的交换,而契约精神和公共意识的缺失,使得权力的争夺更多的是操控能力的争夺。天平依托的是民间人情伦理的操控,而连喜依靠的是物质资源诱惑的操控,他们的角逐正是人在物欲和伦理抉择中的考验,人性的理性契约和感性放纵也在此暴露无遗。在公与私的合谋中,权力个体和乡村群体的压抑得到充分释放,在以权对恶的革命狂欢和乡间法则的自然野蛮的实施中,“乡村正义”得以确立和胜利,“权”与“利”的心照不宣在民间是如此的和谐,这是对乡土宗法制和家族自治制的颠覆,也滋生着人性之恶的膨胀。
乡村场景空间的并置与叠加,祛魅了附着于乡村之上的观念、想象、抽象,而让乡村的存在本体和乡村的生活内里得以立体展示,某种意义上,这是以“真实”为内在诉求的一种乡土言说方式,但绝对真实的无可抵达,也决定了乡村的面貌只能在互相映衬、否定和参照中进行勾勒,乡村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的共存,构成了乡村文化机体肯定与否定兼备的结构模式,而这样的多维性并存,蕴含着乡土文化的暮歌,也饱含着乡土文化的新生,这也是《众生之路》在先锋性的空间化叙事构建中,所营造的独特文学效果,它代表了一种对乡村观照的动态视域,在线性化意义的消解中,内蕴起多维性的隐喻阐释空间。
人伦暮歌:乡村精神的皲裂与疼痛
现代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量,将地理格局中的每一个点都纳入其同化和改造的范畴,南无村也随时上演着各种文化话语主体的争斗大戏。曾经乡村的被启蒙、被革命、被诗意的意象化处境,迅捷地在资本现代性的映衬下,呈现出贫穷、空心、失范的内里面目,伴随着资本现代性的物质感官、人性本能、都市文化等的侵袭,即第一现代性的整体强行介入,“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乡村文化也在艰难的处境当中进入到了被迫的自我渐变和文化差序格局的暗处。
首先是乡村感官现代性与乡土民间伦理性的嫁接阵痛。儒家文化所孕育的乡村伦理以重义轻利为基本价值准则,道统成为国人生存的基本观念法则,在血缘、地缘、家族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稳固的存在着。启蒙现代性运动当中,对人的世俗欲望压抑的格局首先遭到了解构,人的感官享受也被视为是人的现代性解放的第一步,于是,乡村伦理和物质现代在人的身上开始了隐秘而强烈的认同抗衡。物质现代性以及由之所衍生的感官欲望在宣称胜利的同时,巨大的精神代价和未知的神秘宿命,成为感官胜利的强大而无形的制掣之神。《众生之路》当中参差化的财富累积和社会身份的对比,是民间生活“同质”的“渐变”,是人性“异质”的外在催生,它让乡村的物质权力级别开始生成,也作为乡村日常生活变革的典型,成为集体羡慕和怨恨的对象。比如在二福财富的大起大落中,南无村家庭伦理的世俗和道德寻找了彼此共存的和谐——“穷光蛋”是对二福作为资本压抑者的泄愤,“王八蛋”是对二福违背民间伦理的集体压制,资本世界被压抑的泄愤和乡土道德压抑他者的残忍同时共存,由此也完成了一场无形的乡村精神复仇(《寻常巷陌》);铁头遭难和云良死亡,是物质诱惑对人性欲望激发结果的代价(《百年孤独》);木匠福娃通过民间诅咒的方式谋财,却将自己的弟弟“咒死”,诡异的生活偶然具有了鲜明的道德批判意义(《五福临门》)。巧云的物质向往和身份簪越诉求,早已将乡土传统的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家长宗法制破坏,利益资本的权力获得成为主宰人际关系的准则(《普天同庆》)。
民间伦理虽有着抵御现代感官本能对人的生存法则侵蚀的反制作用,但其微弱的道德内化作用,在乡村集体的现代性诉求和物质等级的参照当中,正逐渐走向溃败,物质的现代性是实现人的现代解放的前提,但是,解放方式的缺乏理性的制约,又让这种物质解放重新陷入理性缺失的“物役蒙昧”境地,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种新的启蒙对象。恪守乡土道义原则的学书父亲在合理的物质渴望中开始的道德“越轨”行为(《寻常巷陌》),秀芳对红芳的引诱、永强和新峰的恶行(《五福临门》),围绕死亡赔偿款所上演的亲情虚伪掩盖下的物质企图(《普天同庆》),郭老师在默许两个女儿与自己的道德死敌的婚姻之后,形构出人的道德卑劣与世俗生活的选择可以并行不悖的可能。在这些奇妙的共存当中,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卸去了集体性的道德批判反省,却充满了世俗的钦羡和想象,这是资本物语对民间德语的胜利,也是物质时代对民间道德伦理的彻底摧毁。伴随着物质感官欲望爆发的民间伦理长期以来对性伦理压抑的冲决和释放,“男女有别”的稳定伦理秩序和家庭分工,正被现代性所幻化的人性自由所解构,这种自由在乡村文化土壤当中,并未达到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性境界,却在两性领域进行着道德解放的实践,小说当中诸如云良与小姨子的公开偷情(《百年孤独》),将物质和性别资源叠加,并在无形中成为新的性别交往模式。物质感官是乡村人群内部等级的匀质走向异质差异的一种外因,形成完全不同于乡村宗法制伦理的资本话语,强化着群体对物的奴役关联,这些情景当中物质的合理诉求与道德的隐晦践踏的矛盾是难以理清的价值难题,同时也消解着生存怜悯与道德批判的叙事指向。
其次是乡土空间自足性与乡土被迫城镇化的悲壮抵牾。工业现代化颠覆着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当中人屈从于自然环境、社会道统、封建伦理的关系模式,重新确立了“人”是世界主宰者的地位,与之伴随的是工业现代化的空间载体——都市文化以及所包蕴的物质资本、个体理性、法律制度、自由权利等,作为先进生活方式的确立和认同,于是,从乡土走向城市成为乡土现代性转型理所当然的方向。现代性的发生,是人类理性的独立和自觉,但乡土世界对都市空间的理解,普遍停留于物质解放和欲望追逐的层面,而忽略了对制衡感性蒙昧的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体认同,感性的泛滥将人推向感官的泥淖,最终却是乡村迷失于都市现代性的幻影当中,乡民在身份的跻身转型中也成为在乡村与都市空间无法栖息的幽魂。《百年孤独》当中,传统农民正蜕变为现代工人,农民失去了与大地的亲密,乡土物质在巨大进步中,正面临着乡土精神的遗弃。在物质诱惑面前,庆有和秀芹的传统保守,与铁头和秀芳的现代冒进,代表了固守乡土和走向现代的家庭生活未来,冒险的危机以及被迫的行骗、卖身,是乡民失去大地而又无法跻身都市的绝望宿命隐喻。小说深刻之处在于,这是乡民失去与土地的亲缘之后生活窘境的落魄写照,也是现代物欲破坏了乡村自守之后的扭曲和异化写真,这样的生活尴尬,既是乡村伦理进入都市后无地自容生存境遇的喜戏剧化结果,也是乡村在现代都市结构中虚与委蛇的一种存在方式。《麦黄种谷》当中,兴儿爸的“钉子户”身份,在看似对抗集体、与物质意识逆流的顽固行为,却饱含着农民与大地、人与自然、乡村身份认同与村庄空间挽留的悲壮。银亮对乡村土地的眷恋,虽有对城市化进程中生存艰难的无奈宣泄,但更多隐喻着他对自我身份迷失的孤绝寻觅。
再次是乡村现代变革与乡土本土坚守的艰难和解。现代化的强势来临,将乡村固守封闭的空间悄然撕裂,现代化的科技、知识、开放,激发出乡村长期在伦理压抑下的物欲、权欲的释放,因此,乡村变革体现在人对自我变革的主动性上。老郭对农业现代化的“失败”探索,寄寓着对乡村未来变革的强烈冲动(《团结学校》);学书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之后顿悟到的“只能通过知识来试图改变这一切”是其个体意识的艰难觉醒;南无村对年轻人爱情和个性的尊重,逐步压制了民间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至上的伦理结构,这是乡土的现代进步(《百年孤独》);大贵放下“先祖”的荣耀历史虚荣,同意男子沦进底层群体打工。巨大的观念变迁在悄无声息中显得如此惊心动魄,充满了生存的无奈和企盼的无望,但观念的转变同样孕育着新生的希望。现代性所蕴藏的感官本能的释放,让乡村伦理自治与基层权力专制成为政治领域的奇观。天平坚信民意公平在政治伦理参与中的有效作用,但民意无法抵挡物质的诱惑和侵袭,连喜驾驭着乡村伦理的信用和现代物质的诱惑,民意意识与财富意识、世俗利益和道德抉择,在兴儿一家内部的分化中,已经成为乡村基层选举中乡民集体意识的缩影(《普天同庆》)。民间信用与现代资本展开了赤裸裸的角逐,这是对乡民物欲与德性的考验,连喜的胜利宣告了利益与权力的联盟对乡民们所坚守的朴素自治秩序的侵蚀,也彻底击败了传统的民意信义伦理体系(《麦黄种谷》)。
乡土想象:文化共同体的重建可能
现代化和城市化语境当中,乡土逐渐成为殖民话语中的文化弱者,但无论是挣脱还是回归,批判还是怀旧,乡土始终作为农业文明孕育的龙族人的集体无意识与文化基因密码延续和潜行。李俊虎在《众生之路》当中,并不是要唱衰乡村、祭奠乡村,将乡村彻底历史化,而是要在乡村与都市的空间差异性生活和文化之于人的体验反思中,激活乡村文化遗存在城镇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供给潜力,在“乡下人进城”和“进城而返乡”的双向流动中,探幽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更迭过程中,人的存在困境与文化本体的救赎可能。小说中每个乡村图景的横截面,都是复调式的存在,复调构成了乡土世界当中人际冲突与生活沉滞的症结,尊严与自嘲、堕落与坚韧、信义与背叛,那些瞬息万变的人性质地与心灵幽暗,既是生活绝望的渊薮,也是文化重建的基因。小说当中的乡村志,是乡村文明历史的自觉联接,也是乡土逼仄境遇中的现代涅槃。小说试图打破一贯的单向型的城市改造乡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和文学模式,而在现代语境中遥望乡土,在乡土生活中向往现代,这种互动性孕育着城乡关联即乡土重建的希冀,饱含着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进行文化叠加和空间互补,达到世俗安稳与生命飞扬并行的集体渴望,以此来构建一种“文化想象共同体”,即一种城乡文化的共同和深层的文化意识,“在乡村表现为一种‘土地情结’,在城市则演化为‘故乡情怀’”,其内涵是试图实现异质文化的互动,在完美生活的追求中形构一种同质文化,即“城乡文化高度同质化的一种新型文化共同体”,作为思考乡村走向和乡土命运的企图。
首先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乡土守成价值的审视。现代性的歧义、多维和内在矛盾,使得不同社会领域对现代性的演绎面目各异,文化守成普遍性的被视为是现代性的反动力量而备受压抑,乡土文化也在作为文化守成载体的认同中成为当仁不让的被改造对象。“五四”时期现代性的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就包含了对民间文化守成的决绝批判,启蒙现代性曾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代名词;革命时代的政治狂热,在政治领域对改造历史主体的人民性的极其青睐和对个体价值的极度压抑、对人的平等性的极度重视与对人的阶级差序格局的全力颠覆,使现代性的发生在未开启文化启蒙和物质解放的基础上,便进行超越时代的公共性和集体性的意识形态构建,最终演化为一场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政治噩梦,同时也将激进、暴力、革命注入对中国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当中;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受的全球资本化浪潮,将人从政治话语当中解放出来,长久以来的物欲得到了充分释放,保守、封闭、差序的乡土文化在现代化、都市化、物语化语境当中被视为是旧文化和反现代的落后载体,而物欲解放的国家引导到大众认同,同样将强度、速度、效度视为是现代性快速推进的合法方式,“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文化激进、政治激进、物质激进的历史、社会、现实效果,强化着与文化守成的二元结构的对立,但是,现代性对人的过度张扬、对人的能量的高度自信,也让现代性的恶果不断涌现,在现代性无力自救的境遇当中,乡土文化以及由之所衍生的文化守成,乡土的安详、静谧、自足,正展示出其精神家园的诗意魅力,越来越展示出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拯救和诊治的能量功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马林内斯库所说的“审美现代性”、“超越—反思现代性”。《众生之路》在将现代性作为内在文学精神的同时,却超越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和单向度改造的模式,在双向的文化互动当中,审视和构建着现代与乡土的文化互补,并以追求人的自由生活为理想目标。《寻常巷陌》当中二福的发家史和衰败史,正是当代乡村乃至当代中国财富迅速集聚者从崛起到衰落的典型概括,因为物质资本的迅速跃进而文化理性的空缺,在冒险主义的生活方式中,随时可能爆发生存、道德、伦理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乡土稳定的经济自足体系和膨胀的资本侵略体系之间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而翠莲在二福人生起伏过程中所坚守的隐忍、包容、道义、大爱、坚韧,正是文化守成的一种人格与行为呈现,翠花成为抚慰心灵伤害和命运多舛的“圣母”,接纳着对其稳定自足结构破坏的浪子,拯救着欲望牵制下的生命殇者,完成了对现代化的线性历史合法前行的反动和制掣。木匠小喜老汉在渐变时代保持本色的内在坚韧,以及所具有的隐忍、智慧、沉稳的人格魅力,是追求速度、喧嚣、狂躁时代的人性镇静剂。
其次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自然生命哲学的审视。现代性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生命的本体性和自然性,也随之成为人类对自然、对自我认知的伟大理性精神的被认知对象,生命在祛除了绑缚其上的宗教神学、封建道统、狂热政治、民间伦理的种种束缚之后,展示出其裸露的质地面目。现代理性精神,包括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可以对人的思维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规约,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秩序关系进行重建,但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脱性、神圣性、未知性,只能在无限的认知抵近中,确认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存在,它对生命、灵魂、信仰存在的无力感,正是理性精神实施的缺憾。乡土文化当中充满宿命感的自然生命哲学,是依托于东方道家思想的乡村生命哲学,它走出了现代理性精神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代之以自然生命中心主义,乡村文化将生与死视为自然的轮回、宇宙的法则、人生的解脱,它是乡村苦难拯救的朴素宗教,也是世俗追求节制的另类极端参照。《众生之路》当中,云良的死导致了南无村全体村民集体投资的覆灭,在世俗欲望的幻灭跟前,他们选择了以生命的消亡作为解脱苦难、精神拯救的生存伦理哲学参照——“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歹咱还活着,钱不钱的,就算了吧,本来种地的也没那个有钱的命。”面对家族生命延续后继无人的威胁,婆婆与媳妇尽释前嫌,召集子女捐钱完婚,乡村家长制的大义风范,消释了人情冷漠的生活残酷与物语圭臬的人际法则,乡村龌蹉的工于心计和世俗功利遭到了压制,生命延续的自然得到了尊重和敬畏(《百年孤独》)。乡土朴素的生命哲学,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并以生命的坚韧应对着生之困厄,而人的死亡只是生的一种延续,他隐退到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仍然与生之世界发生着关联,并以未知的幽冥力量,监督着生人之行,制造着活之奇迹。这种乡村生命哲学的信仰,是现代理性试图窥视生命而无效的一种反哺,也是对人类主体性力量过度自信的一种质疑,而这恰恰是对现代性对人类欲望肯定的一种反驳,表现在都市空间当中就是个体之人寻找生之意义的结果演绎,在将现代性所幻化出的宏大、抽象的超脱性命题进行祛魅之后,内涵着对此岸世界和日常世俗的认同和肯定。
再次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新型集体伦理的构建。现代性将个体的独立视为最高的理性法则,“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启蒙现代性当中,个体的觉醒成为颠覆压抑其通往自由王国的前提,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过渡中,虽然个体的自由仍然受制于世俗欲望、社会机制、现实困顿等,但个体一定程度上已经能有限度的超越群体思维的禁锢和制约,在质疑和反叛当中构建起一定的理性自由和解放,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新的自由窠臼,孤独、漂泊、绝望、阴郁、隔绝、荒诞等,它们正成为现代国人所普遍经历的精神困境,但人的本质力量又驱动着人不断寻求生存和精神救赎的种种途径,“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应该被否定”,而重回民间集体、重构群体伦理、回望乡土生活,正是经受着现代都市文明精神煎熬的苦难灵魂的心灵故乡,“乡村的不露声色的敏捷性和大城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乡土生活当中人与人聚居所伴随的生活交往和心灵碰撞,消散着世俗层面和潜在精神层面的人的孤独,乡土世界民间伦理秩序的安稳,接纳着漂泊无依的都市浪子的个体灵魂,乡土世界的集体道德伦理的规约,牵制着在自由标榜的自信中可能上演的精神、思想、行为和命运荒诞的发生和消释,也在集体的想象当中,民间和集体成为当代人生存的精神故乡和诗意家园。李俊虎在《众生之路》当中对乡土的留恋是脱离乡土本体内在视角的一种远观审视和现代语境中的回望,它蕴含着对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缺失的清醒认知,寄寓着完善、补充和矫正都市文化弊端的文化构建企图,因此,“南无村”在文化结构和情感结构的编织当中,是心灵孤独和人性渊薮的精神灯塔。南无村的支书和村长,面对祸害乡村的罪人云良的死亡,仍然念及乡情而去祭奠故友(《千年孤独》);翠莲重新组建家庭之后不忘还前夫二福的外债,她的坚守民间伦理“信义”的可贵,是翠莲的寻根行为,一种为子孙赎罪、解脱道德谴责、忧患现在“幸福”生活的预备行为(《五福临门》);秀娟是民间美好品质的集中体,隐忍、仁慈、狭义、慷慨,她是乡村变革格局中的乡土文化坚守者,她剔除了乡土的污垢和陋相,却坚守着诗意乡村应具备的一切人性要素,她的无欲无求、平静自然,是喧嚣现代的宁静良方,也让她成为乡土文化所孕育的高尚人格存在(《五福临门》);兴儿在渐行消失的户家之间传递消息来艰难的维系着乡村的精神共同体,银亮以及所有无土的村民对土地的寻觅,是农民身份被剥夺之后对孤绝生存境遇和都市生存方式的无奈反抗,而他们的微弱努力,让都市不再是欲望、冷漠、看客、自私的卑微空间,而激发出乡土民间的文化力量,显示出超越都市欲望竞争黑暗场景的温馨光芒(《卖黄种谷》)。
《众生之路》饱蕴的乡土之人日常生活的智慧、生命信条、道德伦理、思维方式,以及最核心的人性本真,颠覆了对乡村风情的批判性或神圣化的刻意营造,而在众生之像的雕刻中,呈现出乡土生命的厚重与卑微、乡间民性的坚韧与苟且、乡土文化的稳固与脆弱等多元化的文化结构系统,这是对乡土文明的遥望,更是人文风景的回顾,曾经被现代性所抛弃的生活方式和人伦质素,在城乡空间叠加期,取消了线性的合理,而在彼此的镜像中实现了互补,它孕育着人的生存与文化演进的“轮回”,表征着人性诉求的永恒和相通。
结语
《众生之路》是对现代文明日益侵袭下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悲壮志史,是对一段即将淡出社会主流的民间生活的记忆挽歌,也是对一群经受着生活磨砺、人性裂变和生命疼痛的乡土众生的重生探秘。李俊虎以乡村精神守护神的信仰、决绝与姿态,将理性批判、诗意营造、冷静剖析融入对乡村刻摹的情感当中,极力避免乡土文学书写的单一化和平面化;他将乡土的自足安守与乡村的动荡变迁、乡村的现世面貌和乡村的精神内里等进行“显与隐”的多维空间并置,谱绘着乡土存在的立体与多极,并通过南无村展示着乡土中国的生存结构、精神变迁和文化重组;他将乡村的“质地”作为小说叙事的主题,这种质地是对乡土记忆和乡土历史的虚幻和不确定性的坐实,是对乡土在被宏大叙事遮蔽和改造后的日常生活化的复原;同时,他有意识的突破乡土言说线性叙事和中心带面的结构窠臼,在解构着“单一人物”(人物之间只是故事演进和情节矛盾的“时空联系”)为文本主流的同时,构建着“众生人物”为文本主体(众生人物是精神与生活群像的“彼此联系”),并在“叙述什么”和“怎么叙述”的叙事领域,重建出一种城乡对立格局中“文化共同体”的乡土未来想象,也正如此,《众生之路》实现了对乡村审视的“历史化”和“记忆化”的突围,而在“并置”和“未来”的维度,构建起独特的“空间没落”美学与“乡村志史”的叙事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