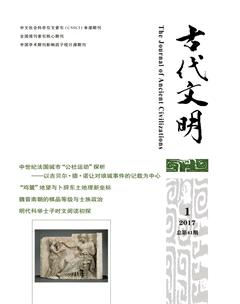赖山阳和他的《日本政记》
张冬阳
提 要:《日本政记》是一部汉文编年日本通史,1845年初刊,是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晚年的主要著作,其议论皆系山阳亲笔,叙事则与门人分担。作为《日本外史》的姊妹篇,《日本政记》体裁严谨,记事简约,夹叙夹议,论古格今,直笔批判,有很强的经世意义,既是赖山阳史论的集大成之作,也可视为日本近世史论的最高峰。其儒家的政治论和诸如“养民造士”、“富国强兵”等主张引领了当时日本的时代潮流,对幕末的尊王攘夷与倒幕维新,以及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诸多设施,都有不小影响。
关键词:赖山阳;《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史学;日本汉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4
在日本山口县档案馆,藏有一套《日本政记》手抄本(共三册,原藏山口县图书馆),系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年)遗爱。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十二日,22岁的伊藤博文(时名“伊藤醇”)与井上馨(1835—1915年,时名“志道精”)等长州藩士结伴,在横滨登乘英国轮船前往英国,随身即带此抄本。其扉页上有伊藤、井上联名题注:
《政记》若干卷,艺国赖子成所著。书中概举吾朝政治所系,论定之,又以足审古今成败之迹矣。然而今将携之海外,虽于此行,素为无用之书,又将有望于归来之日者也?文久三癸亥四月十有三日,志道精、伊藤淳志。1
当船行驶至北冰洋时,伊藤博文读书有感,又在书后题写跋文道:
山阳赖子成所著《政记》若干卷,读之以足识祖宗开辟来二千有余年之事矣。其间世之变迁污隆至于今日者,又可以观矣。然而我王朝衰弊,武臣倨傲,又无甚于今日者。一读此书,不起勤王之志,虽知亿万年之古之事,何益之有!于是乎书焉。北冰洋漂荡志。2
《日本政记》16卷,16余万言,江户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年,名襄,字子成,号山阳、山阳外史、三十六峰外史,通称久太郎)所著,是一部汉文编年日本通史,论述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至后阳成天皇(1586—1611年在位)的史事。该书对幕末的尊王攘夷与倒幕维新,对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诸多设施,都有不小影响,声名远播海外。至今北京故宫仍藏有一套1845年初刻的木活字版《日本政记》(一函,十册),印刷精美,装帧考究,乃光绪皇帝“御览本”,上以朱笔标点、注音与纠误,每卷末钤藏书印,其所受重视可见一斑。
《日本政记》倾注了赖山阳晚年的主要心血,是其另一部重要史著《日本外史》的姊妹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1858—1927年)编写《日本书目志》,搜集对新政有益的日本书籍,作为《日本变政考》的参考文献与后者一起进呈光绪皇帝。在《日本书目志》中,打着“增补”、“校刻”、“校正”、“标注”之名的《日本外史》、《日本政记》诸版本,比目皆是。1可是,国内外研究赖山阳的学者大都聚焦于《日本外史》,而对《日本政记》重视不足。2其实作为“伊藤博文公最爱之书”,3撇开文笔、体裁与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单从影响看,《日本政记》也是一部够分量的日本史学名著。本文论述该书的撰写经过、体裁思想特点与版本等情况,以补学界之缺。
一、《日本政记》的成书经过
赖山阳于安永九年(1780年)生于大坂,出身书香世家,是安艺国(今广岛县西部)广岛藩学头赖春水(1746—1816年)独子,叔父春风(1753—1825年)、杏坪(1756—1834年)亦为名士,“举族皆以才名动天下,犹宋时眉山有苏氏”。4他“幼锐敏,崭然见头角”,518岁入昌平坂师事尾藤二洲(1747—1813年),21岁因脱藩被软禁废嫡,30岁投奔备后(今广岛县东部)大儒菅茶山(1748—1827年),32岁再度脱藩自立门户。他自称“非仕途人”,“天资疏狂,不能从物俯仰”,乃“放浪自适”,“喜平安山水幽秀”,“乐居之,托迹市陌,杜门戢影,除看竹寻花之外,未尝与人相往来”。6文政五年(1822年)冬,买家于京都三本木,家称“水西庄”,庭中草堂称“山紫水明处”,“身优游于京华最胜之地”,7“批山批水,诗酒自适”,又广收门徒,“来学者相踵于门”,8使“关西文坛的主导权几乎全归入他一人之手”。9平生“以气节自持”,“未尝屈己随人”,“诸藩多聘之,皆固辞不应”。10“不独不仕,誓不踏王公之门。”11卒于天保三年(1832年),年五十三。其文、诗、书三绝,僧人大含(末广云华,1773—1850年)视作“本朝东坡”。12斋藤拙堂(1797—1865年)也认为,“髯苏以后七百年,无此风流也。”13
赖山阳“尤留心于史学与经济”,14抱负颇大,“古今史籍制度、兵法及家谱野乘,无不涉猎”。1其《日本外史》22卷,30余万言,“综武门终始”,2乃“生涯精神所注”,3写自21岁被软禁,于28岁初稿告成,“以所谓无求之心著书,取其简约,自便省览”,故“拮据二十余年,藏之箧笥,未尝示人”。4文政九年(1826年)冬,山阳47岁,在送二门人归乡的诗中有“廿岁杀青书才就,一宵浮白酒方酣”之句,诗旁题注道:“时余删改旧著《外史》方成”,说明了《日本外史》的基本定稿。5然“此书事实恐考索未备”,“未肯示人”,称“虽无求于今日,而不无求于千百载,非经大贤之鉴识,不足以保其传也”。6
松平定信(1758—1829年),字贞卿,号旭峯、乐翁(也号风月翁、花月翁),陆奥国白河藩主(1812年转封至伊势国桑名藩),系将军德川家齐(1773—1841年,1787—1837年在职)伯父,八代将军吉宗之孙,曾于天明七年(1787年)至宽政五年(1793年)任首席老中与将军辅佐,总理幕政。他执政时励精图治,“巩固了至19世纪中期为止幕府的政治基础”,7后虽“勇退高踏,久处闲地”,但“犹巍然系朝野之望,所谓儿童走卒皆知识之者”,8仍有国家大事的顾问权,是政界最有声望的元老。文政十年(1827年),松平定信听闻赖山阳修史有成,乃命人“来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赐览观,礼意殷勤”。9赖山阳“窃以其元老劭龄”,认为是个契机,能“取信于天下后世”,乃“不敢迁延,以未定辞,速缮写应命”,10
抄一部献上,并作《上乐翁公书》。该书仿北宋苏辙(1039—1112年)《上枢密韩太尉书》之意,自称“布衣赖襄”,详述著书旨趣。文中有关“义例”部分,如“右族迭兴,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故依实创体,以形世变”等语,大触德川氏之讳,相当尖锐,对此山阳都能以所谓“无求之心”坦然论说,展现了他的史家风骨。11
收书后,松平定信从文政十年(1827年)六月十一日开始阅读,至七月五日读完第二十二卷。“既览,手笔题数言其后,大意曰:叙事适繁简之宜,论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机先。”12遂将自己编纂的《集古十种》一套(二函)与银币二十枚回赠作谢礼。此后《日本外史》洛阳纸贵,姬路藩主酒井氏、彦根藩主井伊氏、米泽藩主上杉氏与广岛藩主浅野氏(山阳旧主)相继索求。13泷泽马琴(1767—1848年)亲抄一本,称“其文佳妙,论辩可听,有史才”,秘藏于家。大盐中斋(1793—1837年)也从山阳处获赠一部,“喜谢以其佩刀”。14
松平定信的首肯,无异为赖山阳私撰史书提供了护身符,强化了他修史立言的使命感。他说:“人有贵贱之相悬,如天地之隔,而知遇之无间,出意念之外者;况昔之所目仰,而今之神契焉!”15山阳“既恃经老侯之许,又感受其知”,16创作热情受到鼓舞,于是始著《日本政记》。
《日本政记》初名《国朝政记》,17约在《日本外史》献上后动笔。文政十一年(1828年)底赖山阳的咏史诗集《日本乐府》,即为撰写《国朝政记》的副产品。山阳年已半百,精力日衰,“自谓性质钝劣,发白齿落,颓然成翁,不知功绪之可见,在不死前者”。1身为儒者,他“自恨解经尚少”,2开始研究《春秋》等典籍。身为文人,他也有计划地整理毕生散文,集成《书后》与《题跋》,作为自家学术精粹。他有感于日本当时的内外危机,又作《通议》二十八篇,宣扬自己的经世说,并以史论的形式加入《日本政记》中。
天保三年(1832年)六月十二日,赖山阳开始咳血,名医新宫凉亭(1787—1854年)认为“是积年劳神所致,所谓‘肺血疾”,以“先生豪杰不怖死”,据实告以不治。3是夜,他召来牧百峰(1800—1863年,名輗,字信侯,号百峰)、儿玉旗山(1801—1835年,名慎,字士敬,号旗山)、关藤藤阴(1807—1876年,养家姓石川,名章,字君达,号藤阴)三名弟子,出示《日本政记》十六卷,分派手稿的修订任务,说:“死生有命。然我上有老母,且志业未成。假令无一生理,宜加医疗,我慎服药,傍为死计耳。”4此时《辽豕录》(赖山阳《春秋》讲义)、《书后》、《题跋》、《通议》诸书皆就绪,“志业”即指《日本政记》。七月七日,山阳在给中川渔村的信中说:“仆以将死觉悟整理著述(《日本政记》),议论大体已了,记事恐死后乃成。虽然,此一片精神依然。天欲成此有用之学乎?仆未遽死也。”5八月八日,赖山阳将《日本政记》记事的修订工作全部委任给牧百峰和关藤藤阴,称书成后可署其名,6嘱咐二人务必尽心完成,自己则专意于史论。此时他“疾益剧”,“乃日夜勉强构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7“其在病床,尚不辍笔,且草且呻。”8九月,《日本政记》最后一篇《论丰臣氏检地》完成后,山阳作《国朝政纪稿本跋》,略述著书旨意:
向乐翁公索余《外史》,既览,手笔题数言其后,大意曰:“叙事适繁简之宜,论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机先。”侍臣月堂窃写寄示。余感知己之谊,又有以自劝。其后作《通议》二十八篇,泛论古今制度、政体得失。近又仿荀悦《汉纪》之意,修《国朝政纪》,起于开辟,至于晚近,记其大事;作论八十余首,于所谓“不任偏私,洞中机先”者,未知能不负公言否乎?而公逝已四年矣,襄今亦获笃疾,殆乎不起,俯仰今昔,抚卷慨然。9
作为一生绝笔,赖山阳对《日本政记》的苦心,主要体现在议论上。九月十一日,他在给筱崎小竹(1781—1851年)与后藤松阴的信中说:“拙著《政记》,展观日本史事,实论经世之务……其事迹让于《外史》,而议论尤多……皆关世道人心非小者也。”10
《日本政记》在后龟山天皇(南朝第4代,1383—1392年在位)“两统合一之条”,本“已有一论”。11天保三年九月十二日,来客猪饲敬所(1760—1845年)就南北朝正闰发问,称“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讳?”12触动山阳心事,“欲极论之,而有肺疾不可剧谈。”13猪饲走后,山阳对门人江木鳄水(1810—1881年,名戬,字晋戈)说:“苟以北朝为正统,岂以新田、楠诸公为乱臣贼子乎!”“方言之之时,目张眉轩,其慷慨激烈,虽病不衰也。”14当夜山阳“咳不能寐,就枕头腹稿,明日录稿”,作《正统论》,附于初论后,事在其殁前十日,“病困棉缀,精神止此,不能精思也”。15九月廿一日,山阳忽曰:“犹有不可不言者在焉!”“即日草之,《内廷篇》是也”,加入《通议》之中。1
天保三年(1832年)九月廿三日清晨,赖山阳病革,自感神志不清,气力尽失,曰:“我死方逼矣!”2于是卧床向关藤藤阴口授《日本政记》的修订事宜,由关藤执笔写作,他则戴着眼镜在枕上审查进度。午后六时许,正在别室续稿的关藤藤阴被山阳召回病房面授机宜,儿玉旗山一旁侍坐,山阳“忽顾左右曰:‘且勿喧,我将假寐,乃搁笔,不脱眼镜而瞑;就抚之,则已逝矣”,《日本政记》因“记事多成于病中,而终不得全脱稿也”。3
作为在门生协助下的作品,《日本政记》只有议论全部出自山阳之手,且由本人亲自校正。山阳执笔的记事部分,止于元龟元年(1570年)姊川合战。从元龟二年至最末庆长三年(1598年)这四十年的记事,皆由关藤藤阴一力承担。关藤的记事有不少参考《日本外史》而来,故与《日本外史》颇多雷同。作为山阳以外《日本政记》的主要执笔人,关藤藤阴有“校史身曾补缺文”、“千疮百孔犹如斯”之语,自认“校雠未详”,多有纰漏。4明治九年(1876年)六月,赖支峰(1823—1889年,名复,字士刚,号支峰,通称又二郎、又次郎,山阳次子)在《增补日本政记》例言中介绍成书经过道:
余先人尝著《日本外史》,作者例言所谓“阃外一典”者;晚年自谓“王室之事亦不可不记焉”,乃因吕氏《大事记》著此书。于是《政记》为经,《外史》为纬,虽私史,合二书本邦事迹一瞩瞭然、略得具备焉,是作者本旨,读者不可不知。
此书先人起草未几,罹笃疾,尚能力疾构稿。记事则开辟迄永禄间先人身亲记之,元龟以降使门生关君达记焉。君达后附托一本水藩丰田天功,以使正记事。今复重订以上梓,亦未能莫谬误。要之先人病间所著,而遂易簀,其缺校雠,则职是之由,读者请正焉。5叙事简约扼要。其雏形可追溯至赖山阳早年所作“三纪”:“提起神武,至后阳成,大事为三卷”,“以其事略,不谓之纪书”,故亦名为“统略”。6文化四年(1807年)三月十一日,山阳在向池口愚亭介绍《日本外史》的信中也曾披露著有“年表一卷”,系“编年大事记”,“可知皇朝世次与诸家合观处”,但亦仅视为《日本外史》绪余,不深留意,7直到晚年方在其基础上附加议论,扩写成书。
针对《日本政记》体裁,赖山阳自称是“仿荀悦《汉纪》之意”,赖支峰称“乃因吕氏(吕祖谦)之《大事记》”,黄遵宪(1848—1905年)则以为“实仿朱子《通鉴纲目》”。8其实无论《汉纪》、《大事记》还是《资治通鉴纲目》,都是简化的编年体,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方便实用,由此也可看出《日本政记》的宗旨所在。明治九年(1876年)佐藤牧山(1801-1891年)在其《日本政记摘注》自序中说:“先辈山阳氏《政记》一书,缩二千年行事于数卷,举其大紧要处,足以观治乱、识成败、考存亡、辨得失、知世变,了然如指掌。”9
比起“刻意锻炼、经年乃成”的《日本外史》,10赖山阳作《日本政记》仅用三四年,得多人相助,“不甚费力气”,正因“编年依年月直叙,作者易,读者亦易”。1从创作动机讲,《日本政记》补充《日本外史》的用意非常明显。《日本外史》状人叙事,“要详各家兴废,以资览观”,“故多琐细难快读处”。2加上“事系一姓之下,而不有统纪以总之,列将家而杂以雄长,举今代而称谓论说”,义例有“欠尊崇者”。3且既以征夷大将军为“正记”,又将南朝武将新田氏“扶正”,“创未曾有之体”,4也难以自圆其说。岩村南里(1784—1842年)论《日本外史》体裁道:
盖镰仓氏以降,武人代管辖天下,必受征夷之宣于朝廷者,而后乃得列“正记”,所以正名分而一统纪,其意固美矣。然新田氏未膺征夷之任,特以专兵马之权,得列“正记”;而织、丰二氏,总军国之重,顾以无征夷之拜,置诸“前记”。一与一夺,自乱其例,有未厌人意者。5
《日本外史》本为各家单独立传,“家别纪之”,6最后合为一书,临时附加“正记”、“前后记”的名目而已,“大抵主明白质实,直写情势,不敢文饰”,“特其中以帝王年号几年几月,表明条理耳”。7赖山阳深知《日本外史》“招外人指摘者,混称姓氏也,以割据豪雄列主将之统也”,早年亦“尝欲作年表大事记冠之,未果也”,8所以将书公开后,即撰《日本政记》补其缺。《日本政记》始自神武,迄至近代,以历代天皇为序,以皇室为中心,以南朝为正统,体裁严谨。“今朝廷者,神武以还大一统之朝廷也。”9比起《日本外史》,《日本政记》“正名分”、“序皇统”之意浓厚。“忠于皇室即忠于祖宗”,“南朝忠臣即祖宗忠臣”,是《日本政记》一大主题。不过赖山阳的皇国思想虽强烈,与国学者的复古神道仍有本质区别,因其理论基础来自儒学。在“崇神天皇论”中,山阳道:
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故敬神无如务于民也。世之称神道者,悠谬荒诞,而无益于民,皆崇神之罪人也。吾尝称:“王业衰而神道兴”……当王政盛时,谁敢腾之口舌,以树私说哉!10
《日本政记》的儒家史观,不但体现在对神道的抨击,其对佛教攻排尤甚,视为败坏伦常、亡国灭种的祸根。“崇峻天皇论”道:儒学与佛说,皆自外国来者,无择也。而佛说一入吾国,有好之崇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学叙人伦,平易无可喜,其文虽外来,而其实固在我,不如佛说之新异,宏阔夸大,足耸人听也。吾尝读三韩之史,其君之惑于佛说,以致乱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佛说……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烈于洪水猛兽之害。奸雄之人,每借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条、足利之崇禅教,莫非宗此旨也。我邦君臣之义,度越万国,而西竺之说坏之,归之于土灰沙尘而止焉。而开其端者,厩户(圣德太子)、(苏我)马子也,可胜慨哉!千载之下,独织田氏断然不惑,庶几匡正祖宗之国者矣。是以今之佛说,行于愚夫愚妇,而为人上者之信之,不至如古昔之太甚,是我邦之幸也。11
赖山阳的“佛教祸国论”慷慨激昂,似乎正是明治初年“废佛毁释(排佛弃释)“运动的理论来源,《日本政记》的儒家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山阳51岁开始治《春秋》,称“《春秋》之旨,在我国,最似不可不识,而未有专攻者”,12将注本命名为《辽豕录》(初名《春秋臆断》),借用“辽东豕“的典故,犹言“井底蛙”,以示自谦与自嘲。和早年仿《左传》、《史记》著《日本外史》一样,山阳的《春秋》研究现学现用,与同时撰修的《日本政记》息息相关。《辽豕录》在卷首“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一句注道:
是夫子开卷第一之特笔也。盖正朔者,王者既命统,所以一天下也。当时诸侯所用,皆周之正月也,苟用之,朝觐贡赋,不可不以致臣职也。而忘其出于周,无致臣节者,故夫子先揭之,以示在今日之天下者,无一人不为周臣者,可谓明白著见矣。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左氏曰:“春,王,周,正月。”公羊氏又曰:“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是皆其得经旨一端者也。1
《日本政记》开篇记神武天皇道:“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于大和橿原宫。”2明白效仿《春秋》笔法。《日本政记》模仿《春秋》的微言大义,历代天皇篇首皆用“天皇即位于XX(宫殿、行宫名)”的统一模式;对于名实不相符的,如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则书“壬戌岁,春正月,皇太子素服制军国事”,登基后再补上“天皇即位”。3又如未曾登基的大友皇子,《日本政记》称为“天皇大友”,虽不书“即位”,仍以一代帝王置于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前,其死曰“崩”。4山阳称“《春秋》之书,有文例,有特笔,有隐讳,是三者而已。有文例,以知彼此之可推;有特笔,以知大义之所系;有隐讳,以知不忍言国恶。”5《日本政记》亦复如是。国学者清宫棠阴(1809-1879年)道:
子成作《政记》,书法谨严,义例简明,以故奄有群史。且立论正大,能出新意,其所言皆人人欲言;不得言者,如书仲哀大皇“病崩”,书阿倍仲麻吕“死于唐”,至神功、应神书“称帝、为皇太子”,至和气清麻吕则书“具官”,此等皆出特见。而天皇驾崩必系年月、立后必书其父之类,通观二千年,一丝不紊。又如以陆奥浮浪之徒戍边,及建武中兴诸论等,最为得当。噫!士生于世,以铅椠为业如子成者,可谓不愧其所学!6
江户后期尊王论甚嚣尘上,《日本政记》体裁严谨,顺应了时代思潮,但一定程度也意味着记述的失真。黄遵宪说:“正闰之辨,为史家聚讼之端。至朱子法《春秋》作《纲目》大书以纪年,论史者尤于此龂龂焉。然余考统系绝续之交、疆域分析之世,古今事变至多,欲强举正统以归之谁某,终不能执一义以自圆其说。”7对《日本政记》国家起源与涉外思想中的“日本本位主义”,黄遵宪也视作“儒者拘墟之见”、“文人浮夸之习”,8说:“《梁书》言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记载本以此为荣。其后学者渐染宋学,喜言国体,宽文中作《日本通鉴》,源光圀驳议曰:‘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遂削之。赖襄作《政记》,并秦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9“源光圀作《大日本史》,青山延于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而弗道”,《日本政记》继承这一隐讳,“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10
由于体裁“无懈可击”,《日本政记》的记事也显得刻板与程式化。冈鹿门(1833—1914年)比较《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优劣道:
《外史》起于源、平,实仿《通鉴》始于韩赵魏为诸侯,寓惩武门僭乱之微意,深得《春秋》笔削之旨。然此书揭霸统,举朝廷之赏罚黜陟归源、平二氏。故幼童若熟此书,唯知源氏、织、丰,而不知有朝廷。此但长奸雄之心,去笔削之旨甚远。赖氏果若欲师《春秋》,则宜首揭大统,大书特书,以表大一统之意。当如北畠准后《正统记》、习凿齿《汉晋春秋》。赖氏不虑及此,将欲何为?
赖氏晚年著《政记》,盖悔《外史》之体裁,特撰此书,以掩前失。其书颇用力于议论。至记事,则汇集群书,其文拉杂。或云:赖氏属稿未半,罹疾,其记事多成于门人之手。其文不妙,固其宜也。《外史》行文畅达,足称良史,而体裁欠妥;《政记》议论剀切,而事迹拉杂。11
三、《日本政记》的史论特点
《日本政记》的重点不在记事,而在议论。赖山阳“以经世之学自许”,“平日以人伦世道自任,抵死不衰”。1他年少气盛时素有澄清天下之志,好论兵政世务;后来虽以处士终其生,未尝一试,却“无念不系属朝廷,无时不痌癏民物,感慨流连,情见乎词”,2将胸中抱负悉数带进著作里。身为史家,他明知“史,记事而已,赞不赘疣”,3却依然在《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中插入大段议论,甚者累累上千言。对此他犹嫌不足,更有《新策》、《通议》两部论文集,尽情宣泄自己议论国事的欲望。《新策》完成于文化五年(1808年),分为“六略”、“八议”与“二十三论”,“梳其治乱之概、制度之略、兵食刑法之沿革”,4主要模仿正史志书、先秦诸子、贾谊论策、苏轼论策与明清制艺文,是山阳史论与政论的开山之作。《日本外史》虽以状人叙事为主,却也有序论、论赞共18篇,“俯仰古今,感慨系之,其中亦有分疏已修撰之意者矣,有补足叙事所不至者矣”,5与本传相得益彰。山阳晚年,“文益精,识益确”,6又将《新策》删订为《通议》28篇,“通论古今和汉”,7阐发“学之所诣、志之所存”,8
自称“蜻洲开辟以来,经世之文纵横极论者无出于此”。9《日本政记》与《通议》同时撰写,最后告成,共有论文92篇,汇集了《日本外史》、《新策》、《通议》的精华,是赖山阳毕生议论的集大成之作。天保九年(1838年)四月上旬,林靏梁(1806—1878年,名长孺,通称伊太郎)为“拙修斋丛书”《日本政记》作序道:
《政记》之书,自神武至后阳成,凡百有八世,上下二千年,教化之隆替,纪纲之张弛,盛衰治乱之交代,莫弗记载焉。间亦加以其平日所见,可谓其论痛快、切当事情乎!余谓,天下之论政者何限,要皆不能出乎山阳之右。而《外史》、《通议》亦皆言政之书。而《通议》仅仅二三卷;《外史》虽卷帙浩瀚,大抵止记人之忠奸淑慝,二书皆不若《政记》之博且详也。然则天下之论政者,莫善于山阳,而山阳言政之书,莫备于《政记》。呜呼!山阳虽不在位,而识者或取,以供其赞治辅化之一助,能出察机慎微之政,使人士奢侈之风止,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亦莫足道者。10
赖山阳“殚毕生心血者,《外史》也,弱冠起稿,强仕就绪”,“上乐翁公后,犹加笔削”,“用心不苟”,“故叙事明快,考证精确,世谓不让马、班”,至于《日本政记》,“其本志在概论治乱兴亡,不在深考事迹”,“于是摭录事之关大体者,冠论首,以期参观领要”。11《日本外史》虽有议论,但“皆指隐微难言之情事,半吞半吐”,“自叙编述之意,或取与叙事相发,不敢甚高论”。12而在《日本政记》中,议论则突破了附属、陪衬的框架,篇幅浩瀚,畅所欲言,与记事相辅相成。“叙事中有议论者,史也;议论中有叙事者,子也。”13《日本政记》“半史半子”,特点突出。明治七年(1874年)正月,石津灌园(1843-1891年)为林南轩(名正躬)《日本政记考证》作序道:
予谓,《政记》与《史略》诸书稍异。盖《史略》主于记事,以便后学;《政记》则主于论断,以审治术。譬如讼狱,记事为讼词,论断则为法律。由讼词征法律,据法律断讼词。史学上,记事、论断相须亦犹是。其相兼者,即《政记》之体然。1
《日本政记》的议论围绕重大史事与主要人物展开,论点以儒家德治主义为基轴,在高举大义名分时,能就事论事,强调即使有名分也应有善政,从而弥补了体裁上的形式主义缺陷。赖山阳推崇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认为帝王应“刚健勤政”,2称“所贵于人君者,刚也,健也”,“自古守文之君,生深宫,长妇人手,坐享成业,谓其当然,不肯励精勤政,外威严而内懦怠,惮见外廷公卿,而好居于内,委祖宗之天下于他人而不省者,比比皆是”(文德天皇论),“仁明寿四十一,文德三十二,其不永年者,亦不勤之效也”。3《日本政记》强调皇室婚姻与立后建储的重要,称“人事莫重于继续,而继续原于婚姻,二者,祸福之所由分也。”4“国家盛衰之机,每由于继续之际”,“爱憎主其中,而党援乘其外,大利所在,大祸所伏也”。5山阳批评圣武天皇“听宫闱之劝”,“不能制其妇也”,以致大权旁落,“积之如筑山,而丧之如燎毛”。6称“冷泉、圆融、花山之际”,“以帝王之贵、宰辅之重,宗庙社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废立黜陟,一依闺阁之私”;藤原兼通、藤原兼家兄弟争权,“至以天位博弈”,“其噪竞无耻,狡悍不忌”,亦“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将祸根直接归罪于天皇“不慎其德,欲败度,纵败礼,以私灭公”,终于“使权下移”。7对崇德天皇,《日本政记》更说“举朝之士皆丧心者也”,“君臣徇私,廉耻丧亡,国家纪纲所以维持天下者,无一存者”。8如果说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的潜台词是“武臣勤王”的话,那么《日本政记》的主要命题则是“天皇亲政”。《日本政记》批评后世朝政的反面,即是对上古帝王“画一之政”的赞美。9山阳在“孝德天皇论”中说:
大凡国朝,以简质治民,上下同心,国如一人,是国势所以威四外也。及通隋氏,变质为文,殆失其故。及至天智,百度大定,后世莫改,大抵取于李唐之制,而所以胜于唐氏者,曰“立吏简,取民廉”,是不失我邦固有之美也。后王之过于模仿,文缛太甚,务于刻剥,则不达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门之始,民反便之,未必不由于此。虽然,武治有其简,而无其廉,所以不如王政也。10
江户时代“崇儒重道”,“人人知儒术之贵,争自濯磨”,“文治之隆,远越前古”。11《日本政记》明言快论,言之凿凿,从体裁、文笔乃至思想都相当纯熟,可以说反映了儒学日本化的最终完成。《日本政记》“应神天皇论”道:
道一而已矣……我邦列圣,保民如子,不让尧舜禹汤,其风俗尊君亲上,相爱相养,又有过唐虞三代之民。则虽无经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义”者耳……今天下之仁义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汉之道也!”有称国学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岂有彼此!载之以文,彼较旧于我,彼来而贡之,我取而用之,与酿冶织缝之工何异!12
19世纪初的文化(1804—1818年)、文政(1818—1830年)年间,市民文化达到鼎盛,《日本政记》吸收了明末清初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江户中期以来的“社会批判思想”,13史观上比“名分论”更突出的是“天道论”,认为民心、士气才是立国之本。“政贵实,不贵名”,“国与民,相须而存者也”,“天之立君,为民也,非为君也”,“夫天托一人养万民,非取万人养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俭以恤天下”,“官爵,名也;权力,实也。名出于朝廷,而实出于天。天以其实与源氏,曰:‘是尝竭力于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实,而朝廷拥其名而已”。14北条氏“终于相摸守、武藏守”,而“敢废立天子,进退宰辅,易置大将军,如弈棋然,而其家得传九世”,正因其“自俭勤以养民,是不有天位而为天职也”。1《日本政记》末尾论丰臣氏检地,称其“剜未剜之肉,浚未浚之膏血”,此“一举而丧先王之泽、绝天地之性、夺生民之命”,“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2除了“民本说”,《日本政记》还有“士气说”,认为“士之气节,关系天下国家”,“国之有士气也,犹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无楫则覆,家无柱则倾,国无士气则亡”,“国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气之振与不振”。3
赖山阳“有用世之才,不得一试,而发诸史笔文章”,4以“泄其牢骚不平之气”,5其论大江广元,称“抱济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为不幸也”,也隐含对个人身世的感慨,国家“所以兴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废且乱,出于其相远,无和汉古今一也”。6“自古国家之乱亡也,必由其威权陵替,纪纲废坏,而英雄之人树大功其间,是以能操其权、遂至移其国者皆然。”7《日本政记》对源赖朝、楠正成、丰臣秀吉等草莽英雄的讴歌,其“英雄不失机”的论断,8与幕末志士相共鸣,也为萨、长诸藩的“造反有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滞而不上;上下之间,痞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于下,必然之势也!当是之时,英伟俊杰之士,多生于下;而上者,皆猥琐顽钝无耻之人,是之谓气运之变,故其势不得不反覆也。9
由于赖山阳的庶民身份和狂放性格,他在《日本政记》中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思索,以及对天皇以下显贵权门无所顾忌地批判,使该书“又超出了单纯的史学、文学的范畴,带有社会启蒙、政治纲领与思想宣传的意味”。10大盐中斋就说山阳“有胆识”,“于人之难言时事,彼独能开口言之,而无有忌惮之情态”。11山阳“大众的正义感”12是《日本政记》史论的魅力所在。元治元年(1864年)五弓雪窗(1823—1886年)著成《政记存疑》,称“其言脱腐苛,洞观二千余年人情世态,俾忠奸两服于九泉,亦谓‘本朝金鉴录可。”13明治六年(1873年)五月长三洲(1833—1895年)为长川东洲《读外史余论》作序说:“山阳著书如钱谷药饵,医时济世,兴发人心,功所博及,至今日大政复古之盛,山阳书与力尤甚。”14明治十四年(1981年)二月廿三日,龟谷省轩(1838—1913年)作《请褒赠赖襄上书》,称“当时幕府威权炽盛,不可触犯。襄独抽直笔,不避强御,论古以格今,其心诚苦矣……其感奋振起,不知几千万。推而论之,谓维新之业,襄与有力焉,亦可也。”15
《日本政记》史论常“合典故于和汉”,16“借汉事形和事”,17以中国史事、人物作参照,也体现了赖山阳的学术个性。山阳“经说归主洛闽,而不甚墨守,要以通古圣贤立言大义为务”,故“其议论以适用为主”,18不拘一格。《日本政记》论题丰富,往往借题发挥,涉及政治,军事,法律、社会、经济、哲学诸多领域,不少地方“辨博纵横”,1“出人意表”。2山阳称“夫先秦诸子,乃天地精华所钟”,3“礼乐,治治世之具,不可施之乱世”,4故好讲“势”论“术”。筱崎小竹(1781—1851年)就说他“不论知人,而论分权”,“恐与孔氏异宗”,5虽“言近而易行”,却属“申、韩口气”。6古贺穀堂(1778—1836年)则赞其议论“大率经济家所忽”,可“噤俗吏之口”,论兵又“噤兵家之口,足为儒生文人吐气”。7赖山阳酷好《孙子》,称“古书平易而精妙不可逾者,唯《论语》;可配《论语》者,唯《孙子》十三篇而已”,他崇尚武治,认为“武治简率,无论无比”。8“吾邦以武立国,中古以来,又统治于武门,官制士伍,皆寓阵法,治农政,通财赋,皆袭战国之旧,是各藩之所同,所以政简事省,国势常强,非外国之所及也。”9“先王常自俭以抚其民,所以丰其食”,“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诸国,是王政所以兴隆,礼文所以备具也;其后徒事礼文,而遗其本”,“而委兵于将吏”,“是王政所以衰颓,而武门代之兴也”。10“国之大政”,“曰兵,曰食”。11“兵
权在上,纲维可挈。”12山阳喜谈地理,《日本政记》屡言“京师形势之劣”,称“京师形势,本不及关东,故北条氏、足利氏皆据关东为巢窟,以能制朝廷”,13也成为日后皇室东迁的先声。
江户时代以史论见称的莫过新井白石(1657—1725年),被推为“德川氏一代伟人”,但“其论大率以和文”,文笔与山阳相去甚远。14
《大日本史》标榜“据事直书,劝惩自见”,15虽有安积澹泊(1656—1737年)的论赞,却被日趋保守的藩政批评,于文化六年(1809年)被删,因水户藩“顾身属懿亲,未敢昌言”。16青山延寿(1820—1906年)称当时史家“各议论则醇中儒者也,不似山阳纵横萦论矣”。17《日本政记》篇幅合理,内容完善,简明实用,集学术、通俗性于一身,是满足市民阶层知识需求的普及读物。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称山阳“不及兼攻海外之学”,“规局偏狭”。18德富苏峰(1863—1957年)拿本多利明(1743—1820年)、佐藤信渊(1769—1850年)相比,称山阳“不通世界思潮”,“毕竟书斋论客”,19都是后人想当然的苛求。《日本政记》史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突破了一般史学的范畴,是当时史书中所仅见的,称为“日本近世史论的最高峰”,也不为过。
四、结语
弘化二年(1845年),江户下谷御徙町,中西邦基(1796?—?年,名邦基,字伯基,号拙修,通称忠藏)用木活字将《日本政记》作为“拙修斋丛书”之一出版,附加天保九年(1838年)林靏梁序文,是《日本政记》最早的刊本。此前该丛书已出版过《日本外史》与《通议》。嘉永年间(1848—1854年),丰田天功受关藤藤阴委托校阅《日本政记》,山阳门人后藤松阴(1797—1864年,名机,字世张,号松阴)与冈田鸭里(1806—1880年,名乔,字周辅,号鸭里)也参与了后期修订。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由京都赖氏当家赖支峰授权,在大坂书商河内屋吉兵卫(浅井吉兵卫,号“龙章堂”,广岛士族)等主持下,赖氏正本《日本政记》在大坂刊行。书用“山阳遗书刊行之记”印,标名“赖又次郎藏版”,末尾有五人列名“同校”:“男:赖复,门人:后藤机、牧輗、石川章、冈田乔”。拙修斋本与赖氏正本差异较大。据《国史大辞典》“日本政记”条,在幕末二十年间,《日本政记》至少有四种异本;明治后在活版外还出过四种木刻版。明治九年(1876年),赖氏正本出“增补本”。明治十九年(1886年),“增补本”改刻,补入了关藤成绪(1845—1906年,关藤藤阴之子)家藏资料。昭和七年(1932年)《赖山阳全书·全集·中卷》所收《日本政记》,以文久元年赖氏正本十六册本为底本,参校明治十九年增补本和拙修斋本,参考五弓雪窗《日本政记考异》(1卷)、林正弼《日本政记考证》(2卷)、雨森精翁《日本政记札记》(16卷)和《日本政记正误》(1卷),是最好的版本。
幕末至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历史读物是《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人气虽逊,但因简明实用的特点,也有像伊藤博文、近藤勇(1834—1868年)这样著名的拥趸。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年)与日本人笔谈时,称“山阳史笔极有生气,识议亦高”,推为日本史家之首。1赖山阳的历史观、国家观与近代“大日本帝国”同声气,故其著作为官方推重,并在战时被用来煽动国民情绪。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外史》与《日本政记》,多系近代由日本人带入。尽管日本在二战后的教科书中抹杀了赖山阳,《日本政记》仍不失为一部前近代的史学名著,在东亚汉字圈拥有广泛的声誉。
《日本政记》作为赖山阳史学的代表,以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学技巧演绎日本历史,是江户时代尊崇汉学的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毕生崇拜者,赖山阳的经世之学,也不外乎将中国政治军事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与日本人过去的历史经验嫁接起来,仍未跳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尽管如此,《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书还是引导后人走上了“王政复古”、破旧维新的自强道路。相形之下,同样讲求“经世致用”的清朝,在面对西洋文化冲击时却未能力挽狂澜,而是任由大树凋零,其中原委,犹值得国人深思。研究赖山阳的学术,不独对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于中国的史学、文学与思想界,对于中国人反思自己、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有不小的意义。
(责任编辑:孙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