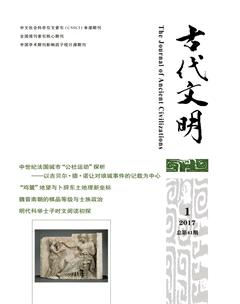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孙卫国 解祥伟
提 要: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关键词:明代中朝关系;抗倭援朝战争;朝鲜宣祖国王;“信任危机”;朝日关系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3
朝鲜王朝与明朝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摩擦后,双方建立起稳固互信的宗藩关系。其后二百多年间,这种关系曾遭受过各种挑战。1592年4月,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则是对明、鲜间互信的宗藩关系最为严重的挑战。先是,战前明朝怀疑朝鲜诱引日本入犯;战争爆发后,进而怀疑朝鲜国王与日本勾结,假倭入侵。面对信任危机,双方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尽力消除隔阂,寻求关系正常化。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有所关注,但仍有很大拓展空间。1从中朝宗藩关系视角看,学术界一般强调中朝宗藩关系的“典型性”,2而对其“非典型性”一面讨论甚少。笔者探究此问题,试图揭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非典型性”的一面,以期丰富学术界对宗藩体制和明代中朝关系的认识。
一、日鲜通信与明鲜信任危机
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明、鲜信任危机,当从朝鲜庚寅通信日本说起。万历十八年(1590年),即朝鲜宣祖二十三年,岁在庚寅,朝鲜派遣黄允吉、金诚一为正、副使回聘日本。1看似寻常的这次通信使活动,实际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味。
首先,这是一次与当时东亚华夷秩序相违背的外交活动。15世纪,由于日本与东亚朝贡贸易圈的变化,朝鲜与日本之间的通使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明朝立国之后,朝鲜和日本分别于1392年和1402年加入明朝主导的宗藩体制,在这一制度圈内,双方通使本属藩国交邻之常规,故而本次通使前,朝鲜遣使日本多达59次,2明廷并无异言。3然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陷入内乱的日本中断了勘合贸易,事实上脱离出“册封—朝贡”体制,4在这种情况下,朝贡贸易圈内的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如再与“圈外”的日本通使,违背了“人臣无外交”的原则。
其次,朝鲜王廷刻意隐瞒通使日本之事,破坏了对明朝的“事大”准则。在1587至1591年间,朝鲜两次高规格接待日本使节,继而遣使回聘,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从头至尾竟不露声色,对明廷讳莫如深。按照东亚华夷秩序下宗藩关系的交往准则,宗主国要“字小以仁”,藩属国须“事大以诚”。所谓诚者,诚信也,亦即藩属国必须忠诚于宗主国,保持一种值得宗主国信任的状态。5朝鲜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这个基本准则。
再次,通使日本时,朝鲜所获得的倭情,对明“从轻奏闻”,继而留下了严重后患。16世纪80年代,日本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开始策划对外扩张,并把主要侵略矛头对准明朝,试图建立一个控制东亚地区的日本帝国。61587年和1589年两次遣使朝鲜,目的就在于探明朝鲜形势,谋划先侵略朝鲜,继而入犯中国大陆。这个侵略野心,在当时给明朝造成莫大威胁,问题可谓严重之至。7在1590年朝鲜回聘过程中,日本蔑视通信使,称朝鲜通信使之行为“入朝”,所带礼物为“方物”,接待礼仪上屡屡违礼慢待,同时在回复国书中明目张胆地要求朝鲜配合其侵略活动。8通过这次通使,朝鲜对日本侵略明朝之野心,已完全明瞭,然竟对明朝故意隐瞒真相,最终埋下明、鲜信任危机的祸根。
1591年5月初,通信使归国后将日本国书呈递国王,由于国书中日本宣称将“一超直入大明国”,9事关明朝上国,朝臣对于是否向明朝通报出现分歧。判书尹斗寿认为应该陈奏明朝,听明廷决断;兵曹判书黄廷彧表示赞同,曰:“我国家事天朝二百年,极其忠勤,今闻此不忍闻之语,安可恬然而不为之奏乎?”10认为应该防患于未然,否则万一日本入犯,明朝没有准备,朝鲜必定后悔莫及。副提学金睟则强烈反对,认为丰臣秀吉的话只是一派狂言,如果仓促陈奏,一来使明朝廷徒为担忧,二来日本必定知道,一定怨恨寻衅,“若既奏之后,果无犯顺声息,则非但天朝必以为不实而笑之,至于日本则亦必以此而致怨,他日之忧有不可言。”11左相柳成龙赞同暂缓陈奏,“闻诸使日本者之言,则必无发动之形,虽发亦不足畏。若以此无实之言,一则惊动天朝,一则致怨邻国,秀吉之怒,未有不由此而始萌也,至于通信一事,直为奏闻之后,万一自天朝盘问其曲折,则恐必有难处之患也。”12宣祖国王认为明朝可能通过福建等地商贸网络得知朝鲜通信日本之事,担心如果隐瞒不报,将来明朝追问,朝鲜则不好交待,因此主张以陈奏为佳,但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1
为此,朝鲜采取了两全的措施:一方面在回复日本国书中,以与明朝系君臣大义,明白拒绝日本的要求,道:“惟我东国,即殷太师箕子受封之旧也……故中朝之待我,亦视同内服,赴告必先,患难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亲者……人臣之有党者,天必殛之,况舍君父而党邻国乎!”2另一方面采纳左承旨柳根意见,对明“从轻奏闻”,即遣贺节使金应南五月份入京时“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至于隐瞒与日通使之事,则以朝鲜被掳人从日本所带回传闻予以搪塞,“若以闻于被虏逃还人金大机等三十余日本刷还者为辞,极为稳当。”3朝鲜王廷虽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最终对明廷采用了继续瞒报和尽量遮掩的处理办法。
与此同时,明朝陆续得到倭情报告。1591年7月,福建海商陈申携带琉球中山府长史郑迥倭情报告送达福建巡抚赵参鲁处。41592年2月,在日华人郭国安、许仪后的报告亦送达。陈申,福建人,遭遇海难漂至琉球,身患重病而滞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遣使要求琉球朝贡和提供壬辰战事所需钱粮。由是,陈申探知倭寇“(将)入北京者,令朝鲜为之向导”。郑迥,字利山,祖籍福建,为明初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5
中郑姓后人。他曾以琉球官派留学生身份来华学习,对明感情颇深。陈申获得倭情后,与时任琉球王廷事务长史的郑迥商议,并通过其帮助,搭乘琉球朝贡船归国报告:“朝鲜国已造船向导助战”。6在日华人郭国安、许仪后均为明朝人,二人因海难被倭寇掳到日本后,以医术见用、见信于萨摩藩主。在郭、许二人帮助下,同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福建海商朱均旺将倭情传回国内,“高丽国遣官入贡为质,催关白速行。”716世纪末的东亚海域,中国与朝鲜、琉球等国之间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还存在着民间贸易。借由这些商业网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情报传递等活动至为频繁,东亚各国彼此分享着同一个“世界”。8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朝鲜私自通使日本之行迹,经由各方情报虚虚实实地传入中国,并传闻成朝鲜勾结并引导日本入犯大明。朝鲜瞒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由此显现。
最后,战争初期,朝鲜在节节败退之际,并未积极向明朝请兵,更加重了明廷对其疑忌之心。1592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军队从朝鲜釜山浦登陆,分三路入侵朝鲜,壬辰战争爆发。由于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9日军很快攻克东莱、金海、密阳、尚州,过天险鸟岭后,直逼汉城。四月二十八日,朝君臣即有“去邠”之议;三十日,国王“西狩”;五月初三日,京城陷落;六月十五日,平壤亦陷,君臣奔义州。10仅两月时间,朝鲜“残我八路、夷我五庙、陷我三京、烧我二陵”,11情况极其惨烈,兵将溃败之巨,引起明朝的怀疑,“你国乃天下强兵处,何以旬日之内,王京遽陷乎!”12另一方面,在如此溃败的情况下,朝鲜并未立即向明请援。朝鲜对辽东兵将持有戒心,迟迟下不了请援决心,“大臣以为辽广之人,性甚顽暴,若天兵渡江,蹂躏我国,则浿江以西未陷诸郡,尽为赤地。两议相争,日久不决。”13更有甚者,朝鲜边将直接拒绝明朝援兵,“宽奠堡总兵召义州牧使黄琎谓曰:‘尔国受兵,自上国不可不救,俺当不日领兵过江,尔其以此意,急急启知。琎曰:‘我国虽猝被兵祸,举国奔播,然敝境兵足以当贼。岂劳大人之救乎?总兵笑而去。”1以此疑虑耽搁,朝鲜请援使节迟迟没有遣出。这一反常举措,使明廷更加怀疑朝鲜遭受日本侵略的真实程度。在彼此疑惧的氛围下,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朝鲜君臣纷纷北逃,国王为假王的传闻便开始播扬,“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2此后当国王真向明朝请求内附之时,明廷则更加顾虑朝鲜立场,怀疑朝鲜国王请求内附是假,所言被犯失国亦诈,实欲作为向导引诱倭寇入犯中国。
壬辰大战爆发之际,朝鲜王朝原本应该仰仗明朝,联合抗击日军,但由于朝鲜在一系列问题上处置不当,加剧了明朝对朝鲜的猜疑。烟火弥漫,疑云密布,两国宗藩间互信关系遭受到剧烈的冲击。如此下去将使战争情势,对朝鲜更加不利。如何重拾明朝的信任,并化解危机,使明朝迅速投入到对日作战中,成为朝鲜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明、鲜对“信任危机”的处置
日军侵略朝鲜,是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明朝也逐渐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3朝鲜无法承受各种传闻所引起的宗主国明朝之猜疑,随着局势紧张,取得明朝信任,得明军大举入援,是唯一应对危局的办法。故此,对于信任危机,明、鲜均高度重视,朝鲜只得接连遣使入明辩诬,明朝不断派人入朝勘疑,双方均积极应对,尽心化解。
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朝鲜贺节使金应南入辽,朝鲜王廷命他视情况而定,灵活奏报倭情,但他发现辽地“一路哗言朝鲜谋导倭人入犯”,态度上亦“待之顿异”,到山海关则被大骂,“汝国与倭同叛,何故来耶?”4意识到倭情已泄,便随机应变,“即答以为委奏倭情来”,遂使“华人喜闻,延款如旧”。5到达北京后,明廷恰刚接到赵参鲁奏报,当时已是“国言喧藉”,皆言朝鲜与日本勾结入犯,只有阁臣许国尚替朝鲜说话,“吾曾使朝鲜,知其至诚事大,必不与倭叛,姑待之”。6见此情形,金应男当即递交所备倭情咨文,辩明朝鲜拒倭立场,得此解释,明廷方“群疑稍释”。7
该咨文虽然传递了倭寇即将入犯的情报,但却以被掳漂流人传闻作为情报的来源,“圣节使金应南之去也,以倭贼欲犯上国之意移咨于礼部,据漂流人来传之言为证, 而通信使往来之言,初不及之也”,8在掩盖与日通使真相的同时,降低了情报的可信程度,影响了明廷对形势的判断,并未解决问题,遗患仍在。
次年二月,在日华人郭国安、许仪后的情报送达后,明廷再度掀起舆论风暴。由于许仪后在日生活多年,与萨摩岛主关系密切,情报非常可靠。此则情报披露了鲜、日交通和日本外犯的诸多细节,如“五月高丽国(朝鲜)贡驴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吾欲远征大唐,以汝琉球为引导)嘱之,赐金四百,高丽之贡倭,自去年五月始也”,“今秋七月一日,高丽国遣官入贡为质,催关白速行,九月初七日文书行到,萨摩整兵两万,大将六员到高丽会齐取唐,六十六国共五十余万,关白亲率五十万,共计百万,大将一百五十员,战马五万匹。”9这使得明廷刚刚消除的疑云,再度泛起。兵部随即“使辽东(都司)移咨于朝鲜,问其然否”。10明朝官方正式诘问,并直接追责朝鲜与日本交往之事。面对这一外交危局,朝鲜于同年十月派出陈奏使韩应寅一行,专门携带辩诬奏文,入京陈辩。
朝鲜首先解释倭情已汇报于明,“已将所闻未委虚的及伊贼哄胁难测事情,节次备咨礼部,顺付赴京陪臣去后,今该前因,已经略具词节回咨都司,计已转闻朝廷。”进而指出日本故意传言朝鲜诱其入犯,意在离间明、鲜关系,“及说入北京,令小邦向导,入福、广、浙,令唐人向导,小邦有无为伊向导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认,而一体准拟如此!虽蛮荒代有逆种,未有似伊狂妄者……乃敢张说虚喝,但得展转疑惑”;继而辩称朝鲜与日本原不往来,然偶为国防及刷还人口计会有羁縻之策,遣人前往实地打探倭情,“要以侦探彼中,以为伊国道里物力,只凭传闻,动静机诈,徒付遥度,委于应敌之道不便故也”;最后倾诉委屈,表白朝鲜事大忠心,“自臣祖先有国,世笃忠顺敬畏”,而现在舆论怀疑朝鲜为日向导,十分冤屈,“乃以向导之名归之,言亦丑辱,臣何不幸!”1奏文层次分明,虽然仍然没有透露通信日本之实,但提到刷还人口遣人使日之事为遮掩,并饱含冤屈之情,对明事大之诚溢于言表。
朝鲜自立国后,一直对明恭顺事大,明神宗宁信其真,接受了朝鲜的解释,“(朝鲜)侦报具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2接着“出御皇极殿,引使臣慰谕勤恳,赏赉有加,降勅奖论。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3礼部亦拟奖敕云:“朝鲜国王李昖,克修职贡,耻言向导,顾效防御,宜示旌嘉。”4受此褒奖,朝鲜再遣申点等入贡谢恩,国王“令奏倭情,比前加详”。5这样,战前猜疑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然而来年大战爆发,朝鲜节节溃败而不请援,再次引起明廷的猜疑。这次明朝率先采取行动。五月末,兵部尚书石星派遣崔世臣、林世禄一行到朝鲜调查实情。此时朝鲜仍没有决定向明朝请援,以为使臣是来商讨入援事宜,故打算将使臣挡在边城,且以朝鲜残破,明朝大兵无法久驻为由,委婉拒绝明朝入援的可能,“托以迎慰,实欲以我国(指朝鲜)残破之状,面陈天兵难久住之意,令差官不到平壤,自义州回去”,6然而随着国王向北一路败退,“时变起仓促,讹言传播”,7假王假倭谣传正盛,朝鲜王廷觉察崔、林入境“以探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而归”,8朝鲜无法承受明朝对其国王真假的质疑,于是改派礼曹判书尹根寿兼宣慰使将崔、林迎入平壤。六月初,朝鲜国王亲自接见,坦诚交代时情:“敝邦不幸,为贼侵突,边臣失御,且因升平日久……寡人失守宗祧,奔避至此,贻朝廷忧恤,重劳诸大人,惭惧益深。”9同时,派领相柳成龙带林世禄到前线探察倭兵。至此,明使查明真相,深觉形势危急,于是“世禄唯唯,亟求回咨而去”。10对此,明朝政府当即做出决定,六月二日即“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11十五日,辽东所派参将戴朝弁、先锋游击史儒带兵一千零二九名、马一千零九十三匹渡江入鲜。12虽然兵马不多,但可看出明廷对朝鲜已经释疑,并开始入援。
至六月中旬,朝鲜局势更加不堪,国王不断与大臣商讨内附明朝之议,并于六月十三日定议内附之策。内附的前提首先是得到明朝的信任,请明援助,关键是必须消除明朝的疑虑。在崔、林二人勘疑释嫌之后,朝鲜又接连派两拨使臣正式请援,一由李德馨到辽东都司,13一派郑昆寿入京面请。14《明史》记载这时期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道”。15此时,国王请求内附之举,恰与先前“假王诱引日本入犯”谣言相合,明廷又难辨其虚实,于是再派使臣入朝勘疑。朝鲜再次被动应对辩诬。
六月十四日,朝鲜国王命大臣“修内附咨文,送辽东都司”。1辽东都司收到咨文后,将其转送兵部,并提出疑虑:“朝鲜号称大国,世作东藩,一遇倭贼,至望风而逃……倭奴谲诈异常,华人多为向导,若携诈阑入,贻害非常,则作何处置?”2为此,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孽先自派遣曾经见过朝鲜国王的指挥宋国臣,以送咨文为名再入鲜境,刺探真伪,“巡按以我曾从黄天使出来,亲见国王面貌,故使之来见真伪”,在看到国王为真王后,国臣复命报称“的是真王,非假王也”,“辽镇信之”。3
内附咨文递入北京,正值明廷百官对是否大规模出兵援朝激烈争论之时。多人激烈反对出兵,如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认为四夷应该为中国守,而不是相反,“中国御倭当于门庭。夫边鄙中国门庭,四夷则篱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4直隶巡按御史刘士忠认为援助朝鲜会加剧国内局势严峻,会导致民心不稳、财政吃紧、兵力部署被扰乱,“天津兵士占民屋夺民食,民思逃窜,而盛暑大雨,军多暴露于烈日霖霪中,又沿海柴草不生,水苦咸,饮食不便,往往嬴瘠。南北兵争窝,互斗汹汹,恐有他虞,是军与民俱困也。天下事定于镇静,扰于张皇,今倭限天堑,飞渡为难,入秋海飓大作,且久战高丽,物力亦罢,岂遽航海与我争衡,未见倭形,先受其敝”。5朝鲜和辽东呈文上达后,进一步加重了明廷出兵的疑虑,为此,兵部尚书石星再派指挥黄应阳、夏时、徐一贯等人携带画师进入朝鲜境内,以侦报倭情为名,核查朝鲜国王真伪。
七月一日,黄应阳一行入境,经过宋国臣一事,朝鲜意识到“此人往还,机关慎重”,国王隆重接待,力图“不使之落寞,以失其心”。同时,大臣尹根寿出示两份日将行长、义智所写的“倭书”,剖白心迹:第一份是六月一日写给李恒福的。希望朝鲜质子于日本,与日本和亲,日本驻兵朝鲜八道,“幸甚以贤计虑,和亲如何?贵国若要和亲,王族及当权之辈,为质子,遣日本可也……若枉党日本,只遣质子而已。吾诸将分遣八道者,粗录其姓名,以备台览”。6第二份是六月十一日写给李德馨的。要求李德馨将日本愿与朝鲜结党、和亲,合力入犯大明之事上达国王,“庶几枉党于日本,相议犯大明乎?又运和亲之筹,然则回龙驾于城中耶?抑亦留龙驾于平安道耶?只在龙襟而已。”7两份“倭书”,反映了日本对朝鲜之威逼利诱,朝鲜由于坚守对明朝的君臣大义而遭日寇侵犯的原委。见到“倭书”,黄应阳等人焕然释疑,曰:“探哨人,不会见真倭,恐是假倭子,今见倭子书契的是真倭,尔国为天子失家失国,许多生灵尽被屠戮,窜一隅而犹不变,真可怜悯。”8
次日,朝鲜国王约见黄应阳三人,满怀委屈哭诉冤情:“上年倭奴欲犯上国,令小邦向导,而小邦斥绝假途之谋。故肆毒蹂躏,古今安有知此事!”黄等大为感动,以至愤呼:“(朝鲜)为贼所迫,不变臣节,而中国不知,反疑之。”当时,彼此“相向哭,良久而止”。9经此了解,黄应阳等人表示不再去平壤观察真倭,而直接回京复命,请朝廷尽快发兵,“尔国坚持臣节,严拒逆谋,搆怨速祸,破国亡家,尔既以尽忠而遭衅,我焉忍坐视而忘情?是以远勤圣虑,特遣侦询,务俾得其虚实,必欲救其生灵,矧流离播弃,仁君之所深悯,而毒痛暴戾,天讨之所必诛,亟遣陪臣,即时东向。”10回国之后,黄应阳立即报告兵部,“星大喜,东援之役乃决”,11“自此中朝知无其它,遂大发兵来救云矣”。12十月十六日,明廷命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兵援朝。1至于朝鲜国王内附之事,本身就面临国内群臣的激烈反对,此后更随战局逆转而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万历朝鲜之役战前东亚疑云密布,明朝对朝鲜的疑虑与日俱增,朝鲜为重拾宗主国信任,先以贺节使金应南兼奏,继以陈奏使韩应寅专门奏报倭犯情节,使宗藩间疑惧初步得以稍释。战争爆发后,局势日渐紧张,朝鲜迟迟未向明请援,加之国王一路北退,各种传闻再起,而此后国王内附请求,又与传闻相和。为慎重起见,明朝主动勘疑,兵部及辽东都司接连派出三批使臣,入朝探查国王、军情真伪。朝鲜亦积极应对,通过国王亲自接待使臣、将日本劝降信件交于使臣查看、带使臣于前线探见真倭等措施,辩诬释疑,最终消除双方信任危机,共同联合对日作战。
三、从明鲜宗藩信任危机看明代中朝宗藩关系
明、鲜信任危机问题的产生及双方的处置办法,反映了明代中朝宗藩关系中较少被关注的两个层面。
第一,信任危机的产生,表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虽号称“典型”,但其中存在“非典型”的一面,朝鲜王朝在事大主义的旗号之下,考量其国家利益,不惜违背宗藩关系准则。
纵观古代中朝宗藩关系史,文献史料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往往是双方“典型性”的一面,与其它藩国相比,中朝往来更加频繁,关系更为密切,交往制度最为完善,堪称中外宗藩体制中的典范。2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并非如此,在14世纪末,高丽王朝曾在北元和朱明之间几次反复,甚至杀掉过明使;315世纪前期,申叔舟等曾出使日本,并留下尊日正朔的案底;416世纪初,在得明“再造之恩”背景下继位的光海君,也对明多怀“两端”之心。5壬辰战争时期在位的宣祖国王,虽然朝鲜史料称其“事大之诚,无所不用其极”,6但朝鲜在战前及战初,却明显存在着对明违礼和瞒报等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朝鲜王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意为之。
本次明、鲜信任危机,始萌于朝鲜私自与宗藩体制圈外的日本通使,并对明朝刻意隐瞒,违背了宗藩间“人臣无外交”的原则;进而朝鲜瞒报倭情并且一味迁延,破坏了宗藩关系中“事大以诚”的准绳,进而在战前及战初引发种种猜疑传闻,几乎影响到了中朝邦交。基于整个中朝关系的视域,该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并不符合宗藩交往准则的行为及其性质?
考察这一决策形成过程,可见朝鲜君臣反复考量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事大“大义”,二是“国家利害”。朝鲜君臣之所以激烈争论,内心纠结,问题在于二者形成一对矛盾,即坦诚上报坚守了事大大义,有碍国家利益;瞒住不报则正好相反,如金睟、柳成龙所言如果明奏倭情,一是惧怕被日本获悉,遭受其疑忌和侵犯;二是也担心明廷发现朝鲜通使日本行迹,以致受到责备。柳成龙还料想,即使丰臣秀吉张狂出兵,也必然无法打到中国大陆,而朝鲜近在咫尺,必然横受其祸,因而日本不能得罪,奏报万万不可。可见在其权衡中,朝鲜国家利益成为最重砝码。商讨最终折衷而行的“从轻奏闻”,看似顾全了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其隐瞒与日通使之事,影响了情报的可靠性,结果干扰了明朝对形势严重程度的判断。
第二,考察两国对信任危机的处置,可见在宗藩体制下,除了进贡、册封等常规仪式外,还存在着处理特殊事件的如辩诬、勘疑等惯常做法,它们都在维护宗藩关系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因受宗藩制度的规范约束,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次宗藩信任危机中,辩诬无疑是朝鲜王朝主要的应对手段。本来朝鲜对倭情特别是擅自交倭之事,极力遮掩,但当其发现瞒报,恶果已现,关于朝鲜引诱日本入犯中国的谣言大起,明朝上下在震动之余,对朝鲜已起疑心的时候,朝鲜迅即采取辩诬的办法。承担朝贡任务的贺节使金应南,率先主动兼起辩诬的任务。而当日本和琉球传来的情报再度引起明廷震动,并诘问朝鲜之时,朝鲜迅即任命韩应寅为陈奏使,专门携带奏文到北京辩诬。大战爆发,朝鲜迅速溃败和假王假倭传闻又使明廷生疑之际,朝鲜重臣乃至国王也加入了辩诬的队伍。由于其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加上两国关系一贯良好,明廷对朝鲜一直信任宽容,百官乃至皇帝都轻易接受了他们的各种解释,一度消除了对其的疑虑和误会,褒奖有加。尽管朝鲜在汇报倭情问题上一味遮掩,不但其辩诬奏文“甚(陈)委曲,而不能悉陈通使答问之事”,1而且国王、大臣几次面临明使勘疑仍对通倭讳莫如深,因而并未尽到“事大之诚”,但双方信任危机很快得以消释,迅速投入到对日联合作战中去,因此,辩诬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明朝作为宗主国则常用勘查实情的手段,消除疑虑。在壬辰战初处置信任危机过程中,明朝勘疑的积极作用尤其明显。当各种谣传泛滥之时,明政府主动遣使,从朝廷到地方连续派使臣入朝鲜,从辨别国王真伪,到眼见真倭来犯,勘疑使节迅速查明朝鲜实情,消除各种不实的传闻,打消了明朝上下对朝鲜的猜疑和减小了大规模出兵支援的阻力,进而为双方信任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利于更好把握中朝宗藩关系的复杂面相,从而更全面看待传统中国与朝鲜的交往。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对壬辰战争时期明朝与朝鲜之间信任危机的产生和处置之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信任危机背景下,明鲜处理双边关系的某些心理态度和所作所为,这是明代中朝关系中为人较少关注的层面,但并不意味着特殊例外和无代表性。任何事物包括明、鲜信任关系,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事大字小”问题上,朝鲜对中国的忠诚和欺瞒、中国对朝鲜的信任和怀疑,皆作为一对矛盾,在中朝关系的动态延续中,此消彼长或相互交替。尽管朝鲜对明朝的恭顺忠诚和明朝对朝鲜的仁义宽容,都非常突出,称颂于史,但不可否认这并非绝对无二与一成不变,因为大义背后还存在着决定双方态度和政策变化的国家利益因素的影响。2另一方面,对于中朝宗藩体制,学者大多关注进贡、册封等重要形式,而对于辩诬、勘疑等却容易忽视。虽然它们不属成文规定,但已广泛且有效运用,甚或约定俗成,无疑同样属于宗藩体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明代中朝关系遇到问题、互信体制受到损害之时,辩诬和勘疑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弥补,从而在维护宗藩体制上起到独特作用,因而应当重视此类交往方式之意义。认识到这些,将有资于更全面地关照整个对明代宗藩关系体系复杂性的认识。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