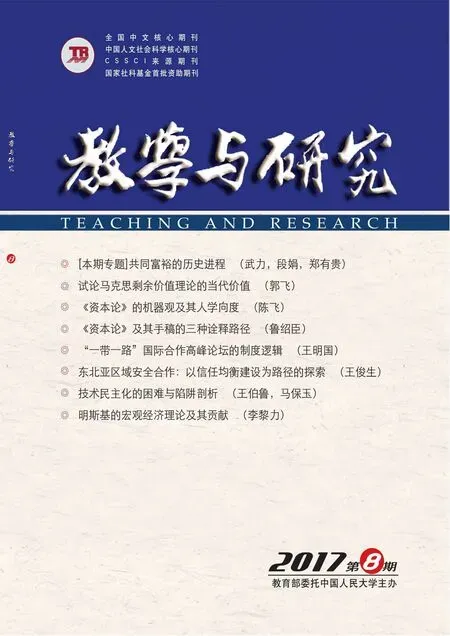《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三种诠释路径*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三种诠释路径*
鲁绍臣
人本主义;权力逻辑;辩证法;《资本论》
当代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主要有以下三种诠释路径:一是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总体、历史和人本主义的诠释路径,他们强调青年和晚年马克思的“一致性”,以及现象与本体、形式与内容、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历史性与认识论张力;二是阿尔都塞和奈格里为代表的政治、对抗、起源的诠释路径,他们强调“断裂”,以及支配与从属、压迫与反抗、起源与结构之间的权力与政治逻辑;三是以新辩证法和价值形式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阅读路径,他们依托文本,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普遍与特殊、质与量、形式性与实体性之间的矛盾与辩证运动逻辑。各自从不同的侧面突显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
虽然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传播史就是一部误读史,但我们不能否认,正是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再编辑、再整理和再出版,以及众多学者持续不断地对相关文本和理论非教条式的艰苦“阅读”与诠释,一个丰富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思想才充满活力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也因此才不可能。而当代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相关基础理论的“阅读”与诠释工作亦从未中断,本文将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阿尔都塞和奈格里“断裂论”的权力政治逻辑,新辩证法学派非人本、非政治的矛盾与辩证运动的客观主义逻辑进行分析、介绍与反思。
一、“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实体主义的修正与继承,由此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和经验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实质上就是教化“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规律’,或者抱一种苟安的宿命论的态度”,[1](P223)从而完全丢掉和抹杀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和社会批判思想。而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人道主义批判,以及马克思早期哲学人类学思想,则随着《巴黎手稿》的出版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违背了人性的本质的理论支点:货币作为私人财产的异化本质,变成了外在于人并调节人类活动的自主性力量,从而压制了人类潜能的实现;非异化的劳动被马克思视为本体论的本质,批判的目的仅在于回归非异化的人性本质,并赞扬了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主张。在此基础上开启了《资本论》及其哲学再诠释的第一个路向,并形成了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路径,以及弗洛姆等人的追随性诠释。
卢卡奇首先从“总体”的视角,对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现代装束的伯恩斯坦等人,都是局限于直接地、简单地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再现之中。当他们简单地吸收了这些决定因素时,既没有对它们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把它们结合到具体的总体性中,就想象他们已是格外‘精确了’。他们对待与具体的总体性无关的抽象规律的这些事实采取了一种抽象、孤立的解释。”[1](P11)这种精确和量化思维的最大缺陷是将历史的东西自然化。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明显,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紧步后尘。辩证法连同总体性超越个别方法论的优越都被他们废除了;部分不能从整体中发现它的规定,反之,集体作为‘非科学的’而被取消”。[1](P11)
卢卡奇非常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P30)回过头来看,当马克思指出他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P47)的时候,已然表明了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当代的社会历史性质,而不是经济学,这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全新的研究思路。卢卡奇就认为自己研究无产阶级的意识状态就是从“商品结构之谜”[1](P92)入手的,即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体不再同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统一体相一致。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解放,而是一种新的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形式,即尽管“新的物性”“最后只能从属于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但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1](P104)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性质进行了强调,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贡献之一。对于卢卡奇等人来说,历史性是总体性的根本特征,缺乏总体性视域的实证主义也必然缺乏历史性的洞见,一旦没有了具体的总体的洞察力,各个孤立的部分的相互关系模式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具体的总体的历史和暂时的性质,将其各种规定性拜物教地视为具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性,最终转化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洗礼的无产阶级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克服的力量。卢卡奇批判这种物化的意识将毫无希望地堕入粗俗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两个极端之中。当然,这一贡献亦有卢森堡的功劳,比如卢森堡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时,同样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3](P117)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洞见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不仅仅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更在于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与立场。
最后,是他们对人本主义和劳动本体论的强调。在卢卡奇看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4](P642)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商品形式导致原本作为人之本质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从而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1](P99)商品形式不仅带来劳动过程的异化,同时也带来了人的意识的“合理化”和一切皆可计划的工具理性态度:“商品的特征,也就是可计算的、抽象的数量的方式在这里以最完整的形式显示了它自己:物化的思想必然把它看作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自己的真正的直接性变得十分明显——作为物化意识——不想超越这种直接性。相反,物化的思想所关切的是,通过‘科学地完善化’使这些有效的规律永久化。”[1](P104)从而原本是反抗迷信和权威的科技理性精神变成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同谋和助手,最终,从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近代哲学理所当然地将近代数学当成了方法论的样板思维模式。对于物化意识的克服问题,卢卡奇认为只能求助于具有自我认知能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的认识产生于对现存的认识,产生于在其特有的社会地位上形成的自我认识和对其必然性的解释。”[1](P18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5](P72)文化意识形态认识论研究因此成为其批判思想的主要线索。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认为青年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异,主张《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仍然保留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论的诠释和理解路径。不是遗弃与“断裂”,而是进一步的展开和延伸。[6](P78)弗洛姆认为,“尽管在概念、心境和语言上的某些变化,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6](P86)同样,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之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7](P85-86)
在柯尔施看来,如果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存在什么差异的话,只在于成熟时期明确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7](P87)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整个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它的最初的面貌自然在实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它没有全然保持不变。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8](P22-23)
但这种一致论的视角并非是不受质疑的。国内有学者指出,“这种建构虽然强调了马克思前后期著作之间的学术联系,但却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淹没了《资本论》特有的科学价值。……削弱了对《资本论》精髓的科学把握。”[9]根据美国学者普殊同的理解,这是一种试图用外在于资本的劳动与人本状态来批判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理论尝试,丝毫不亚于被他们所批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差异不过是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转变为主体的沉思行为,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克服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主客体统一并强调“物化”(Verdinglichung) 原理,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总体”仅仅把握为意识形态的误认,其批判是“异化逻辑”而不是“资本逻辑”的批判。他们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从劳动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从而将劳动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中介着人与自然,创造特定的产品和财富以满足特定的人类需求的存在,对资本论异化的批判与超越,就是要回到这种直接性的世界之中。其薄弱环节和理论缺陷在于,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研究逐渐消失了,其理论旨趣也逐渐转向了艺术和美学。佩里·安德森曾经非常深刻地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转向,并且指出:“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注的问题”。[5](P68)
二、“断裂论”的政治和权力批判路径
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者更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从青年马克思来推论晚年马克思的一致性不同,阿尔都塞更强调晚年马克思对青年时期的断裂与超越。针对以卢卡奇为首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后一致观,阿尔都塞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理论,认为在青年时期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科学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阿尔都塞看来,“如果认为整个马克思的哲学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个短短的命题中,或者包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的论述中,也就是包含在断裂的著作中,那么就严重误解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思想生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种思想的成熟、界定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因此,“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0](P24)
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主要是从权力与支配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前提与起源的视角进行阐发的,主要的特点是反对用黑格尔的哲学来“阅读”和诠释《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一路径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五月风暴”、欧美学生及其后来的后福特制生产成为主导之后,又变成了以奈格里和哈特为代表的自主主义学派,以及哈利·克里夫等人的“政治阅读学派”,明确提出要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政治性”的重新阅读。克里夫就批评人本主义和将资本主义更多地理解为一种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避开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对意识革命的推崇恰恰遮蔽了现实政治运动的根本性地位。最终“革命的策略不可能由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而被创造出来,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1](P57)
当然,他们同样也批评第二国际经济主义的阅读路径:“这样一种《资本论》阅读,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被限制为一种消极化的解释,而且这种阅读将自身限制在‘经济’范围或有效‘基础’上,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工厂理论与它的雇佣工人相互独立。”[11](P43)克里夫同时也直接批判了传统的生产力或者技术解放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使工人阶级免于工作,而是将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和积累。”[11](P138)
与克里夫不同,奈格里等人是从文本学的视角充分利用了《资本论》的第一部正式手稿,也就《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的再阅读和诠释来完成理论建构的,并将其与《资本论》对立起来。他们也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充分借用西方哲学史的其他思想家的传统一样,大量借助斯宾诺莎的内在论思想来再诠释《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以及所谓“消失的第六章”的文本及其思想的,并为分析当代的非物质劳动、知识资本主义等在理论上铺平道路。他们主张“《大纲》对阶级对立中主体性问题的理论分析本身构成革命实践”。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论》非但没有政治,而且“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发展规律客体性中主体性的毁灭”。[12](P283)
如果说阿尔都塞是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话,那么奈里格等人则主要是反黑格尔式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二重性”思想。他们并不认为货币既是交换价值又是使用价值的承载物,而仅仅是权力关系和社会对立的媒介,隐藏或表现对立的社会关系。用奈格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13](P46)从而把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的判断充分彰显出来,将复杂的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完全等同于权力关系,即所谓“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就是权力关系”。[13](P177)在这样的政治性话语中,商品形式和拜物教就不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种强制体系。“阶级斗争就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理解:资产阶级通过强制大多数人出卖他们作为劳动力商品的部分生命——这是为了生存和获得社会财富——而将商品形式强加于他们。”[11](P82)
他们在马克思的如下话语中找到了政治性和主体性阅读的依据:“自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资本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14](P471)从而非常强调工人力量的增长对迫使资本进行战略计划转移的重要作用,进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理解为“生产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历史运动”中主体努力和主体性批判的结果。[13](P82)其不仅仅改变和创构了历史过程,或者使之发生了质变,“同时也带来了作为过程和生产主体的那种发展的主体的参与”。[15](P56)
奈格里批评“科学”地研究《资本论》的学者“沉湎于客观范畴,实际上变成了现实主义的拜物教”。因此,即使事关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必要劳动,最后都应该将自身“定义为阶级斗争的潜能”。[15](P57、136)传统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认清主体性问题,并且认为“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体的对抗性。……唯物主义的道路精确地通向了主体性。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生产力发展无关,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自由的主体反对并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结果。[13](P195-196、198)
亚历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认为,很难说阿尔都塞的“阅读”方法是错的,但却将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尤其是其与黑格尔之间复杂的师承关系上。[16](P44)对于奈格里,柯林尼可斯同样明确指出,奈格里对《大纲》解读的内在逻辑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简化为福柯的权力理论,即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彻底转换成权力和主体理论。不过并非柯林尼可斯本人不重视资本的权力逻辑之维,而在于他将其视为其中之一维,而不是全部。他在2014年出版的《解码〈资本论〉》中,一方面强调通过阅读和诠释,与马克思的文本再对话、再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则认为如果尊重马克思的文本,会发现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三个面向:一是虽然是表面却又十分重要的层面,即自由、平等的交换与贸易,以及由之产生的价值形式与拜物教;二是由这个面向所遮蔽起来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权力与统治逻辑,这主要涉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或者说工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对抗与统治的关系;三是同样被第一个面向所遮蔽,但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得以真正展开的“绝对命令”和前提,即资本间动态的自由竞争关系。第一个面向是外部,或者说表层的关系,后两个是内部,或者说内在的关系。[16](P18)
奈格里等人的激进哲学的困境就在于将主体视为高于关系的存在,或者如果说其也重视对抗性关系的话,却将三重性的关系还原和划一为单一的阶级主体关系,或者说通过一种特别的阅读法,将《大纲》中的资本关系还原为了两个主体——社会资本与社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16](P18)而到了后来的帝国三部曲时期,社会资本网络化为了帝国,而社会主体就更进一步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程活动的社会主体,诸众滋养着帝国的机器并享受一种“共产主义的愉悦”。[17](P413)劳动者和资本的关系也就日渐隐退了,劳动者似乎有足够的权力可以“逃离”、“遗弃”、或者“激发”起对资本关系的颠覆,似乎空间的位移就可以取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真实转型。在这一点上,柯林尼可斯批评奈格里等人犯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犯过的同样错误,除了物和观念外,对他们来说,关系是不存在的,特别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独特的三重关系:剥削、竞争和交换关系。
三、“客观主义”的矛盾与辩证法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MEGA2的出齐,国外再次形成重新阅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热”,也为从“客观主义”和黑格尔逻辑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内部的“普遍与特殊”、“质与量”、“形式性和实体性”的矛盾与辩证关系的诠释提供了可能。用诺曼·莱文的话来说,MEGA2已经引起了重新阅读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一场革命。在思想的传承上,它不但确认了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洞见,证明了青年马克思确实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第二次影响也得到了确认和肯定。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现实总体的逻辑结构的描述,主要是受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辩证法的影响,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非历史的经验主义和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按照齐泽克的说法,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的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克服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人本主义之后,在《资本论》中发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现实运用,才真正“成为马克思”,并真正成为黑格尔的学生。
他们强调马克思对资本自身所遭遇的界限、矛盾与困境的“客观研究”,并且确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描述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运作的方法或手段。因此他们更为关注黑格尔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学理关系,而对传统宏观的社会历史政治变迁不感兴趣。其并不是在预言,而是在分析,这正是差别所在。换言之,这个学派重点聚焦于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商品和交换关系,而不是传统的人本主义或者是劳动价值理论。他们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证的运行模式,而不是剥削、贫富分化(他们注意到了国家干预这一新形式的到来)和阶级斗争,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和阐释路径。关于剥削,普殊同认为,传统的革命主义诠释路径是劳动者的财富不断被榨取和剥夺,无产阶级的极度贫困化使得废除剥削与阶级统治,创造一个新的、公正、合理的分配方式的历史成为可能。但普殊同认为,当代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兴起对这一理论路径提出了严峻挑战,极度贫困化的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到来。
虽然强调《资本论》及其手稿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渊源关系这件事并不新鲜,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很早就毫不犹豫地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8](P191)同样,洛维特更为精辟地指出,至于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从黑格尔那里得到传授,他那些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直接与黑格尔相关的早期著作所表现出来的还不及《资本论》,后者虽然在内容上与黑格尔相去甚远,但若不是吸取了黑格尔使现象成为概念的方式,其分析简直就是不可思议。”[19](P120-121)但在具体而深入的解剖上,即对资本的商品生产过程必然在自身内部包含着矛盾,从而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包含着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充分呈现了资本逻辑内含“无限性”(增殖)与“有限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大社会财富)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本身就是矛盾”,总之,手段——社会生产力不可能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无限的目的发生冲突。
对这些矛盾和辩证法的深入解读,倒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换言之,重新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再发现黑格尔的阅读路径引起了欧美的一个新阐释学派的诞生——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并且与之相关联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价值批判和价值形式学派,他们都共同试图通过重新阅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恢复其与黑格尔逻辑学的丰富渊源关系。代表性的学者有英国的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美国的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英国的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美国的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以及诺曼·莱文和普殊同(Postone)等人。在这些学者看来,只有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特别是“二重性”思想,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发现了商品、劳动、资本等范畴的“二重性”,批判性地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代表的价值不能直接相等。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难以理解“二重性”思想的重要内涵,梅林就指出,“但这批判性的研究所发射出来的灿烂的光辉在开头时与其说使所有的人,甚至是作者的朋友茅塞顿开,无宁说使他们感觉到迷惘了。”[20](P33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重性关系中的矛盾与对抗被遮蔽忽视了。
罗伯特·菲内利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商品概念既不能被理解为单一的价值实体,也不能仅被理解为单一的价值形式,而毋宁说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的两极对立和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主词和谓词的倒置和交换价值的实体化过程,对于劳动力商品同样如此。因此,不管是劳动力,还是商品,其内容与形式之间,都存在异质性的矛盾。一方面,商品作为抽象劳动的结晶而具有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交换而产生的抽象劳动,或者价值,又必须占有一个身体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从而由普遍性真正实现为具体化。通过他们仔细的文本考证,我们总算可以一窥马克思对“价值”问题展开研究的复杂学术历程,同样,马克思有关“价值形式”的思考,同样经历了复杂的思考、修改和调整的过程。
在文本和学理的解读中,他们非常关注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抽象劳动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重要概念的再阅读和再诠释,主张这些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主要不是与技术范式相关的范畴,而是社会形式观念的范畴。只有时时牢记,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形式,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概念。他们进一步主张劳动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实在同一性的关系,而是辩证地相互渗透的对立关系(dialectically interpenetrating opposites)。在亚瑟看来,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也不存在等同关系,因为前者指涉的是一种质的社会关系,后者则主要是一种量的社会关系。罗伯特·菲内利指出,就“价值形式”这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来说,其就具有多重性的发展的纬度:第一层是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价值形式,第二层是一般等价形式,第三层是资本形式,第四层是生产方式等。
当然,这样一种有意无意地忽略剥削和阶级斗争的阅读方案,可以做到“中立”地研究资本主义,但却面临一个齐泽克所描述的尴尬现实:“马克思——今天即便是在华尔街他也很受欢迎——作为描写商品(形式)的诗人,它提供了对于资本主义内在动力(对抗)的完美描述,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中,他刻画了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物化现象(拜物教)”。[21]这就难免被其他左翼学者批评为比资产阶级还更好地为资本作了辩护和研究,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隐性同谋”。在诸多的学者看来,这主要是过于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一致所造成的,对于门多萨等人来说,黑格尔的问题在于用逻辑的辩证法遮蔽了政治运作的辩证法。[22](P5)柯林尼可斯同样认为简单地将《资本论》的概念结构视为黑格尔《逻辑学》的镜像是成问题的。[16](P20)
不过,除了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视角来阅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外,这一学派的贡献还在于仔细研究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与改动。举例来说,泰勒和贝洛菲尔在《资本论的构成》[23](P5)中就指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中,将《资本论》的副标题从原来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改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这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抽象劳动”和“价值增殖”变成了与交换无关的纯劳动过程。这进一步导致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题误读为界限分明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两个部分。在作者看来,并非是只有三卷《资本论》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体,每一本实际上都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Nicola Taylor and Riccardo Bellofiore, Marx’s Capital I, the Constitution of Capital: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iccardo Bellofiore, Nicola Taylor(eds.), The Constitu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I of Marx’s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7.。而MEGA2对《资本论》各个版本的再整理出版,使得人们发现德文第一版关于“价值形式”的描述与其他版本存在重大的差异。
当然,随着MEGA2的出版,对恩格斯的批评还有很多,比如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生产性资本”改成了“工业资本”,从而把同时包括服务业和非物质生产、具有更强社会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狭义的偏向生产劳动过程的范畴。更为严重的是,关于生产力与利润率的矛盾关系,对于马克思的“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长期来看,利润率将下降”的矛盾理论,因为自身的政治立场的原因,恩格斯就将其改为了“高劳动生产率将带来利润率的增加,因为其将降低固定资本的成本”。恩格斯用自己的经验主义的经济理论来代替了马克思自己深刻的哲学思考*Alex Callinicos, Deciphering Capital,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14,pp.41-42;see Geert Reuten, “Zirkel vicieux” or Trend Fall? The Course of the Profit Rate in Marx’s Capital III,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36.1 (2004), pp171-172.。此外还有广被诟病的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所谓历史诠释,将《资本论》第一章的商品生产理解为“简单商品生产”,从而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恩格斯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主义诠释,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节,就将“暴力”视为伴随资本主义诞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等等*John Weeks,Capital,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30.。
四、文本的深度爬梳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再阅读
总之, MEGA2的出版,为人们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学的基础上去重新阅读和诠释《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可能。诸多的学者认为这为我们从受恩格斯所影响的传统中走出来提供了可能,并且也为研究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具体编辑和改动效果提供了可能。自1991年起,专注于研究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内在逻辑及黑格尔遗产的继承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ISMT)”*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xian Theory为推动MEGA2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MEGA2中《资本论》的部分新资料亦逐渐成为了这一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并且已经由Palgrve出版社出版了多本英文论著,其中《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一书,作为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是广博的,思想是复杂的,其必然伴随着新的时代境遇和社会发展,而显得更为“开放”并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和有生命力。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再阅读和再诠释更为相关的,其实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现状,这才是持续地为我们提供再阅读和再诠释的真正动力之源。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卢森堡文选[M].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 上卷.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 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A].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7] 柯尔施. 卡尔·马克思[M].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 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 孙乐强.《资本论》形象的百年变迁及其当代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2).
[10] 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M]. London:AK Press,2000.
[12] 马里奥·特龙蒂. 意大利[A].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C].闫月梅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3]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 张悟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5]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M]. Massachusetts: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1984.
[16] Alex Callinicos. Deciphering Capital [M]. Bookmarks Publications. London: Bergin and Garvey, 2014.
[17] Michael Hardt and Toni Negri. Multitude[M].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4.
[18]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9] 卡尔·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M]. 北京:三联书店,2006.
[20] 弗·梅林. 马克思传[M]. 樊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1] 斯拉沃热·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J].周嘉昕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22] Carlos Alberto Castillo Mendoza. Notasin-troductoriassobresubsunción del trabajo en el capital[J]. Iralka, 17, 2002.
[23] Nicola Taylor and Riccardo Bellofiore. Marx’s Capital I, the Constitution of Capital: General Introduction[A]. in Riccardo Bellofiore, Nicola Taylor(eds.). The Constitu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I of Marx’s Capital[C]. Long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责任编辑孔伟]
ThreeInterpretationsofDasKapitalandItsManuscripts
Lu Shao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Humanism; power logic; dialectics;DasKapital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of interpretation ofDasKapitaland its manuscrip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first,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totality, historical and humanistic approaches represented by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m. Second,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politics, confrontation, origin represented by Althusser and Negri. They emphasize that “breaking” as well as the power and political logic between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origin and structure. Third,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objectivism,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new dialectics and school of value-form. They rely on the text and focus o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apitalism, and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movement. These three inerpret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highlighting the rich philosophical ideas inDasKapitaland its manuscripts.
鲁绍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