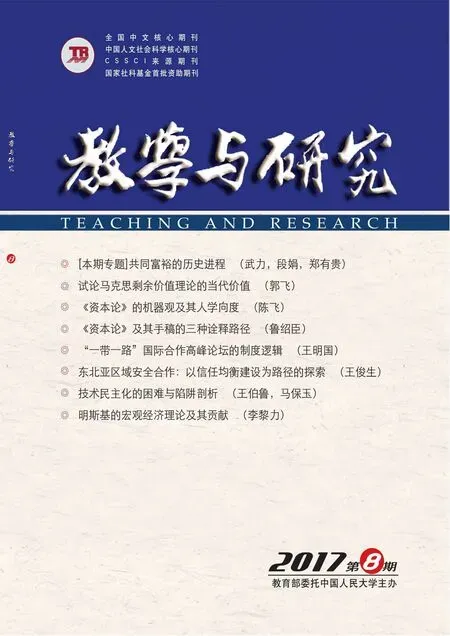《资本论》的机器观及其人学向度*
《资本论》的机器观及其人学向度*
陈飞
机器;资本;异化;自由个性
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马克思对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进行了系统解读。马克思把机器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内在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艺和力量占据主体地位,工人的活劳动仅仅作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附件,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相比工场手工业时期,人的存在方式进一步异化;另一方面,机器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又具有重要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加了社会的自由时间,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由于资本的本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问题,只有在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中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器对人的奴役和支配。
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马克思阅读和摘录了许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艺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方面的著作。例如,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尤尔的《工厂哲学》、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波佩的《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和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等。为了解当时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工艺的现状,他还参观了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对这类著作进行大量的摘录和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甚至对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观念等都产生了不同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重大影响。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思考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同步进行的,他对科学技术的思考隶属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国内关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很少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把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抽离出来,往往从现象层面得出一些具体的实证结论和零星的思想片段,缺少对现代技术与人的进一步异化的关联的思考,更缺少对现代技术与人的自由个性实现这一共产主义事业关系的深层研究。限于篇幅和聚焦主旨等原因,本文以马克思时代的先进技术即机器和机器体系为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宏观语境下,从人学这一特定向度对马克思的机器观进行整合。
一、作为资本的机器与资本的高级形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看,劳动资料发展为近代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为了适应资本要求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划分为两大基本阶段: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在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占支配地位,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法国提供了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真正典型,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分工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行会手工业时期由一个工人所操作的整个手工技术被分解为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由不同工人承担的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相对于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是由于分工。分工产生去技能化的作用,使每个工人不必拥有全面地掌握从事原有整个操作的能力,只是掌握生产过程某个环节的技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更多。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家并没有真正把精力集中在通过机器的创造提高生产率,而是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对劳动环节进行重新整合和组织。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把技术创新作为动力,现代技术也没有内化到生产过程的核心地位。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技术创新,如自鸣钟和印刷术这些伟大的技术发明,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机器仅仅在分工之旁起次要作用。18世纪末,由于市场的极大开拓,工场手工业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这就有了创造更具效率的生产工具的强大动力,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正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机器使手工业生产不再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现代工厂组织形式和机器走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舞台的中心。机器大工业是第二种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何谓机器呢?在与工具的对比中马克思界定了机器的科学内涵。对于工具与机器的区别,马克思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错误观点: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这种观点并未看到二者的本质区别,只是从表象上把二者的区别归结为简单机器和复杂机器,在工具和机器之间没有历史的因素。马克思认为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机器是生产过程中各种工具的组合,一台自动机器同时推动相互协作的各种工具。机器使各种工具形成一个在空间上相互协作的工具链,所有工具都同时运作,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从而保证不同生产阶段的连续性。“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1](P437)不是工具以原子式的方式集合在一起,而是许多相关工具在规模、动力等方面都统一在机器体系之中。技术哲学家西蒙栋对工具和机器的区分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有重要启示,他指出,工具是个体化的,是抽象的技术物体,技术结构的诸要素还处在未解蔽的状态,没有得到展开;而机器是整体化的,作为一个发达的技术物体,各要素已经从抽象走向具体,彼此相互融通,汇聚在一起,并获得充分展开。近代机器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个体工具逐渐向整体机器汇聚的历史。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马克思批判的错误观点:根据动力区分工具和机器,把人力看作工具的动力,把不同于人力的动力,如风力、水力、牲畜力等自然力看作机器的动力。这是根据所依赖的动力类型来界分工具和机器,凡是用人力推动的技术物都是工具,凡是用异质于人力的自然力推动的技术物都是机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拜比吉就持这种观点。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举例,珍妮纺纱机仅仅是工具,而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的畜力拉的犁、风力或水力推动的磨却是机器。倘若如此,机器生产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因为牲畜力这一自然力的开发和利用是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者说,同一个技术物用自然力推动是机器,用人力推动却成为工具,这显然没有抓住工具和机器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认为机器由三个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机器的前两个部分并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而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工具机根据一定的目的作用于劳动对象,工具机直接和劳动对象接触。所以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工具机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本身又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1](P430)即使人本身作为动力,机器与工具的界分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工具机是机器和工具区分的根本标志。工具和机器的区分呈现一种去身体化的趋势:对于工具来说,它是个性化身体技能的一种展示,整个身体都参与了工具的具体劳动;对于机器来说,它强调的是生产的连续性和过程化,工人作为机器的看管者存在,只是身体的某一方面参与了劳动,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虽然马克思反对把动力类型作为区分工具和机器的标志,但是却并不反对把动力类型作为工具和机器的一个重要界分。马克思认为,工具机的创造使蒸汽动力成为必要,但蒸汽机作为一种原动机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它取得了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独立形式,它以煤作为动力,可以由人操控,可以移动,不像牲畜力、水力和风力那样不稳定和受地点限制。
在机器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已不再是分工,财富生产取决于机器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机器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2](P588)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是较多地取决于科学和技术,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作用物的力量。劳动已经不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真正标志,取而代之的是吸纳社会智力、知识体系和自然科学的以机器为代表的固定资本。直接劳动被机器体系强制裹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劳动以机器体系为中介,机器体系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科学和智力成为固定资本的固有属性,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塑造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资本才获得了符合自己本性的充分发展,而具体劳动则被异化为整个机器体系的一个从属的要素。马克思认识到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显然受到了尤尔《工厂哲学》的影响。尤尔指出,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分工居于支配地位,生产要适应工人的技能,人并未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是机器和机器体系的运作,人的技能成为次要的,完全屈从于机器运行的逻辑,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但是,尤尔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他缺乏批判的立场,他的机器观是为资产阶级工厂制度服务的,没有区分开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另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德戴尔同样认识到了机器体系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但是却由此走向了背离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目的,罗德戴尔认为,机器体系可以脱离劳动直接创造价值,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机器体系创造价值,那只是由于机器体系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使劳动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维持劳动能力存续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机器只是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它根本无法代替活劳动,马克思坚持了彻底的劳动价值论立场。
现代机器体系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成为剥削工人的有力武器,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机器体系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是为了对单个工人有帮助,作为资本的一种高级样态,它仍然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机器,是因为它们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对资本家来说是最强劲有力的。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是:“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3](P368)机器的使用,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了,惟其如此,才可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为资本剥削和驾驭劳动的手段,成为与具体劳动敌对的资本的形态,这即是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在马克思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推动力的赞美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是并存的。”[4](P149)问题不是出在机器本身,而是机器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资本的内在能力和本质在机器上得到充分展示,增加了剥削工人的权力。
矛盾和对抗并不是机器产生的,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产生的,所以正如哈维所说的那样,有问题的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机器就自身性质而言缩短了劳动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延长了劳动时间;因为机器就自身性质而言降低了劳动强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提高了劳动强度;因为机器就自身性质而言增加了社会整体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产生了大量的贫民。所以,马克思总结道:“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5](P94)这暗含着,机器的资本形式不是永恒的自然存在,它同样可以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使用,比如机器完全可以在共产主义使用,机器自身的本性在这一社会形态得以恢复。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卢德主义者,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拜比吉、尤尔、贝克曼等人也都发现了机器与工人的对抗关系,马克思的超越之处在于,指出了机器与工人的对抗关系不是根源于机器本身,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隶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宏伟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大量篇幅都是在资本的层面上对机器进行分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提供一个有效路径。随着作为资本的机器体系的逐渐推广,人们改变了已有的生产组织形式,与之相伴的是,人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所以,机器不应该仅仅作为改造劳动对象的一个工具,而应该与人的本质、与人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机器体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完全展现为人的生存境遇,尽管人是机器体系的推动者,但人自身已完全卷入机器体系的“座架”之中,人的自我异化与扬弃都在这一历史性的生存境遇中开辟出可能的道路。人的生存方式在机器体系这一历史性的境遇中完全展现:一方面,现代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使人的异化越发凸显,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另一方面,机器体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自有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文明面,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了必要准备。马克思对作为资本的机器的态度与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态度是一致的,既看到了历史限度,又看到了历史必然性,它是通往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必经阶段。
二、作为资本的机器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层异化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思辨哲学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创立了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这种历史原则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方法格格不入。马克思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在普遍的、不变的人性基础上为社会理论和道德秩序寻找绝对可靠的根据。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塞耶斯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人性观做了准确的概括:“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严格而唯一的对照中,他们企图区别一套普遍永恒的人类特征,并把它们与那些仅仅是社会的、可能发生的和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区别。他们的目的是要确定‘自然的’和‘本质的’人类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作为社会解释和道德价值的基础。”[6](P193)而马克思则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性必然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历史境遇中,根本不存在人类永恒不变的本质。“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7](P326)可见,马克思确立的是一种历史人性观。在人的历史性境遇中,物质生产方式是最根本的因素,它决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力量,而与物质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如何生产、生产什么、生产的物质条件等都是技术的具体形态。机器体系是变革工场手工业的前提和起点,机器大工业这一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必然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当然,技术不仅仅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技术甚至已经和国家权力融合在一起,逐渐成为一个标尺,日益侵入并统一社会的各个领域。尽管异化是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共有的特征,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相比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时期人的异化的存在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劳动异化在机器体系中达到了顶点。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利用工具,他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劳动资料的运动以工人为核心;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服侍机器,机器作为生产过程的主导独立于工人而存在,作为活的附属物的工人被并入作为死机构的机器,不是机器围绕工人运动,而是工人跟随机器的运动,丧失了主体性。机器和机器体系不仅使工人身体上的自由活动荡然无存,而且精神上的自由活动也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1](P487)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工人也屈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但从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来看,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工人运用工具进行的具体劳动,工人的主体地位并未消除,作为支配劳动过程的统一体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然而,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艺和力量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工人的活劳动仅仅作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一个附件,并且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这种机器体系相对于单个工人无足轻重的单调操作,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具有绝对优势的肌体。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还是形式从属,劳动只是在形式上服从资本的指挥,工人的技艺、劳动能力、劳动方式、劳动过程与传统手工业相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所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也就是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被颠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仍然具有自足性。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过去一切血缘的、宗法的、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被资本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交换领域形式自由基础之上的雇佣劳动关系。然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这一时期,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主要采取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方法。在机器大工业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机器体系作为一个总体支配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单个的有意识的工人被分布在机器体系的一个个点上,劳动对资本的关系从形式从属发展为实质从属。实质从属意味着工人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主体地位,完全从属于机器的运行模式,缺乏自主性。区分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根据是劳动过程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变革。
机器的出场意味着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加深了对工人精神和肉体上的规训,资本已经全面渗透和宰制整个劳动过程,工人的劳动不再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展示,而仅仅是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劳动过程内部发生了深刻变革,机器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与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勾连在一起。单个工人的局部技巧和劳动能力在庞大的自动化机器体系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在生产过程中与整个固定资本相比作为无限小的力量,逐渐趋于消失。“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P487)机器体系自身已含有社会权力,它作为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支配和吸收工人的活劳动力。资本用来束缚工人的奴隶制,在哪里也都没有在机器体系中暴露得那样明显,交换领域的形式自由被撕裂了,成为意识形态的幻觉。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往往从宏观历史维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往往忽略从微观劳动主体维度批判资本主义。资本对劳动的规训已经介入到微观生命个体层面,资本对工人的规训已经深入到工人的整个生命时间,按照奈格里的说法,在这一层面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切实贯彻。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对工人微观规训的分析是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马克思认为在机器大工业中,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所特有的专业和技艺被抽象化和简单化,各种专业性的劳动被通约为工人在机器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工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性别与年龄的自然差别,各种劳动在机器的规制下呈现出均等化的趋势。“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8](P560)马克思在这里阐发了一种技术通约化思想。所谓技术通约化就是把技术作为一个尺度或者绝对规则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各种本来异质的事物根据现代技术的要求重新塑造,从而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工人必须顺应机器运动的逻辑,工人的劳动必须符合技术标准,当然这一方面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使人的能力、智力和知识只能在某一方面发展,从而变得单向度化。人的个性存在被镶进技术架构之中,从而不得不被均一化。技术通约化思想在后来的哲学家那里得到重大进展,比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达成了不少共识。海德格尔认为,“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9](P921)海德格尔明确表达了技术通约化思想,人被技术同质化和平均化。马尔库塞曾指出,技术控制已经渗透到一切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差异和对立都被均质化为中立的控制对象。哈贝马斯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已渗透到广大非政治领域,逐渐塑造了人们新的自我理解。
马克思认为,由于机器技术把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机器对工人产生了直接影响: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占有。机器技术有效地瓦解了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也使人的肌肉力量成为对生产来说多余的东西,因而机器成了雇佣非成熟非熟练的妇女或儿童的手段。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整个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受资本统治,儿童受教育的时间遭到剥夺,妇女做家庭事务的自由时间也遭到剥夺。全体家庭成员都被抛到劳动力市场上,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分摊了男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的整个家庭成员生活所需的价值。尽管整个家庭工资水平没变还等于男劳动力的个人工资水平,但是却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增加资本剥削的程度。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哈维曾举例,20世纪60年代巴西出现了经济奇迹,其主导原因在于个人工资下降,但是家庭工资被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巴西的妇女甚至儿童也参加了工作。[10](P228)
机器的使用为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可能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生产的持续性。机器成为工业上的永动机,它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生产,除非它遇到了作为它的助手的工人身体上的自然界限,例如人的意志和身体的虚弱等。资本家具有尽快使用机器的强烈愿望,这当然是为了直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此外,机器的损耗也是加快资本使用的原因,机器的损耗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两种。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另一种是闲置,前一种损耗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这是资本家积极力争的),后一种损耗是由于生锈(这是资本家不愿看到的)。机器还有无形损耗,这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报废。只要同样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生产出来,或者出现了更好的机器,原有机器的价值就会受损。因为它的价值不是由当时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提高之后它本身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家为了对付这种经济上的威胁,就有强烈动机尽快使用机器,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一天24小时运转,尤其在机器的最初生活期。机器所造成的劳动时间的无限度延长,使生命和健康遭到严重威胁,工人发起了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因而产生了由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假如工作日一定,那么劳动强度就获得了决定性意义,劳动时间上的损失,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补偿,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成为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劳动的强化是资本家的一个重要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生命意志和精神遭受更大的摧残,仅仅成为机器的附庸。
三、作为资本的机器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现在和几千年前一样,生产物质生活是人们几千年以来直到今天都必须每天从事的历史活动。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中,塑造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的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方面能够满足人类有机体迫切的生物性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新需要、新能力、新知识、新个性的创造性资源。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机器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为个人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机器体系作为一种“酵母”,它的发展不断地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机器工厂的建立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解体;机器体系的采用逐渐瓦解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旧的生产方式;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城市;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加强了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机器体系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商品,培养了人的需要、消费能力和享受能力的多样性;等等。所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看,机器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生活形式,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现象。
机器是工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工人社会性的对象化,但它具有从属于资本的异化形式,表现为对工人来说外在的东西。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了机器所造成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进一步异化,但同时并没有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进行完全否定,而是敏锐地发现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对机器的思考始终是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这一共产主义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必须扬弃机器异化,充分吸收机器的文明要素。机器异化和机器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自觉地一直在为扬弃自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必要的准备,这是马克思机器观的根本特质。作为资本的机器在无意中发挥了重大的文明作用,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文明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机器和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资本必然将机器体系的发展纳入自己运行的逻辑,从而塑造和引导机器体系的发展,而发展了的机器体系又促进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机器体系上资本获得了充分发展,机器体系是与资本最相适合的生产方式,机器和机器体系是资本增值的现实技术基础。机器体系资本化了,机器体系的运转、发明都要遵循资本增值逻辑。机器体系的使命是生产物质财富,它在物质生产中的科学运用所产生的规模在以往时代是想象不到的。所以,“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规模,也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5](P106)这里的固定资本结合上下文看指的就是作为资本的机器体系,机器体系的资本使用作为取代直接劳动时间的新的财富尺度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绝对必须的前提。如果整个社会还处在极端贫乏状态,人们就会陷入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一切污浊的东西又要全部死灰复燃,人的个性实现根本无从谈起。机器的采用增加了物质财富,同时又增加了消费能力和消费形式的多样性,克服了传统社会消费的贫乏和单一性,塑造了新的个性能力。
机器体系的采用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减少了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从而为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提供可能,这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机器使人们从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人们才可能在科学、艺术等个性方面得到自由发展。因此,马克思写道,通过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5](P96-97)机器体系作为资本完全是无意地通过自己的“财富癖”生产出丰裕的剩余时间,资本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从而为所有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可能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一“必然王国”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一方面必须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必须受技术规律和科学规律的支配,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自由时间中才能实现。在马克思这里,时间具有存在论意义,自由时间是人的本然属性,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除饮食、睡眠等必要的生理时间之外,都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那么,他不过是一台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对自由时间的占有,迫使自由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这是资本本性使然和资本文明作用的限度,只要资本这一生产方式没有被颠覆,机器创造的自由时间就存在被一小部分人占有的危险。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时间相对于马克思时代已经大大缩短了,并且由法律规定。机器体系的资本使用所导致的劳动时间的缩短终归为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提供了可能。
作为资本的机器体系不仅为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创造提供条件,而且也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结合。马克思指出:“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5](P101)机器大生产作为一种发达的生产方式瓦解了传统手工业那种终生使工人固定在一种职业上的分工,它使社会分工获得空前规模的发展,对产品的生产分成无数的部门。机器大工业撕裂了传统手工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原始纽带,使人们建立起了普遍交往,机器这种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一种高级的社会结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1](P627)机器的采用使分工变得国际化,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被机器这一高级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交往彻底瓦解,全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生产和消费逐渐国际化,各民族狭隘的市场和经济被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取代,这就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当然,以资本为主导的交往必然带来普遍异化,但在这个过程却塑造了人的个性的丰富性、普遍性和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的程度和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也和人的交往的程度是一致的。
作为资本的机器虽然能够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一些历史条件,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资本的本性,它并不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个性的问题。机器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这一逻辑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因果必然性奴役着和支配着现代人。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是拥有财产权的自由,这一点恰恰离真正自由个性的实现最远。因为它服从的是资本增值的物化逻辑,自由的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资本。而要使机器能够与人真正相互促进,要使机器成为自由个性实现的必备条件,而不是压制个性的工具,必须变革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推行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1](P451)而要实现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必须超越物化逻辑和私有财产制度,实现一种新制度的创制,这种新制度即是“联合”,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生产实行民主管理和计划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物质财富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机器等生产资料不再遵循私有财产的逻辑而是被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这种联合意味着个人不再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而是把全部物质财富作为自己的作品和本质力量的全面证明。马克思对机器的辩证分析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启示,机器作为资本或者说机器的资本使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它作为发达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由时间的增加和全球经济的交往,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的历史限度,它具有自身无法克制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同时限制资本,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既要利用各种资本发展市场经济,又要限制资本,保持市场经济健康与稳定。
[1] 马克思.资本论 [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M].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 [英]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M].冯颜利译.任平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 [M].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0] [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孔伟]
Marx’sMachineViewandItsHumanDimension
Chen Fei
(School of Marxist,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machine; capital; alienation; free personality
In theCapital,Marx analyzed machines and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Marx linked the essence of the machine with the human being’s existence: On the one hand, in the machine big industry, the machine replaced the worker’s skill and the strength to occupy the main status, the work of a worker was only as an attachment to the machine system, which was determ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 compared to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was further alien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chine as a superior form of capital had an important role in civilization, it had created rich material wealth, increased the free time of the society,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associ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Due to the nature of capital,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 can not ultima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freedom, the communist use of the machine eliminated the slave and control of the machine.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项目号:16CZX013)的阶段性成果。
陈飞,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