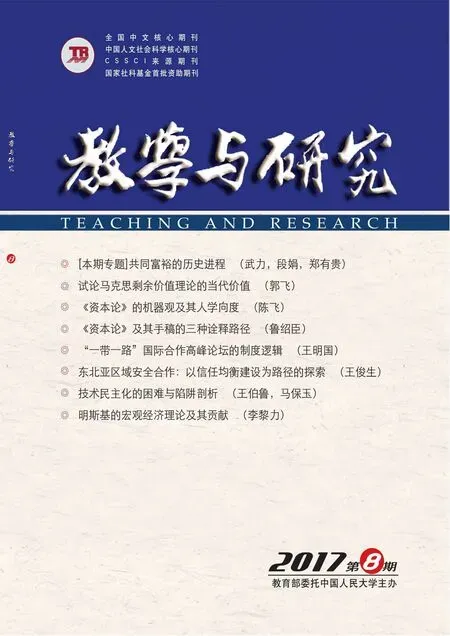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武力
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脱贫攻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范围内,是全球各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国家为加速工业化而不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历史,而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则同时包含着两个目标:一是现有制度能够保障有足够的积累可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发展是硬道理和加快工业化这个大前提下,改革开放之前是在高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基本政策下,实行高度平均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特别是在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其政策目标是:既要通过保证资本的收益以提高积累和鼓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增加人民的流动性收入,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内需和社会的安定。在进入21世纪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党和政府将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和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变化,即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949—1956),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的按劳分配(1957—1978),又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建立和实施高积累政策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6年,为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在单一公有制和高积累政策下,实行形式单一的按劳分配,居民的财富占有高度均等化;1979—2017年,是通过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快速推进,收入分配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也变成按要素分配,私人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扩大。2005年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大了调控初次分配、扩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并制定了2020年“整体脱贫”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一、1978年以前的经济体制与收入分配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改革,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和调整工商业三大举措,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剥削,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大大缩小了旧中国留下的贫富差距。如果从经济结构看,处于领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和数量比重都很大的个体经济,基本上都是按劳分配(农民家庭之间的生产资料占有差距很小,几乎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城市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下的“四马分肥”。
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随后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及后来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等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使得独立后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国家统一受到阻碍,因此国家安全问题处于突出位置,而要应对战争威胁和保证国家安全,就必须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1952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直接关系到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虽然当时的钢产量已经是1949年的3倍,但是与当时的美国相比,钢产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钢产量美国是中国的224倍。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P329)
因此,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即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2](P353)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2](P705)而此后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等,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处于突出地位,这也就使得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被过度强调,高积累政策不断强化。
当1952年基本完成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并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同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建立起“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虽然没有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却保证了为工业化提供高积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一)为保证贫困条件下的高积累和社会稳定,中国确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
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二百多年里,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大大落后了。于是,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实现经济赶超就成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大国的必然目标。
而当1952年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其自身的积累能力则非常有限。作为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能够用于工业化的剩余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绝大多数农户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加上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
而在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农村个体经济,不仅绝大多数发展生产困难,而且会出现贫富分化,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所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P436-437)
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则避免了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和部分人因失去生产资料而陷入极端贫困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另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能够保障在工业化实现前的极低收入水平下的高积累,1956年以后到1976年间,中国的积累率始终在20%以上,极少数年份甚至达到30%以上而没有出现社会动荡,说明了这种体制具有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的功能,从而保障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长期优先发展。
(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计划供应,使得贫富差距极小
单一公有制和高积累政策下的“按劳分配”,使得收入分配出现高度平均的特点,其有限的差距,也主要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和政策则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即中央有关部委不仅严格规定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等级和总额、连奖金、补贴以及福利性收入也严格控制,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当然,还有大量根据国家严格规定的隐性收入和福利,例如,低廉的房租、公费医疗、教育等。
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几乎清一色的农民个体经济,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也基本实现了按劳分配。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按劳分配,国家也有严格统一的规定,例如,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牲畜用粮标准、种子留粮标准等,只不过口粮按人口分配、现金按“工分”分配,由于口粮在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中占主要部分,因此,农民的收入分配更具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国家不仅对农业生产剩余通过统购统销提取,还严格限制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既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也是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也在不同的阶段差异很大。1950—1956年的7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而1957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持续的过高积累政策,居民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很低,即使城市中的高收入阶层,在计划供应和票证制度下,也往往是“持币待购”,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居不下。根据历年统计年鉴计算,改革前,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的恩格尔系数始终在55%之上,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始终高达65%以上。从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其中,住房、医药和教育的费用低,在消费支出中占较小比例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农村居民则不享受国家提供的这些优惠,农村居民在这三方面所占的费用很少。首先是因为在农村住房费用要比城市低,其次,农民为节省费用选择较差的居住环境,再次,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农民也只能选择较低的消费水平或者不消费,当时看不起病的农民大有人在,同时在农村教育水平也很低,失学率很高。不过,当时在农村还实行过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以及“五保户”制度,但保障水平比较低,降低了农民的一部分费用。当然,当时国家对教育的收费也比较低。
二、1978—1991年鼓励勤劳致富的分配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就经济领域来看,重点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潮,为“按劳分配”正名,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与此同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在城市也进行了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普涨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农村家庭经营和城镇个体经济的收入分配不仅使得全社会的居民收入增加,甚至缩小了工农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1978—1991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仍然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非公经济主要还是被称为“光彩事业”的个体经济。但是,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市场机制已经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长期经济“紧运行”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短缺,又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特别是原来处于收入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率先利用“放权让利”的政策和“短缺经济”环境,从事家庭经营和“搞活经济”,使收入大增,一时间在知识分子阶层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抱怨。
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党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和政策开始突破过去20多年一直实行的平均主义束缚。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P152)
在“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的政策下,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包”字进城后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改变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致富的积极性。“脱贫致富”成为整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在改革分配制度的同时,还针对长期形成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态,对经济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即由过去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并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整个80年代,出于补偿前30年高积累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多的“欠账”,轻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改变轻重工业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的消费品短缺所形成的巨大需求也成为轻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79—1988年间,不仅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甚至在1985年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轻工业也是持续高速发展,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重工业。整个80年代,是人们生活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城乡之间、城市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帕累托最优”改进阶段。
三、1992—2012年要素主导分配格局的形成
1992—2012的20年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2年,是新中国60多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收入分配领域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流动性增加;二是要素参与分配,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加。其基础当然是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后,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本参与分配的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决定性作用,高素质劳动力和管理层的供不应求,也导致了雇佣劳动者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和管理的各个行业的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此外,1997年以后买方市场出现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速大大放缓,而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改革,又使得部分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因此,1997年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2008年达到0.491,此后逐渐回落,到2012年为0.474。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在新增财富分配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化,而工薪收入所占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2000年以来,一直在0.46以上徘徊,最高的年份为2008年,曾经达到0.491,之后虽逐步回落,2016年仍然为0.465,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少数国家之一。[4]因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和资本在按要素分配中占比过高所导致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并导致阶层分化,更为严重的是抑制了内需扩大和人力资本提升,从而抑制了社会创新的活力。从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来看,这种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快的情况,固然有利于投资增加和资本形成,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这同时也将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导致新增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过剩,因此一旦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不足时,就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从而迫使国民经济转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特点的调整。
在这个时期,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待遇被压的很低,尤其是那些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所谓的“富士康现象”和2008年以来的“民工荒”即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个时期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主要不是依靠提高收入来调动在职员工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职工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被压的很低,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额的大幅度提升,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低价。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和出口因加入WTO后迅猛增长,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本设施)投资带动的工业发展再次呈现出“重化”倾向,这种生产资料内部的循环和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显然不利于农民和工薪阶层收入的提高,工薪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降低。尽管从2005年起政府加大了二次分配的力度,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财政政策,更加强调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但是,收入分配机制市场化、资本主导分配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四、十八大以来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举措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5](P14)为此,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要求在收入分配方面“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5](P33)
自党的十八大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经济新常态下加以贯彻落实。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慰问河北省阜平县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开启了十八大以来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攻坚战。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7]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8]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要求。规划贯彻以人民为本的原则和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要解决长期以来由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所积累的民生、生态、社会等问题。因此,规划中专门列出“全力实施脱贫攻坚”一篇,以确保5 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并对民生保障、教育和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设等篇都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以真正实现全面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同步进入全面小康。规划中提出:要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做好贫困地区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保障,加大财政、投资、金融、土地等政策扶持,创新政府购买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企业和社会组织帮扶等机制,形成推动脱贫奔小康的合力。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 240万人,249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如期完成;2017年计划使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 000万人以上,完成34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9]
五、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目标。20世纪50年代发展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环境和条件变了,方法和体制变了,但是目标始终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打破了“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束缚,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开发利用了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惊人的财富。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的悬殊,关键是如何将其限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居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市场机制虽然具有扩大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本质,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监管不力,则将这种差距扩大到不合理的程度,应该说这是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还有就是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时间阶段上看,也是利弊得失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贫困、温饱是主要问题时,为“搞活经济”和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不仅促进了改革开放,也提升了全体居民生活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为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快经济发展,对于稀缺的资本和人群给予较高的收入回报,也是合理的;但当市场经济确立、买方市场形成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政府对于资本主导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应该加以控制和限制,并通过二次分配加以调节,这项工作虽然自2004年以后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开始进行,但是总的来说力度不够,具体的方法和步骤还在探索中,确定2020年消灭贫困和实行“精准扶贫”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成果;同样,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实行社会政策“兜底”也是消灭城市贫困的有效办法。
总之,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至今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而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未完成,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目标。实践已经证明,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实现按劳分配,但却不能够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实现富裕,中国要发展并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过,但是市场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却不能迈过,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1] 毛泽东文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2015年有所上升[EB/OL].中国新闻网,2017-01-20.
[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习近平.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EB/OL].新华网,2012-12-30.
[7]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 03-18.
[8]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N].人民日报,2016-09-04.
[9]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7-03-17.
[责任编辑李文苓]
CommonProsperity:PracticeandDevelopmentofSocialisminChina
Wu L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distributi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tackling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how to restri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a reasonable and incentive range is a worldwide problem faced by all countri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is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order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implemented a high standard of basic living security under the two basic policies of “high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n the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policy objectives are: to increase accumulation and encourage investment by ensuring the income of capital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the income of the people, and restric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a certain range, to ensure social stability and domestic demand. After entering twenty-first century, unde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PC has taken on eliminating poverty,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s a short-term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2015MZD009)的阶段性成果。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