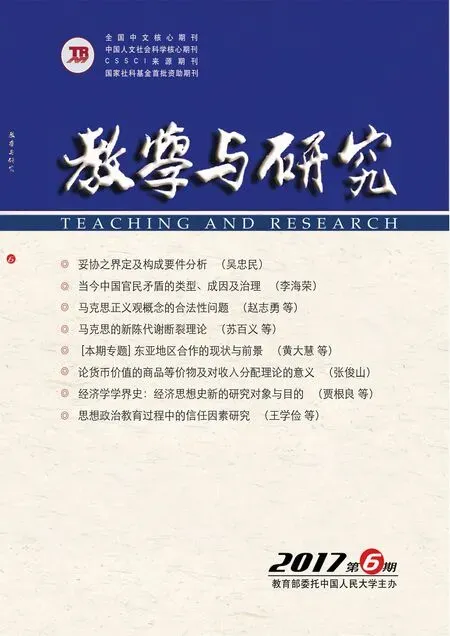当今中国官民矛盾的类型、成因及治理
李海荣
当今中国官民矛盾的类型、成因及治理
李海荣
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治理转型
官民矛盾问题作为一个突出性问题,已经步入“显化期”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一个新的增长点。“直接利益冲突”与“无利益冲突”是官民矛盾的两个基础类别。政府主导与民众需求的矛盾、国家职能转换与民众心理预期的冲突、公共权力与民争利、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网络的助推与放大效应以及矛盾化解手段的单一化等是官民矛盾的诱发因素。化解官民矛盾的形势尽管严峻,但仍有许多优势和空间,而这需要国家的治理转型来实现。
中国当前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期间,任何不和谐的因素都有演变为社会矛盾的可能。其中,官民矛盾日渐凸显,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不仅是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诱发因素,还制约着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目前中国社会涌现出的许多冲突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官民矛盾有关;很多社会矛盾推演到一定程度,问题的症结最终都可以归纳到官民矛盾这一问题上。
一、官民矛盾的基础类型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官民矛盾并非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官民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一直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中很难调和的一对范畴。尽管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因其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有别于以往,它自身呈现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性的特质和形态,并且前者往往通过后者表现出来。总体而言,现阶段的官民矛盾可以分为两大基础类型,“直接利益冲突”的官民矛盾与“无利益冲突”的官民矛盾。
(一)“直接利益冲突”式官民矛盾
所谓“直接利益冲突”式官民矛盾,是指公共权力部门与一般民众存在直接的利益纠葛。这类矛盾中,官与民是对立的直接双方,二者在思想观念与利益分割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纠纷,并且两者在矛盾中各不相让,冲突具有一定的直接性、持续性与对抗性。一般而言,这类矛盾多是由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做出了有损于民众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举动,进而招致大众对政府部门的怨恨和不满,二者在心理上产生了隔阂,在行动上形成了冲突与对抗。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民众在这类矛盾中一般处于“下风”,公共权力部门也往往是这类矛盾的真正制造者与根源。就行动原因和目标指向而言,这种类型的官民冲突即是真正意义上的官民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的改革模式,在成就“中国速度”的同时,也激发了全体民众的利益意识与权利观念。公共权力部门或公职人员一旦行为不当损害其切身利益时,民众异常敏感的神经便会被触动。尽管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也会寻求以各种各样的“抗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双方的行动逻辑如果不相契合,官民矛盾也就随之产生。现实生活中,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强制拆迁引发的官民对峙、工业建设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建设中的民众抗争、城市市容市貌整治行动中的“城管群体”与各类“小商小贩”的冲突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官民矛盾。
(二)“无利益冲突”式官民矛盾
所谓“无利益冲突”的官民矛盾,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官民冲突,冲突的双方尽管表面上是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另有其他潜在的相关者,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只是承担了其他类型的社会矛盾的“溢出”部分。换言之,这类的官民矛盾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其他社会问题的伴生物与演化品,是矛盾弱势一方无法排解的抑郁之气的一种情绪式宣泄,有学者将此类矛盾称为“社会泄愤”事件[1]、 “迁怒型”事件[2]。
当前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和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官民矛盾也呈现出一种“异化”状态,“表现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形态,且这种矛盾直指执政党及其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3]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个社会领域的矛盾与事件,政府总是难以置身度外”,[4]各类社会问题的矛头最终都指向了政府部门。并且与西方国家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西方多数抗争行动往往是反社会的色彩较为浓重,中国则是反政府倾向较为明显。官民矛盾在社会激变期表现出独具中国气质的一些特质:一是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向官请命”的解决自身要求的依赖感;二是具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因官员腐败、政府侵权而产生的对公权部门的不满;三是具有西方语境中的因劳资矛盾、福利弱化、环境污染等连带性问题而导致的对政府部门的怨愤。
进一步来讲,说官民矛盾带有传统痕迹,缘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共同体,君主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是民众的“父母官”,对社会大众承担着无限责任,也是民众赖以依靠的各种民间纠纷的最终裁决者。这种“父母般”的依赖延续到现在,尽管现代社会已建立了诸多的纠纷调解机制,但民众的多数纠纷最终还是希冀由政府来“调停”和“主持公道”。而一旦相关职能部门处理不好,就可能演化成官与民的矛盾与冲突。客观地讲,这类矛盾是一种连带性的矛盾,是各类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和爆发,公共权力部门的“全能型”色彩与过度膨胀,使得各类维权主体向政府机构“集火”,因此,这类广泛意义上的官民矛盾也就产生。
当代中国的官民矛盾其实也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19世纪的中国既受到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5](P334)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无疑受到了西力东渐的影响,因此,西方文明的某些因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中国民众的抗争模式,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正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也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实中出现的一些劳资、个人纠纷等民事问题,往往也归咎于政府部门解决不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民”与“官”的对峙情绪不断堆积、隔阂不断加大、矛盾日益深化,并以不断显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就本质而言,“无利益冲突的官民矛盾”是连带性、附属性的矛盾,尽管民众的最终行为都指向了公共权力部门,但事件的实际责任主体并非是政府机构。就此种意义而言,这些所谓的官民冲突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官民矛盾,它们只是各类社会性问题的衍生品,只不过各个公共权力部门成为矛盾一方的发泄口,无形中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二、官民矛盾的原因
官民矛盾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折射出的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与以民众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两者力量的此消彼长。相较社会结构已经稳定成熟的先发型国家而言,中国社会的力学格局还处于激荡变化中。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使得当代中国官民矛盾的发生与演变机制呈现出一些“中国特色”。
(一)政府主导与民众需求的矛盾
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是在一种时空压缩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压缩的现代化”[6]场景要求各项建设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独特的社会转型“场域”,增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作为一项国家集体项目,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参与。为达成这一任务目标,政治权威系统需要对民众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为了使以往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社会获得重新整合,中国的政治精英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黏合剂”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措施,弥合了各种社会力量间的裂痕,凝聚了建设与改革共识,使中国社会获得了一体化建设的条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此期间得以大幅度提升,公共权力机关在这一过程中也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P31)作为“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风险的积聚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8]当今中国早已是一个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的风险社会,局部问题都有扩大为全局性风险的可能。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条件,在加强风险生产的同时,并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管理预留时间。而为使“社会系统达到一个平衡状态”,[9](P124)中国社会客观上需要一个领导力量来应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风险与危机。在传统风险应对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风险管理职能。可以说,中国各级公共权力部门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管理系统”,职能权属在不断获得和累加。
此外,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社会大众公民意识缺损等原因,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既不能汇集“民意”,也无法制约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造就了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共权力部门“为民做主”的行为,政府机关也就相应地承担起对民众的“无限责任”,同时导致民众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逐步推进,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制度运行的“惯性”作用会使政府与民众的相对位置与共处方式处于一种稳定的结构之中。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深化,中国民众的生活需求逐渐增多并日益多元化,这无疑会给政府的公共供给造成很大压力。一旦双方的供给与需求发生冲突,政府行为就会招致民众的不满,进而将矛盾与冲突引向政府自身,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各级党政官员,也就成为民众抗争的直接对象。
(二)国家职能转换与民众心理预期的冲突
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向民众提供均等的、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是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的合法性来源。目前,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换言之,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还是民生问题。由于转型的复杂与急促,政府在职能定位与政策执行层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挫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导致民众对政府公共供给的心理预期与现实不符。作为刚性需求的公共服务一旦无法获得满足,民众心中的不满甚或是怨气就会不断累积,最终导致整体社会心态的失衡,官民隔阂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总的来看,政府职能转换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职能定位不清。由于各种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制约,政府的职能定位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位、错位问题,这是官民矛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有二:其一,“全能型政府”。在这种体制下,“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10](P3)进而形成国家政治权力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的运行格局。新中国现代化初期的许多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但“全能型政府”在强化政治权力控制力的同时,也过度“嵌入”到市场和社会领域中,侵蚀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土壤和成长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众的基本权利,致使官民关系紧张。其二,“经济型政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发展经济成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GDP”至上主义盛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扰乱政府正常职能的行使,使政府偏离运行的轨道,无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导致官民冲突发生。
2.政策执行缺损。当前中国官民的紧张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具体政策执行导致的。“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而“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1](P4)由于中国各个层面都在急剧转型,很多官员的执政理念与行为方式仍处于发展时期,“其公共服务的职业意识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难以满足民众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要求,甚至有时会出现一些有悖于民众利益的做法”,[2]进而引发官民矛盾的产生。现阶段官民矛盾呈现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逐层递增的特征,就凸显出因政策执行问题所产生的尖锐的官民冲突。
(三)公共权力与民争利
官民矛盾作为现阶段的一个突出性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利益结构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P187)而“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势必会导致相互间不一致的互动行为。重要的是,这样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是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13]如果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社会不满的积聚与社会焦虑的蔓延,社会矛盾的“目标替代”效应就会产生,最终导致任何与“官”有关的事情,都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大众的“围观”,双方的敌对感增强进而引发一系列冲突。此外,党政官员作为现阶段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当下社会格局中仍属于优势群体,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益较多,这也会导致普通民众“仇官”情绪的产生。加之一些政府部门凭借公共权力“与民争利”,更会使官民隔离加深,官民隔阂加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利益结构也处于一个调整过程中,还很不稳定。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进程中,往往忽视了对利益关系的调节,反而经常作为一个“准经济组织”直接介入市场经营活动中。“公众的仆人在管制市场方面常常会有其自己的利益,从而自由的私人选择会被公共选择所遮蔽或取代”,[14](P355)这往往会使各级政府成为“厂商”;[15]而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各级党政官员,也有追求利益的冲动,如果监管不当,“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16](P60-61)进而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直至发生官民矛盾。可见,不论官民矛盾的内容或表现形式如何,最后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有关。
(四)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协调各种关系,让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执政党面对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也是新时期官民关系的一大挑战。这期间,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对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法律地位、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认识,这就意味着之前官民互动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改变。换言之,普通民众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利益主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其政治参与诉求的增多,对社会利益的分配也更为敏感,这也要求执政党和政府部门要及时回应公民的各种需要。加之近些年“以人为本”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亦不断加深,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都使得民众对改革抱有很高的心理预期。
与一般民众的心理预期不同,中国改革的配套设计则相对滞后。作为“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其设计之初基本是一种经济型改革,与其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一开始并未纳入议程。因此,随着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日益增大,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这一过程中,强势群体获得了过多的利益,一部分党政官员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或凭借自己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不合理利益,而底层大众往往缺乏获取优势资源的手段,有时还可能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侵犯,导致他们成为改革进程中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改革进程尽管在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走高,但社会的一般民众时常有“被增长”的感觉,其“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加。这种改革的双重挤压效应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民众对改革的认同,进而加剧官民关系的紧张程度。
(五)网络的助推与放大效应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17](P569)网络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急速地嵌入到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网络以及相应网络生活的出现,为现代社会情境中的一般大众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生存图谱,改变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交往形式以及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同时,“互联网与任何报纸或电视频道相比,提供了更多的新闻来源和更多样化的新闻”,[18](P411)使得网络时代的官民矛盾更为复杂。
网络对官民矛盾的发生有明显的助推与放大作用。与现实社会不同,网络社会具有一定的“匿名化”效应,网络社会参与者可以不用考虑各种法律法规等现实性的约束,无须通过事前审核就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发声,这就使得各类消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较现实社会更为剧烈;官民矛盾作为社会热点问题,其在网络社会受到的关注度更高,经常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而受到“围观”,加之“晕轮效应”的影响,使官民矛盾的负面形象更为凸显。此外,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它的可获得性与可操作性相对简单容易,信息交换的成本也更为低廉,这些因素都使得民众之间的交流更为高效便捷。在社会矛盾频发的当今中国,某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极易在网络社会中被迅速渲染放大,而作为现代化主导者的政府官员则经常成为舆论的焦点,充当矛盾“助燃剂”的角色。近些年发生的“微笑局长”杨达才案、“房姐”事件、“雷洋案”等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网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形塑自身空间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民众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当今中国,网络参与作为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其发挥着动员民众的功能,也充当着民主化训练的工具,可以给公共权力以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些都在改变一般民众与政治精英的互动与交流方式,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时刻发生变化,这对官民矛盾的形成及演变机制都有着重要影响。
(六)矛盾化解手段的单一化
官民矛盾其实并不只是中国现阶段才有的现象,而是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的一大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就曾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19](P303)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已经愈演愈烈,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有可能演变成更大程度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体量巨大的后发型国家,众多的现代化事务在一个时空相对有限的情境下快速完成,本身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改革之初由于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等各种原因,导致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足;尤其重要的是,以经济改革为主的模式没有给政治改革充足的空间,致使政治改革滞后,改革的整体推进存在结构性问题。“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一个后果便是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大,社会问题丛生。而现代政党作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应该“建立正常的管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20](P138)防范因利益分化导致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流失。
由于各种历史及现实性原因,“稳定压倒一切”逐步成为中国政治层面的共识,“维稳”体制渐次形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官民矛盾问题,除了用人民币解决外,还受到很多行政力量的干预;加之各级政府的法治意识参差不齐,制度化吸纳社会矛盾的渠道经常处于堵塞乃至匮乏状态,致使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暂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而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矛盾堆积累加到一定程度,由于某些突发性因素就会到达爆发的节点,致使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泛政治化色彩,导致各级政府及官员成为“社会怨恨”的发泄对象,官民矛盾就会呈现整体比例抬升的态势。
三、官民矛盾的化解路径
较之其他社会问题,官民矛盾因冲突双方的政治身份及力量对比的差异而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放大;加之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场景,更使官民矛盾增加了变数,缓和与化解的机制也就更为复杂。因此,当前需要将官民矛盾置于中国现代化这一场景中来理解,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具体执行来达到总体性变革,以期提升治理的成效。
1.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就根本原因而言,当前中国出现的很多官民矛盾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公共权力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等行为;而公共权力不规范运行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很强的“污名化”效应,民众会习惯性地将众多社会矛盾的发生原因归咎到党政机关及其代理人身上。因此,消解官民矛盾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治理公共权力“失范”,规范公共权力运行。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权力规范已经做出了许多改革举措,相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方略,力求通过依宪执政、依法行政来实现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的建设目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公共权力回归本位,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各项制度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此驯服公共权力的傲慢,打破官民之间的隔离,重塑和谐的官民关系。
2.构建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客观而言,当下的官民矛盾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伴生性问题,表明官民关系的重塑需要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达成。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整合侧重意识形态层面,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整合则主要是利益整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的官民矛盾尽管凸显,但仍然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社会问题,利益诉求依旧大于政治抗争。因此,缓和官民对立亟须建立公正、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防范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与民争利,通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让渡与妥协来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获得,提升民众现代化建设的获得感,以此构筑新的社会合作秩序,缓和官民对立之势。
3.建立制度化的矛盾吸纳机制。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类型,官民矛盾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有效疏导则是此间的主要差别。中国现阶段的官民矛盾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缺乏科学规范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对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改变了之前的矛盾恐慌心态,认识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通过主动地创新社会治理来协调利益冲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此,今后要特别注意建立制度化的矛盾吸纳机制:其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加强官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使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合法的“代理人”及表达通道,减少无序化的抗争行为,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其二,建立制度化的矛盾解决机制,力求通过法治手段在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协商矛盾的解决方式,避免行政性、强制化的硬性整合。
4.积极改善民生。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本质上还是民生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然是当下最具共识的领域。换言之,大幅度改善民生状况可以有效缓解官民矛盾。基于中国现阶段的综合国力,可以首先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之后逐步向适度普惠型的福利社会迈进。这样能使民众享有一个基本生活的底线,主要弱势群体也有一个“兜底”的社会安全网,进而能给民众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发展前景,以此降低整体的社会焦虑,增进官民之间的政治互信,缓和紧张的官民关系。当前中国政府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就是对基本民生保障的一种制度化努力。
余 论
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官民矛盾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后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官民矛盾还会继续存在并可能会因为某些特定因素导致激化。就近期发展动态来看,现阶段的官民关系就呈现出了一些新特质:一是冲突程度的变化,已经由以前的个体性矛盾向群体性冲突发展,表明官民矛盾的指向性更为明确,也说明民众的维权抗争在走向组织聚合,官民矛盾的对抗强度会有所增加;二是矛盾议题的转换,开始由利益之争走向体制批判,反映出民众对当前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满及对制度合法性的质疑;三是互动模式的变更,民众与政府的独立利益主体地位在同时彰显,双方博弈的范围与程度都在增强。这些转变都会对今后官民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并且直接制约着官民矛盾的解决。
同时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就性质而言,现阶段的官民矛盾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尚未演化成“敌我矛盾”;就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层面而言,中国中近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此外,执政党有深刻的执政危机感,对官民冲突有清醒的认识,主动规范自身行为的可能性很高;加之中国政治精英群体依然具备一定的能力优势,这些因素都表明当代中国官民矛盾缓和与化解空间依旧存在。
中国当前正处于转型的节点时期,一个由转型逐步走向定型的关键时期。官民矛盾问题作为现阶段社会问题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和爆发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改革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官民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又是不断生成的,唯有深刻把握官民矛盾发生与演变的时代性、规律性,方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冲突,进而带动其他类型的社会矛盾的协同解决,这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1]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2] 吴忠民.当代中国社会“官民矛盾”问题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2,(3).
[3] 陈世瑞,曾学龙.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与化解之道[J].晋阳学刊,2015,(1).
[4] 黄建军.官民矛盾、信访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J].理论月刊,2014,(6).
[5]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M]. 迟越,王红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6] Chang Kyung-Sup.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South Korean Society in Transition[J].Economy and Society,1999,(1).
[7]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8]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等.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
[9] Talcott Parsons.The Social System[M].London:Routledge,1991.
[10]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11] [美]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吴忠民. 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概念辨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2).
[14]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5] Andrew G. Wader.Local Government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101).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美]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 [英]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19] 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0]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 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李文苓]
* * *
严正声明
最近,有人假冒《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名义,以为投稿人、作者发表作品为由到处行骗,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我编辑部的名誉权,更严重侵犯了投稿人、作者的合法权益。我编辑部已向公安机关举报。敬请各位投稿人、作者在投稿前谨慎行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上当受骗,由此而受到的损失与我编辑部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2017年6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正义观的复合结构研究”(项目号:15BZX018)的阶段性成果。
The Types,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in China Today
Li Hairong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Qi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official and civil contradictions; social contradictions;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s a prominent probl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s stepped into the “period of manifestation” and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and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are the two basic categories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leading and people’s demand, nat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eople’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the conflict of public power competing with the people’s interests, people’s rights awareness, network amplification boosting effect and the simply means of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constitutes the factors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official and people. Although the situation of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is grim, there are still many advantages and spaces. But to realize this go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is needed.
李海荣,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 青岛266061)。
——从于欢案“官民”互动和江歌案的中日舆论反差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