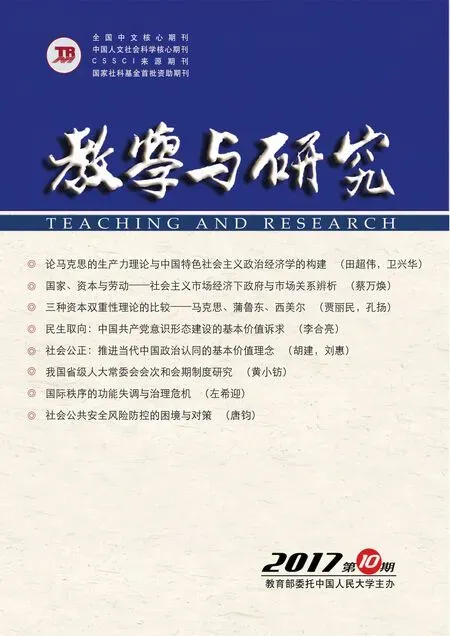国际秩序的功能失调与治理危机*
国际秩序的功能失调与治理危机*
左希迎
国际秩序;功能失调;治理危机;新兴大国;边缘力量
近年来,国际秩序出现了一系列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含全球治理的失灵,更在于地区安全治理走向失序。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在中东地区,美国撤出伊拉克,鼓励颜色革命,并且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战略,这些因素导致中东地区走向动荡;在欧洲地区,美国积极推广民主,鼓励民族自决,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起了美俄关系的恶化。总体而言,这些地区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新兴大国、边缘力量和美国三者的行为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张力。目前来看,既有国际秩序仍然是可以修补的,新秩序创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际秩序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失衡与平衡,危机与治理,崩溃与重建,这些都是国际秩序的常态,其根源是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新世纪以来,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导致其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些危机。[1]针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频发,一些视野广阔、思想睿智的战略家将目光投向了这些问题,并开出相应的处方。[2]深刻理解这些问题,需要将目光拉回到冷战结束之时,甚至是二战结束前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势力范围之争,更是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对立。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其他国家接受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安排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但也暂时掩盖了体系的矛盾。在这种框架下,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家之间的权力碰撞。
然而,权力的变迁仍然存在。在亚太地区,中日、中美之间权力转移速度非常快,已经威胁到现有的地区秩序;在中东地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的权力真空,以及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这两个因素导致地区安全秩序面临重构;在东欧地区,乌克兰事件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发酵,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环顾世界格局,当前国际安全秩序充满了危机。那么,当前国际秩序为什么会出现危机?哪些因素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危机?未来国际秩序变迁的走向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大有裨益。
一、国际秩序的治理危机
当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面临着功能失调的困境。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当前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遇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事关霸权主义内部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治理的危机。[3]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困境,这种危机根本上源于现实的变化,即权力转移、主权规范的退化和集体暴力的兴起威胁到旧秩序的基础。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全球治理的失灵,这种趋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世界是如此多元、如此丰富,观察国际秩序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将目光聚焦于地区层面。事实上,当前国际秩序更为严峻的治理危机集中在地区安全领域。
(一)亚太地区
在亚太地区,中国犹如破土而出的种子,其强劲的崛起态势加剧了地区秩序张力。美国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者,越来越多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面对这一挑战,美国的心态非常矛盾:一方面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防范中国的威胁和挑战。[4]这种矛盾心态和两手战略会加剧中美两国战略互动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这一战略态势将导致三个方面的功能失调。
首先,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频发。以往中美两国分别是作为一个陆权和海权国家而存在,两者的地缘政治错位有利于地区秩序的稳定。[5]然而,随着中国大力发展海军,这种态势未来恐怕将被打破,中美关系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引起美国的忧虑,并导致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竞争,有可能形成一种安全困境的态势。[6]具体来说,鉴于中美所处的位势不同,两国军事战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汲取了1996年台海危机中的教训,中国发展了一批杀手锏武器,以威慑美军并防止其干预台海问题,即被美军称之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2/AD)的战略。美国为了继续维系前沿防御,推出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来应对中国,中美在海军上的竞争以及西太平洋主导权的博弈,势必将引起两国关系走向紧张。[7]
其次,中美两国扮演的角色出现功能失调。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两国提供的地区公共物品也是互补的,共同维系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主要提供经济收益,美国主要提供安全预期。[8]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就不提供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在经济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比中国更重要。中国在此之前的角色,较少在军事领域冲击美国。然而,近年来中国提供安全预期的能力在上升,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正在冲击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权。
再次,中美在规则制定和维护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二战前后,美国基于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建立了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美国一道维系着这些原则。近年来,这一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中国正在试图修补既有的国际制度,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同时创设了亚投行,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试图通过创设新的国际组织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美在安全领域同样存在规则竞争。美国在南海坚持自由航行原则,试图通过规则主导权来侵蚀中国的主权要求;而中国则坚持主权原则来抵御美国。未来,中美之间在规则制定和维持上必然充满了更激烈的竞争,这将会撕裂原本已经碎片化的亚太地区秩序。
整体而言,亚太地区的秩序危机源于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亚太地区长期的稳定与和平是基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因此如何处理权力变迁与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年来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势,一个根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之间的‘大共识’已趋于瓦解。”[9]由于两国间缺少了对最根本战略问题的共识,两国战略互信难以建立,导致亚太地区秩序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冲突、腐败和动荡的地区,诸多复杂因素导致地区性危机频发。然而,最近十余年来,美国与恐怖主义的博弈,地区内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如果刨除旧有的顽疾,仅仅考察近年来新出现的危机,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权力真空给地区动荡埋下了种子。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推广民主,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推翻了一个已有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这一行为本身就改变了地区原有的结构和秩序。由于过度扩张态势的出现,美国减少战略资源的投入。[10]美国撤军后,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威胁到地区秩序。其一,大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加剧。美国撤军给其他大国干预中东事务提供了空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叙利亚危机难以解决,美俄在这一议题上势必持久博弈。其二,美国撤军也给中东地区增加了不确定性,由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关系,原先被掩盖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将会浮现。其三,虚弱的伊拉克和动乱的叙利亚不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尽管美国重建了伊拉克政府,然而这个政府软弱无力,难以治理整个国家。叙利亚国内更是爆发内战,叙利亚政府在反对派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也为其他力量介入制造了借口,给极端组织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美国的战略自相矛盾,引起地区秩序碎片化。具体到对叙利亚政府和伊拉克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表现出非常大的矛盾性,这不仅仅是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更是基于政治制度的偏好。美国在伊拉克支持政府军打击叛军,同时在叙利亚支持叛军反对政府军。然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叛军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还跟“基地”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国的叛军存在某种形式的流通和重叠。美国对此的心态微妙而复杂,即畏惧打击“伊斯兰国”会削弱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打击“伊斯兰国”则会威胁到伊拉克政府的生存,这种自相矛盾的战略导致了“伊斯兰国”做大做强,严重威胁到中东地区的稳定。[11]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抛弃其自身持有的政治偏好,又难以妥善解决“伊斯兰国”崛起带来的秩序碎片化。
再次,区域治理的愈加弱化,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秩序。推广民主制度,铸造一个更加民主的中东,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拉克战争之始,美国就将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设定为重要战略目的,以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然而,如果缺乏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支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将面临着诸多困难。从现实结果来看,美国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基本是失败的。[12]与此同时,美国鼓励中东国家颜色革命的方式也收效有限。如果考察中东地区出现的一些新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仅是源于中东有关国家的内部,更多是来源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失败。
(三)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美欧与俄罗斯的冲突。冷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西方与俄罗斯屡有龃龉,但是并未有直接冲突,更未产生地区战争。然而,乌克兰危机打破了这一局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直接导致其与西方的尖锐对立。究其原因,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秩序的未解之题。[13]分析乌克兰危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洲也出现了地缘政治危机。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城略地,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抢占胜利成果,借助推广民主压缩俄罗斯的影响力。其结果是,西方不顾俄罗斯的安全需求,无视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在西方长期的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和民主推广这三重政策影响下,橙色革命引起乌克兰政局动荡,进而演变为一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在推广民主上有两个失误。其一,西方国家的战略设想将民主推广作为其优先考虑,忽视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其二,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挤压俄罗斯,侵犯其核心利益。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有特殊意义,它不应该加入北约,更不能做双方对抗的前哨,美国推动乌克兰国内两派势力的合作方是上策。[14]
另一方面,国家主权原则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自决原则由来已久,其在《大西洋宪章》中被重申,并成为战后秩序的重要理念。这一原则长时间内更多是适用于殖民地国家独立,并没有被各国鼓励用以处理日常国际关系。然而,科索沃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为借口,开启了民族自决原则创造国家的源头。[15]回到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依靠西方开启的国际法,利用禁止通过武力获取领土这一根本原则,以及同样是根本原则的民族自决原则之间的张力,吞并了克里米亚,这给国际法秩序带来了挑战。[16]这显示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置换国际秩序大厦支柱的行为,弱化其亲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家坚持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同时推广民主制度,试图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这些战略旨在解放原先苏联阵营的国家,将其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这实质上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以降美国战略家一以贯之的战略实践。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家尚能坚持审慎的原则,兼顾地缘战略,避免直接侵犯苏联的核心利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战略家将地缘政治抛置于脑后,屡屡侵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其战略受阻也就在所难免。
二、失序时代的“麻烦制造者”
在国际层面,全球治理问题频频,逆全球化浮现;在地区层面,地区安全的治理也出现了诸多危机。那么,有哪些行为体或力量冲击了既有秩序呢?它们是如何冲击现存国际秩序的呢?总体来说,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力量有三类,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边缘力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这三类行为体的功能大为不同。
(一)新兴大国的挑战
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往往被批评为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针对西方国家的批评,不必讳言,大国崛起必然给国际秩序带来张力,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的强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的影响,对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也会有冲击。因为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即“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17]然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如何塑造国际秩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尝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谋求在既有国际制度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美国无意迎合新兴大国的全部正当利益,在安全上更是倾向于采取遏制战略,这迫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寻求其他出路。
在国际制度上,新兴大国提出了一些思路。其一,中国主持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利于推进亚洲国家的融资。尽管中国一直重申亚投行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组织,并非为颠覆而生,但是美国对此深表疑虑。[18]不能否认的是,亚投行在规则制定方面对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19]其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在秩序观上更加重视寻求影响力。[20]
在安全议题上,新兴大国与美国在国际规则上同样存在博弈。以亚太地区为例,中国正在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其一,在领土争端领域,中美两国在诸多规则上存在不同观点。2013年11月23日,中国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这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抗议。尽管中国宣称设立防空识别区符合国际惯例,中美两国在根本原则上并无重大分歧,[21]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对一些规则理解有所区别。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坚持三大原则,即维护南海的自由航行,对南海的领土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领土争端应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为此美国坚持自由航行,坚持中国要接受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在这些原则上,两国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认为南海的自由航行与安全并不存在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在新兴大国逐渐崛起的态势下,这些国家试图在某些领域调整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必须承认,新兴大国与美国在实力和合法性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这些国家更多的是希望调整而非颠覆国际规则。在现实政策中,中国倾向于通过抗争的方式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借以推动既有国际秩序的改革与调整。[22]
(二)边缘力量的抗争
边缘力量也是秩序的麻烦制造者,它们追求祛除西方建立的国际规则。当前,在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等区域,边缘力量逐渐聚合成带,并与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产生的地缘黑洞重合,从利比亚到埃及,从叙利亚到伊拉克和也门,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这些边缘力量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那么,边缘力量是如何反抗美国的军事存在、祛除国际规则的呢?
首先,恐怖主义活动抗争美国的军事存在。边缘力量之所以是麻烦制造者,是因为其组织形式多样,制造暴力更容易且成本低廉,消除这类暴力难度很大。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力量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邪恶力量”,是一种非正式力量。[23]然而,恐怖主义是一种低烈度的暴力行动,恐怖分子并非毫无理性。实际上,恐怖主义的行为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考虑,即通过绑架、劫持、爆炸和自杀式恐怖袭击等活动实现自身政治目的。[24]相对而言,恐怖主义为代表的边缘力量是国际社会中弱者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抗争,是一种解构既有秩序的力量。
其次,反美主义对抗美国的政治影响。反美主义是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地区和各国家的反美主义形态各异,这既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而存在,更是因为美国主张的意识形态。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它是美国衰落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它同样会侵蚀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马克·林奇(Marc Lynch)所指出,反美主义会影响到诸多政治议程,并极大地阻碍了一致认同的、合法的地区秩序或国际秩序的出现。[25](P170)
再次,伊斯兰主义侵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长久以来,中东地区是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构建的一套秩序。二战以后,在西方的主导下,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秩序建立起来。然而,这种秩序下仍然存在一种思想潮流,即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一个根据《古兰经》描述的政治秩序,这种诉求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26](P96-145)事实上,阿拉伯国家这种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有所结合。2010年12月以来,中东北非地区产生了一系列名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在中东变局中,抗议者产生了一种政治想象。[27]然而,这种政治想象到底是什么,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分别有自己的解读。在西方看来,阿拉伯之春是一种民主运动,是阿拉伯民众觉醒的社会运动,是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推翻专制政权的民主运动。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看来,阿拉伯之春则是伊斯兰的觉醒。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其产生是基于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它撕裂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弱化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加之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使得中东地区的秩序日趋碎片化。
如果审视中东地区伊斯兰与美国的关系,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复杂的互动。中东地区民族、宗教和政治异常复杂,地区秩序缺乏一个核心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国家之间实力相对均衡,地区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加之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巨大,这些力量对美国的抗争更多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倾向。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这些力量旨在瓦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侵蚀美国业已构建的地区规则。
(三)霸权国的破坏
美国控制了规则制定权,一旦规则不再符合其利益,美国往往扮演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总体来说,美国可以操控国际制度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往往使得国际规则丧失了其原有的功效,转变成为美国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不愿意实质性地改革既有国际制度。另一方面,美国抛弃了普世主义的路径,重新回到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过去十余年,美国在安全上的破坏作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这主要有三种途径:
其一,防范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崛起。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俄罗斯外交政策也时常咄咄逼人,美国越来越充满了不安全感,特别是南海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出现,客观上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对新兴大国的战略。为此,美国试图推动亚太联盟转型,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性,鼓励其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美国这种增加对其盟友承诺的行为,有可能鼓励盟友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
其二,坚持人权高于主权,损害主权规范。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了扩展战略,巩固胜利果实。在价值观上,美国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积极干涉一些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提出了“保护的责任”理念,旨在为干涉有“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提供合法性支持。二战后人权革命使得国家主权规范受到损害,推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渐进变革,[28](P246-250)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这两个理念更是成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恰是美国的这种选择,正在瓦解其亲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当今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联合国宪章》而设立的,其中主权平等、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更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和民主推广直接冲击以上基本原则,撼动了既有国际秩序。
其三,积极推广民主,频繁使用武力。如果将美国的战略行为和地区治理危机结合起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9·11”事件之后,美国相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并且通过推翻已有政权,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在单极状态下,美国秉持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积极推广民主以建立符合自己偏好的政权形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行为逻辑,即大力支持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试图通过改造就有的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如果仔细审视这一行为的后果,可以发现,美国推广民主同时加剧了一些地区的碎片化。在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一些政权被推翻,换之以民主政体,其结果是新政府难以掌控、管理整个国家,由此导致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族群冲突凸显,宗教矛盾激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飙升。
三、国际秩序的变革与调整
秩序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因素。对各国政治家而言,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其政治行为的重要目的。然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政治文明程度、军事实力大小、社会治理水平和地缘政治态势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国际社会是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而存在。因此,在不同地区会在特定时间出现一些冲击既有秩序的力量和运动,国际秩序的调整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新秩序与旧秩序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9](P14)新秩序也要等到旧秩序衰败之后方可生长。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力量正在组合,变革已经难以避免。那么,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已经衰败?必须看到,旧秩序衰败与新秩序创设都是困难的,不能盲目乐观。当前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国际秩序与权力结构之间错位产生的功能失调已经难以忽视,然而它并未走向衰败。
首先,当前国际秩序虽然受到冲击,但是仍然具有生命力。尽管当前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一些危机与问题,但是既有国际组织需要及时做出一些调整。然而,既有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理念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的民族自决、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依靠国际规则、自由贸易等理念深入人心,即便美国也难以完全抛弃这些理念。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更多是对这些原则的破坏,而非这些原则无法适用于现实。从现实来看,尽管既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有所流失,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当前的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其次,美国的纠偏机制仍然运转良好。作为一个霸权,强大的纠偏机制是维持既有国际秩序生命力的关键,这种纠偏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上的纠偏机制仍然非常有效。尽管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正在相对衰落,然而,美国并未绝对衰落。近年来,学术界针对美国是否衰落存在争论。事实上,美国经济一直维持着可观的增长速度,不能看低美国的经济潜力。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可以支撑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在外交战略上的纠偏机制同样及时。小布什政府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导致美国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奥巴马上任以后,他坚持美国需要有耐心、需要克制,以矫正以往的战略错误。[30]特朗普上台以后,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试图弥补奥巴马时期外交政策的不足之处。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的战略纠偏一直在进行。
再次,新兴大国缺乏挑战美国的意愿。冷战结束之后,由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其他国家并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近年来,学术界认为有两个趋向正在推翻这一观点,即中国日益强势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然而,这两个趋势很难说明中俄两国会挑战美国。其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过去几年,由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议题上坚持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因此被一些国家认定为强势。事实上,中国只是更加敢于维护国家利益而已,并无意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更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其二,俄国无力挑战美国,其意愿也不强。尽管美俄关系仍然紧张,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等议题上两国针锋相对。然而,两国之间的分歧相对可控,俄罗斯并没有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更无力对美国霸权发起冲击。
(二)特朗普政府与既有国际秩序的调整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正在试图解决国际秩序的治理危机。其思路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一定程度上,目前国际秩序的功能失调还是可以修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家实力只是相对衰落,并未彻底毁坏。另一方面,尽管既有国际秩序受到一些破坏,但是仍然被绝大部分国家认同。就目前而言,特朗普调整既有国际秩序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强自身实力,夯实美国维持秩序的权力基础。一方面,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经济,它主要通过三种措施:其一,特朗普提出了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试图通过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发展。其二,特朗普重视制造业,试图通过推动制造业回归来增加就业,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其三,特朗普推动减税计划,试图通过企业减税吸引海外企业投资,增加国内企业利益,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特朗普也试图重振军事力量。为此,特朗普通过削减等额的非防务性支出来增加防务预算。2017年2月27日,特朗普宣布美国2018年财政预算中,将额外增加54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这将比2017财年增加10%。[31]他还计划扩充现役陆军人数和海军陆战队人数,并宣称将军舰数量从272艘增加到350艘。
其次,美国追求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注重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收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维系到现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开放性。这意味着,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其他国家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享受美国提供的发展红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承担的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近年来,美国试图调整这一态势。奥巴马的处方是美国以TPP为工具,重塑其在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相对而言,这是一种集团化的规则设计。特朗普的处方则截然不同,他拒绝接受TPP,试图通过缩小美国贸易逆差,重新商谈贸易协定,追求一种公平的贸易体系。此外,美国还重新审视新兴大国提出的一些理念和国际制度。在此之前,美国有些战略精英就认为,亚投行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创建并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前景与现有秩序联接起来,以满足新的需求。”[32]特朗普上台以后,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评估,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上有可能会转变立场。
再次,美国正在追求区域内的大国协调。过去几年,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令西方惊呼权力政治的回归,世界重新进入炮舰外交的时代。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俄罗斯外交行为更加强势的因素,但也有美国的因素。换言之,美国长期肆无忌惮地侵犯其他大国的核心利益,无节制地挤压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从而引起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逐渐调整了战略思路。一方面,美国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受到国内政治的阻碍,但是美俄关系已经比奥巴马政府时期大为缓和。另一方面,美国也在调整对华关系,试图通过挂钩战略迫使中国在朝核问题等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事实上,对美国而言,大国协调可能是最为合理的选择。毕竟,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政治多元、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建立符合地区多样性的地区秩序才是明智之举。[33]
四、未来的国际秩序走向
在边缘力量和新兴大国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逆全球化的标志,特朗普政府拒绝TPP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更是被视为国际秩序正在转型的象征。那么,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有三个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美国的权力基础仍然强大,但是仍将被持续侵蚀。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家独大,其超强的实力令其他国家难以项背。然而,有两股力量一直在侵蚀美国的权力基础,即以恐怖主义为首的边缘力量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应该说,这两股力量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他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令国际社会充满了疑虑。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抛弃世界而独行。[34]目前美国权力仍然是稳固的:国内经济仍然运转良好,在可预见时期内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军事力量仍然冠绝全球,其他国家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比肩;政治上虽然声誉受损,但是仍然被广泛认可。当然必须看到,边缘力量和新兴大国仍将持续挑战美国的权力基础,这个历史过程仍在继续。
其次,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能力逐渐上升。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国际制度再安排是核心内容。[35]事实上,当前新兴大国难以完全推翻既有国际秩序,渐进推动这个体系进行修复和改革是明智的选择。对这一点,国内存在一些异议。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未来中美两国可能存在一场“世纪对决”,世界有可能进入一个中国的时代,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内涵。[36]这种战略设想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固有思维,与世界现实有较大距离。事实上,国际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颠覆既有国际秩序并非明智之举。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建立秩序。”[37](P43)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在既有国际秩序内寻求改革,同时在既有国际秩序之外寻求增量改革可能是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也贴近目前的国际现实。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详细阐述了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理念,并且提出了“中国方案”,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强大的中国力量。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38]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成长,国际秩序中的“中国方案”也必将日益受到重视。
再次,国际秩序的文明属性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西方价值和理念建立的,民族自决、主权平等和自由贸易等原则都是西方文明的理念。这种国际秩序在最初必然是依赖于西方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且为其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文明属性日益重要,一方面体现在“9·11”事件以来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近年来欧洲与美国伊斯兰移民的增加,恐怖袭击频发,产生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并非美国一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文明。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会越来越遇到这种文明力量的抵制。这意味着,中国作为新秩序的建设者,面临的困难将是超出想象的。基于此,不管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任何新理念,也不管中国试图在多大程度上改革既有国际秩序,都需要非常审慎,切记通过和缓的方式,切忌低估西方国家的抵制力度。
[1] G. John Ikenberry et al..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M].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
[3]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4] 崔立如.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秩序演变[J]. 现代国际关系,2008,(1).
[5]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 4,1999.
[6] Adam P. Liff,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J].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9, No. 2,2014.
[7] Stephen Biddle, Ivan Oelrich. Future Warfar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ese Antiaccess/Area Denial, U.S. AirSea Battle, and Command of the Commons in East Asia[J].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41,No. 1,2016.
[8]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J].当代亚太,2011,(3);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J].当代亚太,2012,(5);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J].当代亚太,2014,(6).
[9] 达巍.中美还能重建“大共识”吗?[EB/OL].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357483.
[10] 牛新春.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J].外交评论,2012,(2); Marc Lynch.Obama and the Middle East: Rightsizing the U.S. Role[J].Foreign Affairs,Vol.94,No.5 ,2015.
[11] 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4,(10).
[12] Alexander B. Downes, Lindsey A. O’Rourke.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Why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Seldom Improves Interstate Relations[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2,2016.
[13] Rajan Menon, Eugene Rumer.Conflict in Ukraine:The Unwinding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M].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15.
[14] Henry A. Kissinger.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Start at the End[EB/O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 6-d34c451760b9_story.html.
[15] Spyros Economides. Kosovo,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J].Europe-Asia Studies,Vol.65,No.5,2013.
[16] William W. Burke-White.Crime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J].Survival,Vol.56,No.4 ,2014.
[17] 王缉思.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937.
[18] 金立群.亚投行并非为颠覆而生[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171.
[19] 陈绍峰.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J].美国研究,2015,(3).
[20] 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J].外交评论,2016,(1).
[21] 曹群.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J].当代亚太,2014,(2).
[22] Randall L. Schweller,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1,2011.
[23] 郑永年.国际政治中的三种非正式力量[EB/OL].http://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50623-494905.
[24] Robert Pape.Dying to Win: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M].New York:The Random House,2005.
[25] [美]马克·林奇.阿拉伯世界:反美是天性吗?[A].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编.谁在反对美国[C].朱世龙,刘利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6]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M].New York: Penguin Press,2014.
[27] 曾向红,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
[28]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2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 Barry R. Posen.Restraint: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31] President Trump Is Rebuild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EB/OL].https://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28/president-trump-rebuilding-americas-national-security.
[32] Robert Zoellick.Shunning Beijing’s Infrastructure Bank Was a Mistake for the US[EB/OL]. http://www.ft.com/intl/cms/s/0/c870c 090-0a0c-11e5-a6a8-00144feabdc0.html#axzz3 pJO2zDAI.
[33] 阎学通.亚洲应因地制宜建立多样性地区秩序[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26/c1002-27058189.html.
[34] H.R. McMaster, Gary D. Cohn.America First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J].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30,2017.
[35]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J].国际政治科学,2016,(1).
[36]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37] 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J].国际政治研究,2014,(1).
[38]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 28/c_1119641652.htm.
TheDysfunctionandCrisisofInternationalOrder
ZuoXiy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international order; dysfunction; governance crisis; rising power; marginal for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eries of cr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se crisis not only lies in the fail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disorder of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rise of China has intensified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 the troops from Iraq and carried out a self contradictory strategy, which encouraged the color revolution. These factors have led to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ctively promotes democracy, encourage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mpresses Russia’s strategic space, caus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Overall, the formation of these regional crises, mainly because of the actions of emerging powers, the marginal forc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exacerbates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can still be mended, while the creation of a new order is yet a long process.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军事战略转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号:14CGJ022)的阶段性成果。
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