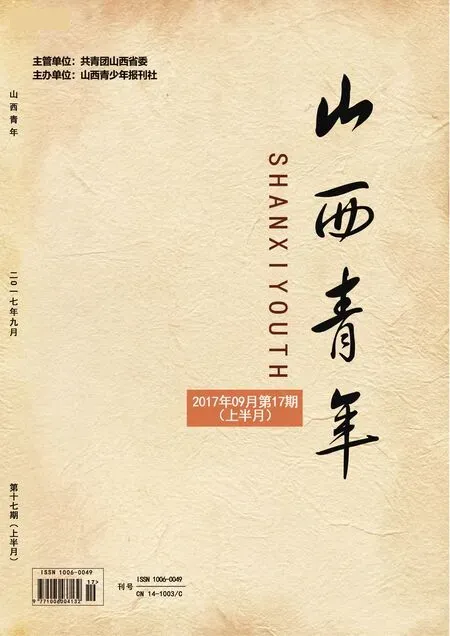自由之重与逃避之轻
——读《逃避自由》
李一苇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自由之重与逃避之轻
——读《逃避自由》
李一苇*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获得自由之后,人们开始逃避自由。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们之所以逃避自由,是为了逃避始发纽带断裂后个人出现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逃避机制可以分为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三种,而纳粹主义是逃避自由行为和后果的集中体现。笔者进一步总结,逃避成为一种经常性倾向,同人们对风险的恐惧有关。要想跳脱逃避自由的恶性循环,必须树立完整全面的人格,追求自发的积极自由。
逃避自由;弗洛姆;风险;逃避机制;积极自由
一、自由之惑:渴望与逃避
自由,一个熠熠生辉的词语,曾被摆在哲思的塔顶、众拥的山巅、革命的终点线。约翰·穆勒认为,自由是人类幸福的要素;萨特认为,自由是主体的选择,可以决定其本质。近百年来的历史无疑是走向自由的历史,多少人为争取自由而献身。“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等原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人渴望自由”①,然而一战过后新的制度登台亮相,竟产生了所有人都无法约束必须臣服的权威——法西斯和纳粹主义。
“我们被迫认识到数百万德国人那么如饥似渴地献出他们的自由,其热情不亚于当年为自由而斗争的他们的先辈们;他们非但不向往自由,反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另有数百万人则漠然置之,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捍卫自由而牺牲。我们还认识到民主危机不仅仅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普遍问题。”②
托克维尔早在十九世纪就已察觉,法国大革命陷入了一个怪圈。呼喊着民主,专注于平等,最终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放弃了自由。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相连,渴望臣服与贪求权力并现。尤其是面对法西斯主义的经验,犹太学者弗洛姆提出疑惑:除了天生的渴望自由,人类是否渴望一种天生的臣服感?
人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开始害怕自由的?中世纪没有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虽然不排除实际生活中具体的个人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主要产生在上层。宗教改革时期,尽管各教派都强调臣服于上帝以获取恩宠,然而加尔文的教义实际上具有一些隐含的作用。预定论宣扬信徒获救与否与现世的功德无关,任何人无能改变上帝预先设定的意图。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论,此种宣称为教徒带来了一种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的孤寂感。然而它带来的现实影响不止于此。
预定论的隐含义是不平等的,无共同责任的。这恰好与资本主义工业性格暗合。人们接受科层制的划分,各司其职;也意味着,风险自担。中产阶级由此产生焦虑和无力感,甚至有敌视和愤怒。现代人由此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人与上帝形成的个体化关系,是人的世俗活动个体化的一记心理准备。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选举,出版,集会,罢工……然而,自由非但没使得人类社会好转,情况恰好相反:人们越来越沦为政治选举、政治宣传甚至战争的工具。
表面上的自由不能掩饰内在的被控制。正如现代广告的态势——诱惑、恐吓、削弱。你以为自己是在看广告,实际上广告也在塑造你。政治选举更是如此:一堆口号,一场表演。政客们塑造着自己和对手,引导着选票。每个投票者表面上拥有神圣的权利,实际上身处其中显得微不足道。
人们对摆脱外在于自己的权力、不断获得更大的自由欣喜若狂,对内在的束缚、强迫和恐惧置若罔闻。他们向孤寂的内心投射自私、自恋,又或是寻找途径——逃避自由。
二、自由的模棱两可
人自出生,便需要适应。弗洛姆区分了静态适应和动态适应。静态适应指对既定模式的适应,比如在中国用筷子,到西方用刀叉;动态适应则指产生新东西、引发新冲动和焦虑的适应,比如孩子惧怕严厉的父亲,将自己的情绪压抑起来。
人之所以要学会适应,是因为有需求。不仅有生物化的需求,也有为避免孤独而产生的社会化需求。人类从原始部落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只要人群聚集,便有管理、分层、惩罚。从众心理因惩罚而生。
原始社会,对抗部落的违逆者很容易就被处死;封建社会,即使是朝堂高位的官员,若想发表自己的政见,依然需要拉帮结派,如此才敢发声谏言;现代社会虽然人们逐渐变得个性化,社会更加宽容,然而某些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依然是人类行为的牵引。比如今日中国,性别二元理论仍然占主流。如果一个生理性别为男性、心理性别认同却为女性的人进了女厕所,不仅会被当成变态,还要承受道德和法律压力。即使是极具影响力的个人、自媒体,在工作中也需要团队合作。合作意味着适应,只有与他人发生友好的联系,才能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
弗洛姆认为,人出生之始是拥有始发纽带的。胎儿与母体相连,从一出生被剪断脐带,生理上与母亲分离,但心理上的纽带还会延续到童年时期。虽然与母亲是两个分离的生物实体,功能上仍与母亲一体。比如孩子受到母亲的照料,且并不能独立做成某些事情。然而,儿童在成长期将逐步实现个体化和自我定位,逐渐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但并不完全排斥父母的权威。及至孩子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自己独立体验外部世界,便认识到父母也与其他实体一样,与自己有别。尤其是青春期的少年,一方面想要探索自己的世界,拥有独特的想法和秘密,排斥他人的管教;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时为付出的代价感到恐惧、后悔和软弱。换句话说,自我力量的增长、自由的增多恰好也意味着孤独的日益加深。“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一旦成为一个个人,他就形只影单,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③
自由,便是这般模棱两可。带走束缚,带来焦虑;带走安全感,带来新世界。为了避免这种始发纽带断裂带来的孤独感,有的人选择放弃个性,还有的人选择爱与劳动,与自然产生自发联系。说得有点悬,意思其实也就是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与世界建立新型的关系,继续维持纽带。后者是弗洛姆认为合理的途径,而前一种,则是所谓的“逃避自由”。
三、逃避机制的恶性循环
弗洛姆探讨了三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权威主义,破坏欲,机械趋同。
权威主义通过除掉自我获取安全感。在自由中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的个体寻找权威,可以建立新的继发纽带,找到自己的行为方式。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渴求权力者与寻求权威者之间有一种“施虐—受虐”关系,渴求权力是施虐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受虐是追求权威者的心理倾向——在某些关系下,安全感、软弱感和被奴役的感觉是并生的。
破坏欲则在于消灭令自己不适的对象。伺机而发的破坏欲为了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感,除掉所有与之相比使个人显得弱小的对象。这是一种与焦虑的抗衡手段,与个人生命的受阻程度成比例,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正因如此,中产阶级以道德尊严作为幌子,表达自己的敌视,以理性化的方式强烈嫉妒那些能够享受生活的人。这是宗教改革的遗留,也是纳粹兴起的原因之一。纳粹主义迎合了这些人的破坏冲动,利用他们反对纳粹的敌人。
机械趋同的机制下,人们往往以为是自己在判断,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思想可能只是环境的产物,或是被灌输的。仿佛赫胥黎描写的美丽新世界——人们在一种不自知的情况下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思想,并不是属于个人的真实思想,是伪思想,还有伪愿望、伪感觉、伪活动——甚至伪自我。机械趋同使人失去了真实的感觉,加剧了不安和无助感。
逃避机制的恶性循环在于,想要逃避因自由带来的焦虑,却使自身陷入另一种控制,永存无力感之中。纳粹主义是逃避自由的实践。渴望征服的权威主义性格造就了施虐—受虐的土壤,散布给同样性格结构的人,并加诸政治实践。人们受到鼓舞,开始仇恨,爱有权者,恨无权者。战争过后的反思又使人发觉权威的荒诞,这同样加深了心理上的不安和惊惶。
四、逃避之轻:自由以外
我想人们所逃避的不仅是自由。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字眼:选择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逃避扩展到方方面面——逃避选择,逃避交际,逃避责任。“逃避自由”说法的另一个重点所在,无疑是“逃避”。
依照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无处不在。个体化伴随着风险的增大。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像传统社会一人出事家族扛。团体对个人的责任减少,同时为个人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既有社会形式解体,新的社会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个体,个人无法拒绝个体化的强迫性,必然接受这种为自己而活、风险自负的生活。决策具有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不得不承受个体化所带来的风险,这就导致了规避风险的逃避策略的产生。
逃避自由,归根结底是逃避自由带来的风险。风险的类别很多,自由带来的是行为和心理上的风险。正如如不以法律对谋杀进行惩治,不仅会导致治安的败坏,或许也会导致良知的泯灭。再如父母放手让子女独立制定关于其未来的决定,一方面可以使子女依照自己的想法实现梦想,但另一方面,子女可能为无法实现其理想目标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都由其一人承担。由此可见,自由附加了风险。
尽管屈从权威依然有风险,但风险可能在名面上会被转移。法西斯靠民选上台,然而二战之后纳粹主义恶行由纳粹党负责——民众的责任无法追究,加以反思便罢。细想之,风险完全被转移了吗?其实并没有。亲手将希特勒送上台的部分民众可能一生都在反思,是什么使自己心灵的独立丧失。犹如前段讲到,即使孩子的人生计划听从父母安排,他还是只能自己承受安排带来的风险——即便对选择不满时有人可以埋怨,然而自我内心的想法终究是无可逃避的。
因而逃避的其他情形也没有丝毫意义。弗洛姆谈论爱的艺术的观点似乎在此处可以借鉴——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勇敢理智而富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具有爱的能力。同样,逃避自由、逃避风险只是一时的宽慰,而一个独立的人格应当向自己负责,不能因为逃避而蒙蔽自己的双眼。
五、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弗洛姆认为,获得自由不逃避的路径是建立积极自由。“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④
积极自由之所以不同于会带来孤独和焦虑的消极自由,因为其源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自我的实现不仅要靠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和积极表达其情感与理性的潜能来完成。”消极自由是因为强制、因为外界暗示而拥有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自发的、自我的活动,具有创造性,能在人的情感、理性、感觉精力记忆之中起作用。
积极自由的内涵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拥有积极自由的人能够预期和把握自身行动的风险,所作所为出于自我情愿的考量,不听信或盲从,更不推卸或责怪。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是谓积极自由。
弗洛姆对自由的探讨还有别的重要意义——警示被奴役的轻易和不自知。正是因为历史惊人地相似,极权主义不断上演,人们才更加需要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关照自身也关照整个社会。我们既反对1984,也惧怕美丽新世界。无论处于圆形监狱的监视,或是娱乐至死的削弱,都是对自我的侵蚀。弗洛姆提到民主政体的必需,也是出于保全完整自我的愿望。
没有自由,却渴望自由;有了自由,却逃避自由,害怕自由,忽视自由。有时,是因为没有看到无形的监狱,被权力支配而不自知;还有的时候,是以为自己渴望更多自由,殊不知,我们常常比自己想象中更自由。怪罪于他人,迁怒于社会,实则是自己不能完全利用自由的手段,或是不愿为自由的后果买单。
我们去想象自由,并不是从空泛的幻想中去想象。从理想中描摹现实更加真实。而社会倘若建立起安全的规则和制度,能够鼓励人们更加勇敢地利用已有的自由,追求更宽泛与合理的自由。安全的规则与制度会降低意外的风险;若为自由付出代价,也不会使追寻者再无立足之地。弗洛姆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更加强调个体的心理因素。虽然很难提出具体的建议,他的意思却是明白的:“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的信念,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⑤
[ 注 释 ]
①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7.
②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8.
③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23.
④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62.
⑤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86.
[1]弗罗姆,刘林海.社会学.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2]弗洛姆,李健鸣.爱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李一苇(199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性别社会学。
D
A
1006-0049-(2017)17-005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