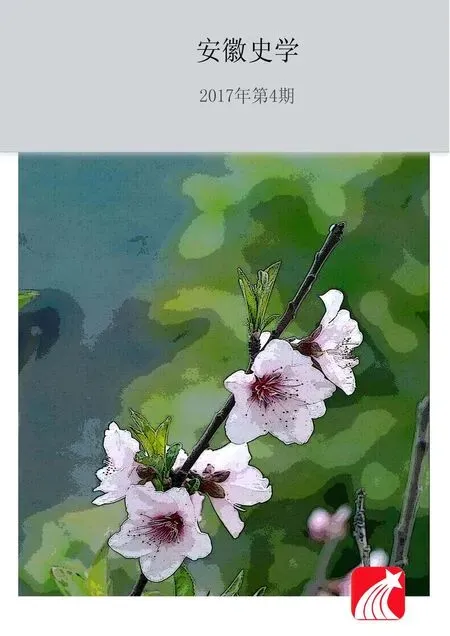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董根明
(安庆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安庆 246133)
·桐城派研究·
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董根明
(安庆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安庆 246133)
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所知录》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专著,其他著述所涉史事和史论亦多,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其“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在明“遗民”阶层和清初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
钱澄之;史学思想;《所知录》;明末清初
钱澄之(1612—1693年),字饮光,初名秉镫,晚号田间,安徽桐城人,明崇祯朝诸生,复社成员,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钱氏曾任南明隆武朝延平府推官,永历朝礼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管制诰,后一度削发为僧,隐居乡里,终身不仕清廷。钱澄之以藏山园、藏山阁为斋号,以斟雉堂为家刻堂号,所著《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所知录》等均由斟雉堂家刻而流传至今。斟雉堂刻本校勘审,印制精,为当时名版,是桐城历时最久的家刻堂号。钱澄之乃桐城派的先导人物,有学者认为钱澄之“当为‘桐城派’之祖”*吴孟复认为:“事实上,桐城民间至今尚以方、戴并称为‘桐城派’;就我们看来,不仅戴名世,钱澄之亦当为‘桐城派’之祖。”参见《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学术界一般称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派三祖”,或将戴名世并列其中,称“桐城派四祖”。。学界对钱澄之的易学、诗学和文学成就关注较多。近些年来对其史学成就亦有所关注,较为深入的研究,如诸伟奇全面论述了《所知录》的史料价值,认为“载述南明隆武元年至永历五年之史事,皆其身历目睹,为南明重要史籍”*诸伟奇:《钱澄之的〈所知录〉》,《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陶有浩认为钱澄之“以其易学思想为指导原则来解决当时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陶有浩:《论钱澄之史学观的易学思想特色》,《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上述成果为系统研究钱澄之的史学思想打开了门径,亦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本文不揣浅陋,尝试以桐城派乡贤的视角,从史著原则、史学批评思想、史料观、史学视野和史学经世等方面系统论述钱澄之的史学思想,以期抛砖引玉。
一、“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
明清换代之际,野史、家传迭出。清廷入主中原后,对南明历史讳莫如深。钱澄之认为史事关涉万代千秋,直书不足则信史难成,史籍所载必须真实。他以秉笔直书的史家胆识,指出“夫史,善恶毕书”*钱澄之:《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田间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75页。,“‘修词立其诚。’世未有不诚而其事足传,亦未有不诚而其言能传其事者。”*钱澄之:《争光集序》,《田间文集》,第215页。“诚”是修史的基础和前提。在编年体史著《所知录》中,钱澄之以其对明王朝的忠贞和身历目睹,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隆武朝的建立、李自成余部的归并、何腾蛟的协调众方、郑芝龙的擅权误国、黄道周的慷慨就义、隆武帝的败亡、绍武朝的短促兴亡、永历朝的建立等。
《所知录》所记为南明隆武元年至永历五年(1645—1651年)的史事,在时间上前后不到七年,其间政权更迭,事件纷纭,正是南明史上极为动荡、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诚如诸伟奇在整理《所知录》时的说明:“钱澄之对这段历史的撰写,所怀情感极为浓烈,而作为史书的载述却平实严谨,比较客观。”*诸伟奇:《钱澄之的〈所知录〉》,《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在《复陆翼王书》中,钱澄之坦言:“足下称仆《所知录》文直事核,仆何敢当?然此二字,固仆平生自矢。以《所知录》为名,明其不知者多,然犹恐知之未悉也。此事甚大,何时与足下抵掌深论,各出其所知以互相质证乎?仆年过七十,一日尚存,未敢一日忘此志,如何如何?”*钱澄之:《复陆翼王书》,《田间文集》,第85页。“文直”,即持论公正不偏;“事核”,即所载之事坚实可靠。班固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77页。钱澄之推崇司马迁,“文直”“事核”成为其著史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所知录》所载史事的真实性,当时人即有很高的评誉。清初浙东史学的开山鼻祖黄宗羲就对《所知录》评价极高:“桑海之交,纪事之书杂出,或传闻之误,或爱憎之口,多非事实。以余所见,惟《传信录》《所知录》《劫灰录》,庶几与邓光薦之《填海录》,可考信不诬。”*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钱澄之对史著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之所以将这部编年史命名为“所知录”,一方面是因为其所载史事“皆得诸闻者也”,亦或“略有见闻,随即记录”,而“间有传闻,不敢深以为信,亦不敢记也”*钱澄之:《所知录·凡例》,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页。;另一方面,“其不知者多”,所知有限,遂名“所知录”。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可以越来越贴近历史真实,但这种认识毕竟是有限的,任何史著所记录的历史也只能是曾经发生的客观历史的一部分。“所知录”三个字不仅反映了钱澄之严谨的史家作风,也表达了其对于历史有限性的认识。与同时代的史学家相比,钱氏的这一认识殊为可贵。
就明史研究而言,所缺史料恰是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而遭毁版最多的以南明年号纪元的史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宗侗认为:“明代史事最缺乏记载者,莫过于南明,所存史料局部为清朝所毁,且当时党争余波未息,记载亦常有各自一说,真伪难辨,使研究者难于选择者。故至今提倡研究南明史者虽多,而能完成有系统之南明史者尚未有,此亦今人之极宜补救者。”*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田间言是录所记较诸野史为确,洵然,其议论亦多平允,与袁特立、刘客生、金道隐皆为交契,而叙五虎事颇无恕辞,可知其持论之公矣。”*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下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条,《越缦堂日记》第7册,北京浙江公会影印本1920版,第16页。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为《所知录》所写“按语”中称:“饮光身历目睹,为记隆武、永历两朝最直接之资料,堪备南明史事之征。”*谢国帧:《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一些涉及南明的史书,如孟森《明清史讲义》、钱海岳《南明史》,以及《剑桥中国南明史》等都将《所知录》列为权威性征引书目。对《所知录》的不足,清末著名南明史料专家傅以礼在考证《所知录》相关史实后,“惜其中尚有失考者”,所举三例失误,属“习焉不察”,然“钱氏人品学术,久经论定,国史列之儒林,洵足当之无愧”*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523—524、523页。。由此可见,经“辗转传抄”而幸存之《所知录》,从某种程度上确实补救了南明史料之不足,体现了其所倡导的“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
对于《所知录》“寓史于诗”的史著表达方式,钱澄之在“凡例”中是这样解释的:“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摅,每有记事,必系以诗。或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不得不存也。”*钱澄之:《所知录·凡例》,第2—3页。钱氏寓史于诗,有学者不理解,甚至认为有违史体。傅以礼道出了钱氏不便言说的意图:“至注中分系诗篇,人亦疑有乖史体,故传本每多删削者,不知钱氏本擅词章,所附各什,尤有关系。只以身丁改步,恐涉嫌讳,未便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咏歌,著补纪所未备。观例言所称或无纪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稿转详等语,即知其苦心所在,乌得以寻常史例绳之。”*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523—524、523页。钱澄之曾自称:“予与何子,皆异时史之所必佚者也,何子之咏史,或心伤之矣。”*⑩钱澄之:《何紫屏咏史诗序》,《田间文集》,第258、257—258页。汤华泉认为,钱氏自编的《藏山阁诗存》十四卷“依时序编排”,“皆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正起到年谱和诗史的作用”*汤华泉:《整理说明》,钱澄之:《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4页。。对于《所知录》所记史事之下多系以相关诗篇的史著特色和以诗载史的风格,钱仲联给予很高的评价:“秉镫诗擅长白描,兼有平淡、沉郁的风格,继承陶潜、杜甫的传统,在遗民诗人中,独树一帜。纪事之作,具有诗史价值。”*钱仲联:《评钱澄之》,钱澄之:《所知录》,第273页。由此可见,钱澄之“寓史于诗”的史著表达方式,不惟其诗人品格的真情流露,亦是特定时代思想政治空气使然。
二、“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


与家传相比,钱澄之认为郡县府志“以备史材”,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古者,列国皆有史,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皆其史也。自列国废为郡县,于是,史之权独领诸朝廷;而郡县以‘志’称,志以备史之采择也。故志详而史略,郡县有信志,而后朝廷有信史。”*钱澄之:《汉阳府志序》,《田间文集》,第237页。在他看来,“史”源于“志”,郡县有信志,而后朝廷有信史,“夫郡志犹国史也,异时朝廷纂修,往往取各郡志以为张本。史不可以不信,则志不信可乎?”郡县府志因其由众人参与撰写,而与家传不同,“惟是郡邑志非一家之私言,乡评难淆,庶几犹存公论之万一于此,而更不信焉,则史宁有一足据者乎?”有“信志”,才会有“信史”。钱澄之认为,史书所载,“善恶毕书,志则纪善而已,不直则纪不足信”,倘若“真者与伪者并列,后且以真者亦不足信矣。”*钱澄之:《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田间文集》,第74—75、75—77页。他认为:“夫郡之有志,以纪天时、地利、人事、物产之异宜,考户口、财货、赋役之消息,稽山川、城郭、官舍、庙祀之废兴,而其大者乃在于明政教之得失,识人物之盛衰,察风俗之升降,使上之人知所鉴戒,而下之人亦知所劝惩。由是言之,志非徒以备史材而已,抑风教之事焉。”*钱澄之:《汉阳府志序》,《田间文集》,第237页。然当今郡志所载,如《名宦》《乡贤传》和《节义传》等却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更有甚者,“今天下修郡邑志者,类取于学宫之诸生领其事,往往一二无籍者夤缘窜入其中,惟上是奉,惟势是趋,惟贿是求,黑白颠倒,致令真正节妇义士皆以与名其书为耻。”有的郡县府志则有违风教:“一大郡志书,不载一代奇伟之人、烈烈可传之事,徒取其小廉细绩、循资迁擢者以为名宦,取曲谨自好、致身显位者以为乡贤,而且皆不足信,今当事之谕令入志者,皆此辈也,亦何取夫志哉?”*钱澄之:《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田间文集》,第74—75、75—77页。在钱澄之看来,郡县府志虽非一家之私言,相对于家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对于那些惟上是奉、惟势是趋、惟贿是求、黑白颠倒、有违风教者参与撰写的郡县府志就不能纳入信史采纳的史料范畴。
关于野史,钱澄之认为“庶几野史犹有直道存焉。”“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诸传闻,既无情贿之弊,亦无恩怨之私,徒率其公直,无所忌讳,故其言当可信也。”但野史亦有存疑处,他认为写野史之人多为“草茅孤愤之士,见闻鲜浅,又不能深达事体,察其情伪,有闻悉纪,往往至于失实。集数家之言,大有径庭,则野史亦多不足信者。”*钱澄之:《明末忠烈纪实序》,《田间文集》,第212—213、213—214、213—214页。在钱澄之看来,野史记载由于剥离了官修史书的种种限制,无情贿之弊,无恩怨之私,自然是直道有余,但野史所载传闻多,而难以察其真伪,往往此书所记与彼书所载不一,虽可弥补国史材料之不全,但亦需存疑辨伪。
对于“所见所闻”的口述史料,钱澄之认为也要存疑和质证。钱澄之认为史家对史料的搜集宜尽可能广泛,除正史、家传、府志和野史外,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是非常难得的史料,即“遍询海内亲知灼见之士”,“所见所闻皆史料也”*钱澄之:《明末忠烈纪实序》,《田间文集》,第212—213、213—214、213—214页。。他认为“文献之不易得也”,而“博访四方亲知灼见士”“询诸遗老”*钱澄之:《争光集序》,《田间文集》,第215页。的口述史料就显得更加珍贵,即“盖文可垂久,而人难求旧,有献以补文之缺焉,且以证文之失焉,则献视文尤重。”*钱澄之:《黄莲生六十初度序》,《田间文集》,第343页。钱澄之认为通过“广求四方淹雅博通之士”*钱澄之:《赠都御史昆山徐公罢总宪监修明史序》,《田间文集》,第316页。口述的史料,虽可以补正史之缺漏,但也要“识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审之又审,然后据实以书”,“至有传闻异辞,事涉可疑者”,别为存疑,或附诸传后,以俟后人考订*钱澄之:《明末忠烈纪实序》,《田间文集》,第212—213、213—214、213—214页。。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代表了清初史学的最高成就,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被学界视为清代史学理论的巅峰之作。章氏对史料的理解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域,主张六经皆史,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章氏遗书》卷9,嘉业堂刊刻本1922年版。他将古代经典、地方志书、公文案牍、金石碑版、谚语歌谣和私家著述等均纳入史料范畴,遗憾的是却未明确提及口述史料的相关概念。“口述历史”的概念化并成为一种潮流虽然于20世纪30年代才形成,但“实际上,口述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它是第一种类型的历史。并且只是在相当晚近,处理口头证据的技能才不再是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譬如,司马迁对荆轲伤秦王所持否定的观点就源于他对当事人口述的补正:“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卷86《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78—3079页。钱澄之关于“文可垂久”而“人难求旧”“所见所闻皆史料”的史学思想,在清初史学界是仅见的。就口述史料而言,钱氏表现出了超越朋辈的史识和史学批评意识,对完善传统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钱澄之认为家传、府志、野史和口述回忆等资料虽具史料价值,但均不足深信,值得史家作进一步的考订和存疑。“若是,则古今书籍之所传,其可信者有几乎?”他认为惟有对史料的来源进行“质证”,对传言者的心术和人品进行“甄别”,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知人论世,才能成就一代信史。“夫欲信其书,必先信其言之所自来,与夫传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无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亲戚知交有意为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谅无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轻听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钱澄之为文推崇韩愈,然“昌黎不敢作史,即此见其慎重史事”*钱澄之:《明末忠烈纪实序》,《田间文集》,第213页。。钱氏提倡直笔,认为有史才、史德者,应该具有“宁受过于一时,不肯受过于万世;宁得罪于当时,不敢得罪于先贤”的勇气,“至于书成,或存或毁,惟当事是听,今则惟有认真而已。”*钱澄之:《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田间文集》,第77—78页。他推崇史官徐果亭,其《死难实纪》“广搜纪录,一无避忌”*钱澄之:《明末忠烈纪实序》,《田间文集》,第213页。。这就是说,史家不仅要有秉笔直书的勇气,还要有科学的考证方法和敢于存疑于后世的胸怀。钱澄之严谨的治史态度和考信不诬的史学批评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像戴名世这样具有史学情怀的桐城派作家,而且对清初史学界乃至乾嘉考据学产生影响。如被誉为桐城派集大成者、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虽反汉学,但不反对考证,而是熔义理、文章、考据于一炉。
三、“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
明中后期兴起的陆王心学企图通过整治人心来挽救社会危机,明王朝的崩塌使得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不得不反思和修正心学的空疏,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倡导经世致用。彭君华在《田间文集》“整理说明”中写道:“澄之少负奇气,有用世之志,故所言均有感而发,内容充实,不为空洞浮泛之论。”*彭君华:《整理说明》,钱澄之:《田间文集》,第1页。马其昶则称先生“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77页。钱澄之曾多次上书崇祯皇帝,纵论“兴学取士”和“保举用人”之道:“臣历考唐宋以来,国家致治皆以保举得人。”所谓“保举者,保其廉也,举其能也。”*钱澄之:《拟上保举用人书》,《田间文集》,第103—105页。他认为当下选才之弊在于“非进士,虽贤而才者,终不得大用,资格限之也。”其实,“以文取人,本属无用”,“资格益严,科目益重,而人才益少矣”。科举考试应该重“策论”,倘若“舍实学而尚浮辞,人才之弊,由此其极也”。当今之世,“时移事变”,祖制之法亦有难尽行者,欲广植人才,宜在各乡设小学,兴太学,“破格用人”,“革故鼎新”*钱澄之:《拟上兴学取士书》,《田间文集》,第94页。。诚如晚清学者萧穆所云:“其书疏、议论、书牍,皆论明季时政,杂文皆纪南渡时事,皆有关于文献。生平经世之略,亦可于此见矣。”*萧穆:《藏山阁集跋》,钱澄之:《藏山阁集》,第531页。

作为具有强烈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的思想家,钱澄之以史家的真知灼见和宏阔的史学视野评价和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从大处着眼评价历史人物,是钱澄之读史评议的一个显著特征。譬如在《蔺相如论》一文中,他指出“蔺相如,勇士也,其气可夺三军之众而凌万乘之主,以死殉节,不辱君命者也。若谓有功于国家,物不信也。”“赵以壁予秦,秦弗予赵城,曲在秦……秦王雄主,其不以壁故负不直之声,激诸侯之怒,而坚其合纵之约,明矣。”然蔺相如宁死不屈君命,故以壁归,“夫使其君无故而履至危,守者以之建功,从者以之显节,谋国者固如是耶?”钱澄之立论有独到见解,认为蔺相如呈匹夫之勇的行为足以祸赵,相反,“秦昭王能容相如,与齐桓公之容曹沫,其度量皆足以霸。”*钱澄之:《蔺相如论》,《田间文集》,第8—10页。其《陈涉论》写道:“太史公列陈涉为‘世家’,在汉功臣之前,徒以其首发难耳……夫胜自起蕲至陈,相去不数百里,遂自立为王,此岂有大志者哉?”钱澄之不人云亦云,认为“古今创业中兴之王,皆身经百战,冒矢石,蹈死亡,未有不躬履行间而能坐议庙堂以成功者也。”而陈涉“未尝见强秦一将,即称王”*钱澄之:《陈涉论》,《田间文集》,第13页。,乡里小人的“鸿鹄之志”,不可能成就帝王事业。在《三国论》中,钱澄之认为“世之论三国者,皆喜备而恶操,而恶权次之,此甚非平论也。夫世之恶操者,指操为奸雄、为汉贼。其指为汉贼者,谓其挟天子而令诸侯也。当董卓乱后,天下尺寸皆非汉有,操之天下,皆取诸强梁之手,非取诸汉也。操迎天子都许昌,奉为共主,存炎灰於既烬,本以为义也,而曰操挟天子。操百战以取天下,未尝以天子令号召天下而有之也;即号召之,当时谁奉天子令者?”他指出:“夫辅天子兴汉室之说,毋论权所不欲,即备亦岂真有心耶?是三人者,亦各自欲王耳。设使操当日不迎乘舆,委天子于群凶之手,汉之亡久矣。以垂亡之孱主,衣租食税数十年,得保首领以殁,操之罪,固未可与后世篡逆者同日语也。”*钱澄之:《三国论》,《田间文集》,第30—31页。钱氏所论言之成理,不守陈见,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并非标新立异。在《李纲论》中,钱澄之写道:“纲建炎初定巡幸之议,即迁都之计也……盖纲之论,于国家之大计则是,而于高宗之私衷则相左也。初,高宗为质,中道脱归,其志惟知逃死而已,父母妻子皆所不顾,而尚肯顾祖宗之疆土、中原之人心哉?”*钱澄之:《李纲论》,《田间文集》,第37—38页。钱氏据史直书,指斥苟安一隅的宋高宗,一针见血,淋漓痛快,毫无忌讳,表现出一代史家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生活在明清换代之际的钱澄之,以明遗民的身份自居。他特别推崇为人臣者的“气节”,以为此关乎“风教”。他以较长的历史时段分析和预测“忠臣”与“逆子”的处境及后世声名,可谓洞若观火:“忠于故王,守死不屈,而比之叛逆?古帝王于天下初附,未尝不录降者之功,而听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后,则必以死事者为忠臣,降者为失节,所以教忠也。”*钱澄之:《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田间文集》,第75页。钱澄之并非盲目推崇忠于故王的节义之士,而是用更加宏阔的历史视角,从大处着眼分析和看待臣子死节的行为。譬如子贡曾对管仲不死子纠予以责难,而钱氏则从管仲所系天下的高度予以肯定,“当是时,天下始知有周,群奉为共主,皆自桓公倡之,管仲之功也。而子贡辈区区以不死子纠之节责之,何其固哉!圣人亟称其功而略其节,以死节事关一身,而不死所系者在天下也。”*钱澄之:《管仲论二》,《田间文集》,第5页。作为桐城派的先导,钱澄之以易学变通观辩证地理解“遗民”坚守与“故主”失势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做出了合理的史学阐释,对清初明遗民阶层如何辩证地看待而今已经“逝去”了的旧朝辉煌给予了情感与理性层面的双重回应。钱澄之的这种史学阐释在清初“遗民”阶层和学术界中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戴名世从内心深处选择了忠于故主而最终获罪清廷的“气节”,还是方苞心系天下而从“南山集案”中汲取教训以仕清廷的“理性思考”,都能从钱氏这一思想中寻得渊源,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13BZS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郝红暖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Qian Cheng-zhi’s Historical Thoughts
DONG Gen-ming
(Library,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246133,China)
Qian Cheng-zhi has a lot of writings in his life,which known was a chronologic historical monographRecordsofWhatOneKnowsand others writings involved in the mostly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ies,that showing a great sense of history and a historical care.His historical thought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the principles of his historical works in “straight writing” and “earnest fact-checking”,history critical theories in “question-leaving” and “cross- examination”,history thought of the world in “past-manifesting” and “future-prospecting”,and wide historical view.These historical ideas had extensive social effects both on the adherents clas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academic fiel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manifested his pioneer contribution as a leader of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file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Qian Cheng-zhi;historical thoughts;RecordsofWhatOneKnows;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248;K249
A
1005-605X(2017)04-0125-06
董根明(1965- ),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