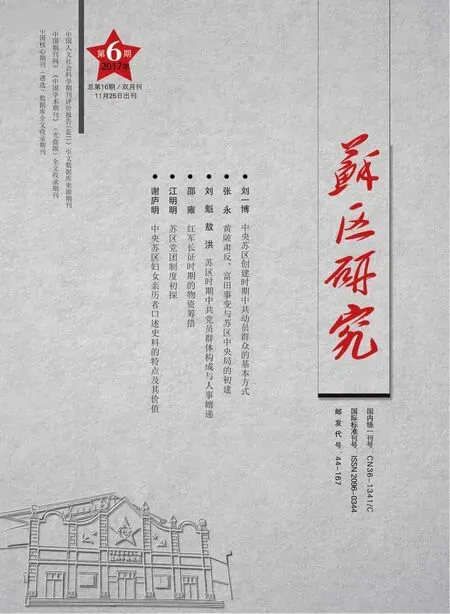红军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
红军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
邵雍
红军长征途中,自然环境恶劣,沿途地方军阀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围追堵截,局势万分险恶。这种大背景决定了红军必须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手段克服困难,解决军需问题。由于长征路过的地区的社会环境、军事环境千差万别,红军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筹措物资。在战争状态下,以缴获、没收居多,在部队休整状态下,多采用自备、购买、自产自采等方式,当然也有几种方式并存的情况。通过自备、缴获、没收、购买、自产自采等途径,红军筹得最低限度的物资,胜利完成了长征。红军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是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它对于支持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对于保持部队的顽强生命力、战斗力,维系部队钢铁般的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红军;长征;物资筹措
红军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多年了,相关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异彩纷呈,但是细化到某一专题,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偏重于政治路线、军事行动,对于后勤保障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已动更要保障后勤补给。某种意义上说,后勤补给直接关系到军队的胜败乃至存亡,应该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
一、自备
现有资料表明,红军在长征前做了一定的准备。早在1934年春国民党军逼近苏维埃国家银行金库所在地石城时,“博古等人采取非常措施,把苏维埃政府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袁征:《长征有无准备考辩》,汤应武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的陈云筹集了60万担粮食,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比原定期限提前一个月出色完成任务。*严爱云:《陈云与上海的深厚渊源》,《现代上海研究论丛》(13),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页。
1O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说:“政委与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供给、卫生部门工作的直接监督与检查,保证武器、弹药、衣服、行军锅、米袋、草鞋等物资材料的必要补充与适当的分配和调剂”;*《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对于分发部队的资材,必须有计划的注意到战士、运输员的衣服、被单、黄烟与打草鞋材料的适当分配与供给,并应注意食物的调剂”。*《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13页。但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了便于行军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得不抛弃大量辎重:“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精简行装,每人只带3天粮食,两三双草鞋”。*《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长途行军加上战斗频繁,物资消耗极快,筹集物资就成了燃眉之急。
在出发长征前,红军是有革命根据地依托的,因此借助当地的党政群团的协助,有目的地进行自筹自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凭借着各革命根据地的资源,红军在长征出发前的自筹自备工作成效显著,对于支撑战略转移的初期作战起到了较大的保障作用。
二、缴获
在长征中经过不断的战斗,红军缴获了大量敌军物资,并对破损武器加以维修,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这是红军武器弹药得以补充的主要来源。“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装备不良而且数量少,使得红军对物资十分珍视,“为了节省弹药,红军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王树增:《长征》,第168页。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旋即占领广东仁化以北的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赤军夺去。”*《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1934年12月由湖南转入贵州后,红军连战皆捷,力克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贵州军阀侯之担两个师被击败后,“大部枪弹多被赤军缴去,赤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59页。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后,打退了来犯之敌,红一军团一直追到乌江边,毙伤2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4月27日,红军在由云南曲靖向马龙的进军途中截获敌军汽车,“缴获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土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方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参见《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68页。后来中央红军伪装国民党中央军来到云南嵩明城及官渡时,当地军政官员“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伕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红军遂将一切军需及伕役照单全收。*《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68页。当红军前卫伪装国民党中央军行抵四川石棉县开罗场时,刘文辉在当地军粮站人员也“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赤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赤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79页。红三军团四师十团二营刚走出草地时主动出击,打败马步芳一个骑兵连,旋宰割死伤马匹,烧火烤肉,有的战士吃了足有二三斤。*《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9月18日红军到达哈达铺,缴获了国民党部队溃逃时留下的几百担大米和白面。*《罗荣桓传》,第130页。10月7日陕甘支队过六盘山后在青石嘴消灭东北军骑兵两个连,缴获了100多匹战马。红军以这些黑马、红马、白马为基础建立了骑兵侦察连,在以后的直罗镇战役中发挥了作用。*《聂荣臻传》,第144页。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横扫滇西,接连攻克楚雄、镇南、祥云、宾川、盐兴、牟定、姚安、盐丰、鹤庆等县城,缴获颇多,得到了充足的给养,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那些天里连有名的云南火腿都吃腻了。*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8月31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在包座之战中大败敌军,“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牛羊”。*《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25页。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在甘南战役中从毛炳文的部队中缴获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总指挥贺龙根据卫生部长侯友成开具的清单,很快给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分别送来了麻醉药品、缝合针线、止血钳、洗伤口的双氧水”,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部门的急需。*《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各路红军走上漫漫长征路之后,遭到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只有通过战斗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在作战时期,军需物资消耗加快加大,这时缴获成为红军补给的主要方式。在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之后,大量的快速的缴获及时、有效地为红军提供了最主要的补给,保障了各路红军长征铁流滚滚向前。
三、没收
根据红军的纪律,一切缴获归公,然后由上级机关分发。长征沿途打土豪没收的财产也是如此处理,除了留下一部分解决部队的给养,另一部分则无偿分给当地群众,赢得群众的支持与帮助。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湖南后打土豪,搞来一匹大骡子,分给了红八军团党代表刘少奇,刘少奇就把自己的一匹黄马送给了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打土豪时,将一件小花旗袍分给某部李指导员。1936年7月李指导员负伤就医后,又将这件旗袍送给了救护他的方面军总医院一排二班护士宋林。*宋林:《红军女护士》,《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红一方面军渡过乌江后,进入黔北的红一军团担负了夺取遵义等城市的任务。1935年1月5日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发出《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明确“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复调查,并且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提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1935年1月5日),《黔山红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红军占领遵义后,“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赤军截获没收。”*《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62页。4月下旬,红九军团攻克滇东名城宣威,休整三天,没收了官僚经营的火腿公司的财物,获得了包括火腿在内的大量物资供应。*郭天民:《从乌江到泸沽》,《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指出:“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还没有大的中心城市,……而我们行动的地区,又是物产比较不丰富、经济比较落后的黔山一带,战争经费与物质资材,是不无困难的”,“更需要我们大力注意,运用群众路线来进行筹款,征集资材的工作。……从前各级没收委员会的组织,均行取消,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立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的工作(团政治处则由地方工作组中指出一个干事为没收征发干事)。……对于商店的没收必须经过团政治处或师政治部的批准。”“打土豪……事前应在群众中调查该土豪的家产,发动群众参加,纠正个别部队中只顾找吃的东西,不注意捉土豪,搜查房间及挖地窖等工作”。“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直接的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1935年2月20日),《黔山红迹》,第275页。6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就关于筹粮、节食、带粮问题致电各军团首长:“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部队应尽一切可能,并派遣部队在规定地区没收、征发及购买一切麦子、包谷、杂粮、盐、油及牛羊猪等食物,统限22日将结果电告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筹粮、节食、带粮问题致各军团电》(1935年6月20日),《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236页。
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经常在部队宿营休息时,不顾疲劳,进行村庄调查分析,“心中有了底数,再向群众核实。”这样打土豪又快又准。女战士们将从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现金、肉类、盐巴全数交给总后勤部供给部长杨立三等人,其他东西则当场分给群众。然后,将没收的全部浮财开个清单,留在土豪家,落款注明“红军某部工作队调查组”,以免土豪回来迫害老百姓。”*李坚真:《融冰化雪步不停》,《星火燎原丛书之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9月,中央红军在哈达铺以东二十多里的理川镇截获了地方军阀鲁大昌的运输队,“缴了大批的布匹和棉花”,首长决定“把这些布和棉花分给大家,为干部战士棉衣……解决了御寒问题。”*徐国珍:《长征路上筹粮》,《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占领西兰大道沿线先后,中央红军又“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衣服、鞋帽给毛炳文军的轻重汽车十余辆。”*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三军大会师》,第197页。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共打击土豪七百多家,将没收的粮食、盐巴、银元等分给群众,其中包括设在黔西鸭池沟附近的四川省盐务局的存盐十万斤。*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342页。同年7月,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在从甘孜到阿坝的行军途中率部筹粮六天,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在大土司家里“挖出了土司埋的三万多斤粮食”。筹粮队“每人都背着五六十斤粮食”。大家把筹来的万多斤粮食装好、扎紧,整整齐齐地放在路边的干土坡上,留给红二方面军的后续部队。*刘良栋:《罗炳辉军长筹粮》,《星火燎原·未刊稿》第3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8页。同年中秋时节二方面军跨出草地,进入甘肃的徽、成、两当、康县地区休整,红军将“地富家里屯积的多余粮全部没收。没收的粮食大部分作为军需,少部分以军队名义还了初到时借吃的债务。”*严汉万:《陇上江南喜迎春》,《三军大会师》,第252页。
但打土豪有一定的困难。红军筹粮困难极大,原因是:一是时间紧张。莫文骅将军回忆说,长征中的吃饭问题是个大难题。“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购买。每天快天黑才到宿营地,即埋锅做饭,吃掉带来的粮食,如不立即筹措,第二天就没吃的了,为了筹粮常常要付出很大的力气。”*《莫文骅回忆录》,第259页。二是会遭到武装反抗。“地主、恶霸都有马有枪。他们把粮食放在寨子里,把牛羊进深山。你要粮,他就守住寨子和你硬拼。有的连队,打了几天,每个人还没有打到三五斤粮食”。*熊友刚:《让粮》,《星火燎原·未刊稿》第3集,第203页。第三,有的地方没有土豪可打。进入民族地区后,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又规定有些土豪不让打。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说,“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1)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2)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141页。同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静宁县回民群众聚居的兴隆镇。该军制订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同样明确规定“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9月中旬陕甘支队从俄界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罗荣桓传》,第131页。
可见,没收这种方式主要用在红军休整时期,前提是红军在军事上有效地控制了一定的区域。这种方式的有效程度取决于红军实际控制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城镇,收效明显,反之,在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乡村收效甚微。
四、购买
中央红军长征时带上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金库所存的金银财宝,还沿途通过打土豪等其他渠道不停地筹款。每当战事不紧部队停下稍作休整时,供给部门总是尽可能组织力量在途经的较大集镇或商业区整批购买部队需要的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药品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为了顺利通过豫西北泌阳县城附近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地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购买”,从而减少了阻拦,赢得了时间。*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星火燎原丛书之二》,第236页。同年末,红一方面军途经黔东南黎平、黄平、镇远等府城时,“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55页。1935年4月初,红九军团攻克黔西北重镇瓢儿井后,也“筹款三千余元,做了八百多套单衣”。*郭天民:《从乌江到泸沽》,《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第78页。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张贴出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5年5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6月25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发出《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指示:“为着争取群众与发动群众帮助红军购买粮食,各政治部、处必须立即教育给养人员及粮食征收人员:(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丁)先头部队政治机关,应责成粮食征收人员每到一地,即找当地革命政府或群众共同商妥各项粮食的价格,共同布告群众及部队周知。(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总政治部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1935年6月25日),《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240页。
1935年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某部来到产粮区毛儿盖附近的沙锅时,麦子已经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总政治部做了统一而严格的规定,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只有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的情况下,才能收割群众的麦子,而在这样做时,必须将所割麦子的原因、数量,用墨笔写在木板上,插在田中,告知群众回来以此木牌向红军领取款项。”*《莫文骅回忆录》,第288页;又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这样战士们饱受饥饿煎熬的状况才有所改变。8月,红一方面军前卫部队某部九连到达毛儿盖一带,饿得难以支撑,就地“摘些苞米叶子和辣椒叶子煮一煮充饥”。一藏族老大娘看到红军并没有吃她家的苞米后立刻跑回家,端来了一盆煮熟的苞米粒,“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苞米粒,给了大娘三块大洋”。*李湘涛:《筹粮过草地》,《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第135页。经过认真细致的群众工作,中央红军离开毛儿盖时情况大不同了,藏民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红军,“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莫文骅回忆录》,第83页。在川西北阿坝地区,藏、羌等族民众曾为途经的数万红军提供大批军粮,仅仅牛羊就有20万头。1938年毛泽东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这一问题时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第159页。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筹集了大批粮食,主要是用银元买的,同时,还从商人和群众那里买到了盐巴、药品和部队需要的东西。”*徐国珍:《长征路上筹粮》,《三军大会师》,第175页。
1936年5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滇西北的中甸县城,经贺龙向当地归化寺活佛言明,请他们帮助操办的军用粮袜“决照价付金钱”。短短两天,在归化寺的帮助下共收购了商人、富户青稞麦3万余斤。*《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同年,红二军团长征过四川德荣县时,在喇嘛寺征集大量大米、白面、青稞、糌粑时,由于藏族喇嘛们听信反动宣传跑光了,关向应政委只好留下粮食清单、致谢信与许多白洋,并对向导说:“如果我们给的钱不够,还可以拿着我们的信向后续部队要。”*颜金生:《艰难的时刻》,《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第270页。
在购买物品时,红军十分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尽量使用在国统区流通的货币,以免在国统区不能流通的苏维埃货币造成对群众利益的侵害。红军每到一处都会设立临时兑换处,专门兑换已流通到居民手中的苏维埃货币,代之以金、银、铜等财物。“红军的采购人员使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王树增:《长征》,第118页。这使群众无后顾之忧,愿意卖东西给红军,更赢得了民心。红一方面军进入湘南大镇延寿圩、宜章城时,“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50页。在贵州遵义“苏维埃票按日均兑现”,商店照常营业。*《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62页。在云南嵩明城与官渡,红军也是“买卖公平,钞票兑现”。*《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68页。
但是平价购买亦非易事。首先,红军初到一地,由于群众不了解,往往一开始不会配合红军的购粮工作。如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进入藏区后,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藏匿起来,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叶剑英率红三军团教导营带头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感动了许多藏民。他们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女战士经常饿着肚子,翻山越岭去筹粮。“天都已经快黑了,可村民们躲进了大山里,粮食还没有筹到。于是,谢飞、钟月林、吴富莲、刘彩香等几个女人点起火把,走进深山去找群众。接连翻了两座山,就是见不到一个人影……当她们气喘吁吁地爬上第三座大山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个老乡。通过做工作,这位老乡帮助她们找到了躲藏在其它山岭的村民。干部休养连的晚饭解决了,可这些女人们却累得没有了吃饭的欲望,只想倒在地上长睡不起了”。*刘丽丽:《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在实在找不到群众时,红军只好采取“留钱(牌)购物”的特殊方式,即红军直接取走已收获的粮食或长在地里的庄稼,留下钱款或借条表示歉意并保证将来归还。其次,即使有钱,要买些东西也不容易。红三军团某连进入广西后,粮食供应困难,炊事班的战士们“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谢方祠:《九个炊事员》,《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第154页。红一方面军进入大苗山地区后,“这一带苗族同胞都跑进了深山,找不到群众”,买不到粮食。*《罗荣桓传》,第121页。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天寒地冻,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贺龙传》,第190页。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高原后,人烟稀少,物产匮乏,藏民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相对于没收而言,购买是一种更普遍、更通行的方式。无论是平时休整还是行军路过,各路红军都需要通过购买来及时补充给养。另一方面,购买也维护了普通百姓、中小商人的利益,有助于建立红军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
五、自产自采
为了缓解红军物资短缺的紧张状况,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必要时自己动手,解决军需。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用来强渡嘉陵江的上百只木船是工兵营会同大批的木匠、铁匠、船工充分利用从各地运来的木料、门板、碎铁、破布等赶造出来的。*参见《徐向前传》,第205页。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第一连承担被服生产任务,生产衣帽鞋袜装备部队。长征途中,该连与原本执行兵站运输任务的第二连在中窝坝地方共同承担就地取材纺毛线织布的生产任务。连续工作两个月,把当地的羊毛全部做羊毛衣,供广大战士爬雪山过草地之用。*王泽南:《妇女运输连》,《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0页。妇女团的战士们还自己动手打草鞋。*赵兰:《妇女团生活片段》,《星火燎原全集》第3卷,第314页。1936年5月部队在康北甘孜、炉霍休整期间,朱德总司令号召战士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帽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杨以山:《永不泯灭的记忆——回忆朱总司令过草地的几件事》,《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7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会师时,送给对方自制的毛衣毛袜数千件。*参见《任弼时传》,第358页。
1936年夏三军会师前,红一方面军一军团随营学校二连要求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每人缝两套衣服送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表示慰劳。于是战士们自己剪裁、拿棉花搓线,用下发的布、棉花学习缝制衣服。到7月中旬,全连每人两套衣服都缝好了。这时天气已经开始冷了,全连又领受了新任务——每个同志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打八双手套或袜子。*杜秀章:《为二、四方面军战友缝衣服》,《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8月间,红一方面军打下盐池县后,部队进行休整,发动战士们打毛衣,准备送给即将前来会师的二、四方面军指战员。一个班分到七八十斤羊毛,先进行煮洗、晒干后设法弹松,捻成毛线,再进行编织。部队行军时,“每个同志除了背枪,还背着几大团毛线,口袋里装得胀鼓鼓的也是毛线,腰里还别着打毛线的针,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打毛线。”到达兴仁堡的时候,有的战士已打好了五双袜子、五双手套和一条短裤;有的同志还打了毛衣,毛衣上面还用驼毛绣着“欢迎阶级兄弟”等字样。*刘强:《织羊毛的故事》,《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第300页。10月打拉池会师时红一方面军送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的毛衣、手套和袜子都是利用打下盐池时缴获的羊毛自己纺、织的。*刘强:《礼物》,《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461-462页。
除了穿的,吃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自己解决。红一军团3师2团在毛儿盖休整时,奉命在东南菠萝子一带筹办粮食,“队伍成连成营的出去挖野菜,釆豌豆苗,……那时所谓粮食,实际是指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青稞麦”。*江拥辉:《艰苦筹粮》,《星火燎原·未刊稿》第3集,第201页。青稞到手后还需自己炒麦磨面做成干粮。1935年8月下旬,红三军团四师十团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时,“每人只带了一小口袋炒青稞麦。一路上大家边走边摘野菜,到了宿营地,在篝火上用搪瓷缸子把水烧开,放一把麦粒,再放一点野菜,调一调,就是一餐。越走到后来,搪瓷缸子里的麦粒越少,终于只剩下野菜了。”*《罗荣桓传》,第125页。前敌总指挥徐向前“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徐向前传》,第222页。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发生断粮,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在草地上寻找能充饥的野菜来当军粮,从此那一带的野菜是我们唯一的吃粮了。……因没有粮食吃,有好多可爱的大马被杀掉充作粮食”。*段文廷:《难忘的军粮》,《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第216-217页。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过草地时“真正的粮食早就没有见到了,连野菜干也吃光了。”*颜文斌:《一碗炒面》,《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第219页。总指挥贺龙亲自去草地的小河边“钓鱼给大家吃,还组织一些人去为部队钓鱼充饥。”*《贺龙传》,第204页。朱德总司令听说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特意钓了鱼熬汤,给没有粮吃的产妇补点营养。*参见《任弼时传》,第204页。
1935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的战士们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前夕,十分缺盐,根据当地老乡提示,她们上白云山找到了一种带咸味的石头,纷纷挥锤敲打。当晚全队以班为单位,通宵未睡,生火熬盐,熬出了好多雪白雪白的盐。当事人回忆说:“接连几天,我们白天上山敲石头,夜晚生火熬盐,一钵钵的白盐,全部集中起来,准备送给中央红军。”*孟瑜:《熬盐迎亲人》,《星火燎原·未刊稿》第3集,第153页。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炉霍短期休整,当时部队缺少粮食,生活困难,很多同志因长期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六月初的一天,朱总司令叫警卫员小胡买来了菜籽,又从老乡那里借来了一张木犁,套上一头骡子,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亲自扶犁耕了起来。”总司令亲自带头种菜,带动了方面军总部警卫通信营全营同志都动手种菜。24日该营奉命开拔时又把菜地移交,将绿油油的青菜留给后续部队的同志吃。*侯正果:《总司令种菜》,《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第32页。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离开道孚后一直都在山林小道间行军。这时医院药品已近枯竭,连退烧药都没有。于是有人提议用凉性草叶贴疮口退烧,发动护士到野地里采摘各种宽叶子,采回后由伤员们辨认识别,分类(车前草、薄荷叶、蛤蟆叶等),再由护士“把叶子洗干净,一片片用针线穿成串,然后吊在筷子上,挂在锅里蒸。”然后“把阴干的草叶,一张张地给伤员贴上。”于是炉霍的田野成了红军的药品供应库,短短半个多月中,由于草叶疗效显著,“轻伤员都能拄着树枝走动了。”*宋林:《红军女护士》,《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第120页。长征途中女战士们在药品紧缺的时候,会不顾危险,到深山野林里去采草药来缓解伤病员们的痛苦。*陈颜秀:《长征路上的女红军》,《星火燎原丛书之五》,第261页。
必须指出,野地采集也有较高的风险。湿草地中“有毒的草,吃后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危及生命。”*《莫文骅回忆录》,第295页。草地上有的野菜吃了也会中毒,浑身浮肿,躺下再也起不来了。因此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下令各部队在草地里不要乱挖乱吃不认识的东西。*《徐向前传》,第222页。总司令朱德则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各连队。*参见《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率部最后过草地时,“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这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有些……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贺龙传》,第204页。至于做针线活不是一般男人的强项,于是就由会做的战士进行帮教,其他战士边学边干,毛衣织了拆,拆了再织,直到织成像样的。红军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解决最低限度的衣食问题的。
自产自采是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解决衣食问题的最后办法。采取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资源极端匮乏,物资极其紧缺,时间极其紧迫,要全面及时缓解全军性的衣食不继问题,只有自己动手进行自救。由于发动面广、可行性强,最终帮助红军走完了长征之路。
革命战争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离不开后勤的保障与物资的供给。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勤保障的成败关系着红军长征的成败,其本身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马无粮草、枪炮无弹药,不可能具备作战能力。远离革命根据地长征的红军,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沿途地方军阀以及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处境万分险恶,后勤补给物资筹措的强度与难度空前增加。要克敌制胜,必须以灵活健全、快速高效的后勤作保证。由于长征路过的地区的社会环境、军事环境千差万别,因此红军必需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筹措物资。一般来说,在战争状态下,缴获、没收居多,在部队休整状态下,多采用自备、购买、自产自采等方式,当然也有几种方式并存的情况。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时期,红军各部队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手段克服困难,解决军需问题。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奋勇作战,将缴获的战利品补充自己。他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将打土豪没收的东西分给群众,并自留一部分军用;又自己动手,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通过自备、缴获、没收、购买、自产自采等途径,红军筹得最低限度的物资,胜利完成了长征。历史已经证明,红军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是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它对于支持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对于保持部队的顽强生命力、战斗力,对于维系部队钢铁般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勤保障方面的奇迹,其经验值得后人认真研究与汲取。
TheMaterialRaisingDuringtheLongMarchoftheRedArmy
ShaoYong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was faced with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siege from the local warlords and the Kuomintang Central army along the way. That background determined that the Red Army must try various device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litary supplies. Because the social and military environment of the long march areas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Red Army must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dopt various ways to raise materials. Under the state of war, most of military materials were seized and confisca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troops' recuperation, most of military materials were self-provided, purchased, self-produced and self collected. Sometimes, those varied measures would be adopt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se ways mentioned above, the Red Army raised the minimum supplies,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s material raising during the long march was correct, timely and effective. It has played a powerful role in supporting the Red Army to complete the long march successfully. It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tenacious vitality and fighting capacity of the army; and maintaining the steely solidarity of the army.
the Red Army; the Long March; the material raising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6.005
邵雍,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