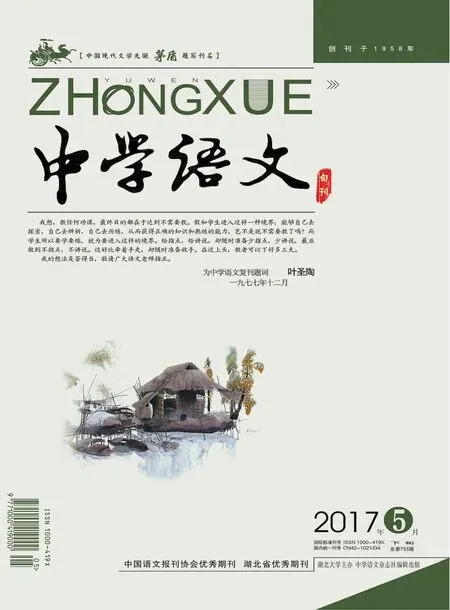审美之维:基于“文本自足”的阅读策略
——以《囚绿记》的主题解读为例
黄梅
审美之维:基于“文本自足”的阅读策略
——以《囚绿记》的主题解读为例
黄梅
陆蠡《囚绿记》的主题在通行的教参上被解读为:文章借赞美常春藤“永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抒发了自己忠于祖国的情怀,颂扬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表达了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之情。并借“有一天”重见常春藤的期望,祈祝沦亡的祖国河山早日获得解放。
这个结论其实是“知人论世”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结果。不过,这种方法论下的主题解读真的可靠么?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文章的叙事脉络和情感脉络在第八自然段发生转折,在此意义上,文本就此可被粗略地划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重在写绿的蓬勃和“我”的快活,而“我”在赏绿中生出的喜悦之情,文中第五自然段有明确的叙述: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的。……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因此,“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这种种“欢喜”,实在是绿色具有的“生命,希望”之意带给一个为生计所累奔波于都市的倦怠者的抚慰。
文章后半部分始于第八自然段第一句话,“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由此,“我”的心理逐渐转变:为了与绿色更接近与亲密,囚住绿色;误认绿条长势更好,生出巨大的喜悦;发现绿条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觉得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和善意,感到自尊心受损,仍旧囚系住它;看见绿条病损,虽觉可怜,却恼怒它的固执,仍旧不放走它;决定在七月尾离开的时候,恢复它的自由;”卢沟桥事件”发生促其提前南归,临行前开释绿条并致以祝福。
从全文结构来看,文章前半部分所写的绿的蓬勃和它带给“我”的慰安,是在为后半部分“我”的囚绿之举做好铺垫。全文的重点,着力于记叙“我”囚绿的经过,以及描写“我”反省出的“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的心理活动过程。后半部分虽有对绿的渴望光明自由,永不屈服于黑暗的描写和议论,但从其在全文占据的篇幅和在文中的实质作用来说,都非这篇文章的题旨要义,而是从属于“我”的囚绿行为范畴,旨在反衬出“我”这一“以爱之名,行己之私”举动的扭曲。因此,这篇文章所写的,实在是一个关于“破执”的主题,具体来说,就是打破“爱即占有”的执念。绿在前后文中的“希望”和“永不屈服”特质,无法借助一个“卢沟桥事件发生了”的时间点,就此托物言志,负担起“象征了不屈服于黑暗,渴望自由、光明的中国人”的所指意义。
而且,一个更本质的逻辑推论关系揭示,“我”出于“爱抚和善意”囚禁了绿,绿反抗的是“我”的“爱”,这也与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风马牛不相及。绿在此文语境中,不能仅仅凭借“不屈服”,或是联系作者该文写作之后的人生遭际,而强与历史事件中的中国人发生联系。教参上流行的主题解读,则是一种贴标签式的做法,徒显生硬和牵强了。
主题解读占据了文学作品阅读的重要位置,我们讲读懂文本,很大意义上就是在谈论主题分析。从《囚绿记》的主题解读来看,当文本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和文本被强行打开,链接上所谓的写作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后,分析出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
文本阅读是不是一定要借助“知人论世”?这就要追问时代变迁和作者经历是否必定影响到文本创作?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社会时代风气定然会对其精神内核的形成有塑造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不能说就一定与作者的每个作品都有鲜明的对应关系。
值得反省的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几乎一直在沿用“知人论世”的僵化套路,陷入考据索隐的泥淖而不自知,却美其名曰“深化主题”。
其实,我们在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可以从审美之维出发,采用一种基于“文本自足”立场的阅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有效可靠地读懂文学作品的难题。
具体到方法操作层面,我们应该根据文本的性质,把握作品的审美特性。如果文本本身是时代感很强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么文本就应该向包括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在内的“外部”敞开,如此,才能深化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例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倘若在解读作品时,教师补充出当时京都检察厅的尸检报告,学生就能通过“伤口胸前皮肉外翻,系子弹从背入,穿胸出所致”的文字记录,与鲁迅揭露与控诉段祺瑞执政府污蔑学生为暴徒的凶残时的大悲愤产生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果文本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类的现代主义作品,传统批评中的“知人论世”就不能派上用场,否则就会胶柱鼓瑟,得出一些荒唐的结论了。有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了阅读障碍,隐藏了文本的深层结构,这时就可能需要适当借助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阐释。文本“外部”的渗入,从主题生发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安排在文本相对“自足”的“内部”阅读完成之后,方能避免学生先入为主,生硬地得出一些标签式或无中生有的结论。同时,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便捷地获取丰富的历史材料时,学会带着问题意识对材料进行甄别和筛选,否则,文本意义会有被浩如烟海的材料所遮蔽。
从审美之维出发,立足于文本“内部”的解读,根据文本性质联系“外部”,才有可能洞幽烛微,揭示出文学作品真正有待发掘的意义。如此,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第三自然段,才是全文的“文眼”所在。他笔下的那片荷塘月色,就是一个为生活所累的中年男人偷得浮生半日闲,暂时逃避现实的精神栖息地,而非仅凭文末标注的一个1927年7月的写作日期,毫无文本依据地联系上“四·一二”事件,将朱自清的月下荷香中徜徉,解读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朱自清,面对这一黑暗现实,他悲愤、不满而又陷入对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之中。”
★作者单位:四川内江市第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