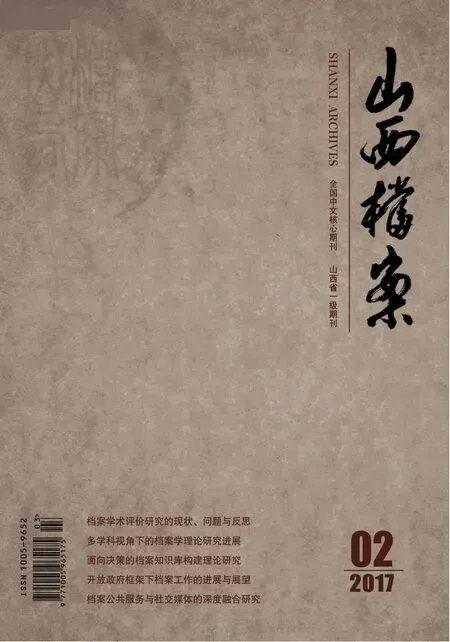档案副本的起源及功能探究
文 / 戈妍妍
档案副本的起源及功能探究
文 / 戈妍妍
档案副本的概念最早可以在西周的儒家经典《周礼》中发现踪迹。古代的档案副本更多的是采用文书形式。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人们不惜成本制作数量众多的副本,真正原因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原始档案。档案副本的功能较多,除了正规功能之外,还有图书、文件等衍生功能。自古以来,档案副本就有着突出的社会治理优势,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档案副本;《周礼》;文书
档案副本制度在我国起源较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就多处提及档案副本情况。根据近现代档案界的观点,档案应具备较强的原始性,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孤本制”被档案界所推崇,即档案的正本只有一个,妥善保存好正本就行了[1]。随着现代印刷技术尤其是电子档案的快速发展,副本制重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档案副本具备较多的功能,古代的档案副本不只是为了保护原始档案,还起到了行政管理作用。
一、档案副本的起源
在档案学的相关研究中,《周礼》关于副本的描述被认为是档案副本的起源。周王跟诸侯所签订的盟约,由天府进行收藏,而副本则交给内史、六官、司会、大史保存。这是较早出现的档案正副本概念,保管者有严格的区分。但档案副本起源的问题依然存在着一些争议。
(一)档案与文书的形成先后问题
文书是古代非常重要的行政产物,《史记·李斯列传》有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徧天下。”从《周礼》推出档案正副本概念来看,当时的盟约条例是由周王跟诸侯共同商定的,完成的盟书收藏进天府之中。这个天府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档案馆,同时复制成一定数量的盟书副本交给六官、司会等保管,以满足日常工作所需。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档案形成要早于文书,前者是正本,后者是副本。许多学者认为,古代档案副本的制作主要是运转公文,例如,西周的司会等官员掌管着大部分的文书,这些都是档案副本的雏形,主要目的是对各邦国以及郡府的社会治理进行考核,以此衡量各地官员的政绩[2-4]。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的解读都没有提到文书究竟是怎样变成档案副本的,因为正本藏入天府之后,并未发挥出文书应有的行政管理作用,也未体现出实际效果,即游离在行政办事流程之外。在这里只有一种解释:档案正本是直接生成的,并成为所有文书的源本,而文书只能作为档案副本继续发挥行政效用。从这一点也可以考证,档案形成要早于文书,正副本之争不存在疑问。而在手工制作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只有正本而不制作副本的情况,这种正本可以看作是档案和文书的合二为一,即正本兼具了两者的功能。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许多文书脱离了手工制作范畴,越来越多地采用印刷技术,这时就出现了文书正本的概念,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文书以文件的形式得到了延续,使得文件正本从形式上开始与档案分离,而且文件正本与副本的区别越来越小。但从档案副本起源上看,档案是早于文书的。
(二)西周档案副本的真正作用问题
相对于现代先进的印刷技术来说,西周的记录技术较为原始,当时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术,只有在竹简上抄录副本。根据《周礼》的相关记载,西周的内史、司会、大史至少各拥有一份档案副本,此外六官也各有一份[5]。六官也叫六卿,相当于后世的六部尚书,在朝廷中掌管着重要事务。西周的档案副本至少有九套。以当时的记录条件来看,这种数量较为反常,难道仅仅是为了长期保存档案?有学者认为,西周非常重视档案,包括实时归档、定时归档,将档案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一定的合理性[6]。但并不能就此认为西周的档案保护意识强于现代,所以西周档案副本的真正作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西周的复制条件远远落后于现代,需要人工抄写在竹简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现代档案副本有着先进的制作技术,许多档案馆采取的也只是三套制。就算西周比现代更重视档案管理,这种九套制的档案副本模式依然留有疑点,何况西周的档案副本制作成本非常高,朝廷应该考虑到是否合算的问题。从文书的角度看,西周制作这么多档案副本,并不只是为了保护档案副本,而是为了更多地发挥出文书的作用,即这些副本就是文书,主要是为了行政管理而不惜代价制作出来的。由此可见,文书是档案的副本有一定历史依据,当然演化到现代的文件又另当别论。
(三)西周档案副本制作的成本问题
从西周的制作条件看,档案副本制作有着极高的成本,制作人员、管理人员、档案库房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根据《周礼》记载的九套副本之说,档案副本的管理人员至少有九人或者更多,而且档案库房也不会少于九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人才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档案副本制作成本,必然产生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就算放在今天也可能让财政承担不起。西周的生产力低下,如果只是为了保护档案正本而花如此大的成本,其动机值得商酌。从历史角度看,西周的少数民族与部落众多,尽管朝廷加大各民族的融合力度,但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国力水平跟唐宋相比有较大差距[7]。西周为什么要花大成本制作档案副本,其出发点只有一种可能性,即行政管理的需要。西周在灭商后大分封的过程中,对全国各地主要实行军事统治,行政管理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用以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份辨别制度较为突出,这也是朝廷制定统治政策与剥削方法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内史、六官、司会、大史等都是行政管理人员,并非是档案管理者,所以档案副本制作和管理团队应该更为庞大。而西周所做的这一切,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将档案副本作为文书形式,主要为行政管理服务。
二、档案副本的功能分析
档案副本在古代就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在行政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档案副本具备多种功能优势,包括信息传播、使用范围、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极大地延伸了档案正本的功能。此外,图书、文件等作为档案的衍生物,也具备了档案副本的一些功能。
(一)正规档案副本的功能
副本是正本的复制品,通常是原样抄录正本的内容信息,使正本有另一种保存方式。根据《周礼》解释:“副,贰也。”这里的贰是指第二本或者更多,但正本仅有一份[8]。档案是人类最早的记录形式,在历史发展及社会变迁下,还派生出文书(现在叫文件)、图书等其它形式。正规档案副本是对原始档案的复制,两者的内容信息没有区别,而从档案资源保护的角度来看,正规档案副本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如可以提高信息传播效果、拓展档案使用范围、使多方持有共同信息、备忘等,促进已有档案的长期保存。由此可见,档案正副本的内容信息相同,但功能是有差异的。档案正本是一种原始的文本,目的是记数、记事等,延伸了人类的记忆[9]。而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出于信息管理和传播的需要,赋予了档案更多的功能,于是产生了副本这一形式。相对来说,副本已经脱离了记数和记事的范畴,延长了档案正本的使用寿命。
(二)图书、文件的副本功能
图书是印刷术发明之后出现的一种信息载体,对人类文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图书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传播信息,在内容展现方面是以复制原始书稿为手段,能够多方持有共同信息,保存地可以有多个场所。这与档案副本的性质基本相同。文件的功能除了传播信息之外,还方便行政办事和政策传达,同样也是以复制原始记录为主,可以多方持有及保存,这符合档案副本的基本特性。在现代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文件在行政管理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对复制文件的认可度日益提高,使得档案正本的权威性不复存在[10]。但文件不具备唯一性,所有传播的文件都是复制品,因而文件在实质上没有档案正本的“合法”地位。为了取长补短,我们可以将文件和档案正本统一归档,即实行“双轨制”。而图书的归档也经常采用“双轨制”,因为图书只有具备统一书号才能出版,并且要通过正规的出版机构发行,才具备“合法”地位。但作为档案正本的“书稿”并没有这些特性,只能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受众真正认可的是图书本身,所以档案正本的权威性受到了一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归档只有采用“双轨制”的方式,才能将图书的合法性“移植”到书稿上面,以提高档案正本的权威性。
(三)档案副本的社会治理优势
档案副本有效地促进了信息传播,拓展了信息使用范围,在社会治理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图书出现之前就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档案正本来说,只能在较小的、固定的空间内传播信息,当人类需要更多的知识传播和经验交流时,副本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被推到社会治理的前台,而档案正本开始“退居幕后”[11]。由于正本存在着唯一性,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管理主要采用副本形式,保存正本是为了提供官吏的查证备忘,副本则为了方便官府办事。在汉代,档案正本的保管地是相府,传达给各地方的是手抄类型的副本。清朝的档案副本则由六科负责抄发,通过批本处理之后发送到各地的衙门[12]。尽管随着印刷技术的流行,图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作为古代社会治理的权威方式之一,大多数都延续着副本抄送的做法,体现出对正本的尊重。直到现代社会才开始普及副本印刷的模式,而正本通常会盖有印章,副本则没有,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自古至今,档案副本都一直发挥着社会治理优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档案副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
档案副本可以随时随地保存信息,因而能够发挥出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档案副本的大量使用,使信息的异地传播和管理成为可能,有效提高了社会管理范围,促进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而为国家管理创造了条件。在古代,档案副本主要是为了辅助公文流转,例如西周的档案副本一般由司会等官员掌管,用于考核各地官府的社会治理,并作为官员政绩的汇报材料。到了宋朝,档案副本还在外交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周礼》是我国的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古代的许多行政工作方式,多处提到档案副本的使用情况。当时的档案副本是一种法令:“凡治者受法令焉。”即官吏在进行社会治理之前要领取“法令”,用这些副本从事社会治理工作[13]。在国家管理的需求下,档案副本被大量制作出来,而当时的印刷术尚未发明,朝廷会安排专门抄写副本的人。据《周礼》统计,负责抄写的达到了120人。由此可见,档案副本自古以来就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总之,档案副本在我国源远流长,种种迹象表明古代的档案副本更多的是起到文书的作用,即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不惜成本制作出大量的档案副本。档案是社会治理甚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在档案理论的研究中,剖析档案副本的功能作用,理清档案副本的起源问题,有益于我国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管先海.对档案价值、档案主体价值与档案客体价值的认识——兼与归吉官先生商榷[J].档案管理,2016,(3).
[2]朱兰兰.我国古代特殊载体档案中的汉字文化探析[J].山西档案,2015,(1).
[3]王云庆,孙嘉睿.盛世出国宝——近三十年来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的重大发现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6,(2).
[4]任越.论文化整合功能视角下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档案事业的影响[J].档案管理,2016,(5).
[5]程广沛,刘旭光.继承·借鉴·创新——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来源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7,(1).
[6]陈小春.西周档案管理制度之副本制度研究[J].兰台世界,2013,(8).
[7]王晖.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8]卜亚男.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J].兰台世界,2014,(26).
[9]邵金耀.新时期档案保护技术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档案学研究,2016,(1).
[10]霍振礼.从文件生命周期透视档案形成规律[J].中国档案,2014,(11).
[11]夏慧.吴宝康档案思想研究综述[J].山西档案,2016,(3).
[12]段保慧.清代副本档案制度考略[J].兰台世界,2014,(20).
[13]杜勇.清华简《皇门》的制作年代及相关史事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5,(3).
G270
A
1005-9652(2017)02-0139-03
(责任编辑:虞志坚)
戈妍妍(1985-),女,江苏睢宁人,徐州医科大学档案馆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