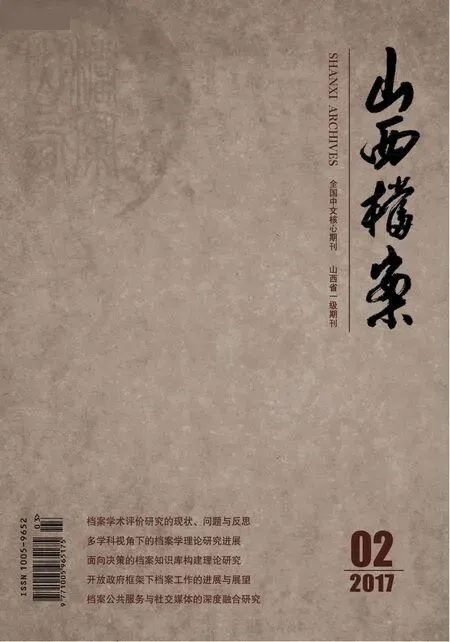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研究
文 / 李颖
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研究
文 / 李颖
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社交媒体对档案公共服务的有用性和有效性源自它自身的特点与实现机制,表现在有助于实现档案社会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的认知、认可以及内部驱动等方面。当前档案公共服务部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意识较强,但停留在浅表层面的应用阻碍了社交媒体优势的彰显,全面统筹的缺失导致了社交媒体应用效果的不显著。真正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需着眼于形成面向本区域的社交媒体服务战略,建立多维的“公众—社交媒体—内容”互动模型,合理选择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工具等。
社交媒体;档案公共服务;开放;互动
现代社会,社交媒体正在以其所具有的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特点,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又在深刻地引发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改变、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各种“关系”的变革。社交媒体带给各个领域与行业的,是机遇和挑战,是反思和变革,更是创新与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部门工作理念不断转变,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敏锐度不断提升,对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档案公共服务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综观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的实践探索,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并存。社交媒体日益广泛的应用,为档案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平台与空间,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档案公共服务如何渗透并融入这一空间,通过实现与社交媒体的“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为社会和公众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社交媒体对档案公共服务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分析
(一)社交媒体的开放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和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的全面认知
社会和公众对档案资源缺乏全面了解、对档案价值缺少正确认识,档案管理活动收、管、用等各个环节工作受到阻碍等问题,已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档案公共服务发展的瓶颈。这既源于档案部门与档案工作者自身的因素,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既有当下引发的新问题,也受不可规避的历史遗留的影响。虽然,在现代档案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积极探索着各种提升档案公共服务的路径,但档案的“高冷”在公众心中并未真正消除,因“不知道、不了解”而导致的陌生与疏远随处可见。因此,只有使社会和公众形成对档案公共服务全面正确的认知,即让公众认知何为档案资源、其有何价值、与自身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何关系以及在档案馆可以获取哪些资源、享受哪些服务等等,公众才能走近档案、走进档案馆,档案的价值才能得以激活,档案馆的责任和使命才能更好地实现。
公众对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全面认知,是档案公共服务破冰之旅的关键。而社交媒体平台,以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满足和契合了档案部门的这一诉求,其极强的开放性有助于高效实现社会和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的全面认知。在社交网络中,社会个体通过网络链接在社交网络上形成各种关系结构,个体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形成具有共同行为特征的网络群体,使得各类“网络信息”得以快速发布并传播扩散。这种基于关系构建的信息传播工具和平台,较之简单的信息搜索、网页浏览等形式,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深更广、信息内容更加有血有肉,更易于被用户感知和接受。这恰恰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公众因对档案部门的职责认识不明、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而产生的“不和谐”,为档案部门对自身及其工作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示和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公众对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全面感知和深刻认知。
(二)社交媒体的互动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和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价值的认可
对于一种产品或服务,只有在全面认知基础上认可并认同它们,才能转化为行动上的选择、接受和支持。综观当前我国档案公共服务,从档案资源自身来看,档案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赋予了其真实性、原始性、关联性等其它信息资源不可比拟优势,其凭证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显著;从档案公共服务机构看,档案部门更加重视开发档案资源,通过多种形式,满足公众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信息爆炸、知识经济等时代浪潮,使之更加渴望获得优秀品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他们既需要“消除不确定性的”真实、准确的信息,也需要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于是,便形成了“档案—档案公共服务—公众”这一链条,即以“服务”将档案与公众链接,档案公共服务的职责与使命便是实现档案价值与公众需求、公众利益的契合,并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当前,因社会和公众对档案部门及其服务存在的“刻板印象”(比如服务的单一性、被动性),使这一链条并未实现良好的运转。社交媒体为档案公共服务部门和公众搭建了一个双向沟通的互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众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更加便利地体验档案公共服务,通过交流对话了解档案公共服务。互动的过程,便是对档案及其工作价值解释和传递的过程。互动的过程本身就是服务的过程,是将“刻板印象”合理化的过程,是为公众持续选择和支持档案公共服务奠定良好基础的过程。建立在 Web 2.0 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允许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创造性社交媒体,为这一互动的实现提供了以往任何媒介都不可比拟的良好平台和空间。
(三)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有助于强化档案公共服务的内部动力
档案资源和档案公共服务主体是实现档案公共服务的两个重要支撑。档案资源的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其结构特点,决定了档案公共服务的内容;档案公共服务主体的思维理念、知识结构、综合素养等影响着档案公共服务具体实现的形式,二者共同影响着档案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质量。从档案资源的角度切入,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更使档案成为一种“泛存在”状态,档案馆正在打破它的“官方”收藏边界,档案资源多元化正在变得更加容易实现。“参与”不仅仅极大地丰富了档案资源,也正在使档案资源变得更具吸引性和可用性,档案馆正在变为真正的“我们的档案馆”;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公众不再是利用者的单一身份,而是同时具有利用者和服务者的双重身份。在参与中,公众不同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为档案资源的深层次、多维度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档案公共服务“产品”更加亲民易用。社交媒体的参与性让更多的公众有意或无意地跨入档案公共服务领域,主体的队伍不断扩大和优化,公众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中体验自己在创造、管理和开发、传播档案信息中的贡献,档案公共服务也因此更具生命力。
二、社交媒体在我国档案公共服务应用的现状
(一)档案公共服务部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意识较强
在我国,2010年以来,社交媒体呈蓬勃发展之势,各行各业充分借社交媒体之优势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指出:2016年,我国各类社交应用持续稳定发展,互联网平台实现泛社交化[1]。2014年杨冬权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包括纸媒、电视、网络,尤其是新兴的网络社交平台宣传档案工作,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关注档案文[2]。在实践领域,以“两微一端”(微博、微信、APP客户端)为例,自2009年开始,档案局馆开始探索微博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到2014年达到顶峰,目前微博账号达到200多个;2013年,档案局馆顺势开始了对微信公众平台应用的探索[3],截至2017年2月,全国各级各类档案微信公众号有近400个;对于移动APP,目前在档案局馆中的应用虽数量较少,但已初露头角,如浙江档案APP,福建档案APP和辽宁省档案馆APP等。面对各种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虽然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大多反应比较敏锐,表现出较强的应用意愿和诉求,付诸实践探索并希望以此为档案公共服务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停留在浅表层面的应用阻碍了社交媒体优势的彰显
之所以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公共服务对社交媒体的应用停留在浅表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仅将社交媒体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使用,缺少对社交媒体所触发的人们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变革的分析。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参与性等特点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交流更快、更远、更自由,更有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的权力、自由平等、安全等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表征现象背后隐藏的对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所带来深层影响,并由此分析档案的价值在这种变革之下如何实现,只有审视档案部门在新的环境之下的历史职责与使命,才能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的真正融合。第二,对社交媒体仍然是一种“粗”应用和“简单”应用。社交媒体应用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形式的社交媒体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微信、QQ空间、微博虽然同属于综合性的社交应用,但在社交关系的紧密度、用户属性及地域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从交流属性来看,微信朋友圈是相对封闭的个人社区,分享的信息偏向朋友之间的交互,微博是基于社交关系来进行信息传播的公开平台,用户关注的内容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兴趣的垂直细分领域,QQ空间则介于两者之间[4]。而当前档案部门的公共服务,对不同形式的社交媒体特征和适用性的深入分析不够,应用过程中随意性较大、主观性较强,也存在盲目追逐潮流的现象。
(三)全面统筹的缺失导致了社交媒体应用效果的不显著
档案公共服务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充分调研、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本组织现状,确定目标、制定规划和方案,才能确保社交媒体应用效果的显现,并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当前档案公共服务部门在社交媒体应用中往往缺少全面的统筹规划,未做充分准备便跟风而上,或者以创新为出发点“边走边看”,导致运营中对所出现的问题不能有效应对,因缺少充足的保障而难以持久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尸账号、昙花一现式等不良服务现象,而“有台无戏”的尴尬不仅与提升服务质量的初衷事与愿违,更埋下了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质疑与疏远的隐患。据笔者统计,当前我国档案部门的僵尸微博(三个月以上未更新)数量达到40%以上,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设中,不活跃公众号(一个月以上未更新)的数量占到了30%(仅包括省市级)。
三、社交媒体与我国档案公共服务深度融合的关键策略
(一)形成面向本区域的社交媒体服务战略
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方略。它是一项工作、一项活动得以朝着既定目标、深入持久开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公共服务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档案公共服务质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要素(比如档案资源、档案工作者、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等)将自身价值和作用最大化,并且各要素之间实现最佳的协调以及良好和谐的互动共振。这就需要形成具有一定站位高度的、具有宏观规划和指导意义的服务战略。比如,在美国,2010年8月,NARA通过了《社交媒体战略》,首先阐明了NARA为什么采用社交媒体;然后重点阐明了NARA社交媒体战略所基于的六个核心价值理念;并详细介绍了社交媒体使用所关注的三个主要领域[5]。2016年,NARA总结六年来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经验和收获,在深入分析数字时代带来的种种变革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工作使命,制定并发布了《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战略2017—2020》,描述了未来三年的发展愿景,以及所要实现的四个目标,并解释了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目标,以及对如何实现目标进行了规划[6]。
在我国,各地档案事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显著,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交媒体深度融合的实现应该着眼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以及现有档案公共服务的优势和短板,并基于公众的成熟度等等,在综合分析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基础上,制定面向本区域的社交媒体服务战略,使档案公共服务相关的各方主体形成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关于“是什么、为什么”的认知框架,从源头上指导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深度融合 “怎么做、怎么做好”。
(二)建立多维的“公众—社交媒体—内容”互动模型
公众、媒介和内容是研究档案公共服务的根本要素,要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仅仅要关注各个要素,更要关注要素两两之间、三者之间如何实现多维的良性互动。在传统的档案公共服务中,档案资源多是既有的、静态的;公众的利用多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求;在服务过程中,服务者将馆藏资源提供给利用者,公众多是扮演了“被满足需求”的索取者和受益者的角色。如前所述,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在档案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正在改变着传统档案信息服务中利用者的角色和身份,扩展了他们的范畴。首先,公众无论有无利用需求,都在愈加不可避免地与档案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档案信息服务内容的构建,“当人类记录与分享日常生活时,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以及人类的个人喜好、政治和宗教立场以及对于事情的反思在产生的那一刻均成为了数字化的档案”[7],“档案成为了共享的工程”。我们无意泛化档案的概念,但社交媒体确在改变着只有经“官方”认可并得以承认的历史才能转化为档案的格局,公众构建内容将越来越普遍。其次,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便是公众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地挖掘档案内容,激活档案价值。档案来源多样,内容丰富,尤其是历史档案,要实现对其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有限的档案工作者难以驾驭无限博深的档案资源,这也成为档案公共服务“黯然失色”的原因之一。比如,众包是公众参与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荷兰国家视听档案馆为视听档案加标签项目、美国公民档案者项目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公众对于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积极作用。公众在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利用需求(比如专业研究、兴趣爱好的满足等),同时,又为更多公众更好地利用档案做了重大贡献,这也恰恰是参与的价值所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必须对其中相关要素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和梳理。其中,社交媒体平台上公众与内容关系的分析与重构是档案公共服务中最为关键的一条线索。因此,在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多维动态模型,是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持。
(三)合理选择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工具
当今社交媒体已广泛存在于互联网应用的各个方面:虚拟社区、即时通信、移动直播、微博微信、音视频等,其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可概括为平台型、社群型、工具型、泛在型等多种[8]。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特点和优势各不相同,比如微博、微信属于典型的平台型社交媒体,微博已成为当前我国颇具影响力的公共信息发布和分享平台,微信则偏重于熟人关系链上的沟通和分享;而社群型的社交媒体,如微信群、QQ群、豆瓣、知乎等垂直化的社交媒体,为用户搭建了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的平台,通过在网络上各种关系的构建,更好地实现了人际交往和自我价值;工具型平台以通过工具提供服务为目的,打破时空界限,将服务延伸至公众学习工作的每一个角落,各种APP客户端应用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社交媒体所载“内容”来看,文字、影音图、视频、服务等,都是社交媒体丰富“货物”的表现。
社交媒体如此丰富的形式与内容,赋予了其多种功能。然而,当前我国档案公共服务中对社交媒体的应用,一是在工具选择上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两微一端”,创新使用多种平台的探索不足,结合自身服务特点,构建档案服务特色的个性化服务平台的探索极其缺少。二是在不同社交媒体应用中,并未根据社交媒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多是将同一内容放到了不同的平台上;而在具体服务过程中,档案“数据多跑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仍存在种种不畅,“群众少跑腿”并未真正实现。因此,实现社交媒体与档案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要善于选择多种社交媒体工具,打造一个立体的社交媒体工具群,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达20多种,在每一个平台下面还细分不同的频道,同时美国国家档案馆根据自身工作特点,量身打造特色社交媒体应用工具[9]。多种社交媒体工具的共同应用,有助于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对更多公众的触及和覆盖。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交媒体的特点和其用户群的特点,为不同的车配不同的货,开发适合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档案公共产品,比如灵活运用碎片化的微叙事方法,讲述档案故事,将冰冷呆板的档案变得温暖鲜活,从而激活其价值,实现更好的传播与利用。
[1][4]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201701/t20170122_66448.htm.
[2]杨东权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23日)[EB/OL].http://www.zgdazxw.com.cn/news/2014-12/29/content_80149.htm.
[3]李颖,史辉.我国移动数字档案信息服务发展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5]李颖.论社交媒体在我国档案馆中的应用——基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实践的启示[J].北京档案,2015,(2).
[6]社交媒体战略(2017-2020)[EB/OL]. http://nara-web.github.io/social-media-strategy/.
[7]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著.刘君,周竞男,译.新媒介:关键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73.
[8]谭天,张子俊.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J].编辑之友,2017,(1).
[9]美国社交媒体平台[EB/OL].https://www.archives.gov/social-media.
G230.7
A
1005-9652(2017)02-0050-04
(责任编辑:虞志坚)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公共服务机理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5CTQ037)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颖,女,博士,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