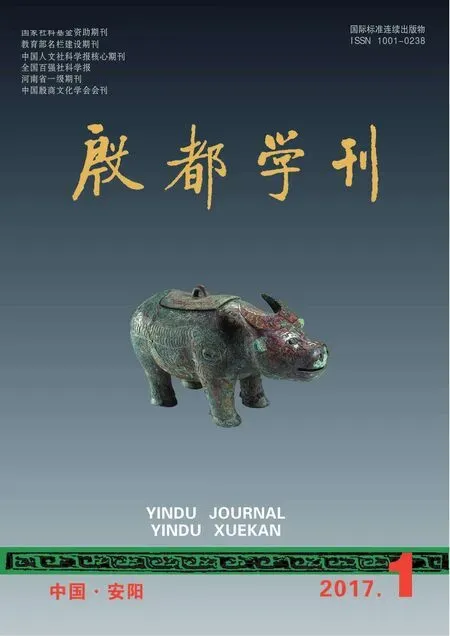宋玉辞赋“微讽”之风考辨
舒 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宋玉辞赋“微讽”之风考辨
舒 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宋玉与屈原并为中国文学之祖,而史书对二人评价差距颇大,《史记》评宋玉“终莫敢直谏”引发后人对其人格的质疑。本文从宋玉辞赋“微讽”风格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价并无人格贬抑之意。而宋玉本身际遇与屈原差相仿佛,空有满腹才情,在上不得君上亲任见察,在同僚中招嫉蒙谤,在下则“不誉之甚”,宋玉虽有拳拳之心却难申其志,而选择“放游志乎云中”,由此形成了宋玉辞赋的微讽风格。同时,宋玉辞赋在文学疆域中有意“铺彩摛文”,开“夸饰淫丽”赋风传统。
宋玉;辞赋;直谏;微讽;文采
宋玉,字子渊,战国楚人,屈原后学,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BC289),卒于楚亡之时(BC222)[1],生平好为辞赋,与屈原并为中国文学之祖[2],后人多称“屈宋”。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盛赞宋玉的文学造诣,并首以“屈宋”并称,曰“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时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骚》),“宋玉含才,颇亦负俗”(《杂文》)。著名诗人李白则以诗句“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感遇四首》其四)高誉宋玉品质之纯;杜甫亦作诗“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表达对宋玉的景仰之情。
宋玉生平事迹极少见载于籍,司马迁作《屈原列传》略提及宋玉,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3]尽管太史公并未对宋玉有苛责之意,而“终莫敢直谏”之论终使得宋玉蒙被人格上的污玷,并不断被放大,以至于在近代,宋玉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谄媚权贵、欺师灭祖的代名,并一度作为政治揶揄的对象而被丑化扭曲。对于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言,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是不可漠视的。既然这段公案由“莫敢直谏”为肇端,本文试从宋玉“莫敢直谏”的因由论起。
一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而后人网罗署名宋玉者的辞赋共计有十九篇:《九辩》、《招魂》两篇最早见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最早见于唐人章樵所编《古文苑》;《微咏赋》最早见于南宋陈仁子编《文选补遗》;《高唐对》、《郢中对》两篇最早见于明刘节《广文选》;《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两篇最早见于南宫邢氏藏本明人辑《宋玉集》;《报友人书》一篇则最早见于明梅鼎祚编《皇霸文集》。这些篇章真伪杂陈,随着近年来楚辞研究和宋玉研究的深入,对宋玉辞赋的界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当前主要观点认为《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共10篇赋可确认为宋玉的作品;至于《高唐对》、《郢中对》疑分别为《高唐赋》、《对楚王问》之异文;作者尚有争议的是《招魂》、《笛赋》、《舞赋》(疑为汉傅毅《舞赋》之摘录)、《微咏赋》、及临沂银雀山竹简中《御赋》等篇。而《对友人问》、《对或人问》、《报友人书》三篇则为伪作。[1]、[4]
从已确认的宋作诸篇可见,《大言赋》、《小言赋》为应制之作,内容前后承接,叙楚襄王君臣游阳云之台,召唐、景、宋作赋以定高下,结果“宋玉受赏”。两篇基本属于取悦于君王而作,穷形尽相地描写大小物象,无讽喻之意。《高唐赋》、《神女赋》二篇同样内容前后有所勾连,叙述楚襄王与神女交欢之事,《高唐赋》主要笔墨描绘巫山地区山水风物;《神女赋》则着意塑造巫山神女绝代风华。赋作之中暗借遇合神女之事批评襄王昏庸无能和无所作为。《风赋》、《钓赋》两篇则全篇讽谕君王,前者以“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对比描写,使大王豪奢和庶人悲惨形成鲜明比照,言辞瑰丽而暗讽辛辣;后者则以钓术寓治国之术,警示君王不应耽于小道而怠于治国。至于《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对楚王问》三篇均以自我辩解为务,发心中愤懑,指斥世俗而无贤,实则暗指君王为君不明,昏聩偏听,其讽谏意味颇浓。《九辩》则以抒情擅场,相较于其他篇章的含蓄,该篇言辞直接,一承屈原《离骚》之风。单就其讽谏方式而言,与屈作的热烈直达,犯言直谏相比,宋作中除《九辩》讽谕较为直白外,其他作品讽谏之意皆迂曲委婉,蓄势不发。故司马迁说宋玉“莫敢直谏”,极是。
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是以史学家眼光观照千古人物的,对于敢言直谏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往往带有明显的肯定倾向。在《滑稽列传》中他将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等一众社会地位极低的倡优列入传记中,极力凸写他们面对君王敢于直谏,善于智谏的事迹,并认为其符合六艺之旨,评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岂不亦伟哉!”[5]这无疑是对他们敢于进言,面谏君过行为的认可褒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追求美政、直言敢谏、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以死相谏,贾谊的上书劝政、无辜被贬、才高盖世、英年早逝的事迹表现出高度崇拜。尤其是对屈原,不同于其后班固、杨雄对屈原“露才扬己”而不知明哲保身的看法,司马迁认为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6]屈、贾二人都以犯言直谏立身而终以悲剧告终,联系司马迁本身也因直谏而遭难的际遇,其惺惺相惜,物伤其类自然在情理之中。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同情悲剧人物,钟情敢谏之士的例子所在皆是,也形成了他衡量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宋玉同为楚国显名者,却未能如屈原一般直谏君王,未能毫无保留地为楚国尽力,以太史公史学家眼光衡量,他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然是略逊屈贾一筹的。惟其如此,说明司马迁对宋玉并未有人格上的贬斥,而是比之前辈屈原,宋玉终究能达到“直谏”的程度是值得遗憾的。
屈、宋虽同为楚人,且均一度为楚王近臣,然气性毕竟不一,时势也各异,所以后人用屈原的标准来衡量宋玉,未必中正。
二
后人指责宋玉的罪名中有一条是“谄媚权贵”,认为宋玉凭献媚邀买高位,方成为楚王近臣。而事实却非如此。宋玉生平无明确史料可考,《史记》但言其在屈原之后,与唐勒、景差并时,笔者从散见于籍的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里试勾勒宋玉生平。
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7]与《隋书·经籍志》“《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8]均认为宋玉为屈原弟子,学界对于屈宋生卒年岁研究的结果证明此说恐不可信,而宋玉作为屈原后进,仰慕屈原道德文章则确实无疑。《韩诗外传》记“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刘向《新序》说“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亦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者,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9]可知宋玉起于微贱,大约受朋友——楚王族同姓景差所荐方与楚顷襄王交接,顷襄王欣赏其文才,引为近臣,宋玉方得以随侍左右。此情在宋玉辞赋中多有反映,《风赋》云:“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大言赋》云:“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钓赋》云:“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出土文献《御赋》亦云:“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这段时期大约是宋玉生平里最为得意的时候,《小言赋》云:“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随侍楚顷襄王左右的文学之臣还有唐勒、景差等人,而宋玉文才高妙,胜出同侪一筹,故而宋玉最受楚顷襄王青睐,单独陪侍楚顷襄王左右的机会多于他人,《高唐赋》记“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神女赋》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或正因为宋玉的才气高绝,不知藏锋,以致招人嫉恨,加之其“体貌闲丽”“身体容冶”而行止放达不拘,以致贻人口实,《讽赋》记“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休还,王谓玉曰……”,《登徒子好色赋》记“大夫登徒子侍于楚顷襄王,短宋玉曰……”,《对楚王问》更记“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自诩圣人,瑰意琦行,而世人嫉诽,其处境与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汉·班固《离骚序》)一般无二。
世人蒙昧嫉妒,宋玉自可不以为意,而作为倚仗的对象,楚顷襄王对其态度又如何?从《高唐赋》《神女赋》《风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的描述可见,楚顷襄王是一个游宴无度,贪淫好色的君王。《战国策·楚策四》中借庄辛之口说楚顷襄王在郢都时“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10]《汉书·古今人表》将其列入下上之品,也可略知楚顷襄王并非一个合格的君上。顷襄王为楚怀王长子,即楚王位之初便听信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谗屈原之言,“怒而迁之”。而宋玉平素“口多微词”,意有讽刺,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五臣《文选注·风赋解题》云:“时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李善《文选注》论《高唐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登徒子好色赋》表面写登徒子好色,实则讽谏楚襄王不要迷女色而误国政。可见宋玉在君王之侧,见王耽于淫乐,时时有所诫喻,可见其拳拳之心。然这并非楚王所喜闻乐见,也不符合楚王心目中对宋玉的身份定位。《襄阳耆旧传》卷一云:“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 宋玉为楚顷襄王近臣确然无疑,而其在楚国朝中所任官职又或是否有所职位都不得而知,比之屈原的“左徒”“三闾大夫”远有不及。
从上述资料大致可知,宋玉生于屈原之后,且出身寒微,一度入仕,而并不得志。与其在《九辩》中“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所反映的仕途不畅是相吻合的。宋玉空有满腹才情,在上不得君上亲任见察,在同僚中招嫉蒙谤,在下则“不誉之甚”,其烦恼苦闷于《九辩》体现得极为明显,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生而贫困窘顿,无师无友,寂寥一人,空任岁月蹉跎,年过中途而一事无成,秋凉似水,孑孓一身,顾影自怜,徒然悲叹而已。又曰: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郄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远去。[11]
君王在上而听之不聪,馋谄之徒在下阻断视听,举朝之中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宋玉怀抱利器却难以见察于君王,与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离骚》)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屈原“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而决绝选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宋玉则“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九辩》)。宋玉选择超越尘俗,放志云外,虽无三闾大夫为国为民九死不悔那般令人感佩,却为贫士选择了一条超越之路。放怀寥廓,对于困顿难行的文士未尝不是一种合理选择。
此外,宋玉一生主要生活在楚顷襄王、考烈王时期,这段时期正值楚国风雨飘摇之际。楚顷襄王元年(BC298年)秦昭王发兵楚武关,大败楚军,斩杀楚军五万人,夺取楚国析邑等十六座城池而归;十九年,秦攻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之地;二十年,秦将白起攻楚,夺楚西陵;二十一年,白起再攻楚,夺楚都城郢,焚毁楚国先王墓地夷陵,楚迁都于陈;二十二年,秦取楚巫郡和黔中郡。同年顷襄王死,楚太子熊完即位,是为考烈王,令尹黄歇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秦兵锋芒东指三晋,楚国暂得苟喘,而其时楚国已被秦蚕食鲸吞,日趋衰弱,再无力与秦争雄。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而无功,返而迁都寿春。
宋玉在家国江河日下,仕途又蹭蹬难行情况之下,选择与庄子同样“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而为辞赋,“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于极声色中暗寓讽刺,形成宋玉式的微讽文风,开后世大赋“劝百讽一”之先声。
三
《汉志·诗赋略》对从战国到西汉的文风迁变有精到概括,曰: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2]
周之文脉本出于《诗三百》,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有治国化民之效,“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至于春秋之后,人心尚战,法势当权,礼崩乐坏之势已积重难返,《诗》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大序》)的传统日渐消弭,宋玉前辈如荀子、屈原之辈在家国遭隳,身世浮沉之时作辞赋以讽,尚能得《诗》之三昧,至于宋玉时,身处末世,一变辞章不尚浮华则例,“竞为侈俪闳衍之词”,后世仿效者比比皆是,驰骋文才,而讽谏意味大为消减。
《诗》因承担着正国安家、移风易俗的使命而具备讽谏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荀卿、屈原辞赋作品的根柢所在。孔子辑《诗》,荀、屈作赋都对作品寄予强大变风易俗的期望,故而孔、荀、屈都以政治家身份跻身历史。至于宋玉,“放游志乎云中”的志向选择决定了其作品社会功能的相对弱化。宋玉更关注自己作品的文学艺术性,所以在丧失部分社会功效的宋玉辞赋中,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却得到放大和张扬。
以《对楚王问》为例,曰: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13]
对于世俗之人的谗毁,宋玉云淡风轻,先以曲高和寡为喻,又以高飞之凤与蕃篱之鷃,纵横四海之鲲与尺泽寸水之鲵作比,形象地说明自身与世俗之人境界上高下之别,自身高行志节自然难为众人理解。宋玉以圣人自况,超然独处,孤高自安,充分刻画了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高洁形象,成为后世孤高负俗、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形象的先声。《文心雕龙·杂文》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卷五《宋玉<对楚王问>解题》云:“此文腴之甚,人亦知,炼之至,人亦知。却是不知其意思之傲睨,神态之闲畅。”何焯《义门读书记》评“宋玉《对楚王问》……气焰自非小才可及。”此篇所展现的铺张扬厉,气势沛然,词巧句丽的气质正是后世大赋的雏形。
宋玉另有散体赋两篇与《对楚王问》同一基调。其一《登徒子好色赋》曰:“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赋中写登徒子诋毁宋玉生性好色,恐淫乱王宫,令楚王心生疑虑,转诘问宋玉,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以示其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与之孕生了五个孩子,反责登徒子才是好色之辈。同时借章华大夫“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之说来阐述自己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观。其二《讽赋》曰:“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休还,王谓玉曰……”同僚唐勒在楚王面前进谗说宋玉容貌英俊,口善言辞而行止不端,调戏主人之女。楚王由此见责于宋玉,宋玉描述当时至主人家中情况,主人之女先是将宋玉引入暗示男女交欢的兰房之室以示爱慕之意;又以华丽的着装示美,以精致的饮食示好,以挂钗的动作示爱,以由衷的情歌坦白心扉;最后径直以死明志,以殉情相胁迫希望与宋玉欢好。面对主人之女三番挑逗,宋玉均无动于衷,且予以拒绝,最后甚至说出“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来断绝女子的求爱之心。宋玉的辩白让谗言不攻自破,楚王感服。两篇文章都穷形尽态地刻画出“宋玉”的立身高洁的正人君子形象,同时留给文学世界以“邻家之女”“好色登徒子”“主人之女”等一众经典文学形象。
在文学疆域中尽力施展其才气是宋玉辞赋的重要特点,讽谏意味则藏而不显,正所谓“意在微讽”。上述三篇散体赋均有宋玉受谗——楚王诘问——宋玉自我辩白这一行文模式,文辞绝艳,令人目不暇接,而其讽谏意味藏而不显,细细深究,各有深意。《对楚王问》文中楚王表现的与世俗之人一般,用世俗之人的“不誉”诘难宋玉,不知好歹,不分贤愚,偏听不明,其为君不明可知。宋玉于文中并未对楚王所责之“遗行”进行辩解,但以曲高和寡,燕雀尺鲵不知凤凰鲲鱼之喻使得“遗行”之诬不攻自破。宋玉的孤高绝尘,自然显现,楚王及世俗之人的昏昧昭然若揭。《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取屈原“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之意。登徒子、唐勒之辈对宋玉心生嫉妒,抓住宋玉“体貌闲丽”“口多微辞”而捏造事端,以“淫”极力诽谤之。宋玉在楚王问责之下,极夸张之能事,描写自身在美色当前,百般挑逗之下尚能义正词严,不事淫乱。相较之下登徒子好色无度,主人之女多情大胆才是真正的“淫”。面对宋玉的辩白,《登徒子好色赋》中楚王信之如初,而《讽赋》中楚王的反应则颇耐人寻味,“王曰:‘止止。寡人于此时,亦何能已也!’”楚王的此番慨叹至少有四层意思,一则楚王自诩有非常之操守,不会为一般的女性示爱所动;二则即便如楚王,直面主人之女示爱攻势,也难保无动于衷;三则是接受宋玉的辩白,消除了对宋玉“不亦薄乎”的质疑;四则认同宋玉做法,接受宋玉的讽谏。此篇赋也是宋玉作品中明确表示楚王受谏的一篇。《讽赋》的主旨可参见宋章樵的解题:“楚襄王好女色,宋玉以此赋之,之词丽以淫,谓之劝可也。”由此观之,《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均是讽谏楚襄王勿贪女色而误国。
与屈原的“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直言世之丑恶、王听不聪不同,宋玉虽同样以高洁不俗自况,“窃慕诗人之遗风”却不热烈直达地表达对君王的指摘、对庸俗谄媚制备的厌恶,而是纵笔于文,重彩华色,逞才使气,以一个文人身份在文学疆域中大展拳脚,以瑰丽炫彩的色调和玄幻无垠的想象将屈原开辟的瑰奇世界进一步拓展。面对与屈原一样伟大的文学肇始者,自然不当以单一的讽喻为唯一评价标准。汉人文章事即家国事,故汉代学者对赋的褒贬,都是以有无“风谕之义”为尺度进行肯定或否定。如杨雄早年学相如作大赋,晚来悔之,以为“没其风谕之义”,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对赋“劝百讽一”颇为不满。至于文学自觉时代,南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认为赋体兴起于战国,造极于汉,是一个由粗朴到精致的历史过程,而正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刘勰对宋玉作品虽有“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之语,认为其讽喻不够强烈,同时却认为“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谐隐》)并未完全否定宋玉作品中讽谏意味的存在。宋玉与屈原生平境遇差相仿佛,而以赋见称,“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杂文》),刘勰认为夸饰淫丽正是赋的“立体大要”。宋玉以其出类拔萃的赋作和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为两汉魏晋以来千百年的赋家开辟了无限可能。也由此刘勰将宋玉与屈原相提并论,认为其“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充分肯定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拓宇之功。
尽管在史学家的眼中,宋玉终究不登大雅之堂;而作为文学家,“铺彩摛文”的宋玉之名足以镌铭千古。
[1]吴广平.宋玉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陆侃如.屈原和宋玉[M].商务印书馆,1930.
[3]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二十四)[M].中华书局,1982.
[4]汤漳平.出土文献对宋玉研究的影响[J].中州学刊,2012.
[5]史记·滑稽列传(传第六十六)[M].中华书局,1982.
[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二十四)[M].中华书局,1982.
[7]洪兴祖.楚辞补注[M].引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M].中华书局,1985.
[8]魏征.隋书·经籍志[M].中华书局,1982.
[9]吴广平.宋玉研究[M].转引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4.32.
[10]刘向.战国策·楚策四[M].中华书局,2012.
[11]洪兴祖.楚辞补注·九辩[M].中华书局,1985.
[12]班固.汉书·艺文志[M].中华书局,1962.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对问·对楚王问[M].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邦显]
2017-01-10
舒鹏,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文献。
I207.223
A
1001-0238(2017)01-00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