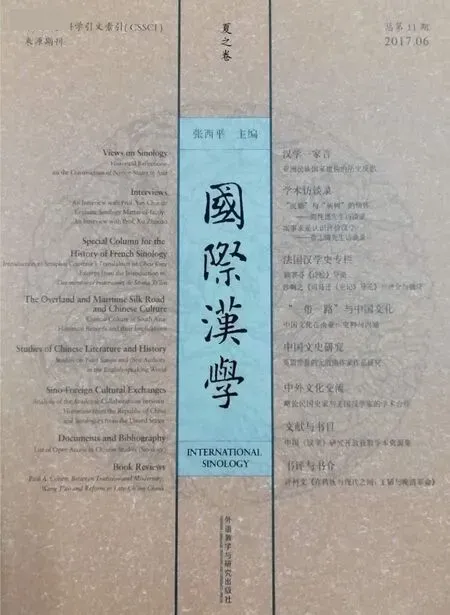略论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学术合作*
□
20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有一批美国汉学家涌向北京访学或进修。他们同中国学者建立学术联系,有的还同中国学者展开学术合作。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一批出身清华、燕京和北大的中国史家亦以留学、访学、讲学或应邀等形式先后赴美。①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到美国匹茨堡访学,老友王伊同教授向其详细介绍了几十年来华裔文史学者在美国的情况。大体说来,以前燕京、清华、北大出身者多,近40年则几乎以台大出身者为主了。具体参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2页。中国史家到美后,他们或应邀请,或出于师生关系,或因个人间的学术友谊,以不同形式同此前曾到中国访学进修后返美的美国汉学家开展学术合作。基于此,笔者拟对民国史家同美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合作研究做一具体的概述与分析。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合作之概况
当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和汉学专业的博士生涌向北京后,他们大多都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学者请益,并借此建立学术友谊。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自1924年与胡适在北平相识后,两人保持着终生之友谊;此外,恒慕义与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顾颉刚及其他中国学者亦维系着长久友谊。②Edwin G. Beal and Janet F. Beal., “Obituary: Arthur W. Hummel(1884-197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5, No.2(Feb.,1976), p.271.1935年至1937年,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以太平洋学会的研究员身份来华在北京进行研究时,陶希圣、邓之诚、冀朝鼎、顾颉刚等皆与之有所交往。据《顾颉刚日记》,魏氏在北平的社交活动甚为频繁,曾与其共席的国内学者有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王毓铨、连士升、陶孟和、洪业、姚从吾、梁方仲、刘选民、鞠远清等。③顾颉刚:《顾颉刚日记》(3),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69页。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在北平期间,结识胡适、洪业、顾颉刚、陈垣等人。④Thomas D. Goodrich,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 A Bibliograp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3, No.4, Oct.-Dec., 1993, p.586.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于1931—1935年在华期间从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学习金文和甲骨文①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6页。,并参加安阳发掘,结交顾颉刚、陈寅恪、李济、傅斯年、梅光迪、董卓宾、柳饴徵等中国考古学者及古史专家多人。②H.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preface.1931—1937年来华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向冯友兰、许地山等几位中国知名学者学习,③W. Allyn Rickett, “In Memoriam: Derk Bodde(1909-200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3, No.4, Oct.-Dec.,2003, pp.711-712.杨树达在日记中记述了1934年卜德招饮情形,同座还有冯友兰、许地山、吴宓及福开森④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1—92页。。两次来华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1906—2001)如是描述在北京的生活情形:“在北京的时光,真是一段美妙的日子。我们请教博学的中国学者,熟悉参考用书和文献收集,练习口语……”⑤保罗·柯文(Paul A. Cohen)、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编,朱政惠、陈雁、张晓阳译:《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Fairbank Remembered),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第7—9页。
在这种交流互动之中,部分美国汉学家开始同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毕乃德即与刚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讲师的邓嗣禹合作,于1936年出版了《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⑥Ssu-Yü Teng and K. Biggerstaff,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Camb.,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viii.魏特夫在北平期间,陶希圣与其合作一年,通过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的经济史研究室替代搜辑辽金经济社会史料。经济史研究室的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君替他做了大批的卡片。“七七”事变之后,魏特夫将其带回美国去。⑦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30—131页。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批出身北京的清华、燕京和北大的中国史家相继来美。他们到美后,以不同形式同此前曾到中国访学进修后返美的美国汉学家开展学术合作。恒慕义利用其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之密切关系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邀请了一批中国史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共同工作和研究。例如,吴光清于1938年加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成为其活跃的一员;⑧《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第24页。朱士嘉于1939年应邀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3年,编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一书;⑨Chu Shih-chia, A Catalog of Chinese Local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王重民于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编撰了两卷本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⑩Wang Chung-min, 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此书稿实际完成于1943年,但到1957年才出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恒慕义于1934年开始负责组织编撰《清代名人传记》。⑪Edwin G. Beal and Janet F. Beal, op.cit, p.266.为此,恒慕义邀请了50位学者参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中国学者,如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邓嗣禹、冯家昇、裘开明、吴光清、王重民、朱士嘉等。“七七”事变后,离华返美的魏特夫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于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凭借充裕的资金及其在中国学术界所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魏特夫招募到一批中国学者与其共同开展此项目,如王毓铨、冯家昇、瞿同祖和赵增玖夫妇等。德效骞(Homer H. Dubs,1892—1969)于1930年开始译注《汉书》。为此,他聘请任泰和潘硌基两位中国学者担任助手。⑫L. Carrington Goodrich, “Homer Dubs (1892—196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9, No.4, Aug., 1970, p.889.
除了依托大型研究项目开展集体合作之外,美国汉学家亦与民国史家进行个人间合作。邓嗣禹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三年间,同导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合著了《论清代官方公文的递送》《论各种公文的程式及其使用》《论清代纳贡制度的规章及其实施》等三篇系列文章。①这三篇文章分别刊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 No.1 (May, 1939), Vol.5, No.1 (Jan.1940), Vol.6, No.2(Jun., 1941)。后以《清代行政的三种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为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立雅同邓嗣禹合作编辑了两部分别名为《中文报刊归纳法》(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和《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册》(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的系列汉语教材。②H. G. Creel and Teng Ssu-yü, 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H. G.Creel and Teng Ssu-yü, 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邓嗣禹再次来到哈佛作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费正清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同其通力合作,在太平洋关系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把那些有助于说明常被人引用而又被误称的中国门户开放的真相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中文译成英文,于1950年出版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油印稿。③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费正清同刘广京在1946年至1949年合作对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近代史藏书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一部页数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④《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页。富路特亦积极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1943年同韩寿萱合作撰写《明实录》一文⑤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Shou-Hsuan Han, “The Ming Shih-Lu,”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3, No.1 Nov. 1943, pp.37-40.;1946年,同冯家昇合作撰写《中国火枪的早期发展》⑥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 Isis, Vol.36, No.2, Jan., 1946,pp.114-123.;1949年同瞿同祖合作撰写了《隋文帝时期宫廷中的外来音乐》⑦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u T’ung-tsu, “Foreign Music at the Court of Sui Wên-t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69, 1949, pp.148-14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国内动荡的局势,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即将建立之时,部分中国史家或因政治原因,或因担心国内已不复具有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或因家庭和学业等原因而选择留居美国。这批中国史家在留居美国后,亦以各种不同形式同美国汉学家进行学术合作研究。例如,张仲礼自1954年开始即协同华盛顿大学的梅谷(Franz Michael,1907—1992)编撰《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与史料》,直至其回国;⑧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s 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p.viii.邓嗣禹、王伊同、孙任以都、唐德刚、刘子健、萧公权、周策纵、朱文长、何炳棣、吴光清等一批留居美国的中国史家参与了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主持的于1955年开始编撰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他们都撰著了数量不等的相关词条,因而出现在执笔人名单中。⑨Howard L. Boorman(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富路特于1962年开始主持编撰《明代人物传记辞典》,在执笔人名单中同样可见一大批留居美国的中国史家名字,如邓嗣禹、房兆楹、王伊同、李田意、罗荣邦、萧公权、孙任以都、吴光清、钱存训等。⑩L. Carrington Goodrich(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坦言道:“在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⑪矶野富士子(Fujiko Isono)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41—42页。由此可以想见,民国史家担任美国汉学家助手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间更为常见的合作形式。20世纪30年代嘉德纳在北平进修期间,聘请周一良担任其私人秘书,任务是替他翻阅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作成论文摘要。①《毕竟是书生》,第176页。后来由于周一良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要去哈佛留学,于是周一良推荐杨联陞,由杨联陞接任,帮其买书及为中日文论文作英文提要约一年。②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页。何兹全经陈翰笙介绍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协助佛朗西斯(John D. Frances)教授翻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何兹全一面译,佛朗西斯一面看译稿,讨论译稿中出现的问题。半年后,何兹全回国,佛朗西斯又找到了王伊同接替。③《何兹全学述》,第84-85页。孙任以都曾作为费正清助理,帮助其查对博士论文,翻译补充中文资料,并替他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做一些翻译;1950—1952年间,又担任拉铁摩尔的助理,帮他记录蒙古人的访问稿。④孙任以都:《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58、60页。
二、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合作之特点
纵观民国史家同美国汉学家的合作研究,不难发现美国汉学家同民国史家所开展的合作研究具有与众不同之处。概括而言,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两大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
其一,基于美国学术界和现实之急需,合作研究项目多集中于汉学基础领域。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基础仍十分薄弱,处于奠基发展时期。以有关中国历史的英文通史教材为例,“在英语界唯一的教材是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它一直是一本权威的教科书。……赖德烈于1934年出版《中国:历史与文化》一书后,作为一本大学的中国史教科书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竞争对手”。⑤S. Y. Teng, “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24, No.4,Oct., 1944, p.294.故此,美国汉学家与民国史家的合作多集中于工具类或基础性项目。例如,毕乃德与邓嗣禹合作编撰的《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属于“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正如其前言中所说,“是为了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书”⑥Teng and Biggerstaff, op.cit., p.vii, v.。 20世纪以来,大量清代档案文献的相继出版,引发了学界无穷无尽的需要。当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在阅读这些档案文献时,发现“在档案文献资料中充满着技术程序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故此,费正清同邓嗣禹合撰关于清代行政方面的研究论文,梳理解释清代公文的类型、作用及传递方式,以使“我们知道这些公文是如何产生和处理的,传送这些公文需要多长时间”。⑦《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62页。《清代名人传记》《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明代人物传记辞典》等治汉学者所必备的参考工具书亦是因当时学术界之所需而编撰。恒慕义组织编撰《清代名人传记辞典》之初衷在于“满足美国汉学界对这种参考工具书的迫切需求”⑧Edwin G. Beal and Janet F. Beal, op.cit. p.269.。富路特组织编撰的《明代名人传记辞典》“是出自于一种需要,1950年代亚洲学会的各种不同学术圈越来越强烈地呼唤一部关于明代的基础性著作的问世”⑨L. Carrington Goodrich(eds), op.cit., p.vii.。顾立雅同邓嗣禹合作编写汉语教材,“尽管有许多人一道联合使这本书能够快速出版,正如前言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珍珠港事件的直接结果”⑩W. Simon, “Review 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by H. G. Creel; Teng Ssu-yü.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 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 by H. G. Creel; Teng Ssu-yü,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2, No.1, 1947, pp.260-261.。
其二,合作研究中史料搜集、挑选、英译及注解等任务多由民国史家承担。美国汉学研究者的汉语言水平,在民国史家看来确实是不敢恭维。著有在国际汉学界广受好评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在邓嗣禹看来其遗憾之处仍在于未能精通汉文;①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11期,第56页。被认为美国学者中在杂学上最渊博的富路特②杨联陞:《富路特,〈中华民族小史〉书评》,《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6期,第42页。,在雷海宗看来“读中文的能力太差”③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第957页。。美国汉学家自己亦承认其汉语言能力有限。费正清曾回忆起其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时的汉语能力自述道:“我的汉语口语即将登上有能力同仆役、零售商人和宾客处理生活上紧要事务而交谈的高原,但还远远没有走近为理解某一专业术语而必须攀登的连绵不断的山峰,更不用说学者之间在旧式交谈中那些文学典故和不计其数的比兴语句了。”④《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4页。拉铁摩尔也曾自述其在撰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汉语水平:“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⑤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由于美国汉学者的中文修养不够,故合作研究中多由民国史家承担史料搜集、挑选、英译及注解等任务。例如,邓嗣禹与毕乃德合编的英文《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虽然在1936年初版的导言没有介绍两者的分工,但在1950年的修订版中却明确说明了两者的分工:新增的大约130部著作由邓嗣禹负责挑选并由其撰写有关描述这些著作的注解,而毕乃德则通读了这些新材料并就版本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建议。⑥Teng and Biggerstaff, op.cit., p.v.魏氏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正式出版的成果是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这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正因为如此,魏氏在该书的总论中高度评价了合作者冯家昇的出色工作:“他在文字材料方面的非凡知识,使他非常适合于作选择、翻译和注释等学术工作,而这些工作则是进一步开展一切工作的依据。”⑦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9页。魏特夫发表于1947年《哈佛亚洲研究》的《辽代公职与中国考试制度》一文的注释中,亦坦承冯家昇的贡献以及有关不同朝代考试制度的重要资料都是由瞿同祖收集。具体见“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0, No.1, Jun., 1947, p.13.在梅谷主持编撰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一书中,所收集的391份有关太平天国原始文献中相当一部分由张仲礼英译,并且他还负责对翻译进行检查。⑧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umes I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ix.费正清与民国史家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共65篇重要文献,邓嗣禹“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的译稿并汇编了我(费正清)编写的有关其作者的大部分资料”,“后来又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学者房兆楹和孙任以都参加进来,担任部分翻译工作”。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400页。顾立雅同邓嗣禹合编的两部汉语教材,其框架结构是遵循顾立雅教授的《汉语文言进阶》(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中的体例方法来编排,但材料的选择和翻译则由邓嗣禹负主要责任。⑩Simon, op.cit., pp.260-261.
三、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合作之余论
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成果,在美国汉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获得极高赞誉。恒慕义主持编纂的《清代名人传记》“是今天人们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最近三百年历史最为详细最佳的著作”①K. S. Latourette, “Revie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by Arthur W. Humme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50, No.4, Jul., 1945, pp.803-805.;德效骞的《汉书译注》“准确又非常贴近中文原文,……体现了译者对其经济资助者的极大负责”②Derk Bodde, “Reviewed work(s):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Homer H. Dub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4, No. 3, Apr., 1939, p. 642.;富路特主持编撰的《明代人物传记辞典》“是自恒慕义出版《清代名人传记》以来关于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西方参考工具书”③W. S. Atwell, “Review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0,No.2, 1977, pp.421-422.。梅谷与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所有关注中国研究的图书馆都应收入此书,众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的图书馆亦应获取这一重要著作,它是中美学术合作的一座丰碑”。④C. Martin Wilbur, “Review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umes II and III: Documents and Comments. by Franz Michael; Chung-Li Chang,”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8, No.3, 1974, p.424.冯家昇与魏特夫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被认为“是一部融高度学术水准与综合性为一体的著作,这使其在所有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中它都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⑤Woodbridge Bingham, “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by Karl. A. Wittfogel; Feng Chia -Sheng,”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9, No.3, May., 1950, p.356.。
美国汉学家与民国史家合作研究的成果能够获得极高赞誉,当然与民国史家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清代名人传记》中,最大的贡献属于房君兆楹夫妇两人,恒慕义在序言中写道:“应该提到编者主要助手房兆楹先生的功绩。房兆楹先生为编辑本书整整辛劳八年,在这期间他所撰写的传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房夫人同他丈夫一样忠忠耿耿为这个事业服务,并且小心翼翼地关注许多麻烦的细节问题”。⑥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富路特主持编撰的《明代名人录》同样受益于房兆楹。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曾如是评价道:“他在这部著作中的角色由其作为合作编者即可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作为由美国出版的两部最为不朽的汉学著作的合作编者,他的名字在西方汉学学术史上将成为不朽。”⑦Edwin G. Beal and Janet F, Beal, op.cit., p.1127.拉铁摩尔高度肯定冯家昇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的作用,他说:“尽管带有非常明显的魏氏理论之标记,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作为辽史之权威的魏氏主要合作者冯家昇多年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能撰著出这样一部高水准的著作。”⑧Owen Lattimore, “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by Karl A. Wittfogel; Feng Chia–Sheng,”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9, No.1, Feb., 1950, p.85.魏氏自己亦承认:“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 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⑨《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 59 页。梅谷如是评价张仲礼之于《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的作用,“张仲礼多年来一直参与此项研究项目,他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史料的翻译。他深刻的学识、对于史料的严谨评估,对大量史料英译的修订和注释,对这几卷著作来说作出了无价的贡献。”⑩Michael, op.cit., p.viii.毕乃德、费正清、顾立雅先后同邓嗣禹合作,在费正清看来“这些人从他的能力和博学学识中受益极大”⑪J. K. Fairbank, “Obituary: S. Y. Teng (1906-8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7, No.3, Aug., 1988, pp.723-724.。
然而,在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研究中定是不愉快者居多。这从民国史家在日记或与友人往来书信中对美国汉学家所表示的不屑和不满便可推知。萧公权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承华盛顿大学约来任教,并参加远东学院十九世纪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到此方知Wittfogel(维特弗格)被奉为‘大师’。因此研究的方法和观点都大有问题。如长久留此,精神上恐难愉快。”①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第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杨联陞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费正清的不满:“费所谓integration非奸人盗窃即愚人盲从,决非大学者气象,原定22开会,提前一天,似乎故意不等广京,亦属可恶。”②《杨联陞日记》,1950年7月21日,转引自刘秀俊著,王学典指导:《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探要》,山东大学,2010年,第84页。王伊同在其《读费正清〈五十年回忆录〉》的未刊稿中对费正清如是评价道:“费君正清,年七十五,皤然老矣。治清史,执美国汉学牛耳,达四纪,号儒宗,而君亦自居而不疑。吁嘻,费君诚儒宗哉!……夫文字之未通,费君诚儒宗哉!其治清史也,典章仰诸邓嗣禹,督抚科道胥吏公廨之制,拱手瞿同祖,清史目录,则唯刘广京是赖……吁嘻,费君岂儒宗哉,盗名欺世已耳!”③王伊同:《王伊同学术论文集》(上编),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年,第513—514页。民国史家在同美国汉学家的合作研究中,其心境不难推知。
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合作不愉快者居多之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于美国学术界所存在的歧视和学术观念的冲突。在杨联陞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李田意来信,云crump(自名迂儒)不肯在AAS年会文学史节目中加入李文(讲三言二拍)亦因crump自己要讨论此题,怕相形见绌。毛子可恨如此。”④《杨联陞日记》,1957年2月8日。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时,往往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⑤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11页。费正清曾如是言道:“我仅设想我的职责是阐述事实,而答案则让它自己冒出来。前来听课的研究生不久即粉碎了我那种只讲事实,不提论点的借口。他们只不过问些并不简单的问题,但我立刻意识到,任何阐述的事实都已在种种预想的框架中,而事实叙述者的首要之事,就是必须注意自己的设想框架。”⑥《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对此,民国史家多难以认同或接受。在中国学者看来,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陶希圣主张“历史的方法必须从史料里再产生,才是真确的。如果先搭一个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进去,那就是公式主义,也就是错误的”⑦《潮流与点滴》,第123—124页。。杨联陞积极倡导“训诂治史”,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萧公权亦主张:“放眼看书,认清对象,提出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不是我主观的,随意的构造。”⑧《问学谏往录》,第211页。王伊同则在评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时直言不讳指出:“方今以汉学家自命者,间或学殖荒芜,而抵掌空谈。傥籍氏书,而怀乎学问广大,非侈谈方法者所克奏功。”⑨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第519页。
20世纪初还处于汉学“荒村”的美国汉学界,之所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就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大重镇,其成功的一大秘诀即在于美国汉学界善于通过学术合作之方式以充分挖掘利用外来知识移民的国际汉学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今天中国学术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妨借鉴美国汉学发展经验,通过国际学术合作以推动我们学术的发展,尤其是研究薄弱的学术领域之发展。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合作中,应掌握学术合作的主导权。因为只有真正掌握主导权,才能充分而有效地将国际学术资源为我所用,以解决自身学术领域所迫切需要提高或解决之问题。国际学术合作的落脚点应是“掌握自己的立场、建立自己的标准、厘清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价值”,中国学术在国际化发展中坚守中国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