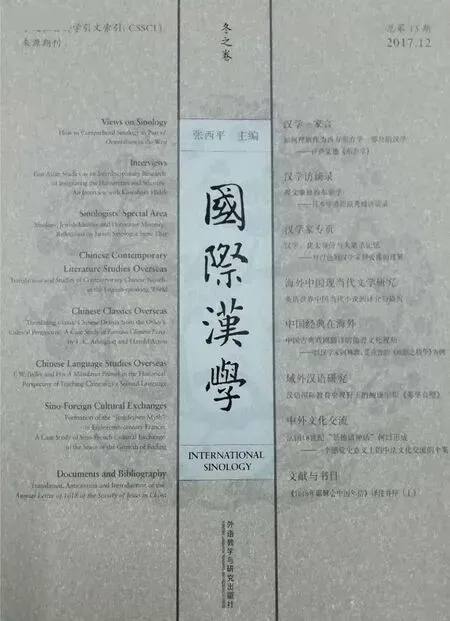法国18世纪“景德镇神话”何以形成—一个感觉史意义上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个案*
□
“瓷器撩拨着人们的眼球,呼唤着人们去触摸,某种程度上好似故意以其妩媚挑逗着人们……”①Jean Mathieu, ed., La porcelaine de Sèvres(《赛佛乐瓷器》).Paris: Chêne /Hachette, 1982, p.5.这是法国著名的国立赛佛乐瓷厂(Manufacture de Sèvres)②国内通行的译名为“塞夫勒”,本文有意译作“赛佛乐”,以期用此更“归化式”的译名略略传递出下文将提及的该厂与华瓷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厂长让·马蒂约先生的话,写在他为《赛佛乐瓷器》一书所作序言的开首。
我之所以引这句话开篇,皆因它道出了瓷器与感觉的关联。但其实瓷器关涉到的绝不仅止于马厂长提及的视觉和触觉。除了艺术性外,瓷器更具有实用性。联想到那些瓷制餐具、器皿、乐器……我们就不能不将这种关联扩展到味觉、嗅觉,甚至听觉。显而易见,瓷器全方位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给予人们最美、最典雅的生活享受。
或许正因如此,自16世纪起,欧洲人就对产自世界瓷都—中国的瓷器爱不释手。那些晶莹剔透、璀璨精美的工艺品、实用器,经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之手被源源不断地运抵欧洲,满足着各国王室和权贵们的需求。
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里建造了著名的“瓷宫”—特里亚农(Trianon)宫。据说,那座宫殿的外墙和屋顶全部砌以欧洲仿制的蓝白两色瓷片,不仅与内饰相协调,更与室内陈列的中式陶瓷器物相呼应。③参阅Monique Mosser, “Ces jardins fabuleux… au milieu d’un désert”(《荒原中这些奇异的园林》),in Pagodes et dragons,Exotisme et fantaisie dans l’Europe Rococo 1720-1770(《瓷偶与龙,1720—1770年欧洲罗可可艺术中的异国情调与奇思妙想》),Paris: Musées, 2007, pp.80—81。尽管两年后路易十四就因仿瓷开裂而下令摧毁瓷宫,但此事仍被时人及后世反复称颂,凸显了法人对华瓷的倾慕和喜爱,遂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那时,中国瓷器—连同仿制品在内④早期论及瓷器的法文书多称此类仿制品为“华瓷”(porcelaine de Chine),而将东印度公司运抵欧洲的中国瓷器(特别是外销瓷)简称为“东印度瓷”(porcelaine des Indes)。这两种称谓所指固定,沿用至今。为清楚起见,下文如无特殊说明,皆按两词特定所指,分别译作“仿华瓷”“外销瓷”。—稀少且昂贵,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拥有。
到了18世纪,新兴市民阶层也有能力加入到追捧瓷器的行列里来。据1700年9月《优雅信使报》(Mercure Galant)刊载的消息,法国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昂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货船在运回法国的货物中就装有“167箱瓷器”。①A.Jacquemart, E.Le Blant, Histoire artistique,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de la porcelaine(《瓷器的艺术与工商业史》,以下 简 称《 瓷 史 》).Première partie, Paris: J.Techener, Libraire, 1861, p.30.按: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国与西方,18 世纪广州之贸易(1719—1833)》,Paris: S.E.V.P.E.N., 1964)称昂菲特里特号船首航中国运回了181箱瓷器,似有误。查其参阅文献:H.Belevitch-Stankevitch,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中国情趣》),亦称运回法国的瓷器数为167箱,且出处相同,亦是1700年9月《优雅信使报》的报道。同样的问题亦存诸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ère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1702-1776,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中。而据专家们考证,1722至1723年,该公司在南特销售中国瓷器大获成功,除官方外,大批巴黎、里昂、图尔、波尔多、奥尔良……的商人纷纷前来竞购,疯狂推高了华瓷的价格,也使华瓷终于走入了平民百姓家,尽管此处所言之“平民”还只是殷实富裕的资产者家庭。②参阅 Michel Bourdeley, La Porcelain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东印度公司的瓷器》).Fribourg: Offre du Livre, 4e édition,1982, p.108。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销售记录称:17世纪末18世纪初,该公司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为15万件,到了1750年左右就增加到20万件,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又快速增加到30万件。③参阅 Philippe Handrère, Gérard Le Bouëduc, etc.,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东印度公司》).Rennes: Editions Ouest-France,1999, p.80。
但这仍然难以满足人们对瓷器的需求。早在路易十四时期,大领主和大金融家们就以“太阳王”为榜样,纷纷以贵金属换取进口瓷器。很快,为了满足这些富人们的需求,也受到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国的影响,法国的制瓷业迅速发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更是建立了一批较大型的瓷厂,如鲁昂(Rouen,1673)、圣—克鲁(Saint-Cloud,1678)、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721)、尚蒂伊(Chantilly,1725)、万塞尔(Vincennes,1738)等。④参阅 H.-P.Fourest, La céramique européenne(《欧洲陶瓷》),CELIV, 1986, pp.239—240(作者为法国陶瓷博物馆名誉馆长);X.de Chavagnac, etc., L’Histoire des manufactures françaises de porcelaine(《法国瓷器制造厂全史》,以下简称《法国瓷厂史》).Paris: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Editeurs, 1906, pp.1—121。到了1759年,已迁至赛佛乐的万塞尔—赛佛乐(Vincennes-Sèvres)瓷厂为路易十五所有,于是正式更名为王家瓷厂,成为法国制瓷业的霸主。⑤参阅 Jacques Silvestre de Sacy, La Chin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Henri Bertin dans le sillage de la Chine (1720-1792)(《中国在启蒙时代:中国热中的贝尔坦(1720—1792)》).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0, p.111.
一、“景德镇神话”成型始末概述
就在法国人这股追捧瓷器的热潮中,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2—1741)⑥殷弘绪神父1699年抵华至厦门,不久便至江西南昌、饶州一带传教。1707—1719年任法国传教团总会长。1719年底至北京,此后又为传教多次返赣。以上史实参阅P.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4,v.II, No 242;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J., 1973,No 245。神父寄回法国两封信,详细介绍中国瓷都景德镇的制瓷业。两信均为他利用在江西传教之便,深入景德镇实际考察,咨询了当地的商人和工人,又参阅了《浮梁县志》(Histoire ou les annales de Feou-leam)和其他相关书籍而写就,分别写于1712年、1722年。⑦参阅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耶稣会士书简集》), publiées sous la direction de M.L.Aimé-Martin, T.III,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p.207。
在1717年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刊出的殷弘绪神父的第一封信长达112页。他在这封信里先详述了景德镇的地理位置、历史与现状,接着就按瓷器的制作流程,对各环节逐一予以详细介绍:从原材料的制备,到成分配比、瓷器成型、模具、上色、烧窑、器形,直至烧完瓷器后的废渣处理,无一遗漏。通读全文,这封信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厌其烦地详述技术细节。
就以瓷器如何成型为例,殷神父这样写道:
第一道工序是将买来的白不子①“白不子”读音“bai-dun-zi”,为制瓷原料。中间一字不仅读音与“不”字相异,且书写亦有区别:其右边一点与上面一横直接相连。不知是否因为字形过于相像,计算机字盘中未收录此字,本文只得借用“不”字。此字正确读音及书写皆蒙复旦大学刘朝晖教授指正,特此致谢。和高岭再次提纯,去除渣滓…… 将白不子粉碎,倒入盛满水的大缸,然后用一根很宽的扁木棒去搅拌它,使之溶解;将它放置片刻,然后取出浮在表面的东西,用上面讲过的方法再行处理。…… 把白不子和高岭两种原料如此制备之后,还需将它们适当配比。要做细瓷,就将高岭与白不子等量相配;要做中等瓷,则将四份高岭土与六份白不子相配。高岭与白不子最小的配比数为1:3。②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s Jésus, XIIe Recueil, A Pairs, Chez Nicolas Le Clerc, 1717, p.286.本文所引殷神父信件中译文均以“豆瓣网”所刊译文(2015.4.13下载)为基础,经与法文1717年版原文核对,略作修订而成。“豆瓣网”译文未署译者名,亦未标注据何文字、何版本译出。
这封写于1712年9月的长信,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如此这般令普通读者厌倦且不知所云的专有名词和技术细节。尽管如此,五年后的1717年,却被杜哈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神父全文刊发在他主编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第12卷中。③参阅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XIIe Recueil, éd.1717, pp.253—365。一译《奇异而有趣的信札》。此信于1712年9月1日写于江西饶州(Jao-tcheou),致时任中国及印度地区传教团财务总管(procurreur des mission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奥利神父(P.Orry)。同年,又被立场、观点完全相左的《特雷武论文集刊》(Mémoires de Trévoux)和《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先后转载。④参阅Pfister, op.cit., V.II, pp.547—548。前者是耶稣会主办的杂志,以出版地小城“特雷武”命名,其办刊宗旨为反击“异教”“邪说”,殷弘绪的信刊于1717年1月号上。后者则是法国政府的官办刊物,注重普及知识,宣传文化,殷神父的信刊于1717年10月号。1724年,殷神父的第二封信又全文刊发在《书简集》第16卷上。⑤参阅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d.1724, pp.318—367。此信注明于1722年1月25日写于景德镇(Kim-te-tchim),但荣振华上引书称此信实写于北京。原信未标注收件人姓名,然据上下文及此卷主编为杜哈德等史实推断,当为杜哈德神父。十一年后,杜哈德神父又将1712年的那封琐碎枯燥得如同专业手册一样的信件几乎全文刊发在《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 de la Chine)上。⑥参阅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 P.G.Lemercier, 1735, T.II, pp.177—204。
《中华帝国全志》是时人眼中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其影响面及阅读效应也就可想而知。从那时起,殷神父的大名就连同他的“Kingte-tching”(景德镇)一起,屡屡出现在法国人的笔下。而那两封专论景德镇制瓷业的书信也就不胫而走,不断被或详或略地援引或转述。仅就18世纪而言,我们在各种文类的作品中均可觅见其踪影:《通用商业辞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⑦本辞典由路易十四的海关总监布律隆的雅克·萨瓦里(Jacques Savary des Brûlons, 1657—1716)编纂。作者生前并未全部完成,由其兄费勒蒙—路易·萨瓦里(Philémon-Louis Savary, 1654—1727)继续修订、补全,并付梓出版(1723—1730),1741年再版。殷神父信的缩写本由后者补在第三卷“瓷器”辞条后。、《北方游记》(Recueil deVoyages au Nord)⑧此书由流亡阿姆斯特丹的法国书商贝尔纳(Jean-Frédéric Bernard,1683?—1744)编辑出版,1715—1738年间共出十卷。殷神父信刊载于1738年出版的第十卷上,参阅下引Gersaint书,第18页。、雷纳尔(Guillaume Raynal, 1713—1796)著名的《欧洲人在两印度地区开辟殖民地与经商的哲学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E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①简称《两印度史》(Histoire … des deux Indes)。此书是18世纪一部重要的“启蒙”著作。1770年首版,书中在谈及欧洲人对华瓷器贸易时转述了殷神父有关景德镇(作者写作“Kingtot-ching”)的部分描述。……,甚至在巴黎著名杂品商热尔桑(Edme-François Gersaint)的拍卖目录中②Edme François Gersaint,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bijoux, porcelaines, bronzes, lacqs, lustres de cristal de Roche et de Porcelaine…(《珠宝、瓷器、铜器、漆器……拍卖详解目录》,以下简称《拍卖目录》).A Paris, chez Pierre Prault, Jacques Barrois, 1747.此书汇集了热尔桑杂品店1736—1747年的拍卖目录。14—45页为作者对瓷器的详细介绍,其中大段援引殷弘绪信,另有多处涉及殷神父信中的实例或描述,在对拍卖品的具体描述中亦不乏对此信的借鉴。此外,热尔桑还谈及南京琉璃塔(法人称为“瓷塔”),借鉴了李明(Le Comte)神父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和杜哈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另需说明的是,18世纪法国尚无古董业,法文“古董商”(antiquaire)一词也迟至19世纪才出现。18世纪的杂品商(mercier)销售范围甚广,囊括了几乎所有的装饰类物品:除梳妆打扮用的各式首饰外,还包括装饰房屋用的各类艺术品、家具、灯具、瓷器、金银器等。竟然也能读到它。1780年,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在他们主持的《百科全书》中专为“瓷器”列了一个条目,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也是对殷神父这两封信的原文照录。③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Neufchastel: Samuel Faulche, T.XXVI, 1780.该词条共39页,其中20页援引了殷弘绪的信,编者称转引自杜哈德书。
众所周知,《百科全书》的目的就是让知识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对“科学与技艺”、对人类活生生的生产活动给予理性总结,以向大众普及知识。④参阅 Madeleine Pinault, L’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Paris: PUF, «Que sais-je», 1993, p.11。如果说我们因此可以理解狄德罗们征引这样一封详述技艺的信,那么,何以游记作品,甚至杂品商的拍卖目录中也要洋洋洒洒大段援引这些令人难以卒读的纯技术性文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对时人而言,殷神父对景德镇制瓷业的描述,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技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中国技艺、中国艺术,甚至中国文化的某种代表。
而一个文本被如此频繁地征引、复述,本身就已结构成了一种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神话”。此处所言之“神话”,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2页),它是指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地域、事件在跨时空流播中出现的种种文本变异体的总和。更简洁一点地说,就是“一个象征的形塑”⑤Yves Chevrel, Littérature comparée(《比较文学》).Paris: PUF, 1989, pp.60—61.。也就是说,一个指称某人物、地域、事件的语符,基于种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在文本不断被转写、转述、重言中,最终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成为某种特殊意义的指代、符号。
为了紧扣“感觉史”这个中心议题,以下,我们将绕过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的文本分析,对“景德镇神话”的形塑过程不做具体讨论,而仅将其视作一个既成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具体探讨18世纪的法国人何以会对景德镇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以致它被神话化;而因“景德镇神话”愈发走红的华瓷又如何在感觉史层面上影响了18世纪法国人的感觉和欣赏趣味。
二、“景德镇神话”成因初探
成因一:回应18世纪法国制瓷业大发展的需求
一个技术手册类的文本得以广泛流播,最直接的原因当然首推其实用性、适应性,即是说,其内容满足了时人对相关技术的渴求。
1712年,当殷神父写作他那封长信时,法国的制瓷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据史料记载,1673年,鲁昂陶器商波特拉(Louis Poterat)发现了软质瓷的秘密,成功地制出了法国的第一件瓷器。但他拒不向任何人泄露天机。而当他1694年去世时,也就把这个秘密一同带入了坟墓。⑥参阅Fourest, op.cit., p.239。尽管不久,圣—克鲁瓷厂自行研发出了软瓷的配方,但软瓷毕竟难与中国生产的硬瓷相比肩,更何况德国人波特格(Frédéric Böttger)也已于 1709 年就研制出了硬质瓷。①参阅Jacquemart, Le Blant, op.cit., pp.403—409。《瓷史》作者称德国相关史料存在着时间错位问题:波特格1709年研制出了真正的瓷器,而商人斯诺尔(Jean Schnorr)发现“欧地高岭”(Kaolin d’Aue)的时间则是1711年。
正是为了回应法国和欧洲制瓷业发展的急迫需求,殷神父才会如此不辞辛劳地去了解景德镇制瓷技术和工艺全流程,并如此翔实地记录下来,这有他的第一封信为证:“……我有时会在景德镇小住,这就使我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这种备受赞赏又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美丽瓷器的制作方法。尽管我以往从未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我相信,对所有关涉制瓷的方法做略为翔实一点的描述,这对欧洲将会是有些用处的。”②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d.1717, pp.253—254.想来,这封信对欧洲的用处不可小觑,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在此信发出后,殷神父又用了十余年的时间“随时记录下”③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d.1724, p.319.按:我虽多方查找可证实殷神父写作这两封信外部动因的资料,惜迄今未果。目前提供的,仅为依照文本逻辑及当时法国特定文化语境所做的推测。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弥补此一缺憾。相关信息,于1722年写出了第二封针对具体问题的补充性信件。
殷神父的信对欧洲制瓷业的最大贡献,恐怕莫过于揭示出“高岭土”的秘密。他在信中写道:“……精瓷的坚实, 完全是由于含有高岭。高岭就像是瓷器的神经。……一个富商告诉我说:若干年前,英国人或荷兰人……买了一些白不子带回国,以烧造瓷器,但因为没有使用高岭,就失败了,就像他们事后所承认的那样。对此事,那个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想不用骨骼,只用肌肉就造出身体来。”④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d.1717, pp.278—279.
作为瓷器“神经”和“骨骼”的高岭土被殷神父揭示,欧洲人才知晓了中国硬瓷的配方,并由此获益。⑤参阅Fourest, op.cit, p.287。其中受益最大者恐怕正是殷神父的同胞们:法国人手上不仅有殷神父的文字描述,且有他以及其他来华传教士寄回的高岭土样本。1751、1765年,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盖达尔(Jean-Etienne Guettard, 1715—1786)两次在科学院宣读论文,称已找到高岭土,并研制出了硬瓷。后一篇论文还正式成书出版,书中详述他如何从杜哈德的书中了解到殷神父揭示出的华瓷配方,并得到来自中国的样品。之后,他又如何通过大量实验在法国找到高岭土与白不子。书的最后,作者对诸多同时代书籍中的相关描述逐一做了点评,批驳了其中的不实之词。⑥参阅 J.-E.Guettard, Histoire de la découverte faite en France de matières semblables à celles dont la porcelaine de la Chine est composée (《在法国发现与华瓷配方相仿物质的历史》).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765。这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时人寻找高岭土的热情与大量投入。1768年,著名化学家马凯(P.-J.Macquer, 1718—1784)经化验证实在利摩日(Limoge)附近找到的黏土确为优质高岭土。从此,法国终于可以生产出堪与中、德相媲美的硬瓷。⑦参阅Jacquemart, Le Blant, op.cit., pp.508—509。
法国人没有忘记殷神父的功劳。1739年,法文词典就收入了“Kaolin”一词,且将殷神父的拼写方法一直沿用至今。⑧参阅 Le Nouveau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e Robert, 1993, p.1441。他们以这种“入典”的方式将殷神父为欧洲制瓷业做出的贡献正式载入史册。而如此“经典化”的认可无疑赋予了该词以权威性,“景德镇”的神话化也由此平添了“神力”,得以飞速发展。
成因二: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崇尚科学,渴求知识
在这样一种追捧瓷器的文化大氛围中,法国著名科学家雷奥米(Réaumur, 1683—1757)自1717年起就对瓷器制造感兴趣,开始了解、调查制瓷业。1727—1740年,他在《王家科学院史》(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杂 志上先后发表了三篇专论瓷器的文章。有研究指出,雷奥米1727年发表的文章显示他深受殷弘绪信件的影响,殷神父描述的制瓷工艺和方法给了他很多启发。此外,他还从奥利神父手上拿到了殷神父辗转带回法国的白不子和高岭土的样品,分析出了这些样品的化学成分,并进行了试验,提出了新的制瓷方法。①参阅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159页。另参阅Guettard, op.cit., p.5。他的方法尽管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却激发了时人对相关问题的兴趣,前文提及的盖达尔正是他的学生。
殷神父信件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法国收藏者普及了中国瓷器的知识方面。前文曾提及杂品商热尔桑在其拍卖目录中也援引了殷弘绪的信。按照热尔桑自己的说法,他很希望对瓷器多一些了解,以便向收藏者们—他潜在的客户—进行介绍,但却苦于找不到相关资料。因为那些去过中国的旅行者们对瓷器都只是泛泛而论,且常常以讹传讹,“只有在华传教士殷弘绪神父,写了一封有关瓷器的很有意义的信”②Gersaint, op.cit., pp.17—18.。于是,我们看到在作者为这本拍卖目录的瓷器部分撰写的专文中,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转述殷弘绪的信。当然,面对非专业制瓷人员,热尔桑还是很聪明地做了取舍:原作关于景德镇历史、地理、环境等的描述,几乎全部保留;而对于原信的技术部分,则只按照生产流程予以粗线条概述,还不时将景德镇瓷器与欧洲的萨克森瓷做一下比较,以调动读者的切身经验,加深对前者的认知。③参阅 Gersaint, op.cit., pp.14—46。
为一本拍卖目录撰写有关拍品的详细介绍文字,这在启蒙时代并不鲜见。而其始作俑者,恰是这位热尔桑。他将自己的拍卖目录命名为《……详解目录》(catalogue raisonné),其中的“详解”二字,实乃热尔桑的独家发明,此前从未有人用过。既为“详解”,就不仅要描述拍品的外形、尺寸,更要解释和说明与拍品相关的知识。这就要求作者搜集、组织所涉及的所有知识,予以分类整理。而这,恰恰生动地表现出了启蒙时代对科学的崇尚和对知识的追求。难怪有学者将热尔桑的所作所为与百科全书派的工作类比,称他丰富和滋养了启蒙理想。④相关史实均请参阅 Guillaume Glorieux, A l’enseigne de Gersaint, Edme-François Gersaint, marchand d’art sur le Pont Notre-Dame (1694-1750)(《热尔桑画店的招牌—巴黎圣母院桥边的画商艾德莫—法朗索瓦·热尔桑传》).Seyssel: Champ Vallon, 2002, pp.387—391。另,首部被热尔桑冠之以“详解”二字的拍卖目录出版于1736年。
殷神父的信出现在这样一本“详解目录”中,也证明了景德镇此时在法国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因为热尔桑认为:目录的出版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告诉公众有关日本和中国古老而美丽的瓷器的起源,如何鉴别其品格,她的成分配料属性,最后还有制作的方式”⑤Gersaint, op.cit., pp.17—18.。而他正是用殷神父的信去达到这种普及知识、引发兴趣的目的的。
由此可见,启蒙时代对知识的渴求也助推着景德镇神话的成型。
成因三:启蒙时代的法国人追求现实、现世的人间幸福
现在再回到殷弘绪那封信的开头部分。他在那段话里除了点明他写信的实用目的—为了对欧洲的制瓷业有用,还部分解释了欧洲制瓷业大发展的缘由:倘若不是欧洲人对那些“备受赞赏,又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美丽瓷器”爱不释手,竞相追逐,怎么会有制瓷业的诞生和发展!
但华瓷为何在18世纪如此受到法国人的青睐?这个看上去似乎仅仅关涉喜好、趣味的问题,却绕不开同时代法兰西民族的思想史和精神生活史。
在史称“启蒙时代”的18世纪,法兰西经历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关键时刻,法国人的思想心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质疑和批判神性;人,从过去生而有罪的神的奴仆,一变而为自己的主人。在从旧有的人与神的关系,向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转变之中,人性得到极大的张扬。法国人冲破传统的禁锢,大胆追求人间、现世的幸福,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追求各种感官“享受”。⑥参阅孟华:《中法文化交流》,载《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或许18世纪对“luxe”(豪华)一词的独特解读可以最完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豪华”的:“这是人们为求得一种愉悦舒适的生活而对财富和技艺的使用。”①Jean-François St-Lambert, “Luxe”,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IX, p.763,1759.此即说,“豪华”已不再是神学家、道德家们所谴责的“恣意挥霍”。人,一旦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就无需再弃世绝俗,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可以,且应该大胆、合理、正当地去追求现实、现世的人间幸福。于是,在18世纪法国人的字典里,如同“豪华”一样,“享受”或“快感”(jouissance)、“富裕”(richesse)、“舒适”(confort)、“愉悦”(plaisir)、“精致”(finesse)、“典雅”(élégance)等词语也都被赋予了追求人间幸福的新意,成为了人们最乐于也最常使用的词汇。而汇总了所有这些词义的“幸福”(bonheur)一词遂成为18世纪的关键词之一。②以上词语在18世纪的独特语义,均请参阅Dictionnaire européen des Lumières(《欧洲启蒙时代词典》),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 Delon, Paris: PUF, 1997。
我们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瓷器,特别是华瓷能博得法国人如此的好感:她的质感、色彩、图案都与典雅、精致、幸福的生活紧密相连。热尔桑在他的拍卖目录中曾用以下词语来描绘一件他认为是“最美的”青花瓷拍品:“她的质地极为细腻”,有“轻柔典雅的白色,无懈可击的蓝色,最后还有精致曼妙的图案”。③Gersaint, op.cit., p.47.热尔桑盛赞的质地、颜色和图案都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感觉有关。而“细腻”“轻柔”“典雅”“精致曼妙”……这些修饰语都再生动不过地描绘出了18世纪的法国人孜孜以求的感官享受。恰如《中国瓷器》一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法兰西民族是享受与求知并重的民族,对她们而言,瓷器这种艺术品,同时满足着精神与眼睛的需求。④参阅 O.Du Sartel, La Porcelaine de Chine(《中国瓷器》).Paris: Ve A.Morel & Cie, Editeur, 1881, p.I。
瓷器因为与典雅生活紧密相连,因而在18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说,那时逛瓷器店竟是一种十分时髦的生活方式,它与去歌剧院听歌剧,参加化装舞会一起,成为了讲究生活品位的人夜生活的一部分。⑤参阅Mathieu, eds., op.cit., p.16。有专家甚至指出,那时的西人之所以为华瓷所倾倒,主要就是因为华瓷“从视觉和触觉上都体现了豪华”(请注意,此处“豪华”的语义恰是在上引《百科全书》给定的意义上),而瓷器上的那些装饰图案也“大大拓展和改变了内心景观”,以其特有的异国情调带给人极大的感官愉悦。⑥参阅Dermigny, op.cit., T.I, p.388。这一评价无疑将热尔桑个人对某件瓷器单品的感受普遍化了,从而在整体上确认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瓷器在感觉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精神文化价值。
与此同时,海外贸易的拓展也为追求人间幸福的法国人提供了物质保障。一方面,咖啡、茶叶等异国饮品的传入,渐渐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而饮食趣味的精细化又反过来推动了对相配套器皿的需求。另一方面,华瓷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⑦参阅Dermigny, op.cit., T.II, p.563。在热尔桑的杂品店中,就存有不少成套茶具,且与茶叶并列放置。⑧参阅 Glorieux, op.cit., pp.270—279。可见生活品位的提高,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都使瓷器受到追捧。法国人对现世、现实幸福的追求,显然为景德镇的神话化运作营造出了最为有利的文化氛围,因而也就大大加速了这一运作进程。
事实上,感觉史与精神生活史、思想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法国人对人生、对世界的观念发生转变时,他们的感官需求、他们的审美眼光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瓷器与这种变化的关系,最突出地就表现在她与罗可可艺术的文化对话中。
三、华瓷在与罗可可艺术的对话中彰显其精神文化价值
18世纪上半叶,法国流行的艺术风格是罗可可(Rococo)。这种艺术风格是在古典主义和巴罗克艺术的对立面上发展起来的。在质疑神性、张扬人性的启蒙时代,艺术从为神权、皇权服务,转而为新兴市民阶层服务。艺术的非神圣化,导致了从建筑、园林,到绘画、室内装饰、家具……都盛行着一种轻飘活泼、愉悦亲切、优雅的风格,这便是罗可可风格。它以丰富的线条、典雅的色彩、非对称性,以及对世俗、自然等题材的偏爱为其美学特征。①参阅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若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概括,我以为或可说罗可可就是一种为人的艺术,尤其是在其初始及上升阶段。
而此时,法国人正痴迷于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和园林,史称“中国风”②国内学界(包括我自己的旧作)一般将chinoiserie译作“中国热”,但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或译作“中国风”更为贴切。。何谓“中国风”?一般的法文辞典给出的释义大多带有些贬义③如《小罗伯尔词典》(Petit Robert) 称之为“源自中国或中国式的小玩意、装饰”。《里特雷词典》(Littré)与此大同小异,但《小罗伯尔词典》特别注明该词1839年才出现,因而这条释义实际上代表的是19世纪—而非18世纪—法国人对中国时尚的价值判断。,唯《大拉罗斯常用词典》(Grand Usuel Larousse)是个例外,特全文照录如下:“源自中国的豪华和新奇物品,或在西方制作的中式物品,以及此类风格的内饰、艺术品、图案。中国风趣味由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17世纪在法国通过大量的瓷器、家具、漆器、丝织品表现出来,随即出现仿制品。瓷器的飞跃发展也部分得益于此风。私人宅邸和城堡中……出现了中式图案。18世纪下半叶此一时尚与罗可可风格同时销声匿迹。”④Grand Usuel Larouss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V.I, 1997, p.1452.这个词条对“中国风”的渊源及其历史沿革做了简洁却全面的介绍,评价亦较为公允。
我们全文援引这一辞条,除了说明法国人如何定义“中国风”外,更希望借此点明瓷器在“中国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最先闯入法国人的视野,调足了他们的胃口,于是才有仿制品的出现,才有法国制瓷业的大发展,才有其他艺术、工业门类的“跟风”。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说瓷器是中国风的“开先河”者。
这个词条还将“中国风”与罗可可艺术相连,可惜只说了它们同时消失的结果,而未提它们彼此相携、推波助澜的光辉历史。
生发于17世纪的“中国风”一直延续到18世纪,而且大有越吹越盛之势。于是她就与罗可可在时间上重叠了,这往往使人将前者视作后者的一部分。⑤我原则上并不反对作如是观。因为“中国风”并非中国艺术本身,它是身处罗可可潮流中的法国人、欧洲人对中国文化选择、接受后的一种艺术形态,是罗可可化了的,理应属于罗可可的一部分。但“中国风”早于罗可可形成,且构成复杂,其中既包括源自中国、流行于法国的工艺品、艺术品,也包括法国人对中国艺术的仿作,更包括他们移植和更新中国元素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如何界定二者关系,确非易事,也超出了本文主旨,故存而不议。它们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或需另文专论,此处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被“中国风”席卷入欧的中国艺术品、工艺品,特别是瓷器,与罗可可邂逅后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对话?这种对话又如何作用于法国人审美趣味的改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人已有诸多研究,但下面这段话却鲜见人提及。鉴于它很好地回答了中法文化对话的问题,有必要把它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翻检出来,重新公之于众:
她(中国风)确曾长期存在过,在一个多世纪里为精神想象提供了最迷人、最多样化的元素…… 她与所有的艺术联姻,无一例外。她为一种艺术提供了变化多端的奇异性和色彩的魅力,为另一种提供了新奇和丰富的装饰原则;又给予第三种生产或装饰方面最明智合理的建议,使我们的教育从此获益。她为欢乐的大众庆典增添了活力,使官方呆滞的豪华节庆平添了生气;她让室内背景更加温馨;又满足了追求奢华和时尚小物品心态的需求。……我们不能说她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她在这个新事物不断萌发的世纪里却融入到了各种艺术和时尚运动之中……⑥Léon Bénédite, “La chinoiseri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18世纪法国的中国风》),in 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装饰艺术杂志》),T.VII, p.380, Paris: Librairie Ch.Delagrave, mars 1887.作者曾长期担任卢森堡公园博物馆(Musée du Luxembourg)馆长,并曾兼任罗丹博物馆首任馆长。
文中所说的“这个世纪”就是18世纪,而18世纪—尤其是其上半叶—最流行的艺术和时尚即为罗可可。这段写于1887年的话,摘自罗丹博物馆首任馆长雷翁·贝内迪特(Léon Bénédite,1859—1925)的大作。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温他对中国风—确切地说,是中国风中源自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对法国艺术影响的评价时,那场中法文化对话的结果也就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了:罗可可从中国艺术中汲取了诸多养料,当为不争的事实。而文中提及的“色彩”“装饰性”“奇异性”…… 哪一样都与华瓷关系密切。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例一:华瓷与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的“中国风”绘画创作
18世纪法国著名画家布歇是将罗可可风格推向极致的一位画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风”画家。他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绘画:《四元素》图(Les quatre éléments,土、水、气、金),《五感觉》图(Les cinq sens,“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中国生活场景》组画(Scènes de la vie chinoise,“ 品 茶 图 ”“ 士 兵 与女古玩小贩”等),《中国系列》组画(La suite chinoise,“中国花园”“中国婚礼”“中国舞蹈”“中国集市”“中国渔夫”“中国皇帝上朝图”等),①《中国生活场景》包括画作甚多,此处列举的仅为核实清楚的两幅。《中国系列》则为布歇专为博韦(Beauvais)织毯厂绘制的组图,所列画作名亦略有缺失。以及一大批此类风格的雕版画和装饰画。这些充满了远东风情的画作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大大丰富了他们对地球另一端那个远东大帝国的想象—一个富庶、幸福的国度。
然而布歇从未到过中国,他据何感知、了解中国?现有研究揭示出,除了各类游记外②早在1960年,Ludwig Dröy就发现了布歇画作《中国婚礼》(Mariage chinois)从结构到场景均挪用了17世纪荷兰人Arnoldus Montanus(1625—1683)在其远东游记《难忘的东印度公司使团》(Gedenkwoerdige Gesantschappen)中刊载的一幅画。1996年,Dröy又发现了更多布歇挪用游记作品插图的例子。参阅Ferrein Stein, “Les chinoiseries de Boucher et leurs sources: l’art de l’appropriation”(《布歇的中国风画作及其来源:挪用的艺术》),in Pagode et Dragon..., pp.86—87。,布歇主要依靠的就是或真或假的中国工艺品,尤其是瓷器。
布歇生前酷爱收藏,他与巴黎专门销售瓷器及各类奇珍异宝的杂品商们关系密切,与前文提及的热尔桑更是私交甚笃。当热尔桑欲将原来的画店改为经销各色古玩杂项的店铺时,他给自己的新店起了一个颇具“中国风”味道的名字—“瓷偶坊”(A la pagode)。为了扩大影响,他向布歇求一幅新店的招牌画,布歇便以《瓷偶坊》为题创作了一幅“命题”画作。③参阅Glorieux, op.cit., p.264。这幅画的正中画了一个有着远东面孔的泥人,他俯首坐在一张漆器柜上,正兴奋地注视着地上堆放着的各式奇珍异宝—新店中即将出售的“宝物”,内中当然不乏中国瓷器。而这个泥人的右手还特意托举着一个中国瓷人,以凸显“瓷偶坊”的寓意。这幅画在法国艺术史上很有些名气,以至于后人出版18世纪巴黎著名杂品商杜沃(Lazare Duvaux,1703—1758)的《销售日记》(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时,特意选用了这幅画作为封里。④热尔桑在法国艺术史上的名声也得益于18世纪另一位著名画家华多(Antoine Watteau, 1683—1721)。早在布歇之前,华多就曾为热尔桑的画店作过一幅著名的油画《热尔桑画店之招牌》(L’Enseigne de Gersaint)。前文所引《热尔桑传》的书名前半段就取自华多的这幅名画。杜沃是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与蓬巴杜夫人(Mme de Pompadour,1721—1764)古玩杂项的主要供货商,布歇也是杜沃商店的常客,后者的《日记》证实:1749—1753年间画家经常光顾此店,购买了大批或真或假的中国货。⑤参阅Lazare Duvaux , 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 marchand bijoutier ordinaire du roy, 1748-1758(《国王御用首饰商拉扎尔·杜沃销售日记》).Paris : Pour la 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français, 1873。最能证实布歇对瓷器热情的,恐怕莫过于他死后藏品被拍卖时留下的目录,内中记载的中国艺术品—特别是瓷器—数量惊人。在全部1865件藏品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工艺品,其中又有将近一半与中国有涉。而总共二百余件的陶瓷器物,半数以上为华瓷或仿华瓷、外销瓷、紫砂等,还细分为古瓷、彩瓷、青花瓷、开片瓷、裂纹瓷……另有瓷雕作品22件。⑥参阅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tableaux, dessins, estampes, brouzes, terres cuites, laques, porcelaines de différentes sortes...qui composent le cabinet de feu M.Boucher, premier peintre du roi(《国王首席画家、已故布歇先生藏品详解目录》),A Paris,chez Musier, 1771。除瓷器外,布歇还收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国漆器、家具、牙雕、绘画、金银器、玉石玛瑙器等。布歇对华瓷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一个名画家大量收藏瓷器,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兴趣?布歇的画作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在《棕肤色宫女》(L’Odalisque brune)、《穿袜带的贵妇及其女仆》(Dame attachant sa jarretière et sa servante)、《女帽商或清晨》(La Marchande de mode ou Le Matin)等作品中,瓷器都不失时机地出现在画面一角,既烘托出18世纪的“中国风”,增加了画作的时尚性;又提升了画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品位,使其更显优雅。布歇的名作《午餐》(Le déjeuner)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幅画描绘了一位时髦优雅的女士和她的女儿正在仆人的伺候下享用午餐,她们围坐在一张黑红两色的漆器餐桌旁,桌上摆放着一套精美的瓷器餐具,以表现女主人时尚而精致的生活。而在画面左侧的置物架上,画家又画了一把漂亮的瓷壶和一个泥塑的大肚子弥勒佛—法人称之为“magot”(读音“马佝”,意为“古怪的矮胖瓷人”)—“中国风”中最流行的工艺品之一。
瓷器不仅出现在布歇的画作中,更重要的是还为他提供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养料,成为他创作“中国风”绘画作品的样本。①参阅 Stein, op.cit., pp.87—94。在布歇的“中国风”画作中,从服饰、器物到整个场景布局,从人物相貌、体态到情感韵味……画家都从华瓷中汲取了大量中国元素,并将其创造性地融入罗可可风格中,向18世纪的法国人展现出一幅幅色彩绚丽、诗情画意、精致典雅的布歇式中国风俗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调色板”也开始发生变化:蓝色、浅绿色、粉色、黄色……诸多华瓷和其他中国工艺品喜用的颜色都出现在布歇的画作中。②参阅Ibid., p.92。更有法国学者认为,布歇在“中国风”画作中甚至使用了一种独特的“仰角透视”,而这恰是在华瓷画片上经常能见到的。③参阅Marie-Laure de Rochebrune, “L’inspiration chinoise à la Manufacture royale de porcelaine de Vincennes-Sèvres”(《中国对万塞尔—塞夫勒王家瓷厂的启迪》), in Pagodes et dragons.., p.113。本文作者为卢浮宫艺术品部主任。以上这些实例都清楚地说明了布歇的画作不仅大量“挪用”、借鉴、汲取中国艺术,而且让“中国风”为罗可可艺术做出了大贡献。借用龚古尔兄弟(Edmond et Jules de Gongourt)的评论,他简直就是“将中国变成了罗可可风的一个省”。
尽管龚古尔兄弟这段话透露出19世纪欧人的某种殖民心态,但它直接论及了华瓷与罗可可、布歇的关系,仍值得介绍,特摘译如下:“18世纪崇尚的冒险国度—中国,曾带来了青花瓷、天青色瓷(bleu céleste)、开片瓷、碎纹瓷,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精妙的珍宝。……布歇的想象在这个小小的幻想国度里嬉戏游乐,忘乎所以,不顾当时批评家们的谴责,满怀爱意地往纸上、画布上、门框上方、扇子上、画商的招牌画上尽情挥洒着这些从华多④1718年左右,华多在拉米耶特宫(Château de la Muette)为路易十五绘制中国风装饰画,布歇曾为华多雕版,由此开启了他后来的“中国风”绘画创作。参阅 Stein, op.cit., p.89。那里借鉴来的巴罗克服饰和面孔。在蓬巴杜夫人首席画家的手中,这些服饰和面孔将中国变成了罗可可风的一个省。”⑤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L’Art du XVIIIe siècle (《18世纪艺术》).Première série, Paris: G.Charpentier Editeur, 1881, p.244.龚古尔兄弟在这里点明了华瓷在罗可可艺术中的地位,更明确指出瓷器是布歇想象中国的主要来源。不过,也正像他们所说,布歇笔下的中国,更多的是他的想象和创造,是他营造出来的“幻想国度”。⑥Stein的研究指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布歇喜爱中国艺术,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所以他会依照观音像画出了“中国农妇”,又将弥勒佛作为中国“医生”的原型。参阅Stein, op.cit., p.93。
布歇在18世纪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合作者、雕版画家于吉耶(Gabriel Huquier, 1695—1772)、他的学生于埃(Christoph Huet,?—1759)、他之后的装饰画家彼耶芒(Jean-Baptiste Pillement,1728—1808)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于吉耶将布歇的作品制成雕版,大大扩大了其影响面;于埃、彼耶芒们则模仿、继承其画风,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了中国风的生命,扩展了其影响力。
例二:华瓷与法国瓷器的创新与发展
几乎所有的法国瓷史都对早期法国瓷厂仿制华瓷的事实“供认不讳”。专家们指出,鲁昂瓷厂早在1644年就以荷兰Delft为榜样,仿造青花瓷,并在自家产品上仿照康熙朝瓷器上的画片描绘中国场景。而到了“1725年左右,所有的法国瓷厂都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仿制中日瓷器的艺术之中”①Emmanuelle Gaillard, Marc Walter, Un certain goût pour l’Orient: XVIIIe et XIXe siècles(《18、19 世纪欧洲的东方趣味》).Paris: Citadelles & Mazerod, 2010, p.39.。
始建于1725年的尚蒂伊瓷厂,初期的器形均仿中日瓷,制出了青蛙状的茶壶、桃形盘、花熏、瓷雕等;阿朗松(Alençon)仿中国外销瓷;斯特拉斯堡是法国较早能生产硬瓷的瓷厂,1766年即生产出了饰有中国风图案的硬瓷瓷器……②本节所涉法国瓷史内容均参阅Fourest, op.cit.;Chavagnac et Grollier, op.cit.。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加诸法兰西民族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各地瓷厂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
在这方面,可以万塞尔–赛佛乐王家瓷厂为例。这座始建于1738年的瓷厂从1750年左右就从中国瓷器作品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各种创作灵感,且将这种学习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③参阅Rochebrune, op.cit., p.112。这种吸收–创新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研制新颜色和设计新图案方面。
就颜色而言,赛佛乐瓷厂初期多仿制中国白(即德化白瓷);18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出了一系列颜色釉的独特配方:先是青金石蓝(bleu lapis);随后又是天青色(bleu céleste)、水仙黄或淡黄(jaune jonquille)、紫色、麻灰色、绿色,以及以蓬巴杜夫人命名的“蓬巴杜玫瑰粉”(rose Pompadour)。④参阅 Fourest, op.cit., pp.240—241。
在这些颜色中,我以为最值得一书的,当数被称作“bleu céleste”的颜色,直译为“天蓝色”。但因其命名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似有必要对其译名略加斟酌。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殷弘绪的信中,原文是这样写的:“《县志》称,古代的瓷器洁白无瑕,传入他国者从前都被叫作饶州宝玉。后文又补充说,有着亮丽白色与漂亮天青色(bleu céleste)的美丽瓷器均产于景德镇。其他地方也产瓷,但其色泽与精美程度却全然不同。”⑤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XV, 1717, p.259.此段译文直接从法文译出。考虑到殷神父所描述的“美丽瓷器”是白、蓝两色并存的,而景德镇又以青花瓷著称,加诸前人对景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之词,故此处似译作“天青色”较为妥帖。
然而,赛佛乐瓷厂自行研制出来的bleu céleste毕竟不是制作青花瓷的蓝色。法国专家们说,它是专为路易十五1753年至1755年定制的餐具而创设的。烧出的釉色略泛绿色,呈绿松石蓝色(bleu turquoise),比青金石蓝颜色稍浅。瓷器表面光滑,其釉色与亚光金边及彩色图案相得益彰,搭配十分和谐。⑥参阅Jacquemart, Le Blant, op.cit., p.524;Rochebrune, op.cit., p.113。按:我曾将一些图册中的bleu céleste瓷器与华瓷比对,感觉这个颜色比青花瓷的蓝色要浅,微泛绿色,似更贴近康熙朝颜色釉中的“孔雀绿”,但较之似乎也还要更浅些,是一种典型的极为优雅的罗可可颜色。所涉图册包括:Fourest, op.cit., p.269, 图222;Mathieu, eds., op.cit., p.19, 图 1;La Porcelaine française du XVIIIe siècle(《18 世纪的法国瓷器》,Lille: Edition de l’Association des Conservateurs de la Région,Nord-Pas-de-Calais, 1986,图 83。
对这个颜色的命名,卢浮宫艺术品部主任M.-L.德·罗什布吕纳(M.-L.de Rochebrune)认定它本身即已明确标示出其中国渊源,因为内中的céleste一词直接源于18世纪法人对中国的称谓—“天朝帝国”(Empire céleste)。⑦参阅Rochebrune, op.cit., p.113。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又称在18世纪上半叶的拍卖目录中,该词也指称绿松石蓝釉的中国瓷器。如此说来,赛佛乐厂研制的bleu céleste或译作“天朝蓝”更为贴切?否则如何凸显出该词语义中蕴含的“中国”之义?
据说“天朝蓝”深得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的欢心,国王曾向万塞尔—赛佛乐厂先后订购了1740件“天朝蓝”餐具,一时传为美谈。⑧参阅Mathieu, eds., op.cit., p.22。蓬巴杜夫人也经常选购“天朝蓝”。仅1745年6月23日,她就一次性在杜沃商店购买了10件价值3167利弗尔的“天朝蓝”瓷器。①参阅Duvaux, op.cit., T.II, p.205。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趣味导向,“天朝蓝”在18世纪50年代很是红火了一阵。《法国瓷厂史》称,赛佛乐瓷厂1753年“年底,销售了数量巨大的‘天朝蓝’”②Chavagnac et Grollier, op.cit., p.151.;而杜沃的《销售日记》则显示,直至1758年店主辞世止,该商店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销售“天朝蓝”。③参阅Duvaux, op.cit., T.II, pp.149—385。其实在杜沃身后,赛佛乐厂仍然继续生产“天朝蓝”。《欧洲陶瓷》一书刊载的一幅“天朝蓝”瓷器图片标注的生产日期就为1778年。
在图案方面,华瓷也一直是赛佛乐厂重要的创作源泉之一。早期的万塞尔厂从德化瓷中汲取灵感,在白瓷餐具上饰以凸起的李子花图案。而18世纪60年代生产的“中国风”瓷器上又都绘有牡丹、菊花这些典型的中国花卉图案,据说其主要来源便是当时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的广彩。④参阅Rochebrune, op.cit., p.112, 114。众所周知,外销瓷中多广彩。这种在国内并非上品的瓷器种类,反而在异国他乡大受欢迎。法国人更是在广彩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各种变异体,使其成为法国瓷器中的一朵奇葩。这显然与法国人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的审美趣味直接关联。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接受现象,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提及图案,就不得不提画片。万塞尔—赛佛乐瓷厂自创立起一直生产绘有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瓷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尤甚。⑤时任国王驻厂特派员的,是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国务秘书贝尔丹(Henri Bertin, 1720—1794)。他不仅自己大量收藏华瓷,而且因为对中国有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两位中国青年(高仁、杨执德)参观赛佛乐厂,并委托他们将该厂瓷器作为礼品赠与乾隆皇帝。参阅Rochebrune, op.cit., p.115。据专家们考证,这些表现中国人生活的画片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经由各种途径流入欧洲市场的华瓷,二是当时“中国风”画家们的作品。这第二种来源尤其值得关注。被仿的作品以布歇与于吉耶合作的各种“中国风”版画为主,而《中国生活场景》组图则是被仿频率最高的作品。⑥参阅 Stein, op.cit., p.93;Rochebrune, op.cit., pp.114—115。除了瓷器上的画片,这些作品还是赛佛乐厂生产的瓷雕作品的样本。布歇笔下“中式”的美丽少女、嬉戏顽童、欢喜老翁……就这样通过工业产品的批量复制,出现在各式日用器和陈设器上,并随之走进了法国的千家万户。
如此一来,以上两个实例就被布歇奇妙地连接起来了:布歇借鉴华瓷创作出“中国风”作品,这些作品又影响了王家瓷厂的画师们,成为他们制作罗可可—中国风作品的创作源泉;而这些“中国风”瓷器,无论其器形、釉色,还是纹饰、画片,都大大丰富了法国瓷器的种类,提升了其质量,同时也以创新和发展的面貌积极参与到了中法间的那场文化对话中去。
赛佛乐瓷厂与华瓷、布歇、中国风、罗可可艺术间这个有趣的接受圈绝非特例。一如专家们所指出的,18世纪,法国所有瓷厂都多少采纳了布歇们创作的中国风装饰图案。⑦参阅Stein, op.cit., p.97。而布歇喜用的那些中国颜色也被半数以上的同时代画家们所分享,以至于专家们称这些源自中国的颜色最终变成了“18世纪的颜色”。⑧参阅 Bénédite, op.cit., p.371。作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罗可可画家,布歇在中国艺术中找到了最符合时代美感的大量丰富的元素,并把它们创造性地移植入罗可可艺术中。
因为时间的重叠,更因为美学取向的吻合,为中国风开先河,且成为其重要组成成分的瓷器,也就为罗可可艺术输送了大量养料,成为罗可可汲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而瓷器自然也在这种文化碰撞中大放异彩。那些千姿百态的精美瓷器,从感观与实用两个方面满足着正在追求现世、现实幸福的法国人的需求。而在他们品茗用餐、梳妆打扮中,在他们点燃花熏烛台、观赏瓷瓶瓷雕时,他们对美的感受,对幸福的理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东印度公司的瓷器》一书的作者说:“进口瓷难以觉察地改变着人们的艺术观念”。⑨Bourdeley, op.cit., p.5.此言甚是,只不过,这句话的主语还需略加改动:不只是进口瓷,法国瓷厂在景德镇神话化过程中的仿作,他们吸收华瓷精华创新后的产品,难道不是同样也都参与到这种艺术观念和感观改变的活动中去了吗?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不同文化会带来感觉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在与异质文化碰撞、对话的过程中,传统一定会发生改变,注入新的元素,获得新的生命,并由此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在法国人观赏、使用、收藏华瓷的过程中,在法国瓷厂仿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眼光在审视、学习和思考中就渐渐发生着这样的变化。这,或许就是景德镇神话得以成型最根本的原因。它也揭示出了华瓷在法国感觉史上特殊的思想文化价值,因为感觉史离不开精神生活史、思想史,甚至应该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尾声:“景德镇神话”的继续
1856年,就在殷神父信件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之后,《景德镇陶录》法译本出版了。译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在“译者序”中,儒莲明确表示是时任赛佛乐瓷厂厂长的埃伯乐蒙(Eblemen)先生建议并鼓励他翻译此书的。①参阅Stanislas Julien, 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中国瓷器的历史与制造》,即《景德镇陶录》法译本).Paris: Mallet-Bachelier, Imprimeur-Libraire, 1856, pp.LXI—LXIV。
埃先生确实是个有历史感、有眼光的领导,他不仅深知赛佛乐厂从华瓷中获益良多,而且深谙景德镇与他的工厂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据《瓷史》作者考证,万塞尔厂的创立离不开殷弘绪的信,因为“长期以来,巴黎地区就存在着想建立一座堪与萨克森厂相匹敌的瓷厂的愿望。而殷弘绪神父的信提供了如此完整的技术描述,确保了这一愿望得到满足”。②Jacquemart, Le Blant, op.cit., p.500.
译者儒莲同样也不敢忘记他的前辈殷弘绪神父,不敢忘记那封被反复传抄、转引,脍炙人口的书信。他在“译者序”中,依然大段大段地援引殷神父的信来介绍景德镇。这既是用“景德镇神话”来为自己的译作背书,又以此昭告世人:他正沿着殷神父的路,续写着景德镇神话……
时至今日,法国任何一本论及瓷器史、瓷厂史的书都不能不提中国,不提景德镇。已经神话化了的景德镇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永远存诸中法文化交流的史册中和现实中。那些美丽的瓷器,是这个“神话”得以“形塑”的基础,同时也因这个“神话”而愈发诱人。
作为全文的结束,让我们依旧回到开篇时引用的《赛佛乐瓷器》一书中去。在这本书的历史回顾部分,作者这样写道:“细腻柔和的触感、精致半透明的白色、悦耳的声音,瓷器一直让人感到惊讶,令人着迷。……她从诞生之地中国进入欧洲,自18世纪起得到了真正的新生和充分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复杂艺术的表现方式,并且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现象。”③Mathieu, eds., op.cit., p.8.
——走进景德镇 “皇家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