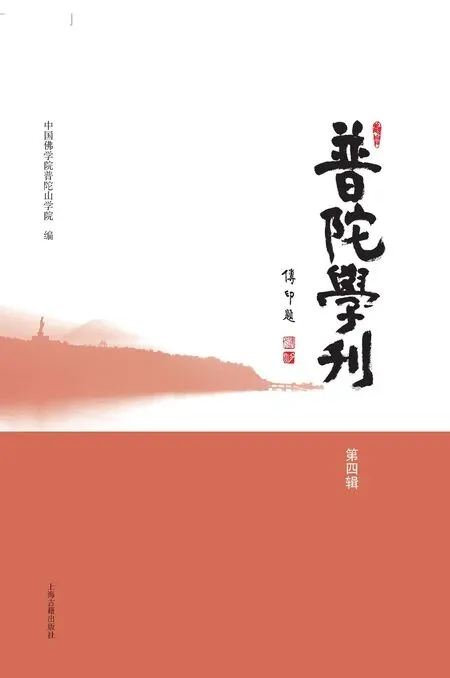佛学的现代转轨
——梁启超早期应用佛学思想探寻
张 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梁启超是属于清末民初时代的人,他在政治上的经历虽有些复杂,但在学术上可称得上是一位著作等身、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及一些其他类型的著作常被人称引,说明了梁氏著作自蕴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光芒和魅力。他的思想多变,以“日新又日新”为特征,其佛学思想也概莫能外。学者大多将梁启超与佛学接触的生涯分为四段:第一段为梁氏早年求学至戊戌变法失败的期间(1891─1898);第二段为梁氏逃亡日本期间(1898─1912);第三段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氏回归国内参与政治活动(1912─1918);第四段是梁氏自欧游回国后一直到其去世为止(1918─1929)。其中前二段可谓梁启超早年佛学思想成型时期,而第一段则是他接触清末维新同志学佛思想最多亦最活跃的时期,第二段是他在日本流亡时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同志思想的冷静省思与总结;至于后二段则是进入民国后他对佛教的兴趣和研究,尤以第四段基本上是他转入学界后在书斋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这前后几个时期中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变化是很大的,难以笼统言之。本文立足于前二段,主要探讨梁启超早期的佛学思想,至于后二段的佛学思想将另文论述。*参王俊中:《救国、宗教抑哲学?——梁启超早年的佛学观及其转折(1891—1912)》,载《史学集刊》总第31期,1996年第6期,第93—116页。进入民国后,梁启超对于宗教和国家概念颇有新的认识,尤其于1920年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这个时期成为他佛学著作最多产的阶段,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乃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至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而他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也就在于此(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 早年的师友学佛缘
清末维新人士在不愿意“全盘西化”,又面临“学问饥荒”的情况下,试图找寻一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理论。于是他们多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佛学作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条“伏流”,是著中,他从龚自珍、魏源谈到康有为、谭嗣同,乃至章炳麟,指出他们都喜好谈论并推奖佛教,包括他自己,“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此中列举的都是晚清思想界荦荦大者,其实,清末维新人士中因学佛而著名者尚有不少,诸如唐才常(字绂丞,1867—1900)、汪康年(字穰卿,1860—1911)、夏曾佑(字穗卿,1863—1924)、宋恕(字燕生)、孙宝瑄(字仲愚)等,他们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诸君子既倡维新,又相与鼓吹、相互影响而促成一种学佛的风气以至思潮,基本上形成清末的一个思想共同体,尽管这只是一种“伏流”,但惟其如此已令人感到暗潮汹涌的澎拜。
京城佛学风气的形成大概缘起于1894年甲午战败的刺激,因思想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崛起中“佛教隐为助力”,又西学之流行与佛理“暗合”。谭嗣同对佛学最初发生兴趣可能就是1895年前后他在从事维新变法运动时接触到京城诸佛学名士,如其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就谈到:“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微契矣。”*《上欧阳中鹄书》十,参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初版,第461页。谭嗣同推尊吴雁舟为其“学佛第一导师”,他在《送吴雁舟先生官贵州诗叙》中称其为“雁舟禅师”。*参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初版,第247页。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从事维新运动,邀请梁启超来做总教习,其周围集聚了一批同志也都常常谈论佛法,如唐才常、刘淞芙、毕永年诸同志。杨文会之子杨自超(葵园)也来学堂担任一些事务。*其中唐才常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并且是一起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的同志,他在思想上受到谭嗣同很深的影响,同样十分推崇“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他也认为“微点(质点)者,释家之微尘也。……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欤!”参《唐才常集》之《辨惑上》、《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篇,转引自楼宇烈:《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谭嗣同在给欧阳师的书信中称唐才常、刘淞芙诸同志“皆上上等根器之再来人也,然不通佛学,则堕落地狱亦不甚难,惟大力扶掖之耳”;在致汪康年书中称其“慈悲如佛”。参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初版,第468、512页。
梁启超与佛教的相遇,很难从他的个人内发的精神史上明确其关联。但可以认为他是以师友交往及读书与佛教相遇的。师从康有为和结识谭嗣同,开始使梁启超与佛教进行了知识的交流。康有为的《大同书》固然与公羊学、“西学”关系密切,但和佛教的“众生平等”说似乎也不无关系。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就是从佛家的“无我”说中引申出来的。因此说梁启超在师友们的影响下,也日益热心于佛学,这大致不错。梁启超最早接触佛学,就是他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的时候。康氏“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62页。当时他和同学陈千秋(字通甫,1874—1895)“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师)决疑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时为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十八岁。此时佛教对他的影响不大。梁启超真正对佛教产生兴趣并于生活中有所实践是在赴京沪从事维新运动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北游京师,交夏穗卿、谭嗣同、吴季清、吴铁樵父子,“则一时喜谈龚、魏之学,亦涉猎佛教经论”。*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梁启超北上赴京追随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夏天又转赴上海,筹办《时务报》。在沪上期间,他与汪康年、谭嗣同、吴嘉瑞、孙宝瑄、宋恕、胡惟贤(字仲巽)等同志过从甚密,相与论佛。据说在上海,他曾听吴嘉瑞(雁舟)等讲演佛法。
维新志士不仅从事维新事业,而且相与学佛,致力研讨佛学,他们的活动区域大致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湘鄂。从孙宝瑄的《日益斋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梁启超与维新志士们在上海热衷佛学的一角情景:“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今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二十四日,诣时务报馆。(中略)俄吴雁舟来,与卓如及余同至徐园,花石盘绕,亭榭极闲,三人茶话。余问:成佛之后堕落否?雁舟曰:一悟不再迷……”*参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册,第57页。另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所记述,“丙申(1896)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吴雁舟、曰谭复生、曰宋燕生、曰梁卓如、曰汪穰卿、曰胡仲巽、曰孙仲愚,其人多喜圆教,统志游觉海,一日皆于光学中现身。乃为偈云: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可见这批维新志士人对佛学的崇尚。梁启超与维新志士们讨论佛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认为格致之学“暗合佛理”可以借佛学而行,而西学传播又可使人“尊重佛书”,于是佛学、西学并行于世;同时也讨论有关迷悟与成佛问题。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有两封书信表明他已修习佛教并将佛学引为谈资:一是《与碎佛书》,二是《与吴季清书》。细读此二书并涉及相关材料,便可进一步深入了解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的学佛交游及其佛学进境。梁启超之《与碎佛书》写于丙申腊长江舟上,丙申腊即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腊月。此信对象是夏曾佑,因其号“碎佛”。梁启超写信的缘起,大概是他从夏曾佑致汪康年书中获悉其近状,“云何失馆,而栖萧寺,穷岁客况,闻之凄怆”。对于夏曾佑的窘境,梁启超等维新志士都伸出援助之手,接济其家庭生活。但梁启超更倾向于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理解夏君的境况,他说:
今岁以来,侪辈之中,咸稍苏息,独君郁郁,穷蹙益甚。惟超知君,已将渐次入不动地,大法成就,必有因缘。缘虽非一,大抵由困苦患难,而断五欲。始教修行,观一切苦,虽复善观,未若身历。世尊自言,“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何以故?地非淤泥,不生莲花;非五浊世,佛不现故。是以非惟不起厌憎,亦且常乐五浊地狱。兄之根器,非复一世数十寒暑之所获,乃从前劫而积善因。虽复如是,小脑大弱,魂为所牵。诚恐一旦不自割舍,境风熏吹,住位将退。梵天哀愍,现种种集,导种种灭,代除世间种种无常,策君精进,起君回向。是故当知非特如是,他日无量苦恼,百倍今日而集君身,何以故?六根我贼。世间一切父母妻子、功业名誉、顺适供养,悉贼党与。党与摧落,贼自灭故。众生迷惑,认贼作子,代贼受苦。若复知者,一切诸苦,皆贼造作,还贼自受,我无与故。凡所陈说,悉皆闻之于君。*梁启超:《与碎佛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11页。
梁启超这是用他从夏曾佑那里听来的佛法根本义谛即四圣谛与因缘观来讨教,这既表示他对夏曾佑栖居萧寺苦况心境的同情理解,也反映他初学佛法时对出世入世之间的一些矛盾困惑。尤其提到“六根我贼”,吾人之无量苦恼、众生之迷惑,皆由于“认贼作子,代贼受苦”,把世间的一切名闻利养看成“贼之党与”,能摆脱这些,“党与摧落”,贼即自灭。这种“认贼作子”即众生迷失真性而不自觉的佛法理论,出典是近世较为流行的《楞严经》。《楞严经》有云:“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参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首楞严经》卷第一之下,该经全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宋首楞大师可度有《笺首楞严经》,笺云:“因由汝之无始,至于今日,认贼作子,失却元来真常之心,故受轮转。法上若认真心为心,成佛有期。若执能推者为心,何殊认贼为子?所有法财功德,一时偷将,然后不免轮转生死。”
梁启超在书信中又告诉夏曾佑说:“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吴嘉瑞)雁舟演述宗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苦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梁启超:《与碎佛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11页。信中所示,梁启超夏天听闻了夏曾佑的说法,接着又听吴雁舟“演述宗风”,他跟从前不一样发了大心,要好好地深入钻研经论,但是苦于不能摆脱世俗的牵缠束缚,无法真正解脱自在,“贼念”与“善念”交相为战,想来这可能是自己根基浅薄,“宿业未尽”。不过自与夏君别后,倒还能依夏君所教“略集经论”、“颇守戒律”,说明他此时已有了一些基本的修行。
大概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梁启超的佛学水平还不是很高,这从光绪二十三(1897)年三月十日他给夏曾佑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睱望如天上也。……专望兄书,以救我魂,兄其念哉!”*梁启超:《与穗卿大师书》,参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册,第75页。梁启超在这封信中向夏曾佑叹苦经:“大为人事所累”,“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近来更有“堕落之惧”,从早到晚无片刻闲暇,静坐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读经了。他恳求夏君帮助,以重起善心学佛,“以救我魂”。
夏曾佑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可惜他没有留下专门论述佛教的著作,无法深入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但从梁启超对夏曾佑的推崇备至中可窥得一二。梁启超说:“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他是假。我十年来久想仿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体例著一部《佛顶楞严经疏证》,三年前见穗卿和他谈起,他很高兴,还供给我许多资料。我这部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请教我的导师了。”*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9、23页。该文写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4月23日夏君死后六日。梁任公在该文中称“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若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梁说十九岁时始和穗卿相识,他们两个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穗卿为什么自名别士呢?此源于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较“兼士”,非墨家便叫“别士”;梁心醉墨学,所以自号“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则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吧”,因此自号别士(见书第22页)。这段话是梁启超在夏曾佑死后所写,此中提到《楞严经》真伪问题,可以印证他以前“认贼为子”的佛学思想确来源于该经不虚。
梁启超与吴季清、吴铁樵父子二人交游学佛,过从甚密。*谭嗣同曾作《吴铁樵传》曰:“铁樵死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年三十二。嗣同初不识铁樵,亦于京师偶见之,片言即合,有若夙契。嗣同甚乐铁樵,又钦其父名,因铁樵请见,连不值。既得见,则三年前对语终日而各不知姓名之季清先生也。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铁樵亦大诧,以为奇遇。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甚密,偶不见,则互相趋。所谓燕赵之士,任侠重诺者,益相助物色而罗致之。”参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初版,第258页。《与吴季清书》写于吴铁樵死后未久,梁启超意在安慰吴季清,由于是平常学佛的朋友,所以就着眼于从佛法来开导。在此书信中梁氏开宗明义就向吴季清提出“生天成佛”问题,问其信不信有生天成佛之说,若信有,那么,“欲生天成佛,其道何由?”梁启超认为,“必厌离世间五浊臭秽,脱屣躯壳,修菩萨行,此不二法门也。故以我佛慧力,而必现出家身以度众生,谓学道人固应尔也。公之悲不可解,超无他言,请公读《本行集经》太子出家品。(中略)今夫铁樵出家之念,不自今日始也,又非彼一人独也。若穗卿,若复生,若启超,皆久发此愿,苦无机缘耳。铁樵之未遇机缘犹吾辈也,彼此次与超同由鄂来,在船上言之详矣。彼此念视我辈尤坚也,然使其不死,十年之内亦必有出家之事。(中略)天下之苦恼未有不生于躯壳者。躯壳与躯壳日相处,则苦恼如丝织,日结日深而不可解,此有家之为害。超既屡为公言之,彼死者有何利益胜于我辈,所不敢知,然于此间苦已脱离无量矣。我辈方且力求解脱之法,而宁能以彼之大乐者为我之大苦?何其大惑耶!此非寻常达观劝慰之言,我辈所日日讲求者正复在此,不可忘宗旨耳。”末了,梁启超请吴季清读《楞严经》前四卷,反复玩味,以遣痴心。梁自注曰:“以佛法言之,只得谓之痴。”*梁启超:《与吴季清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12—113页。由此可窥梁启超当时的佛学知识及其所关心的问题、所涉猎的经典。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作《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依康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始教之言,内中有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卫生等项目。其立志,将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也”与佛言“众生未尽,誓不成佛”相提并论。梁启超于此说,学者当思国之何以弱,种之何以微,众生之何以苦,皆由天下之人莫或以此自任也。我徒此责人之不任,何不自任矣?《论语》曰:志于仁,又曰:仁以为己任。此志既定,颠扑不破,读一切书,行一切事,皆依此宗旨,自无挂碍、无恐怖。对于传教,梁启超则说,“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奇悍无伦。而吾教六经舍帖括命题之外,诵者几绝,他日何所恃而不沦胥哉!”“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也。吾党丁此世变,与闻微言,当浮海居彝,共昌明之。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33—34页。梁启超从保种、保教的角度谈到佛教,重视佛教的救世精神,强调佛教、耶教之行而吾(儒)教之微乃在于“无传教之人”,故此特立传教一项。
综上所述,可对梁启超早年接触佛教的情况做如下分析:1891年,梁氏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师事康有为,受康有为研究佛学的影响较深,但当年梁仅十九岁,人生经验尚浅,对佛教空、无常之说难有切实了解,是可想而知的。日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只能言道“余夙根浅薄,不能多受”。这时除了在他年轻的心中将公羊派经世之学和佛教普度众生思想结合起来,激发救国救民精神外,对佛学的了解当还有限。梁氏真正初尝佛学甘旨,而有所得,还是甲午战争后在京沪等地从事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与友人谭嗣同、夏曾佑、汪康年、孙宝瑄等讨论佛学与西学,颇感兴味。此段时期梁启超充满了发掘新知以拯救国难的使命感,拼命补充他自认为在知识上的不足之处,不仅佛学,他还同时学习中外历史、拉丁文、算学等。这时他之所以对佛学感兴趣,主要的恐怕还是受到周围维新志士师友学佛风气的影响。但他因忙于维新事务,为世事所牵缠,几乎无暇读经、坐禅,对佛学研究还不深入。不过,他从1891年到1897年这六七年间的确在研习佛学方面下了功夫,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这使他得以在变法失败、亡命海外之后,从1899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有关佛学的论文,逐渐形成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
二、 戊戌政变后潜心研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告终结。戊戌政变失败后,志士星散,康、梁逃亡海外,远渡日本。对于梁启超而言,流亡日本虽然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挫败,但也提供他机会亲身见识日本是如何积极学习西方经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透过日本人对西学的介绍和翻译,并冷静反思戊戌变法的血的教训,梁启超不仅对政治,而且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等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在佛学方面,梁启超已超越了过去仅从政治角度来发挥佛教的救世精神,他还高瞻远瞩地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佛学,把佛学放在学术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比类理性的哲学,并与科学相调和,极力阐发和推崇佛教适合于现代人信仰的积极部分,而淡化其中的迷信成分。可以说,这段客居日本是其佛学思想发展和完善的一个极佳时期,因为此时的日本由于受西学的影响亦产生了新的佛教观和方法论,比如日本当时的佛学界注重佛学学理和佛教历史的探讨,这也许启发了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来研究佛学。
梁启超之致力于把佛学系统化为于国家、于民族有积极作用的理论武器,这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关,也与他在日本获得的新视野和新感受有关。这体现在戊戌政变后他写成的一些有关佛学的论文或专文中,诸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写成的《论支那宗教改革》和《自由书·惟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撰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其他在《谭嗣同传》、《仁学序》(光绪二十四年)、《南海康先生传》(光绪二十七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光绪二十九年)及《余之生死观》(光绪三十年)中亦论及佛学。从以上著述列单中,可见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间佛学思考最勤,成果颇丰。其论域亦较宽,涉及佛学在近代社会文化中的多面向考虑。现将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的主要佛学思想梳理如下。
1. 倡言“宗教改革”和“除心中之奴隶”
1899年,梁启超受姊崎正治君邀请到贤哲荟萃的哲学会发表演讲,他依据康有为先生思想谈论两个问题:其一关于支那,以宗教革命为第一着手;其二关于世界,以宗教合统为第一着手。梁启超在会上就谈了第一个问题,后者未来得及谈。对于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说:“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汁之药疗也。我支那当周秦之间,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而自汉以后二千余年,每下愈况,至于今日而衰萎愈甚,远出西国之下者,由于误六经之精义,失孔教之本旨。贱儒务曲学以阿世,君相托教旨以愚民。遂使两千年来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见。此实东方之厄运也。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梁启超祖述乃师康有为发明的孔子之教旨,提出孔教的六个主义:一曰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二曰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三曰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四曰强力主义非文弱主义,五曰博包主义非单狭主义,六曰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引人注意者,是以佛教大乘小乘来比之大同小康,“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往往相反,耽了小乘者,闻大乘之义而却走。且往往执其偏见而攻难,疑大乘之非佛说。故佛说《华严经》时五百声闻无一闻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所得闻。既不闻矣,则因而攻难之。”其第三说孔教乃兼善主义,则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说法四十九年,皆为度众生”,以与“孔子立教行道亦为救民”相提并论。其第五说孔教乃博包主义(即相容无碍主义),梁启超照样以佛教来诠释,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华严法界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55— 60页。梁启超如此以佛教来诠释孔子之大同教,除了说明他深受老师康有为思想影响之外,只能说明他认识到佛教和孔教在思想上和宗旨上有许多类似性,另外也反映出他特别推崇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和博大包容性(他称之为“博包主义”)。梁启超推尊佛菩萨行之积极精进的救世精神,其依据便是“三界惟心”之真理。
同年,梁启超写成《自由书·惟心》一文,未久在1900年3月《清议报》上发表,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可见他与龚自珍、谭嗣同等人一样,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对于“三界惟心之真理”,他引用禅宗史上著名的风动还是幡动争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有二僧因风飘刹幡,相与对论,一僧曰幡动,一僧曰风动,往复辩难无所决。六祖大师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梁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45— 46页。以前学者注意引用梁启超这段文字,大都着眼于批判其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唯心主义思想。其实,梁启超之所以十分重视三界惟心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受外界事物和个人喜怒哀乐的干扰,心无旁骛,勇往直前,发挥大无畏革命精神,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定不移地奋进,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豪杰之士。
何谓“心中之奴隶”?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著《新民说》,其中有《论自由》曰:“是故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吾不乐焉,可以一旦起而脱其绊也,十九世纪各国之民变是也。以身奴隶于人者,他人或触于慈祥焉,或迫于正义焉,犹可以出我水火而苏之也,美国之放黑奴是也。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蚕在茧,着着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47页。梁启超因此说:“故夫泰西近数百年,其演出惊天动地之大事业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于宗教而为之奴隶,固非足贵,然其借此以克制情欲,使吾心不为顽躯浊壳之所困,然后有以独往独来,其得力固不可诬也。日本维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实为五贼(佛典亦以五贼名五官)所驱遣,劳苦奔走以借之兵而赍其粮耳,吾不知所谓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对于众生称为己,亦即对于本心而称为物者也。所克者已,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自胜源,强焉,其自由何如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47—50页。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谓的自由即是能自我主宰的心的自由、心的解放。
2. 彰显佛学:“放万丈光焰于历史”
梁启超以佛诠孔和鼓吹三界惟心之真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佛学思想定位,但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对前辈或师友佛学思想的继承。而能真正代表梁启超佛学思想创造的,则是在1902年他撰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几篇有标志性的论文,于中他明确认为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化,并有改良社会人生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客观而又全面地论述了佛教的真理是什么,而在于他主要论证和特别推崇了什么样的佛教才能为现代人所信仰。这就是梁启超给自己提出的佛学思考的时代课题。这样的时代课题迫使他把自己对佛教的救世的热忱转向对佛学的理性的思考。从以上三篇论文的标题来看,他首先考察了佛学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中的历史地位,然后又比较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最后落脚点仍然探讨佛教与群治(人群、社会乃至国家)的关系,不失他以佛教救世救心的本色。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在当时的《新民丛报》上,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认识佛教思想的。他在《总论》中的开场白是“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即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乩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在他把我国学术思想划分为嬗变更迭的七个时代后,紧接着他指出:“吾国有特异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浅识者或以是为国之耻,而不知是荣也,非辱也。宗教者,于人群幼稚时代虽颇有效,及其既成长之后,则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学术思想之自由也。吾国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浊我脑性,故学术思想之发达,常优胜焉。不见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域,在蒙古,在缅甸、暹罗,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独其入中国,则光大其大乘之理论乎!不见乎景教入中国数百年,而上流人士从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学术之进步,思想之统一(统一者谓全国民之精神,非排斥异端之谓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缚也。”梁启超对我国无宗教的看法立基于对世界几大文明的考察,而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孕育生成,他以无比乐观和喜悦的心情拥抱新世纪中西文明的结合:“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 4页。
梁启超在该论中列出佛学时代一专章以彰显佛学思想之光芒,其发语曰:“吾昔尝论六朝隋唐之间为中国学术思想最衰时代,虽然,此不过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中略)虽然,学固不可以儒教为限,当时于儒家之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博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此有所盈,则彼有所绌,物莫两大,儒家之衰亦宜。”对于是否可把佛学这种渊自于印度的外学加入中国学术思想之疑问,梁启超的看法是,“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光大之、实行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学于他乡,而于所学者,既能贯通,既能领受,亲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谓此学仍彼之学,而非我之学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国亦然,如必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也,则如北欧诸国未尝有固有之文明,惟取希腊罗马、取诸犹太者,则彼之学术史,其终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尝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诸我国取诸欧西者,则彼之学术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论学术者,惟当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出于我之为断。”*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62— 63页。梁启超既游学日本,又放眼观世界文明,而对佛学感到亲切有味,于是有如上之论断自不难理解。
梁启超在考察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发展而谈论中国佛学之特色时,又写下了如下元气淋漓、情致昂扬的文字:“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吾于算学见之,吾于佛学见之。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虽有真宗、日莲宗为彼所自创,然真宗不过净土之支流,日莲不过天台之余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者也。未尝能自译一经,未尝能自造一论,未尝能自创一派,以视中国,瞠乎后矣!此事非我泱泱大国民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思想于一炉而治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顶礼以祝,吾跻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请讴歌隋唐间诸古德之大业,为我青年劝焉。”*同上书,第72—73页。
在许多知识分子热心吸取西方文化的时代,梁启超表彰中国化佛学思想的伟大,预示了他后来通过批判全盘西化来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超越西方文明的极限,再创新的中华文明的努力。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佛学思想的演变,是外来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其决定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求法精神”。梁启超一再说,中国是个大国,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外学难入;然而一旦受之,则必能尽吸取其所长以化作自己的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他又叹之曰:“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於戏!深山大泽,实生蛟龙;龙伯大人之脚趾,遂终非僬侥国小丈夫之项背能望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64页。梁启超在广泛分析亚洲各国佛教史的基础上,他特别提出中国的佛学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梁启超在此特别指出,“中国入迷信宗教之心,素称薄弱”,这主要因为“孔学之大义,浸入人心久矣”。佛耶两教,都是作为外教传入中国,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为主,其哲理浅薄,不足以大餍中国士君子之心也。佛说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方面,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佛教者,实不能与寻常宗教同视者也。中国人惟不蔽于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学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也”。“中国之哲学多属于人事上、国家上,而于天地万物原理之学,穷究之者盖少焉”。这种形而上的学问,“自佛教入震旦,与之相备,然后中国哲学乃放一异彩,宋明后学问复兴,实食隋唐间诸古德之赐也”。*同上书,第73—76页。梁启超标榜佛教的哲学性质,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淡化其宗教“迷信”色彩,这在上举的另外两篇论文中更有明示。
3. 宗教不可“蔑”而“佛学兼哲学之长”
梁启超自入万木草堂后一直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学、西学与佛学交织在一起,不断磨砺激荡成为他思想常青之源泉。至流亡日本时,于1902年10月,梁氏在《新民丛报》第19号上发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表明他已经不局限于佛教来思考问题,而是在更宽广的宗教范围内,与哲学作比类。他说,哲学适宜于学术、讲学等方面,宗教则宜于立身和治事;哲学能造出大学问,宗教则能造出大事业。古往今来能震撼宇宙,唤起社会风潮,诸如一乡一邑之善士,风靡世界之大人物的惊天动地之事业,“则不恃哲学”,而“常赖宗教”。其中他提到日本明治维新前诸人物皆得力于禅学,“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仆后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其在我国,则近世哲学与哲学两者皆消沉极焉,然若康南海,若谭浏阳,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为什么说宗教思想宜于治事呢?梁启超深思之而得五因:一曰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二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三曰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四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五曰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此中他推崇佛之说教乃“大雄”、“大无畏”、“奋迅勇猛”等,“括此数义,取象于师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于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则知无所谓生,无所谓死”。
要而论之,“哲学贵疑,宗教贵信,信有正信,有迷信。”。梁启超由此看出宗教有正信和迷信之分,先不论其正迷,如果有正信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故寻常人所以能为一邑一乡之善士也,常赖宗教;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仰人之至诚,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动,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顾可蔑乎?!”然而,由于宗教与迷信常相为缘,“一有迷信,则真理必掩于半面;迷信相续,则人智遂不可得进,世运遂不可得进。故言学术者,不得不与迷信为敌”。而敌迷信者,则不得不连其所缘之宗教并为敌。故此,梁启超进一步得出,一国之中,这两种人皆不可缺:不可无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无摧坏宗教之人。于此梁启超还根据“生计学公例”来判定,“功愈分而治愈进”,“不必以操术之殊而相非”。所以他又断言说:“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最后,梁启超在该文结束时归宗于佛教,他说:“若夫以宗教学言,则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取一切众生而度尽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44—50页。本节引文皆出自《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4. “应用佛学”
“应用佛学”一词,出自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原文是指谭嗣同善于将佛学基本原理运用于现实生活,在这方面尤以其名著《仁学》为代表。所以梁启超说:“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参见王兴国:《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应用佛学》,《船山学刊》1997年第3期。事实表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为《仁学》作序,为谭嗣同立传,大力表彰谭嗣同维新事迹,积极提倡的就是他所谓的应用佛学,感人至深。显然,梁启超的这一“应用佛学”的称谓,实际上已经蕴含着佛学的现代转换。众所周知,传统佛学的根本立场是要人觉悟生存之苦,追求解脱出世之乐,然而到了近代,出世的佛教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现实的需要。如果佛教不能实现入世转向,它就避免不了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同样,如果佛教缺少理性信仰的基础,它也不能成功地实现其入世转向。对此,梁启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于是提出了他对新时代佛教信仰的六点认识。
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3号发表《论佛学与群治之关系》,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曰“中国群治当以无信仰而获进乎?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答曰: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信仰必根于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极则,但宗教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他对以教育代宗教的说法,“未敢遽谓然也”。由此生出第二个问题,中国群治必须要有信仰,则信仰当需何宗教?答曰:必是佛教。为何不是孔教?他认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尤不达体要之言也。无论景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又无论彼之有眈眈逐逐者楯于其后,数强国利用之以为钓饵,稍不谨而末流之祸将不测也。
梁启超从“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等六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其“佛其至矣”的观点。这就是他揭示的新时代佛教信仰的六点认识。其理皆通俗易懂,他也把这六个方面当作他个人信仰佛教的六个条件。他说,“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依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赡部洲有情众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这六个条件皆通俗易明,一言以蔽之则为“智信说”。
梁启超认为,宗教的存在有其时代之必然。有宗教就有信仰,所以各种宗教都以起信为第一义。但对于信仰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懂得了教义再去信仰它,这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根本不懂教义而强迫自己去信仰,那就是自欺,其结果势必走向迷信一途。梁启超于此指出:“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谓也。故其教义云:‘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尚过于谤佛者。’何以故?谤佛者有怀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梁启超把佛教之起信与其他宗教之“强信”区分开,他说:“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为教主之智慧万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强信为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则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与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为法门。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可见,梁氏之所以推崇佛教,从理论上看,正因为佛教是“信而不迷”。*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45—52页。在该文末,有问难曰:“子曰佛教有益于群治,辩矣,印度者,佛教祖国也,今何为至此?应之曰:嘻,子何暗于历史,印度之亡非亡于佛教,正亡于其不行佛教也。自佛灭度后十世纪,全印即已无一佛迹,而婆罗门之余焰,尽取而夺之,佛教之平等观念、乐世观念,悉已摧亡,而旧习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与印相终始焉。后更乱以回教。末流遂极于今日,然则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
在实践上,梁启超又特别推崇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入世观,“夫学佛者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众生故,乃并此最大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矣”。梁氏对佛教救世精神始终服膺,他在此推崇佛教的“舍己救人之大业”,无异于“夫子自道”,故他说:“吾既托生此国矣,未有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知此义者,则虽牺牲藐躬种种之利益以为国家,其必不辞矣!”毋庸置疑,梁启超眼中的佛教是一种纯粹的、高尚的宗教,他忽略了佛教信仰作为宗教的消极一面,固然显示了他对佛教存有偏好之情,但亦自有他的良苦用心。他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当时欧洲佛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他明确肯定佛教“有益于群治”,认为只有佛教才能达到以信仰统摄民心、开发民智、增进道德、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这种思想延续到辛亥革命后他从日本归来。
三、 从佛学中探索济世的宗教力量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研究佛典、宣扬佛学的原因之一是政治需要,其目的是希望将佛教中的一些教理、教义加以积极改造利用,以作为改造社会的良药。他当时与众不同的是,大力汲取西方研究佛学的方法,对中国佛学研究做了多方面的开拓。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提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以佛学来接通和传播康德哲学,亦以康德哲学抬高佛学,同时还就康德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佛教的思维方式作了比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51页。光绪三十年(1904),又发表《余之生死观》,阐述了佛教的羯磨(业力)、轮回、因果论等,认为佛教教义能比耶教更好地涵括和解释现实;佛教诸说不仅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成就所证实,同样也为近代科学成就如物质和能量不灭、进化和遗传学所证实。*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1—12页。
由于梁启超当时是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学问和文章名满天下,所以,他的佛学文章与他的政论文章一样受到世人的关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佛学在梁启超人生思想旅途的跋涉中,成为他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里仅仅阐述了他戊戌变法后的佛学思想,这是他一生中在佛学研究上有重大收获的第一个时期;当他进入民国新时代并从喧嚣的政坛转入学者的书斋后,他还迎来了其佛学研究的第二个创获期。梁启超在佛学研究方面确实下过功夫,早期著述有如上述,晚年撰著则汇成《中国佛教研究史》一书,内收十二篇论文,对佛教的传入、经义的阐发、佛经作者的辨伪、佛典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诸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其后又将历年佛学论文结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人们常说梁启超的思想“流质多变”,但他对佛学却始终推崇。又说,梁启超“善于鼓动,文字有一番魔力,笔锋常带感情”。因此,如果说谭嗣同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实践“应用佛学”的典范,那么梁启超则主要运用他的才华和健笔,对佛学进行整体而系统的研究阐发,可谓戊戌变法前后鼓吹佛学最力的“理论家”,此不为过。
梁启超由苦心探索挽救社会的宗教力量,而关注佛教信仰的理性化及其与哲学和科学的接通相谐,这一致思路径显示他的佛学思想本质上具有宗教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这样双重性质。他对佛学思想和历史文化悉心研究,着重宣传佛教对于当时社会变革的意义,旨趣在藉佛教振兴来激发民族振兴以挽救社会。民国元年(1912)十月初,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受到政学教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十月三十日,佛教总会在广济寺为他开欢迎大会,僧俗集者百余人。主持者致欢迎词,称梁启超先生“邃于佛学”,“平昔立言,处处提倡佛教,近年新学骤兴,毁教潮流得以不起者,皆先生护法之功,云云”。梁启超致答词,主要讲了如下两层意思:
其一,佛教所谓法身者,与众生非一非二,立夫众生之上,而实存乎众生之中。众生妄起分别相,不自知其与法身本同一体,于是造成五浊恶世,扰扰无已时。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亦然。国民不知其与国家本同一体,故对于国家生人相、我相,于是乎始有一己之利益,牺牲国家之利益者。人人如是,则国家或几乎毁矣。以佛教观点来看,法身譬如国家,舍法身之外求所谓我者了不可得,舍我之外求国家了不可得。国家亦复如是。明乎此义,爱国岂有待劝哉?
其二,说今日中国之道德堕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深忧。推其所由起,不过视自己过重,误认区区七尺之臭皮囊为我,而以我相与与他相对待。殊不知此臭皮囊者,不过四大和合而而成,刹那刹那代谢不已,每七日间迁化全尽。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又非今日之我。欲求我相,了不可得。以云真我,则与佛法身一体,众生所共,何由得私为自我?今日疲敝精神,日日为此梦幻泡影之躯作奴隶。《首楞严经》有言,如来名此辈为可怜悯者。苟能参透此着,则道德之大原,庶可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32—34页。
从梁启超的答词看,他此时对佛学仍然寄以厚望,希望佛教能在振兴民族国家和重整道德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辛亥革命成功,特别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寄希望以佛学改良社会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军阀混战、经济凋敝、道德衰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梁启超在自1902年以来的文章中从智信和科学角度称颂佛教,正是因为他想藉助宗教哲学来提升国民信仰、思想和道德素质。在他看来,对于时弊的改革,不仅仅是要引进新的制度,而且要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觉悟到他们和整体的国家其实有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大乘佛教思想中普度众生的观念,将个人解脱与整体的救赎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思想对于梁启超来说正好可以提供其作为“新民”的精神支撑。梁启超心仪佛教信仰兼具哲学之长,只有放在对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功用目的来考虑,才可得到充分理解。从他对宗教中“绝对的”、“超世间的”与“神圣的”部分似乎没有向往和探索的好奇,就可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为世界所公认。这里仅提两部著作的评论以窥一斑。其一是郭朋等人在《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中对梁启超的佛学思想成就做了如下中肯评价:“单就治学方面来讲,其视野之广阔,学问之渊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梁启超都算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家,是一位贡献卓著的学者。在梁氏的学海生涯中,佛学只不过是他曾一度所兼及者,而其对于某些问题(例如史的方面)钻研的深且细(尽管梁氏在其钻研佛学的过程中,也曾撷取了某些外人的研究成果),视之某些专治佛学者,也并无逊色。我们在叙述梁氏的这些佛学思想时,是深怀感佩之情的。”*郭朋、廖自力等著:《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10月版,第315页。其二是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认为,梁任公“不特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政论家,也是一位睿智深邃的佛学家”。他对梁启超的佛学思想贡献作了高度评价:“梁任公先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颗彗星,无论于政治上、学术上、文化上、史学上,乃至佛学上,都有他的地位。由于他卓越的智慧、伟大的抱负,加之他的锋利的笔调、拔山倒海的气魄,吐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心声,给人一个深远的影响,和鼓舞的启示。(中略)尤其他留给佛学界的功绩,却是永远的、普遍的、深邃的。许多佛教学者们,其影响力往往仅限于某一宗派,或某一经论,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佛教界,并扩至广大社会群众,无不受其伟大思想影响与启示。”
释东初的著作还概括了梁启超佛学思想的五点特性:第一富有启发性,第二富有鼓舞性,第三富有创造性,第四富有历史性,第五富有情感性。其第三说:“由于他的思想卓越,他对佛学的研究,不喜欢谈玄说妙,或嚼古人的滥调,或注经解说,或数公案。由于他丰富的学识,又饱受欧美新知识,故对佛学思想的研究不特富有启发性,更富有创造性,形之于文章,不特新旧兼容,理论与历史并重,且包罗万象。一方面以新的观念,引起国人于思想上、学术上、信仰上发生剧烈改革,一方面矫正国人以往对于佛教之误会,故无一言不针对社会群众,无一语不为国家社会。而于字里行间,绝无令人惊怕之处,娓娓动听,百读不厌。”其第四说:“梁任公治学的方法,是理论与历史并重,故对佛学的研究,亦多以理论与历史兼顾。一面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佛学思想与学说,一面用以唤起国内知识界,了解佛教有助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种治学方法,并非始自梁任公,实得力于日人的著作,惟梁任公得之,却运用自如,加之以他迷人的叙述力,以及新旧融化于一炉的气魄,于是他的文章,独创一格;既不讲究规律,也不求诸琢炼,意之所到,笔亦随之,无意不宣,无意不尽,不仅易于领会,并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之妙。”*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东初出版社1974年7月初版,第559—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