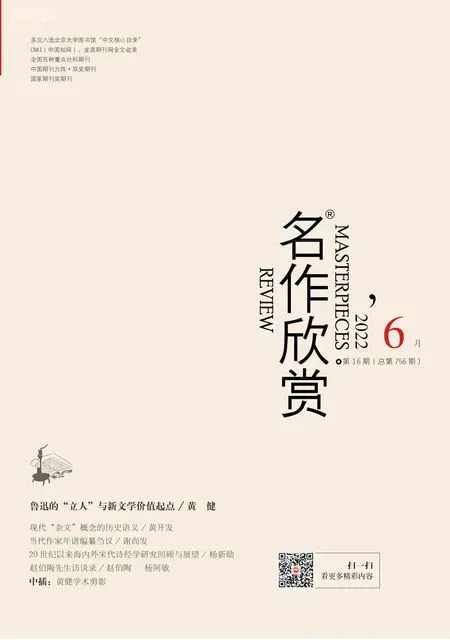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
——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上)
北京 陈漱渝
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上)
北京 陈漱渝
1985年3月1日,丁玲在致日本研究者白滨裕美的复信中坦诚介绍了她跟冯雪峰之间的关系,并说:“不过这都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确,跟丁玲的政治追求、文学成就比较起来,她个人的情感生活相对而言是一种“小事”,然而这种“小事”不仅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艺术投影,而且对她的政治追求和人生道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以史学家眼光观察,从学术角度研究,也就成了一件并不算“小”的事情。
瞿秋白:第一个进入丁玲心扉的男性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三岁半的丁玲遭遇到丧父的厄运,极度绝望的母亲欲相从丈夫于地下。因顾忌丁玲无人收养,她曾将丁玲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余伯强。这一包办婚姻因1922年丁玲执意去上海求学而解除。丁玲此前跟这位表兄毫无感情,解除婚约之后两家的关系濒临破裂。根据现存史料,第一次进入丁玲心扉的男性应该是瞿秋白。
1977年初,丁玲之子蒋祖林曾去山西长治嶂头村探母。有一天,丁玲谈起了瞿秋白跟她和她的闺蜜王剑虹之间的三角关系。王剑虹原是丁玲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一位学生领袖。1921年冬,王剑虹动员丁玲中止在湖南的学业,到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深造,二人从此成为挚友。1923年夏天,因平民学校停办,王剑虹又从上海到南京自修文学。在这里,经柯庆施、施存统的介绍,她们结识了一位身材瘦长,戴一副散光眼镜的朋友,他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在秋白的鼓励下,丁玲和王剑虹重回上海,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这所学校的社会科学系由瞿秋白和邓中夏负责,教师有茅盾、俞平伯、田汉、陈望道等。从此,他们跟瞿秋白之间建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1980年初,丁玲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此文已收入《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跟蒋祖林的谈话中,提供了我们前所未知的新内容。丁玲说:“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王剑虹。”又说:“我看到王剑虹的诗稿,发现她也爱上瞿秋白时,心里很是矛盾,最终决定让,成全她。”“心里很是矛盾”,表明瞿秋白对丁玲还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丁玲对他也是有爱慕之心的,否则就谈不上内心矛盾,也不存在“让”与“不让”的问题。丁玲跟蒋祖林说得很明确:“瞿秋白是我那几年遇到的最出色的一个男子,而且十分谈得来。不过也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在这以前我的确无意于恋爱,我觉得应该多读点书,立足于社会。” 之所以做出自我牺牲,丁玲的解释是:“我很看重我和王剑虹之间的友谊,我不愿她悲伤,不愿我和她之间的友谊就此终结。”(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8页)
重读《韦护》
其实,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丁玲已经谈及她跟瞿秋白之间的感情纠葛,比如秋白除了为王剑虹写情诗之外,也给丁玲写了一首,说丁玲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在此期间,秋白还为丁玲刻过一方印章,丁玲珍藏了半个世纪,于1977年交给了儿媳李灵源保存。这些都表明了瞿秋白对丁玲的情感非同一般。
记录丁、瞿情感的还有丁玲的小说《韦护》,写于1929年冬,1930年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凡三章,八万字。读者多以为这是一部以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韦护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1980年6月,丁玲写了一篇短文《韦护精神》,对她回忆瞿秋白的文章进行了补充说明。她说:“韦护是封建社会里韦陀菩萨的名字,这位菩萨手持宝剑,是塑放在第一殿佛像的背后,面对正殿(第二殿)的佛像。一般的佛像都是面向尘世,为什么唯有它的塑像是背对尘世,只看佛面呢?秋白同志对我解释说,因为韦陀菩萨嫉恶如仇,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但是佛教是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为怀的,生怕这位菩萨犯杀戒,所以塑像时就让它只看佛面,只见笑容,而不让它看见纷扰的尘世和罪恶的人间。秋白同志生前曾经用屈(瞿)韦陀的笔名发表过文章,足见他对韦陀菩萨的这种精神,十分推崇,喜欢把自己比作韦陀。”
小说中的韦护博学多才,风度翩翩,有信仰,有动力,有研究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兴趣,能赢得年轻姑娘的好感,有批评家认为小说“对杰出共产党人气质缺乏足够理解”,“作者写他的文学趣味比写他的革命信仰更为传神”(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页)。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丁玲后来又解释:“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确是我力量达不到的。”秋白本人也读了这部小说,什么意见也没有发表,只是托胡也频给丁玲带了一封信,落款赫然写的是“韦护”两个字。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出生,瞿秋白曾建议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
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小说中的丽嘉是以王剑虹为原型,因为王剑虹的确热烈地爱着秋白(韦护),相互以情诗相赠,并于1924年1月结婚,后被瞿秋白所患肺病传染病逝,年仅二十二岁。秋白当然也爱剑虹,对于剑虹的死深感自责。然而细读这篇作品就会发现,在丽嘉的身上,除开能发现剑虹跟丁玲的若干共同点,如喜好读书,热爱文艺,追求进步之外,还能看到很多丁玲本人的身影,乃至经历,比如,作品中的丽嘉有“一双活泼有力的大眼,笑的时候显出两个笑窝,一大,一小,一个在颊上,一个在微微凹进的嘴角边”。这活脱脱是丁玲少女时代的面影,跟王剑虹的形象不同,可以用丁玲跟王剑虹的合影为证。丽嘉的有些经历也是丁玲本人独一无二的经历,比如曾到电影公司试演。这是丁玲年轻时代的演员梦。为此,1926年经戏剧家洪深介绍,丁玲到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试演了两次,只因厌恶演艺圈里的商业习气和低级趣味,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商品,终于拒绝跟明星公司签订三年的合同。至于丽嘉在一般男性面前的倨傲,那种跟眼神同样锋利的话语,更是属于丁玲而不是属于王剑虹。
那么,丽嘉这一人物的创作素材究竟取自丁玲还是取自王剑虹呢?我认为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其中既有王剑虹,也有丁玲,还有同时代的一些在苦闷中挣扎徘徊而仍追求进步的其他女性。1931年,丁玲曾到上海光华大学讲演,讲词刊登于同年8月10日《读书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丁玲说:“《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我以为,小说中的“柯君”就是以柯庆施为原型,“浮生”和“雯”,有点像施复亮(存统)和王一知夫妇,那位“矮李”,又会让读者联想到李达。当然,懂得文学创作常识的人,都不会真正把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典型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逐一对号。读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丽嘉的素材有些取自于丁玲本人,那作品中韦护与丽嘉的爱情纠葛是否跟丁玲的生活经历相关呢?这个问题,丁玲之子蒋祖林在他的近作《丁玲传》中做出了明确而可信的回答。丁玲曾跟瞿秋白直说:“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读完丁玲这番真情表白,读者就会懂得,《韦护》这篇小说中韦护跟丽嘉恋爱的有些细节,并不专门属于王剑虹;也能准确理解丁玲在光华大学讲演《我的自白》时,为什么会暗称瞿秋白是“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作家”。晚年丁玲撰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时还提供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发现瞿秋白跟王剑虹相恋而未坦然相告时,一度烦躁而愤懑,曾将一腔无名怒火喷射到秋白身上,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另一个细节是,秋白在王剑虹致丁玲信的结束写了几行附语:“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所以,我的新认识是:只有联系丁玲的这篇回忆录和蒋祖林的《丁玲传》,才能更全面地解读《韦护》。
单纯而痴情的胡也频
丁玲在少女时代,率先敲开她爱情心扉的是胡也频。这位出生在福州的青年人生于1903年5月4日,比出生于1904年10月16日(从蒋祖林说)的丁玲要大一岁。1923年冬,胡也频因为就读的大沽海军学校停办,只身漂泊到北平,想投考一所不收学费的官办大学,未能遂愿。在颠沛流离中,他结识了一些住在学区宿舍做着文学梦的朋友,不仅在著名报人孙伏园的举荐下参与了《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而且通过曹孟君的恋人左恭结识了丁玲。胡也频打听到丁玲原有一个弟弟,不幸十岁那年因病夭折,就表示要成为丁玲的“一个新的弟弟”。1925年暑假,丁玲回湖南老家探亲,囊中羞涩,对丁玲一见钟情的胡也频也闻风赶到了湖南。丁玲被胡也频的单纯和痴情所感动,在母亲的资助下,在老家住了两三个月,丁玲和胡也频重返北平。
1985年3月1日,丁玲在致日本学者白滨裕美的信中回忆道:“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全集》,第1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68页)
丁玲和胡也频1925年秋即在北京香山碧云寺附近的一处民房里开始了同居生活,但这时的同居实际上是一种“无性同居”,双方的约定是:谁要有了爱人谁就走,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直到1928年6月住进上海法租界之后,他们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这种恋爱方式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矫情,或者不可思议,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式青年男女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做法。比如哲学家朱谦之(1899—1972),跟妻子杨没累同居六年,至死也是精神恋爱(purelove),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杨没累是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就读时的同学。杨没累三十岁时死于肺病,丁玲曾协助料理她的丧事。丁玲创作《莎菲女士日记》,杨没累就是莎菲的原型之一。
杀出一匹黑马冯雪峰
客观上促成丁玲与胡也频情感升级的是另一个男人冯雪峰(1903—1976)。1983年,七十九岁的丁玲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深情回顾了她结识冯雪峰的经过:“我现在讲的,就是雪峰和我个人的友谊。我们主要是文章上的知己。1927年,我在北京,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过去的党员朋友、老师失掉了联系,寂寞得很。胡也频也一样,和我有同感。那个时候很年轻,也说不出道理来。胡也频就写诗啰!我被逼得没有办法,提起笔来写小说。正在这个时候,王三辛介绍冯雪峰给我们做朋友,教我日文。但教了一天,他不教了,我也不学了。我和胡也频都感到他比我们在北京的其他熟人——也是一些年轻的、写文章的朋友——高明!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们,他是党员。啊呀,那个时候,我一听到是个共产党员,就觉得不知道得到多少安慰!我还是同一个共产党员做朋友了。因为我的老的共产党员的朋友,那时都不在我面前。”(《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冯雪峰跟丁玲交谈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内容:
飞机、炸弹……
金价、银价、棉花的价……
白人、黑人……
资本主义与殖民地。
兵灾、水灾、旱灾……
军阀、走狗、屠杀……
斗争、组织……
(丁玲:《给我爱的》)
然而正是这种政治性的的内容,反映了丁玲跟冯雪峰信仰追求的一致,这成为他们之间情感的契合点。当然,两情相悦的因素是复杂的,有些甚至说不清道不明,但冯雪峰给予丁玲这种思想上的满足,却是丁玲从胡也频那里得不到的。
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三角恋主要发生在1928年2月下旬,地点是在杭州葛岭山庄14号。这里是一处横躺着的庞大的山坡,空荡荡的,夜间树林里常常掉落一些空枝,打破四周的寂静。这处房子是冯雪峰租下的,三位朋友在这里合住了六天之后,胡也频感到无法忍受,要找冯雪峰斗殴。丁玲坦诚地对胡也频说:“我们不要打架,也不要成天黏在一起。你要求的东西我不能满足你,我要求的东西你也不能满足我。这样子僵下去不好,你到上海住三天,我们分开试试。如果彼此能够适应,我们此后分手。”胡也频一气就到上海找他在北平结识的朋友沈从文。沈从文批评胡也频:“你真是个傻瓜。你怎么这么一个蠢人呢?哪里有什么精神恋爱?”结果第二天一早,胡也频就回到杭州葛岭了。这样一来,丁玲就必须在胡也频和冯雪峰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再也不能维持精神恋爱的现状了。
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一个农民的家庭,原名福春,雪峰是他自己改用的名字。1918年,冯雪峰十五岁,刚从义乌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这时,尖酸刻薄、控制欲极强的祖母不顾他的强烈反对,领来了一个十四岁的童养媳,企图强迫他们结婚。只有经常被丈夫暴打的母亲同情冯雪峰的遭遇,并寄希望于儿子:
你好自讨个极美丽的老婆,
你好自由地选择一个。
我既被人误了,
我决不想再来误你呵!
但你千可万可,
总总不可像你爸待你妈这般,
待你的爱人呵。
(《睡歌》,《冯雪峰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925年春,冯雪峰还以“画室”为笔名创作了一篇自传体的小说《柳影》,具体描写了他跟这位童养媳的往事。内容是:这位童养媳虽然出落得清秀,但因为出自包办,他感到“没有一点缘分,没有一点感情”。这位童养媳十七岁那年出轨,跟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子发生了关系,并大胆招引这位男子到家同居,被祖父当场捉住,被遣送回娘家。少年时代,冯雪峰暗恋过一位表姐,但这位表姐已经许配他人,不久就出嫁了(1925年5月《支那二月》第1卷第4期)。冯雪峰是个爱心满满的人,1922年,他在《诗》杂志第1卷第2号发表了一首《小诗》,诗中写道:
我爱小孩子,小狗,小鸟,小树,小草,所以我也爱做小诗。
然而,这位湖畔诗人当时却没有一个恋人。他的另一首诗《拾首春的歌》 中有这样的句子:
没有一株杨柳不为李花而癫狂,没有一水不为东风吹皱,没有一个恋人,不为恋人恼着。
(收入《湖畔》合集,湖畔诗社1923年12月版)
冯雪峰当然也有着这种青春的烦恼。他于1928年3月1日致戴望舒的信中就写道:“今日颇烦闷,终日萦思西湖……”(《冯雪峰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5页)很明确,让冯雪峰烦闷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理他跟丁玲和胡也频之间的关系。
西湖畔的这场三角恋以冯雪峰的退出告终。其原因有两点:一、雪峰虽然对丁玲也有好感,但表现出来的只有彼此谈心的要求,而不愿落入一般男女关系的俗套;二、跟对胡也频的感情比较起来,丁玲对冯雪峰的感情虽然更为炽热,但在她心目中,胡也频是一个弱者,又曾经为她付出了很多,这样纯洁的男人很少,所以她只能中断跟雪峰的联系,而不忍心让胡也频受伤。
1928年7月,冯雪峰跟中共浙江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故乡担任义乌区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义乌县初级中学国文教员。1929年3月,二十六岁的冯雪峰跟比他小七岁的学生何爱玉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七年。
情海兴波的1931年夏
继1928年的这场三角恋之后,1931年夏天,丁玲的情海又波涛翻腾。原因之一是当年2月,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丁玲有了重觅生活伴侣的考虑;原因之二是冯雪峰调任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主编机关刊物《北斗》,双方又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于是,在丁玲心灵深处蛰伏了三年的爱情岩浆又喷发了出来。这是丁玲一生之中产生的最为炽烈的爱情。在迄今留存的六封致冯雪峰的信中,她承认自己“被恋爱苦着”,她再也不愿意欺骗自己的感情。因为有了雪峰,她觉得在白色恐怖的暗夜里又有了生气,有了光明,有了希望。她“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让雪峰永远为自己精神上的引领者。对于她跟雪峰的爱情有花无果的结局,她认为雪峰应负一大部分责任,因为雪峰过于用理性拘束自己,甚至显得有点虚伪。她在信中责备道:“雪峰,想到你那样子,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丁玲的儿子蒋祖林也向母亲问及跟冯雪峰的关系。儿子问:“父亲(指胡也频)牺牲以后,你是自由人了,你有没有想过要同冯雪峰结合的事?”母亲答:“没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想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把他抢过来,但我不愿意欺负弱者。”(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这里提到的“弱者”,就是指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同月,冯雪峰调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双方中断了联系。直到1936年为安排丁玲奔赴陕北,双方才见过几次面。1937年冯雪峰到延安汇报工作,双方又见过两次。新中国成立之后,丁玲与冯雪峰除工作和会议之外,相见极少,往来可数,实际上是隔绝于两个生活圈子,但丁玲对冯雪峰的言行深信不疑。她毫不讳言:“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76年大年初一,冯雪峰因肺炎并发症去世,远在山西农村的丁玲得知这一噩耗,坠入了深深的迷惘,感到无限的悲怆。
好心未必办好事
人的一生中有的事情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而被染上了或浓或淡的宿命色彩。冯雪峰在与丁玲的交往史上,曾出于好意做过一件错事,那就是介绍丁玲结识了冯达。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冯达此后会由一位真实的革命者堕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叛徒。
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原在上海豫园一家照相馆工作,因为英语好,外貌老成,得到了常来照相馆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赏识。史沫特莱的公开身份是《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实际上是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史沫特莱让冯达担任自己的秘书与翻译,并在政治上给冯达以引导。冯雪峰介绍丁玲认识冯达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真话报》工作。
冯雪峰之所以介绍丁玲跟冯达认识,是因为他出于理智控制了对丁玲的感情,而对于恋爱已感到心灰意懒的丁玲又实在需要一个男人的支撑。1983年12月19日丁玲对老作家骆宾基说:“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不能和很多人来往,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冯雪峰哪会料到,1933年5月13日晚,冯达不慎被特务盯了梢;5月14日被捕之后,又在无意中株连了丁玲和到她家开会的潘梓年、应修人——应修人因拒捕而坠楼牺牲。冯达认为他的过失难以被党组织谅解,便错上加错,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甘心情愿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
给丁玲带来最大羞辱的是,在南京被软禁期间,冯达还让丁玲怀上了孩子——女儿蒋祖慧。虽然这个孩子后来非常优秀,是一位成功的舞蹈家,但却成了在历次运动中不断整肃丁玲并拒不为她平反的主要理由。对于这件事的发生,丁玲后来是这样解释的:“冯达曾经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按:指被捕押往南京之后),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按:指莫干山),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手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和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和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个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魍魉世界》,《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当然,也不是没有一个表示理解丁玲的人。周恩来在延安就对丁玲说过:“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况也是‘身不由己’嘛。”
帮丁玲虎口脱险
1936年5月14日,被绑架后在南京羁押软禁达三年之久的丁玲,搞到了一张南京到北平的卧铺免票,一两天后,她带着几件换洗衣服离开了居住的苜蓿园,到北平去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丁玲在北平住在李达家,通过李达夫人王会梧,打听到曹靖华在中国大学教书。丁玲跟曹靖华此前并不认识,但知道他是瞿秋白的朋友,跟鲁迅同是未名社成员,便向曹靖华表达了要找到党组织的强烈愿望,因为估计鲁迅会有联系的途径。曹靖华慨然应允,表示一定转告鲁迅,要丁玲先回南京等待消息。一个多星期之后,从曹靖华和鲁迅处获知这一情况的冯雪峰立即派张天翼到南京跟丁玲接头,凭证是冯雪峰亲笔写的一张纸条。当年4月25日,冯雪峰接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故熟悉上海跟陕北的联络通道,但丁玲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并没有成功。冯雪峰安排丁玲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但去陕北的交通断了,一时不能成行,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露面,无可奈何重回南京。这次丁、冯在上海见面有一个动人的细节。丁玲号啕大哭,想把这三年经受的磨难、遭受的委屈都在故人面前倾吐出来。然而冯雪峰却冷峻地告诫她:“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魍魉世界》,收入《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丁玲无可奈何从上海又回到了南京。这年9月,冯雪峰第二次安排丁玲从南京到上海,并派聂绀弩护送她到西安,等待机会转赴陕北。11月中旬,丁玲终于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现为志丹县),受到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热情欢迎。在保安窑洞欢迎“出牢人”的盛宴上,由“文小姐”华丽转身为“武将军”的丁玲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她是不会忘记冯雪峰的营救之情的。
作 者:
陈漱渝,现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专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等。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