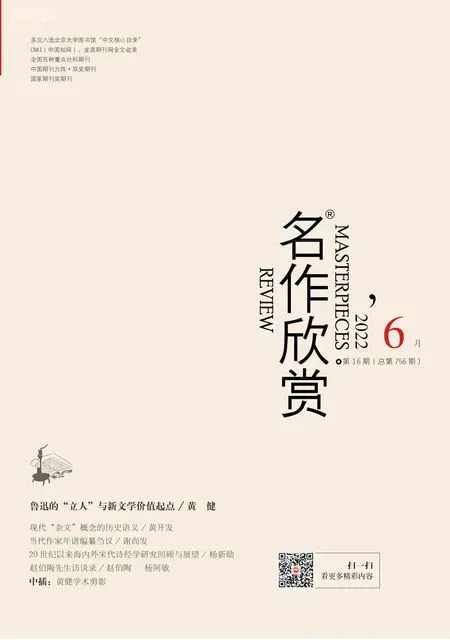亢直:端翔的气骨与坚正的批评
北京 李建军
亢直:端翔的气骨与坚正的批评
北京 李建军
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汤显祖有着健全而伟大的人格,正直是他在人格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批评精神勇敢而坚正,他对万历皇帝和多位首辅大臣的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宾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他的《论辅臣科臣疏》亢直不挠,大义凛然,是一份伟大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汤显祖 人格 亢直 冲突 批评
薇亦柔止,薇亦刚止。汤显祖是一个亦柔亦刚的人。就情感来看,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柔情似水,多爱不忍,对父母家人,对师长朋友,对黎民百姓,都真心相待,纯然一副热心肠,甚至,还有一副急人所急的侠义心肠和男子汉气概。查继佐在《汤显祖传》中评价他说:“喜任侠,好急人。”这是沉甸甸的实话,而非轻飘飘的虚誉。汤显祖喜欢“风骨情神,高华巨丽”“横目之徒,皆足惊殊叹异”的文章,也特别强调那种充满力量的“男子”气概。在给彭鲁轩的信中,他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身为男子,高步中原,他更何论。”
汤显祖有着南人的气质,温柔而多情,也有着北人的气骨,端翔而坚正。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行己有耻,拒绝逢迎,曾先后于万历五年、万历八年,两次拒绝张居正的拉拢,《明史·汤显祖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等对此都有记载,蒋士铨甚至将此事写入他的戏曲《临川梦》。邹迪光在《汤义仍先生传》里说,汤显祖未第之前,就已经名蔽天壤,为海内所倾仰。张居正为了抬高儿子的身价,两番接纳汤显祖,欲“啖以巍甲”,诱以大名大利,但都被汤显祖拒绝了,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他认为,人一旦自欺或者欺人,便无足观矣,所以,他厌恶一切虚伪不诚的做派:“人之精神不欺,为生息之本,功名即真,犹是梦影,况伪者乎?”
蒋士铨的《临川梦》一开始,便写张居正打发叔辈张不痴,以科举“大魁”来拉拢汤显祖,被我们的诗人断然拒绝。张居正以为遍地皆是吮痈舐痔、胁肩谄笑的奴才,故视此天下,皆可诱之以名,啖之以利;但是,他实在低估了汤显祖的人格和气节:“岂知公车之上有一措大,直以草芥视之耶。世悠悠,甘心贫贱,不愿识荆州。”虽然我们的诗人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也获得了极大的尊敬,“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汤显祖像屈原、司马迁、杜甫和曹雪芹一样,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格上最为健康、灵魂最为干净的难得人物,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精神高标,是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价值重建的很可贵的精神资源。
汤显祖对自己的道德期许是很高的,对自己的能力也是自信的。他在《答余中宇先生》中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木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观察言色,发药良中。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恨不见吾师言之,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惟吾师此时宜益以直道绳引天下,万无以前名自喜。”他之所以如此高自标树,把话说得很大很满,就是希望能有机会一展宏图,有机会靠着自己的正直和才能,为国家和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他把“兼济天下”看得很重,未尝因为个人的成败利钝而轻忽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世弃君平,君平未可弃世也。”
作为一个认真而不苟且的人,汤显祖对自己时代伪诈而诡滥的世风,深恶痛绝。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说:“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纵然如此,他也不曾为了现实的利益,改变初衷,降身辱志,从而随随便便做人,马马虎虎做事。

直到万历时代,朱明政权依然故我,依然是以前的那副老样子,那个坏德性。它缺乏最起码的文明教养,是一个尚未脱离野蛮状态的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狭隘,傲慢,凶暴,冷酷,一切坏时代的坏毛病,它几乎全都有。它对黎民百姓缺乏哀矜之心,对知识分子充满疑忌和敌意,拿自己的官吏当奴隶。身处这样的时代,汤显祖自然觉得荆天棘地,格格不入,很不自在。在《青莲阁记》中,他通过与那些开明盛世的对照,尖锐地嘲笑和否定了自己的时代:
……季宣为人伟朗横绝,喜宾客。而芜城真州,故天下之轴也。四方游人,车盖帆影无绝。通江不见季宣,即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宣日与天下游士通从,相与浮拍跳踉,淋漓顿挫,以极其致。时时挟金、焦而临北固,为褰裳蹈海之谈。故常与游者,莫不眙愕相视,叹曰:“季宣殆青莲后身也。”相与颜其阁曰“青莲”。

在汤显祖看来,天下分两种:一种是“有情之天下”,一种是“有法之天下”。有情之天下,是有人情味的,给人活路和尊严的;而有法之天下,却是冷酷的,拿人不当人,让人们艰于呼吸,让英雄进退失据。唐代就属于“有情之天下”,而他自己的时代则属于“有法之天下”。
在所谓“有法之天下”,人没有尊严,人的个性和才情,也都要被扭曲和毁灭。所以,假如李白生于此时,也必束肩敛息,小心翼翼,毫无作为;反过来,假如让季宣生活在唐代,那么,他一定会有机会发挥才能,凌厉一世。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汤显祖不仅对自己的时代极为不满,而且还言无禁忌,尖锐地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和不满。在血腥味很浓的朱明王朝,他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属于典型的“妄言罪”和“诽谤罪”,一旦被有司盯上,是很有可能被抓起来杀头的。
然而,汤显祖在《论辅臣科臣疏》中所表现出来的硬气和亢直,却比这更加令人惊叹和倾服。这回,他直接批评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几位股肱大臣。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典型的朱姓皇帝,性格中充满了由朱元璋那里遗传下来的狭隘、多疑、刚愎、颟顸和冷酷。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几千年来中国的暴君和昏君都有的坏毛病,例如,纵情声色,不理朝政,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文过而饰非,近小人而远君子,等等。糟糕的心性与败坏的生活,最终导致他气昏志惰,力倦神疲,近乎尸居余气。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陕西泾阳人、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曾上疏献四箴,尖锐地批评了万历皇帝政治上的窳败和生活上的混乱: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朱翊钧读罢“震怒”,欲将雒于仁“置之重典”。在申时行等人的“委曲慰解”下,才从轻发落,将他“斥为民”。这样的皇帝,气度实在太小,既不足与谋,亦不可与庄语。
迥远而神秘的上天,大概是——除了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所畏惧”者之外——几乎所有傲慢的统治者唯一敬畏的对象。虽然,对人间的事物,万历皇帝素来无所畏惧,但是,对头顶上的神秘的苍天,他还是心怀虔敬和忌惮的。几千年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如此:不在乎近而可察的民心,不倾听切中弊害的谏言,却在乎高不可问的天意。至于那些既不恤人言又不畏天命的暴君,那些视一切伟大事物皆为戋戋小物的独裁者,就更是等而下之,无足论矣。唉!他们必给人间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难以根除的祸患,也必将成为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引江海不足以浣其污的千古罪人。

却说,万历十九年,即公元1591年,天呈异象:有星如彗,长尺余;历胃、室、壁,长二尺;闰月,丙寅朔,彗星入娄。这个所谓“彗星”,即古人所说的“妖星”,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扫帚星”,是可怕的不祥之兆。这些异象让朱翊钧心绪烦乱,惴惴不安。按照官方的天象解释学,他一定是在德性上有什么过失,老天才如此警示他。

如果说,在前一个“上谕”里,朱翊钧还虚虚地说了一句“咎在朕躬”的话,那么,在后一道“圣旨”里,他完全忘了这异常的天象,只与他有关系,不过是上天对他这个“天子”失望和不满的表示。也许是因为极度恐惧,感受到了心灵上难以承受之重,他便转而迁怒于自己的“大小臣工”。他说自己臣下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市恩取誉”,为了“沽名速迁”;责骂他们简直是一群心肠恶毒的坏人,所谓“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长奸酿乱”“傍观避祸”,全都是居心不良之宵小,全都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恶徒。
因为朱翊钧不懂得“纳税人”这个概念,所以,他也就不明白,每个劳动者吃的都是自己的饭,而不是官家和“寡人”的饭,更不可能毫无来由地砸他朱家的锅,坏他朱家的事,因而,他的“尔等食何人之爵,受何人之禄”的斥责,也就是近乎毫无道理的胡搅蛮缠。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你们吃着百姓的饭,反以百姓的恩主自居,不觉得羞愧吗?没有从百姓那里搜求来的脂膏,哪里谈得上你朱家的“爵”和“禄”。唉!昏愚颟顸,亦云极矣。
由这两个“上谕”可以看出,朱翊钧是一个性格和心性都很恶劣的皇帝。他雄猜多忌,一味切责,缺乏宽容博厚之心,显然是一个心胸狭隘、意识阴暗的人。他虽然年近而立,但其心智却几乎停留在未成年人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人在责备别人的时候,是很容易显示出自己的德性和人格的。他太喜欢用反问句,竟然一连用了四个,显得咄咄逼人,毫无涵养,使人看见他刻薄寡恩的德性。至于将六科十三道切责“罚俸一年”,就更没有道理——这种动辄就说“我们停他的饭”的任性做法,近乎无赖手段,实在太小家子气!

于是,汤显祖便写了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上呈给国家元首朱翊钧。1591年的闰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接到邸报,四月二十五日前,他的上疏就送到了神宗的手上。此疏写得非常精彩,端庄而又跳脱,沉雄而又犀利。这是一个四十二岁非凡的能臣,写给一个二十九岁平庸皇帝的掏心窝子的谏言。
先来解释文中涉及的两个官名。辅臣是指辅弼之臣,后多用以称宰相,在汤显祖的疏文中,具体是指申维时和张居正等人;所谓科臣,即科道官,也称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唐、宋两代仅为八品官,明代为正七品,清代为从五品。
开头第一段,他按惯例引用了朱翊钧的己卯“上谕”,然后,加上了自己的评语:“大哉王言,正君臣之义,诛邪佞之心,严矣粲矣。”
第二段一开始,汤显祖这样说道:“南部诸臣,捧读之余,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变责难皇上,致有此谕。”这说明,朱翊钧所发的一通无名火,确实很不理性,很不合乎常情常理,以至于人们要猜测:他为何要说出这样一些狠话来?汤显祖巧妙地提到了朱翊钧曾对雒于仁等人的“狂愚直言,犹赐矜恕”,既然如此,那么,即使“言官有过言,必见温纳”。
汤显祖注意到,科道诸臣欺君徇私,而辅臣申时行则将“皇上威福之柄”移归己有。为什么会这样呢?汤显祖坦白地说,这是因为人臣若非“天性公直”,则必然“要取富贵而已”。而申时行就是利用辅臣之大权,一手遮天,为自己豪取富贵。他为其子得中进士,大搞科场欺蔽。儿子考试“奏捷”,前来送礼的络绎不绝,“有牛马不计其数”。汤显祖查了日历,发现申时行为儿子“宴功之晨,正星象示儆之夕也”。



如果说,这篇上疏对皇帝朱翊钧的批评还是委婉的,那么,到了最后一部分,汤显祖所说的“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皇上之爵禄可惜,皇上之人才可惜,皇上之法度可惜,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就等于直接批评皇上实在太低能,连自己最宝贵的资源,都守护不住,竟至于为人所欺夺。尤其最后一个“可惜”,彰显了这样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皇帝虽然“经营天下十二年于兹矣”,但“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帝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架空的状态。他建议皇上严厉处理申时行、杨文举和胡汝宁等人,并特别赞扬了“谨守宪令”的别谕都御史李世达,提醒皇帝,这样的人,“务令在内言事,在外宣风”。

汤显祖所说的问题,有具体人的权力腐败,也有重大的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应该说全都是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倘若朱翊钧能够大度“温纳”,那么,晚明的很多社会问题,都会随之解决,而在1591至1620的二十九年间,种种社会问题,断不至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关于我自己,我应该这样说,我从来不是一个贪婪的吝啬鬼,既不是一毛不拔,也不挥霍浪费。我从不醉心于追求财产,只为百姓谋福利……





总之,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就是另一种形态的诗,就是像“临川四梦”一样伟大的文本。它们是同一棵精神之树上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因而有着一样的芬芳,一样的滋味。如果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对我们这冰冷世界的安慰,那么,汤显祖的作品——包括《论辅臣科臣疏》在内——所带给我们的,则不单是情感上的安慰,还有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激励。它给我们提供了捍卫正义的信心和说出真话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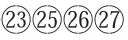

⑦屈原:《屈原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作 者: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