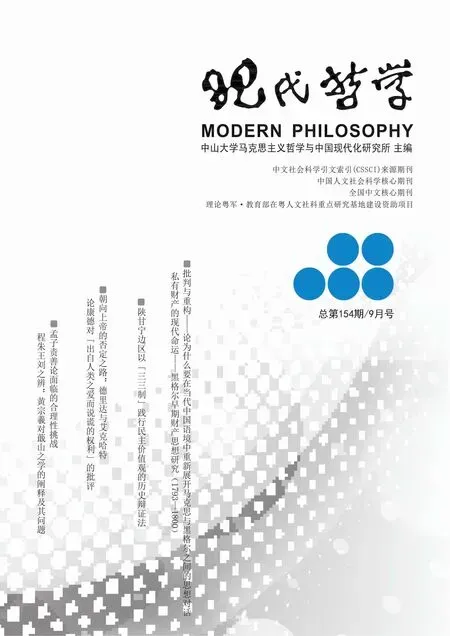“悬搁”上帝如何?
——从现象学含义论看本雅明的“纯语言”
张 琳
“悬搁”上帝如何?
——从现象学含义论看本雅明的“纯语言”
张 琳
针对业界“本雅明的纯语言是指上帝的语言”这一缺乏科学依据的命题,本文提出“悬搁上帝”的建议,从现象学含义论视角展开讨论“纯语言”。首先对“译者的任务”作译者与译本分析,聚焦于其英法译者对“意向”一词的处理,并结合他们自身直接或间接的现象学背景,指出他们对该词处理的原因及合理性;其次从本雅明批判者角度进行反向观望,最终得出本雅明思想中蕴含朴素的现象学因素。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指出,通过“悬搁上帝”可以看到,“纯语言”相当于胡塞尔意义上的“含义”,它与意义、语义构成了三层结构,这也意味着本雅明“意义的传递”这一翻译本质观其实指向胡塞尔意义上的“含义的转渡”。
悬搁;纯语言;现象学;本质;含义
一、“纯语言是上帝语言”的由来
近年来,以“译者的任务”(以下简称“任务”)而蜚声哲学界与翻译界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他的“纯语言”因为触及翻译的本质而吸引人们不断从各种角度展开探究。“纯语言”被看作是一个“抽象晦涩”的纯粹概念、“抵制翻译的果核”、“不可译的东西”或“本雅明的政治心声”等;也有不少学者借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认为纯语言或许就是“普世语言”,即上帝的语言*参见翁再红:《语言转换与经典传播:重读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13页。。保罗·德曼(Paul De Man)认为,本雅明的“任务”激起了受众反应论者的愤怒,所以人们把这归罪于本雅明的宗教背景,认为这是一个后退到诗歌的救赎式概念的例子,这种概念的所谓宗教性是错误的*Paul De Man,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essenger Lec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4, 1983”, in Yale French Studies (97), 2000, p.16.。鉴于德曼所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力,人们把纯语言归为上帝的语言,很难说与此没有关系。而在译界,乔治·斯坦纳对本雅明纯语言的神学归因*参见曹明伦:《揭开“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本雅明信仰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这使得他的学术言说蒙上神学的面纱*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第62页。,但它同时也可能是一个雾障,阻碍了人们跳出他的神学背景去看向更本质的东西,对“纯语言”的认知即是一例。
本雅明这样界定“纯语言”:“语言之间所有超越历史的亲缘性在于隐含在每门作为整体的个别语言背后的那个意向中——但这种意向并非任何个别语言所能获得,而只能由互相补充的所有个别语言的意向总体实现:纯语言。”*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82.“纯语言”可以说是“意向总体”的别称。在其后文中,本雅明对意向对象、意向方式进行了解释,表明语言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也就是说,纯语言的本质是意向。“不同[外国]语言在其意向中互相补充,尽管它们在语词、句子、结构等方面互相排斥。”*Ibid.这说明本雅明认为语词等语言层面因素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深层意向,后者是诸语言所共同含有的东西。由此可推断:在翻译过程中,这个共有的东西是不变的,因而任由语言转换而始终如一,而翻译要做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把它转渡到不同语言中。
本雅明1920年的《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和1921年的“论译者的任务”,所试图要解决的其实就是《小说理论》遗留下来的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现时代的艺术具有了发现真理的权能。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指出翻译者就是无神时代的先知,他要以众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解释诗人的作品所传达的本质*尚方健、林之源:《辩证法:从早年卢卡奇、本雅明到阿多诺》,《学术界》2009年第6期,第156页。。由此可知:第一,翻译者是无神时代的先知,说明他要传递的纯语言不是上帝的语言,否则“无神时代”不成立;第二,诗人作品所传达的本质即纯语言,这进一步明确了本雅明在“任务”中提出的“纯语言是终极本质之物”*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82.这一观点。
其实就翻译问题而言,坚持认为纯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这一观点中包含着一个悖论:上帝推倒了巴别塔,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们拥有同一种语言,于是翻译登场;但纯语言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这难道是说上帝在推倒巴别塔的同时又寄希望于人类再把它建起来吗?因而,若说纯语言是历代语言学者的渴望与追求,则把纯语言归到上帝的语言只会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不可能实现。那么,人们追求的价值何在?翻译的价值何在——本雅明所谓“纯语言的传递”岂不是在自我否定?无论怎样,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向上帝本人求证纯语言是否他的语言。既然如此,何不“悬搁”上帝?从人类理性的角度,看看能否对“纯语言”做出合理解释。
二、“悬搁”上帝的原因及可能性
本雅明曾说过:“我的思想和神学的关系,就如同吸墨纸和墨水的关系,我的思想饱蘸神学,倘若抽掉墨水,吸墨纸上将荡然无存。”*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第65页。诚然,本雅明思想中的神学因素不容忽视,但如果对他一切思想的讨论都唯神学马首是瞻,那么他复杂多元思想构成中的其他成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本雅明是哲学家而非单纯的神学家。他的哲学特质表现出多元性:它包含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政治批判以及童年时代给他重大影响的弥赛亚主义的观念和思维逻辑等等思想*同上,第63页。,他的一生都处于“学术流浪者”状态*Thomas Klikauer, “Review Essay”, in Working USA: 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016(6), p.217.。因而,本雅明的某些观点非神学所能涵盖就完全有可能。而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一味推给他的神学背景,让上帝说话,这无论如何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我们还应避免陷入武断终止论证的陷阱*https://www.douban.com/note/248325658/(2016-11-5引)明西豪森的三重困境中有一条就是武断地终止论证:在论证过程中,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如果不能走出这个困境,论证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
本雅明对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知,这使得他能够以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切近那些普遍受到关注的人的存在问题;另外,他又拒绝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式的整体性哲学传统的阐释*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第64页。。鉴于纯语言恰恰是一种存在但不实存的事物,我们有理由推出:纯语言的得出,与其说是本雅明神学背景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他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所致,相比较前者,后者因为少了那层神秘虚幻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本雅明的思想中或许有一定的、至少是朴素的现象学因素。而对本雅明与现象学关系的认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将纯语言与含义联系起来,因此值得探究。虽然暂不能下结论,但不妨碍我们往下走出关键一步:“悬搁”上帝,从现象学的角度看看纯语言为何物。
三、本雅明的现象学“向度”
这里做本雅明与现象学的关系研究,并非一定要证明他具有现象学背景,而是希望通过分析与论证得出他思想中至少具有朴素的现象学因素。本文将首先对“任务”文进行译文与译本分析,通过英法译者对“意向”的处理管窥本雅明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其次从本雅明的批判者角度反观其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将选取颇具代表性的德曼与阿多诺为对象;最后在得出本雅明思想中的确含有朴素的现象学因素的基础上,本文从胡塞尔含义论角度对纯语言作了分析,认为后者就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含义”。
(一)从“任务”译本看本雅明与意向性的关系
这里聚焦于意向性是因为它是一个为哲学界普遍关注的概念,而胡塞尔的语言分析和意义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联结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个关键桥梁。例如胡塞尔认为,从理论上说,意识可以离开语言而继续存在,反之则不行。此后,这个观点在塞尔那里找到知音,塞尔同样认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第97页。。换言之,在思与言的关系研究中,胡塞尔是一座绕不开的山。如果本雅明思想中所具有的朴素现象学因素得到确认,则有理由认为“任务”中的“意向”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无论它是否源自后者。
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不再指“意图”或“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真正将它作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是弗兰茨·布伦塔诺*倪梁康:《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第47页。。他的学生胡塞尔继承了这一思想,把现象学发展成为一门以意向性为研究核心的科学。
关于本雅明的“意向性”意识,我们可先从“任务”文的英译本谈起,因为佐恩(Harry Zohn)的英译本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汉语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在谈到“任务”文时无法忽略它的存在。这里主要以佐恩对“意向”(intention)一词的处理作为讨论对象。
笔者发现,在佐恩的英译本中,intention系列*所谓“系列”指的是同根不同词性的一系列单词,例如intention,intend,intentio等。出现了23次之多(其中intend出现8次,intention出现13次,intentio出现2次),而德语原文中只有10处——在原文使用Gemeinten或Meinen系列单词的地方,英译文有11处使用了intend系列,而原文使用intention或Intention的地方,英译文2处使用了intentio这个拉丁词汇*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81.。特别是在本雅明区分“das Gemeinte”(意指内容)和“Art des Meinens”(意指方式)之处,德曼认为这是逻格斯与词汇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说是某个特定陈述的意指内容和这个陈述意欲意指的方式*Paul De Man,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essenger Lec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4, 1983”, in Yale French Studies (97), 2000, p.27.,但颇为吊诡的是佐恩的译文中这里变成了意向对象和意向方式。显然,佐恩是从文本整体角度考虑才大胆地将“意指”改为“意向”。那么,佐恩这种处理是任性为之还是有意而为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从实施本雅明“译作为原作的衍伸”这一观念看,佐恩的译文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他应该是看出了本雅明文中所蕴含的对意向的含而未宣的关注,从而在翻译时将它表达了出来;从翻译的大胆“创作”看,佐恩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这种胆识与魄力并不难理解;从现象学角度看,“意向”的添加更有助凸显本雅明“翻译本质为纯语言的传递”这一观念。首先,由于本雅明认为无论原作还是译作都不为读者而写,因此作者与译者不可能具有普通意义上针对读者的意图、意向。所以,对文中“意向”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它主要是一种“指向”,一种原作对译作的指向,至于有没有读者反应,无关紧要。因为原作生而含有可译性,可译性体现为这种意向的指向,这是非常合理的。由于胡塞尔意义上“意向”的主要特征几乎无关“意图”,因此可以说,这里佐恩使用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与胡塞尔的“意向”一致。其次,原文与英译文出入的地方,基本上是meinen一词,本雅明没有用intend,应该与他对intend的限度认知有关。从词义上讲,meinen既可指意向又可指意图、意指,显然它比intend涵盖范围要大一些,尤其是在“意向”包含普通意义上的“意指”之处,用meinen比用intend更合适。从整体语境讲,虽然翻译超越了语言,但毕竟还是与后者密切相关,对翻译的论述不可能完全脱离语言因素,也就是说,“意指”与“意向”会有一定程度的交缠。但这就越发凸显了本雅明对“意向总体”的强调——这里他使用了intention,说明纯语言跟语言没有关系,因而德曼所总结的“翻译是纯语言,只跟语言有关”*Ibid., p.24.是对本雅明的误解;同时,这也说明本雅明对意向的特点比较了解,则前面用meinen而非intend、却被佐恩处理成intend/intention的地方应该是本雅明有意为读者/译者留下一个两可的空间。结合佐恩的学术背景——他的作品中常见的名字有马丁·布伯,弗兰茨·卡夫卡,弗洛伊德等*cf. Pam Saur, “In Memoriam: Harry Zohn”, in Modern Austrian Literature. 2001, Vol. 34 Issue 1/2.,而这些人的共性是对意识的关注,且他们都与现象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可知他对“意向”了解颇深且显然有浓厚兴趣,因而能在本雅明混合使用meinen与intend的语境中敏锐地把握住哪些译作meaning,哪些译作intention。
再来看一下法译本。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曼专门指出“任务”法语译者Gandillac作为一名哲学家,了解现象学,并于现象学在法国极为盛行时期写过相关文章,他这里用“visee intentionelle”来翻译这个“意指内容”,而按当下(德曼时期——笔者注),则应用“vouloir dire”和“dire”,也就是“意指”和“说”来对应这两个短语*Paul De Man,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essenger Lec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4, 1983”,in Yale French Studies (97), 2000, p.27.。我们看到,Gandillac也像佐恩一样,把“意指”处理成了“意向”,尤其是他又有着现象学研究背景。因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两位译者把原文的meinen系列衍伸成了intention系列,至少部分归因于他们与现象学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自然地把本雅明此处的观点与现象学归为一类,因而把后者的术语拿来处理前者meinen的翻译。至于汉译者(无论是从原文翻译还是从英译本转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跟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关,此处不提。但为什么本雅明却没有用intention系列或者说留下了“两可空间”呢?英、法译者是不是存在过度诠释的可能呢?笔者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说本雅明思想中所含有的是朴素的现象学因素——他或许没有受过现象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对“意向”的理解与把握尚未达到应有的确然性,这从他对sense与meaning的混用即可窥见一斑,后文将详细展开。
(二)从对本雅明的批判反观其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
除了译本分析,还可从学界对本雅明的批判进行反角度观望以得出佐证,进一步明确本雅明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德曼和阿多诺对本雅明观点的批判。
在对英法两名译者的批评中,显然德曼也注意到了二者对“意向”的处理。他特别指出:Gandillac做了一个与现象学有关的注脚,提到了胡塞尔,并认可后者的观点,认为意指和意指方式都是意向行为。但德曼却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尽管意指功能肯定是意向性的,但意指方式,即我进行意指的方法,却绝非先天地(a priori)必定是意向性的;若我们不考虑意义或语义而在纯粹形式层面使用语言,则不存在意向;因此两位译者这种处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一门语言现象学,或者一门诗性语言的可能性,一种建立一门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语言现象学的诗学的可能性*Ibid.。但如所周知,语言哲学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位列意识哲学之后,这也是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学本体特征的主要区别*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第96页。。可见德曼这里所谓的“语言现象学”言说并不能站得住脚。由此可推知,如果说他接触过现象学,也应该是后期海德格尔而决非胡塞尔。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参见王广州:《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研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3期。。那么,他有什么理由指责对胡塞尔现象学专门做出注解的Gandillac呢?
他还引用Caro Jacobs所说:“佐恩认为所有碎片被整合在一起,而本雅明却坚持认为最终出现的仍是一个破碎的部分。”*Paul De Man,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essenger Lec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4, 1983”, in Yale French Studies (97), 2000, p.31.从Jacobs的角度看,佐恩对于本雅明本意的理解上有出入。但从本雅明的“任务”看,Jacobs这里存在对他的误读,本雅明自己也是倾向于碎片的整合——原作与译作的和谐统一即是一例。在对“碎片”(fragment)从提喻、隐喻、转喻等进行了语词层面的细致分析之后,德曼指出,本雅明的“碎片”说并不意在构建一个整体*Ibid., p.32.。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德曼恰恰在这里暴露了他对原文主旨把握上的偏差——本雅明既然主要论证原作与译作的和谐统一,这个主旨肯定不会因为个别语词的差异而改变。这一偏差显然是由德曼的修辞语言观所致。我们还可通过德曼对象征和被象征之物的阐释来看一下:从现象学角度讲,这一对概念代表着自发性与被动性,从本雅明后文可知,他意在此,因为他强调了自发性与被动性。但德曼显然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把焦点放在象征本身的修辞功能上*Ibid., p.33.。可以说,他在这里发生的重点偏移主要是因为对现象学不了解。
关于德曼的现象学渊源,本文不予多说,因为Donn Welton对深深影响德曼的德里达现象学的批判已足够说明问题:德里达对胡塞尔作品的解读仅限于《逻辑研究》、《大观念》和一小部分《危机》这些现象学的“导论”(胡塞尔全集的前六卷),而胡塞尔1920年后的手稿,也就是他方法论的主体部分,尤其是发生现象学,德里达并未接触过。换言之,几乎完全基于德里达文本的解构主义和分析哲学在接触的胡塞尔文本范围方面同样有限*cf. Donn Welton. The Other Husserl-The Horizons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95-397.。基于此,如果德里达尚且对胡塞尔现象学了解有限,那么深受他影响的、并未对胡塞尔思想有过直接了解的德曼则更是如此。因而,我们可反角度看到,本雅明思想中正因为蕴涵了现象学因素而受到了德曼的诟病。
本雅明与阿多诺的“阿本之争”为学界所熟知,本文仅就相关现象学的部分进行讨论。本雅明在与阿多诺的通信中曾说过:“系统追问的任务不是探索隐藏的或显现的关于实在(reality)的意向性结构(intentional structure),而是解释实在的无意向性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把独立的实在要素的外在形象、影像组织起来,抽取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建构可能性。”*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第65页。其中“实在”“意向性”“可能性”等都表明本雅明对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具有一定的熟识度,因此他才会在指出阿多诺不足的时候用到它们。由此反观本雅明对纯语言的阐释,可知他不可能弃“意向”而仅仅青睐“意图”或“意指”。
阿多诺参加过关于胡塞尔的研讨班,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的先验性》。可以确定地说,他是从现象学开始接触哲学的*张一兵:《梦幻哲人阿多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29页。。阿多诺认为,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充满了像范畴直观那样自相矛盾的观点*[德]阿多诺:《胡塞尔与观念论问题》,陈磊译,《世界哲学》2015年第3期,第12页。,但由于缺乏对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理路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阿多诺对范畴直观的批判仍然带有局部性和断想性的特征*马迎辉:《范畴直观与现象学的悖论——反思阿多诺对范畴直观的批判》,《现代哲学》2014年第1期,第72、76页。。阿多诺的确抓住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制高点——范畴直观——来展开批评,但显然他并未真正了解胡塞尔的奠基观念,因而无法清楚在胡塞尔视域中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感知与范畴、经验与超越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阿多诺的相关思想与相关表述给人的总体印象仍然是缺乏方法上的明晰性与可控性,仍然是在避现象学方法之难而就辩证方法之易*倪梁康:《过渡与间域——阿多诺的哲学定位》,《读书》2001年第11期,第79页。。
本雅明的哲学兴趣主要集中在康德 (包括新康德主义)那里而不是黑格尔那里*赵勇:《在辩证法问题的背后——试论“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的哲学分歧》,《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124页。,而在海德格尔和阿多诺之间则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海德格尔早期使用的“存在的显现”与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无异,但后期却抛弃了这个原则*参看倪梁康:《过渡与间域——阿多诺的哲学定位》,《读书》2001年第11期,第79页。。鉴此,当本雅明与胡塞尔的哲学兴趣都与新康德主义十分接近,而与本雅明观点相对的阿多诺与胡塞尔的理念也背道而驰时,可进一步推知:本雅明思想中含有朴素的现象学因素。
(三)本雅明的“纯语言”与现象学的“含义”
本雅明在弗莱堡大学读书期间,与海德格尔做了三年同学*Thomas Klikauer, “Review Essay”, in Working USA: 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016(6), p.270.,而且从其入学时间(1912)和后来他对海德格尔就职演说(1933)的不屑——认为那是一堆胡话*Ibid., p.271.——看,他比较认同早期海德格尔(1929年之前)的思想,也就是说,本雅明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是胡塞尔式的,因为早期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想一脉相承。此外,本雅明还是莫里茨·盖格尔的学生,而盖格尔作为现象学慕尼黑学派的成员,尤以现象学审美学与对现象学方法的研究而著称*详情参见倪梁康:《现象学美学的起步——胡塞尔与盖格尔的思想关联》,《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他与胡塞尔的相熟程度不言而喻。笔者认为,这些背景足以确定本雅明对现象学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鉴此,我们从胡塞尔的含义论角度来看“任务”一文的核心观念具有了合理性及可行性。
语言是意识(包含思想)用来表达和交往的工具——而意向性表现了意识的基本性质。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向总是指向某物,不论该物是否实存*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第96页。。因此我们先来看纯语言的结构性:原作与译作在纯语言即意向总体上关联,原作意识指向译作,所以才有了原作生而蕴含着可译性;译作意识指向原作,所以才有了译作是原作的衍伸,而这些都要通过语言表达来操作,于是就有了一个关联:
原作/源语→意向总体/纯语言←译作/译入语
而纯语言超越了语言层面,始终如一。
再看一下纯语言的发生性。本雅明认为:“在个体的、未被补充的语言中,意义从来不会具有像其在个体语词或句子中那样的相对独立性;相反,它处于一个持续的流(flux)的状态——直到它能作为纯语言从各种意向方式的和谐中脱颖而出。”*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78.可知作为纯语言的意义在脱颖而出前始终处于流动中,再进一步,它脱颖而出后也并非当即锁定,而是会向译入语渐入,从显性重新变为隐性,没入译入语的意义中,待读者将其挖掘。所以本雅明接着说:“直到此时,它依然藏在语言内部……是翻译点燃了作品的永生之火,造就了语言的恒久延续。”*Ibid.可见,发生性是纯语言出现的必要条件,这是不容忽略的。它的表象为何呢?答案是含义的转渡,或者用本雅明的话说是意义的传递。从最表层看,这个传递发生在原作到译作,或者源语到译入语。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角度看,如果以纯语言为基点,则它脱颖而出的当下属于现在,之前的时间属于滞留,之后的则属于前摄,三者并非客观意义上可独立分开的三段时间,而是处于一条不间断的流中,每个当下都是“现在”,即“现在”是超越客观时间的,而“现在”瞬间即成“滞留”;而且这个时间之流也并非单线性的,而是叠加式前行,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前浪并未消失,只是被后浪所淹没。由此可更清楚地看到,纯语言从源语一路流向译入语,或许在某一时刻它会被捕捉,或许瞬间又消失不见,但却始终在其中,一以贯之。这样说只是从其特性角度而言,并非说纯语言无法传递,因为它始终在意识之流中,所以不可能消失,只是会随意识“主体”的改变,例如从作者经译者再到读者,而更换载者。但我们看到,就如同渡河之人,在此岸、河中和彼岸的,都是同一个人。
当纯语言的结构性与发生性都得到了现象学角度的阐明,可以说它与胡塞尔的“含义”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胡塞尔的Sinn和Bedeutung分别被英译为sense和meaning/signification*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是后者,这是从整体角度讲的,即侧重成熟后的“含义”——笔者。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第76页。。早期胡塞尔例如在《逻辑研究》中,这两个单词是混用的。一般说来,“含义”在与表达行为相关联时可以称作“语义”,在与直观行为相关联时则可以称作“观念”。换言之,“观念”或“本质”或“先天”在与语言发生联系时会以“语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倪梁康:《何为本质,如何直观?——关于现象学观念论的再思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第51页;倪梁康:《哥德尔与胡赛尔:观念直观的共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可以看到,含义与语义并不在一个层面。从作为客体化行为的直观行为为作为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达行为奠基看,观念显然属于为语义奠基的质料,则可知语义的背后还有观念存在,后者比前者隐藏得更深。此外,从观念即本质看,可知本质的东西在直观行为中,待到了表达行为时,本质之物也披上了一层外衣——语义。随着含义论的发展成熟,差异慢慢凸显,逐渐形成一种三层结构——signification/meaning指的是最内层的含义,即观念统一,sense指意义,meaning指语义。
本雅明在“任务”文中也基本混用sense与meaning。例如,他指出“显而易见,在对形式复现中所要求的忠实极大阻碍了对意义(sense)的传递”,又说“翻译一定要尽量避免想要交流什么、传递意义(sense),这样的话,原作对它而言重要仅仅是因为它已使译者及其作品从接近和表达被传递之物的努力中解脱出来”。*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79-80.可见,两处sense所指并不相同:第一处是本雅明不希望看到的,因为sense的传递为形式复现所困,可知它与语言不相关;第二处是本雅明希望做到的,即“翻译一定尽量避免想要传递意义”,可知它仅指语义。而之前之后的语境中都是meaning。例如翻译避免传递意义的原因是“不应追求与原作意义(meaning)的相似”,可知第二处sense与这里的meaning所指相同;待到后文“关于意义(meaning),一个译作的语言能够——实际上是必须——让其自身离开”*Ibid., p.81.,则meaning又与第一处sense所指相同,都与语言无关。
从“本雅明不仅要求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意义之相当和语义之相近”*曹明伦:《揭开“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86页。可见,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意义与语义的区别,只是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这个“意义”为何。这里尝试进一步阐明:首先,从英语和德语单词的表达看,语义往往指的是meaning/Bedeutung,而意义是sense/Sinn;其次,由于这两个词是同义词,经常被混用,所以当它们作为差异词出现时,我们需要清楚差异何在——语义相似意味着深层意义的不同,这是同义词辨析的一个基本原则,显然sense比meaning深了一层;再次,从“任务”语境看,sense和meaning都不是纯语言,可知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纯语言最深,其次sense,再次meaning。此外,虽然本雅明对meaning和sense基本是混用,但他在一处非常清晰地给出了区分二者的语境:“在其诗性意指中,意义(sense)并不局限于语义(meaning),而是来自被用以表达它的语词所传递的内涵(connotations)。”*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Harry Zohn (tran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80.可见,本雅明自己对sense的定位是语词所传递的内涵,这再一次明确了它不是纯语言,也非语义。胡塞尔始终认为:“这个共同的、客观的世界是被设想的,它是被我与他人所意识到的,但它不是被我体验到的,因为它隐含着对没有真正被体验到的和无法真正被体验到的、而是被他人体验到周围世界。”*[瑞士]耿宁:《意识统一的两个原则:被体验状态以及诸体验的联系》,倪梁康译,《世界哲学》2011年第1期,第10页。意义的缺失可由此得到解释。在翻译语境中,这首先决定了译者无法像作者本人那样领会原作的完整意义;其次决定了读者同样无法完整领会译作。也就是说,意义的缺失是一个无解的短板。综上可知,本雅明停留在了意义层面而未再进一步深入,而现象学的角度则让我们透视到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存在,它才是那个一以贯之的纯语言,这也进一步明确了笔者前述的三层结构,即语义-意义-含义/纯语言的逐层递进。
当本雅明与现象学的勾连得到证实,可以说,本雅明的纯语言作为意向总体和终极本质,就是胡塞尔意义上作为观念统一的含义(或本质、观念)。按本雅明的观点,翻译的本质在于纯语言的传递,那么我们有理由说:翻译的本质就是含义的转渡。这里有一个汉语表达的问题。笔者认为“传递”和“转渡”相比,前者对所传递之物的保全性不如后者强,即转渡不会改变那一以贯之之物,而意义在传递过程中却有所缺失。所以含义既然不变,转渡它比传递它更符合语境。
基于上述,当我们可借助胡塞尔含义论理清本雅明的纯语言为何物时,至于所谓“纯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这种命题,因其缺乏科学论证,在人们为它找到更有力的依据之前,不如先将上帝“悬搁”。
B516.6
A
1000-7660(2017)05-0091-08
张 琳,山东潍坊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青岛 266109)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现象学视域中的翻译本质”(J14WD09)
(责任编辑任之)
——专栏导语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