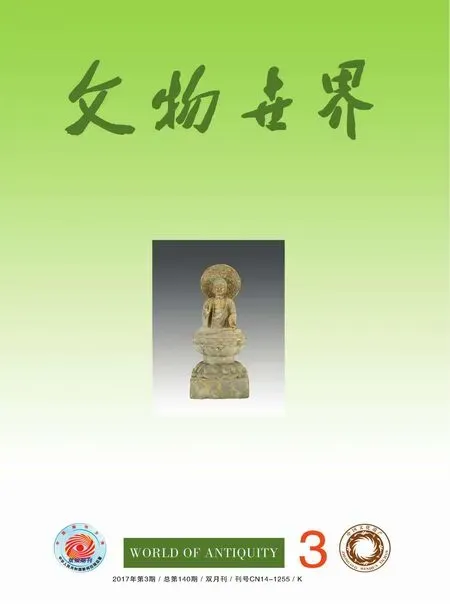山西省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阴武夏
山西省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阴武夏
山西省隋唐考古有很多重要发现,遗址方面有晋阳城、蒲州故城、绛州官署等,墓葬方面有虞弘墓、薛儆墓、温神智墓等,宗教遗存方面有佛道教石窟和大量造像窖藏,手工业方面有陶瓷窑址。本文以这四方面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山西隋唐考古的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
山西 隋唐考古 遗址 墓葬 宗教 手工业
山西省在隋唐时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隋炀帝曾受封为晋王,李唐王朝从此起兵。山西为唐基业所在,太原被封为北都。相应地,山西省在隋唐时期遗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量展开,山西省隋唐考古又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遗址、墓葬、宗教遗存、手工业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山西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山西地区历史时期的城址,近年来开展工作较多,且多为带有课题性质的主动性发掘,涉及到隋唐时期的有晋阳古城、蒲津故城、绛州州署遗址,其他类型的遗址有黄河古栈道遗址和小浪底集津仓遗址。
1.晋阳古城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晋源区,其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前497年),历经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毁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晋阳城从建成到废弃连续使用1500年,城址保存较好,文化遗存丰富,尤其是唐五代时期。
最早对晋阳古城进行考察的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1]。新中国成立后,宿白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也对晋阳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察,根据地表残存的西城墙遗迹和东城的地名信息,并参考《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体复原了晋阳城的轮廓[2]。谢元璐、张颔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对晋阳古城遗址作过初步的勘察,在古城内中部发现一段东西向城墙,推测其为唐代所建[3]。
大规模调查晋阳古城遗址的工作始于21世纪后,前十年的工作主要以调查勘探为主,调查了城墙和城内建筑基址[4]。2010年,晋阳古城遗址获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后,晋阳古城考古队根据之前的调查结果,对重要城墙、夯土基址进行了试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本搞清了从北朝至宋晋阳古城的情况。
城墙方面的成果有,将西南城墙夯土的第三期年代推定为隋到中唐以前,第四期为唐末至五代[5]。此外,苗圃区域内新发现一段唐代城墙[6]。建筑遗址主要发现两处,一处位于西城墙东,该遗迹为一组复杂建筑遗址,即一号建筑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晚唐时期的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带回廊的寺庙建筑,出土了大量瓷片与建筑构件。另一处位于晋源苗圃花窖门口,是一处晚唐五代时期的小型房址,还有7座灰坑和1座窑址。出土遗物主要有建筑材料和日用器具。苗圃区域内其他唐代建筑遗迹与北朝建筑遗迹集中分布,互相叠压,唐代建筑基址保存较差[7]。
晋阳古城东部文化层经过地质钻探,推测应为汾河改道前的古河床,或为文献中记载的“跨水联堞”的唐中城[8]。
2.蒲津故城
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遗址分东、西两城,其中东城现存主要为唐代遗迹,2011年至201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蒲州故城东城的东南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唐五代的遗迹遗物。遗物主要有陶器、瓷器、建筑构件、雕塑、棋子、钱币、骨制品等。其中瓷片种类主要有黑瓷、白瓷、青瓷及少量茶叶末釉瓷和三彩残片。
蒲州故城西门外为蒲津渡遗址,是黄河中游古代三大渡口之一,也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蒲津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发现了铁牛,在对铁牛进行了原位提升、隔水层保护后,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搞清了铁牛的下部结构和遗址地层问题,并发掘到了唐代中期的地层。发现了唐代蒲津桥引桥吊路,其使用年代从唐沿用至宋金时期[9]。
3.绛州官署遗址
绛州州署遗址位于绛州县城西北部的一处高崖上,遗址区中心现存元代大堂遗构,其北面存有清代二堂建筑,最北端为始建于隋代的绛守居园池。
绛州衙署遗址自唐创建,历代皆在原址沿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主动性发掘,唐代遗存发现较少。在现存州署大堂前的西侧附属院落区发现唐代的一块砖铺地面和一处砖砌窖藏,遗物多为砖瓦等建筑构件,还有两个唐代典型的玉璧底白瓷碗和双耳陶罐[10]。在现存二堂以北、绛守居园池以南的宋代夯土建筑基址下发现了两片杂乱无章的铺砖,其时代要早于夯土遗迹,推测或为唐代遗存[11]。
最北端的始建于隋代的绛守居园池,俗称“新绛花园”,亦称“莲花池”,199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试图厘清居园池历代沿革和唐代建筑景观的位置及残存遗迹[12]。
4.其他类型
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山西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以东的黄河北岸的古栈道遗址做了详细的考古勘察。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沿河地段内,发现古代黄河栈道遗迹40处,累计长5000余米[13]。
其中唐代黄河古栈道主要位于两个地点,一处是垣曲安窝[14],在五福涧有“大唐贞观十六年”、“总章三年”的题记两处。另一处是平陆西河头地点,其开凿年代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15]。
集津仓遗址位于平陆县城东,为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唐宋时期的遗迹遗物较为丰富,唐代遗迹有残房址1座,遗物以各类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为多,还有陶瓷器、铜钱等[16]。
二、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1.隋代墓葬
隋建国短暂,隋墓上承南北朝,下启初唐,在文化面貌上不易划分。山西省的隋代纪年墓共发现6座,分别是昔阳开皇三年(583年)王季族墓[17],沁源开皇四年(584年)韩贵和墓[18],汾阳开皇十五年(595年)梅渊墓[19],太原开皇十七年(597年)斛律徹墓[20]、太原开皇十八年(598年)虞弘墓[21],襄垣大业三年(607年)浩喆墓[22]。这些墓主多为等级较高的品官,墓葬形制为砖室墓。此外,太原西南郊发现1座无纪年的长方形土洞墓[23],临汾市西赵村发现2座隋墓[24]。
隋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星墓葬”入华粟特人首领虞弘墓,研究成果丰厚,主要有墓志考释、入华粟特人的石葬具及其图像内容释读、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如发掘者张庆捷探讨了墓志中鱼国的史地和石椁上图像的涵义[25]。荣新江根据虞弘墓志和并州胡人龙润墓志,分析了隋唐时期并州粟特聚落的演变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26]。杨晓春和罗丰分别探讨考证了虞弘墓志中记载的史事[27]。齐东方在虞弘墓简报的述评中指出,以虞弘墓为代表的近年发现的安伽、史君、康业墓这些粟特墓葬在北朝至隋代已将自己的信仰系统和中国的葬式结合起来[28],并另撰文指出“狩猎图”应为“搏斗图”及表现出的西方文化特征[29]。姜伯勤探讨了祆教画像石中所见的胡乐图像,其中谈到了虞弘墓基座正面的胡乐图像与祆教火祭[30]。毕波指出石椁画像中的“夫妇宴饮图”中的女主人应为天界女神,此幅图像的主题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情景[31]。杨巨平解读了虞弘石椁图像所表达的波斯祆教经典、神话传说、宗教仪礼习俗等[32]。此外,隋墓个案的研究还有张红旗对斛律彻墓出土的俑类进行了类型学研究[33]。
2.唐代墓葬
山西省发现的唐代墓葬较多,但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前期,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太原与长治两地。建国后至80年代,这一时期发现的重要唐代墓葬有太原地区的董茹庄唐壁画墓[34]、市郊区唐墓[35]、晋祠唐墓[36]、南郊金胜村唐墓群[37]、西南郊的5座初唐墓葬[38]。长治地区的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唐墓[39]、长治北石槽唐墓[40]、长治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墓葬[41]、代宗大历六年(771年)王休泰墓[42]。侯马地区的3座唐墓[43]。大同西南郊发现的3座初唐时期的墓葬[44]。临汾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群中发现的1座唐墓[45]。
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前,唐墓的重要发现有太原地区的南郊壁画墓[46]、金胜村337号壁画墓[47]、金胜村555号唐墓[48]。长治地区的防爆电机厂唐墓[49]、宋家庄万岁登封元年(696年)范澄夫妇墓[50]、天授二年(691年)冯廓墓[51]、景云元年(707年)李度墓、贞元八年(792年)宋嘉进墓[52]、郝家庄大中三年(849年)郭密墓[53],北郊永昌元年(689年)崔拏墓[54]。大同振华南街唐墓[55]。忻州大中九年(855年)高徵墓[56]。运城地区的万荣皇甫村开元九年(721年)薛儆墓,该墓是目前山西地区级别最高的唐墓[57]。此外,发现的唐代墓志有裴晧及其妻郑氏墓志[58]、襄垣武后时期的连简及妻张氏墓志、向彻及妻韩氏墓志[59]、姚元庆墓志[60]和裴怦墓志[61]。
2000年后发表资料的山西唐墓有太原地区的晋源镇果树场开元十八年(730年)温神智墓[62]、晋源镇3座唐壁画墓[63]、西北环城高速路中发现2座唐墓[64]、晋源区乱石滩唐大中九年(855年)左政墓[65]。汾阳的东龙观和西龙观也发现了一些唐墓[66]。长治地区有上元三年(676年)王惠墓[67]、襄垣浩氏家族墓[68]、襄垣久视元年(700年)李石夫妇合葬墓[69]、屯留西李高唐墓[70]、潞城羌城唐墓[71]、长治云步街唐墓[72],以及临汾尧都区西赵村的10座唐墓[73]。大同地区有南关唐墓[74]、浑源唐墓[75]、城西基建工地的4座唐墓[76]。
目前,山西唐墓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结语部分,为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对年代的推断。
第二类是综合性的研究,主要有《山西考古四十年》[77]、《中国考古六十年》(山西部分)[78]对山西隋唐墓葬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外,较为全面的研究有吉林大学华阳的硕士论文和北京大学李雨生的博士论文。华阳对山西地区唐墓的形制、随葬品、壁画等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与周边地区材料进行比较,大致勾勒出了山西地区唐墓的面貌[79]。李雨生的论文中增加了隋唐墓葬的最新发现,将山西隋唐五代墓葬置于整个北方墓葬系统的大背景下,通过重新认定分类标准和细读墓志,讨论了墓主身份与墓葬形制的对应关系及差异原因,是目前山西隋唐墓葬最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80]。区域性研究有杨丽萍、郎保利梳理了太原与长治地区唐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并总结了两地墓葬的区域性特征[81]。张宏梅分析了长治地区14座唐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及其反映的长治地区唐代的社会生活[82]。
第三类是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等级最高的薛儆墓[83],齐东方先生在书评中谈到薛儆墓的墓葬形制与葬具存在僭越,与当时借丧葬活动做现实政治文章的背景密不可分[84]。学者们的研究亦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僭越及其原因的探讨上,如华阳指出薛儆墓是山西唐墓的一个特例,其依俗归葬但丧葬习俗仍采用了长安墓葬制度,且存在僭越,并分析了无谥号的原因[85]。李雨生通过细读墓志,并综合其他出土材料,再次探讨了薛儆墓的墓葬形制和等级问题,对发现的几个“异象”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解读[86]。
第四类是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墓志、墓葬壁画和出土瓷器三个方面。墓志方面的研究有梁恒唐、梁晋红点校了武客、武则、武道景三方墓志,以此探讨了文水武氏家族[87]。邹冬珍对裴怦墓志铭进行了考释[88],韩利忠、范丽娅考释了平定龙庄唐代墓志铭[89]。刘天琪对晋东南地区唐代墓志的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墓志盖题铭进行了分类研究,从美术史的角度分析了墓志纹饰的源流及其背后蕴含的丧葬文化与礼仪[90]。壁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树下老人”屏风画的探讨,如赵超在唐墓屏风式壁画的研究中,着重对“树下老人”的题材进行了讨论,介绍了它的内容、流行时代与地区、历史渊源等[91]。张童心探讨了薛儆墓残存的壁画内容,认为西壁南部残存的绘画人物为竹林七贤和荣启期,但其具体历史面貌早已淡化,这一题材与太原唐墓壁画更为相近[92]。商彤流梳理了太原发现的唐墓壁画,重点分析了壁画中“树下老人图”的内涵及作用[93]。马晓玲梳理了北朝至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屏风式“树下老人图”的传布,以及在社会大背景的转变下这一题材在丧葬文化中所承载的意义和发生的变化[94]。此外,还有马金花对山西唐代墓葬壁画的综述性研究[95]。墓葬出土陶瓷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谢明良对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器进行的系统研究[96]。
三、宗教遗存
宗教遗存主要分为石窟寺与造像窖藏两类。山西隋唐石窟寺有佛教与道教两种。佛教石窟寺主要有天龙山石窟与西山大佛。天龙山隋代洞窟为东峰隋开皇四年(584年)开凿的第8窟。唐代有十五座洞窟,分别是第4-7窟、9窟、11-15窟、17-21窟,开凿年代大致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97]。开凿于北齐的西山大佛前还发现了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所建面阔五间的大阁建筑遗址[98]。2015年对佛龛、佛阁、佛塔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佛阁为隋创建,唐会昌灭佛被毁,晚唐李克用重建,后晋刘知远重修[99]。道教石窟寺有龙山石窟,其第4、5窟开凿年代最早,可能为唐代[100]。
发现的造像窖藏中佛教造像占大部分,道教造像较少。佛教窖藏主要发现于运城和长治,时代集中在唐代早期,可能是武宗会昌五年大兴灭佛时,人们埋藏起来的。运城平陆县发现有三处窖藏,分别是城西西侯村的隋唐时代的59件铜造像。圣人涧发现一处以鎏金铜造像为主并兼有石造像的窖藏,共34件。
上张村出土了北魏至隋的7件佛教造像[101]。长治市发现两处窖藏,一处位于平顺县西南的荐福寺遗址内,另一处位于壶关县北辛村,出土了12件青石佛教造像碑[102]。此外,沁县南涅水石刻窖藏中,也发现少量唐代造像和一块咸通九年(868年)碑刻[103]。晋中市榆社县还发现两处佛教造像窖藏,一处为福祥寺大殿地面下发现的40多件佛教石造像窖藏,另一处窖藏出土近百件佛教造像,时代大约是从北魏晚期到唐末五代[104]。
山西隋唐时期的塔基发现两处,分别是临汾安泽县的郎寨砖塔[105]和太原晋阳古城西山腰上的龙泉寺[106]。佛教岩画一处[107]。此外,还有一处较为特殊的宗教遗迹是位于灵丘县西南山区独峪乡的曲回寺石像冢[108]。
四、手工业遗存
手工业方面的发现以瓷窑址为主,山西唐代的瓷窑址在晋北、晋中、晋南均有发现,晋北主要有浑源瓷窑址[109]、界庄瓷窑址,晋中有介休洪山瓷窑址,晋南有河津北午芹瓷窑址等。但经过正式发掘且发表资料的仅有浑源的界庄窑,瓷器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三彩器和绞胎器。根据出土器物特征推测时代在中唐后期至晚唐前期[110]。
综上所述,山西隋唐时期的遗迹种类与数量均非常丰富,并且有很多重要发现,为我们研究隋唐时期的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丰富的资料。
(注:本文资料收集至2014年)
本文为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E04。
[1]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山西古迹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2]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3]谢元璐、张颔《晋阳古城勘察记》,《文物》1962年第Z1期。
[4]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阳古城遗址2002-2010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世界》2014年第5期。
[5]晋阳古城考古队《晋阳古城西南城墙水渠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4年第5期。
[6]晋阳古城考古队《晋阳古城新发现城墙解剖》,《文物世界》2014年第5期。
[7]韩炳华《太原晋阳古城遗址二○一二年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7月19日第8版;晋阳古城考古队《晋阳古城遗址2012年试掘简报》,《文物世界》2015年第5期。
[8]晋阳古城考古队《晋阳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文物世界》2014年第5期。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黄河蒲津渡遗址》,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杨及耘、王金平《考古发掘确定山西绛州衙署遗址年代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23日第8版。
[11]杨及耘、曹俊、王金平《山西新绛绛州州署遗址Ⅱ区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11日第8版。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14]李百勤《垣曲安窝黄河古栈道调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山西平陆县西河头黄河古栈道遗迹》,《考古学集刊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6]张童心《山西发现小浪底集津仓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29日第1版。
[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昔阳县沾尚镇瓦窑足村发现隋宁州刺史王季族墓葬》,《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郎保利、杨林中《山西沁源隋代韩贵和墓》,《文物》2003年第8期。
[19]山西省博物馆、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北关隋梅渊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21]张庆捷、畅红霞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22]襄垣县文博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垣隋代浩喆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25]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
[26]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
[27]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
[28]齐东方《读〈太原隋虞弘墓〉》,《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3日第4版。
[29]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
[30]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所见胡乐图像》,《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31]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32]杨巨平《虞弘墓祆教文化内涵试探》,《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
[33]张红旗《从斛律彻墓出土的陶俑看隋代的服饰装束》,《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34]《山西太原董茹庄唐墓壁画》(照片四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35]解廷琦等《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庙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6]王玉山《太原晋祠镇索村发现唐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
[37]沈振中、吴连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发现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戴尊德《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年第1期;山西省文管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
[38]代尊德《太原西南郊区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39]山西省文管会《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40]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41]王秀生、丁志清《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8期。
[4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
[43]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地区东周、两汉、唐、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6期。
[44]边成修等《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45]王寄生等《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群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4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47]侯毅、孟耀虎《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48]侯毅《太原金胜村555号唐墓》,《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
[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防爆电机厂唐墓》,《文物季刊》1995年第4期。
[50]侯艮枝、李奉山《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51]侯艮枝、朱晓芳《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52]侯艮枝《长治市西郊唐代李度、宋嘉进墓》,《文物》1989年第6期。
[53]王进先、朱晓芳《山西长治县郝家庄唐郭密墓》,《考古》1989年第3期。
[54]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55]白艳芳《山西大同振华南街唐墓》,《文物》1998年第11期。
[56]李有成、李培林《唐秀容县令高徵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
[57]张童心《唐薛儆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7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58]杨明珠、张英俊《唐裴晧及其妻郑氏墓志铭》,《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59]向文瑞《襄垣县发现唐武后时墓志碑石》,《文物》1983年第7期。
[60]李百勤《姚元庆墓志铭》,《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
[61]邹冬珍《唐〈裴怦墓志铭〉考》,《文物世界》2007年第2期。
[62]常一民、裴静蓉《太原市晋源镇果树场唐温神智墓》,《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
[63]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晋源镇三座唐壁画墓》,《文物》2010年第7期。
[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西北环高速公路建设墓葬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65]冯钢《太原市晋源区乱石滩唐左政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6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
[67]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68]山西大学文博学院等《山西襄垣唐代浩氏家族墓》,《文物》2004年第10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垣唐墓(2003M1)》,《文物》2004年第10期。
[69]山西大学文博学院等《山西襄垣唐代李石夫妇合葬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7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屯留西李高唐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0年第5期。
[71]秦秋红《潞城羌城唐墓》,《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72]白红芳《长治云步街唐墓》,《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7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7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7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浑源唐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1年第5期。
[7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新发现的4座唐墓》,《文物》2006年第4期。
[7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7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六十年》(山西部分),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79]华阳《山西地区唐墓初探》,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80]李雨生《山西隋唐五代墓葬析论》,《西部考古》第6辑,2012年。
[81]杨丽萍、郎保利《太原与长治唐墓的比较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82]张宏梅《山西长治地区唐墓的初步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8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84]齐东方《〈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书评》,《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85]华阳《论薛儆墓的形制及等级问题》,《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86]李雨生《山西唐代薛儆墓几个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
[87]梁恒唐、梁晋红《从三方唐代墓志看文水武氏家族》,《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88]邹冬珍《唐〈裴怦墓志铭〉考》,《文物世界》2007年第2期。
[89]韩利忠、范丽娅《平定龙庄唐代墓志铭考释》,《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90]刘天琪《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墓志盖题铭——以新发现的晋东南地区唐代墓志纹饰为研究重点》,《美术学报》2011年第5期。
[91]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屏风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年第2期。
[92]张童心《唐薛儆墓壁画上的一个问题》,《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1期。
[93]商彤流《太原唐墓壁画之“树下老人”》,《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
[94]马晓玲《从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向现实生活意趣的转变——以北朝—唐墓室发现的屏风式“树下老人”图为中心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95]马金花《山西唐代墓葬壁画艺术》,《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
[96]谢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中国陶瓷史论集》,允晨文化,2007年。
[97]李裕群《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1期;《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98]李裕群《晋阳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
[99]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204/53005.html.
[100]张明远《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文物》1996年第11期;《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101]平陆县博物馆《山西平陆县出土一批隋唐佛道铜造像》,《考古》1987年第1期。
[102]侯艮枝、刘宝琳《壶关县出土一批石造像》,《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
[103]郭勇《山西沁县发现了一批石刻造像》,《文物》1959年第3期。
[104]崔利民、宋文强《山西平顺县荐福寺遗址出土的唐代佛教石造像》,《考古》2007年第8期。
[105]王春波《山西安泽县郎寨唐代砖塔》,《文物》2011年4期。
[106]李艳《山西太原唐佛塔地宫出土五重棺椁》,《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8日第2版。
[107]崔利民、刘跃忠、杨冠《山西襄垣县化岩角山隋唐时期佛教岩画》,《考古》2011年第5期。
[108]张童心、张庆捷《曲回寺石像冢——盛唐时期塞北边陲的宗教遗迹》,《上海文博论丛》2004年第2期。
[109]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界庄唐代瓷窑》,《考古》2002年第4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