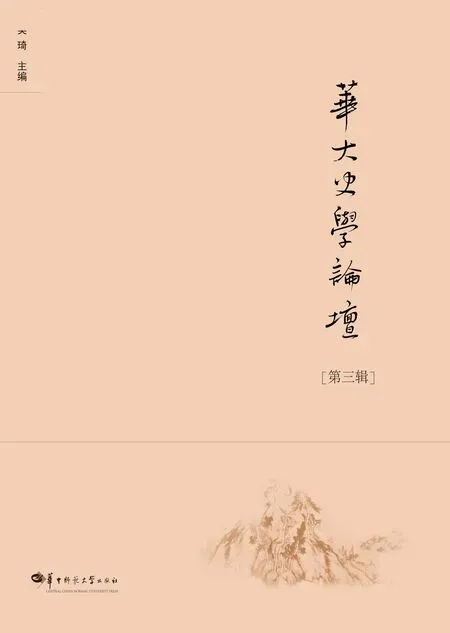从默许到镇压:“五四”时期的王占元及武汉学生运动
邓慧娟
引 言
1919年爆发的五四学生运动,不仅在当时迅速横扫全国,更是在日后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策纵甚至断言,不了解这个运动,“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脾性”[注]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页。。正因其如此重要,故在后世的研究中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研究成果称得上汗牛充栋,基本经历了解放前、建国初期、1990年代的繁荣期和当下的开拓期四个阶段[注]代表性著作有1935年出版的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六十年代华裔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近些年来陈平原借鉴年鉴学派的方法,出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海外也有一批相当成熟的成果,其中包括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除了相关通论性著作外,关于五四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进展亦有不少著述和资料出版,对推进学术认知有所裨益[注]其中包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武汉:长江出版社,2009年;胡汶本:《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庞守信、林浣芬:《五四运动在河南》,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等。。同时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如胡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的研究亦非常丰富*代表性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崔志海的《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等。。
通观当下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点:作为运动中心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五四运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相关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不过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谈到的:“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五四运动在学界的研究中多被视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是现代中国的开端,但正如冯筱才所说,人们往往将“群众运动”与“群众的运动”等同起来,而对于“运动政治之实际”缺乏足够的关注*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因此,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需要得到更好的再解释,观察的重点不应仅限于运动的中心城市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于武汉这样的非中心城市和执政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作为政治革命的“五四”及其在地方的运动过程。
本文拟通过分析处于特殊位置的王占元在五四学生运动期间的态度变化,突出作为地方长官的他在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维持地方安稳和追求政治声望之间的矛盾。
一、王占元督鄂与“五四”前的湖北政局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今属河北)。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还曾加入宋庆的毅军*田子渝,等:《湖北通史·民国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1895年投袁世凯所编练新建陆军工程队,任队官、管带、标统*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674页。。辛亥后,黎元洪主政湖北,后由于二次革命,袁世凯借调黎元洪赴京并安插自己的心腹段祺瑞、段芝贵主政湖北。同时,为驱逐黎元洪离鄂,1913年4月王占元率军驻湖北。1914年4月他被任命为湖北帮办军务,12月代理湖北军务*田子渝,等:《湖北通史·民国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并最终在与段芝贵的争权中获得胜利,1915年8月段调任奉天,王占元暂行代理湖北事务,虽然中央依旧任命了张锡銮为湖北将军,却因王占元的阻碍未能上任。可见彼时,握有兵权的王占元已有效地控制了湖北。到1916年1月王占元被任命为襄武将军,接管湖北军务,正式掌管湖北[注]《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2期,第13页。。同年7月他又兼任了湖北省省长,一时间将湖北的军政大权全部攘于手中[注]《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9期,第1页。。虽然之后,湖北省省长由何珮瑢接任,但何乃是王的心腹,政事多听令于王[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王接管湖北后不久,护法战争爆发,王占元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做法,一面积极准备防务,另一面则与李纯、谭延闿等协商,主张与西南方面调和,而主要目的则是维护武汉安定[注]《湘省之时局问题与财政》,《申报》1917年7月1日,第6版。。1917年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王占元联合李纯、陈光远发表电文,主张停战和谈,这也是作为湖北督军的王占元为数不多的以全国大局为瞻的电文。不过不久,因护法战争爆发,黎天才、王安澜、石星川等在湖北组织靖国军,形势陷入混乱,主张求和的王占元开始改变主意,作为湖北督军的他显然不能容忍辖区的叛乱,但若反对和谈,暂不论与直系首领冯国璋[注]“王在北洋系中,与冯国璋比较密切,所以冯为江苏督军和代理总统时期,王占据湖北地盘得以稳固,后与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并称长江三督,威视睥睨一时。”见《我所知道的王占元——郑廷玺遗稿》,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5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第252页。无法交代,湖南的失守同样也会危及王占元对湖北的统治,因此他只得提出将荆州、襄阳等暴乱地区化为治匪区域,不视为西南和议的范围[注]《南京快信》,《申报》1918年1月17日,第3版。。这样来回矛盾的态度,皆是以统治辖区的安宁为出发点。而这种处理动乱的原则,在1919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中体现得更为清晰。
随着一战结束,在各国列强主张以及国内呼吁和平之声日沸的背景下,吴佩孚在湖南衡阳宣布停战,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此前王占元等多次呼吁和谈,因此在舆论界赢得了不少赞誉。但南北和会没开多久,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就传回国内,皖系的统治再次遭到了攻击。此次和会牵涉多方势力,即便是南北双方内部意见亦不见统一,而其后事实更是证明,由皖系主导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的徐世昌竟意图借这次和谈取消国会[注]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连国会任命的政府和国会意见都不能统一,更遑论本就作为反对党的研究系、国民党等派系。至于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注]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不过作为直系要员,湖北督军的王占元,此时并没有同吴佩孚一般直接站出来反对皖系,而是与同为直系要员的李纯、陈光远一样,对和谈和学生运动起初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注]李纯和陈光远观望的具体材料,见《赣学界游行警告团经过纪》,《申报》1919年5月17日,第7版。。与吴佩孚的选择不同,自然与王占元本人的性格有关,不过王占元所处的位置本就与军人吴佩孚不同,他在学生运动期间身兼多重身份,要平衡多方势力。相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其所管辖的湖北此时仍旧处于从属位置;而相对于控制国会的皖系而言,王占元作为直系要员,处于对立位置;作为湖北督军,一方面王占元有维护地方安稳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人物,能否得到民众和舆论的认同也是王占元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这种多重身份的困扰下,王占元所管辖的湖北成了当时除京、沪地区外学生运动和镇压最为激烈的地区。
二、默许:学生运动初起与王占元之应对
(一)运动初起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在48小时之内答复。两天后,袁基本接受日本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于是中国人民把“五月七日”、“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年是日全国各地学生都举行纪念活动,藉以激励全国人民发奋图强。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运动。5月6日,武汉报纸《汉口新闻报》首先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此则消息即在武汉广泛传播开来。武汉学界得知此事,当即成立学生联合会,后不断开展学生运动。武汉虽不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地区,但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着各派政治势力的纠葛。
1919年“五七”前夕,武汉学生正在酝酿纪念“五七国耻”,筹印传单,上街发散。各个学校都有筹备纪念活动,如中华大学预备举行运动会[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36页。,但各纪念活动“并不是联合行动,而是各个学校单独进行”[注]郑南宣:《“五四”运动在武汉》,1979年,见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湖北: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郑南宣系五四运动中武汉中华大学学生代表,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是以本人认为该作者对武汉五四运动内情极为了解,有一定可信之处。。正值此时,武汉方面得知青岛问题结果不良,民情为之哗然。迨至5月6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全鄂学界愈加激愤。约在5月9日,北京大学学生王长曜来武汉串联,在中华大学演讲,报告北京爱国运动的情形及北京卖国政府的屈辱无能。听报告的各校学生代表群情激奋,纷纷回校组织同学,发电文支援北京学生[注]郑南宣:《“五四”运动在武汉》,1979年,见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湖北: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在王长曜指导下(后又派两代表罗少卿、张伯谦,北京师范28人共同指导了武汉学生运动),武汉各校几经开会商讨。10日中午开武昌十五校代表会议,进行“手续之议定”[注]《武昌十五校代表召开会议》,《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8页。。12日晚又开会议成立武昌学生团[注]《武昌学生团代表会议》,《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5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页。,发表《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注]《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页。,致电美国总统和陆专使[注]《武昌学生团致电美总统、陆专使》,《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3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3页。。14日开联合大会,议定学联章程。最终于17日下午,在中华大学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并决定向督军和省长请愿。
17日会议结束后,各校26名代表先赴省府求谒,时任湖北省长的何韵珊因公务繁忙,派政务韩厅长(山东人)代为接见,韩厅长对学生的态度十分温和,“优礼有加,语极和蔼”[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在谈话正式开始前便代表在鄂的军、商、政各界的山东人,表示对学生的爱国举动表示感激[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以拉近与学生的关系。在韩厅长的温和态度的鼓励下,学生代表高鸿缙提出了学生联合会通过的四项要求:(一)本会联合组织经过,成立情形,恳请立案维持;(二)恳准发行印刷品,提倡国货,鼓励国民爱国思想;(三)恳请协电政府,力争青岛,并请将本会各电,饬电局一律拍电,嗣后不得再有扣留情事;(四)恳准组织游行大会,露天演说,伸张民气,唤起一般下等社会及无学识等人爱国之精神[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学生代表报告后,韩厅长当即表示,前两项或许可以同意,但第四项“诚恐滋生事端,万难准行”[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见此,学生代表纷纷起立,坚决要求批准此四项,并表示“誓必达到目的”[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学生态度十分坚决,韩厅长亦坚持学生代表的第四项要求不敢擅自答应。但为安抚学生,韩厅长表示会禀明省长,明日再为答复,谈话结束后更是亲自送学生出署。各校代表沿长街至督署,求谒见王督军。抵军署时已下午6时余,由军署副官长代为招待,询问来意,答督军因公外出,请各代表于明日(即18号)上午8时再来署谒见。于是,各代表始分途而归[注]《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概况》,《大汉报》1919年5月1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页。。军、省两长皆不接见学生代表,而派其下属代为接见,但其下属对学生的态度都十分客气,两位接见者此番态度实受督军王占元之指示,可见王占元此时对学生的态度是客气、温和的。这与他此前对待学生游行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王占元不管是对学生运动还是对工人运动都是毫不手软,当即镇压的。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鄂籍北大学生方毅就曾因“反对廿一条,响应留学日本回国学生组织救国会,被当时鄂督王占元侦捕”[注]安可仰:《“五四运动”是怎样掀起的?》,《春秋》1979年总第524期。。再者观察1918年以来王占元在镇压武汉当地的工人游行中的表现[注]观《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张影辉、孔祥征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有关五四运动前夕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的相关新闻报道,王占元对工人运动是不赞成且严厉镇压的。,可知作为督军的王占元对于此类有可能扰乱当地治安的学生运动是极不赞成的。而王占元此时对学生如此客气,概因王占元不仅是湖北督军,还是与皖系争锋相对的直系要员之一,而此时的学生运动的斗争对象又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王占元选择以客气、温和的态度对待学生。
(二)默许大游行
18日早8时,武汉学生联合会公举代表兰芝浓、高鸿缙等4人晋谒王督军,面陈该会以往一切情形,并请王占元将有关此次交涉政府来往的电文公开,此外恳求准许游行街市。对此“王氏似有难色,后经四代表陈明此次游街理由,并愿负完全责任,乃蒙允许”[注]《十八日三千余学生大游行》,《大汉报》1919年5月2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此处仍存争议,《申报》在报道此事是称王占元“仍不准举行”游行,学生不听劝告,“乃议取断然之行动,独自游行”[注]《武汉学生团之游行大会》,《申报》1919年5月24日,第8版。。王占元虽不赞成学生游行一事,但因五四运动处于一复杂的时间点,外有巴黎和会,内有南北和会,内外的两个和会是当时国内最重大之两政治事件,此前吴佩孚借停战极快地树立起自身的政治地位,成为当时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近在湖北的王占元,同样在促成南北和谈时起到重要作用且又占据武汉这一军事战略重地,对于在政治上更进一步未尝没有想法。且依据其以往对学生运动的经验,并不认为此次的学生运动会动摇其根本,在学生运动不能触其根本之时,作为山东出身的直系将领,又何不卖学生(国内舆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偏向)和北京政府(虽因派系问题处于北京政府的对立面,但名义上属于北京政府领导)一个面子,以获取更大的政治声誉呢。但王占元一向以左右逢源的手法,保持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注]蒋雁南:《祸鄂八年的北洋军阀王占元》,1983年冬汪正本整理,见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七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作者曾为王占元的部下,1917年11月至1921年8月,在湖北督署任上校参谋,对王占元有所了解。。是以王占元并不能像广东军政府一样,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注]《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见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5页。“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注]《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见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5页。因此,王虽对武汉学生运动不满,却不像北京方面一样逮捕学生并与之发生冲突,也不像广州方面一样全力支持五四运动,仅为默许学生游行,不与学生发生正面冲突,以观望局势,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在王占元的“默许”下,四位学生代表出署后,便通知各校,下午一时,在阅马场集合。至一点半,阅马场已集有三千余人。一点三刻由阅马场动身,首为高等师范,次则一校接续一校,中华大学列于队末。行经武昌路出府院街,经岔院坡至司门口,转长街至督军署,转保安门正街,穿大朝街复至阅马场。学生一面游行,一面由各校代表散布各种油印传单暨联合会简章与宣言书等印刷物。所有传单多系亡国惨语及游行主旨。各校学生每人用纸或布书“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字样。
因学生运动常伴有暴力行动,如北京学生运动时的纵火伤人,而“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执政者与非执政者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说,非执政的一方视为正义之举,大都表示支持,而执政的一方则强调法律、强调秩序”[注]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王占元作为主政一方的湖北督军,是不可能赞成此等扰乱当地治安的事宜的。同时王占元还是直系的主要将领之一,其所处的直系与北京政府所处的皖系之间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注]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2页。直系作为皖系的对立面,不满皖系的内外政策,力主南北议和[注]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2页。,力拒对德条约签字,因此15日,王占元致电政府:“请速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岛领土问题,暂勿签字。”[注]《王占元来电内容》,《晨报》1919年5月16日,第3版。16日,同为直系要员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国务院:“得失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注]《陈光远力争青岛电》,《申报》1919年5月27日,第8版。是以,《申报》道出了王占元的真实想法。
三、默许中严防
自北京学生风潮传播以来,王占元即对此采取措施。5月7日即与何省长协议“对武汉各学校则严重取缔并禁止一般之集会,更增派军队警察为各方面之严重警戒”[注]《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8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页。。后在其指示下教育科召开校长会议,称北京学生风潮为“横暴手段”、“越轨举动”,“即野蛮之军人犹须格于纪律,稍知敛迹,不谓各学子反坦然行之而不疑,殊觉为青年惜”,“鄂当局迭接中央电告,谋思患预防,昨特由公署教育科召集各校长开会,筹议于预防方法。讨论结果,闻解决三端,各于学校切实奉行。用纪如下:‘(一)凡认为煽动印刷品类一律严禁阅看;(二)严密稽查在寝室或自习室关于此事会议,如经查出立即阻止;(三)如东京、上海、北京各处寄来信件须认真检查,如涉及此事应予以销毁。’”[注]《教育科召开校长会议》,《大汉报》1919年5月11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至10日形势愈紧,“更进一步而为特别之戒严,或谓当局另据报告,恐有奸宄乘机煽惑,故防微杜渐,以保公安”[注]《湖北当局之防范(一)》,《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页。。18日学生代表出署后,王督军即电话何省长传集各校长,再次训谕。“此次风潮,迭经谕令,妥为禁止。今者各学生仍然有此举动,假使滋生事端,各校长责任所在,亦有所难辞矣。”[注]《校长之传谕》,《大汉报》1919年5月2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页。各校长立即表示:“如有轻举妄动滋生事端,校长等当担负完全责任。至若举动文明,和平进行,校长等实未便强迫制止。如果抑压,特其恐云云。”于是彼此相视无言,移时(约上午10时余)始各出署[注]《校长之传谕》,《大汉报》1919年5月2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页。。可见,王占元虽默许学生游行,但出自湖北督军身份的考虑仍对此有所防范。“王占元对于人民之激昂极端压制,尤恐军人被激,往日学生星期放假,今则禁止且不许出外游行,更派多数军警出外游行,不准集会结社三五成武,又派员鉴察邮电,凡关于激烈之印刷物与电报不许拍发云。”[注]《山东问题之鄂渚潮》,《时报》1919年5月17日,第4版。
在18日大游行时,因集合时四代表向各校申明“不准自离队伍”、“不准谈话”、“不准有一毫不守纪律行动”,游行过程中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但王督军并不相信学生的自制力,“电令警务处暨卫戍司令部,多派队士巡查街市,并令本署宪兵同为照料,以维治安”[注]《十八日三千余学生大游行》,《大汉报》1919年5月2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67页。。王督军希望将学生置于其监视之下,以便控制局势,防范乱起。
18日游行获得了武汉各界的赞许和支持,效果较为显著,是以学生于20日上午8时再次举行游行,关于此次游行的报道皆称“步伐整齐,秩序井然,观者鸦雀无声,感叹不置”[注]《文华等校学生演讲详情》,《大汉报》1919年5月2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王督军得知学生再次举行游行时,再次劝谕各校长“勿令学生再事游行,或至扰害安宁秩序”[注]《文华等校学生演讲详情》,《大汉报》1919年5月2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同时“加以各区警察,沿途保护学生游行,极行严密”[注]《文华等校学生演讲详情》,《大汉报》1919年5月2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然王督军此举确为“保护学生”?王督军此举是为以保护之名行监督防范之实。后王占元指示韩厅长于22日传见26校代表。学生得知此事,即于21日晚,“议定一种守则,除要求数端外,并担保数事”[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韩厅长接见代表时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表示:“折中所约尚妥协,惟第二项游行演讲未便准行”[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但学生恳求批准此项,并表示愿意接受“多派军警沿途弹压”[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韩厅长仍未答应,表示“转陈何省长商酌再行定夺”[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此前却是同意学生在军警弹压下游行的)。此外,学生代表提及提倡国货一事,韩厅长“对此项极表赞同”[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因韩厅长为王之部下,受其指示,可见当时王占元也是支持提倡国货)。
学生代表出署后,即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对于游行演讲,仍坚持进行”[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页。,并拟定一种游行演讲的办法,呈政务厅长核准,并通知各校。学生坚持游行演讲,又恐被禁,于是“组织十人团分途演说”[注]《学生组织十人团分途演说》,《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25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24日,26校代表于文华大学开会,“决定缓办游行演讲”[注]《罢课之动议》,《大汉报》1919年5月3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页。。学生暂缓游行演讲之事,王占元也不愿与学生发生正面冲突。因此,25日王占元在询问某会长维持学校之状况,谈及中央提前一月放暑假一事时,王表示:“鄂中尚未接到此项通告,此亦百无聊赖之下策,盖学生系明达事理之流,一时熟而过度激之反恐生变,惟有刿切道慰之一法,若虚其卒不见听,则放假后散处田里,设仍自由集合又将奈何,且假满再否开学乎?此种敷衍一时政策殊非根本办法云云。”[注]《鄂学界潮流正在镇压中》,《申报》1919年5月31日,第8版。可见此时王占元对学生之态度是较为和缓的,称赞学生为“明达事理一流”[注]《鄂学界潮流正在镇压中》,《申报》1919年5月31日,第8版。。在同一天他回复内务部发至全国各省督军的漾电,电文中声称,对于内务部的要求已经周知,并且认为“学界虽甚激烈,加以劝阻继以告诫,益有军警严防,尚无过甚之举动”[注]《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为已转饬布告所属一体周知致内务部电》,1919年5月2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26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548页。。可见此时在王占元看来,学生运动尚在可控制的范围里,他亦不想与学生发生正面冲突。
不过,即便如此他对学生的防范并未放松,“二十六日为星期休课之日,官厅方面因武汉学生联合会有于本星期实行露天讲演之说,且鉴于上星期有列队游街举动,故,是日防备奇严,军警各机关之调查稽查探访等,已全部派出密布各区刺探学生行迹。警厅游行队分编二十四排,每排八人,凡预定讲演之地点及各校附近之僻巷、隘口,均驻守一排以示监视之意,各校长皆传集学生在讲堂内苦口劝慰,其走读而未住校者则派管教分赴各寄宿舍,宣达意行,自辰至晚各管教奔走忙碌,因之斯日尚无若何举动”。但“总以劝阻游行演说为最要”[注]《严密周至之防范》,《大汉报》1919年5月3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28日,湖北全体学生致督军省长书中写道:“故将已公决之游行演讲团,暂从缓议。”[注]《湖北全体学生上督军省长书》,《大汉报》1919年5月31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页。此时,省长督军都认为“武汉各界对于青岛问题渐趋于平和地步”[注]《严密周至之防范》,《大汉报》1919年5月3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页。。
四、镇压:形势突变与王占元态度之转变
(一)形势突变与镇压学生运动
28日,26校代表会议“不知受何种刺激,忽焉提出五大条件,首即举行游行演讲决定于29日向军省两署请求,否则同盟罢课云”[注]《罢课之动议》,《大汉报》1919年5月3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页。。王占元得知此事,即“实施临时紧急戒严,顷刻间通衢隘口哨线满布武装,梭巡踪迹不绝,俨成草木皆兵之势。……警戒之严厉,殊非寻常可比”[注]《严密周至之防范》,《大汉报》1919年5月30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页。。形势再次紧张起来。
29日下午,王占元再次令教育科长开校长特别会议,专为学生同盟罢课一事,表示:“罢课如成事实,则军省两长为维持治安起见,不得不为最后严厉对付方法。”[注]《湖北学界风潮之酝酿》,《申报》1919年6月5日,第7版。是日,训令:“除分令随时查缉外,合行令仰该处转饬所属,遇有成群结队作此等不规则之行为,一经查觉无论何人立予拿究,毋得瞻循致干各戾切切,此令至警察方面由署长派各警厅密巡查并派侦探暗中监视学生之行动,至军队方面,如楚望台抱冰亭黄鹤楼等皆严为防范,茶楼酒肆学舍栈房亦派兵士调查,盖防范学生之紧几乎鹤唳风声之势矣。”[注]《鄂学生与官厅相持》,《申报》1919年6月6日,第8版。然而,督军的种种戒令,并不能阻止学生的行为。30日、31日学生开会为罢课演讲作准备,宣读《罢课宣言书》,拟决罢课规约,定于6月1日进行罢课演讲。31日,王督军得知学生将于6月1日实行游行演讲,即“电令各警署于一号清晨多派巡警,严守各校门首,阻其外出”[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页。。并传集军民各长官及各校长开联席会议,“移时王督出席,盛气言曰:‘游行演讲曾一再严令禁止,不图今日仍拟举行,实属有意违抗……吾每年以数十万之金钱教养彼等学生与我为难耶!’语毕怒容勃”。各校长起立表示今日既开会应磋商阻止学生罢课的办法,但王督军表示“断无磋商之余地”[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页。。此时,王占元对学生运动之态度已与前有极大变化,态度十分严厉。同时,他在这一天(31日)传回北京的电文中,已经有表示要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然京师来人游说甚多,现亦派警察督察,稍有违法即行遵令逮办。商界方面,亦严为晓谕”。虽然此时他依然认为“以现时防范而论,尚不至有轨外之举动”[注]《王占元等报告镇压鄂省学生运动及保护日侨密电》,1919年5月3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页。。
6月1日,各校门首早有军警防守,其中中华大学、高等师范和湖南中学三校所布军警最多。由于军警严守校门,于是“各校学生逾垣而出者有之,毁墙而出者有之”[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页。,军警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如学生之被枪伤刀伤殴伤者比比皆是”[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页。,且有数十名学生被捕。各校长即往省署谒见省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何省长表示此乃军队之事,非其力所及,各校长请何代恳督军,督军表示“此事无论如何明日再议”[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2日清晨,各校长见被捕学生仍未释放,复至省署,随省长见王督军,王督军“怒尚未释”[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后某校监力劝若不释放被捕学生,恐愈演愈烈。王督军乃首肯,释放被捕学生。是日10时,省长公署又传见各校校长及各校代表,王督军派副官出席,重申最严之告诫,表示“诸学员如果执迷不悟,恐将来悔之晚矣”[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然学生并未受其威胁,仍于下午1时余,在劝业场门首大开演讲[注]此处存在争议,《恽代英日记》在6月2日的日记中提道:“第一受打击事,即闻各校演讲因度节停止一天。”,军警前往干涉,但“被该校之某西人大加斥辱,挥之而去”[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同时2日当天,表示自己虽然调动军队镇压学生,但实属无奈,并详陈具体的镇压经过,最后指出“幸未滋生事端”[注]《王占元等报告调动军队镇压武汉学生运动密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362页。,可见他对维护地方安稳的重视。3日午后,数十名学生再次于劝业场演讲,被“保安警队以枪围群痛击,受伤过重因而倒地者四人,受轻伤者五人,被拘去者七人”。该日此种情形,多次发生,如湖南旅鄂中学学生演讲未遂被安保警察队追击殴打,圣三一中学演讲队在阅马场被驱逐[注]《学生游行演讲之热潮》,《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4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6月3日,何省长通令各学校6月3日至7月20日为提前放暑假日期,并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学生离校。同时因“六一惨案”、“六三惨案”的惨烈局面,6月3日开会时,“各学生亦多动归思”[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53页。。随着学生大多离校回乡,学生运动也告一段落。
(二)态度突变之原因
从以上惨案之经过看来,“六一惨案”、“六三惨案”之发生系由王督军之下令严惩学生,是给学生的一个教训。然5月上中旬王督军对武汉学生运动还较为保守,以严防为首,避免与学生发生冲突,28日仍表示“总以劝阻游行演说为最重要”,并不希望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若仅因劝阻未成,即令军警殴打学生,酿至惨案,则不属实,因其在对待18日、20日之学生游行时,态度也较为缓和,虽也是劝阻学生游行未成,但仍不至于出兵控制学生。那么,到了5月28日后,导致他态度突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此次突变,以往学界多认为是京津沪学生来湖北劝导所致。如田子渝先生在其《武汉五四运动史》中有关此事的表述是:“武汉学联会为了声援和响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决定6月1日起采取统一行动。”[注]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武汉:长江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但经考察,此次学生态度突变,虽与京津沪学生动员总罢课有一定关系,但非并唯一因素。在26日欢迎北京代表鲁先琦、罗某及天津代表张某等的会议上,京代表罗君“要求各代表转致各贵同人,可否与京津为一致之行动”[注]《武汉学联二十六日会议》,《大汉报》1919年5月2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但“鄂会各代表聆听后当即答复云:罢课一事同人等断难承认,惟遵照贵代表等意旨,协电政府早日答复之一法”[注]《武汉学联二十六日会议》,《大汉报》1919年5月2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此时,武汉学联会并未同意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一同罢课。27日会议上(此时京、津、沪代表已前往上海)表示:“本会自成立以来一事无成,致被外来代表等所讥讽,可耻孰甚,乃共同决定再向军民两政长为最后之呈请。其文稿大致系谓:学生本爱国之热忱,举动文明,而两署竟为严重之干涉,以致民气不申。况近来各省学界均在积极进行之中,亦未闻有若何之取缔严禁,鄂省何故独有不同?至以秩序安宁为言,前者已举行游街一次,其是否与治安有碍已见一斑。须知压制愈重,反动愈重,反动愈激,则收拾更难。学生等特不甘为共和国之无自由权之学生,并不为共和国无自由权之公民云。”[注]《武汉学联二十六日会议》,《大汉报》1919年5月2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页。武汉学生确受北京、上海等代表的刺激,有举行游行的意向,但并未真正下定决心与北京、上海一致罢课。但在武汉学联会30日会议上,商讨游行演讲一事时,因“近得某方面之赞助,以故主张必行者占大多数,乃公同决定,无论如何牺牲,誓必始终办到,一俟各校演讲地点支配妥帖后,即定期实行”[注]《武汉学联二十六日会议》,《大汉报》1919年5月2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页。。是以,武汉学联会态度突变虽与京、津、沪来汉代表有一定关系,但只是受其刺激有举行罢课之意向。真正使学联会下定决心,实行6月1日罢课的是“某方面之赞助”。此中的“某方面”指的是在武昌兵变中未被王占元清扫的军队。约在5月27日,武昌发生兵变,1919年5月30日,此次兵变“以血染花园站结束”[注]何言文:《王占元治鄂时武昌兵变内幕》,《武汉文史资料·史海钩沉》2006年第4期。。此次兵变由孙传芳发起,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武汉市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王占元只想速战速决,并没有彻底地进行清扫。更遑论兵变的士兵还曾在学校当中躲避过[注]何言文:《王占元治鄂时武昌兵变内幕》,《武汉文史资料·史海钩沉》2006年第4期。,与学生定是发生过接触的。且恽代英在其6月4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十时许有来告,一三五七团及学兵营兵士有起为学生后盾之语。”[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53页。吊诡的是兵变如此大事,王占元在事情发生后与中央的两次电文中(分别是5月31日、6月2日)只字未提,他甚至在31日给中央的电文中,还表示因为“各处军队亦经占元密以暗中辅助,总不使其稍起风潮”。不把兵变的消息报告中央,只是谈京沪等地学生来鄂造成混乱,使得他不得不防范学生运动,自然有王占元作为督军不想招致中央对其质疑的顾忌,而亦可以传达出对于王占元来说军队的重要性,他在给中央的电文中传达的是,正是因为得到了军队的暗中辅助,所以可以控制学生运动。因此,军队内部的不稳定是王占元态度急变的重要原因。
其实,作为湖北督军的王占元对1919年夏武汉学生运动的态度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其表现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学生运动初期王占元隐藏了对学生运动的不满,对学生安抚与严防并重;学生运动后期将其不满显现出来,对学生严厉镇压,酿致“六一惨案”、“六三惨案”。也正是因其后期态度的显现,对学生严厉镇压,招致他人诟病,使其在南北和谈中兴起的好名声化为乌有,大受批评。在时人看来,作为山东人又是皖系对手的王占元,此时应该站在学生一边才对。1919年6月8日《申报》在评论王占元镇压鄂学生时,即道:“王占元独令军警蹂躏,此则国人所不解也。”[注]《王占元与鄂学生》,《申报》1919年6月8日,第6版。彭明在编写《中华民国史》谈及此事时亦疑惑王占元为何不“因与皖系的对立而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注]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2页。。不过无论如何,这次学生运动最终酿成的后果是王占元不仅失去了如吴佩孚一样借学生运动成为政治明星的机会,也彻底丧失了政治清誉,无论是在报端还是在民众的心中。
王占元作为一个政治家又何曾不想与在五四运动期间声名鹊起的吴佩孚一样博一个好名声,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添加筹码呢?吴佩孚此人有胆有谋,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在五四运动期间力拒签字,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因此名声鹊起,“从一个军事明星,变为政治明星,由一个高级将领,变为直系领袖”。反观王占元,左右逢源,没有足够的魄力,最终酿至惨案,名声狼藉,在政治上日趋没落。但真正导致王占元不满态度显露的还是其身份。“在其位谋其政”,1919年吴佩孚只是湖南的一个师长,其职责为管理军队,带兵作战,“不处在中央执政地位,其对外言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注]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他自可大力赞扬学生运动。但王占元不同,他有着多重身份,尤其是其湖北当政者的身份,使其在面对学生运动时强调秩序、法律,对学生运动极不赞成,前期因局势未明又身处直系,将对学生运动的不满压下,但后期学生运动愈加激烈,且军队异动,王占元之忍耐已达极限。22日二十六校代表开会时,即表示要吸收军警界之力量,尤其是军界,“正在学界开会游行,力争青岛,多有无形加入”[注]《学生联合会之近状》,《大汉报》1919年5月29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军队乃王占元立足之根本,是以早在北京风潮传来时,王占元就颁布“军营之禁令”[注]《湖北当局之防范(一)》,《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2日,见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页。,禁止军人日间出游,对信件也严加查阅。在学生决议罢课消息传来时,湖北军队获接爱国传单,此传单在官兵中快速传阅,王子春得知后颇为吃惊。“王乃山东人,而其部下鲁籍亦多,诚恐因此动摇至于不可收拾”,王占元立即召集各营长训话,“不可受外界动摇”,“禁止出游”,“更禁止军人与学生间集会行动”[注]《禁止军人与学生集会》,《时报》1919年5月29日,第4版。,且武昌兵变的发生也使王占元的神经紧张,作为湖北主政者、军队首领,王占元再无隐忍的可能,若再不将可能引发军队再次异动的学生运动压下,其立足根基就会被摧毁,其政治生涯乃至生命都将受到威胁,此乃王占元态度显现之根本原因。
五、余论:政治家的权谋——谁来承担镇压之责?
武汉并非是学生运动的中心,按照王占元本人的个性,最终酿至军警镇压学生的惨案是始料未及的。作为湖北督军的他虽然首先要考虑所管辖区的稳定,但不能完全忽视舆论和民心。当动乱与爱国这一不容置疑的出发点相冲突时,王占元政治家的身份开始呈现。因此在6月2日,即镇压学生运动发生的第二天,王占元便给中央发去电文,解释镇压事件,一再强调误伤,已经严惩各校校长,且派人专门看望学生,并特别声明没有滋生事端[注]《王占元等报告调动军队镇压武汉学生运动密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362页。。王占元这一电奏出发点有二,其一向北京方面证明他对湖北仍能进行有效控制,其二撇清镇压学生运动的责任。6月9日,武昌高师的学生致电大总统,直指王占元、何珮瑢“欺压学生”、“解散学校”,要求“罢斥,以谢国人”[注]《上海武昌高师全体学生来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27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在电文中,清晰可见学生将镇压之事的元凶指向王占元本人。6月12日王占元再次发表电文,坚称是因为学生滋闹产生的误伤,且与北京情形对比,表明“京鄂大致相同”,“钧座必不相信”[注]《电陈武昌学生与保安队抵抗误伤情形及鄂中各校提前放假缘由乞鉴谅由》,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27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213-214页。。这封电文充分展现了王占元作为政治家的权谋,此时他已经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为防止北京政府借此作文章以影响到其政治生涯,先拿皖系处理北京事件做例,这样不但认可了政府处理学生运动的方式,又借机证明自己的办法并无不妥。但这一事件并未就此了结,武汉镇压学生事件要有承担责任之人,6月17日国会议员陈为铫发表质问书,内容首先是“质问政府是否有电鄂查办杀伤学生之警察”,不过通篇电文主要讨论警察如何放置枪柄、刺刀以至于伤及学生,并称“就事实而言警察不能不负责者”,在电文的最后,要求政府致电鄂督,及时处理涉案警察,以平息众怒[注]《议员陈为铫等质问书一件》,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27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219-225页。。乍看电文未觉不妥,但仔细比较便可发现,学生在电文中的要求是严惩王占元,而国会这封电文却变为了让王占元严惩湖北警察。表面来看国会替学生发声,表彰学生爱国之心,但事实上实在有模糊焦点、替王占元开脱之嫌疑。笔者没能查到议员陈为铫的具体来历,但就安福系当时控制国会的情形来看,陈为铫不至为王占元开脱,他最终却能如此做的缘由概与王占元在电文中提到的京鄂相同不无关系。所以,尽管表面上王占元直系的身份是他可以借巴黎和会失败打击政敌的有利因素,但同时处于主政身份的他们亦未必是绝对的敌人。6月30日省长何珮瑢复电,称已经惩办涉案军警[注]《电悉该案被告皆系军警已送陆军审判出核办并陈明分别办理各情形由》,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27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这场远离事件中心的运动,最终不了了之。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王占元既没有如梁启超等研究系人物一般把握舆论导向,挑起五四运动的契机,也没有如吴佩孚一般破釜沉舟、独当一面的魄力,他本人的个性和湖北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晰,时人便指出:“鄂督王子春之与时局,外人鲜闻其主张,就其行径观之似专注重于地方治安维持现状。”[注]鄂王督之时局谭(汉口通信),《申报》1918年8月10日,第3版。这可能是直至这场运动结束王占元本人也再没能重新走上政治巅峰的原因。
五四运动因爱国而起,其意义之高尚,不可撼动,就算是受此破坏最大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指摘五四运动之本身,只拿五四运动之形式、其间的暴力行为说事,若敢公开指责五四运动,就会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其政治生涯也便走到了尽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王占元虽没有雄才大略,却还是懂得何为原则,其对学生运动自始至终的不满,并不影响他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无论是在武汉学生运动前还是运动爆发后,王占元始终坚持收回青岛主权,拒绝签字[注]《鄂督王占元覆电》,《申报》1919年5月13日,第10版;《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而作为直系要员的王占元也并非不知道在南北和谈的大背景下,借五四运动打击政敌皖系是个好办法,起初就多次要求重开和会。呼吁和平的他,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虽不能与吴佩孚同一阵营,但却在此时联合提出了“割爱新国会”[注]《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5月21日,第7版。的要求,显然是利用运动之乱,对安福系领导的国会的一大打击。
正如开篇所言,作为政治革命的“五四”,比这场运动本身要复杂得多。不可能支持学生运动的王占元,却不敢在根本的问题上指责学生。一方面作为湖北督军,他必须维持一方安稳;另一方面,这场学生运动,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打击政敌的机会。其实当学生运动的热潮没有燃烧到湖北的土地上时,当王占元还不需要发挥其维护地方安定的责任时,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隔岸观火,甚至借机利用;但当他必须承担作为湖北督军的职责时,那么一切考虑都得以维护其统治为根本考量。正如邓野在书中所言:“五四学生运动带有强烈的暴力行为(纵火伤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执政者与非执政者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说,非执政的一方视为正义之举,大都表示支持,而执政的一方则强调法律、强调秩序。”[注]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王占元本人性格左右逢源,缺乏成熟的政治家必备的魄力,又因其复杂的身份而严厉镇压学生运动,丧失了舆论的制高点,最终声名狼藉,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无论政治派别还是政治人物,其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或许不同,但是,无不以自身的、具体的政治利益为依归”[注]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王占元在武汉学生运动期间的所作所为,说到底,就是围绕自身利益的盘算与选择。不过,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王占元本人的能力和复杂的局势都限制了他去协调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直系领导人和作为湖北督军三种身份的矛盾。可以想见,若是任由学生暴动,当事态的发展超过其控制的范围时,王占元损失的便不仅仅是湖北督军一职;但如今他采取了镇压学生的办法以维护地方安稳,丢掉了政治清誉不说,湖北人民仍请求罢免其职务[注]《旅沪鄂人请罢王占元电》,《申报》1919年6月12日,第12版。。在这场政治革命中,王占元这种矛盾的身份,恰恰是他最大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