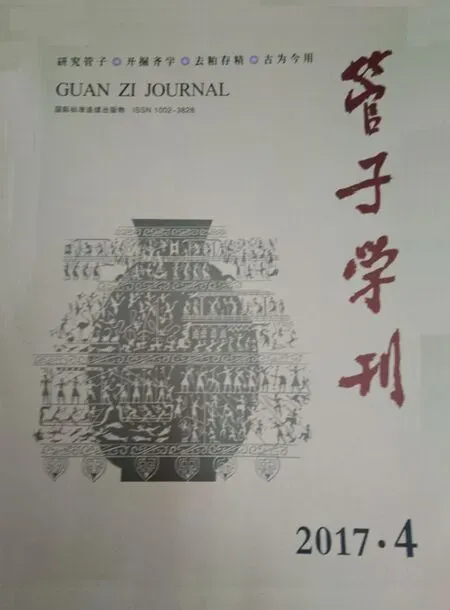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管子·幼官》中的时间、空间与统治:阴阳家之研究
[美]马思劢著,郭鼎玮译
(1.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2.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儒学院,北京 100088)
《管子·幼官》中的时间、空间与统治:阴阳家之研究
[美]马思劢1著,郭鼎玮2译
(1.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2.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儒学院,北京 100088)
在先秦的哲学、政治与经济语境中,战国时期的历法文本有着重要地位,这些文本与长期受到误读的阴阳家学派紧密相关。通过关注早期主要代表作之一,即《管子》形成初期出现的历法文本《幼官》,本文重新审视了阴阳家学派的起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同时,本文试图阐明阴阳思想在齐国特有成熟重农社会中的应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中,《管子》之原貌得以形成,并产生了包括《幼官》在内的数部重要历法作品。本文亦试图展现阴阳家学派的后期演变,其对汉代黄老之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幼官》;阴阳家;早期历法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汉书·艺文志》)
一、对阴阳家学派的关注
战国时期通常被称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黄金时代,亦通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术语中,“百家”之说本为夸张,实际的学派并未有“百家”之多;且可进一步认为,此种说法企图着重强调典型思想的个殊化趋势,或者,强调与个体思想家(“诸子”)相联系的特征──这些思想家中的大多数人可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政治或意识形态趋势相关联。
实际上,《吕氏春秋》《韩非子》《荀子》与《庄子》四书,皆已对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图景进行了各自的概观。这些典籍中,没有一个将诸子或他们的个人思想以学派(“家”)为单位进行分类;确切而言,它们在辨明诸子时,并未将个体思想家定义为任何特定的“家”,其中一些人是因其思想具有相似之处而被归纳在一起的。根据苏德恺的说法(Kidder Smith)[1]129-156,司马谈“重新归纳了这些思想,并将归纳后的形态称为‘家’。在司马谈的时代,‘家’意指‘(专精于某一方面的)人’”,他以如下顺序列举了六“家”:阴阳①在本研究中直接引用了大量西方资料,其对“阴阳”的翻译各有不同,出于方便,本文原文统一将其改为拼音“阴阳”。、儒、墨、法、名、道②然而对于这种命名的应用,我们可能会对“家”的确切含义产生争议;一般认为,其在语言上的影响主要是,诸子百家会以“某种主义(-ism)”的概念表达出来。苏德恺写道:“此处尚有其更为宏大的背景——这是一个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活跃的争鸣运动,通过司马谈分类合并的表述方式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家’),到西汉后期,这个概念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某种主义’。”详见Kidder Smith(苏德恺).“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Taoism,‘Legalism’,et cetera(司马谈与道家、“法家”等[概念的]发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February 2003).130.。班固于其《汉书·艺文志》中,又添四“家”于此名列:纵横、农、杂、小说。即便我们再囊括另外两个历史上很重要却未被阐及的“家”,即“杨朱学派”和“兵家”,其程度仍与“百家”之称相差甚远。
在此战国时期十二“家”中,只有儒、墨二家,以于史可征的形式展现了其坚实的社会学依据,此依据可被认为是相对来说没有问题的——其建立在拥有共同知识与价值体系的师徒传承系统之上。十二“家”中的另外一些,似乎是由少数几个个人代表组成,即法家、名家、农家、小说家和杨朱学派。纵横家与兵家二家,则似是由专业的政府人员构成。然而,杂家却截然不同,因为它是一个笼统的分类,用以囊括数量庞大的一群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无法定义为其他诸家、亦难与其他诸家建立联系,但他们融合而博采了与(业已存在的)各家有关的多种观念与思路。道家亦在诸家中有些独特,它看似如儒墨二家那样包含了师徒体系,但这一学派在整个战国时期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表现形式①马思劢提出了一种解读方式,其将道家看做实践意义上的活动,详见Thomas Michael.In the Shadows of the Dao:Laozi,the Sage,and the Daodejing(道之荫蔽:老子、圣人与《道德经》).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金弘扬亦提出一种解读方式,将其看做一种哲学层面上的调和活动,详见Hongkyung Kim(金弘扬).The Old Master:A Syncretic Reading of the Laozi from the Mawangdui Text Onward(老子:以马王堆帛书文本为起点对《老子》的调合性解读).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马思劢又比较了此二种解读方式根本的得失差异,但即便如此,道家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详见Thomas Michael.“Approaching the Laozi:Comparing a Syncretic Reading to a Synthetic One”(走近《老子》:调和性解读与综合性解读之比较).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12/1(2017).10-25。。
十二“家”名列中,仅余阴阳家以多种原因引人瞩目。其中之一是,根据司马谈与班固的描述,阴阳家并非源于某位哲学家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古代的天文学家,他们观察天的自然运行,并以不同于卜筮预言之流的方式做出预测。此外,司马谈与班固都将早期历法或农历的制订归功于阴阳家,这为君王的统领指导与百姓的田间劳作做出了贡献。换言之,文化政治实用主义与民间智慧是阴阳家所固有的特征,这在其他各家中体现得并没有那么明显。
阴阳家学派令人关注的另一原因,是因其被认为产生了数量最为庞大的著作,这些著作与其他诸家皆有关联,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散佚。尽管如此,许多著作的名目标题还是得以留存,《艺文志》目录中的记载即为一例。
阴阳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没有被冠以“阴阳家”的头衔,而是另有一不同称呼:“方士。”②冯友兰写道:“阴阳家起源于神秘术士。这些术士自古被称为‘方士’,意指诸种秘术的从业者。”(此句出自Dirk Bodde〔D·卜德〕所译之英文版——译注)详见Fung Yu-lan(冯友兰).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irk Bodde(D·卜德).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6.129.所谓方士,据称是邹衍(公元前305-240)的追随者,邹衍本人则常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创始者。方士们之显著特征,即为其专业知识领域的作品——“方术”。他们为诸种神秘玄妙的实践提供了较为简短的指导方法,这些实践包括卜筮杂占、医经方剂、天文历谱与风水形法等等;他们同时以宣扬灾异禁忌与其他形式的日常约束而著称。
司马谈着重展现了方士们制订历法的专业程度,这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起源层面亦与隐秘方术相关。他写道:“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阴阳家学派值得关注的原因还在于其学说重心的抽象性,即其名中的“阴阳”。然而针对这一点,或难有足够充分的历史缘由来明确证实这一“家”确实能够被命名为“阴阳家”。此处易有一可相较参照的批评:针对以“道家”标签指代关注“道”的特定群体这一做法,顾立雅(Herrlee Creel)表达了他的疑虑──据他所言:“如果某一著作使用‘道’这一术语即被归为道家,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有问题;实际上,早期中国哲学都使用了‘道’这一术语,而他们并非都是道家。”[2]2与此类似,就提出了“什么是阴阳家群体”的疑问。苏德恺有类似之论:
首要的难点在于这一群体过于庞大,即使我们能够确定某些以阐释诸种异象而闻名的专家们,(但这仍然不够,)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有汉初阴阳思想在各个方面渗透──例如,甚至兵家亦受其影响。这样一来,阴阳观念的存在,就不能为一个人或一段文本的身份或其隶属关系提供依据。换言之,阴阳观念应是一套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之联系的假设[1]138。
在此,本文认为苏德恺对“阴阳”与“阴阳家”关系的理解,同顾立雅对“道”与“道家”关系的理解一样,都陷入了同种类型的误解之中。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未考虑对“某家”做出定义之术语(即“阴阳”与“道”)的最初语境与应用程度──术语恰为学派提供其基本的身份特征。“阴阳”与“道”,此二术语一旦在各自的特定领域范畴内(自然领域之于阴阳家③尽管这是术士们的共同属性,但此外冯友兰还写道:“阴阳家亦代表着科学的趋势,即他们试图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作出积极的解释。”Fung Yu-lan(冯友兰).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irk Bodde(D·卜德).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6.130.,宇宙演化领域之于道家)成为专有词汇,就说明它们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早期中国哲学的几乎每一角落并得以使用──虽然被归于各“家”的诸子们会赋予这些术语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阴阳家的起源与“阴阳”最初的表述密切相关,其应是作为一种在有限的应用领域(本文认为最可能是农业社会)内有着明确含义的独立概念出现的。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探索过“阴阳”之起源,他们从两个独立且不互斥的方向提供了敏锐而有说服力的论据,做得非常出色。从经验论的角度来看,做得最好的是王蓉蓉(Robin Wang),即认为“阴阳”意指日月明暗[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做得最好的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4],其认为“阴阳”分指男女雄雌①针对阴阳概念,其他重要西方学界研究还包括高罗佩(Gulik)、桂时雨(Guisso)、瑞丽(Raphals)等人的著述,中文研究的经典之论则源于庞朴的论述。详见:Gulik,Robert H.van(高罗佩).(2003).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till 1644 A.D.(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公元前1500-公元1644年])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Guisso,Richard W(桂时雨).(1981).‘Thunder Over the Lake: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Perception of Women in Early China(湖上的雷:五经和古代中国对女性的认识).’In ed.’s R.W.L.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Women in China: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47-63.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Raphals,Lisa(瑞丽)(1998).Sharing the Light: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分享烛光——早期中国的女性与德行).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但本文认为,许多现代研究往往忽略了其明显的政治本质──这种政治本质正源于以“阴阳”为核心的早期中国社会:“阴阳”还可作为统治者的指挥与标杆,用以监督规范农业社会的各个任务与职责。阴阳思想被最初应用于政治层面的驱动作用,此即是早期阴阳家得以被定义的一个特征。
然而,在战国晚期思潮中,一旦“阴阳”的观念与表述超出其原有的特定应用领域(即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并且获得了文化层面上广泛的认同与影响力,这种政治性特征就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邹衍及方士们似是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故他们可被认为是“第二代阴阳家”;他们把阴阳思想引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出于政治需要的领域之中,通过与五行理论融合,用以阐释王朝更替兴衰之顺序,此即是邹衍阴阳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②关于阴阳家,陆玉林与唐有伯有一部非常杰出的专著,但他们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本文所称的第二代阴阳家群体(而对第一代阴阳家关注不够充分)。详见陆玉林、唐有伯著《中国阴阳家》,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所谓第一代阴阳家和第二代阴阳家,二者的区分之处在于,前者的基本思想和实践大体仅限于以阴阳思想为关注重心、只涉及一些五行思想的雏形;而经过邹衍和方士们的历史活动之后,阴阳与五行二者才真正与所有第二代阴阳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处关于两种阴阳家之差异的灵感,部分源于刘宁的工作,她写道:
篇目的分合错乱加上文字的古奥,使《管子》成为先秦诸子文献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古籍之一。尤其《幼官》《五行》等篇,涉及齐国独特的历法制度,但后世却较多地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研究,导致对这两篇内容的理解始终存在误区[5]。
她对阴阳五行的看法亦引出了一些并非无关的问题,问题核心即:五行思想究竟是完全脱离阴阳思想而发展的,还是直接顺应阴阳思想的逻辑而展开、是其必然产生的延伸?这些问题在早先已为梁启超所探讨③梁启超的著述是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详见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但由于缺乏历史证据,究竟为何无法得以确证。然而,白奚的发现[6]正好响应了这个讨论,特别是他把《管子》(亦本文的核心文本)引入了对话之中。他写道:
阴阳与五行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在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各自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才走到了一起。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由《管子》实现的④此处曹立明写道:“四时、阴阳和五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三者各有不同的思想渊源。”他指出,除了阴阳五行之外,我们经常把四时视为此观念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他继续写道:“四时观念的产生最初是与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和物候星象的观察密不可分……商代就开始以不同类型的风来确定四时。四时观念的确立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可知四时教令是阴阳五行说的主要内容,舍此不足谓之阴阳家,这在《管子》一书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详见:曹立明:《〈管子〉“四时”的观念的生态意蕴》,《三峡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同时,两代阴阳家都要与其他诸家区分开来(道家是例外,但这是另一个不同的议题)。其他学派中,极少有人提及“阴阳”,很可能是因为其他诸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术语,也有可能是他们未能在其哲学中为这一术语找到容身之所。直到战国即将结束之际,阴阳思想才开始渗透到其他学派中,主要是儒家和法家学派;而综合了的“阴阳五行”思想,直到汉代受到黄老传统的推进,才普遍流传开来。
战国终结之时,阴阳思想已转变为主流话语中关于宇宙与宇宙生成论的主导范式,然而,难以确定在这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的是阴阳家还是道家。道家同样构建了围绕阴阳展开的主导话语体系,但其源自以质朴初始之道(“元道”)与世界本原为基础建立起的另一种范式。一般认为,直到战国末期,涉及阴阳的宇宙生成论才成为道家的中心论题之一[7]22-23[8]7-13,而在现存著作中,阴阳家并未展现其对世界本原的关注;方士的职业重心则更加偏向实践层面①一些学者,如顾立雅(Creel)和任继愈将方士与后来的“道教”相结合,并认为他们借鉴了当时备受尊敬的道家宇宙论,以提升其事业之地位;然而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用以了解阴阳家尚存疑问,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实际上阴阳家群体从未有意将阴阳思想应用于阐释世界起源。详见Herlee Creel G(顾立雅).What is Taoism?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什么是道家?以及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其他研究).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20;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此外,早期道家似是发轫于南方的楚国,而阴阳家则是起源于东方的齐国,故这其中亦有重要的地理因素需要考虑,不能混淆。
陈荣捷(Wing-tsit Chan)没有考虑阴阳家和道家的区别,故不仅混淆了二者的历史影响,还导致他主张:“阴阳与五行说,可视为早期中国人建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的尝试。”②原文引自Wing Tsit-chan(陈荣捷).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文献选编).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译文参照陈荣捷编,杨儒宾等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译者注此说虽然未能反映阴阳家的真实情形,但这种看法却广泛地存在于当代文献资料之中③例如,牛津线上参考资料库称:“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学派,可能是由邹衍(公元前约305-240年)所创立,是一种在宇宙论层面上的早期尝试;其基础是阴阳对立学说,以及在自然与历史进程中有序循环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理论。”(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25343848.),宣扬这种说法的学者往往忽视了阴阳思想最早得以应用的影响与范围。这样一来,阴阳家的形象更加难以探索──因为阴阳家学派的书写者们对形而上学与宇宙论并没有兴趣。
此即为阴阳家学派值得关注的最后一个原因:不同于其他诸家,阴阳家的起源几乎没有涉及形上学、宇宙论、策略、逻辑、法律或道德等诸如此类的哲学范畴。其发端完全是文化层面的,并且极其务实,可以明确地追溯并集中在战国早期时的齐国文化。早期的,或者说第一代阴阳家思想,在《管子》中首次被得以编纂,并且继续展开为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形成于本文所谓“第二代阴阳家”──邹衍与方士们的历史活动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一方向的继承者们都不会像多数诸家的后学那样被认为是哲学家,而只能被视为一类职业化的专业人士群体。第二个方向则随着黄老之学的出现得以开花结果,最终诞生为一种结合了阴阳五行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复杂产物,其在汉初得以成熟,同时也掺杂了道家的宇宙论、儒家的道德学说、兵家的军事主义等其他思想。
二、阴阳家与《管子》
这部早期作品集托名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政治家管仲,故称《管子》,但与管仲活跃实际时代不符。当代学者通常将该著追溯至齐国的稷下学宫,在当时,大量思想家得到官方赞助支持得以汇集于此,以论辩争鸣思想学术,这为书中庞大繁杂的各类思想提供了诞生环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就被撰写记录并得以收集整理,但在公元前250年或稍晚时候,这些思想就可能已经被吕不韦的门客们所收集,形成可被认为是《管子》原貌的作品,这一点在《韩非子》和贾谊《新书》中都有所提及。最终通行版则在公元前26年左右由刘向编订而成,从《管子》原貌诞生到定本形成期间所形成的许多篇章,亦包含于其中。李克(Allyn Rickett)如是写道: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管子》版本编订为八十六篇,继而分为二十四卷。八十六篇中有十篇已经散佚,其中两篇(第八、第九篇)除分段顺序外,几乎全同;另有两到三篇似是后出,以替代原来散佚的篇章。一些篇章则由一些短小的片段组成,这些段落出处不同、抑或是源于同一材料的不同版本,现存七十六篇中就有四篇是由其他篇章中的若干节或相对应的逐行解释构成的。《管子》的文本内容也被各自命名,分为八类[9]277-280。
接下来,本文将约公元前250年诞生的《管子》原貌文本从刘向版《管子》定本中区分开来。在这八类内容中,包含了《幼官》与《幼官图》的“经言”类(第一至九篇)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然而,个别内容并没有系统地遵循这样的次第——许多后出的文本亦包含在早先的部分中,同样,许多早出篇章也出现了较晚的内容,《幼官》即为这种情形。本文认为,《管子》中早出的若干类内容,以及一些删减去晚出增补后的早期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管子》原貌的一部分——这些内容即是第一代阴阳家的作品。
具体而言,可以发现《管子》原貌的核心部分体现于若干与历法相关的篇章中,它们分散在八类内容各处。这些篇章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将农业历法知识与统治者用以监督四季劳作的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它们包括:第八篇《幼官》、第九篇《幼官图》、第四十篇《四时》、第四十一篇《五行》、以及第八十五篇《轻重己》。
《淮南子》似是第一部与《管子》原貌(最有可能)密切相关的著作。许多淮南王的门客们也曾参与过《庄子》与《楚辞》的编写,故他们参与《管子》的编纂亦合乎情理。由于汉武帝于公元前122年处死了淮南王刘安,这些门客们是否对当时流通的版本进行了大范围编审、其编撰内容与刘向的通行定本相差多少,目前都无从得知。由于受到淮南王门客们的关注,《管子》被《汉书》列入子部道家类作品也就不奇怪了。
《汉书》对其分类很可能是由于《管子》中包含了以《内业》为首的《心术》等四篇,《内业》的内容即被学者们认为是展现了先秦道家思想的本源抑或产物①对这些问题的仔细研究可见罗浩(Roth)的著述。详见Harold Roth(罗浩).Original Tao:Inward Training(Nei-yeh)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原道:《內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1-13.。这些篇章可能吸引了淮南王门客们的集中关注——他们本身就与道家密切相关。然而,虽然《心术》等四篇使人很容易联系到早期道家的思想与实践,但他们所展现的只是该著全部知识与哲学内容中的一小部分。更何况《内业》一篇,不仅产生的年代可追溯至稷下学宫诞生之前,且其背景似是源于道家隐士们所注重的修身功夫,这与《管子》的其他篇章都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同——尤其该篇从未提及“阴阳”的观念。最后,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稷下学者们曾以某种形式来践行《内业》中所主张的修行方法;故将此四篇纳入《管子》原文的做法,首先就需要考虑该篇“如何”“为何”被纳入其中的问题。综上所述,虽然道家思想(和实践)确实在早期《管子》中有所展现,但将其视为道家作品的做法仍然有待商榷。
同样是汉代,刘歆似是最先将《管子》归为法家作品,保存在其目录著作《七略》中;这一分类为《隋书》作为标准并采纳,影响至今——这可能是因为文字史料表明该著最早得以编纂结集是在秦国,而秦国正以推行法家著称。的确,《管子》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强调了法家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例如法、度、则、理等。然而,《管子》思想的早期部分,就与法家主要代言人商鞅和韩非的思想有着重大分歧——前者遵循秩序和谐下的客观自然法则,后者却提倡专制统治下的积极法治。因此,虽然《管子》思想与秦始皇所支持的法家(其以此成就首位皇帝)之间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将该著作为法家作品的做法亦需慎重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者对《管子》进行分类的另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将其作为黄老之学的代表,认为此学说成型于一些古代思想家对道家与法家中心理念的融合,尤其是道家关注“元道”(质朴初始之道)的思想与法家主张积极法治的思想;同时更兼入了强大的儒家价值观——主要是其关于道德的思想。然而,黄老传统时至汉初才呈现为一个实际的学说,虽然将《管子》的早期内容看做是黄老思想的来源是并非是不合理的,其晚出内容也可以作为黄老思想之早期代表,但《管子》早期文本形成时距离黄老思想呈现尚有一百余年,将其归为黄老一类显然太早。
另一种为部分学者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将其视为杂家融合性著作的代表之作②谭正璧写道:“所传管子内容甚错杂,统观全书,以道、法二家之言为最多,故七略以之列入法家。然其间亦多兵家、纵横家、儒家、阴阳家及农家之言,故不如入之杂家为安。至其作者,当非出于管子一人手笔,亦非成于一时。”(谭正璧著《国学概论讲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01页。)。作为班固所命名的诸家之一,其亦可能源于稷下之学,金弘扬(Hongkyung Kim)对此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10]。但杂家与道、儒、墨等诸家不同,其没有师徒传承结构,也没有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作为一个类别,该学派用以展现一类繁杂的思想家群体——他们在根本上与其他诸家没有任何知识或实际层面的隶属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亦如此。他们得以著称的影响在于,其联系各家主要学说,进行融合与重组,从而打破了在思想文化交流中诸家的知识垄断。但本文认为,《管子》的早期部分并非是着重展现杂家思想,若简单地将其归于杂家,意味着无法触及这一部分的实质核心内容。实际上,《管子》的早期部分,展现了先秦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自觉,及其具体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此即源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阴阳家学派;故杂家的分类将会误读和曲解这一事实。
最后,本文认为,早期的《管子》是一部阴阳家作品的基本收藏合集。就传统与现代的学术层面而言,虽然这一分类也逐渐为一些当代中国学者所接受①吕思勉称:“《幼官》第八、《幼官图》第九(以上《经言》)此两篇为阴阳家言。盖本只有图,后又写为书,故二篇相复。”(吕思勉著《国学知识大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其中一个复杂的原因在于,阴阳家的主要代表通常被认为是方士,但他们仅是第二代阴阳家,几乎不可能出现在稷下学宫中;稷下学宫正式关闭时,邹衍只有二十岁左右。虽然阴阳家的基本思想集中在“阴阳”观念上(就其名称定义而言),但我们对这一观念最初的历史仍然知之甚少;再者,我们可从《管子》的早期内容中观察到一个很早就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农业社会),在邹衍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种状态的农业社会就已经作为一种基础范式,实施并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阴阳家与《幼官》
正如《管子》中五个与历法制度相关的篇章(《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所证实的那样,第一代阴阳家很大程度参与了农业社会理想化统治秩序观念的构建。这些观念是齐国文化的重要产物,因为在战国其他文化政治区域的作品中,这样的观念体现得非常有限。
在后文中,本文重点都将集中在上述历法制度文本之一——《幼官》上;作为早期的历法文本,其对“月令”(犹“时令”)类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著作与“河图”“洛书”的传统有着紧密联系②这方面更多的研究,可见李克(Rickett),苏海涵(Saso),史伟兹(Swetz)等人的著述。详见:W.Allyn Rickett(李克).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1,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一卷·修订版).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149-163.Michael Saso(苏海涵).“What is the‘Ho-T’u?’(“河图”是什么?)”History of Religion 17.3/4(1978):399-416.Frank J.Swetz(史韦兹).The Legacy of the Luoshu:The Four Thousand Year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the Magic Square of Order Three(洛书的遗产:四千年来对三阶魔方意义的追寻),2nd Edition.New York:CRC Press,2008.,故《幼官》之历史重要性不言而喻。马绛(Major)等人[11]178将《吕氏春秋》前十二纪的“月纪”部分、《淮南子》的《时则训》部分与《天文训》的主体部分、《礼记》中的《月令》部分、《逸周书》中的《周月》部分、《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部分,长沙子弹库战国墓楚帛书、银雀山出土汉墓竹简《三十时》等文本,同《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及《轻重己》一并归为此“月令”类③除了此处所引用的李克的作品外,针对月令(时令)类著作,马绛等人也引用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和王安国(Jeffrey Riegel)对《吕氏春秋》中这些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详见John Knoblock(约翰·诺布洛克)and Jeffrey Riegel(王安国).The Annals of Lü Buwei:A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Study(吕氏春秋:全译及研究).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管子》中本文认为是第一代阴阳家作品的内容,如果它们确实是最初形成于稷下学宫,并且确实包含在《管子》原貌文本之中,那么这些内容就会早于其他作品,并可能对其他作品产生深刻影响。
针对标题《幼官》,字面上可译为“负责管理青年的官职”,但多数学者赞同李零的观点[12],认为此为“玄宫”之讹误④然而,张富祥认为,“‘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张富祥:《〈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玄宫”指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建筑形制“明堂”,据称统治者在此举行各种与“月令”有关的政教事务。相较是否适合第一代之后的阴阳家,这个标题本身看起来更像是专业性术语,应当被视为后来对《幼官》核心内容的一个补充:因为作为历法文本,其本身仅仅是历法制度,并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标题——就像现代日历那样。
《幼官》的核心内容为统治者提供了精确的指导政令,以监管和规范普通民众的季节性生产任务。《幼官》的文本结构可宽泛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又含有若干层次文本,最早的文本即与统治者的季节性政令条例相关;其又被分为四部分,以与四时相配。
虽然《幼官》是以典型的短文形式呈现,但其原貌应是如文本所述的具体图形①魏德理(Dorofeeva-Lichtmann)把《幼官》中的内容称为“非线性文本结构(non-linear textual structure)”,可详见其著述(2005),Vera Dorofeeva-Lichtmann(魏德理).“Spatial Organ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Preliminary Remarks)(古代中国文本的空间组[序言]).”In 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xt,edited by Kayine Chemla:Springer,2005.。王廷芳、郭沫若[13]140复原了这一图形,此图以四时配四方,四方又各自围绕中方,中方即为统治者君位之象征。四方又以五行之一相配深入诠释说明,并置于各自图位部分②白奚写道:“四时教令的思想最初与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有关,但其上升到天人关系的理论形态并与社会政治发生联系,则有赖于阴阳思想的发展。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的流行是非常自然且容易的,因而阴阳与时令的结合是水到渠成的,四时教令的思想几乎可以说就是阴阳说的全部内容。五行说要与阴阳说合流,选择时令作为结合点是最简捷也是最有效的,因而五行与时令如何结合,便成了合流的关键环节。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五行与阴阳的合流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合流的实现。《幼官》在五行与时令的结合上做了最初的尝试。”(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版,第5期。)。如此一来,春季配以东方木,夏季配以南方火、秋季配以西方金、冬季配以北方水。另一个将《幼官图》认定为早期作品的标志是,它对于五行中“土”的诠释并未配以季节方向,这与后出所见“月令”类作品完全不同。
《幼官》“内层”的起始部分都较为笼统,统一遵循统治者的指令,四时各有不同。这些部分与君主对具体任务的规定有关,在每一季节的不同阶段,不同任务就在百姓中推行。接下来是一些简短的文本,用以说明季节性政令的更多细节,并且这些内容很可能是核心文本的一部分。然而,“中方”开篇未与任何时节联系起来,紧随着就是一段较长的文本,该文本在语言、语调与主题上与其他“内层”部分完全不一致——显而易见,这段文本应是后来增添。同样,据称整个“外层”部分也是如此,虽然“外层”也展现为五个部分,但其却与兵家思想有着直接联系,本文暂不涉及③然而,陈依优先考虑“外层”部分,并将《幼官》解读为一篇兵学思想论述,认为其为齐国提供了一个顺应四时而动的战略思想,目的是成就齐国中原盟主霸业。(陈依:《〈管子·幼官〉的兵学思想》,《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李克将《幼官》的形成时代定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但这个定期只是《管子》原貌得以汇编的时期,“中方”部分与“外层”内容可能即是在此期间被篡入。剔除前述内容后,《幼官》之核心在文本上展现为“内层”的四个部分,在概念上体现为农业社会理想的治理图景,这些内容就构成了第一代阴阳家思想范式的代表之作。本文认为,核心部分内容的形成应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纪晚期,这一时期与稷下学宫设立的时期相吻合。值得思考的是,战国初期,即稷下学宫建立之前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这段时期恰是中国在良性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凭借以可耕土地为衡量标准的重农经济,开始逐步实现自身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阶段正是《幼官》形成的历史背景。针对这一点,李克写道:
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必然在人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尤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早期的农历制度中,就列举了随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以及相应的人类活动[14]150。
《幼官》恰恰反映了李克所言“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层”部分,大部分都是与生产农时直接相关的各类指导规定,用以启动和完成各类任务与职责;依赖于此,人类在农业社会中才能得以蓬勃发展。《幼官》是早期中国的历法文献中最具代表性但并非独一无二的案例,其文本能够使君主臣民及时了解当下和未来的任务,并且能够告知他们重要的季节性禁忌和约束,如果不加以注意,这些禁忌与约束就可能容易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王蓉蓉所述: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预测规律的能力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农业层面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怀疑论层面的抽象问题。面对不可预知的世界,我们可能失去信心,可能感觉根本没有安定感。阴阳思想就是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出现的,通过创造诸种预测手段,接受变化的必然性,这种思想能够缓解失控带来的焦虑[3]15。
然而,《幼官》又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年历或者简单的历法文字,它亦是一部深刻的政治著作,清楚明白地强调了被四时循环围绕的、与“中方”联系紧密的统治者。与各个季节的诠释相联系,形成了一套具备仪式与象征意义的行为和事物,在相应的季节,统治者需要按指示去接纳、吸取并体现它们。例如,春季“君服青色”,夏季“君服赤色”,秋季“君服白色”,冬季“君服黑色”。文本还指示君主聆听适当的音乐、食用适当的食物、饮用适当的井水、进行适当的情绪培养、以适当的态度行政,每个行为皆与其特定的季节相宜。例如,“内层”的“南方本图”称①此处引用的原文,来自李克(Rickett,1998,2001)校正的《管子》文本,本文的英译亦来自其著并略有修改。W.Allyn Rickett.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2,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二卷·修订版).Boston:Cheng & Tsui,1998;W.Allyn Rickett(李克).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1,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一卷·修订版).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藏朴②从李克说,改“薄”为“朴”。W.Allyn Rickett(李克).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1,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一卷·修订版).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178.纯,行笃厚……
《幼官》还规定,统治者在实施各类政府政令时,也要如同自身的礼仪活动表现一样,与各个季节相配。其基本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概念“和”之上的,君主需要将其自身和政策与四时历法完美相符,以“因于时”。除农作之外的行政活动,春季表现为鼓励,夏季表现为赏赐,秋季表现为惩戒,冬季表现为刑罚。例如,“内层·东方本图”称:
合内③从李克说,删“空”字。同上第176页。周外,强国为卷④从李克说,改“圈”为“卷”。,弱国为属⑤虽然文中没有具体说明,但本文认为这是在冬天时将年幼子嗣送往邻国的一种普遍做法,在那里他们将接受异国导师的教育,与邻国皇室建立起家族式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有可能会在其生活中持续下去。当然,春天来临时这些子嗣们就会被护送回他们的母国。。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辞⑥从李克说,改“司”为“辞”。,事变日至……
《幼官》亦告诫统治者,颁布具体政策以开展各种任务,需要在合适且明确指定的时间段里进行。这些任务有着过度简化的倾向,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根据《幼官》的推算,以阴阳运动规律为记,一年被分为三十个独立的时间段,春秋季各八,夏冬各七,每一时间段为十二天;这就为在哪些时间段实施哪些活动提供了精确的指导⑦张富祥为了证实其观点,即“幼官”与“幼官图”是与祭祀仪式相关的文本而非历法性质的文本,特别是考虑到“中方”部分没有日历时间和方向,他指出,被分为“八-七-八-七”的三十节气系统与太阳年不完全相应,同时指出,当试图融合五行时(将一年分成五段),“这一设计是理论性的,与传统的四时制度有冲突,于是将五行‘播而为四时’,采取调和的模式。”(张富祥:《〈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例如“内层·北方本图”称:
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⑧李克认为,此处意指“在收获后将赋税收集缴纳给国家”。W.Allyn Rickett(李克).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1,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一卷·修订版).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181.。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
作为君主独有的责任,针对农业社会中需要监管的季节性活动,不但需要知道开展和完成的准确时间段,还需要确保这些时间段能够广泛、明确地为民众所了解。在《幼官》的描述里,君主并不会像《论语·卫灵公》所称赞的“圣王”舜那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幼官》中的统治者更像是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负责在正确的时间唤起正确的音符。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写道:
合适的次序是被预先确定的。现象以其阴阳能力转化为存在,自然秩序的阴阳参配固定于其中。这正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自然而然,天即阳,地即阴;日即阳,月即阴……人类不能强行宣称这是阴,那是阳,他们只能让万物各归其位[15]46。
但人类如何知道何处是事物正确的位置?回顾《幼官》和其他相关早期中国历法文献的神话起源,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首次创立历法的圣王——这一成就通常归功于黄帝。例如,《史记·历书》即指出:
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载孔子言亦称:
(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
由于后世统治者都是在古代黄帝创建的历法上有所变化区别,故就不再需要圣王了。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预先确定的,并且建立在随阴阳季节运动不断变化的自然次序上(特别是就时间与空间而言),而黄帝仅仅是发现了它们;但一旦被发现,统治者就只需要去遵从这种次序。关于这一点,曹立明写道:
《管子》所说的“因”,就是抛弃自己的主观意见而以万物为法,如实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管子》把“因”看作“无为之道”。那么《管子》所说的“因于时”就是顺应四时的变化而活动,而不是按照主观意愿肆意妄为,这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管子》是部治国理政的大书,它“因于时”的主张更多是为“圣人”即理想的统治者而言的,具体来说就是要求统治者掌握四时变化的规律[16]。
这种为《幼官》所依据的自然秩序逻辑,就是按照第一代阴阳家的阴阳思想范式得以合理演绎的。阴阳家的范式与道家有着实质的区别——在道家的范式中,“阴阳”与“道”的概念在宇宙、创生以及生命本原等维度上都有着突出体现。庄子笔下世界的特点,就是万物之间永恒自然的转化,这些转化永远无法被有意识地预测或者进行管理;对庄子而言,要成为得道之人,需要一种深刻的修行,即放下所有的期望、抛弃所有的成见。
在这方面老子也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万物之本原在于:道生一(混沌之气),一生二(气分阴阳),二生三(阴阳化生天、地、人),三生万物。但是,《幼官》并未将“阴阳”视为在宇宙中积极创生的动因,其对“阴阳”的理解更为克制有限,并未上升到宇宙论的层面。除了“中方”部分,《幼官》的其他部分并未提及“道”;其展示的世界是彻底自然化的,用郝大维与安乐哲(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17]的词汇来说,在《幼官》中并不存在一个“生生(emergent)”①对“emergent”的一词的翻译参考安乐哲著、温海明译《对批评的响应》,《求是学刊》2005年02期。——译注。
与道家类似,《幼官》也将阴阳理解为气的两种属性,不同之处在于,《幼官》将阴阳看做天地的产物,而道家认为是阴阳化生了天地。《幼官》中规定了“地气发”和“天气下”的时期,这种变化中,阴阳是调节天地间自然力量的根本原理,并体现在四时周期运行中:春季阴消阳长,夏季阳盛阴虚,秋季阳衰阴长,冬季阴盛阳虚。以这样的方式,虽然阴阳循环是彼此感应且相互交融的,但其仍按照自然秩序的严格条件逐次展开,这样四时很自然地就表现出阴阳的盈亏。换句话说,通过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监管调节功能,阴与阳就成为“时”的两个构成要素。
除了由天地、阴阳、四时构成的自然秩序之外,还有人类的秩序。在《幼官》中,人类的秩序主要呈现农业化的特征;其很少关注以防御和攻击敌人为主的战争秩序②对战争的关注并未体现在该文历法部分中。虽然《幼官》“外层”部分都与战争相关,但其皆为后人增添。,也不关注人性、正义、真诚一类的道德秩序,甚至不关注仪式与祭祀方面的宗教秩序。人类秩序的蓬勃发展,依赖于成功遵循自然秩序下的农业生产规律,并与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战争、道德与祭祀于此并不重要。
虽然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系统,但自然秩序是基础性的,并且在规范上优先于人类秩序。理想情况下,人类秩序可以与自然秩序规律相感应(包括天地、阴阳、四季等)。《幼官》在这一点上阐述得最为明确;其中写道,统治者在春季“治燥气”,夏季“治阳气”,秋季“治湿气”,冬季“治阴气”。裴文睿称其为一种“模仿性自然主义(imitative naturalism)”,对此他阐释如下:
在春夏之时,生命得到培育:花繁叶茂,作物生长,动物繁衍生息。在秋冬之际,凋亡得以蔓延:花枯叶落,作物收成,动物死亡、冬眠。类似地,人类社会亦必须有其增长发展与休养生息的时期。在春夏季节,“阳”的生命之力正值旺盛,统治者应当慷慨分配社会财富,在轻罪上宽宏大量。到了秋冬,“阴”的衰亡之力达到顶峰,统治者应当严格执行法律,在重罪上积极落实[15]30。
正因为阴阳思想的规律性遵循了基本的自然秩序,其预测能力是任何一种任何占卜都无法比拟的。不过,《幼官》也确实意识到有些情形是背离季节现象之通常规律的,其诠释不难理解:异常的自然现象是由于统治者的做法没有符合时间与空间的自然秩序,从而产生的恶果。就自然秩序的基本条件及阴阳变化而言,如果统治者计算错误、或者忽略它们——无论是错失时节,还是肆意妄为、强加自己主观意志——都会难以实现自然秩序之和谐。这是因为,在这人与自然的有机体系中,人类秩序存在对自然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所以《幼官》强调,如果统治者强行以适合其他时节之气来治理某个季节,就会导致异常或灾难。正如“内层·南方本图”所称:
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
《幼官》与《管子》中其他出自第一代阴阳家的历法文本亦有紧密联系,为了说明其共通之处,此处以《四时》中的一段话结尾——这段话亦体现了本文所探讨的很多主题:
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结论
相对来说,《幼官》的重心集中在“阴阳”思想上,实质上未曾涉及其他政治、哲学与宗教领域,因此本文认为《幼官》是第一代阴阳家的主要代表作品,《管子》中的其他若干篇章亦是如此。不过,本文并不认为阴阳家学派展现了中国思想的古老传统,其应是齐国文化特有的发展,它随着齐国重农主义农业社会的建立而出现;在初始阶段,这一学派是独立于其他诸家发展起来的。其统治角度亦是非常独特的:与殷商不同,阴阳家并不关注对祖先鬼神、自然神灵、甚至天帝的祭祀;与西周不同,其不关注“天”与“天命”的存在;与儒家不同,其不关注道德观念;与法家更有所不同,其对统治者以自身权威立法设刑的做法也缺乏兴趣。
虽然阴阳家的主要关注只限于农业社会,但随着时间推移,第一代阴阳家所仰赖的农业基础被逐渐取代,诸种变化将阴阳思想引入不同领域之中。一个变化出现在齐国,阴阳思想为邹衍所奉行,并应用于政治理念之中;方士们紧随邹衍的脚步,将其应用于占卜预测、召神劾鬼、炼丹长生等方术之中。另一个变化方向出现在秦国,于此《管子》的原貌作品得以编纂汇集,知识分子们首次将阴阳思想与方兴未艾的法家思想结合起来,同时掺杂了道家的宇宙观念;这种相互渗透与彼此融合,直接催生了盛行于汉代的黄老学派。
[1]Kidder Smith(苏德恺).“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Taoism,‘Legalism,’et cetera(司马谈与道家、“法家”等(概念的)发明)”[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February 2003).
[2]Herlee Creel G(顾立雅).What is Taoism?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什么是道家?以及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其他研究)[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3]Robin Wang(王蓉蓉).Yinyang: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阴阳: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天地之道)[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2.
[4]Marcel Granet(葛兰 言).Danses et legends de la Chine ancienne(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M].2 volumes.Paris,France:Libraires Felix Alcan,1994.
[5]刘宁.由上古历法推考《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原貌[J].管子学刊,2013,(3).
[6]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1997,(5).
[7]Mark Lewis(陆威仪).The Flood Myths of Early China(中国的洪水神话)[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8]Thomas Michael(马思劢).The Pristine Dao:Metaphysics in Early Daoist Discourse(质朴之道:早期道家话语的形而上学)[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9]W.Allyn Rickett.“Guanzi(Kuan Tzu):The Book of Master Guan(《管子》)”[M].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edited by Anthony Cua.New York:Routledge,2008.
[10]Hongkyung Kim(金弘扬).The Old Master:A Syncretic Reading of the Laozi from the Mawangdui Text Onward(老子:以马王堆帛书文本为起点对《老子》的调合性解读).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
[11]John S.Major(马绛),Sarah A.Queen(桂思卓),Andrew Seth Meyer(麦安迪),Philip D.Roth(菲利浦.D.罗斯).The Huainanzi: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理论与实践之指南)[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12]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J].管子学刊,1998,(2).
[13]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等.管子集校(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4]W.Allyn Rickett(李克).Guanzi:Political,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Volume 1,Revised Edition(《管子》:中国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散论,第一卷·修订版)[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5]Randall Peeremboom(裴文睿).Law and Morality in Ancient China:The Silk Manuscripts of Huang-Lao(古代中国的法与德——《黄老帛书》).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16]曹立明.《管子》“四时”的观念的生态意蕴[J].三峡大学学报,2017,(2).
[17]David L.Hall(郝大维)and Roger T.Ames(安乐哲).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过孔子而思).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
K877.5
A
1002-3828(2017)04-0014-10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02
2017-11-07
马思劢(Thomas Michael),于200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博士学位,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中国的哲学与宗教。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