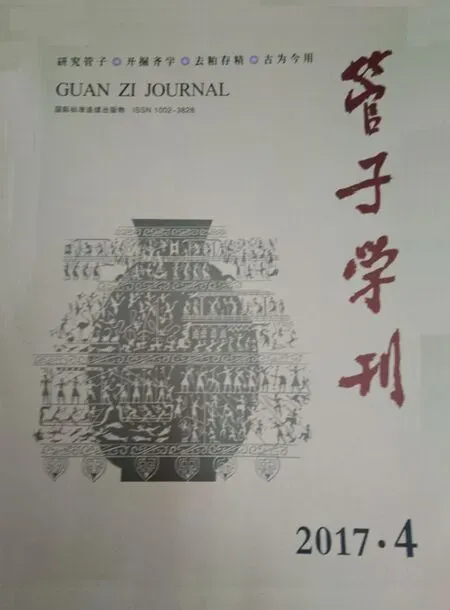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管子·牧民》“四维”说新解
林素英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 台北)
《管子·牧民》“四维”说新解
林素英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 台北)
《管子·牧民》开篇即指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倘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此“国之四维”说,柳宗元之《四维论》,却明白指出该说只有二维,且怀疑其非管子之言。盖因管子之后的先秦诸子学说,虽然人人皆言礼与义,但都欠缺与廉、耻合并讨论之现象,更未出现以礼、义、廉、耻合称为国之四维者,故而相关现象的确值得认真关切。尽管柳宗元之质疑,后续也有学者发出回响,不过,多以文辞绞绕居多,或者诿过于《管子解》或《牧民解》之搀入《经言》,实则无益于解决问题。本文转从不同之角度重新解读《牧民》之文本,从古代宇宙观之借用与渔猎社会之特点,尝试重新架构管仲借用天时地利为“二绳”,再以渔猎社会的网罟实情,建构相当有系统的“牧民”之道。
《管子·牧民》;四维;四维论;天时;地利
前言
《管子·牧民》开篇即于首章《国颂》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点明四维攸关国之存亡。然后于提出“四维”后,续言“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确实指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
然而有关“国之四维”说,唐之柳宗元(773—819)开始提出强烈质疑,于《四维论》之开宗明义,即明白指出“《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文中主要申论“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再于文末肯定“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1]1280。虽然对照《权修》所载,对于牧民之大要已有“修礼、行义、饰廉、谨耻”之进一步说明,则《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说法,似又不应为虚,可惜《权修》也未具体说明礼、义、廉、耻之内涵,自然难服柳宗元之心。盖因管子之后的先秦诸子学说中,举其要者而言,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都欠缺将礼、义、廉、耻合并讨论之处,更缺乏将此四者合称为国之四维者①依据计算机检索“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系统,所得讨论廉、耻之数据如下:《论语》中,论“廉”之段落有1例,论“耻”之段落有11例。《孟子》中,论“廉”之段落有5例,论“耻”之段落有9例。《荀子》中,论“廉”之段落有16例,论“耻”之段落有13例,将“廉耻”合论之段落有5例。《老子》中,论“廉”之段落有1例,论“耻”之段落有11例。《庄子》中,论“廉”之段落有10例(内篇1例、外篇4例、杂篇5例),论“耻”之段落有8例(内篇0例、外篇4例、杂篇4例)。《墨子》中,论“廉”之段落有8例,论“耻”之段落有0例。《商君书》中,论“廉”之段落有4例,论“耻”之段落有1例。《韩非子》中,论“廉”之段落有39例,论“耻”之段落有7例,将“廉耻”合论之段落有2例。。相对于此,倒是先秦诸子,人人皆畅谈礼与义,即柳宗元所见之“二维”,故而柳宗元之质疑亦有可说之处。看似毫无问题的“国之四维”说,先由柳宗元提出质疑,后续也有学者发出回响,则管仲的治国之道到底在“二维”或“四维”,抑或是其他内容,乃牵涉治国之大根本,是值得再深思熟虑之大问题。故而本文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与目的;其次,论述“二维”说之内涵与回响;复次,尝试提出牧民“四维”新说之架构与意义;最后,提出简单结论。
一、柳宗元“二维”说之内涵与回响
柳宗元最早对“四维”提出质疑,而提出“二维”说,其后也引起一些回响,以下择要论述之。
(一)柳宗元之质疑与“四维”之相关回响柳宗元质疑“四维”说之主要论点如下:
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1]1280
柳宗元以为“廉”与“耻”都应从属于“义”,故无法与“义”相抗衡而并称为“四维”之一。柳氏之说,若从严格之类属统摄概念而言,当然无可厚非。然而若以“廉”与“耻”为“义之小节”,则不免小看“廉”与“耻”对于个人气节之重要。柳氏又进而申论管仲以礼、义为“二维”,犹如圣人以仁义立天下之概念,虽有强调彼此倾向之差别,然而都是实践“理道”之异名,故而即使反对将“廉”“耻”与“礼”“义”相提并论而为“四维”,却也不反对“廉”“耻”之重要。
相对于柳宗元以为“廉”与“耻”为“义之小节”,欧阳修(1007—1072)则盛赞管仲之能言,不过却把重点放在廉耻,认为: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2]2070
显然将号称“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分别从攸关客体的“治人之大法”与主体的“立人之大节”两差异处,将原来四者并列之“四维”区分为两大部分。若客观言之,或可称为双重“二维”说,甚且还特别注重关乎个人主体的“立人之大节”,大大有别于柳氏以“廉”与“耻”为“义之小节”的说法。
黄震(生卒年不详)也不同意柳宗元之说,而持不同看法:
子厚谓“廉与耻义之小节”,而病管子四维之言……夫“廉”与“耻”,岂特小节?“廉”纵可属于“义”,“耻”则当属于“礼”,又不当尽指为“义之小节”也。管子之以“维”言者,盖指为治之范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谓①黄震撰《黄氏日抄》卷60,收入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82页,《四维论》之集评。。
黄氏不同意“耻”为“义”,认为应属于“礼”之范畴。若从“礼”之作用在于激发人之自觉,而防范不当行为发生于未然,显然比将“耻”归类于“义”还更恰当。然而无论将“耻”归入“义”或“礼”之范畴,都不该是“小节”而已。
顾炎武(1613—1682)在面对明末清初士大夫变节降清之实况,于引述欧阳修对冯道之评论后,更把重点放在“耻”,认为:
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3]481-482。
顾氏之说,当然是经历国破家亡之后的切身体悟。由此更可见,“廉”与“耻”绝非“义之小节”,而如此有关节操之事,更有待人能否启动羞恶、愧疚之心念而来。换言之,心能否发挥灵明之知觉作用显然极为重要。
以上诸说尽管与柳宗元的“二维”说不尽相同,然而皆不外乎将礼、义、廉、耻,按照个人所见重要性不同作不同之分类组合,且都将此四者之提倡,视为治国之重要管道。同时,还可归纳出一共同现象,亦即“礼”与“义”之重要性是大家所见相同的;而此一现象,又可与计算机检索先秦诸子讨论礼、义、廉、耻之状况统计相同。
(二)柳宗元“二维”说引发之另类回响
相较于上述学者在礼、义、廉、耻四者之间切割、绞绕,另有一类异说,则受到柳宗元“二维”说之影响,转从有关《管子》之成书因状况复杂,故而怀疑“国之四维”一节可能为《管子》之佚篇搀入,而非管子之言。盖因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校订之《管子》有86篇,而今本仅有76篇,已亡佚10篇,因此虽然《牧民》位居今本《管子》“经言”之列的首篇重要位置,而“四维”一节,的确也难保不是《管子》亡佚之篇章搀入。甚且最合理的怀疑,就是该节乃由《牧民解》之解说搀入,而本非管仲之言。
何如璋(1838—1891)即继承柳宗元之说,而认为此节乃《牧民解》搀入:
礼义即礼节,乃治国之法度,所包甚广。文但言“不踰节”“不自进”,则礼义之一端也。廉耻即荣辱,荣辱加于赏罚。法度赏罚四者,御世大纲也,文但言“不蔽恶”“不从枉”,乃礼义之绪余,安得为“四维”?即此可证其非《经言》也。柳子厚《四维论》以“廉耻”二字不能与“礼义”并举,其论甚允[4]12。
何氏之说虽也赞同“廉耻”二字不能与“礼义”并举,然主要归咎于《牧民解》解说之不够周延。不过若从何说以“法度赏罚”四者为御世大纲,又清楚可见其仍然认同应以“四维”为治国御世之大道,只是“四维”之内容必须更动,改采更具有行政效力之赏罚,以取代抽象之荣辱与廉耻观念,达到强化执行法度之效果,促成国治世御之目的。由于何氏乃晚清学者,其“新四维”说已受到西方论“法”的概念所影响,故而该“新四维”说,实可区分为法度(法制)之制定与如何执行两部分,以致或可称为另类之双重“二维”说。该说虽合乎近代之法治概念,然而毕竟与管仲之《牧民》内容距离嫌远。
稍后之张佩纶(1848—1903),则更进一步指出:
礼、义、廉、耻所括非止一端,必谓“不踰节”即足尽礼,“不自进”即足尽义,“不蔽恶”即足尽廉,“不从枉”即足尽耻,转不如《权修》所言之“修礼、行义、饰廉、谨耻”为包举无遗。《牧民解》已亡,疑此乃《管子解》,非《经言》也[4]12。
张氏同样不满意“国有四维”一节之解说,认为是《管子解》之文句传写搀入,本非《经言》之内容,然对“二维”之说也无赞同之意。张氏转从《经言》之另篇《权修》,找出更合适之“修礼、行义、饰廉、谨耻”,认为“修、行、饰、谨”更能凸显实践礼、义、廉、耻之特性,表明其认同礼、义、廉、耻共同组成国之“四维”的内容。张氏之说算是较接近文本之义的说法,然而将问题推给虚拟之亡佚《管子解》,对解决问题并无实质帮助。
上述针对柳宗元“二维”说,都提出或出自《管子解》或《牧民解》不圆满解说之搀入。此固然也是试图解释之方法,不过却也因为文献不足征,亡佚之内容究竟如何,实已不可考,而有节外生枝之嫌,终非良策,仍应另谋解决之道。
二、《管子·牧民》“四维”说之内涵
客观言之,就文本之内容重新思考而不节外生枝,应是较根本可行之办法。倘若文本本身还有其他理解方式,则不必在“二维”或“四维”之文义间纠缠绞绕。以下即尝试从另一可能解读之空间切入,重新架构管仲之牧民思想,或许可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之不同风貌。
(一)“牧民”概念与“绳治”齐国之道
重读《管子·牧民》首章《国颂》,从题旨句“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已隐约透露一些重要,然而过去却一直被忽略之讯息。亦即从起始句之“牧民”特殊语汇,已昭示阅读者应该注意管仲当初受命治理齐国之时空环境,若要正确解读礼、义、廉、耻何以合称“四维”,实无法脱离其时空环境而言之。
位在山东半岛的齐国,古代属于渤海与泰山之间的青州,《尚书·禹贡》之记载如下:
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5]81。
由于山东半岛之东隅已深入渤海湾,即使在周初,仍属偏远地区。当初武王伐纣,虽然快速取得朝歌,不过周之势力根本无法掌控广大东土地区,因此分封姜太公于营丘,主要欲藉太公之文韬武略对抗东夷部族、开发东隅地区,进而与鲁形成夹辅周王室之重要力量。当时位在东边隅夷地区之部族,多数倚靠渤海湾一带渔盐海产之资源生活,因为地方过于偏僻而荒略少开发;古莱州、登州一带之夷人,主要从事放牧为生,进贡之物以蚕丝为主。泰山谷地一带,则以丝、麻、锡铅、松木与奇石为主。大致而言,土地未开发之状况相当普遍。
倘若参照《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前往营丘就职时,莱侯即乘周初定之际,未能致力于远方,故率领莱夷趁机与太公争国。由此亦可见当时齐国所辖之地,乃以夷人居多,于是太公至齐以后之施政,即采取“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之方式,以是而人民多归齐[6]551。至于此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则应与东夷人习于放牧之游牧生活有关,习惯于奔驰原野之田猎生活,而不喜被礼数约束。此一状况,对照《齐风》即可见一斑:《还》《卢令》《猗嗟》,展现齐国人自在傲人的田猎生活;《著》《东方之日》《敝笱》《载驱》,则展现齐国男女开放而不拘礼节约束之处。
基于齐国偏处东隅之地理环境,再加上长期之放牧生活,遂形成偏向豪迈不羁、不拘小节之民风。因为习于放牧生活,所以管仲受命治理齐国,即有鉴于此一特殊之生活习俗,而采用当时国人渔猎生活中最熟悉之语词“牧”,表达其治国安民政策之核心概念。因此《管子·牧民》首章《国颂》,题旨句“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之形成,乃建立在齐国特殊渔猎社会生活经验下的智慧结晶:以“有地牧民者”为统治者之代称,同时也凸显统治者应懂得掌控缰绳如何收放自如的放牧之道;以“务在四时”代表对天时之掌握,且应适时实行正确措施;以“守在仓廪”代表对地利之掌握,且应针对不同之地理环境实行合适之开发运用办法。换言之,此一题旨句,其实已可概括管仲最重要之施政理念:以牧民者居中,成为施政主体,宛如驾驭马匹前进之驭马手,天时与地利则为手中之缰绳,随时视状况之改变而做最好的调节适应。
忖度管仲此一之施政理念架构,或许还是对古人宇宙观之化用,此即《淮南子》所载: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淮南子·天文训》)
管仲借用子午、卯酉为“二绳”,以架构最重要之时空运转轴心概念,再搭配渔猎社会之放牧经验,使牧民者成为居中掌控缰绳之驭马手。“二绳”则是驭马手可以灵活转动180度,甚至360度的可操纵筹码,力道之拿捏与角度之变化,都可适时调整马匹奔跑之方向以达到预定目标。从“二绳”所架构之时空运转概念,已可形成运转自如之四方五位图,展现立体之政治架构。若再加上“四钩”与“四维”之居中联系,则可形成八方九宫,乃至于十二、二十四之时空运转方位图,使时空交织图像更为细密,且与驭马手之完美掌控马匹奔跑之状态相互呼应。由于齐国的天文学成就相当高,因此管仲仰观天文变化,俯察放牧驭绳之状况,遂转化“二绳”概念为天时与地利,且以较具体之“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呈现;再以无论“四钩”或“四维”都具有居中联系以利时空运转之特质,故而以攸关渔猎网罟最具体之“维”的概念,而宣称“四维张,则君令行”。
(二)“四维”如何协助牧民者掌握天时与地利
要理解“四维”如何呼应天时与地利,以达到借用“二绳”而牧民治国之目标,首先必须先明白何谓“维”,再考虑“四维”如何响应对天时与地利之掌握。
《说文》载:“维,车盖维也,从纟,隹声。”段《注》则云:“许以此篆专系之车盖,盖必有所受矣。引申之,凡相系者曰‘维’。”[7]664考察古之用以相系之“维”,最常以草木之茎叶不断搓揉之,使成绳索,用以支撑物体,或与准合用,以为测量水平与垂直之工具,再透过引申水平与垂直纵横交错以制定标准的原理,成就各种事物之法度,而为治国之最重要支撑。具体言之,则“务在四时”可代表纵轴子午线,而以“守在仓廪”代表开发地利之成果的横轴卯酉线。
若能将此“二绳”之功能灵活运诸掌上,则能把握《管子·形势解》所载之状况: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此说明牧民之主能在广开耕地以尽地利之外,进而效法四时生杀有常之天道以引导农事,则可使国家多财,农作收成丰盈而仓廪殷实,否则将导致《牧民》所载前后强烈对比之状况: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管子·牧民》)
经由此反差对比,已可清楚说明能否掌握天时与地利,乃国家治乱之根本关键。甚且从“上服度,则六亲固”,也隐约透露“人和”之概念乃与天时、地利鼎足而立,成为国之安治的三大重要法门。不过此处因旨在强调掌握天时与地利之重要,故而仅以“上服度”一语统括牧民者德行良好之基本前提,且专就天时与地利以言之。例如《枢言》与《山权数》都有天、地、人三者并称之现象:
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管子·枢言》)
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地,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管子·山权数》)
此两则资料都明显把天时摆在最前面,虽也提出“德先”“守时以待天权”之概念,但重在说明牧民者应有德,且懂得适时权衡,故而会特别注重天道四时之变化,纵然遭遇天灾逆行,终因早有防备,且能适时采取必要之救荒措施,故可避免人民陷入沟壑之灾难。
至于天时与地利何以有赖“四维”以维系之,则应溯源渔猎社会之生活方式。《说文》载:“网,庖牺氏所结绳以田以渔也,从冖,下象网交文。凡从罔之属皆从网。”[7]358故知网、纲皆从网而来,乃以粗细不一之绳索交织而成,彼此互相联系支撑,在中间者为小细绳,四周之“纲绳”则由较粗之网纮、网维组成,因而“纲举目张”即叙写渔民张开渔网合力捕鱼,控制自如又井然有序之情形。随着捕鱼之规模大小不同,因而在四周协助拉网之渔民也多寡不一。然而若要使渔获量到达较可观之程度,至少需由四人分别在四角落着力,其余者再从旁协助,则是较稳当之经验法则。管仲之“四维”说,即借用渔捞“四维张”而渔获量大之经验,以协助合乎知天时以尽地利之政令顺利进行。
另外,配合田猎所需,非仅需要有极佳之驾驭马匹的技术,相应的射箭技巧也必须严格要求。回顾古代贵族男子出生三日即要行使射礼,成人举行冠礼之时,其二加之戎装皮弁,也象征男子一旦成年,就应有志在四方以保家卫国之责任,可知勤于习射正是古代男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①其详参见《仪礼·士冠礼》及《礼记·冠义》之相关记载。。一般中原一带之贵族子弟尚且如此要求男子,则长期处于渔猎社会之齐国,射箭技巧是否精湛更是生活中的大事。由于要练就炉火纯青的射箭技术,因此平日大张射侯以锻炼射箭技巧者自然不在话下。猪饲彦博即注意到《大射仪》中出现以小绳缀侯之四角而系之于植以为“维”的现象[4]12。因为抗侯习射需要先系绑四个角落,于是管仲也可说是借重齐人平日之生活经验,使国人易于理解治国之大道在于谨饬“四维”,而不言“二维”或“八维”。
(三)“四维”如何维系天时地利
管仲将礼、义、廉、耻号称为国之“四维”,乃以礼义为纵轴子午线掌握天时,以廉耻为横轴卯酉线掌握地利。再以牧民者位于轴心,借用时空运转概念,而将此两轴线之四个端点成为治国之最重要施力点。
1.以礼义掌握天时
由于上古时期到处是洪水猛兽,在自然环境处处存在危机之生活形态下,使人更容易感受人之有限,而需要寻求特殊力量之协助。因为趋吉避凶非仅是生物存在之法则,更是人情之常,而礼又本于人情所需,所以《说文》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7]2正反映人之心理需求与行为实践,说明人藉由礼仪之执行,始能达成事神致福之祈求。由于危机是时时存在的,因此从周代祭祀系统区分成天神、地示(祇)、人鬼三系,以达到敬受天命、崇德报功,展现人文精神、提升人性光辉之目的[8]276-357,即可说明祭祀乃顺随四时而针对不同对象进行祭祀之差异,祈求国泰民安,资源丰足,希望形成“国多财,则远者来”之局面。因此管仲即明白表示对此三系祭祀系统之遵从:
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管子·牧民》)
由于礼主敬,倘若不诚、不信,态度散漫、倨傲,则无以达到事神致福之要求。透过《左传》刘子一段闻诸古人所云,即最能说明四时祭祀乃古代之生活常态,内存诚敬即是礼义之表现,至于表现在外,则必须遵守仪式之各项要求,而显现出一定之威仪。刘子云: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由此最能凸显有地牧民之能者、君子,第一优先要做的,即是谨肃威仪、敬以行礼,始能引导百姓敦笃守业、把握四时勤于农耕。至于有关“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乃以礼义着重内心之操存,而威仪则发为在外之行为态度之表现,其关系如下:
《说文》载:“义,己之威义也,从我从羊。”
段《注》:“古者威义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郑司农注《周礼·肆师》:‘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为“谊”,是谓“义”为古文“威仪”字,“谊”为古文“仁义”字。’故许各仍古训。”[7]639
由于“义”字从“我”从“羊”,“羊”有美好之义,代表祭祀者以虔敬之心献上美好之物品,藉此表达事神祈福之诚意。复以“我”字取象古代兵器之形,故与威仪相关,引申而为实践礼仪时必须保持敬慎谨肃之仪容。由此更可知礼与义(仪)乃二而一之事,为礼仪实践之表与里,必须兼内在之礼义与外在之威仪而有之,方成为实至名归之礼。
管仲又特别于《四时》强调牧民者上知天时之重要:
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庸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管子·四时》)
牧民者能知天地之信明、信圣,故能遵礼行仪、按时祭祀,带动百姓按四时辛勤农事,以便秋收之时能够仓廪丰盈。收成之后,更应举行报社之祭,回报天地鬼神赐予风调雨顺之气候,而得使农作丰收、大有年之恩德。由于五谷丰收为仓廪丰实之根本,因此《小匡》之中,虽记载士农工商之四民各有其四时应力行之大事,不过对于农民应笃行之职责述之最详,且还深表敬意:
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耞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秀,列疏数,首戴苧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管子·小匡》)
由于古代农业最需要适时掌握四时之变化以进行农耕,从春耕之前的烧田、翻土、犁田等准备工作,到播种、育秧、插秧,以至于多次清除田草,引水灌溉等等工作,不但极为费时费力,还需费心照顾,更需仰赖上苍帮忙,提供农作物有风调雨顺之生长环境,进而可期待秋天之丰收大有年。倘若农民不能勤勤恳恳专心致力于农事,而好逸恶劳,耽误农耕之时,即使后来幡然悔悟而想补救,往往也会因为时节已过,以致落入虽勤苦而难成之结果。
齐国原本主渔盐、工商之利,然而国家经济并不甚佳,故而管仲更深知衣食足之重要,也因此特别注重尽地利以开发农耕。对照《诗》之所载,《齐风》虽未选录农事祈报诗,然而从《豳风·七月》诗中每月之农家生活记事,已可说明农家生活之共相。《豳风·七月》虽非采自齐地,以致每月之具体行事内容会随着地域差异而稍有不同,然而都明确说明按照行事历老实做事之重要。对照《周颂》为数可观之农事诗或祈报诗,例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丝衣》等,都可见辛勤耕作与祭祀酬谢天神、先祖之重要。有鉴于此,管仲在指示顺民之经时,即明白说明“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为实践重点,当然也是施政之主体工作。
2.以廉耻善尽地利
管仲最早将人民之职业进行士、农、工、商之分类,只是历代“四民”之顺序不尽相同。将农之排序放在齐国向来注重工、商之情形,凸显管仲重视农事为治国根本之重要地位。荀子则强调“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进而称“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务使四民各尽其职,且从其将农之排序改列在士之前,成为“四民”之首,更直接点出攸关衣食充足与否之农民问题,乃是治国之根本,故而特重农民之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因此管仲紧接在题旨句“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之后,即指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说明牧民者应重视“有土斯有财”之事实,从广为开辟耕地,以提高农产收获量而增加财源。若能如此,则非仅远者慕名而来,既有之人民也不会见异思迁,随便迁徙。由于能专心致力于农事生产,因此在仓廪实、衣食足之民生要求外,再进而从知礼节、知荣辱之层次提升生活质量。如若不然,则将沦于“野芜旷则民乃营,上无量则民乃妄”①《管子·牧民》“野芜旷,则民乃营”之“营”,原作“菅”,房玄龄于《注》云“菅,当为奸。”然而“旷”与“菅”之韵不协,因此安井衡以为“菅”当为“营”,乃字之误。“营”,犹贪也,引自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3页。之状态。盖因田野旷废荒芜,生产无法满足民生基本需求,则人民居无定所、到处游荡,于是蝇营狗苟、贪得无厌,寡廉鲜耻之行为无所不为,导致民淫而刑繁,社会无法安定、国家无法治理。
盖廉与耻之本义均与农事有关,以下即先从字形结构分析“廉”之语义:
《说文》载:“廉,仄也,从广,兼声。”
段《注》:“此与广为对文,谓偪仄也。廉之言敛也。堂之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廉,隅也。又曰: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7]449
从“廉”与代表“殿之大屋”的“广”相对为文,故知“廉”有堂屋偪仄之义,因为古之堂屋边缘称为“廉”,有隅、棱之限制,因此有收敛、节制之义,遂可引申居住于堂屋内之人,行事清、俭而不逾越隅、棱之限制。“廉而不刿”之语词,即根据古代生活状况而引申为行事正直而不伤人之义。又因为“廉”以“兼”为声,而此“兼”声又有示义之作用,所以应再进一步追溯“兼”之语义。从“兼,并也,从又持秝。‘兼’秉持二禾,‘秉’持一禾。”[7]332以及“秉,禾束也,从又持禾”[7]116-117之记载,又可知“廉”之字形结构意义,实可追溯到农业社会之生活经验,此从金属类收割谷物之器具,乃在“廉”加上偏旁“金”以行辨义之用,而称之为镰刀,即可见一斑。谷物收割后,取象人以手持禾即为“秉”之基本状态,倘若所持稍多,则以“兼”之持秝、持二禾为限,倘若超乎此,则为贪多务得、令人嫌恶之现象,故而“廉”之引申义乃可与“贪”相对。
至于“耻”之语义,则从《说文》:“耻,辱也,从心,耳声。”[7]519所载,可推想该入乎耳而著乎心者,应属闲言闲语一类之批评而非赞誉之言辞,故而让人听闻之后会产生有所“辱”之感觉。
若再查考“辱”之语义,则发现“耻”与“辱”互为转注,而《说文》载:
辱,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畺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7]752。
古代农业社会观象授时的主星即是大辰星,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中的房、心、尾三宿之总称。二月初,角宿开始在出现龙角于东方,即俗称之“二月二龙抬头”,也是植物冒新芽之时。房星则为龙腹,后来也称农祥星,凸显把握时机工作将有利于农事发展。由于心宿二是一颗相当大而且亮之一等星,也称大火星,三月黄昏时即见龙辰,最引人注目。因此观察天上龙星出现之位置,即是掌握节候以致力农事的最重要时期。《国语·周语》即记载虢文公在宣王即位而不行藉田礼时,即举古之天子于立春日率臣民迎春气,带领臣民启动春耕之例勇敢进谏①其详参见左丘明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周语上》(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第15—17页:“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王其祗祓,监农不易。”,于是宣王乃使司徒、司空等准备举行藉田礼。因此对照《说文》也有相关记载:
辰,震也,三月昜气动,雷电震民,农时也,物皆生。从乙匕,匕象芒达,ㄏ声。辰,房星,天时也[7]752。
无论从“辱”或“辰”之语义,都可见掌握大辰星在天空之位置,以及时进行相应农事工作之重要。由于春耕之后到秋收之前最重要之农事,为次数频繁的去除田草之工作,倘若稍有怠惰,则田草蔓延,抢走农作物应有之养分,以致有前功尽弃而农田荒芜之虞,因此勤于使用除草器去除封疆之杂草,正是保障农作物好收成之重要工作。
再从《说文》所载:“槈,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作从金。”[7]261可见“辱”原为去除田草时所借助的器具,且为槈、耨、鎒之初文,所加之偏旁,即用以区别薅器使用材料之差异。由此亦可推知去除田草为农家及重要之工作,因此会发展出不同材质之除草器具。由于田草滋生快速,去除田草之工作就必须接二连三反复进行,因此最是辛苦繁重,若农民无法持之以恒,则将功亏一篑,轻则造成农作欠收,重则甚至毫无收成。一旦松懈怠惰,相较于别人辛勤耕耘而获得仓廪丰实,遂相形见绌而感到后悔莫及,尤其在听到邻居之闲言闲语,更要深深引以为耻。
综合上述记载,“廉”与“耻”(“辱”)原来都与农事有关。农事中,尤其是历时较久而单调繁琐之去除田草工作,更是严格考验农民能否不好逸恶劳、见异思迁,而专心安于农耕的重要活动,更是耕地之开发利用能否切实有效之重要关键。倘若能按时完成例行之农事工作,加上老天帮忙,则能使家家仓廪实而人人衣食足。能具备如此安分守己、专心尽职之精神,一旦出仕为官,也将是多能之贤才,因此管仲要特别说“是以圣王敬畏戚农”。
(三)牧民者转化“四维”本义而为施政枢纽
管仲为彰显“四维”本义能具体呈现于社会生活中,于是政府必须合理安排各级行政人员,使其担负一定之职责以推动政策之施行。同时,为求“四维”之整饬能达到较佳效果,遂有刑赏之搭配使用以顺应民心,且以省刑为施政要务。盖因管仲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而施政必须务本之道理,故明言“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更明了“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为牧民者尤应避免之施政窘境,故而《牧民》紧接在“四维张则君令行”之后,则言“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并补充说明“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管子·牧民》)。
《牧民》虽不再说明何谓“两原”,不过,从《说苑》所载李克对魏文侯论述刑罚之源,乃“生于奸邪淫泆之行”,则可视为是对障蔽“两原”最好之说明:
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泆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说苑·反质》)
李克此段论述虽无法证实其是否受到《管子》之影响,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其实正好为《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正面立说,转从对立之层面论述奸邪淫泆、寡廉鲜耻等悖礼失节之行为,乃刑罚之起源的批注。由此可知牧民者务在去除导致奸邪淫泆之“文巧”本源,以免有害于农事、有伤于女工,以期人人皆能专心致力于各自之本务。由于仓廪实,源自顺应天时以尽地利之集体努力;衣食足,源于深耕易耨,力除田草以利秧苗欣欣向荣之生长──故而可由于心官发挥其功能,进行反思省悟,再推而至于为人处世应守之节度,成为建立个人节操、规划治国蓝图之根本,因此说“四维张则君令行”。一旦君令能顺利推行,则民富国强、社会安宁、人人自在佚乐之理想国度即可达成。
当然,要达到理想之国度,《牧民》始终不忘“上服度”之重要,因此以下两段正可凸显管仲辅佐齐桓公治国之要道:
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仲深知牧民者有德,乃国治民安之重要保障。由于有德,故能将施政重点优先放在照顾百姓之民生问题上,且透过严刑罚与信庆赏之不同方式,懂得凡事皆应以身作则、预作准备,使百姓能知礼节、明荣辱,遵守法度而远离邪恶,即使遭遇天灾,也因已预先防备,故不至于轻易陷入灾难之困境。牧民者能顺应民心以施政,不行险侥幸而以诚待民,故而百姓亦乐意亲近之。此外,还应懂得知人善任之重要:
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牧民者必须深明天时,慎选公正无私之人协助施政。上行下效之结果,则一切遵循天道而行,故能安于职守、动而有节,勤于开垦、不违农时,以致衣食丰足,进而彻悟奸邪、巧诈之非,尊荣、耻辱之差异,而懂得自我节制、不恣意放荡。
综上所述,可知原本与四时变化相对应而遵礼行仪之“礼”与“义”,转而成为国家订立各项制度之主客观依据。原本直接关系农事进行必须按部就班、按时专心致力工作,持取谷物必须有所节制之“廉”与“耻”,则成为判断个人节操高下之参照基准。尤其当“廉”与“耻”之引申义大行,且工商业逐渐兴起之后,原本“四维”有关农事之本义即隐晦不彰。从《墨经》之用字,即显见“廉”与“耻”之引申义在当时已经大为流行。《墨子·经上》之“廉,作非也”,《经说上》进而言“己惟为之,知其思耳也”①分别见于《墨子·经上》,孙诒让撰《墨子闲诂》(台北:华正书局,1987年),第284页;《经说上》,第304页。然《说文》无“思耳”合体之字,别本则分为两字。孙诒让即怀疑“廉”为“慊”,且疑“思耳”之合体字,或为《荀子·强国》“虽然,则有其諰矣”。中之“其諰”,又因杨倞注云:“諰,惧也。”故孙氏即以此之义为:慊者己虽或为非,而心常自恨,犹知惧也。。裘锡圭即认同高亨《墨子校诠》“耻之作‘思耳’合体,犹恊之作勰”之说法,主张“廉者所行或非,己虽过而为之,而心知其耻”,认为以合体之“思耳”为“耻”,乃文从字顺之卓识[9]426。此一现象,也与《郭店简》中从“心”之字特别多之现象一致,其中尤以《性自命出》为然。此说明在战国以后,已相当重视“心”对于一切作为之重要意义,故而强调廉者因为“心”发挥思辨之功能,于是会对自己之所做行为了然于心,当其所作为非,则会感到惭愧羞耻。时至荀子,更特重“心”具有“虚壹而静”之“大清明”能力[10]649,故能对任何事物详加辨别而“知类明统”,能明辨当为与不当为,懂得有所不为之重要。
结论
由于农事为民生之本,而农事最需要仰赖天时、地利与人事之多方配合,于是《牧民》在牧民者为明主之预设下,遂以“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二绳”,且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至于“四维”该节以下之解说,仅为举例说明之性质,并非意在周延定义“四维”之用:
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藉由点出生活中常见之小节,如不踰节、不自进、不蔽恶、不从枉一类容易遵行之行为,说明“四维”之应用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者,人人皆可力行而为之。由于实践“四维”无论对于国家、社会,抑或个人,都有无所不在之重要功能,因此在1945年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原本属于“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转而成为各级学校之共同校训: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希望藉由人人易懂之内容,养成良好的生活规范,从小就能及时培养良好的处世态度及高尚之道德情操。
综上所述,《牧民》所载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说法,乃管仲借用古代天文之“二绳”概念,并灵活运用渔猎社会之生活智慧,再转化出以“四维”达到“绳治”齐国之重要纲领。
[1]柳宗元.四维论.[M]//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冯道传·序[M]//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顾炎武.日知录·廉耻[M]//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4]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
[5]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
[6]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M].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台北:兰台书局,1972.
[8]林素英.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9]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
B226.1
A
1002-3828(2017)04-0005-09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01
2017-09-30
林素英,女,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三礼学思想、经学思想、先秦学术思想。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