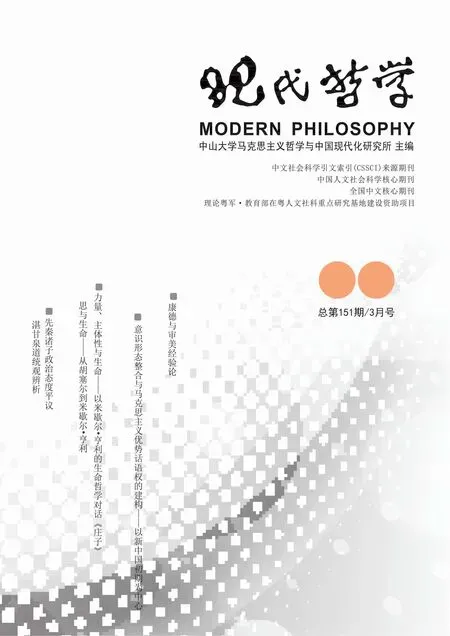力量、主体性与生命
——以米歇尔·亨利的生命哲学对话《庄子》
姜丹丹
力量、主体性与生命
——以米歇尔·亨利的生命哲学对话《庄子》
姜丹丹
本文从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的思想中提炼出力量、主体性与生命三组命题,由此出发梳理与剖析米歇尔·亨利在从当代文化批判与对传统现象学的反思扬弃的基础上倡导的“生命现象学”,并尝试在与中国古典《庄子》文本中的一些例子进行跨文化对话,思考在如何返归生命本身、在自身感触的基础上抵达对生命与世界的双重体认,调动生命内在的潜能、力量,以另一种主体性即生命主体性的范式,以身体性的、深沉的主体性悖论,抵抗主体的异化、重新培养关注自身生命与世界的当代伦理观。
米歇尔·亨利;《庄子》;生命;身体;力量;主体性;跨文化
法国当代哲学家、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1920-2002,另译为米歇尔·昂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识别出三个表述“力量、主体性与生命”的彼此联结的组合。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对传统意向性现象学的反思,提出在“彻底的临在性”(immanence radicale)的视野中关注生命本身力量的现象学思想,透现了二战后法国现象学在结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文化批判思想所进行的现象学内部超越思潮中的一种侧重物质性、临在性、身体性与生命实践相结合的倾向。这组命题如同三个环环相扣的思想密码,或许可以启发我们从亨利所界定的不同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的另一种主体性——可称之为“生命主体性”的角度,重新进入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经典文本《庄子》的思想世界,并通过关涉的生命、文化与自然等主题的反思,接通当代的跨文化对话与跨文化批判思潮。
一、力量:技术、个体与自然
米歇尔·亨利反思西方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教条主义的解读,提议从生命现象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卡尔·马克思的哲学著作,认为在其中实现了西方传统思想的真正的颠覆,尤其是引入一种全新的、作为实践(praxis)主体的人的概念,并将行为视作一种身体性的活动,从而用“主体的、个体的、鲜活的”活动来界定现实,以强调“劳动的主体力量”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根基所在。*亨利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过去遭到误解、被教条化或没有被真正理解。他特别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根本性哲学著作,即写于1842-1846年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亨利的相关著作Michel Henry, Marx: Tome 1: une philosophie de la réalité, Paris: Gallimard, 1991; Marx: Tome 2, Une philosophie de l'économie, Paris : Gallimard, 1999;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 De la subjectivité, Paris: PUF, 2003; Tome III,De l’art et du politique, Paris: PUF, 2004.
亨利揭示了马克思用两个方面的异质元素建构“生产力”:一方面是客观的力量, 如原材料与器具;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力量, 即主体实践活动本身,作为“身体主体性”的具体实现。亨利对此提出如下反思:在生产力量所规定的世界历史中,这两个方面的力量并不都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其内在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在这些力量中,客观的元素不断增长——在器具、机器与工厂部署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主观的元素,即鲜活生动的生命主体性的那一部分却不断减少。亨利深入反思这两方面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在经济层面和真实层面的后果。在经济层面,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文明走向废墟。资本,是价值与剩余价值,仅能通过劳动的主体力量来生产。当这种生动的力量逐渐消失、生产变得越来越客观时,价值与资本的生产也就随之消失。假设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不需要具体人介入的生产流水线,生产大量的“使用价值”,但最终没有生产出劳动的“真正的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绝对局限,资本主义的命运对应主体性在生产中的命运之上。亨利指出生产力量的演变历史,在存在或者说人类生存的结构中引发了深刻的撼动。在这段历史中,主体性与生产被联系在一起,随后逐渐分化。当人的生活与生产迭合,被物质技术层面的任务、劳动所占据,生命就不再体会到天然的节奏,而是丧失精神性,从而出现主体性凹陷中残存的人的命运的迷失及个体的悲剧。*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I, De l’art et du politique, Paris: PUF, 2004, p.38.借助推进马克思的生产力量这两个方面构成的理论,亨利进一步诉求鲜活生动、机体官能性的主体性,认为真正的生产价值是与这种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取消了生命主体性的部分,生产的价值就只停留在使用价值的层面,在质的层面上降低价值。亨利在这其中看到资本主义的绝对局限,认为主体性在生产中的命运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但又会引发个体的危机、主体性的凹陷,引发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心理危机及生命的困境。
亨利指出,在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唯科学主义里,不免会有否定人所特有的本质、同时把主体的生命缩减到一系列客观性的倾向。对此,他认为可以用生命现象学的光来映亮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即主体的劳动、主体生命的活动。亨利肯定马克思的“决定性的直觉”在于:唯有生命,也就是个体生命才拥有力量与效率;如果用抽象的整体取代行动的个体,就意味着消除一切有效率的能力,使生命进入毫无活力的状态,导致人类文明走向废墟。这是他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做出的对当代文化批判的思考。
面对当代社会处境中环境危机日剧的问题,亨利反思以个体劳动力改变地球面貌作为革命的观念。他反思主体试图改变地球面貌的“幻觉”,认为需要这种能力的幻觉直到海德格尔那里依然存在。由此出发,他指出当代技术的发展与过度使用对地球的日益加深的损害。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实践倾向亦与主体哲学的思维有关,即将人等同于高高在上的主体、作为事物的主宰,同时意味着将世界看作客体、客体绝对服从于作为主体的人、人发明出的技术的控制。当代文明的一些困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受到工业、技术发展的损害的困境,在他看来皆是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造成的。
亨利肯定马克思所强调的主体力量、主体实践活动,同时在更广义的哲学史范畴里批判理性知识与技术霸权对生命的遮蔽性,以及在改造自然方面的暴力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早在科技萌芽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描述了这种危险性,《庄子》的一些寓言性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从生命与劳动的视角反思技术的弊端的思想资源。比如《庄子·外篇·天地》汉阴丈人*《庄子·外篇·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的例子:菜园里的老翁抱瓮取水浇菜,子贡问他为何不用一种名为“槔”的机械,一天可以浇灌百畦,用力很少,见效却大;老翁反驳道,他不是不知道提水机械的功能,只是不肯用它,因为“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老翁不注重机械带来的效益、有用性与效率,却重视在朴拙的身体劳动方式中维护内心的“纯白”,注重体验身体劳动的生命感觉,不愿以物之“有用”忽略心之“无用”。因而,庄子与其说反对技术本身,不如说是反对仅仅注重技术或者说技术代替身体主体性的危险倾向。
亨利指出,当代技术生存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是逐渐成为“对愿望的愿望”*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 De la subjectivité, Paris: PUF, 2003.的历史,即唯一愿望是主体通过技术的进步控制世界的欲望。要走出困境,就要去除“主宰性的主体性”,即希望成为自然主人,用理性与技术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在《庄子·外篇·在宥》云将东游时与鸿蒙的一段对话*《庄子·外篇·在宥》:“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意!治人之过也!’云将曰:‘然则吾奈何?’鸿蒙曰:‘意!毒哉!仙仙乎归矣!’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鸿蒙曰:‘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辞而行。”中,庄子也揭示今人称之为的“人类中心主义”控制性的主体愿望在扰乱物性、破坏自然方面的深重危害。在云将求教“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如何治理时,智者鸿蒙答曰:“扰乱自然的常道,违逆万物的实情,自然之化则不能完成,惊散兽群,鸟皆夜鸣,危害及于草木,祸患及于昆虫。这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云将请教治理的办法,鸿蒙指出他“中毒太深”,这里讲的“中毒”指的是在主体范式下对世界的控制愿望,是治理者通过过于人为的方式去改造自然的思维模式。鸿蒙所提示的解决途径是要“修养本心”,忘却形体,摈弃聪明,和自然元气融为一体。因为滥用心智的“知”与“治”会离失本根,逐步造成世界的“六气不调”;而回归合乎本根的无为之境,意味着返归万事万物原本自生自化的原初境态。这可谓从自我修养的方面提倡基于生命平衡伦理的环境伦理之道。
亨利反思当“技术的世界体现一种入侵性的客观性”会“取代主体的真实的劳动”,因而提倡一种回归生命本身的现象学,探求具体的主体生命的广大领域,这样的领域才能界定人类的真实存在。然而,这种存在被古典哲学与现象学缩减为人与世界的关系,缩减为主体客体认知关系的简单化。生命的内在本质完全超脱出这种秩序的关系。生命现象学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本身之上投射一束新光,当代世界的荒芜在于贬低甚至损害人类的真正生命以及生命本身的要求,用抽象化的价值再现、观念化的普遍性,替代具体的生命、生活,取消主体性的生产也就会贬值。*Michel Henry, Entretiens, Cabris: Sulliver, 2005, p.96.
《庄子》在讨论到技术活动的寓言中,提倡“技进乎道”的艺术性追求和心灵超越,提供了与在生产活动中丧失主体生命价值相反的另一种模式。比如“梓庆削木”*《庄子·外篇·达生》:“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的例子,做鐻的工匠在劳作前要“斋戒”七天,在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情况下,凝神专注,进入山林,观察树木之质性,选择好木材,鐻的形象了然于胸才开始制作。尽管亨利认为亚里斯多德关于生产的“四动因说”仅仅从外部因素来规定生产,笔者却认为在此体现的第四“动因”可以充分说明匠人在生产中的必要性。《庄子·外篇·达生》里,工匠尤其把技艺与内心修养结合起来,消除自我杂念,体现达到忘境、平淡境界的主体性的创造。亨利指出依据古希腊的词源,“技术”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主体的技能,即关涉到身体主体的投射与延续,而祛除身体性,制造丧失个性的特征,就没有真正创造价值,而是仅仅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物品、商品。在“梓庆削木”的例子中,抵达“心斋”的主体与作为整体的世界或道融为一体,“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是与”,所以生产的价值带上合乎自然的生命主体的标记,其生产的结果是转化为具有“出神入化”的创造性力量(“见者惊犹鬼神”)。
二、生命主体性:身体与精神
在现象学思想的历史脉络中,亨利反思现象学还原中的“意向性”原则,并认为这种原则以先验主体性为根据,实际上构成一种外在性的指向模式。亨利认为无论是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都限于我思的传统,忽视“内在性”,其主体性都是向外的主体性。首先,亨利反思外在性,以内在性对立于超越性。其次,他认为主体性本身的现象化无法构成还原的真正基础,而时间性构成意识引向了一种主体“出窍”(Ek-stase,另译为“绽出”)的状态,等于将主体性外在化,反过来成为意向性的对象,让主体自身现象化。在这种现象学逻辑中,原本规定为先验构成基础的主体反过来成为被构成的对象,因而无法真正成为“还原”的基础。这就会产生一个关键的矛盾,即只能通过对象的显现来说明主体本身的显现。
从“世界”、“存有”的现象学走向生命现象学转向的语境中,“我是谁”的问题在亨利的哲学视野里就翻转为“我如何显现”、“我如何给出”的提问;从生命为依据,亨利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命的自我彰显,即主体的内在性如何向自身显现,在这种问题意识里,他把“彻底的临在性”(immanence radicale)的确立与回归作为途径,需要以非意向性的方式建立对自身直接的、无差异的、零距离的“真正的自身意识”,而不同于在存在一元论的视角下以自我为意识对象的“自我意识”。这种彻底临在性的自身意识是对自身生命的揭示、体证,这种反身性的模式就是亨利所提出的“自我感触”(auto-affection)(不同于康德立于感性基础上将自身设定、对象化的“内在感觉”)。他所思考的“自我感知”的模式有一个关键的生命现象学的支点,即立足在身体主体性的感触基础上,以身体的模式建立对自身的感触。
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的建构与其进行文化批判的思想相互交织。在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虚假的主体以及现代主体性的膨胀对自然的危害的基础上,亨利在身处后现代思想消解主体性的语境中试图重新肯定主体性的必要性与价值。他所重构的主体性具有实验性的意义:“在彻底的内在性中的原初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属于一种回归原初、本真的范畴,与关联进步、绝对理性的主体性范畴相对立;主体性不是封闭在思维、意识层面的主体性,而是投向行动的、机体的主体性,即以身体为主体、身体作为现象显现的场所,不同于传统以“意识”为基础的主体性概念。而注重身体的主体性,也就意味着反对将身体缩减为物体、认知的对象,承认身体的主动性,承认我们认识事物都是从自身身体的角度出发。
在这个层面上,米亨利借用19世纪法国哲学家曼·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对身体经验的分析。比朗在1805年出版的《思维分解报告》(Mémoire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里分析身体活动现象中“努力”的问题,提出“我能”而非“我思”的模式。他以意志与情感为基础,认为“我思”不是“我思想”,而是“我能够”、“我感故我在”,身体伴随着感觉运动的完成与努力的感受。亨利进而推出“我感到我思故我在”,并特别强调“我能是机体性身体的延展,是纯粹的主体性”,而“我能”与世界的遭遇是从身体的内部发生的,世界与“真正的身体性”发生的关系带有情感性的“自身感触”。*Michel Henry, Entretiens, Cabris: Sulliver, 2005, pp.114-115.在《身体现象学与哲学》一书中,亨利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诠释:“身体的本体论属于本体论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先验的内在经验才可能完成,换言之,属于主体性的领域。身体的现象学存在,换言之,身体的原初、实在且绝对的存在,正是一种主体的存在。同时身体的绝对内在性被肯定了。”*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Paris: PUF, 2011, p.73.亨利分辨出三种身体观:“客观的身体”,如客观事物一般存在于外部空间的身体;“机体的身体”,从生物学角度的人作为动物而拥有的身体;“主体的身体”构成我们的主体性,“真正的主体性”是不可见的,只能通过自我感触、自感的模式去体认,“我就是我的身体”*Michel Henry,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Paris: PUF, 2011, pp.179-182.。
通过这个视角,亨利汇通梅洛·庞蒂引入“身体-主体”的图式作为知觉活动与世界在场的联结点的身体观,身体不是纯粹物理性的身体,也不是意识的身体,而是身心交融的身体。但亨利反思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中的主体性,认为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里虽然有一个主体化的身体,但依然在胡塞尔的影响下,还是与“意向性”相等同的主体性,意味着身体成为意向性,身体投入世界,不断地站起来走向世界。他反驳梅洛·庞帝的观点“身体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载体”(le corps est le véhicule de l’être au monde),质疑的就是身体作为媒介的工具性、载体的观念。他认为身体直接介入世界,在付出身体运动时无需诉诸任何中介。 而且,亨利认为关键在于为身体——而不再是知性——赋予力量,赋予让我们朝向世界敞开的能力,主要的问题在于了解身体的力量如何呈现出来,在身体将世界显现出来之前。
在亨利看来,首先,在行为中直观认识并不起作用,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实践活动中,意识层面的直观是被悬置的。比如当我们开车时,我们并不从外部看我们开车的行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会专注地自如驾驶。在没有感性或知行的任何再现介入的条件下,我们不会在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把行为作为对象来审视和思考。其次,我们不能仅仅说我们可以行动而不需要对行为的直观,实际上“行为必然与任何直观相异,行为只有在不是直观时才成为可能。行为既不是对其本身的直觉,也不是对任何事物的直觉。当行为成为直观,行为会转化为目光、观看、静观,但都不再是具体的行动”。当直观与行动同时发生时,这个同时性也就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外在性,意味着一种直观可以在行动之外发生。再次,亨利认为还要把这种彻底排斥在行动之外的直观问题思考到底,即在彻底的临在性(immanence radicale)中思考。马克思所思考的实践的主体性,与费尔巴哈的客观直觉完全不同,在实践的概念后面呈现“主体性概念的一种绝对崭新的意义,也就是在彻底的临在性中的原初的主体性”*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I, De l’art et du politique, Paris: PUF, 2004.。
在《庄子》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强调实践中的身体性的例子。比如“吕梁丈夫游水”(《庄子·外篇·达生》)、“津人操舟”(《庄子·外篇·达生》)、“列御寇为伯昏无人施射” (《庄子·外篇·田子方》)等例子, 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一种忘记主体内部的情绪以及外物的干扰,却又守住安适沉稳的内在主体性。由于习练而技术纯熟,达到顺应物性自然,从而让身体本身自如自在地行为,在技术活动(游水、操舟、射箭)充满难度或极限挑战的处境中(“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觞深之渊”、“履危石,临百仞之渊”)都能达到自由行动的超脱境界。这种身体行动达到自由的境界,通过“忘”的途径在“吾忘我”的基础上达到与外物相通而抵达内外的平衡。如果过于看重外物的价值则有可能造成“内拙”而影响身体行动的发挥,或者甚至造成自身生命的异化。只有在不过度加以人为意识控制的“无为”之中,才能保留深沉平淡的主体性,从而自如自由地进入与事物的内在性,与周遭环境的相沟通、相适应的生命存在方式。
亨利指出,在反思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主体性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主体性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主体性具有实验性的意义,即“在彻底的内在性中的原初的主体性”,提倡回归原初,回归本真的范畴。它不是封闭在思维、意识层面的主体性,而是投向行动的、机体的主体性,却又以悖论的方式将我们带回到自身最内在的部分,即“彻底临在性”的深度空间。*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 De la subjectivité, Paris: PUF, 2003,pp.24-25.进而,亨利指出这与西方哲学的习惯不相符合。换言之,在这种视野里,他“认为思维把我们投给世界,投给外在性的主导,然而,行动与这个世界不同,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自身的最内在的部分。但是,当行动突然召唤我们,也就是带我们潜入到我们自身最深邃的部分,潜入绝对主体性的幽幽深夜之中,直到我们身体的各种力量沉睡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与这些力量相汇合,我们驱动这些力量——突然之间,机体的主体性的各种潜能都实现, 根本的我能够展现,构成我们的存在,在那里,我们在原初的整体里与自身融合为一体,没有了超验,也没有了世界”*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 De la subjectivité, Paris: PUF, 2003, pp.24-25.。在亨利看来,行动并不是仅仅把我们带向外界,而是在身体行为的过程中,用意识的搁置让人与自身的力量的“潜能”相汇合,甚至在一些时刻可以有进入或者重新返归原初的整体的能力。这里体现的就是生命内在的能量如何在身体的范式(身心不分的整体性范式)中返归全部潜能汇合并一同作用的状态。这有可能把人引向返归世界的原初浑然一体的境界,不是通过认识自我、再现或改造世界的方式,而是返归行动、身体机能的主体性,并带向深层的主体性,重新进入与世界的内在性相沟通的状态。
在这段近乎神秘诗意的深沉主体性的描述中,亨利的思考体现了逻辑上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接近《庄子·内篇·应帝王》“唯道集虚”的“心斋”状态的描述。在壶子向列子和季咸展示逐渐进入“大虚静”状态的例子,壶子从形如槁木、湿灰到呈现在身体中呈现天地生机,“虚若委蛇”,却暗含如深渊般的生机。他这样说明这种内功:“吾乡示之乙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这种经验好比亨利所界定的体证自身、体证世界的主体性的双重呈现模式,但指的是一种具体又“深沉的主体性”,即生命、肉身。这促使本来自以为是的季咸在看不懂之后,“三年不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快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即走向返归原初、朴素状态的自身修炼。《庄子·在宥》描述“君子”的状态:“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在此,可以说,庄子描述的道家式“君子”的内在精神肖像体现出一种符合“深沉的主体性”的经验描述,这种经验可谓是在忘却、剥离意识主体的基础上抵达的,等同于《庄子》所提倡的“不为物役”、“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主体性,呈现出深植于主体生命内部的不可见的活力源泉。
同时,我们也要提到,亨利在身体、显现与主体性方面的现象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的庄子研究。尤其是毕来德认为《庄子》提出的主体性典范落在身体的自我知觉的范式上,体现出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静态特征的反思,而《庄子》文本关涉的身体经验提示作为在身体行动中知觉与意识的主体,身体作为现象与意义显现的场所透现出身体体证的权力。因而,毕来德将庄子的“坐忘”经验里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诠释为“随顺肢体,停止视听,失去队自己与对事物的意识”,将《应帝王》列子意识到“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的返归素朴生活的选择诠释为返归于自身,“回到身体”。*Jean-François Billeter, 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Paris: Allia, 2004, pp.120-121.中译本参见[瑞士]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在讨论《庄子·在宥》北成门与黄帝对谈听音乐的经验,即“听之以气”的身体经验时,毕来德也指出这种返归的主体性退回到“深沉的接受性”*同上,第127页。,即以气化归虚的身体的被动性方式接纳与深度感触。亨利反驳比朗以主动性、努力的能动性为依据的主体性,强调被动性的承受作为“自身感触”的基础,让生命感受浸透自身,也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即在纯粹地感触性中的生命呈现,体证到自身生命的本源,首先促成一种身体对自身的原初显现,继而从被动性的自身感触逆转为对于事物与世界的双重层面的深度感触与体认。
亨利提出,生命现象学首要的职能正是“呈现”的双重性,揭示生命中不可见的现象,植根在主体的身体中,“我能”的力量从内部抵达世界,超验在内在性中找到根基。《庄子》“逍遥游”的例子似可对应这种身体的力量的自身呈现与转化。比如,在“游”的行为中,“忘我虚己”,祛除外在化、封闭在自我意识中的主观性,却保存完整的内在的主体性,揭示在忘我的超越对待的境界中的内在力量,从而在虚静无待的状态中,在重归原初的、深沉的主体性的层面上,与天地相应合,摈弃外在的限制,“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获得身体自由运动的转化力,实现主体内在的超越,从而达到“天下治矣”的境界(“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也是《庄子》所颂扬的无为却胜物的“至人”的境界:“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内篇·应帝王》)以“心斋”的方式实现“自身感触”,又同时体证、鉴照外物,而并不因此受到损伤和异化。
在《庄子》文本中,对“真人”、“独人”的刻画都有体现主体性不为外物所左右的“无己”的生命状态,比如“夫有土者,有大物业。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 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外篇·在宥》)。个体特立独行, 不宥于外物的羁绊,唯有如此才能顺应自如地体验天地万物。庄子所描述的“虚若委蛇”状态(《庄子·内篇·应帝王》),即与权威如老虎般暴戾的太子相处之道,虚己以待,消除对立,则祸患不来,可以说,这是避免洋溢在外的主观性而进入“深邃主体性空间”的策略,体证自身,并达到与外界的恬淡相处。“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外篇·刻意》)在平淡之中达到的“深沉的主体性”,即是形与神不受外物侵袭的呈现“彻底的临在性”的完备境地。
在《庄子》文本中也可找到一些反例,即迷失或丧失“深沉主体性”的人们。比如《庄子·杂篇·徐无鬼》从欲望增加对心性的损害的角度描述这种丧失主体性的危险:“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这也正是亨利所揭示出的当代人在工作、消费,物质欲望所带来的抽象化替代中丧失精神性、失落生命价值的生存困境。在《庄子·杂篇·庚桑楚》里,在俗务中迷失自身而到晚年深为困惑的南荣趎请教老子:“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深。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握身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在这段对话里,在《庄子》中作为哲学人物出现的“老子”这样形容南荣趎所呈现的生命困境:“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老子进一步把南荣趎困惑的根源归结为外物所累(“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导致六神无主、流浪在外、无知而迷茫的精神状态。惟有通过洗涤自身,剥离为外物的复杂和欲望的过度所牵绊和堵塞的主体性,才有可能抵达平淡而澄明的“自身感触”之境。这意味着不是封闭在自我的内部,而是返归“深层主体性”,从而获得在“虚”与万物之间自由穿梭、体证生命与世界的能力。
三、返归生命本身:文化与生命的力量
亨利剖析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些内在矛盾,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回到生命本身”的原则,这种返归并不是素朴幼稚的,而是一种现象学根本立场的颠覆逆转。他指出当代文化的危机首先在于“遗忘生命”,提倡把个体生命放在哲学关怀的核心位置,将现象学建立在个体生命的力量的基础之上,从“世界”的现象学走向生命的现象学。亨利认为生命的本质应在于自我转化与自我实现。但是,当代文明的野蛮性却将生命的本质扭曲,造成技术的盲目演进,这种通常被认为是积极的演进却贬低个体生命的意义。
亨利写道:“科学信念进而科学迷信导致全部其它价值的瓦解,以至于质疑我们的生存本身,最终导致生命本身受到损害,正是它的全部价值(不仅是美学,而且还有伦理和神圣的东西)以及伴随它们的还有每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都在摇摇欲坠。”*Michel Henry, La Barbarie, Paris: PUF, 1987, pp.8-9.从伽利略时代以来,文化让位于野蛮,在这种抽象性的野蛮中,“生命的自我否定”构成关键性的事件,伴随着精神性与文化价值的衰落。与此相反,亨利提倡“原初能量的文化”,提倡关怀内在的、先验的生命,这不同于先验意识,指的是具体的、实际的、个体、在融合身心的自身感触模式上建立的生命。
对《庄子》而言,培养个体的生命的独特性与完整性、提升生命价值与境界是核心的向度。《庄子·外篇·天地》颂扬精神与身体保全主体性的人:“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是“至德之人”的修为,亦同于“浑沌氏”之术。“全德之人,浑沌氏之术者也,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在汉阴丈人例子的结尾,子贡返回鲁国告诉孔子他的见闻,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浑沌氏之术”指的是不加分化、无有差别,从而不会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分别与变化之中、“独立而不改”的复朴生命。在《庄子·内篇·应帝王》里,“浑沌”的例子,倏忽正代表世间的速度、机巧、认知模式,为“不识不知”的浑沌凿七窍而导致浑沌身亡*《庄子·内篇·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正代表认知对朴素内在的伤害。讲求浑沌氏之术,意味着不让内心淹没在外物之中,不为外界的知识与处世的技术打通五窍,保持自身天然的完整性,也保持着“深沉的主体性”的生命生机。因而,《庄子》所探求的生命价值首先在于内在本真完备的处在自然状态的保全。
亨利把“体证到自身这一独特属性”称之为生命的知识,相对于科学知识,这是“一种最深刻形式的知识”,进而言之,“鲜活的生命在其自身中就是这一原始的知识”。*Michel Henry, La Barbarie, Paris: PUF, 1987, p.16.《庄子·外篇·胠箧》批判科技理性意义上的“知”过度追求所导致的混乱后果:“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世人用各种机械工具捕捉动物,损害自然生态的平衡,并将知用于争论,导致社会的混乱。相对过于好知的欲求,《庄子》讲求“恬淡无为”“不知之知”,正是体证自身鲜活生命和维系与万物并存、共生的方式。
《庄子·杂篇·庚桑楚》在论述“灵台”一说时,讲到修身养性的三个步骤,即“知止乎其所不能知也”,“备物以将形, 藏不虞以生心, 敬重以达彼”,内外兼养,心存诚敬,以通达相异的他者,体现出与儒家理想相沟通的伦理性维度,意味着以返归自身的感触模式去感触和抵达万物与世界。这种生命的知识需要生命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如果杂念、欲望入侵内心则必有损失,而抵抗入侵性的外物喧嚣,就是保持内在“灵台”完备清静、整全的必要方式。体道之心,本应是虚静无所持守,但又是有所持守,持守本然之行或道,也就是在亨利意义上的深沉的主体性或生命的“彻底临在性”的保持。
《庄子》同样注重生命的自我转化之道,以“无待”之心、无己-吾丧我为前提,将真正的深层主体性从功名利禄、是非善恶及形骸的限制里解脱出来,从而实现内在的超越和内在的自我转变,达到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保留主体性,不为外物所化,“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庄子·外篇·刻意》)。《庄子》继而指出:“虚无恬淡,乃合天德。”“以天合天”是将主体生命的文化境界放在宇宙与自然、道与天的范畴上衡量,将生命放置在自然的秩序之中,以是否合乎天作为最高的标准。《庄子》把维护生命自然本性、不求以人为改变自然的人称为“天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庄子·杂篇·天下》),或“真人”,“其一与天徒,其不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也谓真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内篇·杂篇·大宗师》),“以天待之,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也谓真人”(《庄子·杂篇·徐无鬼》)。《庄子》提供的反例是“齿缺”有一番对话,问此人是否“可配天乎”,是否要邀请他。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且乘人而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如果以自身为本,以外物为异,讲求巧智与速度、效率,则在应对繁杂的外物的过程中,内心也会被对外物的探求所束缚,被异化的这个人好比是在技术与消费时代的现代人的一幅精神肖像画。“未始有恒”,不能保留恒久的准则,丧失内在的、深层的主体性,失去合乎自然的“天德”,因而也就丧失在“彻底的临在性”中实现临在的超越的可能性。
《庄子·外篇·在宥》还以外形消亡之后的骷髅的主体性的保存,借言死后之乐,来形容摆脱了权威的压迫、超越生命有限性的超脱境界:“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从容自得,与天地共长久。这是“得道之人”广成子向困惑的黄帝所讲述他所体验的“至道”境界:“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而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夜,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夜。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这里呈现的是返归深沉主体性的一种修养之道,不为外物动摇心神,祛除智巧的扰乱,最终合乎天道,与自然合为一体,守持纯一的阴阳和谐的境地。“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这就是《庄子》将自身修养与宇宙论结合找到的生命与天地的自然常理一致化的途径,保存深层次的主体性并接纳自然性,与自然万物相应和,可谓在生命修养的双重意义上的修“道”。
亨利指出:“生命的知识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源头处,它让生命变得可能,与生命迭合,也是生命的本质。”*Michel Henry, Entretiens, Cabris : Sulliver, 2005, p.107.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生命关怀的修养功夫是一种贴近生命本质的“生命的知识”,在探求不以技术理性损害心灵,强调主体生命力量的价值,保存与维持主体性的内在性,追求生命自身转化的层面上,亨利对当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可以在《庄子》找到深层的思想回应,这种回应可以启发从自我关怀到环境保护的当代伦理重建的可能性。
在对生命的被动性、接受性的认识上,亨利的观念最终趋向于基督教神学的生命“给予”:“绝对生命的内在进程,是圣言在其上的绝对发生。”“在现象学的层面上,生命的被动性的赋予,使得生命的问题与上帝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经历生命,好比接受某种东西,也就意味着必然要对自身有无限的尊重。”*Ibid., p.118.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视野里,生命要顺应一种不可知的神圣力量的给予,生命因此具有宗教意义的神圣性;这种神圣的向度在《庄子》却是属于“天”的自然范畴,生命要顺应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给予,呈现出一种被动性的自然,而自我修养功夫的极致就在于通过“虚己”、“忘我”的途径,在返归深层的主体性中合乎天道,以体证自身临在的“自然”的方式应合“天道”的自然过程,呈现“以天合天”的转化力与创造力。这一点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在对《庄子》文本的重新诠释中探讨生命的主题,具有与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不同的悖论性,意味着《庄子》在无为中求生命的转化,在虚静中抵达临在的超越,这正是看似消极的内在生命力量的一种积极的“呈现”。《庄子》的这种思想资源呈现出与在经历后现代思潮解构之后重新建立的法国当代生命哲学如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与文化批判的对话可能性,反过来这也启发当代人思考如何在物的逻辑、在无余的世界里避免主体的异化,而且在生命修养的跨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如何重新培养“不为物役”,去除“机心”的阻隔,在世界之中与物恬然相处,从而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滋养世界与自身生命的可持续性的自然、健康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 任 之)
B565.59
A
1000-7660(2017)02-0053-09
姜丹丹,(上海 200240)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暨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兼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通信研究员、科研项目主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子课题“法国生命哲学的新发展”(14ZDB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的当代诠释与中法跨文化对话”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