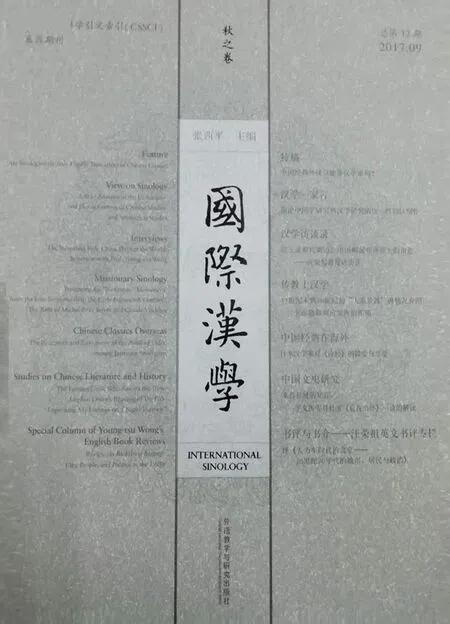简论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的统一性和区别性
□
一、国外中国研究历史上的概念沿革
在西方语言的传统中,“Sinology”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西方最早设立关于汉学研究的教席是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1814年12月11日正式设立了一个“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①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1页。(Une chaire de langues et de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意义。”②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但此时在法文中并未出现“Sinologie”,在英文中更没有“Sinology”。在法文中第一次出现“Sinologie”这个词是一个“叫L.A.M.Bourgeat的人1814年在Mercure etranger(《外星》)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L’histoire de la sinologie’(汉学史)的文章中,③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d., Tre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 V.15.Paris: Gallimard, 1992, p.540,转引自尹文娟《〈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但这一词直到1878年才正式进入法语词典中”。④参阅尹文娟《〈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在此感谢尹文娟送我此文。英语中的Sinology显然是来自法语,有人认为“它进入英语词典的时间是1882年”。⑤参阅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15.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538.尹文娟《〈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欧洲著名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认为用“ologies”这样的词根来表示学科或研究领域是19世纪以后的事,在英语里“Sinology”是很新的词,“第一次见于1838年,不久,再次见于1857年,……把‘汉学’解释为‘研究中国的事物’已是晚近之事,直到1882年才开始。因此可以说,直到1860—1880年间,希腊文和拉丁文杂交的‘汉学’一词才转化为通常意义上的词汇。这个时期,中国研究和中国本身才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学术上一个专门的课题”。⑥傅海波(Herbert Franke)著,胡志宏译:《欧洲汉学史简评》,载《国际汉学》第7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81页。但也有学者认为,有时人们也把它写成“Sinologue”,实际上欧洲的汉学家们现在有时还这样写。⑦David B.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Eisenbrauns, 2001, p.xi.在来华传教士所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一卷中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称为“Chinese Scholar”,1838年第一次出现了“Sinologue”,在1849年18卷8月号上刊登西方第一个汉学书目《关于中国的著述》(List of Works upon China)中也出现了这个词,尹文娟认为:Sinologue这个词是在1849年《中国丛报》发表汉学书目到1851年《中国丛报》停刊期间逐步固定下来的。参阅尹文娟《〈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
傅海波所说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杂交的“Sinology”是说词根“Sin”是希腊文,词缀“ology”是拉丁文,学科的意思。日本学者认为“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称chin)而来的。这一读音中否认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in、Thin的发音,更进一步形成了Sinae、Thinae的发音”。①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尽管对“Sinology”词源学上出现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它的内涵认识大体是一致的。Sinology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语言、文献、历史的研究。尽管,在西方早期汉学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参与其中,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汉学著作,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中国士大夫们帮其润色,乃至与其合作而成的。但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后,Sinology指的是非中国人参与的西方人自己的一种关于中国语言、文献、历史的学问。至于在当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开始在西方的汉学系中任教、著书,那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个现象并不能改变Sinology的基本含义。②参阅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载《国际汉学》第2期(辑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将英文中“Chinese Studies”翻译成“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起源何时,谁第一个使用这个汉语概念,尚待研究。但要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从梳理美国汉学的历史入手。
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源于传教士来华,1830年2月25日,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和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到达广州,揭开了中美关系史和美国汉学史。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前后发行了20年,它不仅成为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成为当时欧美汉学界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美国汉学的摇篮。1848年《中国丛报》后来的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出版了他的代表性汉学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1848),1876 年卫三畏返回美国后在耶鲁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汉学系。这个时期的美国汉学虽然在对中国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上与18世纪前来华耶稣会士有很大不同,但仍在传统汉学研究范围之内。
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学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简称IPR)的成立。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字、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注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③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期)(辑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6—7页。实际上,此时从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汉学家移居到美国生活,他们带去了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这说明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和欧洲的汉学研究之间并不是一个截然分明、毫无联系的两种学术传统,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结的,而又逐步分化的过程。参阅柯马丁(Martin Kern):《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载张西平、李雪涛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这里,我们看到不同于传统汉学研究的“中国学”的产生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西方现代中国学诞生于美国;
第二,美国现代中国学起始于太平洋学会的成立,完成于1941年远东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④1956年该学会更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出版《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三,美国现代中国学产生于太平洋战争,应美国的国家需要而生,正像当年西方传统汉学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而诞生一样,美国的现代中国学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研究”。⑤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第四,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和传统汉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区别是打破了传统汉学研究局限于文献、语言研究的狭小范围,把传统的汉学研究置于地区研究的框架之下,“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①《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期(辑刊),第9页。正如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所说:“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即地区研究—作者注)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了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1936年以来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②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前言》,第3页;参阅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二、中国学术界对域外中国研究的应对
在汉语的传统中“汉学”指的是与注重义理的宋代理学相区别的发扬汉代经学中重训诂、考据、版本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刘师培写有《近代汉学变迁论》,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述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变迁,说明了“汉学”兴起的原因、过程和主要人物基本的学术主张。长期以来,“宋汉轮回”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宋学”重义理,“汉学”重考据③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其实“宋学”和“汉学”是一对不可分的概念,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近来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和清乾嘉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之间有种相互联系的“内在的理路”,这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朱熹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是同时存在的,但后来陆王学派不再重视“道问学”,而把“尊德性”发展到了极致。即便这样,在双方的论战中,都需要回到原典,如王阳明为其良知说找到根据,就要重订《大学古本》。这样,知识论的传统并未断绝,清代的学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一方面全面整理儒家典籍,另一方面做思想还原,找出儒家观念的原始意义。因此,表面看宋明理学和清乾嘉学派似乎没有关联,“其实若从思想史的综合观点来看,清学正是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派的争执不决的情况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即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但是这一发展的结果,不仅儒家的智识主义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因而从潜流转变为主流,并且传统的朱陆之争也随之而起了一种根本的变化”。④参阅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10页。
这样以“尊德性”为其特征的“宋学”和以“道问学”为其特征的“汉学”实际上有着内在理论的联系。思想史意义上的“宋学”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以往理解的那样僵硬。同时,也揭示出在汉语里原本的“汉学”概念有两层含义:在狭义上指的是“清代以训诂、考据为其学术追求的乾嘉学派”,⑤“汉学”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蕃学”相对,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夏,当时在中央设有“蕃学”和“汉学”,“这里的‘汉学’是指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称谓。”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在广义上指的是整个中国学术。⑥《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第3页。正如柳存仁先生所说:“汉学要包括义理,就是哲学史、思想史这些学问,是顺理成章的事。”⑦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汉学”有了这两层含义,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台湾出版的《汉学研究》和《汉学研究通讯》,以及中国大陆出版的《清华汉学》都是从广义上来理解“汉学”这个概念的。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何时将“Sinology”称为“汉学”?《汉语大词典》在解释时说:“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记日本国人语》:‘日本之讲汉学,自伊藤仁斋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东来传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携并进,至19世纪,汉学(Sinology)于焉确立。’”①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中卷,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3404页。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如何称谓日本对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的研究的学问;二是谁首先将Sinology转换成汉语的“汉学”概念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江户时期(1603—1867)是日本的传统汉学时期,日本近代文化产生以后,传统的汉学就已经终结,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开始形成。②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实际上不仅是在日本,在整个东亚对“汉学”的理解与解释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含义,
在接触中华文明较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汉学”在许多场合是儒学的代名词,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在这些国家,“汉学”与其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长盛不衰,不仅是某些国家(如日本、越南等)某一历史阶段学术研究的全部,也是某一历史阶段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学说。③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页。
第一个将“Sinology”翻译成“汉学”的可能是王韬,王韬在他的《法国儒莲传》一书中将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翻译成《汉学指南》。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近来研究者指出:“该书的中文名称应该是《汉文指南》,译成‘汉学’显然是王韬之误。不过从王韬所译的‘汉学’一词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法国的‘Sinology’所代表的欧洲的中国研究。”⑤《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第11页。接着应是朱滋萃,在他所翻译的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中将“Sinology”翻译为汉学,他在书中说:
以上概观寻道而来的欧西底中国研究,顺次进步;尤其以耶稣会教士作中心的在国中本地的研究底进展,以及建于这基础上的欧洲本国的学者探究的勃兴,此后随时表现光荣的成绩。在这潮流里,各以天赋的才能,为欧洲汉学吐气。⑥石田干之助著,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平:北平中法大学,1934年,第240页。
而后是1943年出版的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一书,也将“Sinology”翻译成“汉学”。此书是国人所写的第一本西方汉学史,虽然书中多引用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一书,但也有自己的贡献。⑦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用“汉学”来表达“Sinology”时, “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⑧余英时:《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载《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第190页。余英时先生认为“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⑨同上。所以,在笔者看来,这里的“汉学”既不是指乾嘉考据学派,也不是指一族,即汉族,或一代,即汉代之学问,而只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之学问。将西方人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或许是从1942年唐敬杲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一文开始。⑩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或许在今后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修订。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国外的中国研究成果。1981年孙越生先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研究展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95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和1996年阎纯德先生主编的《汉学研究》先后创刊。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看待国外的中国研究上存在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用“汉学”称谓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种意见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他说:
“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些学者主张把“Sinology”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汉学”的“汉”是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Sinology的语根Sino-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这是希望读者注意的。①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序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这里,李学勤先生讲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称为“汉学”,并对“汉”字做了明确的限定。任继愈先生也持这种观点。②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国际汉学》第8期(辑刊),第1—8页。为了与国内的“国学研究”相区别,用“国际汉学”“海外汉学”来加以限定,阎纯德先生认为“最好把‘国际汉学’‘海外汉学’统称为‘汉学’,‘国内汉学’称谓‘国学’”。③阎纯德:《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孙越生先生,他所主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就是这个理解的产物。④他在《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前言中明确指出,应将“Sinology”的翻译从“汉学”改为“中国学”,见《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朱政惠认为“传统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研究统称为中国学”⑤朱政惠:《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思考》,载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何培忠对这样的认识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
由于如今国外“中国学”不仅有关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环境等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也有传统汉学高度重视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而使用“中国学”这一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人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的中国有更好的理解。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我国学术界也应跟上时代的变化,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中国学”。⑥《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第12页。第三种意见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他说:
我以为关于对“Sinology”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事件的区分概念,例如把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展开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或许会更接近于他们的研究特征的实际。至于说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它们或许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例如当代政治、当代经济等等),而不是我们所十分注目的经典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等)。⑦严绍璗:《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国际汉学》第5期(辑刊),第8页。
严先生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和较早做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侯且岸先生接近,侯且岸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汉学和中国学相互连接,又有区别,以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为汉学,以地域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研究的为中国学。⑧《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期(辑刊),第1—12页。严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的主要不同在于:他所讲的“中国学”只是“Sinology”,而朱政惠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学包含了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两部分。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汉学大会”和“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召开,出版界大量翻译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著作,无论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还是当代中国研究都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版,以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命名的学术集刊、著作也越来越多。①张良春:《国外中国学研究》,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年;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吴兆路主编:《中国学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陈学超主编:《国际汉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王荣华、黄仁伟主编:《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程洪、马小鹤主编:《当代海外中国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韩强、梁怡主编:《海外中国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潘世伟、黄仁伟、周武编:《中国学》,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外研究中国的著作剧增,西方学术界在中国研究上也开始发生变化,欧洲传统汉学研究开始出现式微的征兆,对中国当代的研究开始日益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主力军。同时,中国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上继续沿着“汉学”和“中国学”两条学术路线在发展。如何理解日益增长的国外中国研究,这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的统一性
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再到专业汉学的长期过程,每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从传统汉学研究转变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是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研究开始的。实际上在费正清那里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研究整体,只是研究的目的和重点开始向现代倾斜。这点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汉学”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分化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面对学术的中国、文化的中国、经济的中国、政治的中国,任何一个汉学家都没有力量全面把握,任何一个学者都只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中国。这样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一定会以不同的学科成果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异常多样的学术形态。
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促使西方的中国研究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是传统汉学的语文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研究,从语言学、历史学角度展开学问。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始终是传统汉学的基本任务。而美国中国研究尽管也有着对历史中国的研究,但已开始将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主要支撑。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也开始运用到中国研究中。不同的学术方法开始运用于中国研究之中,从而在对现实中国的考察中,田野调查成为他们的基本功课。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分野也越来越大。
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的片面性认识也是造成国外中国研究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历史的中国灿烂辉煌,但已经死去,它只是作为古代文明的木乃伊被陈放在历史博物馆中。很多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如醉如痴,著作等身。但他们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持有很大的偏见。当代中国快速发展,财富不断增加,社会急剧变化,充满活力。但汉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发展,因为,历史的中国已经死去,当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完全“异类”的国家,甚至国家的合法性也不给予承认。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在国外一些中国研究中完全被割裂了。
而当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时,现实的中国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将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在社会发展上传统的血缘宗法社会在农村已经逐渐解体,金钱至上观念的流行也似乎在远离传统的儒家社会。现实的中国好像再次印证西方中国研究中的“汉学”传统和“中国学”的分离的合理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汉学形态”和“中国学形态”,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理解和学术方法问题,实际上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统一的中国?还是历史与现实断裂的两个中国?这是西方中国研究中历史中国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分野的根本原因。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呢?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讲话时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认识中国时要看到它的五个维度。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正如习主席所说:
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看到当我们面对国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时,就能以中国研究的统一性对国外的研究加以辨析,就能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对其展开我们的研究。
四、海外中国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区别性
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我们认识、辨析,并与国外研究者展开对话的出发点。但当我们具体展开学术研究时又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历史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在内容上涉及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多个学科,这样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海外的历史中国研究必然呈现出传统汉学研究的特点。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只是在近三十年才开始的,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面对四百年的西方汉学史,面对上千年的东亚汉学历史,仍有大量的学术工作亟待展开。基础文本的翻译、主要流派的研究、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等等都有待展开。对海外汉学的这些研究基本是在传统的人文学科中展开的,并积累了基本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中国学,绝大多数学者的重点是放在新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研究上。由于中国当代的发展道路独特,经济体量大,国家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国外这些研究大多数从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展开,如政治学、国际关系、法学、经济学等领域。近十余年来,由于中国快速发展,逐步进入世界的中心,一些全球性问题也开始融入到当代中国研究之中,并日益成为重要的方向。例如,对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关系的研究、对中国环境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研究、中国军事研究等等。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远远跟不上国外的发展,尚不能全面对国外中国学整体发展进行研究。因此,国内学术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必须走专业化道路,按照不同的学科,使用不同的方法展开我们的研究。因此,无论是以汉学的概念还是以中国学的概念都已经无法概括、表达国外的中国研究。由此,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展开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汉学”或“中国学”的概念上已经无法使研究深入,学科化是其必然的选择。从大方向来说,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基本在人文学科领域,对域外中国学的研究基本上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从小方向来说,无论是对汉学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学的研究都可以在更为具体的学科背景下展开。这样我们看到,海外中国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性,认识到这种区别性是我们展开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然,语言的使用和流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并非仅靠学术的理解来决定。在目前情况下,以“汉学”和“中国学”来概括代表国外整体的中国研究仍会继续下去,在一定意义上也需要有一种整体把握国外中国研究的表达,我个人认为使用“国外中国研究”为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2015年更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就是为了能够统一表达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其传统汉学研究还是以社会科学方法展开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无论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汉学,还是其后日本以“中国学”为自称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目前由我主编的《国际汉学》仍然保留刊名不变,其宗旨仍是从整体上展开对国外历史中国研究的对话与研究。但一定要看到,学科化的研究将是未来展开对国外中国研究的基本趋势。正如没有分工就不会产生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一样,没有学科化就不会有现代学术,尤其是面对像中国这个庞大的文明体,学科化是展开研究的基本路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体一样。
当然,在我们按照不同学科,以其区别性特点展开对域外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统一性特点,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本土学者要始终站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上来把握域外的中国研究。例如,从对域外的汉学研究来说,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西藏、蒙古、新疆这些研究均不在汉学研究之中,他们大都是将其放在中亚研究学科的。但在中国学者展开对他们的研究时就必须纠正这一点,将西藏历史文化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研究等纳入到汉学研究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学术领域中展开的对域外汉学界的研究,所使用的“汉学”概念和西方所使用的“汉学”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汉学概念是表示这门学问“非一族一代之学问”,是对国外整个历史中国研究的再次研究与评论。
同样,在我们展开对国外当代中国的研究时,也要从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出发,分析、鉴别、对话国外的中国研究。例如,研究中国的“一带一路”时,西方学者会很自然地用“马歇尔计划”来加以比较,其实“一带一路”是和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的。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他们完全解释不了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这些重大的新思想,实际上中国这些外交理论在当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是无法解释的,这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了解。因为,这是中国古老智慧在当代的发展,不了解历史中国是无法解释今日之中国的。
因此,中国的统一性是我们从事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而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既连接又不同的区别是我们按照不同学科展开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