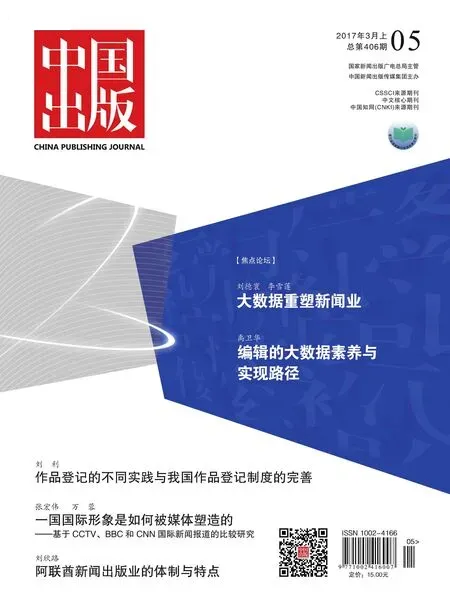出版企业国际化类型与走出去模式关联性探究*
□文│崔 波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出版企业开始融入国际文化产业系统中,正成长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体。既然企业是文化走出去的主体,那么不同的企业是不是存在着大致相同或者相似的走出去发展模式?就同一企业而言,在国际化的不同阶段,是否可以采用相同或相似的模式?本文仅以企业国际化网络理论为工具,聚焦生产核心内容的出版企业在国际化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结合文化贸易活跃的中外企业个案,透析出版企业走出去的规律。
哈格(Hägg)、乔楠森(Johanson)、哈马克威斯特(Hammarkvist)和马特森(Mattsson)等瑞典学者应用网络理论分析产业内企业的国际化行为,阐述了网络关系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标志着企业国际化网络理论的形成。乔楠森和马特森更进一步形成了企业网络国际化关系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国际化程度是两个重要的变量,将国际化的企业在国际化网络中区分为“早起步企业”“全球企业”“孤独的国际化企业”和“晚起步国际化企业”。[1]其中,“孤独的国际化企业”在企业网络国际化关系模型中处于市场国际化程度低、企业国际化程度高的位置,只能单打独斗地开拓国际市场。“全球企业”在企业网络国际化关系模型中位于市场国际化程度高、企业国际化程度高的位置。笔者通过检视文化贸易活跃的出版企业,发现企业在国际化关系模型中所处的位置与某种类型的文化贸易模式有较强的关联性。一般而言,早起步的国际化出版企业对应着代理运营模式,全球企业对应着合作经营模式,孤独的国际化出版企业对应着独立经营模式。晚起步的国际化出版企业面临被前三者划分的市场,因此在进行文化贸易中举步维艰,但是可以通过练好内功,实现跳跃式发展,即晚起步的企业对应着内向国际化模式。
一、代理运营模式
早起步企业在模型中处于“双低”状态,即任何有效的信息和知识无法从企业网络中获得,在海外业务的开展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早起步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一般借助代理商。代理商对国外市场的知识和以往的经验可以帮助早起步的企业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运行成本。如果能得到国外销售商和海外客户的认可,他们就会推进下一步的国际化经营。
我国出版产业国际化起步较晚,对海外文化市场和各国法律法规了解不够深入,因而代理运营模式更多局限于版权输出领域,即依托国外某一版权代理公司或者代理人,将某个语种的翻译权售卖出去,版权的附属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因此,国外文化企业进入我国市场所采用的代理运营模式就值得借鉴。比如受制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国外数字出版公司在中国境内不能独立开发和运营网络游戏,因此它们大多寻求中国境内的代理,由代理商负责商业销售用途的游戏点卡和相关产品的制作,而游戏的开发、更新、维护则由国外网络游戏公司负责。代理商为获得游戏在国内的运营权,需付给国外游戏开发商一定数额的代理费。由双方商定利润结算方式并签订相关书面协议,按照协议,国内代理商将合同规定周期内的游戏点卡和周边产品的销售利润按一定比例付给国外游戏开发商,或者国内代理商根据游戏运营状况与国外游戏开发商协商利益分成。在代理运营模式下又有三种分支模式。第一种是权利金模式,即不管国内游戏代理商是否成功售卖用于商业销售用途的游戏点卡或周边产品,都必须在双方约定的固定周期内支付国外游戏开发商一定比例的版税,该版税率视该周期内的产品零售价而定。第二种是利益分成模式,结算方式由游戏开发商和国内代理商事前商定,相关协议签订后,国内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须按协议商定的比例将该时段内产生利润的一部分支付给游戏开发商。利益分成模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先由国内代理商预估自身运营情况,然而再与游戏开发商协商利益分成,签订协议后将利润按照之前的约定分成付给游戏开发商。第三种是区域版权一次性付款,游戏开发商和代理商共同商定一个版税率,由代理商一次性给付游戏开发商,交易完成后所产生的利润由代理商占有,并可以在协议规定的某区域内生产某种游戏相关产品,或者自行开发后续程序,无须给游戏开发商付版税。
二、合作经营模式
在企业网络国际化关系模型中,全球企业处于“双高”状态,即在高度国际化经营环境中从事高度国际化经营。由于这些公司前期具备了国际化出版经营知识,因而有能力建立销售子公司协调海外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经营活动。融入海外市场的诸多分支机构像一个个与国际网络相连的神经,源源不断向总部提供外部资源信息,总部决策者可以依照这些信息,通过战略同盟、企业并购投机资本联合来扩大在国际网络中的影响力。
最近几年,合作经营模式应用于我国数字出版和图书出版中。早在2008年,腾讯投资800万美元,获得美国游戏公司拳头游戏(Roit Games)开发的《英雄联盟》中国大陆的代理权。随着《英雄联盟》在全球知名度提升,国内玩家数量迅速增长,2011年腾讯出价2.31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我国最近几年推行的“借船出海”的图书出版走出去也多是采用合作经营模式,即中外出版单位联合海外出版公司从事图书出版,或中方借用外方销售渠道在海外发行图书。如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加蓬恩萨姆(NTSAME)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非洲常见病防治》一书,由双方讨论选题,内容涵盖疟疾、艾滋病、伤寒、埃博拉等非洲常见病的防治,在非洲市场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鉴于我国童书选题在海外获得一定知名度,2012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共同投资成立的麦克米伦世纪公司,通过这一海外“桥头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方面熟悉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熟悉了英语国家童书市场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借助合作公司,提升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海外的影响力。目前麦克米伦世纪公司已经设计出针对不同年龄段读者的清晰产品线,生产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图书,最高单册销量已达80多万册,公司全面实现盈利。2015年接力出版社与埃及的大学出版社、埃及智慧宫文化投资(出版)公司合作创办的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看中的就是中国童书在阿拉伯国家的巨大需求,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在中国选择优秀童书,请阿拉伯专业、阿语汉学家翻译,按照阿拉伯少年儿童阅读欣赏的习惯进行策划、制作、终审,出版的童书发行至阿拉伯22个国家。接力社埃及分社生产的第一批图书亮相今年沙伽国际书展,选题大多发掘于接力社已出版的原创绘本“没想到婴儿创意图画书”系列丛书。
三、独立运营模式
孤独的国际化企业在模型中处于“一高一低”状态,即企业国际化程度很高,而其市场国际化程度很低。这类出版企业事先已经取得了有关国外出版市场的知识与经验,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国际化水平较高的网络,只能依靠自身资源和能力开拓国际市场。孤独的国际化企业虽然在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中遭遇的风险较大,但由于在国际企业网络中获得一定地位,因此较之国内同行而言往往具有更多的优势。
我国出版业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走出去格局,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物市场。[2]这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出版企业国际化水平,但是出版企业市场国际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面对这种情况,我国走出去的出版企业大多采用跨国兼并与收购等方式进行独立运营,以获得与国外出版企业平等对话权。尽管有学者提出跨国兼并与收购后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甚至巴克马(Barkema)、沃门兰(Vermeulen)、哈里波连(Haleblian)、菲克斯坦(Finkelstein)、瓦瑞(Very)和斯科韦格(Schweiger)等人还进一步从学习能力的视角分析跨国收购与兼并失败的原因。比如,哈里波连和菲克斯坦以行为学习理论分析发现收购者的收购经验与收购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呈“U”型关系;[3]瓦瑞和斯科韦格认为,“收购目标的学习”和“收购经验积累学习”是兼并收购过程中的两种学习形式,在跨国收购兼并的不同阶段,收购者会遭遇不同的难题,从而加大跨国兼并与收购的风险,这对企业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挑战。[4]但是,在海外独立运营自建出版公司是风险和利润都比较高的国际化模式,只有具有超强实力的大型出版集团才能抵御国际市场的诸多风险,从而开辟经营领域。比如,截至目前,中国出版业最大的一次跨国并购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2014年完成的,该集团斥资8500万美元收购一家美国童书生产商。通过本次并购,凤凰传媒集团在北美拥有可拓展的平台,从而实现与迪士尼、沃尔玛等国际知名大企业平等交往,该公司首个项目就是出版发行根据迪士尼同名动画片授权的图书《冰雪奇缘》,在美发行近500万册,创造了该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5]保持着国内少儿出版界的“十二连冠”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全资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将其作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个海外全资子公司,保持其品牌的独立性和运行的国际化,并助推浙江少儿出版社每年有50种畅销新书实现跨国同步出版。[6]
四、内向国际化模式
出版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向国际化”(outward-internationalization),另一种是“内向国际化”(inward-internationalization)。“外向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口生产性要素或非生产性要素而实现的企业国际化。“内向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进口生产性要素或非生产性要素而实现的企业国际化。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是文化贸易中不可或缺且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企业内向国际化过程会影响其外向国际化的发展,企业内向国际化的效果将决定其外向国际化的成功”。[7]发达国家文化贸易的历史也证明了上述论断,即文化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对本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共同消费品的文化贴现和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被认为是拥有最大国内市场的国家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8]文化产业内需市场的补充和发展,市场竞争机制的激发和完善,除了需要培育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还需要激发丰富并深刻的外部效益。例如激发本土的文化认同,进而强化文化认同;增强本地文化与创意氛围,在提升文化产业附加值的同时培育全民的创意涵养;在满足本土文化创意消费的同时产生集聚效益,增强本土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创新能力。
我国大多数出版企业国际化与国外出版巨头相比有着很大差距。盲目推动它们走外向国际化道路,参与国际出版产业的竞争,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应当善于挖掘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国外出版资源进入中国文化产业链条中,这也是一种变相走出去的方式。内向国际化模式中主要有以下三类做法。
第一类是启用具有海外出版背景的编辑。近几年,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0多家,通过启用这支海外编辑力量,或引进具有海外出版背景的人才进入出版社,有助于出版社开发具有国际市场潜力的选题。比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任命在德国生活30年的儿童文学作家朱奎为德国分社社长,朱奎与几家德国知名童书出版社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对此类人才的启用,可以促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国内出版选题与国际童书市场接轨。
第二类做法是引入外来技术。我国部分出版装备制造企业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逐步由依赖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在许多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国外相比技术差距不断缩小。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可以深化国际合作,重构分工协作体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形成良性的发展态势。除了引进吸收,还可在出版装备领域的贸易中寻求突破,寻找可以打入国际市场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文化装备品牌。同时,通过参股、收购等方式与国外出版相关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吸收国外优势资本和管理经验,通过投资交易更好地引进先进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曾经的印刷设备龙头高斯国际在2010年被上海电气全资收购的案例值得借鉴。高斯国际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筒纸胶印机生产企业和三大印刷设备制造商之一,销售额曾创下60亿元人民币的记录。但是从2009年开始,受金融危机拖累,高斯国际印刷包装机械行业在全球市场份额出现大幅下降,曾一度跌至50%,亏损严重。2010年,世界印刷包装业下滑趋势刚一止步,上海电气集团顺势完美收购高斯国际。
第三类做法是引入外来消费。以印刷包装“出口不出国”模式为例,由于中国印刷包装成本低于国外,部分出版社的印刷厂把自己优质而价廉的印制服务运用到国际合作出版项目之中,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出版更多的输出图书,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印刷厂赢得了国际订单和不错的经济效益,一举两得。此外,网上书店同样也是引来外来消费的主要平台。启动于2011年的亚马逊中国书店,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设立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的特色书店,与美国亚马逊电商图书销售最新趋势保持同步,弱化地区差异,实现全球图书资源共享,主要经营方式有:直接给美国亚马逊网站供货、自主备货营销(由亚马逊负责美国境内物流配送环节)、中国图书海外直邮,满足世界185个国家或地区读者的订购需求,保证从不同层面满足美国读者的订购需求。截至2015年6月,该书店实现发行图书26万多册。
五、结语
目前,我国参与走出去的出版企业大多是“全球企业”和“孤独的国际化企业”,因而采用的模式大多数是合作经营和独立运营模式,代理运营模式大多由版权输入的出版企业采用,但是应用得较为简单,从严格意义上讲,尚不属于“早起步国际化出版企业”。由于我国有很多出版企业尚未深入参与到文化贸易中,仍须选择内向国际化模式苦练内功,方能真正参与出版产业国际化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模式只是大致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国际化出版企业。也就是说,某一类国际化出版企业不应固定在某类模式上,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再者,出版企业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有诸多变数,迫使出版企业不能限制在某一固定模式上。当然,最终的效果如何则要靠国际文化市场的检验。
注释:
[1]Johanson J, Mattsson L 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ystems: A network approach// Hood N, Vahlne J E. (eds).Strategies in Global Competition[M]. New York: Croom Helm, 303-321
[2]刘昕. 原创童书整合资源待发力[N].国际商报,2016-09-09
[3]Haleblian J,Finkelstein S.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Acquisition Experience on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 Behavioral Learning Perspectiv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1)
[4]Very P,Schweiger D M.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as a Learning Process: Evidence from a Study of Critic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Deal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1, 36(1)
[5]张贺.把分社开到海外去[N].人民日报,2015-12-24
[6]叶薇,李月红.浙少社收购澳童书出版社[N].浙江日报,2015-08-28
[7]Welch L S, Luostarinen R K. Inward-Outward Connection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1993, 1(1)
[8]考林·霍斯金斯,斯特亚特·麦克法蒂耶,亚当·费恩.全球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导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