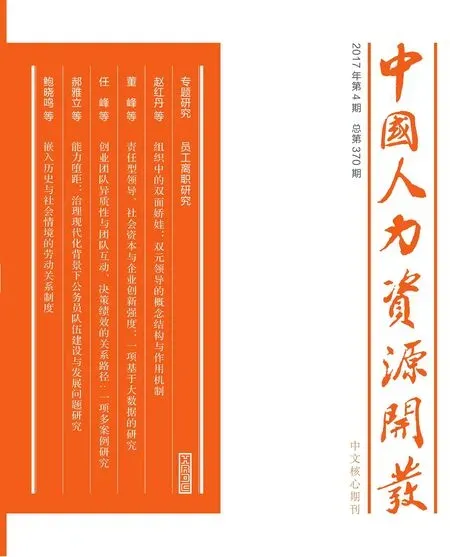嵌入历史与社会情境的劳动关系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启示
● 鲍晓鸣 孟泉
劳动关系
嵌入历史与社会情境的劳动关系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启示
● 鲍晓鸣 孟泉
本文通过对我国当下劳动关系制度研究的反思,提出过往研究缺乏将制度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与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这样导致了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僵化地分析制度,以及把制度作为理性选择结果的误判。而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为克服这一缺陷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洞见。因此,未来我国劳动关系制度研究应站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劳动关系制度 历史与社会情境 历史制度主义
一、未被参透的制度:导入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发展至今,关于制度的讨论已经成为提出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在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劳动关系理论中,无论是对宏大的产业关系系统、雇佣关系系统的描述与分析(Dunlop,1993;Kaufman,2004),还是三角平衡模型的提出(Budd,2004),制度一直扮演着“灵魂”的角色。劳动关系制度体系的构建也是这一理论学派所秉承的最终信条。正式制度(例如,从国家层面的三方协商到区域或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再到企业层面的员工参与)与非正式制度(例如,劳动关系管理中的惯例)遍布于劳动关系系统的各个层面;系统中各方主体(员工、工会、企业,以及政府)的行为无一不受到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制度既可以作为构造劳动关系系统中各方主体行为与关系的重要因素,也可以作为不断被主体之间的互动所创生、改变或消弭的结果。这一点从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1975)对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以及托马斯·A·寇肯(Thomas A. Kochan)、 哈 里·C· 卡茨(Harry C. Katz)与罗伯特·B·麦克西(Robert·B·McKersie)(1986)提出的策略选择模型中可见一斑。因此,作为劳动关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制度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
关于制度嬗变性的洞察对传统而保守的旧制度主义以及以制度经济学为依归的制度研究不断构成挑战。在旧制度主义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影响下,一种从结构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去构建劳动关系理论的范式被生产出来(吴清军,2015)。因此,劳动关系理论研究陷入了一种静态化与单一化的困境:既忽略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也局限于单一情境下的制度所呈现出来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视角下,这是回避劳资冲突对制度不断形成挑战而造成的结果(Hyman,1975)。但基于历史视角所孕育的制度变迁特征以及基于情境因素所导致的制度多样化在新制度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与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政治学理论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途径的兴起(March和Olsen,1984;何俊志,2002)。新制度主义不仅是对20世纪60至70年代流行的行为主义途径的反思,更是对制度主义传统的回归与革新。通过将制度带回到理论研究的核心,新制度主义重申了制度相对于主体的独立地位;特别地,制度构造了主体的行为甚至偏好(March和Olsen,1984)。同时,新制度主义引入了主体的偏好与行为对制度起源、延续和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看法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Lowndes,2002)。
新制度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何俊志,2005)。虽然研究者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是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相对独立地发展出新制度主义的各种“变体”。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具体而言,新制度主义的产生深受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分别建立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Hall和Taylor,1996)。就本体论而言,上述三种新制度主义的变体——特别地,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计算途径”,即假设主体的偏好是既定的,他通过计算所有可能的选项以确定最佳的行为方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相反地,社会学制度主义采用的则是“文化途径”,即假设主体的偏好是被具体的文化所构造的,并且文化为他确立了“适当的”行为方案;此时,主体的行为遵循的是满意而非效用最大化的标准(Hall和Taylor,1996)。在本体论上,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看法。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具体的制度下,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确立了各自的身份、利益;但主体仍然具有一定的理性,能了解他的偏好。同时,历史制度主义与另一新制度主义的变体——建构制度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交流:前者越来越多地将“理念”(ideas)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Hall和Taylor,1996;Hall和Taylor,1998;刘圣忠,2010)。虽然有学者质疑新制度主义的各个变体之间融合的可能性(Hay和Wincott,1998),但相较于其他变体,历史制度主义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则是不争的事实(Hall和Taylor,1996;Hall和Taylor,1998)。
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途径,历史制度主义完全可以被运用于建立劳动关系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制度主义被广泛地运用于比较劳动关系的研究,如对制度多样化的描述以及对制度多样化背后主体利益差异的分析(Wailes et al.,2003)。例如,理查德·M·洛克(Richard M. Locke)与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1995)研究了为何在面对共同的内外部挑战时,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且承受了不同的结果。从各自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出发,凯瑟琳·西伦和久米郁夫(Ikuo Kume)(1999)考察了德国与日本在工会制度上的差异。李耀太(2008)则探究了为何在政治上采取威权主义的同时,新加坡建立了类似于福利工会主义的劳动关系系统。但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学界仍然鲜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较为系统地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且探讨历史制度主义对研究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应用性。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概述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研究的特征。在随后的两个部分,我们将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对两个核心问题——制度对主体偏好与行为的影响以及制度起源、延续和变迁的动力机制——的回答。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特征,如何利用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研究途径构建本土化的劳动关系理论。
二、中国的劳动关系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我国对于劳动关系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本文虽难以穷尽所有的劳动关系制度研究,进而反思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但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近几年引发学界反复撰文讨论的几个制度议题进行分析,包括劳动合同(李小瑛、Richard Freeman,2014;唐鑛、刘兰,2016;张成刚、吴锦宇,2016)、集体谈判(程延园,2004;倪雄飞、许杏彬,2011;李丽林、张维,2013)和三方协商(刘炎白,2009;陈晓宁,2010;李丽林、袁青川,2011)。就途径而言,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研究正在经历从旧制度主义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转变。
在旧制度主义的视角下,研究者倾向于采取静态的角度,单方面地研究具体的制度对主体偏好与行为的影响。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研究者对这一法律的研究几乎都是运用旧制度主义的途径。例如,李小瑛与Richard Freeman(2014)研究了《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的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覆盖与工资拖欠,以及企业工会覆盖的影响。在将雇主纳入研究的范畴后,张成刚与吴锦宇(2016)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对工资水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唐鑛与刘兰(2016)探究了《劳动合同法》如何重塑劳资之间的共享价值。他们的论述是以这一法律重新界定了劳资之间的行为空间为出发点。因此,依然没有摆脱旧制度主义的研究途径。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超越旧制度主义的研究途径,转而采取动态的视角,研究主体如何主动地参与到制度起源、延续与变迁的过程中,即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研究途径。但相关研究几乎都是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出发点:研究者隐含地假设主体是理性的,对制度应当实现的目标有准确的认知,并且能够据此建立相应的制度。在此基础上,这一类研究的关键词是“制度设计”:研究者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既存的制度为模板,将中国相应的制度置于其中;对无法吻合的部分则视为后者的缺陷,进而设计主体所应作出的调整(程延园,2004;李丽林、袁青川,2011;李丽林、张维,2013)。例如,倪雄飞、许杏彬(2011)提出了集体谈判的理想模型。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政府应当在集体谈判当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并且要通过偏重保护原则扶持劳动者群体;同时,工会应该增强代表性、独立性与积极性。这一模型显然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系统的基础上。又如刘炎白(2009)以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三方协商为模板,将它界定为协调劳动关系双方主体之间利益对立与行为对抗的制度。在此基础上,他从法律、主体与程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有些研究者意识到完全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既存的制度为模板,进而研究中国相应的制度即便不是不可取,也至少是片面的;他们转而强调中国制度体系的特殊性。例如,田野(2014)研究了集体谈判在中国建立与运转的路径。他指出,国际政策扩散并非是在完全扩散与完全不扩散之间二选一的过程;在本质上,它是国内制度转换的过程,即既存的国内制度被用来实现和国际政策相一致的新目标。又如乔健(2010)关于三方协商的考察也是采取类似的研究途径。在将中国的三方协商界定为一种来自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政府机构与准政府机构之间功能性协调机制的基础上,他才探究了它可能的变迁路径。但这些具有历史制度主义特征的研究仍然流于表面——仅仅强调新旧制度之间的互构——对主体缺乏关注。
三、制度中的主体:偏好与行为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内涵应当被界定为“规则”(rules)。在此基础上,制度的外延从正式制度(例如,宪法、法律)扩展到了非正式制度(例如,惯例)。彼得·A·霍尔(Peter A. Hall)于1986年出版的《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一书被认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开山立派之作(蔡相廷,2010)。在这本书中,彼得·A·霍尔将制度定义为“构造社会各单位中个体之间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遵守程序、标准操作规程,以及规范”(Hall,1986:19)。在十年之后发表的论文中,彼得·A·霍尔和同事对制度做出了相同的界定:制度是“镶嵌于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例行公事、规范与习俗”(Hall和Taylor,1996:6)。进一步比较这两个定义,前者明确了制度对主体的影响,而后者则凸显了政治结构对制度的作用;两个定义互为补充,将制度置于与主体和结构互动的关系中。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身在制度中的主体受到了“过滤器”(filters)效应的影响:制度有选择地支持主体的某些利益与实现这些利益的方式(Immergut, 1998)。这一选择性来源于制度构造了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它是建立在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权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权力等价于“控制某人的权力”(power over),即一个主体影响另一个主体去做一件后者不愿意去做的事情(Dahl,1957);另一方面,权力也可以被理解为“促进某事的权力”(power to),即一个主体通过推动他的利益的实现和/或积极/消极地影响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而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Lukes,2005;Levesque and和Murray,2010)。基于具体的制度,权力在主体之间被不平等地分配。换言之,不同的主体处于不同的权力地位:制度在允许某些主体主导决策过程的同时,将另一些主体置于相对服从的地位(Hall,1986;Hall和Taylor,1996;Thelen和Steinmo, 1992)。进而,如果将权力等价于“促进某事的权力”,那么主体所处的权力地位就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一地位赋予了主体在具体制度下的集体身份。这一身份的背后是制度对主体特定利益合法性的认可/否定与对主体动员相应利益的支持/反对;另一方面,权力地位制约了主体在具体制度下的机会结构,这一结构决定着主体对不同行为有效性的看法及最终行为方案的选择(Hall和Taylor,1998;Immergut, 1998)。通过这一方式,制度不仅建立了主体对结果施加压力的方向,而且构建了这一压力的程度(Hall,1986)。换言之,制度的作用在于推动权力关系的生产,进而影响主体在行动中的主观选择,最终导致主体之间利益格局的重构。
维多利亚·C·哈特姆(Victoria C. Hattam)(1993)对美国商业工会主义理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的研究正是运用了历史制度主义途径来解释制度对主体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工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发生了转变:从将他视为与银行家、律师和土地投机商等“非生产者”相对应的“生产者”,到认识到自身作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工人”。伴随着这一身份转变而来的是针对劳动问题频发的解决方案的转变:工会转而采取政治罢工,以期实现它的目标。具体而言,工会通过向州政府与议会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做出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决定,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关系。但法院做出的判决最终撤销了州议会的决定。上述努力被挫败的结果是,工会开始认为,针对劳动问题,政治行动并非是很有前途的解决方案;应当在既存的劳动力市场关系下维护工人的利益。因此,劳工运动逐渐转向了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与集体行动(Hattam,1993)。如果说工会身份指的是工人利益的等级体系,即通过损害某些利益而促进另一些利益(Dufour和Hege,2010),那么美国工会正是在特殊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下重构了它的集体身份:将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利益置于作为公民的利益上。
如前所述,基于具体的制度,权力在主体之间被不平等地分配。实际上,主体所得到的是“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特别地,它主要指的是“基础结构资源”(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即物质与人力资源,以及通过流程、政策和方案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所进行的分配(Levesque和Murray,2010)。但主体所能拥有的权力资源绝不囿于此;主体在制度之外仍然可以掌握其他类型的资源。例如,主体所拥有的“内部团结”(internal solidarity)与“网络嵌入”(network embeddedness):前者指的是用以确保集体凝聚力和协商活力的机制;后者涉及到主体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之间保持着横向和/或纵向的联系(Levesque和Murray,2010)。更重要的是,主体的权力还决定于他能否运用自身权力资源,即涉及到“战略能力”(strategic capabilities)(Levesque和Murray,2010)。例如,主体所能够进行的“中介”(intermediating),即调解内部的利益冲突与促进外部的合作行动(Levesque和Murray,2010)。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给劳动关系制度研究的启示在于不能将制度与主体剥离:主体的权力地位在制度中得以(重新)界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主体之间利益格局的重构。但不能忽略的是,制度与主体之间必然呈现互构的关系(Giddens,1984):主体并不完全被制度所构造;相反地,他会在制度塑造自身权力地位以致集体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四、制度的起源、延续与变迁
如前所述,相较于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动态的视角看待制度。这一点在历史制度主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除了关注制度中主体的偏好与行为,还对制度从起源到延续再到变迁的过程进行了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在具体的制度下,主体的集体身份与利益受到影响;因此,那些利益受损的主体必然会和获益的主体产生冲突。基于冲突论的假设,历史制度主义开始挖掘引发制度起源、延续与变迁的动力机制。特别地,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事件的“时机”(timing)与“顺序”(sequencing)格外强调(Orren和Skowronek,1994;Pierson,2000;Thelen,2000)。
对制度起源的研究源于研究者对历史事件所引发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关注①(Olson,1965)。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是起源于制度真空中:任何制度的起源都是在一个已经充满了制度的情境中(何俊志,2003)。因此,对新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行动问题而言,相应的解决方案受到既存制度的制约。换言之,对研究制度的起源而言,在具体的时点之前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的顺序——至关重要。表面上,既存的制度涉及到对旧的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如前所述,既存的制度以规则建立了主体之间现存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地,主体所处的权力地位不仅构建了他的集体身份,更塑造了自身行为方案。因此,在面对新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行动问题时,主体对自己在其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采取怎样的行动都心有定见。结果是,主体对新的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遵循旧的方案。对既存的制度而言,如果主体遵从旧的方案解决了新的集体行动问题,那么无疑是对它进行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因此,这一制度得到了“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结果是,在未来面对集体行动问题时,主体仍然倾向于依靠既存的制度;主体参与到对他的权力地位的“再生产”(reproduction)过程中。这无疑阻碍了替代性权力关系与相应制度的产生,进而形成了这一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Thelen,1999)。
从各自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出发,凯瑟琳·西伦和久米郁夫(1999)对德国与日本在工会制度上差异的研究正是运用历史制度主义途径来解释新制度的起源和既存制度的延续。以德国为例。在十九世纪末,劳动问题频发。工会领导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工会制度,进而凝聚工人的力量,最终推动集体行动。摆在他们面前的一种选择是构建行业工会,即将属于某一行业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在这一工会制度下,工会会员按照统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为了防止有工会会员降价出售,工会领导通过对学徒制进行规制(例如,设置学徒人数的限制、提高技能认证的难度),进而降低从学徒成为帮工再晋升为匠师的人数,最终减少会员之间的竞争。但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上,当时的德国已经存在具有准公权力的行会。具体而言,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于1897年颁布了《手工业者保护法》(Handwerkerschutzgesetz)。在这一法案下,手工业行会垄断了规制学徒制的权力。因此,行业工会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结果是,工会领导转而选择建立产业工会,即将在某一产业中工作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不论他们属于何种行业。同时,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也一直延续到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Thelen和Kume,1999)。
上述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在纳粹党执政时期被改革:政府建立了同时覆盖手工业和工业的制度;特别地,技能认证不再被手工业行会所垄断,而是由工贸商会负责技术工人的这一认证(Thelen和Kume,1999)。此时,既存的制度出现了变化。如前所述,制度的延续是建立在主体的权力地位——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再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制度的变迁必然是对现存权力关系的打破与重构(Thelen,1999)。在这一过程中,“理念”(ideas)发挥着根本作用。理念可以被定义为“集体行动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Steinmo,2008:131)。理念的作用在于重构主体的集体身份与行为方案:在面对新的历史事件和集体行动问题时,仍然具备一定理性的主体——特别地,处于服从地位的主体——认识到,与之前相比,他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新的集体身份与行为方案所代表的权力关系不容于既存的制度,即理念和制度之间产生“摩擦”(friction)。这一摩擦构成了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Lieberman,2002)。
仍然以Thelen与Kume(1999)的研究为例。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当时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德国机械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大型的机械制造企业开始自主提供职业培训。但它们没有权力对技术工人进行技能认证:这一资格被手工业行会所垄断。因此,工人在接受培训后很可能被其他企业挖走:他们不需要在企业中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技能认证。同时,大型的机械制造企业也无法吸引到最有雄心的学徒:技能认证代表着更高的地位与权利(例如,通过得到匠师的资格,从而招收学徒)。面对这一问题,它们意识到,工贸商会应当被赋予与手工业行会同等的权力,从而能够对工业领域的职业培训进行技能认证。但这一方案自一开始就遭到手工业行会的反对:放弃对技能认证的垄断权力将使得手工业部门在与工业部门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后者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培训(Thelen和Kume,1999)。
总体而言,主体是将理念作为“蓝图”,进而推动制度的变迁(刘圣忠,2010)。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制度变迁的模式具有多样性(黄宗昊,2010)。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主体将理念固化为制度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对情境的分析应当从两个维度入手:其一,政治背景,即偏好既存制度的主体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他能够捍卫现状;其二,制度特征,即既存制度是否有相当的模糊地带供主体进行诠释与执行(Mahoney和Thelen,2010)。在此基础上,制度变迁可以被划分为四种模式。首先,当否决的力量较强时,主体无法如实地表达他的理念。如果诠释与执行的空间又较窄,那么主体也不能直接调整既存的制度。此时,主体以“改良”(refinement)或“修正”(corrective)的名义,将新的制度附加在既存制度的边缘上。这一制度变迁模式被称为“层叠”(layering)。其次,当否决的力量较强,但诠释与执行的空间较宽时,虽然主体仍然无法如实地表达他的理念,但不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此时,主体表面上遵循既存的制度,实际上却不履行他的责任。在阳奉阴违下,既存制度久而久之地走向衰亡。这一制度变迁模式被称为“漂移”(drift)。再次,当否决的力量较弱时,主体可以如实地表达他的理念。如果诠释与执行的空间较窄,那么此时,主体将重新发现和激活已经存在但被既存制度压制的制度或引进并且培育外来的制度。这一制度变迁模式被称为“取代”(displacement)。最后,当否决的力量较弱,而且诠释与执行的空间较宽时,主体不再遵循既存的制度,而是重新界定它所代表的规则以实现新的目标。既存的制度经历了旧瓶装新酒的过程,最终发生变迁。这一制度变迁模式被称为“转换”(conversion)(Mahoney和Thelen,2010)。尽管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将它们分类,但在现实中,制度变迁的路径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呈现更为复杂的演进逻辑。
仍然以Thelen与Kume(1999)的研究为例。纳粹党上台后对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进行了改革。德国政府不断为发动对外战争做准备。为了灵活地分配劳动力,职业技能必须实现标准化。因此,德国政府试图在工业部门建立一个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负责部门内公司的技能培训和认证。具体而言,它将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转化成帝国职业培训学院,并且要求所有企业遵循后者制定的培训准则与方法。结果是,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被排挤出工业部门。实际上,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早在1908年时就已经在大型的机械制造企业的主导下得以建立。它成立的目的就是构建由工贸商会主导的工业部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总体而言,为了实现制度的变迁,德国政府运用了“取代”的模式(Thelen和Kume,1999)。
在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经历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其他的制度变迁模式;特别地,“层叠”的模式得到运用。具体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完全参与到对工厂内部技能培训的管理与监督中。实际上,早在1919年,工会就提出建立更为民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否则它将把匠师与学徒之间的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非教育关系,进而纳入集体谈判的范围。这将导致手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企业只向学徒支付很少的工资甚至不支付工资(Thelen和Kume,1999)。如前所述,正是在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下,产业工会的工会制度得以建立。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会领导逐渐地利用这一制度去侵蚀既有的制度,进而渐渐地实现他的目标。从短期看,产业工会的起源似乎给予了手工业行会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正反馈,进而促进了后者的延续。但在长期上,前者实际上是通过“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打破了后者的路径依赖,进而推动了它的变迁(Pierson,2000;Thelen,2000)。
五、历史制度主义对中国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本文从制度对主体偏好与行为的影响以及制度起源、延续和变迁的动力机制两个方面阐述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途径的主要内容。这对构建本土化的劳动关系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动态性与多元化的特征,更加注重分析制度和主体之间互构的关系。这不仅提升了研究者对制度的认知,也启示了我们在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研究中需要有新的研究问题被提出;或者说,至少应该有一些运用历史制度主义途径来分析的关键问题。
1.劳动关系制度起源、延续与变迁的总体逻辑是什么?
尽管还没有研究对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研究的现状进行客观的评价,但鲜有结合多学科的视角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在关于劳动法的研究中,对法律执行过程中主体的认知以及它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仅仅存在有限数量的研究(Gallagher等,2015;Hui,2016)。中国对劳动法功能的争论也缺乏充足的实证数据的支持(董保华,2016)。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制度所处的情境对它产生的影响。例如,一些关于集体谈判的研究对它不同的变化路径进行了比较,并且分析了各自的机制(闻效仪,2011;雷晓天,2016)。然而,在历史的视角下,如何将某一制度从起源到延续再到变迁的总体逻辑挖掘出来,仍然是未解之题。我们进一步要提出的问题是,劳动关系制度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内部是否以及如何实现再生产?
2.主体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劳动关系制度的延续?
在劳动关系制度的研究中,路径依赖一直作为制度功能或制度本身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如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李昌徽(Chang-Hee Lee)与李琪(2004)对集体谈判形式化问题的分析。但这一判断的误区在于路径依赖不应作为解释变量;它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释的问题。在制度与主体互构的过程中,哪些主体对制度持接受、排斥甚至反对的态度,会造成路径依赖的具体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发生变化。因此,解释为何会出现路径依赖需要分析制度涉及的主体对它产生的作用。例如,为解释集体谈判形式化,吴清军(2012)挖掘了党政联合工会与资方讨价还价的指标管理机制,而这才是造成集体谈判形式化不断延续的动力机制。
3.不断变化的劳动关系制度之间在功能上是否以及为什么会存在互补或冲突?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劳动关系制度体系的研究者曾经提出,劳动关系制度之间互补或冲突的关系是一个尚未深入分析的问题(Muller-Jentsch和Weitbrecht, 2003)。中国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非常缺乏。历史制度主义对主体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讨论,恰好就为追问中国不同劳动关系制度之间互补或冲突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途径。
总而言之,基于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特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理论不仅需要关注制度变迁本身,更应当研究主体——特别地,处于服从地位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是怎样发掘与运用他的权力资源来取得优势,进而实现自身理念。
注 释
①集体行动问题是指面对具体的问题,群体中的个人有A和B两种行动选择。个人基于个体理性做出A选择。但是和B选择相比,对于每个人而言,此时的结果都比较差(Olson,1965)。
1.Budd, J. W. Employment with a Human Face: Balancing Efficiency, Equity, and Voi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2.Clarke, S., Lee, C. & Li, Q.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42(2): 235-254.
3.Dahl, R. A.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1957,2(3): 201–215.
4.Dufour, C. & Hege, A. The legitimacy of collective actors and trade union renewal.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10,16(3): 351-367.
5.Dunlop, J. T.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6.Gallagher, M., Giles, J., Park, A. & Wang, M. China’s 2008 labor contract law: Implem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workers. Human Relations, 2015, 68(2), 197-235.
7.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8.Hall, P. A.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Hall, P. A. & Taylor, R. C.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5): 936-957.
10.Hall, P. A. & Taylor, R. C. The potential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 response to Hay and Wincott. Political studies, 1998, 46(5): 958-962.
11.Hattam, V. C. (1993).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 The Origins of Business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Hay, C. & Wincott, D.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8, 46(5):951-957.
13.Hui, E. S. The labour law system, capitalist hegemony and class polit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6, 226: 431-455.
14.Hyman, R. 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75.
15.Immergut, E. M. (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8, 26(1): 5-34.
16.Kaufman, B. E.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Events, Ideas and the IIR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4.
17.Kochan, T. A., Katz, H. C. & McKersie, R. B.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Levesque, C. & Murray, G. Understanding union power: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for renewing union capacity.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10, 16(3): 333-350.
19.Lieberman, R. C.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2, 96(4): 697-712.
20.Locke, R. M. & Thelen, K. Apples and oranges revisited: Contextualizedcomparisons a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bor politics. Politics & Society, 1995, 23(3): 337-367.
21.Lowndes, V.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in D. Marsh & G. Stoc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60-79.
22.Lukes, S.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ition). 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3.Mahoney, J. & Thelen, K.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 Mahoney & K.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1-37.
24.March, J. G. & Olsen, J.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 78(03): 734-749.
25.Muller-Jentsch, W. & Weitbrecht, H.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German Industrial Relations. Mering: Rainer Hampp Verlag, 2003.
26.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7.Orren, K. & Skowronek, S. Beyond the iconography of order: Note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L. D. Dodd & C. Jillson (eds.),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tics: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311-330.
28.Pierson, P. (2000).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000,14(1):72-92.
29.Sikkink, K. Ideas and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alism in Brazil and Argent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Steinmo,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 D. Porta & M. Keating (eds.),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Plurali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18-138.
31.Thelen, K.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1): 369-404.
32.Thelen, K. Timing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000,14(1): 101-108.
33.Thelen, K. & Kume, I. The rise of nonmarket training regimes: Germany and Japan compared.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999, 25(1), 33-64.
34.Thelen, K. & Steinmo,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 Steinmo, K. Thelen & F.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2.
35.Wailes, N., Ramia, G. & Lansbury, L. D.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3, 41(4): 617-637.
36.蔡相廷:《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与研究取向——政治学研究途径的探讨》,载《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2001年第41卷第2期,第39-76页。
37.陈晓宁:《论三方机制下工会的角色定位》,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70-74页。
38.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36-142页。
39.董宝华:《〈劳动合同法〉的十大失衡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第10-17页。
40.何俊志:《结构, 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25-33页。
41.何俊志:《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载《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03年版,第438-451页。
42.何俊志:《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交流基础与对话空间》,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第45-51页。
43.黄宗昊:《历史制度论的方法立场与理论建构》,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5-176页。
44.雷晓天:《国家、资本与劳工: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形塑力量——基于文献的思考与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21期,第102-108页。
45.李丽林、袁青川:《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8-26页。
46.李丽林、张维:《工业化国家的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度的多样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东岳论丛》,2013年第3期,第24-30页。
47.李小瑛、Richard Freeman:《新〈劳动合同法〉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载《劳动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17-41页。
48.李耀太:《新加坡劳、资、政三边关系的检视: 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载《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2008年第2期,第93-107页。
49.刘圣忠:《理念与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研究》,载《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1期,第1-8页。
50.刘炎白:《论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之构建》,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1期,第250-251页。
51.倪雄飞、许杏彬:《我国集体谈判机制的模型建构》,载《中国劳动》,2010年第8期,第26-28页。
52.乔健:《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走向三方协商与社会对话的第一步》,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31-38页。
54.田野:《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劳资集体谈判的中国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118-138页。
55.闻效仪:《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谈判为例》,载《社会》,2011年第1期, 第112-130页。
56.吴清军:《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66-89页。
57.吴清军:《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制度研究及转向——欧美劳动关系理论研究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第196-221页。
58.张成刚、吴锦宇:《〈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市场影响的实证考察》,载《学海》,2016年第3期,第160-166页。
■ 责编/ 张新新 Tel: 010-88383907 Email: hrdxin@126.com
Embedding the Labour Relations Institution withi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Bao Xiaoming and Meng Quan
(Schoo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Montre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bou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n this paper, through re-thinking the current studies on labor relations institutions, we argue that previous researches in China take more static perspective in analysing labour relations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rationale person. It is because these researches did not embed institutions with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However, theories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ffers a good insigh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erefore, the new research questions should be raised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Labour Relations Institutions;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鲍晓鸣,蒙特利尔大学产业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电子邮箱:ikexiaoming1990@ gmail.com。
孟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集体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机制的系统化建构研究”(14ZDA006)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